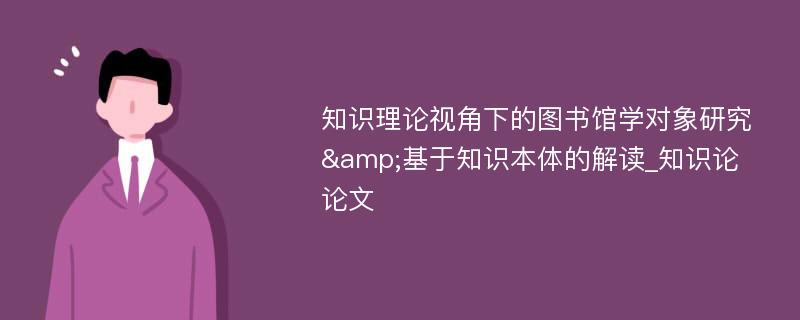
知识论视野中的图书馆学对象研究——基于知识本体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论文,图书馆学论文,本体论文,视野论文,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2003年,王子舟在《图书馆学基础教程》一书中提出“知识集合”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学应根据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及其关系建立自己的研究客体体系,并宣称:“我试图站在知识论者的立场,希望图书馆学研究能在知识领域里前行,并使图书馆学成为对社会人群有益的一门科学。”①而另一批学者,如彭修义、刘洪波、蒋永福、王知津、柯平、张晓林、邱均平、李后卿、盛小平、马恒通等,分别从知识组织、知识管理、知识服务、知识资源、知识传播等角度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核心是研究对象)进行了新的阐释,形成了以“知识”为核心概念的新的理论体系。2009年,吴慰慈、张久珍在《新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六十年》一文中认为,“知识论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②。
2 图书情报学主要的知识论观点
知识论来自于哲学领域,是探讨知识本质、起源和范围的一个哲学分支。“但随着学者们对‘知识’问题的研究与应用,知识论的发展已从一元辩论走向多元理解,因而它广泛涉及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传播学、管理学、信息(智能)科学以及图书情报学等不同学科领域。”③
图书情报学的知识论观点源自知识社会学理论和知识基础理论。“知识社会学”是德国图书馆学家卡尔施泰特(Karstedt P.)提出的理论观点。他从知识的社会性理论中引入了一个新概念,即“客观精神”,图书是客观精神的载体,图书馆是客观精神得以传递的场所。有了图书馆这样的社会机构,人类文化的创造和继承才有了可能。“知识社会学”以“客观精神”为研究对象,而知识社会学正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把知识的社会性引入图书馆学并作为其理论基础,还有谢拉(Shera J.H.)的“社会认识论”。谢拉认为,应把知识作为整个社会组织中独立的要素,尤其是作为以书面交流为基础的认识体系进行考察。图书馆工作本质上是人类知识的管理工作,知识及其交流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组成部分。
知识基础理论源自哲学家波普尔(Popper K.R)的“世界3”理论。20世纪60、70年代,英国图书情报学家布鲁克斯(Brookes B.C.)将其移植到图书情报学研究。波普尔的“世界3”是指独立于物理实体(世界1)、精神世界(世界2)之外的客观存在,即精神产品的世界。这与卡尔施泰特的“客观精神”,以及今天我们所说的客观知识有密切的关联。这个理论在1982年被青年学者刘迅引进到我国图书情报学界,为我国后来的知识论研究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20世纪末兴起的知识经济浪潮加速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化研究,与知识相关的命题成为社会科学关心的主题。图书馆学很快接受了“知识”这一概念,并将其与自身原有的知识结构进行对接,产生了众多的知识流派,成为21世纪图书馆学研究的一大特色。这些知识流派可以粗略地分为三类:知识交流学派、知识组织学派和综合性的知识学派(如知识管理说、知识服务说、知识资源说、知识集合说等)。
知识交流学派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谢拉的“社会认识论”。他在《图书馆学教育基础》一文中指出:“交流是社会结构的胶粘剂”,而图书馆正是实现知识的书面交流的社会机关。20世纪80年代,受“交流说”和“知识说”的影响,知识交流说在我国图书情报学界流行开来,其标志为宓浩的《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一文。知识交流自称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实则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种新的解释。“知识交流说”理论层次较高,“它能涵盖图书、情报、档案等多门学科,但最后如何返回图书馆及图书馆学中,用于揭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机理,却显得较为乏力”④。马恒通提出的“知识传播论”可以看作“知识交流说”的一个变种,因为传播也是一种交流。
知识组织学派在图书情报学领域也有较长的历史,以分类、编目为主的文献组织构成了图书馆学知识组织的最初的理论形态。20世纪80年代末知识组织的理论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如1989~1990年,马费成、胡昌平、刘植惠、丰成君等人撰文探讨了知识组织的相关问题,并认为知识组织是图书情报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刘洪波在《知识组织论:关于图书馆内部活动的一种说明》一文中认为,知识交流对图书馆活动的外部关系给予了有力说明,但未能揭示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本质和机理,图书馆内部活动的实质是知识组织。另外,王知津、蒋永福等人也从“知识组织”的角度分析了图书馆工作的本质,提出了应该从知识组织的视角来理解图书馆学。
综合性的知识学派主要有知识资源论、知识服务论、知识管理论、公共知识管理论、知识存取论、知识集合论等等(当然这种分法只是一个大致的分法)。综合性的知识学派,试图在知识的平台上,实现交流说和组织说的融合。
3 知识论视野中的图书馆学对象研究——基于知识本体的解读
3.1 知识论与知识本体
康德被认为是知识论的鼻祖,他指出,一切经验和知识都是由感性因素和理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感性因素就是我们感官提供的后天感觉印象,它是构成一切经验和知识的内容或质料,理智因素是我们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形式,它为经验和知识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人的认识活动就是用先天的认识能力(“形式”)去整理后天的感觉材料,形成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科学知识。为此,康德在改造亚里士多德范畴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类12个范畴,把它作为组织“感性”知识的工具⑤。康德的知识论哲学虽然着眼于人的认知行为(认识论),但其目的和意义在于对本体的解释(即“自在之物”与“现象”的关系)。晚近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兴起以来(主要在20世纪20、30年代以来),传统的基于个人主义的认识论哲学受到置疑和批判,个人、社会和自然统一和谐的宇宙观(本体观)备受推崇。而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横断学科的迅速发展使知识的交叉融合进一步加速,旧的本体观(指从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最终成型的具有鲜明的欧洲主流文化特征的哲学形态,其体系不仅博大精深而且有浓重的超验主义和先验论色彩)向知识本体(或称为现代本体观,是指通过改造旧本体使其加入人文、结构化和实证化的素材成为新的哲学本体观)的转换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⑥。
20世纪60、70年代,计算机科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模拟人的思维和认知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人工智能成为信息科学的最前沿领域。由于人工智能与思维和认知有密切的联系,知识本体的概念很快被引入到这一领域。1991年,Neches等人给出了知识本体的新定义,即“组成主题领域的词汇表的基本术语及其关系,以及结合这些术语和关系来定义词汇表外延的规则”。代表性的观点还有1999年B.chandrasekaran等人的定义:“Ontology属于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内容理论,它研究特定领域知识的对象分类、对象属性和对象间的关系,它为领域知识的描述提供术语。”2001年,斯坦福大学的Natalya.F.Noy和Deborah.L.McGuinness认为:“一个本体其实就是一套关于某领域概念的规范而清晰的描述,它包含类(Class),每个概念的属性(Properties)描述及其特征和相关限制条件。”除了人工智能,知识工程也是知识本体得以广泛应用的一个领域,被国内引用较多的定义有:1993年Gruber的本体定义,即“本体是概念化的明确的规范说明”;1997年,W.N.Borst的“本体是共享的概念模型的形式化的规范说明”;1997年,Fensel的“本体是对一个特定领域中重要概念的共享的形式化的描述”等等。此外,图书情报学者也从知识组织的角度给本体作了新的解释⑦。
人工智能、知识工程、图书情报等领域关于本体的研究验证所谓知识本体(客观现实的抽象本质)是与人的认知活动密切相关。笔者认为人工智能、知识工程、图书情报等领域关于本体的定义并非仅提供了一个领域知识的描述框架,而是通过这个知识描述框架(实际上是一个概念集合,或称知识集合)达到对“自在之物”(本体)的把握,实现存在物(客观对象)的某种功能。本体(客观现实的抽象本质)是通过知识集合或概念集合来表示的,简单地说,知识本体就是知识按照一定的关系有序组织起来的知识集合。康德知识论的缺陷在于他把人的认识(知识和经验)与本体(“自在之物”)对立起来,即人只能认识现象,不能把握本体。而知识本体(指深受现代科学思想影响的现代本体观)认为,人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如某领域、某层次、某维度等)实现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把握。因此,知识本体可以这样定义,即基于不同领域、不同维度对客观世界的概念化、形式化描述。
3.2 图书馆学对象研究——基于知识本体的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成了众多的图书馆学流派(研究对象之说)。这些新的理论观点对拓展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推动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的整体性。不仅客观世界是一个整体,图书馆所面对的人类知识也是一个整体。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不断分化在提高分支领域研究效率的同时,也弱化了学科整体的研究效率⑧。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知识的融合提供了契机,而知识本体(现代本体观)重新被哲学等社会科学所关注就是这一趋势的反映。事实上,我国图书馆学界中已经有很多学者通过探讨范式及其转换这一命题,向综合性的知识本体这一思想靠近,并且希望借其解决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图书馆本质问题或者说对象研究问题)。如蒋永福、王明霞的《21世纪图书馆学研究方向与重点》⑨一文中指出知识化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内涵深化方向,强调了范式的形成对图书馆学发展的意义。作者首先介绍了美国学者对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分类,如米克沙的机构范式和信息运动范式(信息运动范式又分为系统导向范式、知识非常状态范式和意义建构论范式,后两者又合称认知观范式)。在此基础上,蒋永福等评价了机构范式、系统范式和认知观范式的优点和不足。最后,作者指出认知观范式的个体主义局限性促使人们寻找基于集体主义或社会维度的新范式,而领域分析范式和阐释学范式的出现就是这些努力的结果。蒋永福等人的观点虽未提及知识本体或本体等概念,但其阐述的内容已经涉及“知识化”、“领域分析”等这些知识论本体观的核心思想。而张欣毅的几篇文章《超文本范式——关于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哲学思考》⑩、《触摸那只无形的巨手——基于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认识论(上)》(11)和《回眸一个科学本体论的进化史:基于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本体论观照》(12)对知识本体的论述更为透彻。作者以科学本体的演化为线索,阐述了图书馆学研究范式与本体研究的同步进化的关系,评述了机构范式、广义文献范式、客观知识范式、文献信息范式、信息资源范式、认知范式和文本范式等主流范式,并主张以文本范式、信息范式和认知范式三大思想来源构建业界的基本本体论,即“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范式或者说“超文本”范式。
从2004年起,青年学者熊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图书馆广义本体论导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的重建》、《论图书馆学范式的形成与转换》和《追问图书馆的本质——近30年来国内图书馆本质问题研究代表性观点述评》等,提出用广义本体整合和统摄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本质)。作者认为图书馆学近200年的历史主要是“客体——中介”综合范式形成与转换的历史,目前图书馆学范式全面转换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可能形成的新范式是“本体——客体——中介——主体”综合范式。为此,作者在系统梳理现有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以本体论方法为主导的、以客体论方法、中介论方法和主体论方法为从属的“一元主导,多元一体,从属有序”的方法模型。这个方法论模型是建立在“对图书馆的广义本体存在及运动的审查”基础上的,“它既适用于图书馆学的宏观研究领域,也适合于微观研究领域;既适用于图书馆学的动态研究领域,也适用于静态研究领域”。熊伟还认为这个“图书馆广义本体存在及运动”的总体层次理论模型具有关联性、有序性和延展性,是解决图书馆学对象(图书馆本质)研究的方法论体系(13)(14)(15)。
笔者认为,除了范式角度,知识论也是解释本体思维的一个有力工具。众所周知,图书馆学的宗旨是为人们获取知识提供方法和工具,即提供知识的知识,为此就必须对知识(是什么)及其来源(是如何产生的)进行深入的研究。图书馆学借助于哲学、社会学等理论成果,通过客观知识(或称世界3、客观精神、载体知识)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把自己的知识体系建立在更为广阔的人类知识体系之上,创立了知识社会学(卡尔施泰特)、社会认识论(谢拉)和知识基础论(布鲁克斯)等学说,从而实现了图书馆学在知识层面上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与对话。“晚近学者Steve Fuller将社会认识论作为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与谢拉有关”(16)。但随着人们对知识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仅靠客观知识不足以解释知识及其来源,也无法正确理解知识的组成,于是,主观知识(又称隐性知识、会意知识等)、客观知识以及二者的关联与转化就成为图书情报学新的理论增长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知识观就是这一思潮的反映。无论是社会认识论,还是建构主义知识观都强调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在人的知识活动中的重要性,都试图把对客观世界(本体)的解释建立在“主体——中介(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客体”的知识框架内。这样,就使孤立的(自在之物)、抽象的本体观转换成一种可解释、可表达的知识论本体观(知识本体)。
此外,知识论者还从知识的来源入手,认为知识的本质(知识本体)只不过是人对认识客体的一种映射,并非是绝对的客观存在。由于客观世界(认识的对象或客体)的运动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作为映射的知识只有在一定的视角下才具有现实的意义(即真实地反映对象的某些特征)。康德基于这个观点,把众多的映射知识(感性知识)划分为不同的范畴和领域,从而使知识之间建立起一定的联系,成为一个有序的知识集合。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本质上是在探讨图书馆的本质,即所谓本体层面的问题,而具有哲学属性的知识本体无疑能给我们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基于此,笔者认为:第一,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多元化存在是合理的,是基于不同视角下对图书馆本质的解读。这种现象并非图书馆学所独有,其他学科一样存在,没有必要大加鞭挞,口诛笔伐;第二,图书馆学对象研究的重心在于寻找知识的关联性和互补性。作为客体存在的图书馆是一个发展中的有机体,而作为映射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自然也处在不断地完善和演变之中。从知识本体的视角来看,每种对象之说都可以看做是反映图书馆知识运动特征的知识因素(或称知识因子、子本体、下位类类目等),只有把各种对象之说整合成一个系统的有序的知识集合,才能完整地反映图书馆本质的全貌;第三,基于知识本体的解读,我们认为综合性的知识学派应该成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主流,而知识集合说与知识本体所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它是最佳的图书馆学对象(图书馆本质)的表述形式。
注释:
①④⑧王子舟.图书馆学基础教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3
②吴慰慈,张九珍.新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六十年.图书馆杂志,2009(5):5-13,17
③李后卿,鲁沙沙,支晓娟.图书情报学视野中知识论流派研究述评.情报资料工作,2009(2):18-20
⑤葛圆圆.当代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的知识论视角探析.图书馆杂志,2009(11):2-6
⑥http://baike.baidu.com/view/29987.htm? fr=ala0_1_1
⑦余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⑨蒋永福,王明霞.21世纪图书馆学研究方向与重点.图书馆,2003(1):26-31
⑩张欣毅.超文本范式——关于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哲学思考.中国图书馆学报,2003(3):14-19
(11)张欣毅.触摸那只无形的巨手——基于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认识论(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3(1):7-11
(12)张欣毅.回眸一个科学本体论的进化史:基于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本体论观照.图书馆,2005(1):34-38,45
(13)熊伟.图书馆广义本体论导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的重建.图书与情报,2004(5):4-8
(14)熊伟.论图书馆学范式的形成与转换.图书情报工作,2004(5):43-46,57
(15)熊伟.追问图书馆的本质——近30年来国内图书馆本质问题研究代表性观点述评.图书馆杂志,2008(7):5-9
(16)李爱民.图书馆学如何与现代性问题相关.图书馆,2009(2):5-7
标签:知识论论文; 图书馆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图书馆学研究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体感觉论文; 认识论论文; 范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