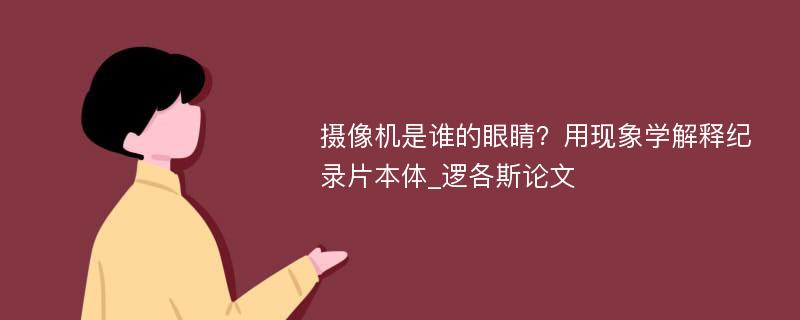
镜头是谁的眼睛?——试用现象学阐释纪录片本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本体论文,谁的论文,纪录片论文,镜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02 [文献标识码]A
一、镜头①与眼睛
根据通常的观点,影视属视觉艺术范畴②。人们也习惯于把影视的构造单位“镜头”比作眼睛,因为镜头及其组织方式给人以视觉的体验。根据麦克卢汉的观点,影视镜头可以看做人的眼睛的延伸。然而镜头与眼睛在呈现方式上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镜头因其强大的构造能力不仅能够跨越和重组时空,还能超越单个人的视野所见,因而带来了超越肉眼呈现的自由。它不仅能记录现实,还能表现心理的真实,甚至可以虚构。电影先驱维尔托夫正是看到了镜头的强大的表达能力,把镜头称为“电影眼睛”,即比肉眼更强大的“眼睛”。
但是上述理论还是非常粗疏和浅陋的。麦克卢汉的观点非常大胆,却更像一种直观判断。我们不能忘记,镜头的呈现作为一种构造性的呈现,在有所呈现的同时也可能造成遮蔽。那么就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危险,即在影视大行其道而扩展我们视野的同时,因为遮蔽而造成的失实就会混淆大众的视听。而维尔托夫所推崇的镜头表达的自由,如果没有找到这个自由借以依托和发生的根据,要么就让人觉得是任意为之,要么让人觉得空洞无谓,甚至这种未经推敲的自由本身就是相当可疑的。
我们必须对镜头作为意义产出和传播的机制的本质结构与过程取得新的洞察,才能知道镜头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使眼睛得到了延伸,才能看到镜头构造和呈现意义的根源和界限,从而为纪录活动的自由赢得保障。
纪录活动看起来并不复杂。我们可以从形式上做出如下初步描述:纪录片是作者通过镜头来看,用镜头构造这个看的如何,然后将它公布到观众眼前,让后者看镜头所看。
海德格尔曾在《逻各斯》一文中阐释过“听”③。海氏实际上把“听”阐释为人通过归属于逻各斯的运作(即存在之解蔽④)而从事的创建世界的活动的建构环节。因此他说的“听”超出了耳朵的听(听觉),而指涉人与事物交往的所有方式,当然也包括了眼睛的看。在《逻各斯》文中,海氏首先从词源学探询希腊人说的“逻各斯”从何种经验而来。经过一番考据,海氏认为逻各斯的源始意义是“置放”⑤,基于此,海氏又将听(看)阐释为对逻各斯的“置放”(即“道说”⑥)的倾听⑦。因为听以倾听逻各斯(即存在的道说)的方式归属于逻各斯,因此听本身也是一种逻各斯⑧。我们也可说听是一种属于人的解蔽的方式⑨。
海氏对逻各斯、置放和听的阐释比较复杂,笔者在此将他的理论转换和改造成一种视域理论,后者更加容易理解。
二、视域理论
(1)被保存的无蔽可以被规定为“视域”⑩。
存在本身的运作方式(即逻各斯)是从遮蔽中涌现出无蔽(11)。这种运作乃是从遮蔽之黑暗当中产生自发闪耀的光亮,此光亮照亮一块区域,此区域就是无蔽,无蔽乃自我照亮的澄明。人居于存在的解蔽运作当中,承受了无蔽的澄明,这些澄明被保存下来,使人有了视域。视域使得人的活动不是被动承受澄明,而是能从自身(即属于人的视域)中发出光亮并以此去照耀那个自身澄明的无蔽,从而能够使事物具有属于人的意义。
(2)视域照亮生存的意义场,并帮助组建世界。
人的被视域照亮的意义活动构成意义场,这个意义场的展开乃是与因被照亮而向人呈现的事物交往。视域保存着存在者在与人的交往当中显现的意义的总体,以此方式,视域帮助我们组建起自己的世界(12)。
(3)本真的听(13)(包含看)是身体(14)的存在方式。
本真的听是人置身入于澄明的无蔽当中,去承受事物的自身闪耀和涌现(即无蔽的道说),本真的听是身体的本真存在方式。身体意义的产生不依据人的明确的需要和目的,而保持在一种混沌状态。身体居留于世界而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事物的意义是在整体当中呈现的,是非明确和不固定的。身体的意义被保存下来后也依然保持整体性、非明确性、游离性和开放性。身体机制使人在与事物交往的时候采取开放和非确定性的方式,从而将人保留在与事物的多义联系当中,也即一种意义游戏的状态。
(4)非本真的听(15)(以及看)则是话语(16)的存在方式。
话语机制不能忍受事物处于混沌和不明状态,它使人关注切近的需要和目的,将源始的整体性的身体意义拆分为明确和固定的意义单位的组合,以供人订造和使用。在创建明确和固定意义的过程中,话语机制将身体的意义游戏所昭示的可能意义转化为现实之物并加以保存。它创建的种种现实之物使人获得了确保自身生存的必要的物质基础,进而使人从自然状态提升出来,拥有了一个属于人的世界。
但话语机制创建的确定的意义使身体意义的丰富性受到损失,意义游戏所保有的游离性和开放性受到限制,意义游戏的活力也逐渐枯竭。当源始的身体意义被分解为标准化的意义单位后,身体意义就逐渐被遗忘和遮蔽了。
(5)身体视域和话语视域既相互照亮也相互遮蔽。
本真的听和非本真的听都是视域运作方式的组成部分。身体视域所照亮的身体的意义场与话语视域所照亮的话语的意义场相互提供意义的可能性,即相互照亮,但又都试图让各自的意义取向来影响、主导人与事物的交往,从而遮蔽对方。在这种斗争当中,人才进行现实化的与事物的交往。
虽然身体和话语的意义机制同时存在,两种意义也都会在视域得到保存,但因为身体被遗忘,话语机制通常占据主导地位。话语机制遮蔽着身体的意义,然而身体的意义是一种持续的涌现,它总是能够从话语机制的帷幕之后穿越出来。
(6)世界视域先于个体视域。世界视域就是语言。
个体人在其生存活动当中能形成属于自己的视域,即个体视域。但个体人的生存并非在真空当中展开,它必须与事物有所交往,而它与之交往的事物可能同时处于他人的视域之内,这样,个体就不能完全自主地决定其生存,而需要通过在世界中与他人交往来实现。个体视域也不是从孤立的个体生存中产生的,只要人生存,它就总已经在由语言所组建的意义世界当中,而个体视域首先就来自包罗历史和现实的意义总体及其结构的语言。语言赋予个体以个体视域,又以促成个体交往的方式在个体视域之间形成交流并将它们联合起来。因此语言是一个总体视域,又称世界视域(17)。正是语言将所有个体都纳入一种交往和理解的共同存在当中,这种共同存在使得所有个体首先作为交往的人而不是孤立的人而存在。
三、什么是“看”
根据视域理论,可以对“看”做如下阐释:
(1)眼睛的看就是让眼睛去承受事物自身闪耀的光亮,同时又以人的视域去照亮事物,从而相互照亮。相互照亮不是被动接收,因而是构造性的呈现。作为视域与事物的相互照亮,看将在照亮当中生成的意义加以保存,因此,看是“解蔽”。
然而,因为“看”总是从视域中看,而视域总是有其界限,因此,作为解蔽的“看”就必然同时也是“遮蔽”。遮蔽是双重遮蔽(18):一、视域所提供的可能性给出了“无蔽”的范围,超出此范围,“看”难以取得任何意义,或根本“看”不到,比如视而不见的情况;二、已经被视域赋予意义的事物,其意义被视域所限定了,事物的更多的可能性被遮蔽了。
(2)在相互照亮当中,看将相互照亮的光亮(即意义)保存到视域当中,通过组建视域、组建人与诸事物的交往,看参与到了人组建世界的生存活动当中。
(3)看与真实。
在《论真理的本质》一文中,海氏指出真理的本质是无蔽,而无蔽必须从存在的解蔽运动得到解说(19)。存在的解蔽就是事物的自身闪耀,而人以其视域与事物相互照亮就是人承受无蔽的方式。进一步说,人以身体向事物敞开才使人首先获得事物自身闪耀的无蔽。因此,身体视域与事物的相互照亮是一切认识的合理性的来源,因而也是真实性的来源。而话语的表象活动必须向身体视域照亮的意义场开放才能确保它对事物本身的开放,从而取得真实性。
在本真的看中,个体以其身体去承受事物的自身闪耀,并让其话语向身体开放,是个体视域与事物相互照亮,以此方式获得的真实是个体真实。个体真实如同伽达默尔说的偏见一样有其合理性(20)。
个体真实需要得到某种“综合”。因为个体的真实总是在其相对独立的视域之内,个体视域之间的差异会导致真实的差异。我们说个体生存是通过与事物交往实现的,而他们所交往的事物却可能是公共的,视域的冲突因此会现实化为行为的冲突。视域的分裂与冲突呼唤一种融和,这个融和必须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相开放来实现。这个相互开放意味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照亮,意味着个体要尽量将其视域公开出来,以便让他人了解自己产出真实的内在根据,从而让他人理解自己,同时,个体自己也应努力去观入他人的视域,理解他人产出真实的缘由。因此,一种作为“综合”的真实,乃是个体之间相互敞开、照亮而得到的真实,它不是什么“客观”事实,而是一种人与人相互“同情”的交流状态。它是共同真实。
(4)两种看。
我们说看是解蔽也是遮蔽,这不等于说所有的看都是毫无差别的和正当的。只有身体向事物开放,而话语向身体开放,才能得到真实。以此方式得到的真实,虽然同时也必然是有所遮蔽的,或说有局限的,但作为“解蔽”来说,它是正当的,可靠的。我们将这种真实的看称为“身体式的看”。
在身体式的看以外还有一种“话语式的看”。话语式的看有明确的目的,而且它不像身体的看那样保持着与事物的意义游戏的关联,这种看受话语意义系统的引导,并试图从事物中看到明确的乃至规范化的意义。这种看跳出了意义游戏所采取的与事物的切近“距离”,而使观看者站到事物的对立面,从而事物变成了对象、客体。在话语式的看当中,身体承受的事物的自身闪耀被话语视域过滤了,因而构成进一步遮蔽。这种遮蔽应该接受批判。
不论是身体式的看还是话语式的看,都是从视域当中看。在视域当中发生着身体与话语的争执,人们的看总是在两者的争执中展开的。在日常生活中,两种看常常纠缠在一起。
四、镜头的“看”
现在来阐释镜头在何种意义上是眼睛的延伸。
显而易见,镜头的呈现与眼睛的呈现因为物理特性上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镜头的视阈与眼睛不同,在镜头纪录的一帧当中,它将视阈之内的事物加以采集,视阈之外的事物被忽略。镜头的看是在平面上看,景深是幻觉。镜头的看可以通过场面调度来安置镜头内的物像,从而在视阈之内构造看的重点、顺序以及形式关系。镜头的看能够通过选择聚焦性能不同的透镜来看,能够通过变焦来看,能够迅即变换观看的立足点。镜头的看不必按照物理时间展开,它可以压缩,可以跳跃,甚至可以扩张,还可以打乱顺序。
除此之外,镜头的呈现相对于眼睛的呈现的最显著的差别是:它能把眼睛的呈现保存起来并公布出来。镜头的呈现把所看到的图像储存在相关设备中,并在后期剪辑时将图像编辑成成品影片,成品影片可以用各种播放设备播放出来,于是非拍摄者的观众也能够看到拍摄者拍摄时所看到的情景。可保存,可公布,这两个早已让人习以为常的特性却带来了镜头的看相对于眼睛的看的本质区别。
拍摄者通过镜头来看是拍摄者对事物进行感知的方式,它能够被保存下来。镜头的看不仅是被动的感知,它不仅承受事物的自身闪耀,也从其视域当中来照亮事物,这个照亮乃是构造性的呈现。镜头在感知的时候就已经在进行某种表达了。比如,镜头选取的物像总带有选择性,在这个选择当中已经透露了选择的标准,不论这个标准对拍摄者是明确的还是无意识的,都表明一种意义。镜头在场面调度和运动方面的一切举动都带来意义。剪辑也带来意义。剪辑是对“看”的组织,这种组织基于作者感知事物而产生的理解。如果作者能秉持身体式的看,即他让自己的身体向事物开放,让话语向自己的身体开放,那么,他就不会任意选用镜头的技术手段,而总是会谋求镜头的呈现与自身所承受的光亮的协调。所谓的“技术”手段本身并无任何意义,意义产生于镜头如此处置影像时形成的作者与物像的互相照亮。
镜头的看作为公布,是把拍摄者通过镜头所感受到的意义向观众公布出来。这种公布并不是绝对公布,但是观众至少得到一个机会仿佛身临其境般的来到拍摄者的位置上,看拍摄者之所看。
五、视域融和
下面从视域融和的角度来解说镜头如何保存和公布眼睛的看。
(1)可能性
眼睛的看是个体视域与事物的相互照亮,而个体视域有相对的独立性,个体的看所承受的光亮是他人难以感受到的。眼睛的看因而是封闭的和专属的。但作为世界视域的语言能够促成个体视域之间的交流并把它们联合起来,这意味着眼睛的看有可能得到某种传播。具有封闭性的眼睛的看是如何实现在不同个体间的传播的呢?
我们此前提到过两种真实:个体真实和共同真实。个体真实要求个体自觉做到身体和话语的双重开放,在个体真实的基础之上,个体之间的相互开放才达致共同真实。共同真实是不同个体间视域各自照亮的意义场进行交流的有效方式,在照相术和影视发明之前,各种艺术创作及其传播活动是其典型形式。海德格尔说,艺术的本质就是真理的创建(21)。但显然,这两种真实都是理想状态的真实,仅个体真实就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因为许多个体的身体视域已经被话语视域遮蔽,通向个体真实的道路被阻断了。但真实并非遥不可及,因为身体的意义总是或多或少的能够从话语的控制之下穿越出来,让我们感受到端倪。因此人们总是能在话语的遮蔽之下多多少少实现部分的共同真实。
共同真实是一种视域交流与融和的状态。但不同个体的视域如何能够通过交流与融和来实现共同真实呢?首先,要想向他人传播自己视域内的意义,需要让他人从个体的视域看出去,这意味着为了传播个体视域内的意义必须尽量向他人揭示自己的视域。考虑到个体的视域作为整体通常对个体遮蔽着自身(22),要向别人和盘托出自己是非常困难的。排除和盘托出的方法,展示自身视域的方式是暗示。暗示是展示从个体视域看一系列标志性的事物时的感受,一系列的展示不是完全展示,但它能召唤他人投入自己的视域和想象,他人仿佛置身于个体所处的种种情境之中,自己感受着个体所感受的一切。暗示中包含着一种解释的循环:在一系列的不完全展示当中,每一个展示都将个体视域照亮的小块区域向外展示,被照亮的小块区域召唤我们去想象它的整体,当一系列小块区域纷纷向我们展示的时候,我们对整体的想象就可以更加充分,而当我们对整体的想象更充分的时候,每小块区域的意义在更充分的整体想象之下也更加显明,如此循环,整体和局部都会充分和显明起来。通过暗示的方式,个体的视域(即个体分有的世界)能够显现出来。
第二,从试图理解他人的个体角度来说,观入他人视域和世界的方式同样是进入解释的循环。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观入他人视域时如何控制和运用我们自身的视域。一方面我们要遵循个体真实所要求的身体和话语的双重开放,双重开放才能获取他人向我们自身闪耀的光亮,才为理解他人取得可靠的起点。另一方面,我们在接受他人闪耀的时候又要保持批判,因为在不同的闪耀中我们得到的对于他人视域和世界的整体想象可能是相反的,这不排除他人刻意遮蔽自我的可能性,我们要尽量选择那些发自他人的不包含或仅有少量表演成分的局部闪耀,以此为依据去观入他人,并将遮蔽的成分剔除。
在纪录片的制作和传播过程中可能有多重视域融和发生。首先,作者通过向拍摄对象开放自己,得以观入拍摄对象的意义世界,这是作者向拍摄对象的融和;第二,作者选取拍摄过程中看到的拍摄对象的一系列局部闪耀,以此方式向观众展示拍摄对象的意义世界,但作者的展示是通过选取和设置一系列镜头来实现的,作者选取和设置镜头的系列方式同时在暗示作者的视域本身,以此方式,作者实现向观众的开放和融和;第三,观众在观看纪录片时,通过向作者设置的镜头序列开放自己,首先向作者融和,继而向拍摄对象融和;第四,结合上述过程,纪录片能够实现拍摄对象、作者和观众三者视域的融和,作者自身视域及其纪录实践是融和的中介。
与眼睛的看的封闭性不同,镜头的看作为可以保存和交流的意义空间,使得个体的感知能向他人公开,使个体的看能成为共同的看,并促成深层交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镜头延伸了眼睛。
(2)迫切性
纪录片所肩负的融和世界视域的责任因世界视域的内部断裂的急剧恶化而格外迫切。我们说作为世界视域的语言是将分立的个体视域联合起来的中介,语言实际上是组建世界的意义总体即意蕴的存在方式。但正如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一文当中所指出的那样,人及其所在的世界已经被卷入作为“入于订造的促逼(23)”的解蔽方式的“集置”(24)的“命运”(25)当中。在“集置”的解蔽运作当中,所有事物都因其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来被看待和设置,由此在事物之间形成的意蕴总体就是由以人的需要和欲望为指引的结构来组建的。我们知道身体和话语是解蔽的两种方式,集置的解蔽就是让话语的确定性片面地遮断身体的游戏性。当身体的意义游戏被遮断的时候,事物自身闪耀的光亮就被遗忘了,人类就陷入话语所追求和俘获的有限意义的自我增殖的封闭循环当中。但是在话语的解蔽机制背后隐藏着人对事物的无限向前攫取的欲望,在这种欲望的支配之下,不仅事物失去了作为意义游戏场所具有的对人的亲密性和启发性,而变成满足自身欲望和榨取他人的工具,而且人本身首先在话语对权力的过度追求的过程中被权力占有了。当意义生成方式及意义整体被话语操弄的时候,作为世界视域的语言也开始腐败了,从而栖居于语言之家中的人也被抛入放逐的旅程。海德格尔说人已经走到失去其本质的悬崖的最边缘(26)。
当人本身被纳入片面追求欲望满足的集置的漩涡的时候,人首先就向自身发出了索取和订造的要求,在这种要求之下,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如下新现象:一、由于个体的身体视域被话语视域遮断,人与人就难以通过身体的开放而相互照亮,从而陷入沟通、理解的困境;二、为了达成欲望的再生产,人本身被订造为各有分工的庞大的社会生产机器的零件,精细分工的要求不限于生产领域,更是整全的生活方式,于是人日益走向“单向度”,但协作的紧密化又把人与人的交流限定在生产和消费等标准化的领域,亲密性的交流日益式微;三、人与人日益分裂成不同的阶级、阶层,拉大的差距使得沟通的需要下降,矛盾增加;四、即使大众传媒创造出日益趋同的人群(分众化恰恰是同化的运作方式而不是相反),但它作为话语实践的环节加剧了话语对身体的控制,而人与人之间基于身体视域的本真差异日益消失,结果同样是沟通需要的下降和矛盾的增加;五、话语遮断身体意义之后,那些建基于身体意义的宗教、艺术逐渐消亡,而话语权力的内部纷争又导致众多话语系统并立和激烈斗争,斗争中,几乎所有的话语的权威都在下降,于是人们更加陷入一种无中心无信仰的状态,沟通和理解愈加困难。
(3)身体式的纪录片
但并非所有纪录片都通过身体和话语的双重开放以及以作者为中介的交流而达成视域融和。我们说“看”有身体式的看和话语式的看,纪录片也可以分为身体式的纪录片和话语式的纪录片。前者是那种更多地运用身体的感知的纪录片,它通过作者身体的开放和对拍摄对象的持续观照,在镜头中将身体承受的拍摄对象的一系列闪耀纪录下来,并根据拍摄对象的自身闪耀所暗示的意义世界来结构镜头。身体式的纪录片能将那锁闭在拍摄对象那里的被话语所遮蔽的生活世界向外公布,并赢得相互照亮的真实。相反,话语式的纪录片因为更多地从先入的和固化的话语视域出发看事物、结构镜头,必然增加对事物的遮蔽。
六、结语
镜头能够呈现一种超越肉眼所看的看。这种看把作为世界视域的语言本身所要求的交往、沟通实现为切实的看,它能打破个体视域的封闭与局限,使人学会敞开自身、观入他人视域,达到相互照亮。镜头作为眼睛的延伸,向人们提供了一种共同的看,并塑造一种共同主体。因此,它不止是作者的眼睛,而是作者在其中的共同主体的眼睛。在这个眼睛的背后,应该是人类的良心。
注释:
①本文言及的“镜头”概念,实际上是camera lens和scenes的统一体。Camera lens是影视艺术在拍摄和阶段的存在形式,它的存在就是去拍摄,从而获取一种“看”,也即scenes。Scenes则是影视艺术在编辑和传播阶段的存在形式,它是若干段“看”的结构体,在被结构的“看”的集合中,会产生超越段落之“看”的整体之“看”。影视的存在恰恰就是贯穿了制作和传播两个阶段的,所以camera lens和scenes应该是统一的。中文“镜头”没有对两者做区分,我把它规定为两者的统一体。
②说影视是视觉艺术,隐含着视觉对声音的统率作用。其实视觉与听觉在本质上都是身体的存在样式,而身体的存在样式首先不是所谓的“感知”,而是以身体视域去照亮事物,同时也承受事物发出的闪耀。相关理论见后文的视域理论。
③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逻各斯》,载《演讲与论文集》,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第227-232页。
④关于“存在之解蔽”:海氏认为“存在”具有“两重性”(也称存在论差异,即存在者和存在的差异),“存在者的存在”是一种“有”,而“存在本身”是一种“无”。但正是这种“无”却给出了“有”,作为“无”的“存在”通过区分化的运作而使“存在者”的“有”得以生成,并且“无”还统率着“有”。这里说的“无”就是遮蔽着一切的绝对“遮蔽”,而“有”则是从遮蔽的黑暗与无中涌现出来的澄明,即“无蔽”。存在从其二重性区分化运作而生成无蔽的过程就是“解蔽”。“逻各斯”是存在展开其运作的方式,因而“逻各斯”也是解蔽的方式。相关理论可参考孙周兴著《说不可说之神秘》第一章第一节
⑤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逻各斯》,载《演讲与论文集》,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第221-226页。
⑥关于“道说”:“道说”意指存在本身的“说”。后期海德格尔用一个非形而上学的词语“Ereignis”来指示存在,国内学者孙周兴将它译为“大道”,并将“大道”的运作译为“成道”(Ereignet),而将“大道”的言说译为“道说”(Sage)。海氏认为存在的解蔽通过一种寂静无声的言说向人说语言,而人的本质就是去倾听和接受存在的言说(也即大道的馈赠),人正因为能倾听道说才有了自己的语言,因而道说是语言的本质。可参考孙周兴著《说不可说之神秘》第五章,以及海氏著《语言的本质》和《走向语言之途》(载孙周兴译《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1997年5月)。
⑦关于“倾听”:海氏指出,言说的本质是对道说的呈现、置放和保存,而不是发出声音或表达意义,与此相应,听也不是对声音的听觉接受和意义转换,而是对在道说当中被呈放出来的东西的倾听。因为道说是一种聚集起来的呈现,听就是聚集起来的倾听。可参考海氏著、孙周兴译《逻各斯》,载《演讲与论文集》,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第227-229页。
⑧关于“一种逻各斯”:海氏原文称它为“这个逻各斯”。因为听作为逻各斯(即所谓采集着的置放)并不是存在本身展开运作的方式,而是人居于存在当中所采取的属于人的解蔽方式,这种解蔽方式因为归属于逻各斯而具有逻各斯的特质,因而被称为“这个逻各斯”。参考海氏著、孙周兴译《逻各斯》,载《演讲与论文集》,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第229页。
⑨关于“属于人的解蔽方式”:请参考注释④。“解蔽”是从遮蔽中涌现出无蔽的运作过程,它原本是属于存在本身的,但人通过参与到存在本身的解蔽当中的方式,自身也具有了解蔽的能力。“听”作为属于人的逻各斯,是属于人的解蔽方式。
⑩关于“视域”:视域原本是胡塞尔的术语(可参考倪梁康著《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修订版),三联书店,第216—217页;也可参考黑尔德为胡塞尔著《生活世界现象学》撰写的《导言》,见倪梁康译中文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5月,第13页)。笔者在此借用这个概念,并将之与海德格尔的理论做结合与改造,而并不沿用胡塞尔的严格定义。
(11)关于“遮蔽”和“无蔽”:请参考注释④。
(12)关于“世界”:此处使用的“世界”概念指世界的本质,海德格尔称之为“世界之为世界”。海德格尔认为“世界之为世界”乃是由缔结因缘的指引关联网络组建的总体意义结构,即意蕴。可参考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第97-104页。
(13)关于“本真的听”:海氏说,只有当我们归属于在道说当中被传呼的东西时,才有本真的听。这里说的被传呼的东西就是在置放的道说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而归属于道说意味着将在作为解蔽的置放当中被争得的无蔽(也即置放的道说和呈放)带向对人的呈现。可参考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逻各斯》,载《演讲与论文集》,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第228-230页。
(14)关于“身体”:根据视域理论我们可以对身体做出如下界定:(1)人因为有身体才能承受无蔽之澄明,身体是一切意义产出的根本源头。(2)身体是意义场。身体的意义机制是产出作为整体呈现的、非明确、不固定、游离态、开放性的意义。(3)身体是视域的组成部分。身体产出的意义能得到保存,同时,被保存的身体意义自发进行着意义的游戏,被保存的和在意义游戏中生发的意义能照亮的生存之意义场。(4)身体与话语两种意义机制争夺着对生存意义场的控制权。双方在争执当中促成生存的展开。可参考郑力烽著《乡村身体——从纪录片中的身体现象看乡村人群的生存》(硕士学位论文)第27-29页。
(15)关于“非本真的听”:非本真的听不是对逻各斯的道说的倾听,而是以人自身为尺度来听。海氏暗示在古希腊所发生的存在的闪现(即逻各斯本身在这个逻各斯的运作的道说当中被暗示了),但这个闪现如惊鸿一瞥而迅即熄灭,未能得到保存。由此而来出现了存在本身被遗忘的局面,其结果是人们沉沦于存在者之上,流连于存在者的已经显现的明确、固定的意义,这些意义已经被赋予人,而人同时也被这些意义所塑造和束缚,人并且习惯于以自身的明确、固定的需要(即人为自身下定义)来规定事物、向自然也向自身不停索取。但是作为意义的源头的存在本身却被遗忘了。
(16)关于“话语”:此处使用的“话语”概念主要受到福柯的启发,但与福柯的话语概念意义不尽相同。受到启发之处主要是福柯将话语和身体对立的提法。福柯视话语为权力运作的方式。在他的早期著作当中,身体一直作为话语权力的规训的对象出现,但正如《话语权力的终结》一书的作者说的那样,福柯并不是简单的反对主体,而是反对被话语权力控制的“主体”,而“真正属于自己的主体”却是他终生的隐秘追求。实际上在他未完成的《性经验史》第四卷(《肉体的忏悔》)中,他已经在谋求超越话语权力的控制的主体和身体(可参考吴猛、和新风著《文化权力的终结:与福柯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423-425页)。而与福柯的“话语”概念的差别在于,他的“话语”概念意指围绕特定对象的各种陈述的集合,它以陈述为最小单位,从形式上看,它是语言内部的现象。但笔者在本文中使用的“话语”概念首先意指一种意义产出和保存的方式,而不限于意义的表达。本文使用的“话语”概念可以包含词语的生成,也可以包含陈述(群)的生成,它也不限于语言内部,对福柯来说的种种“非话语”的存在,如机构、技术、社会等,作为意义结构的方式,都可以属于本文所使用的“话语”的范畴。但本文使用的“话语”概念与福柯的“话语”还有一处相通之处,即它们背后都是“权力”在进行运作,稍有差别的是,本文把“权力”阐释为无限攫取事物的欲望。
(17)参见伽达默尔著,夏镇平、宋建平译:《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11月,第59-69页。
(18)关于“双重遮蔽”:可参考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艺术作品的本源》,载《林中路》(修订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7月,第40-41页。
(19)参考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论真理的本质》,载《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13-234页。
(20)关于“偏见的合理性”:参见伽达默尔著,夏镇平、宋建平译:《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11月,第8-9页。
(21)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艺术作品的本源》,载《林中路》(修订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7月,第59页。
(22)关于作为整体的个体视域遮蔽自身:在人保存无蔽的逻各斯中包含着两重对立的因素——带向呈放和对安放的庇护。带向呈放是使事物有所显现,对安放的庇护是将事物置入无蔽的整体结构当中加以庇护,庇护使事物隐入无蔽的整体当中。由此可见,人的解蔽活动既解蔽又遮蔽,通过解蔽获得的无蔽既“显”又“隐”。“显”者是无蔽中的个别事物,“隐”者是无蔽整体,也即视域。参考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逻各斯》,载《演讲与论文集》,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第221-242页。
(23)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逻各斯》,载《演讲与论文集》,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第24页。
(24)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逻各斯》,载《演讲与论文集》,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第3-23页。
(25)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逻各斯》,载《演讲与论文集》,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第23-33页。
(26)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逻各斯》,载《演讲与论文集》,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第26-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