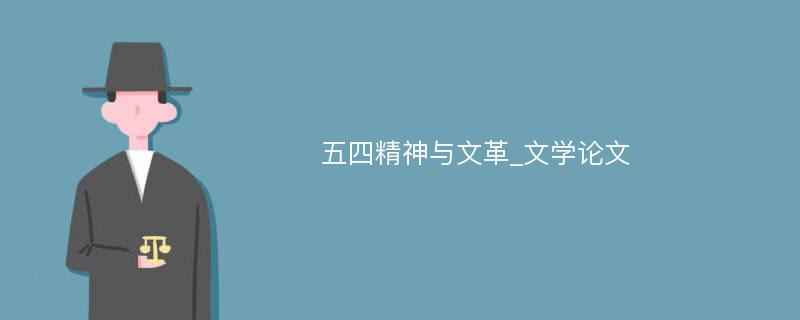
“五四”精神与文学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革命论文,精神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来,从不同角度研究、探讨或涉及到“五四精神”的文章可谓是汗牛充栋,然而全面、系统地专门论及“五四精神”的文章却不多见。假如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继承、弘扬的“五四精神”到底是什么?这个看似熟知的问题,却很难用几句话准确、全面、简明地予以回答。因此,笔者试图把“五四”精神归纳、概括为主观精神、人文精神、启蒙精神三个方面,进而论其在文学上的展开,并就教于大家,以求匡正,以便有利于在新的世纪进一步发扬光大“五四精神”。
一
“五四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人的主观精神的肯定与高扬。主观精神本自于西方的生命主体哲学、人的主体精神等现代进步思潮。生命主体哲学是指人的个性表现形式的精神生命和关于“人”的主体意识、意志、精神的表现特征。生命主体哲学认为人的基本存在形式就是人是有个性的人,从动力论的本体论观点来看,社会就像一架机器,人就是这机器的动力,全靠人这个动力,将社会这架大机器发动起来,社会动力的来源就是每个个人的能动性和主观性。因而要改造社会,实行社会变革或革命,争取社会进步,就必须给每个个体的人以充分发展的自由。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总是得通过具体的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这就必须得承认个人的主体性,自主意识等。
“五四”时期对于人的主观精神的肯定和高扬,这既是对两千年来封建社会客观精神的一种反动,又是封建统治阶级大一统的客观意志崩溃的必然。五四时期,中国正处于清王朝解体,民国名存实亡,军阀割据这么一个社会历史环境条件下,封建的大一统的意志已被打碎,新的统一的社会意志还不可能形成。这为人的主观精神的解放和发扬提供了可能,人的主观精神潜力的开掘和发挥都具有了相当的自由。在这样一个有利于张扬主观精神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19世纪后期的尼采、叔本华、斯蒂纳尔等人的主观哲学思想、生命主体哲学被大量介绍进来。“五四”新文化的先驱者们大都是留学欧美、日本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拿来了西方的这些思想,把它们变成主观、个性主义的武器,用来打击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封建思想文化。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人都接受过尼采、叔本华等的影响,介绍过这些人的哲学思想。郁达夫还专门写过介绍斯蒂纳尔的文章,宣传他的思想。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就曾开宗明义地为“人权、自由”张目,号召青年挣脱“陈腐朽败”的封建专制伦理思想的束缚,争取人格独立、思想解放、精神自由。鲁迅在他的《破恶声论》一文中曾大声疾呼:“人丧其自我矣,谁则呼之兴起?”十年之后鲁迅的“大声疾呼”才得到了响应,1919年7 月李大钊在他的《我与世界》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性解放自由的我,……。”毫无疑问,五四时代的最强音是“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注:鲁迅《伤逝》《鲁迅小说全集》。)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完全自觉的个性意识与主体意识。“五四”时期主体个性自由意识在理论上的表现,是胡适、周作人提出的“个人本位主义”。胡适在他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曾说:“社会最大的罪过莫过于摧折个人的天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于是他呼吁道:“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周作人在他的《人的文学》一文中说得更为明确:“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郭沫若也曾明确地说过:“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所以我便借文学以鸣我的存在”,“一任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注:郭沫若《论国内的文坛及我对于创作的态度》《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女作家庐隐也宣称:“创作的作品,唯一不可缺的就是个性——艺术的结晶,便是主观——个性的情感。”(注:庐隐《创作的我见》。)
显然,高扬“五四”主观精神,与“五四”新文学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提倡主观精神的不仅仅是政治思想家,更多的则是文学家。在“五四”时期,思想家与文学家往往是统一于一体的。在“五四”,高扬人的主观精神往往依赖于文学这个载体,所以我们看到的对于主观精神的阐发,大多与文学创作分不开。冰心就曾说过:“文学家,你要创造真的文学吗?请努力发挥个性表现自己。”(注:冰心《文艺丛谈》。)这里所说的“发挥个性表现自己”指的是发扬主观精神。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了30年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胡风干脆把主观精神作为他的文艺理论体系的支柱和核心,提出了要发扬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可谓是把“五四”倡导的主观精神用于文艺理论建设上的典范。当然胡风为此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胡风的人生悲剧本身也就充分地体现了“五四”主观精神。
就文学的创作而言,“五四”时期,主观抒情小说十分盛行。比如“身边小说”的出现和流行,这种小说往往是以作者的自身经历的想象性的形象构成作品的主要内容。这便于作者借题发挥自我的主观感受,倾诉“我”的心灵的主观情感。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郁达夫的《沉沦》等则是这类小说的突出代表。此外,朱自清、张资平、庐隐、冰心等人均有这方面的作品问世。此一时期比“身边小说”更为盛行的是婚恋题材小说。这是因为婚恋小说也便于主观个性抒发,又是反对封建礼教的突破口,是处于青春期的男女最为关注的内容。于是这类小说便成了个性解放和主观情感或意识有效表达的载体。这些主观抒情性极强的作品都十分重视“自我”形象的塑造。鲁迅作品中的“我”,郭沫若笔下的“爱牟”,郁达夫小说中的“于质夫”都有着极鲜明的作者自我形象的投影和主观精神的折射。再如叶圣陶的《萌芽》、许地山的《缀网劳珠》、庐隐的《海滨故人》等作品,以象征性的环境气氛的渲染,抒发或表现了主人公的情绪感受。这些作品,不论是对个性自由的呼唤还是对爱与美的追求,或是为了建立平等自由的理想王国,都带有极强的主观情感,都蒙上了一层浓厚的主观色彩,不同程度地追求或构筑着自己的主观理想世界。总之,“五四”主观精神由于依赖文学作品为载体,才得到充分高扬与有效倡导,从而最终促进社会意识的进步。
二
在“五四”时期与主观精神的倡导紧密联系着的是人文精神的张扬。“人文”概念在西方最早产生于19世纪西欧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产生、发展的顺序经历了人文科学、人文主义,尔后才出现了“人文精神”,即“人文主义精神”的宣扬。从最一般意义上来说,人文精神就是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是一种肯定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本性和个性解放的人生态度。它包括人权、人道、人性等内容。可以说是从特定角度对人的本质的反思。在我国古代也有“人文”一词,但它是与“天文”一词相对而提出的。我国古代的“天文”是指自然现象、自然秩序等;“人文”是指人事条理、人的精神生活形式。具体地说中国古代所谓的“人文”主要的是指区别人与动物的,人类所特有的文化、文饰、美饰等精神产品价值及其存在形式,它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所强调的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权、人性等人的本质特性是有着根本的质的区别的。因此,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在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并无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只是到了近、现代,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各种进步学说,各种现代思潮涌入中国之时,人们才用“人文”一词来翻译humanism这个英文词汇。
早在清末,“五四”之前,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等人就已经引进了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但他们主要是出于政治改良之目的。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思考,“仍然是顺向性的反思,即仍然是企图在自身的文化体系中克服缺陷”。(注:刘再复、林岗《“五四”文化革命与人的现代化》《文艺研究》1988年第3期。)而到了“五四”时期,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则是一种逆向性的反思。目的是为了推倒整个传统的旧文化体系,引进西方异质文化,创建全新的道德文化、人文精神。跳出传统的儒家学说“内圣外王”的封闭圈,致力于追求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要义的人的解放。因此,发现人、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以及终极关怀意识的形成,就成了“五四”先驱者们大力提倡和追求的理想。“五四”人文精神的主要内容就是人的解放,使人从自然和社会的各种限制其自由健康发展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获得作为一个不断向上发展的人所应有的人格、权利。这种现代个性意识的出现,这种对“人”自身价值的发现和认识,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思想规范,摧发并促进了走向人的现代化的“五四”个性解放运动和人文精神的产生、形成。
“五四”时期对于“人”的认识,表明人的个性从外在的封建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凝结成一个独立的精神个体。这种认识,这种对于人的个性解放的要求及其启蒙,在“五四”时期,在经历过了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禁锢下的中国,必然要从婚姻家庭、恋爱自由为开端,从性爱意识角度来体现个性意识的特征,进而唤醒国人的个性意识的觉醒,这是当时普遍而又合乎客观现实的步骤。
只有真正觉醒了的人,才有可能把自己觉醒了的个性对象化到他人身上,只有对他人的人身权利和价值给予真正尊重的人,才有可能尊重自我的权利和价值。当“五四”时期的理论倡导者们,在思想意识上明确了“人”应有的权利之后,便把肯定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的现代意识自然地注入到文学的体内,必然地要借助于文学这个载体进行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倡导者周作人早在1918年底就提出了“人的文学”和“僻人荒”的主张,第一次把反封建伦理道德的人的解放同文学联系起来。这是周作人在继胡适、陈独秀关于“文学改良”、“文学革命”论提出之后,对新文化运动的又一重大贡献,它把新文化运动引向了深入。于是现代个性意识、人文精神,便成了“五四”新文学的主题。一批具备了现代意识的作家脱颖而出,他们以激愤之笔揭示封建伦理纲常的虚伪和非人性的本质。叶绍钧的《一生》、刘静农的《烛焰》、冯沅君的《贞妇》、孙俍工的《家风》、曹石清的《兰顺之死》等一批小说都揭示了封建伦理纲常下妇女非人的生活。而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痛苦》、胡适的《终身大事》、田汉的《获虎之夜》、侯曜的《复活的玫瑰》、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遗言》等一批戏剧、小说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觉醒了的一代青年背叛家庭,争取自由独立权利的要求和斗争。
在封建社会中,妇女从来就是被污辱、被欺压的对象,从来就是男性的附属品。只有到了“五四”时期,妇女的命运才引起了先驱者的普遍关注。因为她们也是“人”,也是一个完整的精神个体。正是由于受压迫最深,因而也就最麻木、最愚昧和不觉悟,所以她们也就更急切地需要获得“人”的解放。“五四”作家同时作为启蒙思想家,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妇女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塑造了许多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艺术形象。鲁迅曾在他的《灯下漫笔》一文十分沉痛地指出在中国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中,压在最底层的是妇女与儿童,在其上则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受压迫,不仅是经济上的压榨,更是精神上的奴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受压迫最深的也是最不觉悟的。因此,对妇女的人格独立意义与价值的发现与肯定,就成了“五四”“人的觉醒”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成了衡量一个民族的觉醒、社会进步的标志。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在人类的发展的一定阶段中,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文精神,固然有它相当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当把人的权利等异化为“绝对观念”,“绝对意志”时,它就会走上反面。从理论角度讲,以人为主体的人文主义其实也就是把个人作为主体的一种主体论。这种以自我为价值体系的主体,是作为社会、群体的对立范围而存在的,但是光讲主体性不讲对立项的社会与群体,便使人变成了自己设定的价值观的奴隶。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一个带历史性的矛盾。“五四”的伟大并不在于解决这个矛盾,而是顺应历史潮流首先对它进行勇敢的探索,力图找到历史的纵向要求与现实的横向影响的契合点,为构建社会的新型文化伦理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人文精神仍然没有过时,仍然值得高扬。
三
一切先进的思想、学说,不能仅仅停留于思想家、理论家的思想观念之中,而是要让它变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这就是要让广大民众认识它,了解它,接受它,从而使之变成促进社会变革的动力。但是在“五四”时期,广大民众还处于麻木、愚昧、落后、不觉悟的状态之中,封建专制的种种清规戒律还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自由。这就需要用启蒙精神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使他们觉醒,使他们认识到“我”也是人,“我”应当具有做人的资格,有人的尊严,人身自由,获得人的权利等等。
18世纪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资产阶段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启蒙主义者把宗教迷信和专制制度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以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批判、否定神权统治;他们以“自然法则”为依据,提出“自由、平等”的口号,来否定专制制度和贵族特权。要求从教会的束缚下解放个性,以先进的思想启发、教育民众。他们继承了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且比人文主义更进一步地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宗教专制制度。“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或国家制度,一切都要受到最无情地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注: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04页。)他们以理性的光辉来描绘未来,认为“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不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注: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53页 )他们崇尚理性, 强调思想意识的力量,把启蒙教化作为改造社会的途径。启蒙的结果,终于促发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在“五四”时期,文化先驱者们在引进西方各种进步社会思潮,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必然也注意到了人类文明史上继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又一次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他们不仅学习、输入西方的启蒙精神,而且把它与“五四”时期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紧密联系起来。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就曾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全面详细地介绍了爆发于法国的这场反封建的启蒙运动。接着又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指出了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相互关系,认识到思想启蒙必须有赖于文学这个载体来进行。于是他把文学革命引入思想启蒙的轨道,提出启蒙文学的主张,使其成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之承担起思想启蒙的重任,配合思想启蒙的开展。“五四”时期的中国,刚刚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自我意识的觉醒,都还远未深入到民众之中。思想文化方面的革新远比推翻一个旧的社会制度要复杂、曲折、艰难得多。长期以来,封建的文化伦理道德观、宗法、家族意识已构成了国民的心理潜意识或无意识,养成了奴性性格。要使民众真正觉醒,获得主体精神,认识到人自身的价值等等,非先知先觉者们对广大民众进行启蒙不可,而这种思想启蒙又非借助文学这个载体,别无良法。
陈独秀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全面展开了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启蒙工作。他们从一开始就深刻地认识到新文化运动的现实特征,意识到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特殊使命:历史要求他们不是一般地抽象地宣传西方进步的思想学说,而是要求他们必须把这些学说思想灌输到民众的头脑中去,彻底改变受了千年封建思想统治的民众个人的精神灵魂。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入手改造国民的灵魂,实现社会意识观念的全面变革,而这又是围绕社会伦理革命而展开的。因此,思想启蒙家把思想革命看得高于政治革命,而伦理革命则是思想革命的主要内容。当时提出的“提倡新道德”就是指建立在民权主义政治学说上的“个人本位主义”。“反对旧道德”就是指反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家族本位主义”,陈独秀就曾写了这方面的系列文章,猛烈攻击封建伦理道德的核心“三纲五常”等。已触及到了一个中国社会变革的极其深刻的现实问题,积淀为每个社会成员的无意识心理结构,及那种内化为广大国民的灵魂与性格。同时,启蒙思想家还号召有识之士,身体力行地把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想带到农村去,“治理这些乡村的人”。李大钊就曾在他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进行思想启蒙工作。因为“只有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这便是对知识分子启蒙作用的一种历史的肯定。
在“五四”先驱者的启蒙意识中,一方面包含了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人”的价值的肯定与期待——他们的悲剧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另一方面,先驱者们又不能不看到农民因长期受精神上的奴役而形成的愚昧、麻木的不觉悟状态。他们的被发现、被肯定的“人的价值”,与他们自身不觉悟状态,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于是在启蒙思想家这里,产生了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文学课题。在这里启蒙的知识分子与被启蒙的下层人民之间所具有的“平等”意识,最能体现出“五四”时代启蒙精神的特色,也是启蒙者的深刻可贵之处。
但是,伦理变革并不是思想革命的唯一表达方式,作为一种理论思维,伦理革命不可能从现实性上完全担负起变革民众思想,改造社会的重任。这里必须有另一种形式的介入。在现实性上,“这种形式”必须最易于贴进人和社会,在理论层次上表现为现实与意识观念的最初环节,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具象的形式,不言而喻,“这种形式”便是文学,文学的实质是形象的和感情的。因此,也只有它才能充当思想革命与人及社会现实之间的中介环节。换句话说,个性解放及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必须有一个合适的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才能启发民智,唤起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达到启蒙之目的。这个载体就是文学,也只有文学才能担当得起如此启蒙之大任。正如李大钊说过的:“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赖于新文艺为之先声。”(注: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李大钊选集》第61页,1959年版。)再如鲁迅的弃医从文,周作人放弃学工转而从事文学活动等等。都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文艺是改造国民精神的利器。当然这些认识也是与中国古代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密不可分的,只不过所载之道不同罢了。
陈独秀不但较早认识到文艺革新与思想革新、社会改革的密切关系,而且还提出了改革文学以配合思想启蒙之设想。与当时尚在美留学的胡适取得联系,应陈独秀之约请,“五四”文学革命的第一篇重要文章,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发表。随即陈独秀自己也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为进一步阐明文学革命的基本纲领原则,提出了“三大主义”,作为对胡适文中所提出的“八不主义”的声援。陈独秀的文章更为鲜明地规定了文学革命反封建的思想启蒙的性质和任务。“五四”前期的现实需要直接服务于思想启蒙运动的“启蒙文学”,不是对文学自身进行启蒙的“文学启蒙”。“文学启蒙”虽然也是一种启蒙,也是思想启蒙的重要任务之一,“五四”先驱者们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旧文学、旧文学观念应当改变,应当进行“文学的启蒙”。但这只是文学自身审美价值的追求。如果彻底否定了“文以载道”的观念,则意味着新文学在抛弃旧文学观念的同时,也将丧失其直接效力于思想启蒙的社会功能,也有悖于陈独秀当初发动文学革命的初衷。因此,关涉文学自身的启蒙的主张虽已被提出,但却被束之高阁。“五四”前期深重的时代课题,决定了文学内容的革新不能纯粹追求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而必须服从于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不应否定文学的“文以载道”的观念,而是应以新“道”替换旧“道”,使文学不再成为宣传封建思想文化的手段,而应成为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工具。1918年底周作人在他的《人的文学》一文中提出的文学观,充分体现了时代课题对文学的这一要求,第一次明确地完整地阐明了启蒙者的人道主义思想,系统地阐述了“人”的意义,明确地提出了以文学来进行思想启蒙的主张。他的所谓“人的文学”指的就是表现合乎人性的生活,宣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学。1919年3月他又发表了《思想革命》一文, 强调了思想革命对于文学革命的重要意义。总之,周作人的新文学观突出了“人”的发现,又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既同传统的旧文学划清了界限,实现了文学内容的革新,又能使其成为思想启蒙的工具,促进启蒙运动的深入开展。“五四”时期,文学内容的革新,其根本意义首先是政治的、文化的,而不是艺术的,审美的。“五四”文学革命也只有在救亡图存的思想启蒙中,在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中,才能充分显示出它的意义和价值。而思想启蒙也只有借助于文学这个载体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显示它的时代价值。
今天,我们重论“五四精神”,那是因为它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存在,还没有“复归于它的历史性”。我们还没有走出“历史循环”的怪圈,获得真正的历史的进步。虽然我们今天的社会变革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五四”,但是“五四”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即使是一些肤浅的问题,也还没有被当今人们所认识。甚至还要被当作“异端邪说”被拒之千里。因此,我们今天既要解决“五四”未曾提出过的问题,又要对“五四”所提出的问题“重新做起”,而且还要接受“五四”“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的教训,要“做”得更好、更扎实、更彻底、更深入。
标签:文学论文; 人文精神论文; 文学革命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陈独秀论文; 新青年论文; 历史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