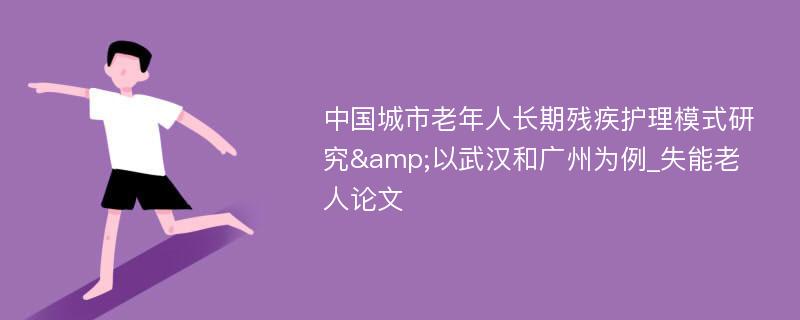
中国城市长期失能老人照料模式研究——基于武汉和广州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州论文,中国论文,老人论文,模式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0672(2013)01-0005-06
一、研究背景
根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①。人口老龄化在导致老年人口比例和总量增加的同时,也导致了需要照料的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其中长期失能老人群体的规模也日益扩大。长期失能老人群体与其他老年群体相比,其照料需求更为复杂,且持续的时间更长,对照料服务体系的要求更高。在中国当前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体系的背景下,对长期失能老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照料模式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长期失能老人的照料模式,主要是指当长期照料决策一旦作出并不再变化时,长期失能老人的非正式支持内部不同照料提供者,非正式支持与正式支持之间,以及正式支持内部不同照料提供者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和状态。国外已有较多文献对这一议题进行了探讨,总的来看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对照料模式进行分析的:一是对于特定的照料任务,到底是由谁来承担,即长期照料的承担者是如何确定的。目前主要有两种确定模式:第一种模式,层级补偿模式(the hierarchical compensatory)。这种模式认为,老年人照料依赖的偏好是倾向于从最亲密的家庭成员开始,根据关系的亲疏和照料的可获得性来确定照料者——首先是配偶,然后是各自的子女,再是关系较远的家庭成员或其他人(Cantor & Brennan,2000);第二种模式,任务主导模式(taskspecific theoretical)。这种模式强调长期照料任务的匹配性,即将长期照料不同任务的要求(较近的距离,高度的热情或技术性要求)与照料可能提供者如配偶、子女或正式机构的服务专长对应起来,从而实现长期照料任务的高效提供和实现(Litwak,1985; Messed et al.1993)。二是根据非正式照料资源与正式照料资源之间的关系,一般划分为两种类别:第一种,“替代模式”(the substitution model),这种模式认为正式照料介入到照料体系中会减弱甚至取代非正式照料(Agree et al.,2005);第二种,“互补模式”(the supplementary model),这种观点认为,正式照料提供者被视为是对非正式照料者的努力给予辅助或帮助,只是当被照料者的照料需求增加超出非正式照料者的能力范围时才提供支持(Davey et al.,2005; Li,2005)。三是分析了长期失能老人在接受照料的持续过程中,网络的变化情况。诸多文献发现,老人的网络一般是沿着社会网络——支持网络——照料网络这一路径呈逐渐缩小的趋势,随着老人身体健康状况和照料需求的变化,非正式支持和正式支持资源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发生着变化(Barrett & Lynch 1999; Keating et al.1999; Norah K.et al.2003)。
通过对国外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对于长期失能老人的照料模式这个议题,国外已有了较为成熟和成体系的研究。本文试图将国外文献中对于长期失能老人照料模式探讨的三个方面,应用到对中国城市地区的分析中,通过与国外研究所得结论的比较,来发现中国城市地区长期失能老人照料模式自身的特点。
三、资料来源和收集方法
美国国家长期照料调查(National Long-term care Survey NLTCS)将长期失能老人定义为:65岁及以上,且存在至少一项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或日常活动能力(IADL)指标的完成需要他人帮助,并且这种状态持续或预期会持续90天及以上,即判定为需要长期照料的老人(Michael & Berit,2004)。本研究参照这一标准,于2011年7-8月,在武汉市和广州市运用立意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法,访谈了13个居住在家中和21个居住在养老院的长期失能老人②,根据其在接受照料的过程中不同照料提供者的相互关系,来对其照料模式进行分析。
四、访谈资料分析
(一)非正式支持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
照料提供意味着家庭功能的分担,是一种家庭共同体的决策行为。在中国,家庭在社会中仍保留着其特殊的重要地位,因而老年人照料的决策通常是家庭成员共同商议的结果并在家庭成员之间共同承担责任。虽然通常主要会由一至两个主要的照料者来承担,但其他家庭成员或亲属也会分工合作,这一视角强调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和合作的特征(Stephen & Christianson,1986; Townsend,1965)。
1.配偶与子女的关系
调查所接触的长期失能老人中,既有配偶提供照料,子女同时也给予一定照料帮助的情况非常少,一般是首先由配偶来承担照料责任,只有当配偶去世或配偶无法提供照料时,子女才可能承担部分责任。
个案Y09,男,75岁。我住进来(养老院)之前,我跟老伴两个人住,都是我老伴在照顾我。两个儿子都下岗了,自己都顾不过来,哪还有时间管你。小儿子偶尔过来一下,大儿子很少来。
个案Y19,女,80岁。我跟老伴都是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后决定住进来的(养老院)。之前我跟老伴一起住,生活上基本能够自理,四个儿子都很忙,都有自己的家庭,过来也帮不了什么,就不要他们过来了。我们生活上都能应付的来。
访谈资料显示,现实生活中长期失能老人当出现照料需求时,由于子女本身不愿意提供照料,或老人不愿意麻烦子女,而导致多数情况下,配偶与子女二者并不是同时起作用,而是存在明显的先后顺序。老人一般情况下首先依赖的是配偶,当配偶能够提供照料时,子女通常认为有一个“缓冲层”存在,而出现责任分担甚至是责任推卸的状况。个案Y09和个案Y19两位老人,由于配偶无法提供长期照料后,没有考虑依靠子女来承担照料任务,即并没有完全符合“层级补偿模式”所提出的照料提供者由内而外确定的规律,而是直接选择请保姆/钟点工或入住养老院,跳过了子女这一层级,出现了与“层级补偿模式”不一致的“隔断效应。”
2.子女之间的关系
个案J01,女,90岁。保姆全天都在这,子女根本不管你,在武汉的不来,还总是嫌你,在外地的又没有时间回……还是独生子女,生一个好。
个案J03,女,76岁。(儿子、女儿)过来啊,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来一次,他/她们一天到晚都在忙,都有自己的子女,有多少精力来管你,你何必勉为其难呢!
个案J08,女,92岁。(小儿媳转述)我们姊妹都还走动的比较多。逢年过节她们回来看一下老娘。(哥哥)回来的蛮少,因为海南远。资助倒是不怎么资助,就是你需要什么,就跟你寄点回来,他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
个案J11,女,85岁。(小儿子转述)前天保姆叫我过来,我以为她(老人)不行了,讲话都不会讲了,后来我去拿点药吃,吃了两天就好了一点。平时我有空就过来看一下,我住的地方离的也不远……我自己也做不了什么,我那个腰不行,做粗活都做不了,站久了都要坐一下。我老婆现在带孙子,平时也没时间过来,我姐姐那边也是,全都要带孙子。
访谈结果显示,长期照料任务在家庭内部的分工与合作程度远不如家庭成员与正式支持分工与合作的程度深,家庭成员中往往只有1到2个主要照料者,其他人至多只提供少许的辅助性帮助。更为普遍的情况是除了主要照料者之外再没有其他家庭成员提供帮助,使得长期失能老人的照料网络显得很单薄,一方面对于主要照料者来说,照料任务由于没有其他人的帮助而导致任务集中压力较大;另一方面对于老年人来说,照料由于提供主体较少而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满足最迫切最基本的照料需求,因而需求的有效性和充分性往往难以保证。
(二)非正式支持与正式支持的关系
1.家庭成员与保姆/钟点工的关系
对于一部分居住在家中的长期失能老人,他们的照料提供一部分来自于家庭成员,一部分来自于保姆/钟点工,两种照料资源同时存在共同起作用,但现实情况是这二者之间既不是替代关系也不是互补关系,更多的呈现的是一种补充的关系,即二者都发挥作用,但仍不能够完全满足老人的长期照料需求。
个案J04,男,77岁。(平时)三餐我们自己弄,我们两个人(夫妻)一个手是好的,一个脚是好的,可以互相的(帮忙)。请钟点工有两三年了,之前就是这样自己过的。像我们这种情况,居委会批准免费安排钟点工上门服务,一天1个小时,一个月30个小时。但平时钟点工不在的时候,也只有靠我们自己。
个案J06,女,83岁。女儿在居委会上班,离我这很近,但不是经常过来,也没时间。偶尔过来看一下我,帮我做点事情。(钟点工)一个月来十几次(后经了解是14个小时一个月,14次/月),我符合条件就到居委会去申请,国家照顾的,每天一个钟头,洗个衣服拖个地,再就是洗个被子。我衣服都是攒着,一次来一起洗。
以上两个个案,分别体现出配偶、子女与保姆/钟点工在长期照料过程中的关系。在访谈到的13个居住在家中的长期失能老人中,配偶为主要照料提供者的比例很小。由于长期失能老人多处于高龄阶段,且照料需求是长期的,照料任务是繁重的,配偶往往难以单独承担照料任务。尽管根据“层级补偿模式”,长期失能老人倾向于首先选择配偶来提供照料,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限制条件的,是需要其它诸多的辅助力量才可以实现。中国当前的正式照料资源还十分缺乏,所能够提供的照料,无论是在支持力还是在专业性上都远远无法满足长期失能老人的需求,因而也远达不到“任务主导模式”的理想状况,更多是基于现实限制因素下的一种低水平的安排与妥协。
2.家庭成员与养老院护理人员的关系
当长期失能老人入住养老院之后,正式支持便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家人往往只是起着辅助性的作用。
个案Y03,女,78岁。(剪头发)我的儿子来,我就下去(被儿子抬下去)连车子(轮椅)一起抬下去,推我出去走一下,每个礼拜都来。
个案Y05,女,81岁。儿子他隔一天就来,买点吃的喝的,过年的时候也回去,一般是孩子接我回去,在家待半天。
个案Y07,男,65岁。就我二妹妹还经常来看一下我。(退休工资)也是我二妹妹帮我取,你不靠她我早死了。我有五个兄弟姐妹,有个弟弟住在(养老院)对面都不管,我都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了,他不来你怎么办!
通过与老人的访谈我们发现:
第一,当老人入住养老院后,家庭成员介入的程度与老人在家接受照料的程度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有关。个案Y03、Y05和Y07老人入住养老院后,家庭成员无论是子女或是兄弟姐妹都经常过来,照料活动更多的是饮食和生活上的帮助,与养老院实现功能上的互补。同时,这三个老人在入住养老院之前都是由这些家庭成员提供照料的,人住养老院后仍得到了延续。个案Y03“儿子是实在没有时间照顾我,我自己愿意过来,儿子不愿意我来,但没有办法”,个案Y05“之前是跟儿子一起住的,后来(我)脚萎缩了动不了,儿子想照顾也照顾不了”,个案Y07老人摔了之后看病入住养老院都是老人的二妹妹办理的,住进养老院之后仍然经常过来。国外的一些研究也表明,将老年人送进长期照料机构是摆脱亲手照料义务束缚的需要,但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是对传统养老观念的否定,而是对正在变化的家庭生活的适应性应对,如日益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对收入的追求导致家庭情感的疏远、妇女日益增加的劳动参与率和家庭地位的改变等(Omran & Roudi,1993)。
第二,由于入住养老院,家庭成员的作用由工具性照料转向更多的是监管性照料,即由直接的照料提供者变为了间接的照料管理者。Bowers(1987)认为,照料老年人是一种看不见的(无形的)工作。对照料的定义需要通过对不同阶段照料的理解和体验来进行。运用扎根理论,Bowers将照料概念性的划分为五个独特但又相互重叠的维度:预期的、预防的、监管的、工具性和保护性的。预期性照料指照料者基于可能产生的照料需要而形成决策的行动;预防性照料指涉及直接减缓身体和心理恶化的行动;监管性照料是一种有目的的行动,包括安排、核实、保证、建立和支付等行为,往往这一系列行动可能有时会有时又不会被认为是照料行为;工具性照料指具体实施亲手照料的任务,也是研究这一议题最主要的内容;保护性照料主要指维持老年人的自我形象,避免身体和心理的恶化而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护性照料是最容易由于不恰当的对待而被忽略的。访谈资料显示,当老人入住养老院之后,多数家庭成员的作用由工具性的照料活动转变为监管性照料,更多是确认老人在养老院是否过的好,另外还起到核实和支付的作用,多数家庭成员在这一阶段便从主要照料者的身份中退出。
(三)长期失能老人网络的变化
长期失能老人的照料模式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内容,即长期失能老人网络的变化。长期失能老人的网络呈现出一种逐渐缩小的趋势,即沿着社会网络——支持网络——照料网络这一路径逐渐缩小,照料者只是老年人社会网络中的某一特定的人。
个案J01,女,90岁。老伴在青山福利院住,我照顾不了没办法。五年前我摔了一跤,在康复医院住了三个月,必须要坐轮椅,走不了。现在身体越来越差,但我清楚的很一点不糊涂。还好我有退休工资,不想去养老院就在家请了个人。三个儿子都不想管我。我现在是跟三儿子、儿媳一起住,他们平时很少管我,主要是靠保姆。
个案Y07,男,65岁。我在这里(养老院)住了七年多。当时我在外面打工从梯子上摔下来。老板不管,老婆当时也下岗,女儿还要读书,看到我(摔成)这样,就跟我离婚了,女儿也跟老婆一起跑了。住院的钱都是我二妹妹借的,现在在这里也只有她过来看一下我。我女儿很少过来,老婆就更不说了,我有五个兄弟姐妹,有个弟弟住(养老院)对面,从来都不来看我。
个案Y09,男,75岁。我住进来(养老院)二十几天了。去年还能走,今年就不能走了。我是到别人介绍的一个地方理疗,第二天就烫伤了。在医院住了一个多礼拜就出院了,伤口也一直没好,现在还越来越严重了。我现在翻身都困难,老伴也没法照顾我了,虽然她(老伴)身体还可以。两个儿子都下岗了,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功夫管你,现在这样的更不想管你了。
国外很多研究都对长期失能老人网络的变化给予了较多关注。处于最外层的社会网络是个人周围的社会纽带或联结,通常用其组成成员的规模、结构和密度以及地区分布来描述(Vogt et al.1992);支持网络则是现实存在的可能的社会网络(Jennings 1999),指那些愿意提供支持的成员。支持网络是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子集),由那些提供情感和实际帮助的人组成。社会网络转换成支持网络是需要一些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老人社会网络的规模、结构和密度——个人纽带的强度和持续性;老人和社会网络成员间支持的规范性和互惠性;老人的个人特征;社会网络成员地理上的可接近性(Martire et al.1999)。照料网络和支持网络有其共同的地方,即都指提供情感性或工具性的支持,情感性的支持包括提供社会交流、安全感、确定感、鼓励和监督(Harlton et al.1998);工具性支持包括物质的或有形的帮助,包括家务劳动(做饭、打扫卫生和房屋维护)、陪伴(包括一起购物)、外出帮助(交通)、帐单支付等(Keating et al.1999)。访谈资料结果表明:当照料由短期变为长期的持续行为或照料强度增大时,支持网络中的一部分人会退出,支持网络缩小为最后的照料网络。随着老人日常生活依赖程度的加深支持网络会逐渐耗尽,当支持提供的对象变为有长期健康问题或功能缺损的老人时,可能会由指定的人作为长期照料者,即支持网络中只有一部分会变成照料网络。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1.介于“替代模式”和“互补模式”的“补充模式”
对于中国城市地区的大多数长期失能老人而言,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之间可能既不是“替代模式”也没有达到“互补”的状态。一方面,“替代模式”认为正式支持介入到照料体系之中会减弱最终甚至取代非正式支持,但调查显示目前中国的情况是正式照料服务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居家养老服务所提供的一些钟点工上门服务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远远不能满足长期失能老人的需求,特别是对于高度长期失能的老人,替代的效果非常弱,即正式支持虽然存在,但作用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虽然在正式支持存在的情况下许多长期失能老人的家庭成员还承担着一些照料任务甚至是主要的照料任务,但这并不表明就达到了一种“互补”的状态,因为有些长期失能老人即使是两种支持同时存在,二者合力的作用也仍然十分有限,且二者照料的提供不是同时的。最关键的是“互补模式”认为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共同提供可达到照料的充分性,在这一前提下实现了二者的合作,而访谈资料中长期失能老人的情况更多的是一种“补充模式”,即照料的提供是不充分的。
2.“层级补偿模式”中的“隔断效应”
长期失能老人的照料模式并不是“任务主导”型的,即每一个照料任务并不是由最适合的人员承担,这是由于目前中国的长期照料服务体系还不完善,专业化程度还远远不够。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中国的长期照料模式更类似于“层级补偿”模式,即大多数的照料任务首先是由配偶承担,然后是家庭成员中的子女,最后才是寻求正式支持的帮助。但只是类似还不是完全等同于“层级补偿”模式,因为访谈资料显示在长期照料提供者由内向外层级补偿的扩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隔断效应”,即老人很多时候觉得子女是外人,当配偶去世或无法提供照料时,并不完全首先想到的是子女,在子女这一层级出现了部分的隔断效应,即有可能直接选择请钟点工/保姆或入住养老院。
3.长期失能老人网络的“核心化”
老人会由于与他人建立联系而产生不同规模的网络,包括社会网络、支持网络和照料网络,从规模上看是逐渐缩小的,而从稳定性上看是逐渐增加的。当老人逐渐出现身体健康上的恶化而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依赖他人的时候,会出现网络规模缩小和稳定性变差的现象,最后社会网络和支持网络的规模逐渐缩小,作用逐渐减少甚至消失,最终可能只剩下照料网络,照料网络可能是家庭成员等各种非正式支持,也可能是自己购买或政府提供的各种正式支持,对长期失能老人的照料起着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可以说,长期失能老人的网络沿着社会网络——支持网络——照料网络逐渐萎缩的过程,是老人的网络“核心化”的过程,即最后留在网络中的都是对老人起着最关键和核心作用的力量。
(二)讨论
本文运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通过与国外长期失能老人照料模式的对比,发现中国城市地区与国外模式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鉴于当前中国城市地区老年人照料服务体系特别是长期照料服务体系还十分薄弱,因而特别需要针对老人特别是长期失能老人的具体需求和生活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来应对中国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口和老年服务需求。
收稿日期:2012-08-07
注释:
①数据来源:http://www.chinapop.gov.cn/xwzx/rkxw/201104/t20110428_356999.html。
②文中访谈对象均用代名,以J表示居住在家中,以Y表示居住在养老院,后面加上数字表示访谈时的顺序。限于篇幅,访谈资料的详细背景与获得过程未予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与笔者联系。
标签:失能老人论文; 社会支持论文; 中国武汉论文; 武汉生活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个案工作论文; 钟点工论文; 家庭成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