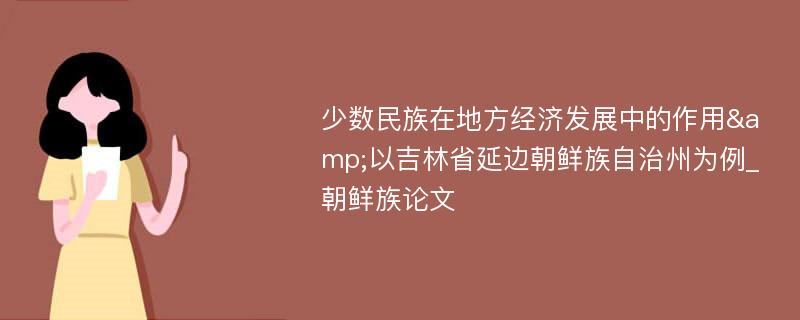
少数民族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论文,吉林省论文,个案论文,少数民族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经济改革使沿海地区的发展先行了一步,而居住着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边陲地区却不得不等待它们的发展机会。然而,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区并没有被动地等待自己时来运转;相反,它们从实际出发,制订了适合于本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遍布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网络的形成与运用,是这些发展战略中最为成功的模式。
延边是吉林省的一个朝鲜族自治州,与朝鲜和俄国接壤。改革以来,延边充分利用和开发自己的民族资源,利用民族关系网络,不断改善生活水准并吸引外资,从而推动了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具有本民族文化特征的发展动向。
传统的陷阱
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政策,民族政策有了新的变化。新的民族政策为朝鲜族人民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使他们在地方自治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加强,更加展现其民族的文化特征。然而,自治权的提高并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原因是朝鲜族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阻碍了他们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
奥利维尔(Bernard Vincent Olivier )在研究中国东北的朝鲜族时,认为许多朝鲜族人民没有抓住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给予的发展新机会:如生产专业化的商品,从事副业生产,进行技术革新等;相反,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有些朝鲜族农民反而变得无所事事了。究其原因,首先,朝鲜族人顽固地坚持水稻种植而不愿意从事其他商品经济活动,他们对经营副业生产及学习新的技能缺乏兴趣。(注:Olivier pp.197—198;
Che Zhejiu, "Lun
Yanbian
fazhan waixiangxing jingji" (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Yanbian'sOutward Oriented Economy),Yanbian daxue xuebao (YDX) 1 (1989) P.16”)其次,许多朝鲜族人深受重农轻商的儒家价值观的影响,他们缺乏商业精神,少有经营有方的企业人才;传统的朝鲜族农村社区较之汉族社区,因缺乏商业传统和商业经验,更未商品化。
如果认为儒家的价值观是一种精神包袱的话,那么朝鲜族传统中的另一个特点却使他们能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动。作为近代的一个倾向于流动的少数民族,他们并没有深深地把自己扎根于一个地方。历史上的朝鲜族人,当他们面临经济及其他困难时,往往会迅速地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流动。1982—1990年间,在东北的朝鲜族人有10%以上曾经为寻找新的就业机会而流动过;与此同时,居住在城市的朝鲜族人口数量增加了40%,城市对他们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而且,他们的流动目标并不局限于东北的城市,许多人往南方移动,迁往经济欣欣向荣的广东、海南、山东、 河北与江苏等沿海地区, 以致这些地区的朝鲜族人口在1982—1990年期间比原先增加了3倍多。当然, 由于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朝鲜族人数量原本就很少,现在出现的这种人口增加现象并不特别引人注意。例如1982年,山东省的朝鲜族人口只有939人,而广东省只有154人。在北京的7700朝鲜族人口中,占半数以上是在1990年代才进入北京的。(注:金光世、朴阳春(译音),《中国朝鲜族人口的发展、构成及其特点》,《朝鲜族研究论丛》第二辑,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金秉高(译音),《中国朝鲜族人口发展和分布变化的趋势》,《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在1980年代中期的“出国潮”中, 朝鲜族人也深受影响,一部分人把握住时机,果断地涌向边界。
朝鲜族人对向外流动的热中似乎与奥利维尔所称的朝鲜族人的保守态度存在矛盾关系。事实上,这种情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鲜族人的一个特点,即所谓“随大流”的特点。一旦有足够数量的社区在开发或经营某一特定项目获得成功之后,几乎所有的其他人便会紧随其后,争相仿效。他们有流动的传统,有超国界的民族联系,于是出国成为他们走出困境的一条新路,也为社会流动打开了新的大门。
延边的开放
对外开放政策在延边的实施,总的来看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区域经历的情况是相同的:在开始时,地方政府的改革步伐缓慢,而群众却热切地希望能尽快地跨越边界去争取经济发展的机会。与其他地方所不同的是,延边在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方面存在政治方面的阻力。
在刚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候,延边的企业和商社只能够与那些同中国有良好关系的国家进行接触。到1988年,延边已经与1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关系。(注:车哲玖(译音)主编,《吉林少数民族经济》,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对延边来说, 最自然的合作伙伴是北朝鲜,意识形态和民族方面的纽带促使双方都愿意建立合作的关系。双方在官方层次上的经济合作,带动了民间的经济联系活动。在1980年代,前往北朝鲜探亲的延边朝鲜族人持续增加,虽然朝鲜当局视生意买卖为非法,但探亲者们仍设法零卖一些随身带去的商品以支付旅行费用。由于朝鲜的货币不能与人民币兑换,探亲者不得不用手头上的朝鲜货币在当地购买朝鲜商品,再带回中国后卖掉。那些对中朝两国的市场行情熟悉的人通常能因此赚到好些钱,这成为许多延边朝鲜族家庭收入的一种来源。
然而,延边的商人却不能与在经济上极具吸引力的韩国建立贸易和交往关系。自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到1974年中韩开通邮政与电信业务之前,中韩两国之间的直接接触始终处于冻结状态。1974年后,中国允许少数人去韩国探亲,但在好几年时间里被批准的人数极为有限。有些富有心计的人很快就意识到,诸如中药材之类的东西在韩国拥有巨大的市场,而将韩国商品带回中国出售更是有利可图。根据一些报道,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来自韩国的服装、收录音机、卡拉OK播放机等东西成了抢手货,这反映了延边和韩国间的非官方贸易在1980年代中期以来就已经持续发展了。
在中国和韩国既没有政治关系也没有正式商务关系的情况下,大部分贸易不得不通过第三者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贸易关系不是在东北的朝鲜族居住区进行的,而是由沿海省份那些享有对外贸易特权的商务机构引导的。中韩间的直接贸易和韩资引进在1998年成为现实,然而,延边的工商企业界仍未能从中韩关系变化中得到好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中央政府的政策限制,地方领导人在对外关系方面也一直采取裹足不前的保守态度。当公众在发展对韩贸易关系方面的热情日益高涨之际,他们既妒忌沿海开放地区能先行一步,又为自身所受束缚而产生一种说不清楚的挫折感觉。在延边,正是当地的朝鲜族人民突破了限制,用各种方式开展了对韩国的贸易。
1991年是延边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年。中央政府重新评估了与延边有关的一些政策和问题。1991年中韩在对方首都互设了贸易办事处,同时根据图们江地区发展计划,在联合国发展署的支持下召开了东北亚经济合作研讨会;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事态的出现都使延边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延边开始由一个封闭的后院向一个国际合作的中心发展。这些变化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国际关系的取向上,对韩国的政策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央政府或许曾指令延边要迅速与韩国的企业建立关系,以吸引对图们江地区发展项目的投资。因此,延边的官员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中央的推动下前进的,不管心中是否情愿,他们开始与韩国的投资者和商人建立关系了。同时,中央政府还提议使延边成为民族自治区的一个发展样板(注:金中国,《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朝鲜族与国外朝鲜民族关系问题》,见孙云来、沙云忠(译音)主编,《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与对策》,北京,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从而促使延边必须在改革开放中取得最好的成绩。
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
延边把促进对外经济联系列入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其一系列活动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激活当地朝鲜族人民的网络联系,使之变得生气勃勃起来。
政府公开鼓励朝鲜族人民出国探亲,并争取与国外的亲戚建立业务联系。中韩建交后不久,官方的《延边日报》就发表文章,强调这种亲戚和家庭关系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注:《做好边境贸易这篇大文章》,《延边日报》1992年8月28日。)。 延边当地的研究者也对有这种亲戚关系的家庭数量和“质量”进行了调查,发现有海外关系的家庭占了延边家庭总数的23%, 其中有将近5 万户家庭有亲戚居住在北朝鲜, 有3799户的家庭有亲戚在韩国,还有442 户家庭有亲戚在朝鲜半岛以外的其他国家。这份调查不仅统计了有海外关系的家庭数量,而且这些亲戚在海外所从事的职业情况也得到了反映。(注:金中国,《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朝鲜族与国外朝鲜民族关系问题》,见孙云来、沙云忠(译音)主编,《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与对策》,北京,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根据调查, 占七成左右的海外亲戚从事工商业活动,他们的经营规模估计达到了100万美元, 这无疑对推动延边朝鲜族人利用这种关系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当地还提出了诸如“探亲带项目,通信引项目”之类的口号,反映了政府对加强国际间的亲属网络联系的重视。
在官方推动的各种促进引资的活动中,十分重视利用朝鲜文化作媒介,其中有些以文化为名进行的活动具有纯粹的经济意图,也有一些活动旨在使海外的朝鲜人看到高度凝聚的中国朝鲜族社区的力量,从而促进建立互惠合作的伙伴关系。1992年8月, 延边州政府在北京举办了朝鲜族文化节,就是这类文化活动的一个成功范例。当时,组织委员会邀请的海外宾客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具有朝鲜族背景的海外来宾有500多人,他们在文化节期间与延边的企业、公司进行了业务谈判, 并达成了40多项协议。这种文化节的组织理念也从“文艺搭台、经贸唱戏”的口号中得到了体现(注:金中国,《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朝鲜族与国外朝鲜民族关系问题》,见孙云来、沙云忠(译音)主编,《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与对策》,北京,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
但是,在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中,朝鲜族人并不处于最被重视的地位。延边州政府认为朝鲜族人的海外关系是一种有用的资源,但并不是当地吸引外资的主要资源。在探讨延边经济发展战略的有关文章和书籍中,研究者对本地朝鲜族人的作用往往并不十分重视,联合国发展署的图们江项目对当地朝鲜族人的作用也没有作任何明确的定位。
为了激活朝鲜族人的联系网络,促进海外朝鲜族人的投资和贸易,地方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绝大多数的举措与活动并不是在官方经济互动的“高层次”领域上进行的。当地朝鲜族人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的、实际的经济目标。他们利用已存在的社会网络,或建立新的对外关系,目的只是为了迅速赚钱,扩大社会声誉,而他们的朝鲜族背景则是赢得机会的关键。
基层的战略
中国在1980年代中期放宽了出国旅行的限制,刺激了朝鲜族人的“出国热”。最先对朝鲜族人产生吸引力的是北朝鲜和前苏联。但朝鲜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到那里去找活干是难以获得利益的。1987年后,当通过正式途径向苏联远东地区输出劳动力刚刚开始的时候,有数千中国的汉族人和朝鲜族人蜂拥而去,因为那里不仅很接近延边,而且还严重缺乏劳动力。由于在苏联远东地区已有许多朝鲜人,所以前往做小生意的人可以很容易地在亲戚朋友家里住下来。但是,在苏联远东地区做买卖只有小利可图,并且有各种风险的威胁。后来,随着前往韩国成为可能,“流动的”朝鲜族人便设法前往韩国;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中国的朝鲜族人前往韩国成为热潮。
1992年中国朝鲜族人前往韩国的人数有了明显的上升。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国与韩国在这一年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方便了人们去韩国探亲访问;其次是随着中国工人和生意人在远东的增多,俄国人对他们的态度变得越来越不友好, 当地的环境对中国人也越来越恶劣了(注:Pavel A.Minakir,"Chinese Immigrat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Regional,National,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in:Jeremy R Azrael & Emil A.Payin(eds)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Implications for Migration.CF—130—CRES,Rand,1996 〔 Online 〕 . Available: http: //www. rand.org/publications/CF/CF—130/〔1997,April 13〕pp.93—94 )。 1992年,留在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朝鲜族人尚有20000人,到1994 年只剩下2000人了,而前往韩国的人数却达到了20000人次(注:Rim K-m- suk,"Chungguk Chos-njokt- r- i' Ch'ulguk Y-r' e Taehan Sago."(Considerations on the "Leave -the - Country - Fever" of the Korean Chinese National Minority),in :Kim Dong - hwa & Kim S-ng-ch' - 1 & Yi Hong - u (main eds)Chungguk Chos-n Munhwa Hy-nhwang Y-ngu.(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Korean Chinese Culture) Harbin:Heilongjiang chaoxian minzu chubanshe,1996,p.139-140.)。韩国的报纸称,1992年在韩国被非法雇佣的中国朝鲜族人有23000人;1994年,这一数字超过了40000人,他们在韩国成为人数最多的非法外国劳工群体(注:Choe Seung -
chul:"Government,Lawmakers Create Measures for Ethnic Koreans in China",Korea Herald 14.12.1996.)。据韩国司法部统计,到1994年3月, 已经有超过12万人次的中国朝鲜族人到过韩国。(注:金中国,《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朝鲜族与国外朝鲜民族关系问题》,见孙云来、沙云忠(译音)主编,《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与对策》,北京,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
为了获得前往韩国的签证,申请人必须要有亲戚的邀请信,签证的有效期通常被限定为30天。尽管有这一系列的严格限制,前往韩国的合法或非法的旅行者人数仍然继续增加。有些不能得到签证的朝鲜族人,为达到目的而不得不在延边寻找韩国人建立关系。在延吉的韩国记者报道说,当地有许多朝鲜族人想与从韩国来的旅游者、学生或商人结交朋友,有些人请求他们帮助在韩国介绍工作,还有些人攀认他们为“亲戚”,也有人在黑市用钱购买签证,或用钱请人介绍工作。于是,有许多韩国的私人职业介绍所派人进入中国的朝鲜族聚居区域,向当地人许诺工作安排;也有一些韩国婚姻中介机构以婚姻介绍和签证为诱饵。很显然,这些机构是不可靠的。在1995到1996年期间,有许多骗子和欺诈事件被揭露,上当受骗的家庭达10400多户,这些家庭多数居住在中国东北, 他们因为轻信中介人有关签证、工作或婚姻的许诺而耗费了所有积蓄;据估计,被诈骗的钱约合4100万美元,约有600 名韩国人被涉嫌到这些诈骗案中(注:"Action Urged Against Fraud Victimizing Korean -Chinese",Korea Herald 19.11.1996;"Crackdown Starts on Korean -Chinese Fraud Cases",Korca Herald 3.12,1996; "Group Starts Drive to Aid Ethnic Fraud Victims",Korea Herald 5.12.1996)。到1996年深秋,多数诈骗案已经大白天下,有很多报纸报道了东北三省朝鲜族人的愤怒。韩国国内的舆论也迫使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以保护中国朝鲜族人的利益。韩国政府在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采取了若干措施,以重塑韩国人对中国朝鲜族人的形象,韩国政府还实施了其他一系列特殊措施,并与中国就控制非法入境问题进行合作。
中国朝鲜族人的“出国热”与中国人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现象是同步出现的。成千百万的中国农民涌向城市去寻找工作机会,尤其以涌向沿海地区为最多。同样,中国的劳动力输出也增加了,人们根据心目中的富裕地方确定自己该奔赴何方。对延边朝鲜族人来说,他们的流动是根据资源的可能性而定的,他们在流动自由中得到了许多实际好处,在中国各民族中,曾经出过国的朝鲜族人数比例处于较高的水平,有1/4的延边朝鲜族家庭收到过其在国外工作的家人汇款;许多家庭还安装了先进的电信通讯设备,移动电话、传真机及因特网,频繁地与国外进行业务通讯和个人联系。
然而,并不是所有朝鲜族人都从这些新机会中得到好处。一方面,有些社会弱者不得不用一些可疑的、甚至非法的办法去牟取财富;另一方面,有一些打工者则从事着受剥削的、肮脏、困难、危险的工作。
少数民族资源的经济意义
要评估少数民族资源的直接经济意义是困难的。在对外贸易和投资的统计中,投资者或商社、企业的民族背景并不能得到反映,一般情况下只列出了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因此,人们并不知道由朝鲜族人所控制的日本投资、加拿大投资所占的比重;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外国在中国朝鲜族区域的投资决定是与该地的民族背景相联系的;同样,中国朝鲜族人在国外工作期间到底挣了多少钱也是难以估计的,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在国外做生意。
金中国是一名延边的朝鲜族研究人员,他曾计算过在延边的“韩国企业”数量,根据统计,1992年延边共有三资企业212家,其中131家有国外的朝鲜人资本投入,来自韩国的资本投入占了最重要的部分,达72家,有北朝鲜资本投入的为10家,其余49家企业则由在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朝鲜人部分投资或全部投资兴建。(注:金中国,《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朝鲜族与国外朝鲜民族关系问题》,见孙云来、沙云忠(译音)主编,《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与对策》,北京,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
1994年是韩国对延边投资额上升具有意义的一年。从1993到1994年底,韩国在延边投资的企业从72家增加为321家, 绝大多数是小型及中等规模的企业。对延边投资的第二次飞跃出现在1996—1997年,获得韩国投资的企业上升为393家,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许多投资为大型项目;在此期间,实际到位使用的外国投资比前一阶段增加了2倍;到1997 年底,韩国投资高居延边全部外国投资之首,占外资总数的53%。(注:China's Tumen River Area.Investment Guide.Yanbian/Hunchun-98.UNIDO sponsored report,1998,pp.5—7)
1990年代初,延边吸收的外资在吉林省内只占微弱的份额,到1996年,延边吸引的外资已占吉林全省外资量的30%;1997年,随着延边人口在全省的比重变化,延边吸收外资比重又减少为23.5%。珲春市接受的外资占延边州总数的四分之一,为9800万美元,此投资的大部分用于对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开发。然而与吉林省的其他经济开发区相比,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的状况尚不理想。 例如,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到1997年已登记的外国投资价值为12200万美元, 在吉林省的绝大多数韩国投资是直接投到长春市。此外,当具体地考察韩国在中国的投资地点时,情况更是令人不安。韩国对中国投资的大部分是在山东省和辽宁省,到1996年9月底,山东省位居韩国在华投资的榜首,为75400万美元,其次是辽宁省, 为29800 万美元。 (注:Changchun
Economic
&Technological Dvelopment Zone 〔Online 〕. Available:http://www.chinarainbow.com/english/cckfq/kai.htm 〔1999,March 8〕.)
延边自治州与韩国之间的官方贸易数量仍然不多,根据官方统计,从1990到1994年,延边与北朝鲜之间开展边境贸易的价值高于在正常信用证与现金交易下的外贸价值。与北朝鲜的易货贸易在1993年达到了高峰。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为在1990年代初,延边政府虽然已经与韩国建立了新的经济联系,但北朝鲜仍是其亲密的盟友,韩国还没有成为吉林省的最大贸易伙伴。到1993年,吉林省的商品主要仍是向香港、北朝鲜、日本和俄国出口。总的来说,延边所分担的吉林省对外贸易的量仍然是低的,不到总数的10%。可是,1990年代初吉林省的边境贸易量却几乎有一半是由延边分担的。
但是,有一些不完全的证据表明,延边的朝鲜族人民通过民族联系的网络,推进了国外朝鲜人投资者在延边的业务。首先,民族的亲合力促使一些投资者选择延边为投资目标。一个韩国商人曾对我说,他选择延边进行投资,主要是当地朝鲜族人与他“有共同的民族认同”。1980年代规划的中国东北发展蓝图显示,韩国企业界对支持中国朝鲜族聚集区经济发展有浓厚的兴趣。其次,相同的民族背景是韩国商人在延边投资的重要原因。由于双方有相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民族价值观,所以在商贸交往的每一阶段都比较容易接触,所谓“跨文化的交流”障碍对他们之间的业务谈判并不构成障碍,企业中的雇员可以不经过翻译便明白自己的职责,并且可以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管理。某些曾经对中韩贸易问题进行过讨论的韩国人认为,延边的朝鲜族人对韩国投资者来说是有利的资源。也有人认为,文化接近已经对韩国的中小企业主向中国朝鲜族地区投资产生了刺激,如果他们投资于其他国家,将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投资指南对这一理念也表示赞同,它断言韩国的投资受到了民族、语言和市场等因素的推动。
延边是好些著名的中国朝鲜族商人的家乡,这些商人有广泛的国际商业联系。然而,延边州政府吸引人才的努力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尽管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联系网络十分活跃,其能量却并不必然地满足进行大规模国际商贸的需要。如同奥利维尔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朝鲜族人的生活背景是农村,他们并不具有经商的传统,绝大多数想要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并没有长远的目标,而只想在短期内尽快致富,他们认为投资长远项目是得不偿失的。
到1990年代中期,延边朝鲜族人与北朝鲜的紧密联系仍是进一步与韩国发展贸易的障碍。据对延边一位朝鲜族人的访问,他说那些想要保持同北朝鲜做生意的人,通常是一些找不到韩国合作伙伴的人。虽然与北朝鲜的贸易已越来越无利可图了,仍有许多延边的朝鲜族商人为了保持与北朝鲜公司的伙伴关系而避免同韩国人接触。可见,“左的影响”仍是进一步扩大与韩国经济贸易联系的阻力。
尽管延边自治州已经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中国其他地区却吸引了绝大多数的韩国投资。据韩国方面在1996年所作的中韩贸易研究,在没有提到图门江地区的情况下,认为长春市所吸引的韩国投资在吉林省占了大头。最受韩国投资者欢迎的地方是山东省和辽东半岛。辽东半岛与韩国相邻,两地各位于黄海的两岸。到目前为止,虽然延边朝鲜族人民所构筑的经济网络在吸引外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实际到位的外资并未使延边州政府和企业界人士感到满意。
朝鲜族网络对于促进延边的家庭经济似乎比对企业界的推动更具有意义。朝鲜族人之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关系以及新建立的联系,使延边朝鲜族家庭的收入得到迅速增加;那些在韩国工作的家庭成员,即使有的人是非法打工,他们的收入对其家庭而言是一条特别容易改善生活的捷径。
要估计延边正式对外输出的劳务情况是有一定困难的。据有些文章研究,自1989到1993 年, 延边人与外国企业正式签订的劳务合同约有7000个。由于在此期间,输出劳动力中的一部分人在国外同时被雇于多家企业,延边居民实际在国外受雇的人数要少于7000人。一位研究人员声称,90%以上在国外工作的延边人是朝鲜族人。(注:金中国,《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朝鲜族与国外朝鲜民族关系问题》,见孙云来、沙云忠(译音)主编,《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与对策》,北京,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在这4年间,延边通过正式的劳动输出而收到的汇款达1400万美元,这就意味着每份劳务合同的平均价值约为2000美元。1992年前,未记录的中国朝鲜族劳动力在国外的人数尚未被估计过。1992年, 一项估计认为在韩国约有23000名中国朝鲜族非法劳工,假如每人每月的打工收入最低为1000美元的话,那么他们的总收入至少是每月2300万美元。以此为基础进行计算,1994年在韩国有4万名未登记的中国朝鲜族人, 并不是所有人的劳务收入都能寄回家乡的,虽然根据有关资料对他们在国外打工时间的长短及汇款回家的数量的多少进行估计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但与1994年延边的实际国外投资资本积累为1亿1300万美元相比较,毫无疑问的是, 这些人寄回家的钱构成延边重要的外汇收入。
对非正式民间贸易的价值进行估计,同样是不准确的。据当地政府主管外贸部门的计算,每年延边与北朝鲜之间的民间贸易价值有可能超过1200万美元,与韩国之间的民间贸易价值则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尚不得而知。
1995年,延边自治州的年人均消费量为2803元人民币,在吉林省地市级的行政区域中为最高。与吉林省其他县镇的城镇人口相比,延边的城镇人口花起钱来就简直不当作一回事,他们平均每年每人消费4589元,这一数字比吉林全省城镇人口的年平均消费量要高出800多元, 在全省排第二位。(注:《吉林省统计年鉴199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第198—199页,第267页。)由此可以假定, 延边人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消费能力,很可能是受到其外汇收入的支撑。所以,从收入的层面上看,延边朝鲜族社区因其民族背景而在改革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
结论
在1980年代,延边的朝鲜族人民也被卷入到了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改革的洪流之中,他们在改革进程中不得不寻找新的发展路子,重新获得一个民族的幸福地位。国家对人口流动及出国旅行政策的放宽,为朝鲜族人提供了能改善生活水平、并具有本民族文化特征的发展手段。延边朝鲜族人继承了本民族喜好流动的传统,在其邻近的周边国家、尤其是在南北朝鲜获得了各种可赖以营生的发展资源。他们为获得新的财富资源,利用了原有的民族联系,构建了新的联系网络。随着延边自治州在中央政府的鼓励下参与到国际贸易业务之中,当地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扩展朝鲜族人的民族网络关系,探索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促进本地经济。例如,延边州政府为了吸引来自朝鲜半岛以及海外朝鲜工商界的投资,组织以朝鲜族为内容的国际商贸洽谈活动。直到199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的关系和网络已经在基层构成。这种关系主要地是以迅速争取经济利益为目标,而不在乎建立起跨国家的长远而持久的贸易关系。虽然延边朝鲜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改革开放中有了显著的提高,但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也与各种社会问题相伴随:已经过时的传统习俗又死灰复燃,分配不均问题日益严重,犯罪率上升;与韩国的密切联系也对延边朝鲜族人的民族认同产生了影响。
从基层开始形成的朝鲜族人联系网络的运作似乎正处于转变过程之中。首先,韩国的各种骗子乘中国改革开放之机浑水摸鱼,使许多朝鲜族人因被诈骗而在经济财产上蒙受了巨大损失,从而导致他们对韩国人的认同发生了危机,许多朝鲜族人已经开始反思自己一度对韩国的迷恋。其次,延边朝鲜族人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后,也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问题(比如生活方式方面),于是批评的声音已经在延边的朝鲜族人中回响。第三,作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后果,韩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资源已经明显地萎缩了:由于韩国不再可能象过去那样向流入的中国朝鲜族人提供工作的机会,延边朝鲜族人为保持住现有的生活标准,不得不寻找新的营生手段和发展机遇。北朝鲜在未来最终可能实行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政策,将为中国的朝鲜族人提供意想不到的新的挣钱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