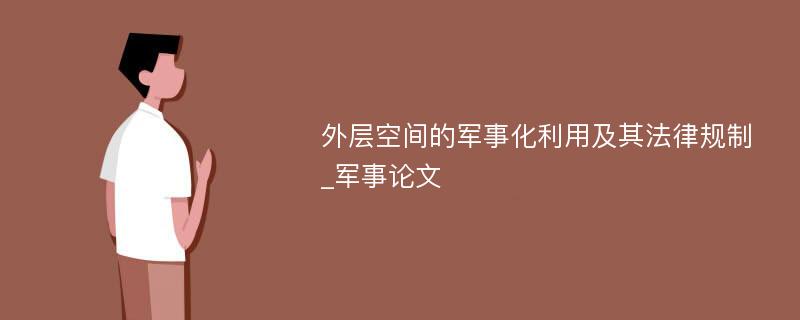
外层空间的军事化利用及其法律规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事化论文,外层论文,规制论文,法律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1月11日,我国进行了一次外层空间(以下简称外空)试验,成功地用一枚导弹摧毁了一颗500英里高轨道上的老化气象卫星。这是自1985年美国用导弹摧毁一颗在轨卫星以来,世界上的第一次此类试验。① 虽然这次导弹打击的对象是我国的一颗老化气象卫星,但此消息一公开,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国对航空技术外空利用问题以及外空军事化利用问题的关注,也引起了学界对外空军事化的国际法律规制问题的探讨。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苏联就已经将航天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了。美国和苏联分别于1959年和1962年发射了他们的第一颗军用照相侦察卫星,从而使外空成为冷战时期美、苏竞争的重要领域。此后,美、苏两国围绕研制和部署各类军用卫星、外空武器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外空已经成为未来战争的制高点,可以说,“未来战争的成败将取决于各方所具有的空间实力”。② 因此,在21世纪,外空对世界各国而言,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现行的国际法虽然确立了“和平探测与利用外空原则”,但对于目前外空军事化日益加剧的发展趋势仍缺乏有力的约束。因此,国际社会应在联合国框架下,对和平探测与利用外空的国际法律制度作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一、外空的军事化利用
外空的军事化利用是指以军事为目的或具有军事服务性质的各种利用或穿越外空或直接在外空发展和部署外空武器的活动。外空的军事化利用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利用人造卫星支持和增强以地球为基地的武器系统和陆海空军的作战效能;二是发展和部署以外空为基地的武器系统或从陆海空发射穿越外空的武器,以打击或摧毁对方以地球和外空为基地的各种武器或使其丧失正常的军事功能。因此,美国1959年在外空部署第一颗军用卫星就已经标志着外空军事化的开始。20世纪末,随着美国宣布部署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及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外空武器化的趋势也初露端倪,“武器进入外空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③ 当前,外空从军事化向武器化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遥感卫星与通讯卫星的军事化利用和反卫星武器的发展
在人类进入外空初期,各空间大国主要通过在外空部署军用卫星来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到目前为止,各主要国家已经建立起了比较齐备的军用卫星体系,军用卫星已成为各国先进武器指挥系统不可或缺的神经中枢。据统计,1999—2008年的10年间,全世界将发射308颗军用卫星,占此期间发射的全部卫星总数的1/5。④ 当然,这也只是一个估算的数字,因为还有很多卫星具有军事和商业双重用途,它们也可以直接被用来执行军事任务。目前用于军事目的的卫星系统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遥感卫星,如美国于1959年发射的科罗纳间谍卫星,它可以用来拍摄战略性目标,然后通过电影返回舱的方式将数据传送到地球,用于战略分析。另一类是通讯卫星,如意大利的情报通讯和预警系统,该系统被放置在地球静止轨道上,由一颗卫星、管理控制中心和海基、空基地面终端组成,可以覆盖地球表面的广阔领域,在国家领土上进行声音、图像和数据传递。21世纪初发生的几次局部战争中,军用卫星通过战场态势感知、目标定位、攻击引导等方式参与作战,成为重要的战争支援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空军事化早已经成为事实。⑤ 军用卫星系统成为现代作战指挥和战略武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带来空间防御问题,反卫星武器随之而生。反卫星武器是指用于击毁离地面几百公里以上的轨道卫星或使其丧失正常功能的空间防御武器,主要包括陆基反卫星武器和天基反卫星武器。陆基反卫星武器是指从陆地、水面(水下)和近地空中发射的拦截器。天基反卫星武器是指从卫星或其他航天器上发射的空间杀伤拦截器。从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起,美国陆海空三军先后研制和试验了采用核弹头、动能拦截弹头的共轨式、直接上升式反卫星武器和激光反卫星武器,共进行了30多次试验。⑥ 当前,反卫星武器已经达到了实战水平。
(二)从陆海空发射穿越外空武器的发展与部署
尽管《反弹道导弹条约》对进攻性战略武器进行了限制,如该条约第5条规定禁止发展、试验与部署海基、陆基、天基和移动反弹道导弹体系,但对陆基雷达、拦截导弹并没有作禁止性规定,因此,弹道导弹防御武器(BMD)等陆基武器越来越受到有关国家的青睐。目前,一些技术发达的国家正在发展自己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如以色列的箭系统(ARROW)、俄罗斯的S300/400以及由美国与西欧联合研发的中程扩大防御系统(MEADS)等。1999年7月2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了《国家导弹防御法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轰动。该法案允许美国一旦在技术上达到要求,就可以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以防止美国领土受到故意的或偶然的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N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陆基NMD反导弹防御系统、海基NMD反导弹防御系统、天基反导弹激光武器等都属于空间武器,这些武器的研发、部署已经付诸行动。在美国的引导下,日本以及欧洲的部分国家也已经开始部署和建立导弹防御系统。⑦
(三)以外空为基地的武器系统的发展与部署
尽管《反弹道导弹条约》及《外空条约》对于以外空为基地的武器部署予以明确禁止,但事实上,美、俄等国已经部署了相当数量的外空武器。如美国的反导弹防御系统,有的部署于外空,或以外空目标为打击对象;有的则以外空为基地,为地面武器系统提供目标信息和导引。随着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新一轮外空军备竞赛也是风雨欲来,各国加紧了外空武器的研制与部署。以美国为例,虽然1996年克林顿政府制定了一项新的太空政策,强调“和平利用太空”,即“克制使用间谍卫星支持军事行动,太空武器控制和太空武器不扩散”。⑧ 但2001年1月的“拉姆斯菲尔德报告”建议加强美国的空间实力,部署太空武器系统,明确否定了“和平利用太空”政策。⑨ 随后,美国开始不断研讨与完善太空战的理论和原则。2003年美国空军发布《2020年远景规划》,提出“全谱优势”思想,认为只有控制外空才能控制地球。⑩ 2004年8月,美国空军又提出了一个名为“全球打击”的新战略,强调美军要在太空“自由攻击”敌人并免于受到敌人攻击,必须装备能携带精确打击武器的军用航天飞机,能在45分钟内对全球的任何目标实施毁灭性的打击。(11) 2005年3月,拉姆斯菲尔德签署新的《国防战略》,指出“空间控制”就是“确保自身空间行动的自由,同时防止对手具备这种自由”的能力,进一步明确了美国今后太空军事化的发展方向。(12) 2006年10月6日,布什政府公布了最新的“国家太空政策”。这标志着美国的空间政策开始转向确保美国太空安全和绝对自由,并向着遏制别国空间开发、维持美国在外空领先地位的方向发展。(13)
二、目前国际立法对外空军事化利用的法律规制
现行的国际法主要是通过《外空原则宣言》、《外空条约》、《月球协定》、《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以下简称《登记公约》)、《反弹道导弹条约》、(14) 《禁止在大气层、外空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以下简称《禁止核试验条约》)等一系列的国际条约与国际法律文件来对各国的外空军事化利用行为进行直接法律规制的。
1963年《外空原则宣言》不仅确认和平探索与利用外空关系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且规定各国在探索与利用外空时应该遵守的九项原则涉及与外空活动有关的所有重要方面。尽管这些原则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却“获得了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一致赞同,实际上奠定了国际外空法原则的基础”。(15) 《外空原则宣言》为以后的国际空间立法提供了根本的原则性指导。
1967年《外空条约》作为国际空间立法的宪法性文件,对外空的军事化利用作出了明确的限制性规定。该条约第4条第1款规定各缔约国“承诺不在环地球的轨道上放置任何载有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种类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不在天体上装置这种武器,也不以任何方式在外空设置这种武器”。第4条第2款规定各缔约国“应专为和平目的使用月球和其他天体。禁止在天体上建立军事基地、军事设施和工事;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和进行军事演习。不禁止为了科学研究或任何其他和平目的而使用军事人员。为和平探索月球与其他天体所必需的任何装置或设备,也不在禁止之列”。从《外空条约》对外空军事化利用的规制来看,条约禁止在外空放置和设置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种类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禁止在天体上建立军事基地、军事设施和工事,禁止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和进行军事演习。
1979年《月球协定》在坚持《外空原则宣言》和《外空条约》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军事利用月球和其他天体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月球协定》第2条规定:“月球上的一切活动,包括其探索和利用在内,应按照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先前的规定。”第3条第1款进一步规定:“月球应供全体缔约国专为和平目的而加以利用。”为此,其第3条规定了4项禁止令:(1)不得在月球上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或从事任何其他敌对行为或以敌对行为相威胁;(2)禁止利用月球对地球、月球、宇航器或人造外空物体上的人员使用武力或任何武力威胁;(3)不得在绕月球的轨道上放置载有核武器或其他种类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或在月球或月球内放置或使用此类武器;(4)禁止在月球上建立军事基地、军事设施及防御工事,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及举行军事演习。根据《月球协定》之规定,“月球”一词不仅指月球本身,还包括环绕月球的轨道或其他飞向或围绕月球的轨道;有关月球的规定也不仅适用于月球,还适用于太阳系内除地球以外的其他天体。可见,对于月球军事化的规制,《月球协定》比《外空条约》更彻底、更严格。但遗憾的是,美国等空间大国并没有签署该协定,这就使该协定的影响大打折扣。
1975年《登记公约》对空间物体实行强制性的登记制度,提高了各国空间活动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对于防止或抑制外空军事化具有积极作用。《外空条约》明文禁止在外空携带、配置和安放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公开的登记制度可以对此类行为进行监督与核查。
此外,有关限制或制裁外空军备的多边和双边条约也对外空军事化利用进行了相关的规制。例如,1963年《禁止核试验条约》对外空武器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它规定各国应保证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大气层、外空、水下(包括领海或公海)三个环境内,禁止、防止和不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其他任何核爆炸;如一国在任何其他环境中进行的核爆炸所引起的放射性尘埃出现于其管辖或控制的领土范围以外时,这种爆炸亦应禁止。1977年《禁止为军事目的或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也对限制外空武器的使用作出了规定。它规定,各国应承允不为军事或敌对目的使用具有广泛、持久或严重后果的改变环境的技术。这里的“改变环境的技术”是指通过蓄意操纵自然过程改变地球(包括其生物区、岩石圈、地水层和大气层)或外空的动态、组成或结构的技术。但由于该条约只规定了禁止使用此类技术,没有规定禁止研究、发展和实验此类技术,而致使该条约在实际中难于执行。
三、防止外空军事化利用的现行国际法面临的严重挑战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现行防止外空军事化、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的国际法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面对外空军事化的现实及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的趋势,有关防止外空军事化、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的现行国际法律制度的不充分性与不明确性日趋明显。首先,现行国际空间法似乎并不完全禁止外空的军事化利用。例如,《外空条约》仅仅对在外空发展与部署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种类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作出了禁止性规定,并不明文禁止在外空发展与部署除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外的其他武器,而且条约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一词也没有进行明确界定。其次,现行国际法对军用卫星没有作出任何限制性的明确规定。就现状而言,军用卫星还受到某些多边或双边条约的保护。例如,军用卫星的无线电业务和通信是按照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定进行登记和运行的,《国际电信公约》第35条规定各国的无线电业务和通信不得受到有害干扰,据此,军用卫星也受《国际电信公约》的保护。同时,美、俄两国之间缔结的若干双边协议也对军用卫星给予了保护。而且,若军用卫星未经登记且双方没有缔结有关协议时,一旦一方的军用卫星受到对方通信干扰,则无法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这无疑为美、俄发展反卫星武器提供了法律漏洞。再次,尽管现行国际法对于月球和其他天体主张全部非军事化,禁止各国以任何借口进行军事利用,然而对于禁止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建立军事基地、军事设施和工事,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和军事演习的规定只是作了重点列举,对于任何其他与军事有关的活动却没有予以禁止,而且既未禁止使用军事人员进行科学研究或把军事人员用于任何其他和平目的,也未禁止为和平探索活动使用必需的任何器材设备。(16) 最后,虽然现行国际法禁止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建立军事基地、军事设施和工事,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和军事演习,但似乎并不禁止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以外的外空进行此类活动。
第二,现行防止外空军事化、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的国际法律制度正面临各国有关空间活动的国内立法及政策的侵蚀。现行防止外空军事化、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的国际法律制度的不充分性与不明确性,为有关国家外空军事化甚至向武器化方向发展提供了振振有词的辩护理由,为他们随意曲解以“和平目的”利用外空提供了机会,这些空间强国制定的有关开发和利用外空的国家政策正逐步侵蚀着现行的相关国际空间法律制度。在“和平探测与利用外空原则”建立之初,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目的”的解释就存在两种争议。以中国、苏联为代表的国家认为,“和平目的”是指非军事化利用太空,即禁止在外空从事一切军事活动,不论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的。(17)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空间强国则认为,“和平目的”仅限于排除侵略性的军事化利用外空,并不排除非侵略性的军事目的的利用外空的情形。由于《外空条约》规定“各国在进行探索和利用外空的各种活动方面,应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而且《联合国宪章》也没有绝对禁止一切军事活动,因此,他们主张将外空军事活动分为“可允许的”和“不允许的”两类,非侵略性的军事化利用外空属于“可允许的”。甚至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凡有关国际空间法没有禁止的军事活动,都属于“为和平目的”利用外空的范畴。(18) 在此理论支持下,美国等西方空间强国纷纷制定各自的空间发展计划,将国家的空间活动用于军事目的,甚至准备在外空部署空间武器。如美国在1983年就提出“战略防御计划”,接着在1989年提出“智能卵石计划”,2001年提出TMD和NMD,2004年提出“空间探索计划”,2006年提出“太空作战计划”等,这些空间发展政策皆定位于“防御性”与“非侵略性”,使现行国际空间法的“和平探测与利用外空原则”几乎形同虚设!
实际上,深入分析现行国际空间法的立法旨意,我们不难理解“和平目的”利用外空不仅排除侵略性的利用外空,也排除任何为军事目的的利用外空。“和平目的”利用外空就是要求外空非军事化。人类探索与利用外空不能用于军事目的,更不能用于侵略目的,其理由如下:首先,如果现行国际空间法只是期望禁止侵略性利用外空的行为,那么整个国际空间法律体系就没有必要多次强调为“和平目的”;既然现行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已经明确规定“不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那么各国在利用外空时本就应遵守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其次,《月球协定》通过禁止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建立军事基地、军事设施及防御工事,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及举行军事演习,来进一步补充“和平目的”,这已经表明现行国际空间法的“和平目的”不仅限于排除侵略性利用外空的行为,也排除非侵略性的军事防御与军事试验等行为。最后,《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与《南极条约》对“和平目的”的解释,进一步表明“和平目的”是与禁止“任何军事性质的措施”、“有利于军事目的”相联系而使用的。(19)
第三,外空军事化利用的国际实践对现行防止外空军事化、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的国际法律制度构成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人类探测与利用外空的实践表明,外空军事化已经成为现实,且正朝着武器化方向发展。国际社会探测与利用外空的实践不仅严重冲击“和平探测与利用外空原则”,也对现行的国际空间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现行的防止外空军事化、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的国际空间法律制度及其监督机制若不能尽快完善与发展,外空军事化将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外空武器化局面,外空军备竞赛也将无法遏制,现行的防止外空军事化、武器化的法律制度将面临崩溃,国际和平与安全将面临新的威胁。
四、防止外空军事化加剧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完善及中国的对策
面对外空军事化及外空军备竞赛的现实,为真正实现外空的和平利用,防止外空进一步军事化、武器化,阻止新一轮外空军备竞赛,国际社会必须在联合国框架下完善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加强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协调能力。
(一)防止外空进一步军事化的国际立法亟待完善
从外空军事化利用的现状来看,目前国际法律对遥感卫星与通讯卫星的民用目的与军用目的还难以明确界定,且对卫星用于军用目的缺乏明确法律规制。现行国际法对于卫星进行了保护性规定,如《国际电信公约》第35条第1款规定:“所有站台的设立和运转方式,不论其目的如何,都不得对其他成员国或被承认的私人运转机构或其他正式认可的从事无线电业务的运转机构依照无线电规则而运转的无线电业务和通信,进行有害干扰……”由于军用卫星的无线电业务和通信也是依照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定进行登记和运行的,因此,军用卫星也依照第35条的规定不受有害干扰。同时,1971年《美苏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的协定》和1973年《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协定》都要求美、苏不干预或攻击任何一方的预警系统(包括预警卫星)。由此可见,目前要通过现行国际空间法律体系来禁止或限制军用卫星是十分困难的。在外空军事化已经成为现实的情况下,禁止在外空部署一切类型的武器是防止外空武器化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亟待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国际社会对此已经进行了不少努力。1981年第36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上苏联就提出了“缔结禁止在外空部署任何类型武器条约”的议题,意大利也提出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决议草案,联合国大会对此通过了相应的决议。(20) 加拿大也于1998、1999年连续两年提出防止外空武器化的具体设想。在2000、2001年的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上,中国政府也提出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法律文书的要点草案。然而由于美国政府对外空武器化问题谈判的抵触,特别是2001年美国布什政府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国际社会关于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的国际立法受到严重冲击。
为了防止外空进一步军事化、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国际社会必须在联合国框架下对现行的国际空间法律制度进行完善。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行国际空间法律制度进行完善:(1)在联合国框架下,国际社会应该就禁止在外空部署一切空间武器进行国际协商,争取通过一项关于禁止在外空部署任何类型武器的国际文件,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关于禁止在外空部署任何类型武器的国际公约。(2)国际社会也应就禁止对空间物体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问题进行谈判,防止已经出笼的反卫星武器的进一步扩散,最终达成一项关于禁止对空间物体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国际公约。(3)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国际电信公约》与相关外空条约之间的协调。“和平探测与利用外空原则”是国际空间法的基本原则,“和平利用”意味着外空利用应建立在非军事化基础之上。卫星的军事利用显然有悖于“和平利用”原则。因此,《国际电信公约》不排除对军用卫星的保护是与相关外空条约的规定相冲突的。基于此,笔者认为,要么依照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对《国际电信公约》进行修改,要么由全体缔约方对《国际电信公约》第35条进行专门解释,明确排除对军用卫星及民用卫星军事化利用的保护。(4)国际社会应重新审查现行《外空条约》、《月球协定》等防止外空武器化相关条约适用的充分性与明确性。外空军事化的现实已经充分证明现行国际空间法律制度对于防止外空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的局限性。为此,各国加快对《月球协定》的签署和批准程序及缔约方进一步完善《外空条约》第4条及其相关规定,是国际社会防止外空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的根本要求。(5)进一步加强外空物体的登记制度,完善现行的《登记公约》。1975年《登记公约》所规定的登记国对外空物体的登记内容仅限于“一般功能性”,而从国际实践来看,美、苏等国发射的卫星有2/3是军用卫星,但在登记内容中从未体现其军事功能。因此,《登记公约》应明确规定如果外空物体载有任何类型的外空武器,必须立即通知联合国秘书长。此外,还应对卫星军事功能的公布及登记期限等相应规定进行修改。
(二)加强联合国框架下外空非武器化及防止军备竞赛机制的建设
防止外空军事化的进一步加剧,禁止外空武器化及军备竞赛,最终实现外空的和平利用,国际社会必须在联合国框架下加强各机构的职能及其相互之间的协调,共同实现外空和平利用的目标。
第一,充分发挥联合国和平利用外空委员会(以下简称外空委)的协调作用。联合国外空委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和审议有关外空和平利用的技术和法律问题,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报告和建议。然而,在实践中,外空委在外空非武器化及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却十分有限。实际上,目前在协调外空非武器化方面最现实的机构就是外空委,如果外空委不能切实发挥协调作用,外空非武器化及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步伐将会更加艰难。因此,在2005年外空委第48届会议上,中国代表就明确提出,外空裁军问题不能仅由裁军谈判会议和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大一委)处理,对非和平利用外空的关切是外空委的必然职责,外空委在外空非武器化及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方面应作出更大的努力。(21) 具而言之,在外空非武器化及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方面,外空委的协调作用主要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应在加快有关外空非武器化及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国际立法进程中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应加强与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等机构之间的协调,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直接纳入谈判议题并促进谈判进程。
第二,进一步加大联合国大会及裁军谈判会议的政治影响力,通过政治谈判等途径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发展。从1982年起,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就把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列入议程,此后每届会议均有该项议程。从1985—1994年,裁军谈判会议还设有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外空特委会),专门审议外空问题。1999年,第54届联合国大会再次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决议。决议强调谈判缔结一项或多项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国际协定仍是裁军谈判会议外空特委会的首要任务。然而,在防止外空军事化、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方面,裁军谈判会议及其外空特委会至今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笔者认为,联合国大会在协调外空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方面的主要职能应包括:(1)加强对外空非武器化及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国际法的促进和发展,通过国际政治性文件、提请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等方式进一步完善和丰富相关法律制度;(2)通过对外空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问题的关注,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对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外空武器化行为及军备竞赛行为进行注意;(3)通过联合国大会的政治影响力促进“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议题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中讨论的深入。
第三,加强联合国安理会对外空非武器化及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监督与核查机制。外空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是一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应将防止外空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纳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加强联合国安理会对国际社会发展、部署、使用空间武器的监督与核查机制的建设,对于从根本上防止外空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在当今主要空间强国本身就是安理会成员国、现行的国际空间法对于外空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本身就存在严重不充分性与不明确性的情况下,要真正发挥安理会的监督与核查作用尚存诸多障碍。
第四,充分发挥联合国国际法院对国际法发展的司法作用,通过国际法院的司法机制不断完善和发展现行的国际空间立法。一方面在相关空间争端解决中,积极发挥国际法院司法判决的作用,为现行国际空间法的完备及发展准备司法基础;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的作用,进一步完善现行国际空间立法。如联合国大会应就外空的“和平目的利用”问题要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通过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来对现行国际空间立法中的“和平目的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问题进行澄清。
(三)中国在防止外空军事化、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中的立场及对策
作为当今世界上的空间大国,中国在推动空间技术发展方面为人类探测与利用外空作出了重要贡献。针对外空军事化日益升级的趋势,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在联大一委、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及联合国外空委会议等多种国际场合多次阐明中国政府的观点和立场,积极倡导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联合国框架下的现行国际空间法律制度,防止外空军事化、武器化和阻止外空军备竞赛。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外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探索和利用外空的最终目的是推进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为人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外空应服务于而非损害各国人民维护和平、增进福利、谋求发展的根本目的。确保外空的和平利用、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是各国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不能等到外空武器实际成型、产生了真正危害,也不能等到一国率先将武器引入外空而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更不能等到外空武器扩散时再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是关键。否则,各国和平利用外空的权利和外空资产的安全都将受到损害。同时,中国政府认为,早日达成一项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的国际法律文件,有利于维护对外空的和平利用,维护外空资产的安全,促进在外空的国际合作,并增进各国的共同安全。为此,中国政府愿与有关各方携起手来,共同缔造一个没有武器、远离战火、安全洁净的外空。(22)
为了实现外空非军事化和非武器化,中国政府认为,作为联合国授权的裁军和军控条约谈判机构,裁军谈判会议是谈判和缔结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法律文件的最佳场合,国际社会应该充分利用裁军谈判会议这一重要机构,加快完善和发展相关法律制度,弥补现行法律制度的不充分性和不明确性。(23) 为此,中国代表团与俄罗斯、越南、印度尼西亚、白俄罗斯、津巴布韦和叙利亚代表团,于2002年联合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关于未来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国际法律文书要点》的工作文件,并与俄罗斯代表团联合发布了三份专题文件。实际上,早在1984年10月,中国就向联大一委第一次提交了一项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决议草案,强调外空只应当被用于和平目的而不应该成为军备竞赛的场所,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巨大空间能力的国家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制止外空军备竞赛。(24)
然而,由于美国等空间强国态度消极,特别是美国2001年底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后,国际社会关于防止外空军事化、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的法律制度建设及监督机制建立等方面一直未能取得有效进展。相反,随着美国等国家的导弹防御系统的建立,外空军事化、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呈现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作为空间大国和负责任的国家,为实现外空非军事化、非武器化,我国政府应该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倡导和推动防止外空军事化、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第一,正视外空利用已经军事化的现实,将我国空间活动及空间外交定位于防止外空进一步军事化、防止外空武器化和阻止外空军备竞赛。在外空已经军事化的今天,要全面实现未来外空非军事化,这只能是国际社会的良好愿望。为此,在防止外空军事化、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方面,我国政府应审时度势,在制定本国空间政策和空间外交中正视外空已经军事化的现实。而在完善和构建新的防止外空军事化机制中,将近期目标一味地定位于追求外空完全非军事化是不现实的。联合国框架下的核不扩散机制的形成及发展对构建新的防止外空军事化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25) 联合国框架下的核不扩散机制的前提是承认核武器已经存在的事实,通过国际协商赋予有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一定的国际义务,逐步构建一个法律、经济、政治的安全机制,从而实现从削减到逐步消除核武器的目的。同样,在防止外空进一步军事化和军备竞赛方面,我国既要正视外空军事化的现实,也应正视现阶段全面实现外空非军事化的困难,将国际立法及国家空间政策和空间外交的重点引向防止外空进一步军事化、防止外空武器化和阻止外空军备竞赛上。
第二,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努力发展我国的空间技术,跻身世界空间强国行列,提高我国在国际空间领域的地位,加强我国在国际空间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中国空间实力的加强,不仅有助于防止外空进一步军事化,也有助于遏制西方空间强国正在进行的无节制外空军事化利用活动。2007年1月11日我国进行的外空试验,标志着我国空间实力的显著提高。尽管我国政府事后已经通知相关国家,且重申我国的外空试验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但是我国的这次外空试验仍震惊了其他空间强国,引起他们的极大关注。这些空间强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对防止外空军事化所持的反对态度,也逐步开始考虑外空军事化可能引起的后果,也开始重新评估防止外空军事化谈判的重要性。
第三,积极参加联大一委、联合国外空委及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等国际机构的活动,推动联合国框架下防止外空进一步军事化、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机制的逐步建立。作为空间大国,中国应积极推动外空委在完善和促进国际空间法律制度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加紧对防止外空军事化、武器化的国际法律制度的立法研究和建议。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积极引导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加紧对防止外空武器化、阻止外空军备竞赛的讨论和协商,积极促成相关国家就防止外空进一步军事化、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缔结国际文件和国际条约。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应充分利用联合国大会的政治影响力,积极推动联合国外空委及联合国裁军会议等国际机构在关注和防止外空进一步军事化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
基金项目: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资助项目(06SFB5034)。
注释:
① 参见《时事开讲:美国渲染中国导弹击落卫星》,http://bn.sina.com.cn/phoenixtv/index,shtml.
② 陈宏、王震雷:《太空战争风云录》,中国友谊出版社2003年,第277页。
③ Theresa Hitachens,Weapon in Space:Silver Bullet or Russian Roulette?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U.S.Pursuit of Space-based Weapon,http://WWW.cdi.org/missile-defence/spaceweapon.cfm.
④ 参见税世鹏:《新世纪初军用卫星技术及市场发展评析》,《中国航天》2000年第3期。
⑤ 参见翟玉成:《还太空以和平——从布什的新空间探索计划谈起》,《现代军事》2004年第3期。
⑥ 参见苑立伟等:《美国反卫星武器综述》,《中国航天》2004年第4期。
⑦ 日本从2007年起将引进导弹防御系统,用以拦截以日本为目标的弹道导弹。此外,日本等国可能将追加配备美国的一种高性能移动式新型雷达。参见李平:《日本开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重庆晨报》2007年1月3日。
⑧⑨⑩(11)(12) 参见《美国挑战外空条约 准备在太空布置进攻性武器》,http://defence.org.cn/aspnet/articl—1—52703htm.
(13) 参见《美国太空政策变了脸》,《世界报道》2006年10月20日。
(14) 《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主要内容前文已述及,此处不再赘述。
(15) 贺其治:《外空法》,法律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16) 参见[韩国]柳炳华:《国际法》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6页。
(17) See B.Jasani,Outer Space:Militarization Outpaces Controls,Maintaining Outer Space for Peaceful Uses,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1984,p.221—252.
(18) 参见[美]布里奇:《国际法和外空军事活动》,《阿克朗法律评论》1980年第4期。
(19) 参见《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第2条和《南极条约》第1条。
(20) 参见联合国裁军事务部编:《1982年联合国裁军年鉴》第7卷,联合国翻译司中文处译,第364页。
(21) 参见《中国代表团团长苏伟先生在联合国外空委第48届会议上的发言》,http://WWW.chinesernission-vienna.at/chn/zxxx/t199697.htm.
(22) 参见何洪泽、邹德浩:《中国代表胡小笛在联大就神六发射发言 强调外空非军事化》,http://WWW.cnsa.gov.cn/n615708/n942529/n942833/70710.html.
(23) 参见《中国代表团在裁军谈判会议一期会全会上关于工作计划的发言》,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jks/jkcjxb/wenjian2006/liucaijuntanpanhuiyi/t309196.htm.
(24) 参见张爱宁编著:《国际法原理与案例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页。
(25) 核不扩散机制是联合国框架下所倡导的一种消除和遏制核武器扩散的国际安全机制。该机制要求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要帮助其他国家获取拥有核武器的能力,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而没有核武器的国家要放弃获取核武器。经过多年的努力,国际社会在防止核扩散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建立了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核心的防核扩散的全球机制(包括《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多边机制(如核供应国集团、桑戈委员会)、双边机制(如《战略武器限制条约》、《战略武器削减条约》),实现了一些有意义的战略核武器削减,推动了核不扩散国际共识的形成。参见陈须隆:《核不扩散机制透析——国际安全机制的一个案例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8期。
标签:军事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军事卫星论文; 军事化管理论文; 中国导弹论文; 通信卫星论文; 法律论文; 反卫星武器论文; 月球轨道论文; 武器论文; 空军论文; 国际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