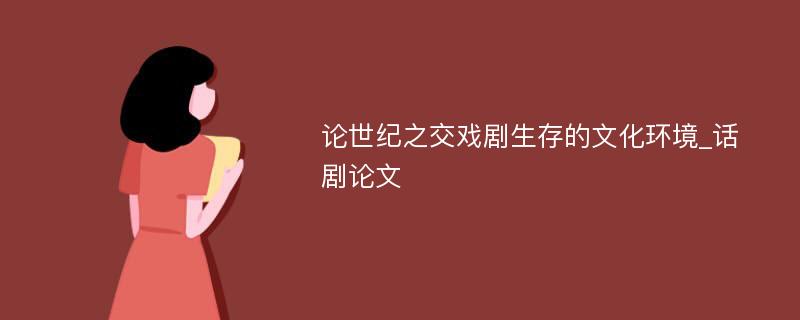
论世纪之交话剧生存的文化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话剧论文,环境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戏剧是大众化程度最高的艺术形式。虽然它的脚本也和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样式一样,都诉诸于纸张和印刷,但对它欣赏的最后完成,必定借助于舞台的二度创作。与雕塑、绘画相同,戏剧极强调它的观赏性;但与前二者比,戏剧又有非常集中的时间和空间要求。从某种角度上说,戏剧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市民文化的典型象征。人们有看戏的愿望,就是因为在达到生活温饱之后,有寄托闲情逸致和回味人间悲欢的精神消费需要,这为戏剧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宽阔的生存空间。这种消费需求,既创造了观众,更创造了舞台。中国话剧产生于戏剧历史长河的下游,它是戏剧文化不断丰富的产物,更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发达阶段的标志。随着话剧艺术样式的精致和完善,它逐渐由通俗艺术流变为高雅艺术。有时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甚至变成少数人颐情养性的工具。话剧的发展,曾经有过令人炫目的灿烂和辉煌。而市场经济必定要把它自身的价值体系推演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伴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与高雅文化背道而驰的大众消费文化应运而生。话剧正受到电视、多媒体、综艺晚会、歌舞、音乐会等的严重挤逼,明天将是什么观众支撑起话剧那沉重的舞台?话剧的船,将停泊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纪之岸?我们有必要将当前话剧生存的文化环境作一次认真的分析。
一、现在是标举通俗的时代,而不是追逐高雅的时代
戏剧的生命源头在民间,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支撑起戏剧的舞台。随着艺术门类自身的发展和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戏剧逐渐变得精致高雅,特别是话剧。这不仅仅是指它本身的千锤百炼和精雕细刻,更主要的是指它的文化内涵的逐渐雅驯变得越来越适应高素质小范围的人群观赏,就像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喜剧逐渐远离莎士比亚的绿色森林和风流小镇,而走进上流社会的厅堂,戏剧被笼上了高雅温馨的帷幔。高雅艺术的显著特征是精英性和超前性。所谓精英性就是指艺术的贵族化倾向,只有少数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才懂得欣赏,如像20年代徐志摩们的新月社戏剧,包括像丁西林、杨绛、王文显等的戏剧,深厚的文化含量使之过于沉重而很难走进大众;超前性就是指为实现这种艺术形式的先锋性所进行的哲学探索,真正伟大的雅艺术往往接近某种宗教精神,往往带上形而上的本体论色彩。总是从哲学文化层次体现人类对生存本质的追求,最终走上抽象和极端。像法国的荒诞剧和印象派绘画,真正能够欣赏的人总是极少数。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转轨,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刺激了人们的多层次消费欲望,人们的心理潜能盼望各种有效途径的释放。非常重要的是,物质层面的提高并不能相应迅速地带来精神层面的升华,这就决定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刚刚具备了温饱条件的中国人精神生活追求的层次。刚刚具有的物质享受心态总使人难以割舍世俗而去追逐高雅。人们还远没有达到过度的物质享受之后对消费的厌倦。现在,因为拥有闲暇和追求消遣将给中国话剧造就千千万万的观众,这实在是中国戏剧振兴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人们需要符合自己审美口味和欣赏水平的艺术形式,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言情小说获得张力最大的读者群的成功令戏剧沉思,通俗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为普通人圆一个释放情绪的形形色色的白日梦,它是一种成年人的童话。通俗小说的成功正是它借鉴了戏剧冲突的方法,总是通过一系列故事悬念来控制吸引读者的情绪,小说人物的悲欢离合赚取了普通人宝贵的眼泪。这种基本定型的叙述思路造成了规定的心理期待,改变情节的走向读者是不答应的,小说家有时甘愿成为读者的奴隶,读者并不追究金庸琼瑶小说中一些常识性的失误,只要正义最终战胜邪恶,少男佳女最终团聚,就满足了普通读者阅读的心愿。
话剧的艺术实现形式决定了它是通俗艺术,特别是在当今时代。话剧不是案头艺术,不是个人阅读,而是由数百乃至上千甚至更多的观众和演员共同创造。普通观众看戏的最大愿望就是娱乐。戏剧制造娱乐的主要手段就是悬念和故事,就是要紧紧抓住观众的情绪,迅速把观众导入规定的戏剧情境中,让观众感觉到戏中的人物事件就是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和事,让观众的情绪和戏剧扭结在一起。像曹禺先生所说,真正的好戏,要能够达到戏能“咬”人的效果。如果观众被戏“揪”住,难以摆脱由戏剧情境所诱发、调动起来的激动和兴奋,戏剧就获得了成功的动力。现在有人对所谓没有情节的散文诗式的哲理剧大加赞赏,认为突破情节是戏剧革命的曙光,并以契诃夫的生活剧作为例证。这实际上是对契诃夫戏剧的误解和对戏剧的误导。如果戏剧放弃它本身的冲突,只是通过人物对话来演绎所谓的哲学和哲理,把话剧演成没有剧情的散文诗的朗诵,那戏剧的散淡之时便是观众的散淡之日。戏剧史上不乏永载史册的案头剧,例如莎士比亚时代的大学才子戏,我国20年代初的“问题剧”。由于缺乏戏剧演出的舞台实践,尽管雅致华丽,也永远只能付诸印刷,而不能走向舞台。
二、现在是感性享受的时代,而不是理性教育的时代
大众文化的特征就是它的娱乐性、消遣性、刺激性。它必须进入市场的运作。大量的新闻小报、影视故事、综艺晚会都是以满足各阶层民众的娱乐兴趣为宗旨。大众文化的消费效果就是消除疲劳,调节情绪,颐养性情,轻松精神。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普遍加快,工作负担重、压力大,激烈的竞争使人变得浮躁,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逐渐疏离、隔膜,人的心理普遍感到紧张。加上人的大脑又被各种信息所包围,广告像夏天的暑气一样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信息的膨胀使人十分疲惫。当人们稍有余隙走进剧场时,首先希望的是心情放松,暂时忘却工作的紧张忙碌,搁置人与人之间的嫉妒争斗,和亲人朋友一起获得一次心灵的轻松放飞。请看当今各种综艺节目,即使是教授、名流来做嘉宾,也只是参与一些文史科普常识的竞猜和趣味游戏的表演。当获得一个廉价的奖品和本方阵的观众一起开怀大笑时,并不感到丝毫的掉价。看话剧演出也是一样,人们不愿意心情过于沉重,看得太累。从某种角度说,今天是个更需要喜剧,而不要悲剧的时代。但是,现在的话剧仍然习惯用严肃沉重的题目,诱导观众对人生哲学层面的东西作理性思考,迫使观众对本来在生活中就感到非常疲劳的诸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生活的真善美”、“人的生存境遇的危机”等形而上的问题做出选择和判断。不少剧作家仍然没有改变“观众到剧场来看戏,就是来接受教育”的传统思维方式。诚然,任何一个真正伟大的剧作家都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任何一部真正伟大的戏剧都会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但是,类似生活教科书和人生指南的戏剧却会使坐进剧场的观众就像小学生一样被动接受教师的指点。变革的形势逼迫戏剧家不得不重新思考非常原始的问题:观众坐进剧场到底是为什么?英国美学家科林伍德在《艺术原理》中探讨娱乐的特性时指出:娱乐是以不干预实际生活的方式释放情感的。大众娱乐从根本上说是超乎功利的,它不直接与人的灵魂挂钩。琼瑶小说中的少男少女有时很煞有介事地讨论人生,但让读者们操心的决不是主人公采取了何种人生态度,而是少男少女的结合采取了何种解决矛盾的方式。人们不喜欢戏剧直接充当政治上的启蒙老师。人们到剧场来是享受艺术,是精神休息,而不是在大礼堂听政治报告。
三、现在是诠释故事的时代,而不是张扬主题的时代
戏剧的原始意义,用王国维的话说,是“以歌舞演故事”。人们对故事的兴趣,特别是对故事曲折、离奇的好奇心,反映了人类一种最基本的文化心理。名人传奇、明星婚变、黑幕曝光、警匪追杀、宫闱秘闻、领袖生平等题材不断被炒作,正是因为有广泛的文化消费需要。话剧也是演绎故事的一种最基本的艺术形式。绝大多数观众能看懂话剧,最基本的也是要看到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本身的奥秘是它情节的传奇性,观众希望在这种故事的展开、冲突、逆转、结果的刺激中获得感观的满足。如何诠释故事,将成为剧作家苦恼的难题。现在有些剧作家抓住百姓对一些熟知的文化色彩很浓的故事仍然情有独钟的心理,利用戏剧形式对传统故事进行改造并获得成功。如魏明伦早就改造过《潘金莲》,现在又改造了《杜兰朵》。《西厢记》一直被各种戏曲形式反复改造,至今仍然手法翻新。最近,报载一个南方剧种将要对《梁山伯与祝英台》进行彻底改造,甚至增加祝英台的母亲也有英台类似婚恋经历,而反对梁祝婚姻的主要障碍是其伯父的情节。上海京剧团的新编历史剧《狸猫换太子》也红遍半个中国。一种值得深思的社会心理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越是熟知的故事,越是被人炒作,观众越是津津有味。诠释故事的另一层意义还在于:戏剧情节的组合成份越来越多,剧作家不屑于传统的因果关系的故事,而往往打破时空界限,对情节进行超时空的组合,这种情节的组合方式使故事容量增大,涵盖生活的面加宽,情节的丰富变幻使戏剧的主题变得复杂深厚。探索剧《魔方》就是典型例证。这是由九个根本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小剧组合的话剧,当有人问及它的主题时导演幽默地说:它有九九八十一个主题,你问的是哪一个?寻找文学作品的主题,是中国评论家习惯成自然的思维定势。评论一出戏,首先就思考:戏的主题是什么?主题不鲜明的戏,就不是好戏。这使我们再一次想到曹禺在新中国成立后回答评论者询问《雷雨》主题时的尴尬。因为曹禺自己在酝酿创作《雷雨》时的感觉只是不可压抑的原始创作冲动力,压根儿就没想到它要表现的主题是什么。况且,一个时期以来,有些评论家一谈到主题时就一定要进行非褒即贬的简单判断。这样一来,一些戏剧,特别是“主旋律”戏剧,在没有创作之前,剧作家就套上了一个隐形的项圈,它是表现重大主题的创作,必须格外小心谨慎。这就使得很多挂上“主旋律”号的戏剧无一例外都是那样严肃庄重,叫人活泼不得。最近,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汇集众多精英投排公演了法国喜剧《居里夫妇》。一说到剧名,中国观众并不陌生,居里夫妇是中国观众熟悉的科学家,观众也很容易联想到电影《居里夫人》。这无疑是一个主旋律话剧,但法国剧作家却是以喜剧形式来表现科学家的生活和工作的,据说青艺选择的角度就是情节的别致谐趣,许多细节令人捧腹,形象地表现了居里夫妇的智慧、幽默、执著。国内也有写科学家的剧目,但总是过多强调他们的献身精神和作为英雄的光彩,似乎他们的日常生活也笼罩了一层驱不散的神圣光环,丝毫不能出现任何阴影。实际上,故事是一个永恒的经典,剧作家可以根据自己对故事的不同理解,多侧面、多角度进行再创造,再发展。乾隆一再被“戏说”,《白蛇传》、《穆桂英》、《杨贵妃》等一直被“新编”,观众都是那么乐此不疲。据说苏州观众如醉如痴地欣赏秦瘦鸥《啼笑姻缘》改编的苏州评弹,几十年长盛不衰,恐怕就在于对故事的诠释不断翻新。80年代的探索戏剧克服了主题单一的倾向,剧作家敢于探索生活本质,提出自己对生活内蕴的独特理解,戏剧主题显得丰富、深邃,同时驳杂。但由于有些探索剧突出了情节的反故事性,使戏剧走向哲理的玄奥和抽象,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事实证明:话剧远离故事,不注重情节的生动性、观赏性,要赢得多数观众是很难的。
四、现在是高度综合的时代,而不是突出个性的时代
作为任何一种面向大众的艺术形式,都必须充分考虑观众覆盖面的复杂性,考虑观众不同的兴趣和爱好,尽可能充分地满足更多观众的消费需要。这是大众文化经纪人和策划人最基本的艺术定位。只要看看影响颇大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单就知道,策划者苦心孤诣,花样翻新,最终都只能在小品、相声、歌舞、声乐几大块中轮番炒作,扔掉任何一个块都将遭致部分观众的唾骂。策划人非常清楚:这种舞台千万不能倾斜。只要是面向广大观众,就必须走向综合,走向各种艺术形式的渗透、嫁接、改造。再看现在各种综艺节目,都要因为观众的口味不断转换,扩展它的外延,开始是呆板地照搬舞台节目,再到熔音乐、舞蹈、戏曲、小品多种艺术样式于一炉,现在又向益智性综艺节目发展,特别注意贴近百姓的生活,注重观众的参与性和趣味性。
话剧是任何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台词和对话是话剧的根基,它是以语言的音响形象为媒介,直接诉诸观众听觉的符号。也就是说,话剧的情节推进,主要是靠语言来完成的。话剧的台词是极富魅力的,甚至一句独白,一个停顿,一声叹息,都包含十分丰富的潜台词。这同时对话剧的欣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80年代初,话剧步入低谷时,一批年轻的戏剧探索者,勇敢地创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屋外有热流》、《车站》、《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野人》、《魔方》等话剧,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借鉴了其他艺术门类的手法,渗入歌舞、哑剧、戏曲的元素,增强了话剧的表现力。另外,话剧的舞台美术技巧大幅度提高,声光等视觉效果的改善极大地改变了话剧的单纯性,丰富了话剧的表现力度。但遗憾的是,话剧的台词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我们仍然记得北京人艺上演郭沫若、曹禺、田汉等人的经典话剧时,于是之、兰天野、英若诚、刁光覃、朱琳等话剧表演大师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那声音的醇厚,吐字的清晰,声调的顿挫,真可谓字字珠玑,让人回味无穷。现在我们已很难欣赏到这种高水平的对话艺术。40年代,张瑞芳扮演郭沫若历史剧《屈原》中的婵娟,曾将“你是无耻的文人”推敲为“你这无耻的文人”,这“一字之师”的故事已成为遥远的戏坛佳话。不用说,戏剧家们“十年磨一剑”,千锤百炼的台词艺术已不多见,恐怕更主要的是,广大观众由于长期受到各种娱乐综艺节目的浸润,音响的刺激已经使听觉迟钝,现在真正能够对话剧的台词和对话艺术高度敏感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这不能不说是话剧的悲哀。有责任感的话剧工作者忧心忡忡:现在看真正纯正的话剧难,演真正纯正的话剧更难。最近中央实验话剧院上演话剧《坏话一条街》,有人说是语言从剧情的剥离日益增长的标志。语言艺术的表演确实引人注目,民谣、谚语、俏皮话、歇后语、绕口令纷至沓来,当整出戏成为展示角色语言天才的场所时,我们不禁又问: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话剧吗?
五、现在是观众分流的时代,而不是舞台中心的时代
戏剧艺术又被称为舞台艺术。当欧洲第一个镜框式舞台——巴尔玛法尔纳斯剧场1618年建立以来,它成为近代舞台建筑的范本。以固定的舞台作为演出地点,逐渐形成了统治欧洲四百年的舞台中心时代。不管人们对舞台与观众席分离的现状怀揣多大不满,不管人们对破除演出区的清规戒律提出多少设想,舞台作为演出中心的核心地位始终不可动摇。人们所谓的戏剧空间概念,很大程度是指舞台空间。长期以来,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品位、不同欣赏水平的人流,从四面八方奔向舞台,舞台成为万众瞩目的圣殿。而如今的舞台逐渐被人们冷落和遗忘。人山人海奔剧场欣赏戏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包括电视、电脑、 家庭影院、 VCD在内的家庭娱乐方式的极大丰富,把大部分中国百姓留在家里。 即使喜爱戏剧的观众也可以在电影频道、文艺频道等电视中欣赏到他们愿意看的节目。不用说,如痴如醉欣赏话剧的观众已越来越少,即使有愿意看话剧的观众,也可能为城市交通的堵塞、购票的麻烦、剧场的遥远而望而生“退”。加上随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对精神生活追求的美学分化,文化商客又处心积虑想方设法占领老百姓双休日、节假日等黄金时光,人们除了传统的观看电影、戏剧的单一娱乐方式外,还有看画展、听音乐会、上健身房、上酒吧、夜总会、到公共图书馆、游名胜古迹等文化消费方式。这一切,都使得当今的观众逐渐分流。更重要的是,观众的这种分流体现出小范围、私人性、重亲情的特色。人们越来越不习惯于大众场合、喧闹气氛、淹没个性的娱乐方式,而倾向于远离人群、感情组合、清静狭小的娱乐天地。社会生产的高度综合反而使人与人之间不愿过多聚集,不愿在公共场所表达感情,没有特别吸引人或引起关注的魅力,要把观众不分层次万众归心地吸引到舞台前来是越来越难。另外,随着舞台几百年的自身发展和积累,舞台自身的体重越来越大。固定的高档灯光、音响装置、笨重的道具装置、层迭的豪华帷幕,使舞台越来越“胖”。加上话剧演员基本功的衰退,使很多人离开微型话筒就不能说话,如此种种都使舞台无法轻松。遥想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莫里哀在带领剧团辗转英伦三岛和法兰西外省,飘流演出于全国各地,他们的舞台辎重到底有几驾马车?我们今天的舞台难以迁徙和活动,话剧离开舞台设施难以正常演出,此中尴尬,是怨剧团还是怨观众?发达国家的戏剧艺术都由主流戏剧、商业戏剧和实验戏剧组成,代表国家演出水平和标志的国家大型剧院毕竟不多,而商业性和实验性的戏剧占大多数。在我国,商业性戏剧还基本处于萌芽状态,将来有所作为的可能要数包括小剧场在内的实验戏剧。小剧场戏剧最早出现在我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作为戏剧自我拯救和自我涵养的工具,有人说,它的特点不仅在“小”,而且在“空”。所谓“小”,就是指剧本短小,内容集中,演出范围小,职业特点鲜明。学校的校园戏剧,工厂的职工戏剧,部队的军旅戏剧等等,它的特征就是业余性、探索性、自娱性。实际上现在不少专业艺术团体都参与和渗透进去了,这也是戏剧寻找市场的有效途径。所谓“空”,就是无论是专业剧团修造的固定小剧场,还是利用各种空余地临时改造的演出场所,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固定舞台,整个舞台空旷简单、背景清晰,每个戏都可以根据自身内容想象、演绎、延展它的空间,舞台的可塑性极大。鲁迅说过,中国的旧戏,几乎没有什么背景,很像民间的剪纸,或类似绘画中的白描,线条简洁明朗,很值得借鉴。更主要的是,这种舞台可以随时转移,极大地方便了演出。这一切,都似乎在昭示着话剧走下神圣的殿堂,走向世俗和百姓。而现在我们要问话剧的是:面向市场,你有几分胆怯,几分矜持,又有几分自信?
本栏主持,范春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