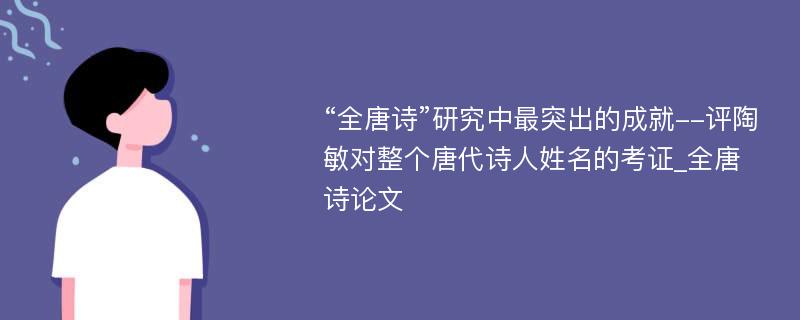
《全唐诗》研究最突出的成果——评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唐诗论文,人名论文,最突出论文,成果论文,陶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作者评介陶敏先生新近出版的《全唐诗人名考证》一书,认为该书广泛占有史料,穷究史源,缜密细致地考证出《全唐诗》中大量未知人名,并纠正了书中许多人名、官名、地名等错误,以及前人和今人对《全唐诗》中人名的许多误考,是研究《全唐诗》成就最突出、学术价值最高的一部著作。
关键词 唐诗 史料学 《全唐诗》 《全唐诗人名考证》
1982年11月19日,当时在湘潭师专外语科从教的陶敏先生给我一信,说正在湘潭讲学的卞孝萱先生希望他搞一个《全唐诗人名索引》。由于卞先生介绍了我从事《唐刺史考》撰写的情况,因此他希望能与我相识。对于《全唐诗》中的人物,我在研究李白和从事《唐刺史考》撰写的过程中,曾经因诗题往往只称姓及官职,或称姓及行第,或称姓及爵里,或称姓及身分,有时甚至连姓都没有,仅称官职等等而苦恼。现在,陶敏先生有志于编撰《全唐诗人名索引》,它无疑会给唐诗研究者带来极大的方便。于是,我立即复信陶敏先生,支持他的想法,建议他改作《全唐诗人名考》,将《全唐诗》中所有未知的人名考出来,这对唐诗研究者更有价值和意义。从此以后,我俩通信频繁,交换成果,交流信息,彼此都获益甚多,成为莫逆之交。陶敏先生还参加了我所承担的《元和姓纂》和《元和姓纂四校记》的整理任务。整理工作一结束,陶敏先生便集中精力撰写《全唐诗人名考证》,并在1990年底完成了这一重大工程。现在,这部著作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陶敏教授向学术界送来了一部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工具书,为唐诗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免除遍稽典籍之劳的极大方便,也为学术界树立了踏实精细治学的良好榜样。
1
所谓“人名考证”,顾名思义就是要考出未知的人名。本书最大的贡献,就是将《全唐诗》中数以千计的未知人名大部份考了出来。考订之精审,收获之巨大,令人惊叹。有些诗集前人已有注释,但仍有许多未考出的人名,本书都一一考了出来。如王维《酬郭给事》诗,清人赵殿成注、今人陈铁民、张清华所作年谱、杨军所作诗文系年均未考出其名。本书据《姓纂》卷十颍川郭氏:“纳,给事中,陈留采访使。”证知此诗中“郭给事”当即郭纳。又据《新唐书·玄宗纪》及《全文》卷三二三萧颖士《蓬池禊饮序》,北图藏拓本《赠尚书兵部郎中李公神道碑》,对郭纳的事迹作了考订。再如岑参《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送许拾遗恩归江宁拜亲》、《送许员外江外置常平仓》等诗中的“许子”、“许拾遗”、“许员外”,过去研究者都不知其名。今人陈铁民、候思义《岑参集校注》亦称“其名不详”。本书据贾至《授韦少游祠部员外郎等制》、《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六二《润州上元县福兴寺碑》、《旧唐书·代宗纪》等考知“许子”、“许拾遗”、“许员外”为同一人,名登,江宁人,至德末、乾元初由右监门卫仓曹参军迁右拾遗;广德二年由拾遗迁员外郎,时岑参亦在长安;大历五年已为金部郎中。同时还考出杜甫的《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因许八寄江宁旻上人》两诗中的“许八”亦即许登。这样,不仅考出了岑参、杜甫五首诗中的未知人名,而且将许登的仕历也勾勒得甚为清晰。
类似例子在本书中俯拾皆是。如据《旧唐书·甄济传》考出岑参《虢中酬陕西甄判官见赠》诗中的“甄判官”为甄济,时在陕州来瑱幕。据颜真卿《颜允臧神道碑》及殷亮《颜鲁公行状》考出岑参《夏初醴泉南楼送太康颜少府》诗中的“颜少府”为颜允臧,时为太康尉。据杜甫《送李校书二十六韵》考出岑参《送弘文李校书往汉南拜亲》中的“李校书”为李舟。据于邵《与杨员外书》及《旧唐书·杨炎传》考出岑参《寻杨七郎中宅即事》中的“杨七郎中”为杨炎,时为兵部郎中参西川杜鸿渐幕等等。所有这些,前人乃至今人的《岑参集校注》均未注出过。
即如号称有千家注的杜甫诗。本书仍从中考出不少前人未曾考知的人名。如杜甫《七月三日戏呈元二十一曹长》诗,旧注系此诗为大历元年作于夔州,但这位“元二十一曹长”之名,各注本都未注出。本书据《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以及《姓纂》卷四河南元氏称“持,都官郎中”,又据《国史补》卷下称“尚书省丞郎郎中相呼为曹长”,证知“元曹长”当即元持,时由郎中贬为夔府别驾。再如杜甫《惜别行送向卿进端午御衣之上都》诗,这“向卿”指谁?各注本亦均未注出,本书据贾至《授向萼光禄少卿制》称“荆南奏事官守太仆卿同正向萼……可守光禄卿同正”,对照杜诗称“尚书勋业超千古,雄镇荆州继吾祖”,证知“向卿”当即向萼,时在荆南节度使卫伯玉部下。又如杜甫《敬赠郑谏议十韵》中的“郑谏议”,各注本亦未注出,本书据颜真卿《颜允南神道碑》考知郑审天宝末在朝官谏议大夫,时杜甫在长安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但未授官,故诗有“使者求颜阖,诸公厌祢衡”之语。证知“郑谏议”即郑审。他如考如杜甫《徐九少尹见过》诗中的“徐九少府”为徐知道,《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四韵》中之“卢十四弟”当即卢岳等等,类似这样通过细密考证考出的人名,不胜枚举。
2
本书的首要特点是广泛占有资料,穷究史源,除史传之外,诗文序跋、笔记小说、姓氏谱谍、公私书目、佛道两藏、金石碑帖均掌握运用,正因为博采众书,融会贯通,所以,有左右逢源之效。如从《茅山志》、《庐山记》等考出王昌龄《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中的“黄炼师”为黄洞元,韦应物《寄黄尊师》、《寄刘尊师》、《寄黄刘二尊师》为黄洞元、刘玄和,包佶《宿庐山赠白鹤观刘尊师》中的“刘尊师”为刘玄和;考出李德裕《尊师是桃源黄先生传法弟子》及《寄茅山孙炼师》中的“尊师”、“孙炼师”为孙智清;据《十国春秋》考出栖蟾《寄问政山聂威仪》及王贞白《礼聂先生新安重围先生能两军之好》诗中的“聂威仪”“聂先生”为聂师道;据《金华赤松山志》等考出贯休《闻赤松舒道士下世》中的“舒道士”为舒道纪;据《真仙通鉴》等考出许彬《酬简寂熊尊师以赵员外庐山草堂见赠》诗中的“熊尊师”为熊德融,李中《庐山栖隐洞潭先生院留题》中的“谭先生”为谭紫霄,罗隐《题洞玄先生草堂》中“洞玄先生”为闾丘方远,据徐锴《茅山道门威仪邓先生碑》考出李中《思简寂观旧游赠重道者》中的“重道者”为曾为庐山道副的重安寂等等。又如据《高僧传》卷六《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证知刘得仁《送智玄首座归蜀中旧山》中的“智玄”即知玄。据《北梦琐言》及《宋高僧传》卷十七《唐南岳七宝台寺玄泰传》,证知齐己《送泰禅师归南岳》中的“泰禅师”即玄泰。据《宝刻类编》卷八慕幽书《吴重立寿州司马傅公碑》及《南唐释迦佛并部从功德记》,证知齐已《送幽禅师》诗中的“幽禅师”即为慕幽等等。所有这些考出的道释人名及其事迹,对研究上述韦应物、李德裕、刘得仁等诗人的生平交游及其诗篇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书中还充分利用地下发掘出来的资料(唐人墓志)与纸上的材料(典籍)结合,运用“二重证据法”,不仅考明唐诗中未知人名及其事迹者甚多,而且还补充了许多已知人名的鲜为人知的事迹。如王维《宋进马哀辞》,序云:“中书舍人宋公之子也。”前人均不知“宋进马”为何等样人。本书据《通鉴》、《元龟》、《会要》、《新唐书·杨国忠传》等记载,考知“中书舍人宗公”为宋昱;又据1952年西安南郊出土的《唐故殿中省进马宋应墓志铭》,考知“宋进马”即宋昱之子宋应,《志》称其父宋昱天宝二年自监察御史贬桂阳尉时,宋应年六岁,知宋应为进马于天宝十四载卒时年仅二十。利用此《志》,宋昱及其子进马宋应的事迹就都搞清楚了。再如杜甫有《奉酬寇十待御锡见寄四韵复寄寇》诗,寇锡,历代注家均不注其事迹。本书引用《千唐志·有唐朝议郎守尚书工部郎中寇公(锡)墓志铭》,才使读者第一次对寇锡的事迹有全面的了解,并证知杜甫写此诗时寇锡正在监岭南选。
又如《全诗》卷五一三裴夷直《献岁书情》注:“一作《献刘蕡》。”李商隐有《赠刘司户蕡》、《哭刘蕡》、《哭刘司户蕡》、《哭刘司户二首》等诗,但《新唐书·刘蕡传》记载其事迹极简略。本书据《全文》卷六○九刘禹锡《王质神道碑》,考知大和八年至开成元年裴夷直和刘蕡同在王质宣城幕。又据北图藏拓本《唐故梁国刘府君(珞)墓铭》(大中十年):“烈考讳蕡,皇秘书郎贬官,累迁澧州员外司户。……先人禀气劲挺,临文益振,奋笔殿廷,众锋咸挫。虽以直窒仕,而以名垂世。”不仅补充了刘蕡自柳州司户移澧州司户等前人不知的事迹,而且可见时人对他的评价。
3
本书的显著特点是考证的缜密精细,力求做到外部资料的证据与诗中所用词语典故所显示的人物身份和事迹相切合,即内证与外证相结合,使考出的人名坚实可信。如《全诗》卷二○六李嘉佑《奉酬路五郎中院长新除工部员外见简》诗云:“一门同秘省,万里作长城。问绢莲花府,扬旗细柳营。”陶兄稽之典籍,唯路嗣恭一门可以当之。据《旧唐书·路嗣恭传》:“子恕,字体仁。初,岭南衙将哥舒晃反,诏嗣恭自江西致讨,授检校工部员外郎,得以军前便宜从事。”证知李嘉祜诗中“路五”当即路恕,时新除工部员外郎,题中“郎”后的“中”字衍。路恕觐父洪州,故用胡威典故“问绢莲花府”。恕授工部员外郎从事军前,故诗云:“词锋偏却敌,草奏直论兵。”大历八年,李嘉佑为袁州刺史,属洪州都督府管辖,故有赠答,且呼恕为“五郎”。又据《全唐文》卷六二○独孤良弼《路太神道碑》:“建中三年夏五月,孝孙前秘书省著作郎应、洎令弟怀州刺史恕、前秘书省校书郎凭。”可知大历中路恕兄弟均在秘书省,故诗称“一门同秘省”。经过这样内证和外证结合考察,断定李嘉佑诗中的“路五”为路恕就有充分说服力,无懈可击,确凿无疑。
又如《全诗》卷一二七王维《送祢郎中》,“祢”下注:“一作徐。”陶兄认为唐代绝少祢姓,更无仕宦显达者,“祢”当从注作“徐”,且据诗中有“岛夷”、“卉服”、“珠官”等词,以及“早晚方归奏,南中才忌秋”等内证,证知徐乃出使岭南者。又据《新唐书·徐浩传》及《全唐文》卷四四五张式《徐浩神道碑》等外证,证知徐浩曾为都官郎中、为岭南选补使,都督张九皋为之飞章请建旌德碑。从而考知王维诗中的“徐郎中”当即徐浩。此诗当作于张九皋天宝十载至十二载为广州都督期间,不仅订正了姓,考出了名,又给诗编了年。
又如《全诗》卷五七八温庭筠《经故秘书崔监扬州南塘旧居》,陶兄据《旧书·崔咸传》及《文宗纪》知崔咸卒于秘书监任,又据白居易大和二年作之《祭弟(行简)文》称“拟凭崔二十四舍人撰序”,证知其年崔咸曾官中书舍人,与此诗称“西掖曙河横漏响”合。又据《旧传》称“既冠,栖心高尚,志于林壑,往往独游南山,经时方还,尤长于歌诗”,与引诗中以之比谢眺,称他“松竹风姿鹤性情”合,《传》称咸为陕虢观察时,“自旦至暮,与宾僚痛饮,恒醉不醒”,与此诗称“为酒求官得步兵”合。《传》称咸曾佐李夷简幕,而李夷简元和十三年至长庆二年为淮南节度使,与此诗称咸在扬州有“旧居”合。以此数端内外证结合考证,陶兄才断定此诗中“秘书崔监”必为崔咸,他如考订《全诗》卷六七六郑谷《寄左省张起居》当为寄张茂枢之作,《全诗》六九七韦庄《婺州和陆谏议将赴阙怀阳羡山居》,《和陆谏议避地东阳进退未决见寄》中之“陆谏议”为陆希声,《全诗》卷七○五黄滔《喜侯舍人新命三首》中之“侯舍人”为侯甑等,都不仅以内外证结合考出了人名,而且还考出了该人的事迹,读者提供了更多的资料。
4 《全唐诗》中有不少文字的讹误,本书在考证人名的过程中,常与校勘、辩误相结合,订正了许多诗中人名、官名、地名等的讹误,从而使人们可对诗篇内容有新的理解,对诗作的系年也须作新的修正。如:杜甫有《寄赠王十将军承俊》诗,旧注以为上元二年作,但不知王承俊为何许人。陶兄据两《唐书·崔宁传》及《通鉴·永泰元年》记载,剑南节度使部有大将王崇俊,而杜诗称“将军胆气雄,……出入锦城中”,与王崇俊为成都大将相符。证知“王承俊”当为“王崇俊”之讹。陶兄还指出:诗云“时危未授钺,势屈难为功。宾客满堂上,何人高义同”,当指崔旰为王崇俊求节钺未得,王崇俊为郭英所衔而言,诗当作于永泰元年五月郭英义至成都欲杀王承俊而未杀之时,这不但订正了人名之误,而且还订正了旧注系年之误,并使读者对诗的内容可有正确而深切的理解。
再如李洞有《送安抚从兄夷偶中丞》诗,前人都不知李夷偶为何等人。陶兄从《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七乾符四年九月僖宗《遣使宣慰蕲黄等州敕》称,“今故遣国子司业李夷遇,将我惠渥,恤彼荒残。……汝、随、申、安、蕲、黄等州,凡经王仙芝、尚君长所攻劫处,悉加抚育”,对照李洞诗中称“六州安抚后,万户解衣眠”内容相符,证知“安抚从兄”当为李夷遇,题中“偶”字为“遇”字之讹。这不仅订正了人名,也向读者提供了诠释此诗的相关资料。又如皎然有《冬日送颜延之明府抚州觐叔父》诗,“抚州叔父”一看便知指颜真卿,大历三年为抚州剌史。但颜真卿之侄何以与其远祖同名“延之”?前人均未认真考察。今人贾晋华《皎然年谱》系此诗于大历三年冬至五年冬,亦未考颜延之其人。陶兄从皎然《妙喜寺达公禅斋寄李司直公孙房都曹德裕(裴)从事方舟颜武康士聘》诗注:“即鲁公犹子也。”考出“士骋”为颜逸字,据颜真卿《晋侍中颜公大宗碑》:“(含)十五代孙逸,好文,武康令。”独孤及《送武康颜明府之鄂州序》中的“武康颜明府”即指颜逸。武康县属湖州,由此证知,皎然在湖州所作《送颜延之明府抚州觐叔父》应正作《送颜逸明府之抚州觐叔父》。盖诗题既讹“逸”为“延”,后人又误移“之”字于“明府”前,遂形成真卿侄与其远祖“延之”同名之误。经过陶兄缜密考证辨析,始使此诗恢复本来面目,使人恍然大悟。
《全唐诗》中官名之误甚多,本书多一一辨析证正。如岑参《送李司谏归京》诗云:“别酒为谁香,春官驳正郎。”前人与今人之注都曲为解释,从未发现其中之误。“司谏”指左、右谏议大夫,分属门下、中书二者;而“春官”乃指礼部,属尚书省;诗中称谓与题不相应。而且谏官或礼部郎官均不得称“驳正郎”,其中必有文字之误。陶兄据《新书·百官志四上》东宫官有“司议郎二人,正六品上,掌侍从规谏,驳正启奏”,由此证知此诗题中“司谏”当为“司议”之讹,诗中“春官”当为“春宫”之讹(春宫即东宫)。这样订正后,使诗题与诗的内容完全一致,人们才能正确理解诗意,这是陶兄精辟的发明。
又如贾岛《送李傅侍郎剑南行营》诗,李嘉言《长江集新校》未校出其中之误,陶兄据姚合《寄李廓侍御赴西川行营》诗证知此同时作之同题诗;此诗中“傅”当为“廓”之讹,“郎”当为“御”之讹;又据姚合《寄雩县尉李廓少府》证知此诗中“去年新甸邑,犹滞佐时才”,即指廓官雩县尉而言。这不仅订正了诗题中两个讹字,而且由此可引导读者参考姚合同题诗以深入研究当时情事。类似这样的订正官名在本书中随处可见,尤其是订正“侍郎”与“侍御”的互讹更是屡见不鲜。
这里还可以举两个从内证订正诗题的例子:《全诗》卷五八李峤有《马武骑挽歌》,诗中有“昔年凤”、“帝子家”、“试马”、“吹箫”等词语,可断定死者是驸马。然初唐时期无马姓驸马,陶兄由此断定题中的“马武骑”为“武驸马”的倒讹。盖“驸”讹为“骑”,后人以“武骑”乃官名,遂乙“马”于“武骑”前。此说甚为合理,解开了“初唐无马姓驸马”之谜。初唐武姓驸马甚多,有尚新都公主的武延晖,尚永乐公主的武延基,有先后尚安乐公主的武崇训、武延秀等。又如张说有《徐高御挽歌》,“高御”非官名,亦不类人名。陶兄据诗中有“蒲密遥千载,鸣琴始一追”用子路治蒲邑、卓茂为密令,宓子贱治单父的典故,断定徐某必为县令。然唐无高御县,陶兄想到唐人常将“邮”字写作“卸”,又可能讹为“御”,故断定“徐高御”必为“徐高邮”之讹。按今北图藏影宋抄本《张说集》果作“徐高卸(邮)”,证实陶兄之判断完全正确。这些都显示出陶兄知识之渊博,研究之细密深入。
《全唐诗》中“江南”与“河南”、“河南”与“河中”等地名互讹者甚多,本书都一一进行辨析订正。如卷三三二羊士谔《郡中玩月寄江南李少尹虞部孟员外三首》,注云:“时枉卢云夫书,分司入洛。”“江南”非府名,何来“少尹”?陶兄据诗中称“洛浦”、“洛阳人”,证知“江南”乃“河南”之讹,并考出“李少尹”为李益,元和四、五年为河南少尹。题中称“孟员外”,注称“卢云夫”,陶兄考出卢云夫为卢汀字,与羊士谔同年;又据韩愈《和虞部卢四(汀)酬翰林钱七(徽)赤藤杖歌》注:“元和四年分司东都作”,证知卢汀以虞部员外郎分司入洛;由此知题中“孟”字乃“卢”字之残讹。这样既订正地名之讹,又订正姓氏之讹。再如许浑《和河南杨少尹奉陪薛司空石笋诗》,稽考元和至大中间薛姓为司空者唯薛平,但薛平未尝为河南尹,何以由“河南杨少尹奉陪”?陶兄据《旧唐书·薛平传》考知其曾检校司空兼河中节度观察等使,又据《新唐志·艺文志四》考知杨巨源曾在大和中为河中少尹,证知此诗题中“河南”为“河中”之讹,“杨少尹”即为杨巨源。
《全唐诗》中还有不少地名和姓均误者,陶兄根据诗意亦能考证清楚,订正其误。如《全诗》卷七二三李洞有《上灵州令狐相公》诗,但唐末无宰相姓令狐而镇灵州者,且诗中称“征蛮(一作南)破虏汉功臣”,亦与“灵州”不合。《英华》卷二六二此诗题作《赠高仆射自安西赴阙》,但称“安西”亦与诗中“征蛮”之语不合,且安西自贞元三年陷蕃后唐王朝未曾除授官吏。故“灵州”、“安西”均必误。陶兄据《新书·高骈传》考知高骈曾为安南都护,大破南诏蛮,进为静海军节度,加检校尚书右仆射,证知此诗题当为《赠高仆射自安南赴阙》。《英华》讹“南”为“西”,而《全诗》题目则全误。
类似这样订正《全唐诗》中人名、地名、官名、姓氏的例子极多,不胜枚举。这也是陶兄对唐代文学研究作出的重大贡献。
5
前人和今人治唐诗者甚多,其中也有人曾考证过诗中的未知人名、地名或诗篇的系年,也有的指出诗中错误而力图订正,但往往由于治学的粗疏,其考证结论并不正确,本书中对前人的误考多予以辨析订正,与此同时,在考证《全唐诗》人名过程中,也对各种典籍中的讹误一一予以订正。如岑参有《故仆射裴公挽歌三首》,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认为“仆射裴公”指裴冕,裴冕大历四年十二月卒,故系此三诗为是年作。其实裴冕卒葬长安南毕原,见《全文》卷三六九元载《裴冕碑》,与此诗中所说“礼容还故绛”不合,故“仆射裴公”决非裴冕,闻说误。陶兄据《全文》卷四七九许孟容《唐故侍中尚书右仆射赠司空文献公裴公(耀卿)神道碑铭》考知耀卿卒葬绛州稷山县姑射山之阳,其子八人,符汉代荀氏八龙之数,正与此诗中“时仰八龙名”、“礼容还故绛”等语合,证知此诗的“仆射裴公”当指裴耀卿。耀卿卒天宝二年,则此三诗当为是年作,时岑参正在长安。这不仅订正了人名之误考,也订正了编年的错误。
再如《全诗》卷三四三韩愈有《和崔舍人咏月二十韵》,题下旧注云:“舍人,崔群也。愈元和七年以职方员外郎下迁国子博士,此诗是其年八月所作。”陶兄指出,刘禹锡有《奉和中书崔舍人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二十韵》,当与韩诗为同和诗。然元和七年刘在朗州,韩愈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不可能与长安之崔群唱和;时韩、刘二人均遭贬黜,而诗中并无迁谪意;崔群为中书舍人时在翰林,诗亦未及其学士身份;故陶兄断定此“崔舍人”决非崔群,而应是崔邠,诗当作于贞元十八年,时邠为中书舍人,愈为四门博士,刘为京兆渭南主簿,同在长安,因此三人得以唱和。订正了旧注之误。
又如李商隐有《寄成都高苗二从事》诗,自注:“时二公从事商隐座主府。”冯浩注云:“商隐座主,高锴也。”而对“高、苗二从事”则无注。陶兄据《全文》卷七七五李商隐《上座主李相公状》指出,此诗中“座主”决非高锴,而是李回,时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冯注大误。同时,又据北图藏拓本《唐故朝议郎河南府寿安县令赐绯鱼袋勃海高府君(瀚)墓志铭》:“故相国江州李公在相位,一见深国士之遇,……相国节制庸蜀,……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掌节度书记。相国廉问湘中……。”证知此诗中“高从事”为高翰,时在西川李回幕。
本书还运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对旧史及其它书中的错误也作了订正。如《旧唐书·韩皋传》云:“[长庆]二年,转左仆射。……其年,以本官东都留守,行及戏源驿暴卒。”然《全唐诗》卷二七一窦庠有《东都嘉量亭献留守韩仆射》,“韩仆射”即韩皋;《窦氏联珠集》褚藏言《窦庠诗序》:“昌黎公留守东都,又奏授公为汝州防御判官,改检校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昌黎公”亦指韩皋。证知韩皋确实以仆射留守东都,并未于赴任时卒于道。陶兄指出《旧唐书》在“行及戏源驿暴卒”前盖脱去“长庆四年正月以左仆射召”之类文字,甚有见地。这是以唐诗证《旧唐书》脱误的生动一例。
再如《全唐文》卷四九一权德舆有《送袁中丞持节使回鹘序》,而《全唐诗》同人又有《送袁中丞持节册南诏五韵》,此两“袁中丞”当为同一人。《序》云:“今年春,回鹘君长纳忠内附,……于是诏工部郎袁君加中宪之重,被命服之贵,将行,又拜祠部郎中,……持节册命。”陶兄据《旧唐书·袁滋传》:“转工部员外郎。贞元十九年,……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持节充入南诏使。未行,迁祠部郎中。”证知权《序》中的“袁中丞”即为袁滋。《序》中又有“滇池昆明”、“唐蒙开地”、“诸葛渡泸”等语,证知《序》中的“回鹘”均为“南诏”之误。又据《旧纪》证知袁滋于贞元十年六月使南诏,《旧传》“十九年”之“九”字衍。这是据唐诗结合旧史订正《全唐文》之误。
类似这样订正各种典籍之误的例子还有很多。所有这些,可以看出陶兄花了大量的精力,但他为唐代文史研究工作者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可靠的依据。
6
陶敏教授原来有个庞大的计划,拟将《全唐诗》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考察,除本书外,还准备撰写《全唐诗重出诗考》、《全唐诗伪诗考》并和我合作撰写《全唐诗作者小传正补》等。但前二种现已由佟培基、陈尚君两位先生先期完成,而后者我俩只写了几篇文章,未果成书。不过陶兄已将涉及人物的重出诗、伪诗、以及诗作系年的考证成果,融汇在此书中,所以此书能不拘于一家一集,也不限于未知人名,考订的内容极为丰富。考订的工作又极为缜密。所以,可以说,本书是研究《全唐诗》取得学术价值最高、成就最突出的一部著作。除了提供大量可供引用的具体成果外,它所采用的广泛占有资料的方法,内证和外证结合研究的方法,地下材料和纸上材料结合的“二重证据法”等等,都能给后学以重要启示,具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
本书尚有一些缺点,主要是有些伪诗当时未能发现,如《全唐诗》卷六七一唐彦谦《忆孟浩然》、《过浩然先生墓》、《赠孟德茂》等乃宋末,元初戴表元之作,尚有一些可考的人物未考,新出土的墓志尚可以补充一些人物事迹等等。但这些都只是白璧微瑕,无损全书的学术价值。何况陶兄后来对这些问题已有所发现,在校阅清样时曾写入《校后记》中,可惜出版社未予印出,只能待以后重版时再作修订补充了。
收稿日期:1996年12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