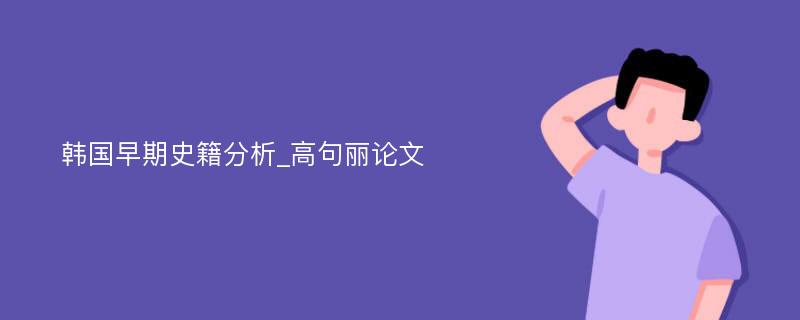
朝鲜早期史书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史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06)02—0045—19
编成于高丽中后期的《三国史记》(1146年)和《三国遗事》(13世纪后叶)是朝鲜现存最早的史书了,但在朝鲜历史上,从三国、统一新罗到高丽前期都出现过数量繁多的史书。这些早期的史书通常被通称为“古记”,但是其实际的名目非常繁杂,演变的过程也很漫长。由于这些早期史书已经湮没无存,我们只能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采编了早期史书的著作和其他文献中寻找线索,所以迄今早期史书的面目依然模糊不清。朝、韩、日的学者们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批驳了否认早期史书的观点,肯定了早期史书的存在和其记录的基本真实性,也认识到了早期史书的复杂性,并对旧《三国史》、《一统三韩记》、《古典记》等许多具体的史书进行了考证。但是,没有弄清的问题还很多,关于早期史书的认识远未达成共识。本文即想通过具体的统计和考证,对早期史书的名目、分类和演变线索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与学界方家们共同探讨。
一、“古记”是朝鲜早期所有史书的通称
在《三国史记》中出现了“诸古记”这个说法。在“卷八新罗本纪第八·孝昭王·十一年”的注释中有“诸古记云‘壬寅七月二十七日卒’”的内容,说明在高丽中叶,“古记”已经是一种通称了。那么“古记”的外延究竟是怎样的呢?
根据笔者的统计,在《三国史记》中,共提到“古记”类书籍26次,其中提到“古记”16次,“海东古记”2次,“三韩古记”1次,“新罗古记”3次,“本国古记”2次(一指高句丽本国古记,一指百济本国古记),“古传”1次,“新罗传记”1次(见附表1)。此外所引用的书籍都有明确的作者和书名。由此,很多人就把“古记”看成是某种官修史书或者系统的断代史的统一书名,但实际上,情况要更为复杂。
附表1 《三国史记》引用诸《古记》类统计
出处 古记名称 引用次数 形式
本记新罗
古记5 注释
诸古记 1 注释
本记3 注释
古传1 正文
高句丽海东古记1 注释
百济 三韩古记1 注释
古记1 正文
志
祭祀 古记3 正文
海东古记1 注释
乐新罗古记2 正文
古记2 正文
地理 古记2 正文
职官 古记1 正文
本国古记2 正文
列传 金庾信上 古记1 注释
张保皋新罗传记1 注释
强首 新罗古记1 正文
首先,上述以“古记”指称的6种书籍,有国别史,有三国史, 还有不能明确其内容的史书,这就已经说明“古记”的形态是不统一的。
其次,“古记”的指称本身也是不稳定的。在《三国史记》中出现了“古传”和“新罗传记”这两个不以“古记”指称的书:
儒理齿理多,乃与左右奉立之,号尼师今,古传如此。(《三国史记卷一新罗本纪第一·儒理尼师今元年》)
此与新罗传记颇异,以杜牧立传,故两存之。(《三国史记·卷四十四列传第四·张保皋》)
这两本书与用“古记”指称的书有什么差异?这两本书一出自本纪,所引为国王事迹,一出自列传,所引为臣民事迹,显然都是史书的性质,与前面“古记”看起来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唯一可以看出的就是使用了“传”字。莫非纯粹传记性的史书(虽然还不能肯定这两本书是这样的史书)就不能用“古记”来指称了吗?——不是的。
《三国史记·卷四十一列传第一·金庾信上》中有“此与本记真平王十二年所书一事而小异,以皆古记所传,故两存之”的注释,“金庾信传”是依据金庾信的玄孙金长清所作的《金庾信行录》“删落之,取其可书者”而成,所以上述“古记”之一当指《金庾信行录》。这样看来,纯粹传记性的史书也被称为“古记”。上述“古传”和“新罗传记”和“古记”指称的史书没有根本差异。而且,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像《金庾信行录》这样的有明确作者的个人传记作品也可以被称为“古记”,“古记”显然是各种史书的一种通称。“古传”和“新罗传记”只是个别的书名,或者是另一种不规范的指称。
《三国遗事》提供了更多的线索。笔者统计了《三国遗事》中所引用的指明的本国史料(不能判明国别的亦算在内,见附表2),结果发现, 《三国遗事》一共有150处引用了79本(篇)本国史料,但是其中所谓“古记”、“乡传”、“传”、“古本”、“别记”之类的说法出现得很多,虽然名称一样,但却在不同的地方指称不同的书,无法判明。如果把这些不明指称除去,在《三国遗事》中所引用的指明书(篇)名共有54种。在与“古记”相关的“书名”记录中,有“古记”10处,“新罗古记”1处,“新罗别记”1处,“高丽古记”1处,“百济古记”1处,“驾洛(国)记”2处,“新罗古传”1处,“本朝史略”2处,“东明记”1处,“壇君记”2处。此外又有“乡记”1处,“乡古记”1处,“乡传”11处,“古传”3处,“山中古传”1处,“古典记”1处,“别记”3处,“别传”4处,“记”2处等。如此繁杂的名目,一方面说明了这方面的史书数量不少,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这些名称的用法很不严格,如卷三“塔像第四·辽东城育王塔”云:“按古传,育王命鬼徒每于九亿人居地立一塔,如是起八万四千于阎浮界内。”这里“古传”是指佛经。而书中又出现了寺庙“古记”的提法,多云“某寺内传古记”,这里的“古记”是指寺庙自传的有关自身历史的记录。在提及《三国史》时又称之为“乡传”。所以,在《三国遗事》里,“古记”、“乡传”、“古传”、“乡古记”、“乡记”等提法都用来泛指本国古籍,其间的界限并不严格。
附表2 《三国遗事》引用诸《古记》类统计
卷数题目
引处引用
内容
一纪异 古朝鲜 正文古记 君神话
马韩
正文崔致远云 罗丽起源
靺鞨渤海
注释新罗古记 渤海建国
正文东明记靺鞨侵新罗
正文指掌图靺鞨地理
正文东坡指掌图靺鞨地理
正文指掌图靺鞨地理
伊西国正文(云门寺)诸寺纳田记 纳田事
五伽耶注释驾洛记·赞驾洛开国
注释本朝史略 驾洛国之数
正文本朝史略 改驾洛地名
北扶余正文古记 北扶余建国神话
高句丽注释壇君记君婚育神话
注释壇君记君婚育神话
正文珠琳传·第二十一卷朱蒙出生
卞韩·百济正文致远云卞韩即百济
辰韩 正文崔致远云 辰韩地名取涿水地名
新罗始祖·赫居世王注释(前引某书)古本 六部议会之年
第二南解王正文金大问云 新罗王之称
第四脱解王注释(所引书)古本脱解生年
延乌郎·细乌女注释日本帝记 无记录
桃花女·鼻荆郎注释(所引书)古本真智王即位之年
善德王知儿三事正文良志师传 载善德王创寺事
正文别记 筑赡星台
金庾信注释(所引书)古本白石是百济人
注释(所引书)古本春南人名
太宗春秋公注释崔致远之说春秋见庾信妹之日
注释(所引书)古本阿海辞奉针之故
注释乡记 唐兵人数
正文新罗别记 刘仁轨盟文
正文古记 金庾信送粮食之事
正文百济古记 义慈王自尽死
正文新罗古传 金庾信坑唐兵
二纪异
文虎王法敏正文乡古记抗唐之事
正文别本 重筑南山城等
万波息笛 注释(感恩)寺中记感恩寺来历
元圣大王 注释日本帝纪 日本王之名
注释(东泉)寺记 东泉寺概况
孝恭王注释(所引书)古本雀巢之年
金传大王 注释(金宽毅)王代宗录太祖娶新罗王室女
南扶余·前百济·北扶余正文古典记百济国号变更
武王 注释(所引书)古本武王之名
后百济甄萱正文李磾家记 甄萱血统
正文古记 甄萱出生
正文崔致远书 代太祖致甄萱
驾洛国记 注释(文人传)驾洛国记驾洛国记
三兴法
顺道肇丽 正文僧传 顺道至丽之年等
难陁闢济 注释僧传 申流王即位之年
注释僧传 载难陁事迹
阿道基罗 正文我道碑文 我道小传
注释古记 墨胡子之称
原宗兴法 注释乡传 朝臣之名
注释乡传 造寺之议
注释乡传 斩舍人之异象
注释传葬地
注释乡传 大兴轮寺始建之年
注释僧传 大兴轮寺始建之年
正文乡传 兴轮寺忌日社会
注释僧传 新罗王出家名法云事
法王禁杀
注释古记 弥勒寺创始
宝藏奉老·普德移庵 正文高丽古记 羊皿之事
注释神志秘词序盖苏文之名
注释传盖苏文之名
正文本传 载普德移庵详事
正文僧传 载普德移庵详事
正文本传 载普德弟子事
三塔像 迦叶佛宴坐石
正文玉龙集载迦叶佛宴坐石
正文慈藏传载迦叶佛宴坐石
正文(吴世文)历代歌 逆数四万余岁
正文(金希宁)大一历法数一百余万岁
正文纂古图数二百余万岁
辽东城育王塔
正文三宝感通灵建塔由来
正文古传 育王立塔
高丽灵塔寺 正文僧传 载普德传
正文(普德)本传 普德立灵塔寺
皇龙寺丈
注释别传 阿育王聚铁之数
注释(皇龙)寺中记铸像之日
正文别本 铸像之由来
注释别记 所载与别本同
正文(皇龙)寺记 金常造成之日
皇龙寺九层塔
注释(慈藏)本传 慈藏西学
注释(皇龙)寺中记受建塔原由之处
正文(安弘)东都成立记九层之象征
正文(皇龙)寺中古记 建塔过程
注释(皇龙)寺中古记 塔遭霹雳之年
皇龙寺钟·芬皇寺药
师·奉德寺钟
正文
(金弼奚)钟铭文繁未录
灵妙寺丈六 正文良志法师传创寺因缘
注释良志传像初成之费
三所观音·众生寺
正文新罗古传 中国画工事
栢栗寺 注释别传 载玄琴与笛事
注释别传 载郎徒事
前后所藏舍利
正文义湘传舍利之事
南白月二圣·努肹夫 正文白月山两圣成道记 两圣传
得·怛怛朴朴
注释乡传 二士之名
注释乡传 二圣所居处
注释记朴朴之言
注释传娘归北庵
注释古记 景德王即位之年
注释古记 白月山南寺成之年
洛山二大圣·观音·正
注释(义湘)本传 义湘之事
趣·调信
注释(所引书)古传梵日事在前
鱼山佛影
正文古记 万鱼寺由来
正文高僧传惠远闻天竺有佛影
正文星函西域记佛头恶龙
台山五万真身
正文山中古记 慈藏入唐
注释别传 慈藏入唐载慈藏入唐之事
注释古记 净神隐居之年
注释记在位之年
溟州五谷山定叱徒太子传记
正文溟州五台山宝叱徒太子传记 宝叱徒太子传
台山月精寺五类圣众 正文(月精)寺所传古记月精寺创立之事
南月山 正文(金堂主)弥勒尊像火光后记建造甘山寺缘由
天龙寺 正文讨论三韩集天龙寺之事
伯严寺石塔舍利 正文古传 石搭之事
灵鹫寺 正文(灵鹫)寺中古记 灵鹫寺由来
四义解 圆光西学
正文(古本)殊异传圆光传
正文海东僧传 滥记宝壤事
宝壤梨木
正文宝壤传宝壤身世
注释清道郡都田帐传准 载宝壤名
正文新罗异传 滥记鹊塔璃木之事
正文海东僧传 无宝壤传
归竺诸师
正文(广函)求法高僧传往天竺之人
慈藏定律
注释乡传 太宗见慈藏
元晓不羁
正文古传 元晓身世
正文乡传 元晓轶事
正文(元晓)行状 元晓经历
义湘传教
注释(崔侯撰)本传载义湘辽东被捕事
注释(义湘)行状 载义湘辽东被捕事
注释大文类载贤首之文
正文锥洞记智通所撰
关东枫岳钵渊薮记
注释关东枫岳钵渊薮石记荧岑所撰
胜诠骷髅
正文(胜诠)碑文 载胜诠事迹
正文大觉国师实录 载胜诠事亦
心地继祖
正文(金宽毅)王宗代录释冲献太祖袈裟等
正文(桐华寺所传)简子释冲献太祖袈裟等
五神晓 明朗神印
正文(金光寺)本记明朗造寺
注释(金光)本寺记三师为律祖
正文堗白寺柁贴注脚广学等随太祖上京
五感通 郁面婢念佛西升 注释乡传 婢西升事
正文僧传 婢西升事
正文本传 西生之年
广德·严庄 正文
(元晓)本传 载铮观事
正文海东僧记 载铮观事
憬兴遇圣
正文
(玄本)三郎寺碑 载憬光事
五避隐 朗智乘云
正文
(元晓)偈子 节选
正文
灵鹫寺记 赫木庵事
缘会逃起·文殊岾
注释
僧记 缘会身世
信忠挂冠
注释
三和尚传 载信忠奉圣寺
正文
别记 断俗寺由来
五孝善 大城教二世父母·神 正文
乡传 大城之事
交代
正文
(佛国)寺中记佛国寺由来
由此也可以证明《三国史记》里出现的“古传”和“新罗传记”更有可能是另一种不规范的通称,而不是具体的书名。由于金富轼是参照中国正史的体例编纂《三国史记》的,所以有意识地对早期史书的通称进行了规范,这才形成了我们见到的以“古记”通称之的现象。《三国遗事》的编者一然在这方面的意识没有那么强,所以《三国遗事》里早期史书的指称就比较随意。而且,在《三国史记》里终究还是留下了早先指称比较随意的痕迹。
不过,在《三国遗事》里还是能够看出,早期史书的指称大致可以分为“古记”类和“乡传”类两种。前者包括古记、古传、史略、古本、记等,后者包括乡传、乡记、别记、别传等,前者的内容似乎多是国家大事,后者的内容似乎多是人物和地方掌故。只是两者之间又经常混用,尤其是“古记”似乎更有统指的意味。
综上所述,在高丽时期,“古记”是对早期所有朝鲜史书的通称,在高丽以前,这样的通称还有“古传”、“乡传”等多种。由于《三国史记》的影响,后世才沿用了“古记”这个指称。不过在高丽时期,“古记”和“乡传”等通称还是有不严格的区别的,这个区别应该说正反映了朝鲜早期史书的分类。
二、朝鲜早期史书的分类
朝鲜早期史书的情况虽然非常复杂,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提供的材料梳理出一个大致的线索。
朝鲜早期史书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史,一类是通史。
先说专门史。这主要是在统一新罗和高丽前期,由某些文人杂采早期史书或民间传说所写成的专门记叙社会某一方面的史书。在《三国史记》中,金富轼就引用过统一新罗时期的金大问的著作,并说其“作传记若干卷,其《高僧传》、《花郎世记》、《乐本》、《汉山记》犹存。”
《花郎世记》可能是列传的主要材料之一,因为在列传里,有不少花郎的故事。
《乐本》,应该是写有关新罗音乐历史的,因为是“传记”,所以应该是写人物为主的,但在《三国史记·杂志·乐·新罗》中,引用的都是“新罗古记”、“罗古记”和“古记”,而于勒一段内容与本纪有异,如注知名字的差异,注知三人都学琴,而在本纪中是各学琴、歌、舞。如果本纪依据的主要是通史系统的古记,那么乐志依据的古记就不是通史系统的古记,那就很可能是《乐本》。《乐本》很可能也被看作是“古记”之一。
《汉山记》,汉山是地名,《三国史记·卷三十五杂志第四·地理二·汉州》:“本高句丽汉山郡,新罗取之,景德王改为汉州。”真兴王十六年曾“巡幸北汉山,拓定封疆”,这里是新罗和高句丽的国境线,战事频繁,太宗王七年时高句丽靺鞨曾兵围北汉山城。《三国史记》说金大问“圣德王三年(704年),为汉山州都督”,他应该是那时候搜集了当地的民间传说而写成的。《汉山记》应该是以汉山周围地域为范围的记载战争英雄的传记作品,像列传里的“匹夫传”等就有可能来自《汉山记》。
另外在《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法兴王·十五年》的“新罗肇行佛法”的记载后,有注释说明是据金大问的《鸡林杂传》而写成的。显然,在撰写专门史方面,金大问是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此外,《三国遗事》也引用过金大问、崔致远、金宽毅、安弘等人的著作。
《三国史记》的“地理志”是依据景德王时的地理材料写成的,因为其中有大量的“景德王时改名”的记载。景德王十六年(757年), 对全国郡县进行了大调整,呈现在“地理志”中的面貌,就是那个时候的样子。然后由金富轼等人加上了一些“今名”,但在景德王时名和“今名”之间几乎没有其他的材料,所以地理志依据的是景德王时的材料,而不是那以后写成的材料。此时距金大问做汉山州都督已经过去了50年以上,这个材料不可能是金大问写的了。
此外,《三国史记》还参考了金长清的《金庾信行录》、崔致远的文集和《帝王年代历》。金石文有薛仁宣撰《金庾信碑》、崔致远撰《鸾郎碑序》、朴居勿撰《三郎寺碑》、韩奈麻、金用行撰《我道和尚碑》、无名氏撰《贞菀碑》,另外还有薛聪“所制碑铭,文字缺落不可读”。
在《三国遗事》里,这样的史书通常被称为“乡传”或“乡记”、“别记”、“别传”等。“大城孝二世父母”、“法敏抗唐”、“玄琴与笛”、“太宗见慈藏”等故事都标明来自这样的史书。在很多情况下,一然没有点出具体的书名,只以“乡传”等指称,点出具体书名的有《壇君记》、《王代宗录》、《古典记》、《李磾家记》、《星函西域记》等,还有一本“古本殊异传”,很可能就是大部分已经散失的《新罗殊异传》。从这些书名可以窥见“乡传”类,也就是专门史的大致内容,即具体人物传记和轶事掌故。
在专门史中,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史书,就是佛教典籍。佛教是高丽的国教,从新罗到高丽,都有很多贵族子弟皈依佛门,所以僧人的文化素质普遍比较高,也就留下了许多朝鲜佛教的历史资料。《三国史记》显然引用了某些佛教史籍,因为在本纪中,有一些关于佛教僧徒的故事记载得很详细,不像古记一般行文简略的样子,但指明的只有金大问的《高僧传》。在《三国遗事》中,则多次引用了“高僧传”、“海东僧传”、“僧传”,还有一些具体的传记如《三和尚传》、《宝壤传》、《良志法师传》、《慈藏传》等。还有一些庙宇的历史文献,如《(皇龙)寺中记》、《(灵鹫)寺中古记》、《(金光寺)本记》、《(佛国)寺中记》等。这些史料虽然记载的是佛教在高丽的发展历程,但也从一个侧面记载了朝鲜的历史。这些佛教典籍都可以通称为“乡传”,但是有时又称“古记”,是指称比较混杂的一类。
再说通史。朝鲜古代的通史史书包括各国的本国史和综合朝鲜半岛各国的通史。这种通史从很早就开始出现了,到高丽以前一直没有停止记录,但是,我们又不能以静止的观点看待这个通史的系统,因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通史又经过了几次大的改造。下面就专门谈谈这个问题。
三、朝鲜早期通史及其改造
在通史方面,早在三国时期,三国就分别有各自的史书。通史系统在《三国史记》中有记载,往往被人误以为是通史的发端。又有很多人以为《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是直接引用并删改了这些通史的,由此而引发了各种批判和疑问。其实,记载在《三国史记》中的通史史书,基本而言,既非古史的发端,亦非古史的定型。通史系统早在《三国史记》之前就已经历过多次改造。
先看新罗的通史。《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第四·真兴王·六年》云:
秋七月,伊湌异斯夫奏曰:“国史者,记君臣之善恶,示褒贬于万代,不有修撰,后代何观?”王深然之,命大阿湌居柒夫等,广集文士,俾之修撰。
这部史书的书名,有人认为就是《国史》,其实文中并未指明。“居柒夫传”中也说是“修撰国史”,不能判断这就是书名。而且,这部书也不是新罗最早的史书。
上述史实发生在公元545年。在此之前,公元502年,智证麻立干“下令禁殉葬”,“始用牛耕”,次年定“新罗”国号,取“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之意”,又次年“制丧服法颁行”,又次年“定国内州郡县”,公元514年,始有谥法, 法兴王立,不再用方言而称“王”。公元517年,法兴王“始置兵部”,520年,“颁示律令,始制百官公服朱紫之秩”,次年首次向中国南朝朝贡,“遣使于梁贡方物”,528年,“肇行佛法”,次年“下令禁杀生”,536年,“始称年号”,544年,“许人出家为僧尼奉佛”,显然,从智证王开始,新罗展开了全面引进汉文化的浪潮。在这个时候提出修撰国史,当然是从汉文化的角度提出来的,汉文化中儒家最重视修史,所谓“君臣之善恶,示褒贬于万代”,正是儒家观念。所以,这是新罗第一部以儒家观念修撰的史书。在《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从始祖时就不断地出现德、道、礼、让等儒家概念,非常系统,显然是后人所加,不是原始记录的面貌。
既然“广集文士,俾之修撰”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一定是修古史而不是从此开始历史记录,所以这是一部以中国正史形式重新修撰的古史。它有原始材料,也正说明它不是新罗的第一部史书。考之《三国史记·新罗本纪》,除了神话之外,第一个客观的历史记录是始祖八年“倭人行兵”,第一个语言记录是始祖三十年,其时是公元28年,而第一次文字记录是公元125年, 祗摩尼师今十四年“王移书百济请救”,使用的当然是汉文。在使用了汉文以后,代代相传的神话传说才能被记录下来。但是,还不一定是史书的形式。中国的史书,是从“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开始的,是类似帝王起居注的形式。新罗如果没有大事记和起居注之类的材料,就无法写成按年代排列的本纪。这种史书什么时候有的呢?我认为当在奈勿尼师今(356—402)之后,因为在此之前,王系的血统记载是比较混乱的,尽管经过了整理,还是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像王的年龄偏大,如讫解尼师今是于老之子,即位时于老去世已经61年,而讫解在位47年,殊不可信。奈勿以后,王系就清晰了,说明新罗的原始史书是从奈勿以后不久正式出现的,至真兴王时以中国史书的形式进行了整理。
再看高句丽通史的情况。《三国史记·卷二十高句丽本纪第八·婴阳王·十一年》云:
诏大学博士李文真,约古史为新集五卷。国初始用文字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至是删修。
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出现的第一次使用文字的记录是大武神王十一年的《贻汉将书》,其时是公元28年,其次是公元98年、太祖大王四十六年“遂纪功于岩,乃还”。第一个除神话传说之外的客观记录是始祖三年“黄龙见于鹘岭”,其时是公元35年,历史记录也开始得很早。《留记》的写作当开始于此时。《留记》的完成年代却很晚。如果它在“国初”就已经完成,“至是”方始“删修”,那么中间的几百年的历史记录在哪里呢?从原文的意思来看,显然“古史”就是《留记》,并未指出另有史书,而此次李文真是把以往的历史记录都“约”、“删修”了,参之《留记》有百卷之多,内容肯定不少,所以它应该是记载时代很长的记录。《留记》之名,当取汉字之意,为留下记录,以待后人整理之意(“留”有一极不常用的义项是“治理”,但高丽以前朝鲜古籍,其名均与书、史有关,未有如《资治通鉴》者,故不取),有似于中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原始史书或实录。如此,《留记》有可能是高句丽的第一部史书。《新集》才有五卷,删削不少,也是儒家观念的缘故。这时是公元600年,距高句丽全面引进汉文化的小兽林王时代已经300余年了,以中国史书的形式重修史书是很正常的。不过,这本《新集》金富轼没有看到,因为“高句丽本纪”在长寿王以后使用的几乎都是中国史料,而长寿王以前,相对于“新罗本纪”和“百济本纪”,却是存有神话故事最多的部分,所以金富轼所据的高句丽史书,主要却是李文真删削以前的古本(但不一定就是《留记》)。
再看百济通史的情况。《三国史记·卷二十四百济本纪第二·近肖古王·三十年》:
古记云:“百济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然高兴未尝显于他书,不知其何许人也。
有人认为百济的第一部史书就是《书记》,其实此条是说以前百济没有文字记录,现在有了高兴,可以记录了,“书记”是以书记录之意,并非书名。
不过,如何理解这条记录呢?此条写在“王薨”之后,当是近肖古王之事,已不知确在哪一年,所以写在王本纪之尾,所以其时间应该算在近肖古王即位的公元346年至去世的375年之间。参之“新罗本纪”的记载,公元125年,祗摩尼师今就“移书百济请救”。《日本书记·卷十·应神天皇》更云:
应神二年,命荒田别使于百济,搜聘有识者。国王择宗族,遣其孙辰、孙王随使入朝,应神喜焉,特加宠,以为皇太子之师。于是始传书籍。……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胜于我,是秀逸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翌年春,王仁持《千字文》来,菟道稚郎子习诸典于王仁,莫不通达。
其时是百济古尔王五十二年,公元285年,尚未有《千字文》, 这条记录有存疑之处,但事情记载得如此清楚,当与百济有此交流无疑。这说明百济的汉学那时已经十分发达,有“博士”官职,所以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未有以文字记事”,不能认为是百济国内没有懂汉文之人,或汉文没有用于内政外交。
那么是否能认为以前百济没有用文字记录历史的传统,而此时开始了这个传统呢?也不对。因为考之“百济本纪”,自始祖温祚王元年起就有客观记录,二年即有语言记录,看起来不像“未有以文字记事”的样子,所以百济的原始史书,恐怕还要比此时早很多就有了。“未有以文字记事”,只能理解为以前没有以中国史书的形式记录历史。高兴所记录的方式一定与以往不同。他是“博士”,是“得”来,即从中国来的文臣。公元375年是中国东晋孝武帝宁康三年, 其时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等国均有国子博士、五经博士等,而东晋此外又有太常和周易、仪礼等博士,总之是研究儒家典籍的经学博士,是受儒家观念浸润最深的一群人。如果高兴是到百济以后被授的博士,那么根据《日本书记》上条还说,百济人阿直岐、王仁东渡日本时带去了《易经》、《孝经》、《论语》、《山海经》等中国书籍,则百济的博士也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官职。高兴既是博士,所做的记录也一定是从儒家观念出发的,只是与新罗人修撰国史不同,他并非整理古史,而是从那时起记录当代史。百济一直到国亡,没有重修史书的记载。
以上是三国时期各国通史的面貌:各国都较早开始了原始记录,新罗和高句丽后来又以儒家观念和中国史书的形式重修,百济是以儒家观念开始新的记录。这可以说是通史系统的第一次改造。但是,这些儒家观念的贯彻,显然是不彻底的,否则我们现在就看不到那么多的神话记载了。
到了统一新罗的近三百年时间,古史系统又经历了改造。采用“某国古记”这样统一的书名,或者都被通称为“某国古记”,本身就说明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和环境中成书的。三国时期的通史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现在看到的古记的内容,有本纪、列传,以干支纪年,完全是按照中国史书的形式来撰写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国时期,通史是国家出面组织人撰写的,是官修史书,只此一部。而现在的所谓“古记”,仅属于通史系统的,一个国家就不止一部。如新罗有《新罗古记》、《新罗传记》、《新罗别记》、《新罗古传》,高句丽则有《高丽古记》、《海东古记》,百济有《百济古记》、《三韩古记》等,此外又有《驾洛(国)记》、《东明记》、《壇君记》、《本朝史略》、《古典记》等书名。这本身就说明了三国时期的古史后来又经过了重写,而且版本不一,似已非官修。我可以举一些证据。
《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中的“或云(作)”、“一云(作)”很多,可以发现从不指中国史籍,中国的材料从来都明确指出来,而这些“或云(作)”经常同时有两个,最多的有三个,如“百济地理志”中的“悦己县”,注释云“一云豆陵尹城,一云豆串城,一云尹城”。说明其所据底本至少有四部,或者底本不足四部,其中一部或数部已经是两部以上的底本所合成,已有“一云”字样。这就说明三国的原始史料经过了后来的多次整理。上文说过《三国史记》全书“或曰(云、作)”的注释共有118处,“一曰(云、作)”的注释共有294处,数量庞大,绝大多数是关于人名地名的异名,可以看出人名地名的异名占了《三国史记》原典材料差异的主要部分。其次应该是事件发生年代的出入,但其数量远远少于前者。
为什么人名地名会出现这么多的异名呢?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异名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同一个名的不同汉译法,比如东明王名朱蒙,又名邹牟、众解,琉璃明王名类利,又名孺留,金官国又名伽落国、又名伽耶国,都是这种情况。在翻译的过程中,开始的翻译多是直接的音译,后来则兼顾含义,至少希望在汉文中可以讲通,所以就出现了音译名字也有好几个的情况。比如高句丽第五慕本王本名解爱娄,这就是高句丽名的汉译名,又名解忧,就是在此基础上兼顾含义的结果。二是在原来的民族名字的基础上又另起汉名,造成一人(地)多名的现象。比如高句丽太祖大王“讳宫”,小名“于漱”,小名即高句丽名,大名是汉名,是直接用汉文起的名,并不是“于漱”的翻译。统一新罗以后,更对全国的郡县地名进行了统一的改造,几乎全以汉字重新命名。像上述“悦己县”就是这个情况,它与百济名“豆陵尹”没有关系。这些人名地名的变更也在一次次的古记整理中被记录下来,形成了多重“或云”的情况,这也反过来说明了古记经过了数次整理改造,所以才能将最原始的名字到纯粹的汉名都记录下来。
《三国史记·卷十五高句丽本纪第三·太祖大王·九十四年》注释云:“案《海东古记》:‘高句丽国祖王高宫,以后汉建武二十九年癸巳即位,时年七岁,国母摄政,至孝桓帝本初元年丙戌,逊位让母弟遂成,时宫年一百岁,在位九十四年。’”郑求福先生统计了《三国史记·列传》的年代表记方式,因为在列传中金富轼没有做统一工作,保留了原材料的面貌,结果在三国时期的事件,以“某王某年”或加干支的形式占了绝大多数[1](P532—535),而统一新罗的时间,以“中国皇帝年号某年”或加干支的形式占了绝大多数。这说明统一新罗时期写成的史料基本采用中国年号。上文以中国皇帝年号纪年,又直呼王名,不可能是高句丽时期的原作。在《三国遗事》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古史系统的“古记”都采用了中国年号。又,《本朝史略》之书名,见于《三国遗事》,所引非高丽事,而是驾洛国事,则“本朝”当指统一新罗。又,统一新罗时修史成风,很多人在写私史,现在知道的就有金大问的《高僧传》、《花郎世纪》、《汉山记》、《鸡林杂传》,崔致远的《帝王年代历》,金长清的《金庾信行录》和无名氏的《新罗殊异传》等。正是在这个浪潮中,古史被重新写过,神话传说被改造,也可以想见,许多未被记录在古史中的神话传说现在也被发掘出来,重新揉进了历史。像“高句丽本纪”中的琉璃明王(类利)寻断剑的故事,与中国的干将、莫邪子赤比寻剑报仇的故事很相似,而琉璃明王的时代是西汉后期,干将、莫邪的故事最早见于东汉的《吴越春秋》,显然是后人加上去的。类利的故事在李奎报摘录的“旧《三国史》”中更为详细,说明这是“旧《三国史》”就有的故事,非金富轼所撰。
在《三国史记》的“杂志”中,可以看到新罗的祭祀、乐、官制、色服等记载得很详细,和高句丽、百济的情况完全不同,这种记载方法是从中国史书那里学来的,而本国通史没有这样的体例。这说明,在统一新罗以后,新罗的历史被按照中国史书的体例重新写过,而其他两国的历史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
以上情况都说明,三国的通史在流传到统一新罗之后又经历了大规模的改造。
尽管这些早期通史大都又流传到了高丽,但三国之间的材料并不均衡。这个问题,通过比较三国记载中相互有关的内容,就可以判明。金富轼在写作《三国史记》的时候,可以把三国的史料交叉使用,即把某国“古记”中的材料用在另一国的“本纪”中,但是,各国“古记”毕竟也是详内而略外,不可能对自己国家军队的情况不了解,却对对方的军队的具体情况、行动很清楚。比如“百济本纪·武王·三年”记载了新罗贵山、帚项的战斗故事,故事是从新罗的叙事角度记录的,贵山又仅是新罗小将,不是大人物,这就说明这段记载的原典应是出自新罗而非百济的“古记”。依据这样一些内容上的判断,基本可以知道某段记载的原典出自某国“古记”。我统计了三国“本纪”相互有关的内容的相互关系(见附表3—1、3—2、3—3、3—4),结果发现,“新罗本纪”里有记载而相应的另一国“本纪”里没有记载的情况有13次,而“高句丽本纪”的这种情况只有1次,“百济本纪”的这种情况只有5次,“新罗本纪”里记载详细而相应的另一国“本纪”里记载简略的情况有15次,而“高句丽本纪”的这种情况只有6次,“百济本纪”的这种情况有13次, “新罗本纪”里没有记载而相应的另一国“本纪”里有相关记载的情况只有1次, 而“高句丽本纪”的这种情况有12次,“百济本纪”的这种情况有11次。可以发现,“新罗本纪”在相关内容的记载上占有绝对的优势。
附表3—1 《三国史记》三国的“本纪”中相互有关内容的比较②
年代 新罗本纪高句丽本纪百济本纪
始祖二十一同 同 ——
始社四十 有 有 无
南解十六 ——少 多
儒理十四 多 少 ——
脱解七同 —— 同
脱解八多 —— 少
脱解十同 —— 同
脱解十四 同 —— 同
脱解十八 多 —— 少
脱解十九 多 —— 少
脱解二十 多 —— 少
婆娑六同 —— 同
婆娑二十六多 —— 少
祗摩二多 —— 少
祗摩十四 多 —— 少
阿达罗十二同 —— 同
阿达罗十四多 —— 少
阿达罗十七同 —— 同
伐休五多 —— 少
伐休六同 —— 同
伐休七同 —— 同
奈解四同 —— 同
奈解十九 异(对)—— 异(错)
奈解二十三同 —— 同
奈解二十七异(对)—— 异(错)
奈解二十九多 —— 少
助贲十一 多 —— 少
助贲十六 多 少 ——
沾解二同 同 ——
沾解九多 —— 少
同 —— 同
沾解十五 同 —— 同
味邹五同 —— 同
味邹十一 同 —— 同
味邹十七 多 —— 少
味邹二十二多 —— 少
儒礼三同 —— 同
有 无 ——
讫解二十八同 —— 同
奈勿十一 同 —— 同
奈勿十三 同 —— 同
奈勿十四 ——少多
奈勿十六 ——无有
——少多
奈勿十八 多 —— 少
奈勿二十 ——少多
奈勿二十一——同同
奈勿二十二——同同
——同同
奈勿三十一——同同
奈勿三十四——同同
奈勿三十五——少多
奈勿三十七多 少——
——少多
——多少
奈勿三十八——少多
奈勿三十九——多少
奈勿四十 ——少多
——无有
奈勿四十三——无有
奈勿四十四——无有
奈勿四十六有 无——
实圣二同 ——同
实圣十一 有 无——
讷诋二有 无——
讷诋八少 多——
讷诋十七 多 —— 少
讷诋十八 同 —— 同
讷诋三十一无 —— 有
讷诋三十四多 少——
讷诋三十八异 异——
讷诋三十九有 无——
慈悲十一 少 多——
慈悲十二 ——同同
慈悲十七 多、异(年)—— ——
慈悲十八 ——多、异(年) 多、异(年)
慈悲二十一——少多
炤知三有 无无
炤知六有 无无
——无有
炤知七同 —— 同
炤知十一 多、异(对)少、异(错) ——
炤知十一 无 —— 有
炤知十五 同 —— 同
炤知十六 多 少少
炤知十七 多 少少
炤知十八 多 少——
炤知十九 同 同——
炤知二十一——少多
智证二——同、异(年) 同、异(年)
智证三——同同
智证七——有无
智证八——同同
智证十三 ——多多
法兴八无 —— 有
法兴十——少多
法兴十二 无 —— 有
法兴十六 ——少多
真兴一——多多
真兴二有 —— 无
真兴九多 多多
真兴十一 同 同同
多 少少
真兴十二 多 少——
真兴十四 同 —— 同
多 —— 少
真兴十五 多 —— 多
——少多
真兴二十三同、异(年)—— ——
真兴二十四———— 同、异(年)
真智二多 —— 少
真智三有 —— 无
真智四有 —— 无
真平二十 ——同同
真平二十四少 —— 多
真平二十五多 多——
真平二十七同 —— 同
真平二十九——同同
——同同
真平三十 同 同——
同 同——
真平三十三有 无——
多 —— 少
——同同
真平三十四——同同
真平三十八少 —— 多
真平四十 多 —— 少
真平四十五同、异(月)—— 同、异(月)
真平四十六多 —— 少
真平四十八同 同同
同 —— 同
真平四十九同 —— 同
无 —— 有
真平五十 同 —— 同
真平五十一多 少——
善德二少 —— 多
善德五多 —— 多
善德七多 少——
善德十一 有 无——
多 少——
少 —— 多
少 —— 多
有 —— 无
同 同——
善德十二 多 少——
善德十三 少 多——
同 —— 同
善德十四 有 —— 无
少 多——
多 —— 少
真德一多 —— 多
真德二多 —— 少
真德三多 —— 少
太宗二同 同同、异(月)
太宗六少 —— 多
太宗七多 —— 多
有 无——
多 —— 多
多 少——
文武一有 无——
有 —— 无
有 —— 无
多 —— 多
文武二有 无——
文武三有 —— 无
少 —— 多
文武四有 —— 无
有 —— 无
有 无——
文武五有 —— 无
文武六有 无——
有 无——
文武九无 有——
文武十多 少——
文武十二 多 多——
附表3—2 新罗本纪与高句丽本纪、百济本纪的比较结果③
有
多 同 少 无 异
与高句丽13
15 6
4
1
1
与百济 10
31 30 7
6
2
与高句丽、百济 35
3
0
0
0
总计26
51 39 11 7
3
附表3—3 高句丽本纪与新罗本纪、百济本纪的比较结果
有 多 同 少 无 异
与新罗 1
6
6
15 12 1
与百济 1
4
14 16 6
0
与新罗、百济1
2
3
4
2
0
总计3
12 23 35 20 1
附表3—4 百济本纪与新罗本纪、高句丽本纪的比较结果
有 多 同 少 无 异
与新罗 5
13 30 24 11 2
与高句丽4
16 14 2
1
0
与新罗、高句丽 0
2
3
3
3
0
总计9
33 47 29 15 2
“百济本纪”记载详细而相应的另一国“本纪”里记载简略的13次情况中,主要是对“高句丽本纪”的,对“新罗本纪”的情况在真兴王以前几乎没有出现,相异的情况也是“百济本纪”是误抄,如“肖古王·三十九年”有“罗王奈解怒,命伊伐湌利音为将,帅六部精兵,来攻我沙岘城”的记载,“新罗本纪”的记载却晚十年,在“奈解尼师今·十九年”条中。但“奈解尼师今·十二年”才有“拜王子利音为伊伐湌”的记载,所以“百济本纪”的记载是错误的。在真兴王以后,“百济本纪”中重复的内容比“新罗本纪”多的情况开始出现,但有很多是把新罗的事情移到了百济的部分来写的,如“武王·三年”的记载信息比同年的“真平王·二十四年”多,但多的是新罗贵山、帚项的故事。
以上情况透露出了史料本身的面貌。这说明,尽管三国的通史都流传了下来,但新罗的通史内容比较齐全,而高句丽的通史只存长寿王以前,百济的通史内容也残缺不全。从“高句丽本纪”中可以看到,有关中国的事情几乎都是以中国史料为基础写的,这不是因为金富轼信任中国史料——恰恰相反,当出现两国史料的矛盾时,他总是信任本国史料——而是因为高句丽的古记缺乏外交记录,这从高句丽与新罗、百济的外交事件也多摘抄而来可以佐证。但“高句丽本纪”的内容并不少,尤其是在长寿王以前,但其内容实以故事传说为主,说明高句丽的古记也是以故事传说为主,在三国的古记中可能是经过后人删改最少的。百济的古记比之高句丽的古记更像史书,资料系统一些,但比之新罗的仍远远不如,所以要从新罗那里移来一些做补充。
在统一新罗后期或高丽初,通史系统又经历了第三次改造,这就是把三国的通史综合在一起所写的史书。在《三国遗事》中,出现了“《三国史》”、“《三国史记》”、“《国史》”、“《三国本史》”等书名,其中《国史》指金富轼编纂的《三国史记》,其余的书则另有所指。这说明了高丽前期的确存在一本或数本综合了三国历史的史书。
《三国史记》的年表与本纪所依据的底本是不一样的,这从年表和本纪的大量差异比如国王的名讳、事件的年代、用语的不一致等可以判断。比如在本纪里,新罗始祖朴赫居世的死亡写作“升遐”,在年表里却写成“薨”,又如“新罗本纪”中的太宗武烈王在年表里写成“太宗王”,“高句丽本纪”里的太祖大王,年表里写成“古祖王”。这些说明,年表不是在本纪写成之后,再根据本纪来写的,而很可能是直接根据另一个年表来写的。年表里也有极少数本纪里所没有的记载,如新罗神文王四年有关中国的“光宅”年号在新罗不行的记载,以及孝昭王四年和五年有关中国武周年号不行的记载。《三国遗事》也有一个年表,这些都说明在高丽前期,存在一个年表。由于年表是把三国的历史合在一起排列的,所以这是三国综合通史存在的一个佐证。
更为重要的证据是所谓“旧《三国史》”,不过关于这本史书,还有许多需要辨明的地方。
四、“旧《三国史》”辨析
李奎报在长诗《东明王篇》的序中说:
越癸丑四月,得旧《三国史》,见《东明王本纪》,其神异之迹,喻世之所说者。然亦初不能信之,意以为鬼幻。及三复耽味,渐涉其源,非幻也,乃圣也;非鬼也,乃神也。况国史直笔之书,岂妄传之哉!金公富轼,重撰国史,颇略其事。意者,公以为国史矫世之书不可以大异之事为示于后世而略之耶?……矧东明之事,非以变化神异眩惑众目,乃实创国之神迹,则此而不逑,后复何观?是用作诗以记之,欲使夫天下知我国本圣人之都耳。
在诗中,李奎报歌咏了解慕漱和东明王的事迹,并且以注释的形式留下了许多原文。从这些原文可以发现,“旧《三国史》”中保存着比《三国史记》更多的神话故事,虽然经过了改造和综合,但是儒家正史的观念显然还不强。遗憾的是李奎报只留下了“东明王本纪”的一段记录。
许多学者由此出发,对“旧《三国史》”进行了研究。现在在韩国占主导方面的观点是,认为“旧《三国史》”是一部完全不同于诸古记的史书,它是一部完备系统的通史,不但综合写了三国的历史,而且有突出的民族性,其主导思想并不是儒家思想。如此一来,《三国史记》所呈现的儒家倾向和民族文化的丢失就都是金富轼的责任了。但对于这些结论,我还有很多疑问。
关于“旧《三国史》”这个提法,目前只有李奎报(1169—1241年)在《东明王篇》中明确提到,但这本书是否写了完整的三国历史,还无法证实。一些学者认为,一然在《三国遗事》中也引用了很多“旧《三国史》”的内容,但他没有使用“旧《三国史》”这个名词,而是使用了《国史》、《三国史》的提法。上述关于“旧《三国史》”的结论,都是利用《三国遗事》的资料得出来的。有学者更据此认为“旧《三国史》”还写了渤海国的历史,在三国中以高句丽居首,并题为“高丽本纪”。但是《三国遗事》所引用的“三国史”、“国史”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尚可商榷。
金富轼所撰的《三国史记》确定其书名,应该是在他写完的时候。他的《进〈三国史记〉表》的题目可以证明。但也有人认为这个题目是后人所加。但在《玉海·卷十六·地理·异域图书·淳熙·三国史记》中又有记载:“元年(1174年),五月二十九日,明州进士沈忞上海东《三国史记》五十卷,赐银币百,付秘阁。”现在在《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艺文二》中的确载有“《三国史记》五十卷(并不知作者)”, 说明《玉海》的记载是可靠的, 也证明《三国史记》在1174年以前就已定名为《三国史记》,此时距《三国史记》的成书不过28年的时间,而一然还没有出生。确定了这一点,对我们分辨“旧《三国史》”很有用处。
我将《三国遗事》中的类似引用进行了统计(见附表4),结果发现有“国史”、“三国史”、“史”、“三国本史”和“地理志”、“年表”、“本记”、“列传”等提法。我把引用它们的内容与《三国史记》的内容进行了比较,把异同的条数进行综合,见下表:
附表4 《三国遗事》引用“国史”、“三国史”及与《三国史记》之比较
卷数 题目引处 引用内容比较异同
一纪异马韩注释 本纪罗丽建国时间同,综合而成
正文 三国史 秽貊地理同,文字略异
乐浪国 正文 国史有关乐浪半同,半无
靺鞨渤海注释 三国史 有关渤海半意同,半无
注释 地理志 朔州领县意同文不同
正文 三国史 有关靺鞨意同文不同
高句丽 正文 国史·高丽本纪 朱蒙传说同,文字略异
卞韩·百济 正文 本纪温祚即位之年异
第二南解王 正文 史论宜存方言同,文字略异
第三弩礼王 注释 年表弩礼王即位之年 同
二纪异文虎王法敏 注释 国史四天王寺并寺之年时同,事不祥
金传大王正文 史论总结新罗同,文字略异,
无金富轼使宋事
南扶余·前百正文 三国史记圣王移都事同,时误抄
济·北扶余 正文 百济地理志 百济疆界同
正文 史·本记温祚开国同,文字略异
武王注释 国史弥勒寺异名 无
注释 三国史 武王血统同
后百济·甄萱正文 三国史·本传甄萱血统大同,少生年
正文 史论总结甄萱、弓裔 同,文字略异
驾洛国记正文 三国史 投新罗之年 同
三兴法顺道肇丽正文 高丽本记佛法之始同
正文 百济本记百济佛法之始无
阿道基罗正文 新罗本记新罗佛法之始同
正文 三国本史(记) 佛教肇始之年同
原宗兴法正文 新罗本记异次顿献身 不同年
注释 国史大兴轮寺始建之年无
正文 国史真兴王妃卒年同
宝藏奉老·普德 正文 高丽本记道教之兴普德移庵意同文异
移庵注释 国史普德移庵意同文略
注释 国史荣留王之名 同
注释 国史求佛老之年 同
正文 国史载普德移庵详事 无
三塔像迦加佛宴坐石正文 国史皇龙寺由来 同
金官城婆娑石塔 正文 驾洛国本记 婆娑石塔由来无
正文 驾洛国本记 金官亦名驾洛无
皇龙寺九层塔正文 国史建塔过程半有半无
前后所藏舍利正文 国史梁送舍利事 同
弥勒仙花·未尸 注释 国史始奉花郎之年同
郎·真慈师
洛山二大圣·观 注释 地理志 奈城郡地理 同
音·正趣·调信
台山五万真身注释 三国本史(记) 慈藏入唐之年同
注释 国史无净神父子之事 同
注释 国史无神文王弟争位事同
四义解圆光西学正文 三国史·列传贵山帚项之事同,文字略异
正文 三国史 圆光说法无
慈藏定律注释 国史无太宗见慈藏事 无
五神呪明朗神印正文 文武王传(纪) 明朗禳退唐兵无
五感通仙桃圣母随喜佛事正文 国史·史臣曰东神圣母同,文字略异
五避隐信忠挂冠正文 三国史 信忠创断俗寺不同
表1 《三国遗事》引用《三国史》类史料的内容与《三国史记》的异同①
同异 半同
三国史 4 22
国史9 53
三国史记1 00
本记7 51
地理志 3 00
史论4 00
年表1 00
列传1 00
从上表可以发现一些规律。“地理志”、“史论”、“年表”和“列传”与《三国史记》的有关内容是一致的。这可以说明它们就是指《三国史记》的部分内容,或是《三国史记》的某一原典。“三国史”、“国史”、“三国史记”到底指什么,还需要具体分析。
《三国遗事》肯定引自《三国史记》的地方有两处。第一处是卷二“纪异第二金传大王”,“史论曰”与《三国史记·卷十二新罗本纪第十二·敬顺王九年》的“论曰”内容基本一致,只缺少金富轼与宋臣交流之事以及个别字的差异,但《三国史记》的某些史论也并非金富轼所撰,乃是沿用原典而来,判断这条“史论曰”的确抄自《三国史记》的证据是,它也照抄了其中“昔钱氏以吴越入宋,苏子瞻谓之忠臣”之句。苏轼此言见于《东坡全集》卷八十六《表忠观碑》,此文成于北宋熙宁十年,即公元1077年,是高丽文宗三十一年,加之它流传到高丽的时间,至少应在肃宗以后了,距离《三国史记》的编纂已经很近,而在《高丽史》中也可以看到北宋神宗年间的言论文章,都是在高丽睿宗、仁宗以后才被提及,所以这句议论当是金富轼所发,并非任何原典所有,而《三国遗事》此处的确摘自《三国史记》。第二处是卷五“感通第七·仙桃圣母随喜佛事”的“《国史·史臣曰》”直接引用了上段史论所缺的金富轼与宋臣交流之事,只有个别文字有差异。这两处肯定引自《三国史记》的地方,是同一段史论,但一曰“史论曰”,一曰“史臣曰”,可见一然在引用时并不十分严谨,而《三国史记》在这里被称作“国史”。
《三国遗事》直接标明引用“三国史记”的一处是卷二“纪异第二·南扶余·前百济·北扶余”:“按《三国史记》,百济圣王二十六年戊午春,移都于泗泚,国号南扶余”,但这个“三国史记”倒未必是金富轼所写的《三国史记》,理由有二。一是在《三国史记·卷二十六百济本纪第四·圣王》中,此条写在第十六年上,这显然是一个传抄的讹误,只是不能肯定是《三国遗事》抄错或其流传中的讹误亦或是《三国史记》流传中的讹误。但显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三国遗事》并未抄错,《三国史记》此条也的确写在十六年上,那么,《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都分别抄自某一原典,只是其中一本抄错了。第二个理由是《三国遗事》所引此条的年代表记方式为“三国某王某年加干支”的方式,而《三国史记》的本纪一律采用的是“三国某王某年”的方式。在《三国史记》的列传中,一共有7种表记方式,其中有“三国某王某年加干支”的方式,郑求福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说,这证明列传的原典有很多,表记方式也有很多种,而金富轼没有像在本纪中那样对此进行整理统一。由此可知,朝鲜原典的年代表记方式的基本类型是以“某王某年加干支”或直接以干支记录的可能性很高[1]。我认为郑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三国遗事》此条抄自某一原典,而非抄自《三国史记》之后又查万年历之类加上干支的可能性是很高的。综合两条理由,虽然不能肯定《三国遗事》此条指明抄自《三国史记》的内容的确不是抄自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但至少证明这种可能性很高,只能存疑。
由上可知,《三国遗事》把金富轼的《三国史记》叫作“国史”,而所引用的“三国史记”则很可能指另一本书,这说明在当时的高丽,大家并不十分尊重金富轼为《三国史记》所取的书名。到李朝初,在徐居正的《东人诗话》中,仍然说“金富轼《三国史》亦不载”[2](P225) 等等,指称上仍然不统一。
上表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所引书与《三国史记》相异的部分。因为相同的部分不能肯定是引自《三国史记》,而相异的部分却能肯定不是引自《三国史记》。这样,我们应该把“半同”的部分也算作“相异”的部分。可以发现,所谓“三国史”、“国史”与《三国史记》的异同条数基本相当,在“本记”中的情况也是这样。所以说,《三国遗事》所引的“三国史”和“国史”都有相当部分和《三国史记》不一样。考虑到上述把金富轼《三国史记》叫作“国史”的事实,则“国史”显然用来同时指称《三国史记》和此前的某一本或几本史书。在《三国遗事·卷四义解第五·圆光西学》中,记载了“《三国史·列传》”中的贵山、帚项的故事,与《三国史记》的内容基本一致,后面却说“据如上唐、乡二传之文”,把《三国史》称为“乡传”,证明在《三国遗事》中,所谓“三国史”、“国史”、“三国史记”等指称,是极不严谨的,同一书名可以用来指称好几本书,而同一本书也可以被指称为好几个书名。因此,《三国遗事》的引文证明了高丽前期的确存在一本或数本系统的三国通史史书,但是,却不能仅以书名指称就认为《三国遗事》所引的“三国史”或“国史”就是李奎报所见到的“旧《三国史》”。
因此,关于“旧《三国史》”,真正的证据仅有李奎报的《东明王篇序》一处。虽然《三国史记》书名已定,李奎报也点出了“旧《三国史》”这个书名,但正如一然(包括崔佑甫碑)可以把《三国史记》叫做“三国史”或“国史”一样,李奎报也可以用它来指称《三国史记》以前的任何一本有关三国的史书。他在《东明王篇序》中后面又说:“况国史直笔之书,岂妄传之哉。”又把“旧《三国史》”叫做“国史”。如果说这里的“国史”乃是泛称,不是书名,那么从文中之意来看,“旧《三国史》”也完全可能是泛称,不是书名。因为有了《三国史记》,所以就把以前的史书称作“旧《三国史》”,正如《三国遗事》把以前的史书称为“国史”和“三国史”以区别“三国史记”一样。
学界之所以重视“旧《三国史》”,一个原因是它把三国的历史综合到了一起写,似乎这也就意味着它是经过系统的改写的。但三国的历史本就纠葛很多,古记既是故事体的或传记体的,某些就没有严格的国系线索,故事内容也交叉于三国,都可以称为“三国史”,而到了统一新罗,高句丽的历史和百济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是“国史”的一部分。从《三国遗事》中可以看到,“三国史”、“国史”不仅写了三国的历史,而且写了古朝鲜、扶余和渤海国的历史,但正因为其指称的混乱,所以无法肯定这些内容是存在于一本书中。如果是很多本书都被通称为“国史”,而其中每本都没有写全上述各国,那么其面目就与学界所谓“旧《三国史》”相去甚远了。反过来看,诸古记名目繁多,各国皆有,甚至有像《海东古记》这样外延模糊的书。这些各国通史在金富轼的时代就已经互相编辑或至少是组合在一起了,那么称之为“三国史”亦不为过。也就是说,李奎报看到的书实际上也有可能是各国通史的混合,所以,远古的神话才得以完整地保存,但不能肯定就是一本综合了三国历史的重新写过的“旧《三国史》”。
综上所述,朝鲜早期史书中的通史系统在高丽中期以前,已经被组合到了一起,但是其具体面貌尚不清楚。尤其是是否有统一的体例和完备的思想体系,还不能证实,所以对金富轼的《三国史记》的批评也还需慎重。
收稿日期:2005—06—30
注释:
① 考虑到一然在引用古籍时经常述其大意或综合而成,所以本表将意同文略不同的情况一律算做相同的情况。的确有完全不同内容的情况才算作异,部分相同部分不同或没有的情况算作半同。
② 此表第二、三列里是“新罗本纪”、“高句丽本纪”、“百济本纪”在相互有关的内容上的记载进行比较的结果。某年条内如果出现几次共同的事件,则分别计算。如果两列都是“多”,则是两国本纪各有对方所没有的信息。本表统计的是各条中实际信息数量的比较,不计文字的差异。因为新罗的资料多,所以以新罗王纪年。
③ 此表与附表3—3、附表3—4是把附表3—1中的情况按三国本纪分别进行统计而得出的。
标签:高句丽论文; 新罗论文; 高丽国王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三国史记论文; 历史书籍论文; 史记论文; 三国遗事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百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