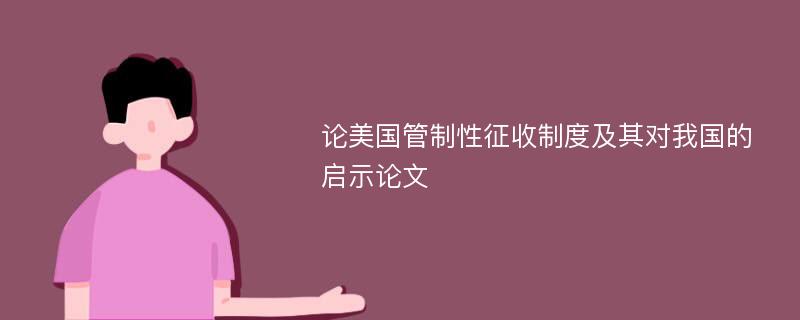
论美国管制性征收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许迎春**
摘 要: 管制性征收是在政府管制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为了保障私人财产的权益而在美国产生的一种新型征收制度,其经历了奠基、确立和发展三个时期。美国管制性征收的判断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当今美国管制性征收的判断主要采取绝对标准、关联性标准、多因素平衡标准和“背景原则”的例外规则,其救济措施是公正补偿。管制性征收制度代表一个国家对私有财产权保障的努力,该制度无论在实践还是在立法层面上都具有很强的合理需求。我国应创立管制性征收制度、设定符合国情的判断标准和建立公正补偿的救济措施。
关键词: 管制性征收 判断标准 治安权 私有财产权
一、 问题的提出
管制性征收① 管制性征收(regulatory takings)在美国早些时侯也被称为反向征收(inverse condemnation)。由于管制性征收与反向征收相比更能阐明政府行为的性质,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管制性征收”这个法律词汇在美国得到更为普遍的采用。 源于美国,是一个在判例法中发育出来的概念。相较于传统的征收,管制性征收并未通过正式的征收程序剥夺财产权人的财产,而是通过立法或具体的行政行为过度限制财产权人的财产,导致财产权人的财产有重大程度的减损或基本权能的丧失,以至产生类似征收的效果。
尽管我国并不存在管制性征收这一法律概念,但实际上,现实生活中已出现大量类似的法律问题。如我国的《土地管理法》《动物防疫法》《文物保护法》《森林法》《防沙治沙法》和《自然保护区条例》等都有过度限制公民财产权的立法,② 《土地管理法》第43条、第44条;《动物防疫法》第25条、第31条、第32条、第48条;《文物保护法》第17条、第18条、第19条、第21条、第22条、第26条;防沙治沙法》第12条、第16条、第17条、第18条、第19条、第21条、第35条;《森林法》第7条、第8条、第32条;《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第27条、第28条、第32条。 还有各地的禁摩事件、山西煤矿兼并重组事件、张谷英古宅改建事件、石光银植树造林却禁止砍伐事件和为保证APEC蓝无数企业被勒令停产事件等。我国管制性征收制度的缺乏,导致实践中出现的大量管制性征收问题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这样只能任由矛盾出现并激化,因此我国亟待建立相应的管制性征收制度。虽然管制性征收或类似制度存在和运作于许多国家,但是出现得最早、发展最为成熟的则是美国。目前我国学者对美国管制性征收制度的研究刚刚起步,在管制性征收的判断标准与救济措施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一些学者没有区分早期的与现今的判断标准和救济措施,误以为一些早已被弃用的判断标准与救济措施在当今美国仍然适用,而且较少有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去探索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管制性征收制度。因此,通过了解目前最为成熟的美国管制性征收制度,借鉴其中的有益经验,并立足于我国国情进行分析,进而构建我国的管制性征收制度,这有助于解决我国日益增多的管制性征收问题。
二、美国管制性征收制度发展的历史回顾
美国管制性征收是在政府限制私人财产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为了保障私人财产权益而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征收制度。从1776年至1922年,这一阶段为美国管制性征收制度的奠基时代。这一时期,美国的征收制度尚处在传统征收阶段,当时学者的普遍看法是政府为了公共使用的目的强制取得私人财产所有权才构成征收,而限制私人财产的使用权则不构成征收。③ Steven J.Eagle, Regulatory Takings,Ann Arbor: Michi Law Publishers,1996. 此时政府为了防止私人财产的有害使用,保护公众的利益,可以以治安权限制私人财产,④ 治安权是一种州政府的内在权力,经常部分地被授予地方政府行使,以对私人权利施予与促进和维持公共健康、安全、美德和一般福利相关的合理限制。 即便给私人财产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也不予补偿。然而,在20世纪初,美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蓬勃发展,美国从原先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商业社会,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以及各种工商企业的建立,导致城市的居住环境日益恶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些城市开始对土地利用进行管制,并制定了大量的管制条例,但有的管制给土地所有者及企业施加了过重的负担,从而引发了是否应当将政府的管制行为予以适当限制的思考。
从1922年至1978年,这一阶段为管制性征收制度确立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国家开始对经济领域实行广泛的干预,政府的治安权范围有所拓展。在这一背景下,1922年在联邦最高法院产生了管制性征收的经典案例马洪案,⑤ Penn sy lv an ia C oa l C o.v.Mahon , 260U.5.393 , 415 , 416(1922). 该案被视为管制性征收制度诞生的重要标志。在该案中,宾州煤炭公司将一块土地的地上权转让给马洪的前任房主,但在合同中明确保留了在其地下采煤的权利,后来马洪在知情的情况下买下了该地产。1921年宾夕法尼亚州为防止地面建筑物下陷危险而颁布了禁止煤炭公司开采房屋下煤矿的《柯勒法案》,于是马洪据此向法院申请禁止煤炭公司在他的房屋下采煤的禁制令,而煤炭公司自然不满,从而引发了诉讼,该案件最后被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决《柯勒法案》对宾州煤炭公司采矿权的限制实质上构成了征收。在该案中,法院首次确认政府的管制行为限制私人财产达到一定程度也可以构成征收,并确立了判断管制性征收的四个标准,即“经济影响程度”标准、“破坏法律所认可的财产权”标准、“有害使用”标准和“平均利益互惠”标准,⑥ 在“经济影响程度”标准上,法院认为宾州煤炭公司的煤炭价值减损是巨大的,因为该法规剥夺了煤炭公司的支撑产权,将该财产从煤炭公司转移给马洪,因此这实际上剥夺了支撑产权所有人的全部财产利益。在“破坏法律所认可的财产权”标准上,法院认为该法规剥夺了宾夕法尼亚州法律所承认的土地中的产权——支撑产权——一种非常值钱的产权,致使完全丧失支撑产权的煤炭公司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有害使用”标准上,法院认为采煤导致地层的下陷只威胁到该地层上方马洪的房子,由于马洪在购买该房产之前已经知道其没有支撑产权,其购地时地价也随之相应地减少,因此煤炭公司的采煤行为不构成公共妨害。在“平均利益互惠”标准上,法院认为政府的管制行为如果带来的互惠好处或者“利益”可以补偿其损失,那么其管制行为就是合理的。但是在本案中,不存在此种互惠的利益,因为煤炭公司并无法从该法规中获益。因此,综合以上四个判断标准,法院认为该法规构成了管制性征收。 由此建立了管制性征收制度。然而,在这一经典判例诞生后的50年里,美国并没有出现第二个类似的案件,管制性征收制度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这一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为振兴经济,美国政府推行罗斯福新政,在经济政策上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国家开始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和立法。此时政府的治安权得到极大的扩张,私人财产权受到法规的限制也越来越多,这引起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抵制,但是在罗斯福总统的强力干预下,支持新政的自由派大法官逐渐取代保守派大法官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⑦ 在1937年之前,联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中,有6名属于保守派大法官,他们试图维持最少政府干预和私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观念,对政府干预经济的立法持反对的立场;另外3名属于自由派,对干预经济的新政法案持支持态度。然而在罗斯福总统实行“填塞法院”计划后,从1937年至1941年,原来9名大法官中有7人退休或去世,于是罗斯福总统任命了雨果·布莱克等7名自由派大法官。至此,联邦最高法院完全掌握在自由派大法官手中。 最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放弃了之前对经济立法进行严格司法审查的做法,而采用合宪性推定的原则,只是对涉及人权的立法仍然采用严格的司法审查。这种双重审查标准反映了法院对于私人财产权保护力度的减弱。⑧ JG.E.White: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New Deal.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从1978年至今,这一阶段为管制性征收制度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国家颁布了大量的管制法规,除了传统的区划法规,还包括环境保护法规、标志管理法规、文物古迹保护法规、租金管制法规和农地保护法规等。此时政府的治安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而这在促进公共利益的同时,也给私人财产权带来了过度限制的不利影响,导致针对管制性征收的索赔案件大量出现。并且,这一时期由于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崛起,美国对私人财产权保护又进一步趋于强化,尤其在里根总统执政时期,其不仅大力促进产权保护和实行减税政策,还任命了三位大法官⑨ 里根总统任命的三位大法官:保守派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1981年)、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1986年)、温和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1988年)。 ,使得保守派大法官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取得了多数,相应的联邦最高法院加大了对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因此,这一时期管制性征收制度得到极大的发展,各种新的判断标准也纷纷确立。1978年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诞生了一个经典案例,即宾州中央运输公司诉纽约市案⑩ Penn Central Transportation Co.v.City of New York, 483 U.S.104(1978). 。在该案中,纽约市的地标保护法将中央车站确定为地标,法律规定要想改变地标的任何外部设计风格或在原址上兴建任何新的建筑物都要经过地标保护委员会的批准。该车站的所有人宾州中央运输公司两次提出在中央车站上面建造一座55层写字楼的申请,但均被地标委员会以摩天大楼与中央车站建筑风格不和谐为由而予以驳回。于是宾州中央运输公司向州法院提起诉讼,称地标保护法限制中央车站的建设构成了管制性征收。最后案件被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判决地标保护法对中央车站的限制不构成管制性征收,从而无需给予补偿。[11] 在本案的判决中,多数大法官认为地标保护法对宾州中央运输公司的经济虽有一定影响,但并非是不合理的。因为公司已经将本案所涉土地用作火车站与办公室,而且它的原始投资也得到了合理的回报,同时,由于法规允许公司将其空间开发权转移到其在附近拥有的八块土地上,从而降低了法规对公司的负面经济影响。在政府行为性质方面,法院认为本案中地标保护法令只是限制了中央车站对其空间权的使用,但并没有侵入其空间权。在投资回报期待受损害方面,法院认为公司的主要投资期待是将其作为车站兼办公室,而且市政府也允许其继续以现有方式使用土地。因此,其基本的投资回报期待没有受到法规的干涉,公司损失的只是一种“机会损失”,即不能在中央车站之上建造一座摩天大楼,而不是法规禁止其继续以现有方式使用土地。 从该案件中提炼出来的“经济影响程度”“政府行为性质”和“干涉合理投资回报期待程度”三要素标准被称为多因素平衡标准,该平衡标准已成为当今美国法院判断管制性征收案件的主导标准。由于多因素平衡标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而联邦最高法院在后来的司法判例中也建立了一些更为清晰的辅助性判断标准,如在洛利托案和卢卡斯案中建立了“永久的实质性占有”和“剥夺全部经济价值”这两个绝对标准,[12] Loretto v.Teleprompter Manhattan CATV Corp, 458U.S.435(1982); Lucas v.South Carolina Coastal Council, 505U.S.1003(1992). 还在诺兰案和多兰案中发展出了专门适用于强制捐献的关联性标准。[13] Nolan et ux.v.California Coastal Commission, 483 U.S.285(1987);Dolan v.City of Tigard, 512 U.S.687, 114 S.Ct.2309 (1994).
(3)优化平台网站结构,增强平台的安全性,对于电子商务平台来说,其方位的数据量和网站本身的安全性,是有个至关重要的运营因素。有很多方法可以很好的实现,但是数据挖掘可以通过客户本身的拥塞和访问平台的性能,来提示平台管理者加以改进平台的各项访问策略。比如网站的缓存策略、网络传输策略、流量负载平衡机制和数据的分布策略等。同时还可以有效防止非法人员恶意访问平台,消除平台的弱点,提高站点可靠性,保证平台的正常运行。
三、 现今美国管制性征收的判断标准
美国管制性征收制度的发展一直是由法官基于宪法的规定而对治安权与私人不动产权利的相互关系进行各种不同的解释而推动的。由于判例法中各个法官的司法哲学不同,因此判例中管制性征收判断标准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完善的。[14] 彭涛:《论美国管制性征收的认定标准》,载《行政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 譬如早期在马洪案中确立的“有害使用”标准、“平均利益互惠”标准和“破坏法律所认可的财产权”标准虽然仍旧残存着,而且确实偶尔被少数法官所采用,但是它们基本上已被新的判断标准所取代。[15] John G.Sprankling, Understanding Property Law (3th ed.),New York: Michi Law Publishers, 2017. 现今美国管制性征收的认定包括以下三个判断标准与一个“背景原则”的例外规则。
腕管综合征(carpal tunnel syndrome,CTS)是很常见的神经周围卡压性疾病,正常人群中的发病率约为3.82%[1-2]。发病的原因是由于腕管内的压力增加或者是容积变小而导致正中神经受压,早期表现为桡侧2对半手指感觉麻木有时候伴有疼痛。当保守治疗无效时需及时切开减压以解除神经压迫,若不能早期解除压迫将导致大鱼肌萎缩从而导致拇指对掌功能障碍[3-4]。
(一)绝对标准
绝对标准是指永久的实质性占有标准和剥夺全部经济价值标准。由于这种标准与多因素平衡标准相比,该标准不需要对多个因素进行权衡,且更加简单明了,因此被称为绝对标准。
建设古今辉映的历史文化名城。大力实施繁荣文艺事业“311”计划,不断创作出“吴门力作”,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最精彩的一段”,做大做强“博物馆城”“百园之城”“世界遗产城市”“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品牌。大力扶持文化产业新兴业态,培育一批龙头旗舰项目。
1.永久的实质性占有
“永久的实质性占有”标准是指当政府或其授权第三者永久的实质性占有私人不动产时,就构成了管制性征收。该标准源于“洛利托诉曼哈顿有线电视公司”一案。本案的案情系纽约州法律规定,房屋出租人须允许有线电视公司在其出租的公寓上安装有线电视电线,原告洛利托认为此举构成了征收,因此向法院起诉要求有线电视公司给予补偿。
“背景原则”例外规则的提出与美国是一个普通法系国家密切相关,虽然美国也有制定法,但是其制定法都是普通法基本原则和规则的法典化,因此在两者的关系中,普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该例外规则要求政府的管制行为不仅要符合制定法,而且要符合这些制定法所体现的普通法的背景和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联邦最高法院在管制性征收的案件中,加大了对公民的私人财产权的保护。[46] Roderick E.Walston,“The Constitution and Property: Due Process,Regulatory Takings,and Judicial Takings”,32Utah Law Review(2001).P.379.
“永久的实质性占有”的构成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侵占的“永久性”[18] 永久性只是个技术性用语,它是一个表示侵犯财产权严重程度的标签。因为理论上没有一种占有是永久的,因为占有均可能因未来的某种原因而终止。 和“实质性占有”,二者缺一不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强调,根据这一标准,并非所有的实质性占有行为都构成征收行为。它严格区分“永久性占有”与纯粹的“临时占有”行为。如大学生偶尔在购物中心进行示威的行为[19] Prune Yard Shopping Center v.Robins,447U.S.74(1980). 或者农地的泄洪行为,这些“临时占有”行为对所有人的财产权干涉相对来说要轻微很多,它不会完全取消所有人的不动产的使用权或排他权,[20] Nolan et ux.v.California Coastal Commission, 483 U.S.285(1987). 因此这些不构成管制性征收。
2.剥夺全部经济价值
“剥夺全部经济价值”标准是指当政府的管制性法规的效果致使不动产的所有经济利益或者有效用途被完全剥夺时,就构成了管制性征收。该标准出自“卢卡斯诉南卡罗来纳海岸委员会”一案。[21] Lucas v.South Carolina Coastal Council, 505U.S.1003(1992). 在该案中,卢卡斯在南卡罗来纳州棕榈岛购买了两块住宅用地,计划在该地建造单户型住房,但两年后该州制定了全面保护海滨地区的管理法规,该法规禁止卢卡斯在该地建造任何住宅。
卢卡斯认为该法违反宪法修正案第5条和第14条而构成征收,于是向法院起诉。初审法院认定构成了管制性征收,判决给予卢卡斯120万元的补偿费。南卡州最高法院推翻了该判决,认为该制定法是为了防止公共妨害,这是治安权的正当行使,不构成征收。最后该案被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法院以五比四的判决将本案发回南卡州最高法院再审。撰写判决书的斯卡利亚大法官认为虽然联邦最高法院一般倾向于根据个案事实的调查来审理管制性征收案件,但是他还是确定了两种不经具体案件事实的调查就可以判定存在征收的情形,一种是管制性法规强制财产所有人忍受永久的实质性占有其财产;另一种则是管制性法规剥夺了不动产所有的经济利益或有效用途。[22] Agins v.City of Tiburon, 447 U.5.260 (1950 ). 本案的情形即属于后者,这种通过管制性法规要求将土地基本保持自然状态,使得土地所有人失去了所有经济上有益或者生产性用途,会带来以防止公共妨害的伪装下变成某种形式的公共服务危险,这要求政府为此支付补偿。[23] Lucas v.South Carolina Coastal Council, 505U.S.1003(1992). 斯卡利亚大法官在该案件中提出的剥夺全部经济价值的标准,被学者们认为提出了一个新的判断管制性征收的绝对标准。
这两个绝对标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努力将管制性征收判断标准明确化的一个表现,以建立一种简单明确的标准,将治安权的正当行使与管制性征收两者截然区分开来。
(二)强制捐献的关联性标准
2.政府行为性质
1.“基本联系”标准
基本联系标准是指强制捐献与政府的管制目的之间须存在本质联系,而不能是政府的主观臆断,否则该强制捐献行为就构成了管制性征收。
基本联系标准源于诺兰诉加州海岸委员会一案。[26] 同注[20]。 本案的原告诺兰在南加州的两块公共海滩之间有一块临海土地,原告计划在其土地上重建一栋房屋,而请求加州海岸委员会颁发建筑许可证。加州海岸委员会认为,在该地建房会妨碍公众使用海滩,并且会造成公众观赏海景的心理障碍和海滩的拥挤,因此政府要求原告须同意在其土地上设定公共地役权,以连接两块公共海滩,便利公众前来观赏海景,方能同意原告建房。诺兰认为这种强制捐献地役权属于未给予补偿的征收,因而向法院提起诉讼。
1.经济影响程度
目前,对木兰溪进行治理时,逐渐由原来的下游流域治理转向全流域全面治理,水利部门在此基础上,抓住发展机遇,转变了对木兰溪的治理以及发展观念,从而全面建设木兰溪的防洪工程,对木兰溪的干流进行全线治理,进而有效提高木兰溪的沿线安全,使防洪安全以及水环境治理和景观建设有效结合,为创建优美莆田城市、建设木兰溪百里风光带奠定良好的基础。
2.“大致比例”标准
“大致比例”标准是指强制捐献与开发项目的影响在性质和程度上须符合基本比例,否则该强制捐献就构成了管制性征收。该标准源于多兰诉泰格德市一案。在该案中,多兰计划将他在市中心的商店扩建,于是向市政府申请建筑许可。但市政府认为其商店的扩建有两个不利影响,一是会增加不能渗水地面的面积,易导致附近河流的洪水泛滥;二是因为扩建的商店将吸引更多的顾客,从而会加重所在街道的交通堵塞。因此市政府要求多兰将其地产的大约10%捐献给泰格德市,以用于建设暴雨排泄系统及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多兰认为该强制捐献构成了管制性征收,最后将该案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在该案中,代表多数意见的伦奎斯特大法官指出要判断该强制捐献是否符合宪法,必须先处理两个问题:一是该强制捐献的土地与州政府所促进的公共利益之间是否有基本联系;二是此种联系如果存在的话,该市所要求的强制捐献土地与原告计划开发项目产生的影响之间是否存在所必须的联系程度。对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该强制捐献的土地符合诺兰案的“基本联系”标准。因为捐献建设暴雨排泄系统的土地可以促进该市防洪的公共利益,捐献建设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土地与可以减少该市交通堵塞的之间也存在某种联系。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认为根据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要求必须存在“大致比例”,即该市必须具体列举所要求的每项强制捐献与计划开发项目的影响在性质与程度上均存在联系。根据这种新的标准,他认为起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的案卷中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捐献洪泛区土地的合理性,因为原告本来就未利用该块防洪的土地,因此看不出为何要将其转为公共产权。况且市政府宣称该区域用作休憩之用,亦与防洪无关。同样地,他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捐献建设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土地与减少交通流量之间存在程度和比例上的合理关系。市政府只是提供简单证明认为,建设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可以降低市区里车辆需求,减轻交通负荷,但是并没有定量化证明交通流量因为原告扩建商店所增加的程度,也没有定量化证明人行道与自行车道确实可以缓解增加的交通流量。因此,基于以上理由,多数大法官认为该强制捐献土地虽然满足基本联系标准,但是不符合大致比例标准,构成了管制性征收,于是将本案发回俄勒冈州最高法院再审。
可见,“大致比例”标准是将诺兰案确立的“基本联系”标准进一步量化,且比“基本联系”标准的要求更高,其不仅要考察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联性,而且还要考察两者间的关联程度。这也反映了联邦最高法院加大了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
聚谷氨酸是使用微生物发酵法制取的生物高分子,具有优良的水溶性、超强的吸附性和生物可降解性,降解产物是无公害的谷氨酸,在农业上可促进植物根系发育,增强植物抗病及抗逆能力。进入本世纪,个别国际知名公司开始进行含聚谷氨酸复合肥、水溶肥的生产和应用的研究,含聚谷氨酸磷酸二铵产品生产在世界上尚属首次。
土壤孔隙率:用已知容积(V)的环刀切削土壤,使土样充满环刀,再用天平称量环刀中土壤的重量(m1),在烘箱(105°C)中烘干土壤水分,称量烘干后土壤的重量(m2).再将环刀垂直全部压入土样,将土装入容器(记容器重量为m3),在烘箱(105°C)中烘干土壤水分至恒重记为m4,则
(三)多因素平衡标准
如果政府的管制行为既不是永久的实质性占有和剥夺财产全部经济价值的行为,也不是强制捐献,而仅仅是减少财产价值的过度限制私人财产的行为,那么法院就可以采用多因素平衡的判断标准。多因素平衡标准是一种视具体案情而异的个案审查和综合考虑多种要素,以判断政府的管制行为是否构成征收的方法。多因素平衡标准重点考察的有三个要素,一是“经济影响程度”,二是“政府行为性质”,三是“干涉合理的投资回报期待程度”。
联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判决加州政府必须给予补偿。由斯卡利亚大法官所主笔的多数意见认为,根据案情,此案的审查标准不同于正当法律程序的案件,亦即并非以政府是否合理地决定管制措施为准,而是以管制措施是否能实质促进管制目的而定。依据此项标准,斯卡利亚认为强制捐献地役权与管制的目的之间欠缺基本的关联性。因为海岸委员会管制的目的在于保护公众观赏海滩的能力,以及帮助公众克服使用海滩的心理障碍和避免海滩拥挤,但是斯卡利亚认为既然已有公共海滩,为何又需要通行原告的土地以观赏海景?他也表示无法理解捐献地役权如何消除公众使用公共海滩的心理障碍,以及如何降低因原告的房屋所造成的拥挤。[27] 同注[20] 斯卡利亚并且表达他对政府的不信任,他认为财产权受到限制时,必须以治安权是否实质地促进管制目的为标准,以防止政府藉由本案的交换条件逃避补偿的责任。因此,基于以上理由,法院认为该强制捐献地役权不是为了这些目的而行使其土地使用管理权,而是“彻底的勒索计划”,构成了管制性征收,须支付补偿。
经济影响程度是指政府的管制行为造成私人财产价值的减损程度。管制行为给财产权人的财产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易被法院认为构成管制性征收,而造成较小的经济损失则容易被认为是治安权的正当行使。
[32]新华社:《中国电视剧出口泰国面临三大困扰》,http://m.silkroad.news.cn/article/6848,2017年4月7日。
在考察政府管制措施对私人财产减损程度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前提问题便是作为受侵犯的财产利益的参照系的财产利益范围的界定问题,美国法学界一般称为分母问题。[28] Kiefer, Christopher.Reconciling the Internal Inconsistency and Resolving the Denominator Problem in Takings Law.The Boston University Public Interest Law Journal,2000,16:171. 分母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洪案,在该案中,霍尔姆斯大法官认为应当将财产中受到法规限制的部分财产分割出来,然后将分母仅仅适用于这部分财产。大法官布兰代斯不同意霍尔姆斯的观点,他指出正确的分母应是煤炭公司所拥有的“整个财产”,财产价值减少的程度只有把受法规限制“开采相应位置的煤炭价值”与“全部煤炭的价值”作比较才能得出。大法官布兰代斯的上述观点后来成为大法官布伦南在宾州中央运输公司案中采用的规则。大法官布伦南认为“应当适用征收条款的正确部分是公司拥有的全部财产,而不仅仅是纽约市不批准在中央火车站上方修建一座高层办公大楼的空域。征收的司法实践不会将一个整体财产分割成各个部分,并作出每一个特定部分的权利是否被完全剥夺的决定。在认定一个特定的政府行为是否构成征收的时候,法院关注的是对财产整体的侵犯的性质与程度。”该原则后来被称为“整体的财产包”原则。“整体的财产包”原则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卢卡斯案”的判决以后变得愈发重要。
为了在管制性征收诉讼中胜诉,财产权人总是想方设法地运用各种方式将财产分割成各个部分,然后主张其分割部分的财产被政府完全征收了,这种行为被称为主观分割。[29] Radin Jane, Margaret.The liberal Conception of Property: Cross Currents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Takings[J].Columbia.Law Review.1988,88:1667. 如果任由财产权人随意对其财产做出分割而不作任何限制,那么管制性征收几乎自动构成,这将严重妨碍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行使。因此在管制性征收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财产权人的主观分割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概念分割。目前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已经明确表示反对财产权人将其财产权分割成各种权利而以此主张该项权利被征收。如在宾州中央运输公司案中,法院拒绝了原告提出的其火车站上空的空间权被征收的诉求,认为政府行为对财产的经济影响程度应从车站整体来考虑。而在吉斯通烟煤协会案中,法院也拒绝了原告提出的将煤矿支撑产权分割出来构成独立财产的请求。[30] Keystone Bituminous Coal Association v.DeBenedictis,480 U.S.470(1987). 二是时间分割。在这方面联邦最高法院也是持反对态度。在塔霍湖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采用了它在“宾州中央运输公司案”中采纳的“整块土地”规则,并且判决土地所有人无法“将一块暂缓开发32个月的土地与每个土地所有人的非限嗣继承地产的剩余部分分离,然后主张那块土地被暂缓开发的决定构成征收。”[31] Tahoe-Sierra Preservation Council, Inc.v.Tahoe Regional Planning Agency, 535 U.S.302,122 S.Ct.1465 (2002). 因为该地产不会由于其经济利用被暂时禁止而变得毫无价值,一旦土地禁止利用被解除时,该项财产即恢复到它原来的价值,所以法院判决政府的暂缓开发条例不构成管制性征收。三是地理分割。在这方面法院的态度虽然并非始终如一,但在多数情况下,在涉及这一类质疑分区条例的征收案件中,法院往往将整个地产视为整块土地,即使地产的不同部分被划归不同的区域。[32] See Romona Convent of the Holy Name Alhambra, 26 Cal.Rptr.2d140(Cal.App.1993). 综上,总体而言,目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倾向于对财产权人财产的主观分割进行比较严格的限制,尽量扩大作为分母的财产包。
强制捐献是指政府为减少建设工程项目的不利影响,要求开发商向社会公众捐献土地、改善物或其他利益作为地方政府批准开发商开发其土地的条件。[24] 同注[15]。 由于强制捐献涉及到政府强制索取私人不动产权益,因此其司法审查标准十分严格,近来联邦最高法院采用“基本联系”与“大致比例”的关联性标准来判断强制捐献是否构成管制性征收。[25] 土地开发许可为什么可以成为一种对私人财产权的限制?这是因为政府设定许可实质上是对该许可领域进行一定的管制,并且许可授予之后还将伴随着监管。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经贸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整体技术水平、企业管理能力、资本累积、工业体系、人均收入水平以及总体供给能力与整体消费实力显著提高,引领我国开放发展由“引进来”迈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新格局;二是西方国家开始着手构建以“竞争中立”“管制一致性”等为内核的新的全球经贸规则体系,将开放发展的谈判与改革议题拓展至海关之外的“非关税”领域;三是我国比较优势体系发生结构性变迁,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四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趋缓,需求萎缩。
政府行为性质是宾州中央运输公司案提出的三要素之一,在该案件中法院对政府行为性质的解释是“与政府调整经济生活的利益与负担以便推进公共利益的时候相比,当政府的行为是实质性占有财产的时候,可能更容易构成征收。”[33] Penn Cent.Transp.Co.v.New York City, 438U.S.104(1978).124.
由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述解释非常模糊,因此导致了该要素在司法实践中有着不同的理解。相比较而言,以下三种是较为准确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是指政府行为的方式。即考察政府行为是“实质性占有”还是“限制使用”私人财产。由于“限制使用”相较于“实质性占有”侵犯性更弱,其不易构成管制性征收。如在宾州中央运输公司案中,法院认为地标保护法规只是限制了宾州中央运输公司对其车站上空空间权的利用,但并没有侵占其空间权。因而法院判决地标保护法规不构成管制性征收。第二种理解是指政府行为是否废除了基本财产权利中的特性。该种含义源于霍德尔诉欧文案,[34] Hodel v.Irving,481 U.S.704 (1987). 在该案中,国会为了防止印第安人保留地由于继承导致土地过度的分割的问题,通过了一部《印第安土地合并法》,该部法律规定印第安人不得将其所拥有的小块的土地在死亡时传给其继承人,土地应转归保留地,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土地的地块过于零碎的情形。欧文认为该法令对其土地构成了管制性征收,于是向法院起诉。该案最后被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法院以多因素平衡标准进行审查后认为,经济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也不存在据以投资的预期,但是法院认为政府行为性质有问题,即它实际上剥夺了财产所有人将财产权转移给继承人的权利,而遗赠权自封建社会以来一直是英美法系的一部分,对遗赠权的剥夺,就像对排他权的侵犯,这给财产所有权人施加了特别重要的负担。因此法院认为该部法律构成了管制性征收。第三种含义是指管制行为适用的范围。如果管制的适用性越普遍,如更多的人、更大的范围和更广泛的受影响利益,则不容易构成管制性征收;反之,如果管制的对象仅仅是针对特定的个体,则容易构成管制性征收。如在东部企业诉阿普菲尔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将政府管制行为是否针对特定的个体作为政府行为性质因素加以考虑。法院认为,因为该法规将“一些雇主挑选出来,让他们为遥远过去的行为承担大量的负担”,所以它的性质是非同寻常的。[35] E.Enters.v.Apfel,524U.S.498(1998). 因此,该部法规构成了管制性征收。由于该种含义涉及到了征收法的目的,即防止政府使某一部分人承担了根据公平和正义的原则本该由作为整体的公众所承受的负担,因而这也是一种恰当的理解。
3.干涉合理的投资回报期待程度
合理投资回报期待是指财产权人基于法的安定性要求以及对政策连续性的信赖,对政策或行政行为所产生的合理的期待及相关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36] 李锡锌:《行政法上的正当期待保护原则述论》,载《东方法学》2009年第1期。 当其因政府的管制行为而受到严重干涉时,导致财产权人的合理的投资回报期待无法实现,政府的管制行为就容易被认为构成了管制性征收。
有鉴于此,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司法判例对合理投资回报期待的过度适用的现象进行了限制。在卢卡斯案中,斯卡利亚大法官指出,加州海岸委员会的关于在海岸建造或者重建住房而附加公共通道的公告,不能否决财产权人所拥有的排除公众在其私人海滩上散步的期望。[40] Nollan v.Cal.Coastal Commission, 483 U.S.825(1987).856. 而在帕拉佐罗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为合理投资回报期待的正确适用提供了指导意见。在该案中,根据“注意规则”,罗德岛最高法院认为,帕拉佐罗在取得财产时已经知道相关管制措施的存在,其缺乏合理的投资回报期待,因此判决帕拉佐罗败诉。然而,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罗德岛最高法院的这一做法,认为不能仅因为财产权人在颁布相关管制法规之后才获得了财产这一事实而驳回财产权人的诉求。因为财产权人虽有服从政府管制的义务,但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政府的管制措施极不合理,对财产权人施加了难以承受负担,而这种不合理性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那么财产权人即使在管制性法规颁布后才取得财产,其仍然有权获得补偿。然而,法院也并不认为财产权人取得财产时对管制法规的知情与财产权人的合理的投资回报期待完全无关。奥康纳大法官认为,财产权人在取得财产时对管制性法规的知情与财产权人的合理投资回报期待是相关的,但在特殊情况下还要综合考虑其他相关的因素。最后,法院认为“合理投资回报期待只是多因素平衡标准的一个因素,不应该以财产权人是否具有合理投资回报期待作为否决征收诉求的决定性因素”。[41] Palazzolo v.Rhode Island, 533 U.S.606(2001).606. 该案是对合理的投资回报期待认定标准的新发展,并对合理投资回报期待在管制性征收判断标准中的地位作出了恰当的定位,对于合理投资回报期待要素的妥当运用具有重要意义。[42] 郑嵘:《美国管制性夺取制度研究》,厦门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判断财产权人的投资回报期待是否合理时,一个重要的参考就是财产权人取得财产时所处的管制环境,如普通法、州财产法和已存在的相关管制性法规等。[37] Michael M.Berger.Happy Birthday, Constitution: The Supreme Court Establishes New Ground Rules For Land-Use Planning[J],Urbatsch Law Review.1988, 20:765. 在判断标准方面,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注意规则”,即财产权人如果在取得财产之时就已经知道对其财产施加限制的管制性法规的存在,那么其对该财产以被限制的方式的使用就不具有合理投资回报期待。[38] Steinm, Gregory, Takings in the 21st Century: Reasonable Investment-Backed Expectations after Palazzo lo and Tahoe-Sierra,Tennessee Law Review, 2002,69:891. 虽然合理投资回报期待对于财产权人的滥诉行为构成了必要的制约,但是合理投资回报期待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矫枉过正的趋势,以致使管制性征收制度在平衡政府的治安权与私人财产权的过程中过分偏向了政府,其中一个显著表现就是出现了推定注意规则。该规则是指在财产权人取得财产之时,即使政府限制财产的管制性法规尚未制定或生效,但是如果法院推定财产权人注意到潜在的管制制度,并能够合理预见到法律可能会限制其财产,那么财产权人就不具有合理投资回报期待。[39] Ruckelshaus v.Monsanto Co, 476U.S.986(1984).1008. 此外,合理投资回报期待在多因素平衡标准中的地位愈加凸显,法院甚至将财产权人有无合理投资回报期待作为判断管制性征收的决定性因素。这对于财产权人极不公正,而且由于推定注意规则的主观性太强,使得其容易被法官滥用,以致受到了诸多的批评。
本文以案例研究法分析咪蒙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与管理情况,通过对咪蒙公众号的运营情况介绍,运用媒介成功标准理论的各项准侧、媒介领袖人物的价值来探讨该公众号的经营管理成功经验。
一体化制图平台是基于ArcGIS 10.1开发的,其中,制图表达是基于规则的高级智能化制图方式,作为要素类的属性存储于建库数据中,在属性中增加Rule ID字段记录要素的符号信息。一体化制图平台能快速完成地图的符号化和注记自动配置,具备境界跳绘、河流渐变、提取地类界、植被转点等多种统改工具,使1∶10 000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快速出图得以实现。
改革探索中,普洱率先在全国推行绿色经济考评制度,景东等17个县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量化到干部考核,针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事件,实行综合考评“一票否决”;玉溪市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建立覆盖全流域的责任体系,实施环境监管网格化,在全省率先建成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点位覆盖全市各县区……
总之,多因素平衡标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法官在运用该标准中主观性较强,自由裁量权也比较大,但是法官的裁决须遵循一个中心规则:“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征收条款是要防止政府强迫个人单独承受根据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应当由作为整体的公众所承受的负担”。[43] Armstrong v.United States, 533 U.S.606(2001). 在该规则的指导下,法官在管制性征收案件的判断中须将上述三个要素结合在一起来进行全面审查和综合权衡,以判断政府的管制行为是否对财产权人施加了超过了其应承担的社会义务的负担。如果多数法官认定政府的管制行为导致财产权人承受了过重的不公平的负担,使其遭受了特别的损失,那么政府的管制行为就构成管制性征收,政府应该给予公平补偿,以实现“恢复当事人间公平”的目标。
(四)“背景原则”的例外规则
“背景原则”的例外规则是指导致私人财产经济上的有益利用失去一切可能性的政府的管制行为要避免构成管制性征收,除非该管制行为既符合财产法等制定法规范的要求,又符合这些制定法规范所体现的普通法基本原则的要求。[44] 美国财产法和妨害法的背景原则有管制普通法上“妨害”、公共信托规则、公共航行地役权和火灾紧急事件等。如果政府的管制行为符合这些背景原则,那么政府的管制行为就可以无须补偿而取消财产权。
该例外规则出自卢卡斯案,在该案的判决意见书中,代表多数意见的斯卡利亚大法官认为“有害使用”标准仅是法院先前对维持一个减损私人财产价值的管制而无须补偿这一点进行说明时所做的尝试而已。某一管制行为到底是属于防止有害使用还是属于促进公共利益,必定因人们基于不同的视角而见仁见智,要在两者之间作出区分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有害使用”的标准就不能作为判断管制性征收的依据,仍然须以财产的经济使用价值遭到完全剥夺为准。事实上,先前以防止财产有害使用为由不构成征收的判例,原告的财产损失都未达到完全被剥夺的程度。然而,他认为此项标准仍然有例外。亦即当所有人的财产权显示被限制使用的利益并非自始属于财产权的范畴时,则该限制并不构成征收。斯卡利亚大法官认为财产权虽然负有内在义务,可以受到治安权的限制,但若因此就剥夺财产权人所有的经济利益,便与宪法文化所记录的历史契约不合。他认为唯有该限制自始存在于财产权本身,亦即依据州的财产法及妨害法的背景原则,该财产自始负有此种限制时,该项造成严重损失的管制才可以不必补偿。[45] Lucas v.South Carolina Coastal Council, 505U.S.1027(1992). 依据此项标准,斯卡利亚大法官认为南卡州政府仅表示原告财产的使用违反公共利益或普通法格言“使用你自己的财产时不得损害别人的财产”等结论性主张尚不足够,南卡州政府仍需举证依照该州的财产法及妨害法的背景原则,原告的财产使用属于被禁止的行为。因此,联邦最高法院将本案发回南卡州最高法院就上述未举证的部分再审。
本案的多数意见由马歇尔大法官主笔,他首先引用先前的判例并指出,当存在某种得到政府授权的永久的实质性占有的时候,不论其所促进的公共利益多么重要,也不论其对所有人的影响有多么轻微,法院一向都是认为构成征收。[16] 458U.S.419(1982). 其次,他强调此种永久的实质性占有行为使得所有人无法对该部分财产行使排他、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能,而排他权正是财产权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对于这种极端情形,法院认为所有人享有历来就存在的补偿期待权。因此,基于以上理由,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永久的实质性占有对财产权侵害的严重性远非其他管制措施所能相比,其本质上就是征收。[17] Id.at436-38.
综上,美国管制性征收制度实质上是一种财产权保障机制,该制度的建立彰显了美国司法机构对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努力。在近一个世纪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逐渐发展出上述判断管制性征收的三个标准与一个“背景原则”的例外规则。这些标准在法院审理管制性征收案件中不断被使用,而且每一个标准都在提出后被随后的判例不断地进行细微的调整与发展。因此美国管制征收的判断标准是有生命力的,处在不断的发展完善当中。[47] 同注[14]。
四、现今美国管制性征收的救济措施
在1970年中期以前,一般认为对于管制性法规限制私人财产权过度,以至于构成管制性征收时,唯一的救济方法就是宣告该管制法规无效或者类似衡平法救济措施[48] 衡平法的救济措施:禁止令、特定履行、废除和改正。 ,以避免妨碍政府治安权的正当行使。然而,在经过几十年的不确定状态后,现今的法律规定非常明确,管制性征收的救济措施是公正赔偿。
3.过度包装,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片面、错误的消费观念。在商品买卖中,支撑整个商品贸易活动的核心在于其使用价值。过度包装行为,则是将包装这一“无效”属性放在了核心位置。这是一种不健康的消费观念,其背后折射的是不成熟的消费模式。
该救济措施源于1978年的圣地亚哥煤电公司案和1987年的第一英国福音派路德宗教会案,[49] San Diego Gas & Electric Co.v.City of Tiburon, 447 U.S.225(1978); First English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v.County of Los Angeles(1987). 在这两个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逐渐明确了管制性征收的救济措施是公正补偿。在圣地亚哥煤电公司案中,因圣地亚哥市政府的区划将煤电公司的工业用地改变为农业用地,初审法院与上诉法院都认为市政府的区划构成管制性征收,因此判决市政府给予煤电公司由工业用地变成农业用地所减少的价值三百万美元的补偿费。然而加州最高法院却将本案驳回,建议依照阿金斯案的二选一的判断标准重新判决,[50] 即一项管制性法规如果没有实质性地促进正当的国家利益, 或者使得所有人的财产变得不具有经济上可行的用途, 就构成征收。 于是上诉法院因此推翻地方法院的判决。本案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法院认为本案因缺乏加州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因此以该院无管辖权驳回上诉。在该案件中,布伦南大法官提出了著名的不同意见书,他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案件有管辖权,而且管制性征收应给付公正补偿。因为依据马洪一案,管制性法规有时会越过治安权正当行使的界限而构成征收,而管制性征收基本上和其他须给付补偿费的征收并无不同。虽然管制性征收可以经由政府的修正或废除造成侵害的法规,从而消除管制性征收的状态,因而只有临时的,而非长期的管制性征收,但是在此种情形联邦宪法规定必须付给从管制法规开始造成管制性征收时至政府废除或修正法规时止,此段时间的公正补偿。[51] 谢哲胜:《财产法专题研究》(二),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 布伦南大法官所提出的临时性的管制性征收,须给予公正补偿的意见于1987年的第一英国福音派路德宗教会案被联邦最高法院所采纳,在该判决意见书中,法院认为征收条款的目的“不是限制政府干涉财产权利本身,而是发生构成征收的正当干预时可以得到补偿”。[52] First English Evangelical Church v.County of Los Angeles, 482U.S.315(1987). 因此,该案中胜诉的原告第一英国福音派路德宗教会可以取得管制行为给其土地带来不利影响之日与判决之日期间的补偿。不过,教会无权要求将“临时征收”改为长期征收,因为这可能违背政府的意愿使用征收权。然而,政府享有选择权,其既可以选择修正管制性法规或撤销违法的管制行为,也可以行使征收权。如果政府选择维持相关的管制行为,财产权人有权取得长期管制性征收的补偿。如果政府选择修正管制性法规或撤销管制行为,财产权人只能取得管制行为生效期间发生的临时管制性征收的补偿。
长期管制性征收的损失补偿的计算方法与传统征收的情形是一样的,财产权人有权取得征收当日财产的合理市场价格。而临时管制性征收的损失赔偿计算方法相对复杂一些,虽然在理论上临时管制性的补偿是该征收期间的财产用途合理的市场价格,但是这一标准通常难以适用。因为典型的管制性征收案件涉及的是政府限制空地未来用途的行为。[53] 同注⑮。 例如,如果不存在该管制条例,某甲可能在空地上已经兴建了所计划的酒店。如果只补偿甲的土地处于未开发状态的合理的租金价格,对于酒店的收入而言,属于不完全补偿。但是酒店可能经营不善,因此潜在的利润损失很不确定,不能作为补偿的计算依据。在这种情形下,多数法院会查明存在该管制行为与没有该管制行为之间的不动产价值差额,然后再根据这一差额和合理的市场回报率来计算补偿数额。
③使用该软件可在计算模型内查取任意位置滑弧的安全系数,据以确定可能的滑动区域,指导除险加固方案的科学合理选取。
五、美国管制性征收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管制性征收制度历时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其在平衡私人财产权和政府管制权力之间矛盾的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吸收借鉴该制度的合理内核,这对我国的财产征收制度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立足我国具体国情,可以得出以下三点有益的启示:
(一)创立管制性征收制度
为了防止政府的管制权力过度扩张,保护私人财产的合法权益,我国应该建立管制性征收制度。虽然我国法律上没有管制性征收这一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法律上的管制性征收概念无法建构。从上文的司法判例梳理中可以发现,美国的宪法中也没有管制性征收的概念,管制性征收概念是从“征收”概念中发育出来的——如果管制“走的太远”,产生了与征收类似的效果,就构成了管制性征收。[54] 刘连泰:《确定“管制性征收”的坐标系》,载《法治研究》2014年第3期。 因此,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的管制性征收概念也同样可以从我国的征收概念中发育出来,我们只要对我国宪法第10条和第13条中的“征收”的含义进行扩张解释,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55] 我国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13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依据宪法解释的方法,我们可以将这两个条款的“征收”作广义的理解,使其既包括传统的征收,也包括因私人财产权受到政府管制行为过度限制而构成的管制性征收。这样,既从宪法层面上为管制性征收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又避免了轻易地修改宪法,维护了宪法的稳定性和严肃性。其次,建议在《物权编》中引入管制性征收制度。我国目前正在对民法典的物权编进行编纂,我们可以借这次物权法修改完善之机,在其《物权编》中规定财产征收的种类。如可以规定我国的财产征收分为三个类型,一是征收,二是管制性征收,三是征用,然后对其内涵分别进行界定。最后,在时机成熟时应当制定统一的《财产征收法》。对管制性征收的定义、补偿原则、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和救济途径内容作具体的规定。例如,法律可以规定:管制性征收是指政府或政府的授权机构的管制行为对财产权人的财产施加了过度限制,导致了财产权人特别牺牲时需要公正补偿的行为。管制性征收的补偿原则以公正补偿为原则;补偿标准是以公平市场价值为标准;补偿的方式是以货币补偿为主,其他补偿方式需要征得被征收人同意方可;管制性征收的救济方式有协商、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这三种方式。
(二)设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判断标准
美国管制性征收判断标准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和吸收,但是不意味着我国可以完全照搬。因为美国是普通法系国家,遵循先例是其原则,虽然美国的多因素平衡标准看似灵活,但是其要受到先前司法判例的严格约束。而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如果没有固定的标准,任由各级法院的法官自由裁量,这势必会造成管制性征收判断标准的混乱。因此我国需要建立符合国情的管制性征收判断标准。
我国管制性征收判断标准的构建,建议采用“公害标准-形式性标准-实质性标准”三步走的判断标准体系。第一步,从公害标准出发,法院须首先判断政府管制的财产是否构成公害[56] 公害在我国是指凡污染和破坏环境对公众的健康、安全、生命及公私财产等造成的危害。由于该种定义过于宽泛,建议借鉴日本环境基本法对公害的界定,将公害限制在大气污染、恶臭、噪音、水质污染、振动、土壤污染和地基下沉等七种现象。 。若是,则无论给私人财产价值减损多少都不构成管制性征收;若不是,再走下一步。第二步,对于不是防止公害的管制行为,法院须采用形式性标准来判断是否构成管制性征收。此时法院须审查政府管制行为的对象是普遍的民众还是特定的个体,若是普遍的民众,基于公平负担的原则,一般不宜认为构成管制性征收;若是特定的个体,再走下一步。第三步,针对管制对象是特定个体的管制行为,法院须采用实质性标准来判断是否构成管制性征收。就实质性标准而言,法院须要考察政府的管制行为是否因限制财产权人的处分权而造成财产的经济价值损失70%以上,[57] 因为政府的管制行为没有取得私人财产的所有权,而只是仅仅限制财产权人对其财产的处分权,其侵犯私人财产权的方式较轻,因此政府的管制行为只有造成严重程度的经济损失才能产生类似征收的效果。其次,美国对管制性征收的认定也十分严苛,不轻易判定政府的管制行为构成管制性征收。当然,本文只是给出一个初步的建议,这一比例是否合适,或者采用其他比例如60%,仍需进一步论证和讨论。 或者政府行为是否对财产的某个部分进行了“永久的实质性占有”,若是,则一般构成管制征收;若不是,则一般不构成。对于造成私人财产价值减损比例低于70%,但高于30%的管制性行为,虽然不构成管制性征收,但构成了过度限制,财产权人可以请求政府改以限制程度较轻的管制方式或者给予财产权人土地发展权,以减轻财产权人的经济损失。对于造成私人财产价值减损比例低于30%的政府的管制行为则属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是私人财产为了社会的公共利
我国政府的管制行为构成管制性征收,也应当给予公正补偿。为管制性征收建立起良好的补偿制度,不仅有利于政府将管制行为的成本内部化,使政府更加谨慎地行使公权力,而且有利于补偿财产权人所遭受的损失,保护公民的私人财产权。
在补偿原则上,我国的管制性征收的补偿应当实行公正补偿原则。所谓公正补偿原则应该是完全补偿原则,指政府应对被征收人因管制性征收所发生的一切损失给予完全的补偿,使被征收人恢复到没有被征收前的状态。虽然该补偿原则可能为政府带来过重的经济负担,但无论从社会发展、权利保护和法治建设考虑,还是从公平正义角度出发,采用“完全补偿”原则,应当是未来我国财产征收补偿的大势所趋。[58] 沈开举:《行政补偿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为此,在适当时机我国应当将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公正补偿”。以及将宪法第13条第3款规定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公正补偿”。在没有修宪之前,我们应当依据宪法解释学的方法将上述宪法条款中的“补偿”理解为“公正补偿”。
在补偿标准上,我国的管制性征收应该实行市场价值的补偿标准。所谓市场价值标准,是指在一个自由公开的市场上,就被征收的财产而言,一个自愿的买方所愿支付的价格。[59] See Westchester Country Park Comm’n v.United States, 143 F.2d 688,692(2d Cir.1944). 由于市场价格补偿比较客观和公正,操作性比较强。因此在目前各国征收的实践中,大多都以财产的市场价格进行补偿。在补偿方式上,我国管制性征收应当以货币补偿为主,其他补偿方式需要经被征收人同意方益所应承受的正常负担。
(三)建立公正补偿的救济措施
可,坚决杜绝由政府违背被征收人的意愿单方面决定补偿的方式。
在补偿的计算上,可以分为如下两类:对于长期的管制性征收,被征收人的损失补偿可以依据被征收当日的财产合理市场价格来估算,估算方法可以采用可比销售法[60] 可比销售法是指参考类似财产在该地区最近的销售价格来估算财产的市场价格。 、总体收入法[61] 总体收入法是指根据财产的现有价值而计算的净收入来决定财产的市场价格。 和复制成本法[62] 复制成本法是指根据当前市场上更换或重新购置被征收财产但减去折旧的成本来估算财产的市场价格。 这三种估价方法。对于临时管制性征收,其损失补偿的计算相对复杂一些,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多数法院的做法,即查明存在该管制行为和没有该管制行为之间的不动产价值差额,然后根据这一差额再结合市场回报率来计算补偿的数额。
六、结语
通过以上对美国管制性征收制度的梳理和分析,从中可知,管制性征收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美国为保护私有财产权,防止政府的管制行为过度限制私人的财产而产生的。为了限制政府的管制权力过度扩张,更好地保护私人的财产权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上个世纪20年代通过马洪一案创立了管制性征收制度,赋予了所有人在其财产受到过度限制时而请求法院予以司法救济的权利。然而,由于我国目前管制性征收制度的缺乏,导致私人的财产在受到政府的管制行为过度限制时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这严重损害了私人的财产权益。随着现代福利国家和行政国家的崛起,这些过度限制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的立法和行政管制措施在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多,这亟待我国建立相应的管制性征收制度。因此,以管制性征收为切入点,探究美国的管制性征收制度,借鉴其有益的经验,这对于构建我国的管制性征收制度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文系博士后基金“管制性征收制度研究”(项目编号:2017M611947),国家社科基金“美国管制性征收制度研究”(项目编号:14CFX010),“双一流”建设文化传承项目专项(项目编号:2018WHCC08)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 许迎春,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系副教授,法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
标签:管制性征收论文; 判断标准论文; 治安权论文; 私有财产权论文;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