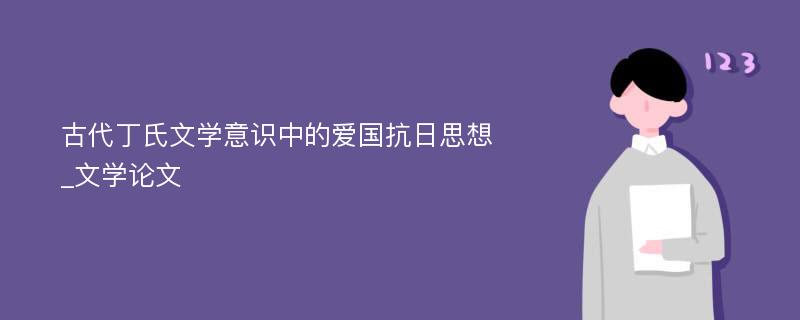
古丁文学意识中的爱国抗日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论文,意识论文,思想论文,丁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古丁是东北沦陷时期的一位爱国作家,他投身文学事业,并利用文学进行反满抗日活动,他在《明明》期刊的创办过程中,他的文艺主张和创作实践,均印证了他作为一位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有良知的中国人、中国作家的铮铮铁骨和赤诚之心。
古丁从关内回到东北之后,即投身于文学事业,他虽然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高举起文学救国的旗帜,但在整个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创作中,还是能使人看出他文学意识中的进步意义的。从他和疑迟、滕更(即外文)组织的艺术研究会起,到辞官为民办起“艺文书房”专事文学创作和出版业止,将近10年的时间,一直在利用文学进行反满抗日。本文拟就几个具体问题,谈谈古丁文学意识中的爱国抗日思想。
(1)关于《明明》的创刊。
《明明》是1937年3月在长春创刊的, 它的创办者是日人稻川先生。稻川任编辑主任,毛利担任编辑,古丁虽然未任什么角色,但为刊物出谋划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刊创办初期,只是一个通俗性的综合读物,文学色彩并不鲜明。从一卷六期开始,改为纯文艺月刊,吸引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文学爱好者。尤其是出刊了创作特辑,编发了古丁的《暗》、小松的《夕刊的消息》、田兵的《老师的威风》、疑迟的《江风》、徐狄的《雨夜》、零影的《请老师》等6篇短篇小说, 更引起了文坛的注意,继创作特辑之后,时逢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为了纪念鲁迅先生的逝世,又出刊了《鲁迅纪念特辑》刊登了毛利(率嘉)、罗绮、徐狄等人的悼念文章,还有古丁由日文翻译的《鲁迅著书解题》,比较详尽地介绍了鲁迅先生一生的著述。接着,《明明》还出版了一期日本文学特辑,介绍了日本进步作家夏木潄石、石川啄木等人的文学作品,这样,《明明》在东北文坛上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占据文艺阵地,《明明》同仁提出了“写与印”的主张,埋头写作和出书,以填补文学作品缺乏的现状。于是,在1938年出刊了特大号的“百枚小说”,即400字原稿纸100页的作品。此后,还在“万民之所需”的目标上,借助日人城岛舟礼的资助,创办了以城岛舟礼的名字作为丛书总称的《城岛文库》,出版了古丁的《奋飞》、疑迟的《花月集》、小指的《蝙蝠》3本短篇小说集,另有古丁的杂文集《一知半解集》, 百灵的诗集《火光》。所有这些,都会使人看到《明明》出刊的功绩,就是有些对《明明》同仁存有异议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古丁等人在开拓东北文坛上是有功劳的,特别是认为《明明》的创刊,使文艺有了新的生机。
早在艺术研究会成立之时,古丁等人就想创办一个刊物,但苦于没有资金不能如愿。后来,经笑迷先生介绍见到他的老师稻川先生时,稻川先生主动提出:“我要办一种汉文杂志,你帮帮忙。”古丁欣然答应了。因为这正符合他们的心愿。但杂志叫什么名字呢?稻川先生把早就起好的名字告诉古丁:“志名叫《乐土满洲》,好吧!”当时笑迷和古丁都不表示赞意”。他们想了几个志名,如《骆驼》、《绿洲》、《沙漠》、《珊瑚》等,可稻川先生也不表示赞意。随之,他从兜里掏出来创刊号的目录:“大臣访问记,职业妇女访问记,恋爱新讲,东洋的性药,柳巷探险……没有一篇文艺。”于是,他们的意见更有了差异。此后,他们围绕“乐土”与“沙漠”,“春药”与“文艺”争论了三个月之久,最终诞生了《明明》。
另外,从《明明》的编辑情况看,更可以看出它不是“官准立案”的。除了古丁等几个青年人天天跑到稻川先生那里,帮助他做些事情之外,主要是稻川先生一人忙于拉稿、写稿、编辑、校正、邮送,编辑部连个像样的屋子都没有,“只是在他的一间小室里”。试想,“官准”的刊物能这样困难吗?这困难没有把稻川先生吓倒,他凭借着韧性终于把《明明》办起来,而且和古丁等人合作得很好。同时,在办刊物的过程中,使他认识了在执教鞭时认识不到的许多事情,知道了“满洲的青年与其要春药,毋宁要强心剂,与其要柳巷探险,毋宁要窝棚写照。”然而,“为了一些不快的事情往他的身上缠绕”,他不得不回国,离却了《明明》。从《明明》刊名的确定,到创刊号目录以及后来所发的作品内容,都可以看出古丁创作思想的倾向。第一,古丁不同意刊物的名字叫《乐土满洲》,为什么呢?不是当局把满洲称为“王道乐土”吗?古丁不同意,岂不有背当局的旨意。这就不难看出,古丁的文学意识中所含有的反满抗日的爱国思想。第二,古丁对稻川先生拿出来的“创刊号目录”,无题也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又是为什么呢?很显然,他是对那目录中的文章不感兴趣,因为这些文章中没有反映出当时的所谓满洲的本质问题。当时的现实生活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东北人民过着亡国奴的生活。亡国之痛,人民之苦,是当时人民所共同关心的大事,哪有闲心谈什么“大臣访问”和“忍受”、“性药”、“探险”等问题呢!第三,从古丁和稻川先生的矛盾与统一中,也可以看出来当时古丁的思想是比较进步的。直到稻川先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站在国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立场上,古丁才与其合作,创刊了《明明》,并为这刊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在《明明》的创刊号上,古丁就写了一篇《闲话文坛》,批评有人提倡的满洲文坛的所谓“独立的色彩”。其实,这种所说的“独立的色彩”,正好迎合了日本侵略者提出的“满洲要独立”的政治主张,也就是要把满洲从中国的领土上分离开来。对于这种主张,古丁是极力地进行反对的,他批判的虽然是形而上的继承和文贼之类,但所赞扬的却是鲁迅等人的反抗精神。
至于谈到“官准”问题,古丁向来是反对的。他在谈到小说、诗歌、戏曲和译文之后说:“理论呢,我不敢梦,因为倘有的话,该是官准的东西,有若无!总之,文人多少要学一些节操,也不妨独自开拓一条各自的文学道。文学终非政治,涂成清一色的企图该会萎缩文坛的。”这就把“官准”的文艺的害处告诉了大家,而“官准”的害处最大的,还在于“下意上达”,“官准的文章里而能有‘下意’是梦想,因为有若无!”这就看出了古丁之所以反对“官准”,主要是从民众着想的。在他看来,文艺如果不能反映人民的生活,那将是莫大的悲哀。在当时,谁能“买几石红粮舍给吃树叶的人类”呢?文士既不是政客,也不是扩音机,而应该是人民的代言人。就古丁的这种文学意识推断,他和稻川先生创办的《明明》,怎么也不该是“官准立案”的吧。
(2)关于“写与印”的问题。
在《明明》创刊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古丁几次谈到“写与印”。他说:“我们很希望着实的作、译,为我们的文坛出品,为我们的文史填写。我们在着实地写与印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未必是所见皆同。”为什么要提出来“写与印”呢?古丁认为:“在人类的工作里,我认为‘快点’倒是第一要件;因为倘能‘快点’,就能‘快点’完成,较之预约而终不履约是强得多了。非特要‘快点’建设,而且要‘快点’破坏;我憎恶‘慢点’建设或‘慢点’破坏的说教者。……总之,快点吧!一个城市不是这样在‘快点’里‘快点’地将要筑成了吗?文坛岂能例外?快点!还是要快点!快点写!快点印!我憎恶一切阻碍快点写快点印的人或非人。”如果说,“写与印”是古丁的一种文学意识和文学主张的话,那么根据当时文艺荒芜的情况,这种意识和主张无疑对文坛是有促进作用的;多写多印,是改变文艺现状的一种有效办法。
对此,在当时有些人认为,古丁只顾多写多印,不注意写什么、印什么和为什么写、为什么印。特别是抓住了古丁的“没有方向的方向”的话,说古丁的“写与印”是不管方向的没有目的的什么都写什么都印。其实,古丁的“没有方向的方向”,实则是有方向的。他说,要“救治不可救治的哑吧和聋子,也不妨朝着不知道方向的方向奔突。”这种“救治哑吧和聋子”,难道还不是一种方向吗?况且也还说,“在这‘没有方向的方向’里寻出来方向”来,“这方向必须是韧性所指示出来的,而非蛮性所莽撞出来的;更须分清风车与巨人,但也不必过虑皮破血出,倘真有方向的话。”这就可以看出,古丁的“写与印”还是遵循着一定的方向的,只不过他是要寻找到合适那时气候的一种方向,并不是盲目地“写与印”。特别是在山丁提出来“乡土文艺”的主张以后,古丁对“写与印”的主张谈的就更加明显了。他说:“我还是照例的‘没有方向的方向’,也不相信什么‘主义’和‘色彩’,因为一到批评家的手里就要浑然,甜蜜,甚至于变质、转形。但是,也不无信条:不写让人读了起好感或美感的东西,不写让人读了莫名其妙的东西,不写让人读了乐观的东西。”这里所说的“让人”,显然是指日伪当局或是和其共通一气的人,要么就是那些脱离现实的新八股之类。所以,批评古丁的“写与印”就是迷失了方向,这是很不公正的,因为古丁向来是反对那些“美化人生的艺术家。”
在《明明》的“城岛文库丛书发刊辞”中,曾提出文艺为“万民之所需”的主张,这自然也代表了古丁的文学意识。应该说,这是古丁“写与印”最明确的目的。但是,有些人还是反对,说这是打着为“万民之所需”的旗号,而实际不是为“万民”,只不过是一个骗人的鬼话。我认为,为“万民之所需”,确实是古丁的一种主张和目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万民”最为需要的,是驱逐日寇,收复被日本侵占的国土,不再过亡国奴的生活,不再受欺压和凌侮。文艺若能起到这种作用,难道不是文艺家们最大的期望吗?所以古丁等人的这一种文艺意识,是适合当时需要的。同时,古丁还说过:“满洲文学,至少满洲人文学,还不具备自己的理论,有的不过是‘写’与‘印’而已,我们名之曰‘写印主义’。至于写什么,怎样写,那都是有了作品以后的事。首先要努力写出作品。总而言之,现在我们还没有作品,所以首先要从无到有。这种心情和设想至少是满洲文学者一致的想法。”(《满洲文学杂记》,载1939年《文艺春秋》)古丁的这番话,也是符合当时文学实际的。在当时的所谓满洲,确实是作品很少的,尤其是1935和1936两年,几乎无人敢进行创作。这种情况下,古丁提出来大胆地进行写与印,也确实是一种勇敢的行为。这种行为,在当时政治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无疑也是对时政的一种背叛。
关于“写与印”的主张,最完整最鲜明的,还是体现在《艺文志·序》中。这个杂志的创刊号序。既然是整个《艺文志》同仁的主张和思想,那么自然也包括古丁在内,况且,当时的一些反对“写与印”的人们,都把“写印主义”作为对古丁一个人的批判。“序”中写道:“艺文为文化的最具体的东西,满洲作为艺文的素材,不失为绝好的宝库,作为艺文家的温床,不失为至上的栋梁。而这些宝库是需要来发掘的,而这些栋梁是需要来架设的。本志……要担负这发掘宝库架设栋梁的重任,都也愿意附骥识者,一年来一步步向前发掘,向上建设的”。“艺文之事,端在写与印,其所写,无嫌天地之广,芝麻之小,倘有真意,自可永传;其所印,无论苍海之巨,粟粒之细,倘存善根,当能久远。”很显然,这是鼓励作家要多写多印。为了不使别人误解且主张明确,古丁特别强调了作家要“有真意”和“存善根”两点。所谓“有真意”,就是作家要发掘真实的题材,写真实的生活,抒发真实的感情,这样,写成的作品才有真实的意义。所谓的“存善根”,则是惩恶扬善之意,这是作家应有的思想,也是创作的终极目的。
检验一种主张是否符合实际,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实践,要看创作,要看写出来的作品是否有推动文学发展和影响当时政治形势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古丁等人一是写出了众多的作品,也出版了不少专集。《奋飞》、《平沙》、《一知半解集》、《浮沉》(古丁)、《蝙蝠》、《无花的蔷薇》(小指),《花月集》(疑迟)等,都相继问世。二是这些作品,不仅揭露了日伪统治者的罪行,鞭挞了侵略,而且也确实丰富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命名文学在几度兴衰中又重振和发展起来。如果把其他派别的文学作品也算在内,那么当时的文坛的活跃和文学作品之多,是空前的。当然,这不能就说完全是古丁等人提出来的“写与印”的功劳,因为这繁荣的局面确实是靠大家的。努力才做到的。“写与印”的主张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文学发展的作用。
(3)关于“独立的色彩”、 “感谢情调”和大东亚人杰传的问题。
自穆儒丐发表了小说《栗子》以后,东北沦陷文坛曾刮起了一股“独立色彩”的歪风。这股风按其鼓吹者之意,自然是强调文学要有地方的色彩,亦即当时的“满洲的文学必须是满洲的”意思,这种强调本身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但遗憾的是,这个主张正与日本要把东北从中国的疆土上割裂开来,变成一个“独立”的所谓的新国家不谋而合了。因此遭到了古丁的反对。他说,要使“满洲”的文学有独立的色彩是可以的,“这个意思,不消说,是颇中肯的。但是,我希望不要由于这语汇生出偏执的见解。”这“偏执”指的就是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就是满洲的独立。因为古丁只相信“地方色彩”,不相信什么“独立的色彩”。他还进一步解释说,“独立的色彩”,“骤然一听,似乎满篇道理,但细加吟味,却又是‘虎老赶’。作者的文笔不同,该叫做‘作风’,再新鲜一点说该叫做‘文脉’。但我们仍称之为‘作风’或‘文脉’,不相信这新语汇。”从以上简短的介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古丁的文学意识是很敏感的,他不但能很快的摄取了文坛上出现的一些现象,而且还能透过这现象看到它的本质,并且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联系起来,找出它的前因后果,论断它的现在与将来。
随着“独立色彩”的出现,“感谢情调”的文章也出现了。感谢什么呢?在当时古丁自然不断说有些人是感谢大日本帝国的恩赐,所以他说:“望文生义,似乎是作者必须在执笔以前,先谢天地,再拜饭碗的。”“但是,读者跟作者一样,有愿读充溢着‘感谢情调’的文章的,也有愿读非‘感谢情调’的文章的。有爱看温室里培养出来的鲜花的,但并非全无偏爱原野里杂生起来的荒草的。”如果把古丁的批评翻译过来,就是他批评那种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文章,并且指出人们是不愿意看那些由日本侵略者培养出来的作家和文章的。他还把这种“感谢情调”的文章比做是“吉利文学”,把创作这样文学的文士(而不是真正的作家)称之为“吉利文贩”。而真正的文学,必须是“有所欲言,才有所写,所谓‘言’并非学鹦鹉;鹦鹉虽言,只是出于口,未尝发自心。因为她的言,句句是主人传授的,其声音虽比主人清脆娇媚,而脖领上都系着一条精致而华美的丝带或银链。因此她的风采和态度也许会漂亮而高傲,但至多不过是早晨‘早安’晚上道‘晚安’,顺应着时辰说几句吉利话而已。”特别是“自从官也招标商也收买的风气起来,这‘吉利话’就跟着洋溢四野,文坛也吉利,天下也吉利,宇宙也吉利”,我们的文学就变成了鹦鹉一样的颂扬和学舌的文学了。所以,“感谢情调”的出现,无疑是破坏了文学的性格,葬送了文坛的生机。这是所有正直的文学家为之担心和反对的,古丁首先站出来对此进行批判,指出这条“暗流”的危害,表明了他文学意识中的进步倾向。
在“独立色彩”和“感谢情调”还没有绝迹的时候,文坛又来个要描写“大东亚人杰传”的主张,这个主张的发起人仍然是穆儒丐。他在《玄奘法师》的结尾,提出来要写《大东亚人杰传》,说这能使“大东亚文学的兴隆”。古丁就此主张,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大东亚人杰传》(《艺文志》一卷第十二期),对穆儒丐进行了批评。古丁说,穆氏的提言写大东亚人杰传,固然使文学“又得了一条新路”,但是,要看写怎样的人杰了。在大东亚,不乏英豪俊杰,“要在作者按其所崇拜,就其所景仰,当然要体嗅相近,方能执笔妥贴”。也就是说,穆儒丐所谓的人杰,当然要写与他“体嗅相近”的,即是《福昭创业记》之类的历史题材的传记体的小说。而这种传记,“写古人如今人,绘昔日如今日,使其精神与近代交感,使其肉体与时势同行,其间,活路作者的性格,发挥笔墨的妙谛,自非易事,所以,也是作家必经之修辞。”因此,古丁认为,文风的振兴,“非仅技巧与方法的问题”,而是精神的把握和灵魂的溶解,这才是大东亚文艺振兴的又一生面。
古丁向来是主张文学要以描写现实为主的,即使是写历史题材的传记,也不能离开现实。尤其是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东北,不描写这样的现实,而主张写历史题材,那不是文学的正途。尽管许多东北作家由于描写现实的黑暗遭到了在东北的日本文人的反对,“指摘我们为什么偏偏刻画暗而不刻画明,为什么偏偏描绘灭而不描绘生”?还说这样是会“给人类以毒害的”。但是古丁却觉得这仍然是文学之道,并且反批评说:他们“忘掉了我们是在暗与灭里求着明与生。……我们只是相信暗的尽头一定是明,灭的终点一定是生。不想自慰,更不想他慰,单单地给文人骚客所描绘的美丽与甜蜜加添一些丑恶与苦涩,甚至于呕吐与唾弃。”“文坛自有文坛的路途,倘有人以文坛为官场为情场的进阶,那只怪他的面孔太热烈,而不是我们的面孔冷酷的了。”由此看,古丁的文学意识是很鲜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