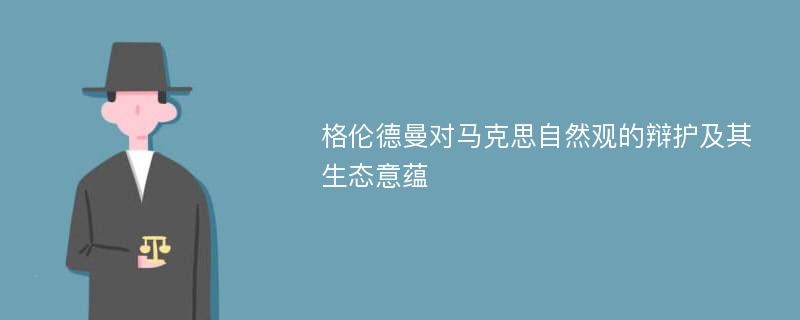
·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摘 要:马克思的自然观秉承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并强调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必须支配自然。西方绿色思潮却将其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并进而指责马克思的自然观存在生态空场。针对这一理论挑战,格伦德曼将马克思的“支配自然”阐释为以理性为主导、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以人类利益为趋向的控制自然,将其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阐释为现代的、扩展的、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从而阐发了其中所蕴含的生态思维,驳斥了西方绿色思潮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诘难,维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生命力。
关键词:支配自然;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理性;历史唯物主义;格伦德曼;马克思
格伦德曼是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西方绿色思潮对马克思自然观的批判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他在将“支配自然”与支配自然的“特定方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区分开来的基础上,将马克思的“支配自然”的观念阐释为以理性为主导、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以人类利益为趋向的控制自然,并将其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阐释为现代的、扩展的、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从而阐发了马克思自然观所蕴含的生态思维,驳斥了西方绿色思潮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诘难,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
一、西方绿色思潮对马克思的“支配自然”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质疑
西方绿色思潮不仅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及其主导下的“支配自然”观念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且还质疑马克思的“支配自然”和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由此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主张对立起来,并进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西方绿色思潮是通过将马克思的“支配自然”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生态危机关联起来的方式对其进行质疑的,他们正是基于此而提出生态危机的解决必须以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摒弃支配自然的态度为前提。他们的质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实际工程中,溶洞的形态千差万别,在进行动力学分析时,不可能将其逐一讨论。本文参考文献[25-27],假定溶洞断面形状为圆形,并将与盾构隧道轴线近似平行的溶洞、隧道和地层简化为平面应变问题来进行分析。详细方案如表4所示。
第一,西方绿色思潮质疑马克思秉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拒斥自然的内在价值,忽视自然的极限,与生态主张相冲突。在他们看来,作为实践哲学家,马克思的所有理论探索都以人为理论参照点,以人的利益和需要为其理论探索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他主要聚焦于变革“剥削人”的社会关系以达到人的自我实现。具体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只具有相对于人的工具性价值,没有独立于人的内在价值。因此,他并不关心人对自然的剥削,而是在强调生产力及技术发展为满足人类更为丰富的需要提供可能性的基础上,片面强调利用技术手段来支配自然以满足人的需要。关于自然的极限,他们认为,马克思对马尔萨斯主义的批判虽然并没有直接否定它的存在,但却将它视为社会历史的产物,并特别强调技术对于推延自然的极限所具有的巨大作用,忽视了人类对于自然的生存依赖以及技术本身的发展将会遭遇的物理极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的极限对他而言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他们由此提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对于技术的盲目乐观态度,必然导致他片面强调自然对于人类的工具性价值,而忽视自然的极限,最终造成不可避免的生态危机。
原来如此……袁安的母亲在妓院里听到的,李离的父亲由酒席上听到的,那些不可思议的故事,那些流光溢彩的传奇,都来自一个在深山里信口开河的老瞎子,就像柳毅遇到洞庭龙王,魏征砍掉泾河龙王的脑袋,这样半真半假的传奇,茶余饭后是很好的消遣,可是你选择了相信它,并因此跋山涉水梦寐求之……袁安抬头盯着李离看,李离将手捂在双眼上,四个少年,一时间觉得之前吞到胃里的黄粱酒,比黄连胆汁来得都要苦。
科学的规划只有真正得到落实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于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来说也是如此。公共图书馆要发展除了政府的科学规划外,还离不开对规划的落实保障,否则再好的规划也仅仅是一纸空文,展现不出其效用[7]。近年来,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这些法律的出台对于促进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保障作用,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是我国第一部图书馆专门法,也是国家对于公共图书馆事业重视的表现。西安市也可出台一些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来规范和保障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并认真落实这些法规中的要求,真正使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落到实处。
第三,西方绿色思潮指认马克思是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的追随者,没有看到人类与自然是休戚相关的有机统一体,存在着“生态空场”。在西方绿色思潮看来,马克思仍旧遵循主、客二分的理性主义哲学思维逻辑来处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把人看作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把自然视为人类为了自我实现而必须征服的对象和被动客体,这就打破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必然造成对作为人类“生态家园”的自然的掠夺与奴役并引发生态危机。美国生态学家克拉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指出,马克思把自然视为人们用来发展和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的一个“客体”与“他物”,或者一种“食物库”和“劳动资料库”[2]。澳大利亚生态学者罗宾·埃克斯利也强调,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与自然是对立的,自然并不是应当予以尊重的对象,而是一种具有约束性和威胁性的外在力量,人的自我实现就在于通过与自然的斗争而实现对自然的支配。简言之,西方绿色思潮认为,马克思的这种立场无法为分析与解决生态危机提供理论工具,相反,他对待自然的这种态度反而会带来更为严重的生态破坏。
语文教师信息化能力是语文信息化教学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信息化教学能力概念的2002年被祝智庭、胡小勇首次提出[1],十六年后的今天,“互联网+”的概念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数字化校园,信息化教学的概念深入到教学的每一个所在。学生创新精神、时代意识的培养与教师信息化能力水平的高低密不可分。
西方绿色思潮之所以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视为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主要是因为他们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混同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缺陷在于:其一,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剔除了理性本身所固有的关于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将理性视为“短期的经济理性”,只关注自身行为的直接经济后果,专横地将首要利益与直接的经济利益相等同,致力于追求“专横的利益直接性”,而漠视其他利益尤其是生态利益视[3]32。其二,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将价值简化为“经济价值”,执着于对抽象的交换价值的追求,忽略了价值本身所蕴含的科学、审美等维度,没有看到人类所需要的并非是表现为经济价值的抽象劳动的凝结,而是使用价值的丰富性,从而造成人的本质的扭曲。其三,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秉持人类沙文主义立场,将技术的进步等同于社会的进步,并将其与人的自由和幸福直接关联起来,并力图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对自然的征服,以满足人的各种非理性需要,这就导致了对自然的“征服”与“主宰”,生态危机也便成为不可避免之事。格伦德曼由此指出,西方绿色思潮正是基于此而指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因此,生态危机的解决必须以摒弃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代之以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前提。
二、格伦德曼对马克思“支配自然”观念的辩护
格伦德曼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利用技术手段来实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维持人类生存、解决人类既依赖于自然又利用和改造自然这一悖论的全新解决方案。鉴于“每一个技术,甚至是最柔软的技术,都构成了对自然的支配”[3]18,马克思确实秉持“支配自然”的观念。但马克思“支配自然”观念却因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而备受质疑。格伦德曼洞察到“支配自然”观念遭到诘难的根源所在,通过对“支配自然”观念的分析而将支配自然的一般意义与支配自然的“特定方式”区分开来,并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阐释为以理性为指导、以客观规律为准绳、以人的利益为趋向的有意识地控制自然和以消除人的“奴役效应”为目标的控制自然,从而阐发了马克思自然观所蕴含的生态思维,彰显了马克思思想的当代生命力。
第一,格伦德曼分析了马克思“支配自然”观念遭受批判的根源所在。他指出,西方绿色思潮之所以质疑马克思的理论具有生态思维甚至认为其具有反生态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将马克思的“支配自然”的观念混同于支配自然的“特定方式”。格伦德曼认为,支配自然本是理性主导下的人类行为,但近代理性却因其与资本主义深度结合而发生了异化,蜕化为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支配自然”观念正是在这种理性的主导下成为支配自然的“特定方式”,从而导致了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从近代理性蜕化为工具理性而言,近代理性秉持人类与自然机械对立的二元论思维,将人类视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万物的尺度”,把自然当作孤立于作为主体的人类之外的被动客体与对象,把知识还原为技术,试图以技术为手段来征服自然以满足人的需要和欲望,而忽视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从近代理性蜕化为经济理性而言,理性在资本的裹挟下,异化为短期的经济理性,人类在这种理性的主导下,异化为盲目追求“专横的利益直接性”的“理性经济人”,他们把自然作为人类的资源库,只关注其直接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其美学、环境等内在价值,为了追逐利润而对自然进行肆意掠夺,最终酿成了生态领域中“公地悲剧”。简言之,格伦德曼认为,正如威廉·莱斯所指出的,应该遭到批判的并非是“支配自然”观念本身,而是凸显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支配自然的“特定方式”,把握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是为马克思“支配自然”观念进行辩护的理论基础。
第二,格伦德曼将马克思的“支配自然”阐释为有意识地控制自然。所谓“有意识地控制自然”就是人类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对自然进行的理性支配。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具有三层含义:其一,马克思所谓的支配自然是以理性为指导的人类行为。他认为,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受到人文主义的熏陶,且直接来源于培根、笛卡尔等启蒙思想家,这就决定了该观念具有毋庸置疑的理性特质。但他又指出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不以交换价值及人的虚假需要的实现为目标,而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前提与条件,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指归。因此,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理性是蕴含生态理性的真正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体,与近代理性具有本质性的差异。其二,马克思所谓的支配自然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他指出,马克思虽然主张支配自然,却并不认为人类可以肆意支配自然,而是强调人类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因为人类是自然之仆和解释者,只有掌握并科学地运用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才能成功地实现对自然的支配。正如施密特所言,“所有对自然的支配以有关于自然的各种联系和过程的知识为前提”,若漠视客观规律,人类“只能灭亡”[4]。其三,马克思所谓的支配自然以人的利益为趋向。格伦德曼认为,“支配”的概念只有与支配主体的利益与需要相关时才有意义,马克思既主张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支配自然,又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的支配,这显然是以人的利益为参照辩证地看待支配自然。因为他认识到支配的结果必须要符合支配者的利益,而一个没能考虑到支配自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的社会,很难说是成功地支配自然的社会。简言之,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的“支配自然”的概念只能被理解为有意识地控制自然的同义词,它非但不是生态问题的根源,反而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出发点,“当前的生态危机正是由于支配自然的不足所造成的”[3]92。
第三,格伦德曼强调马克思的“支配自然”是以消除人的“奴役效应”为目标的控制自然。格伦德曼通过将支配自然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方式对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进行了有力辩护。他认为,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财富”是人的自我实现,“只有一个能够释放所有人类力量的社会才是真正的‘人类社会’。”[3]234正如共产主义的经典论述所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物质变换。”[5]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共产主义是真正的人类社会。格伦德曼进而指出,支配自然是人类力量完全释放的基础。他认为,在马克思看来,支配自然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之中,既是维持人类生存的根本前提,也是消除自然对人的“奴役效应”的基础。由于共产主义社会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裕为前提,因此,它必须通过支配自然来解决人类的“必然性领域”问题。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正是基于此而把支配自然视为人类力量完全释放的基础。格伦德曼最后强调共产主义意味着人对自然的支配达到顶峰。他认为,由于支配自然是人类摆脱自然对于人的“奴役效应”获得自主性的前提,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人类获得充分的自主性得以自我实现的社会,因此,“共产主义必然是人类对自然的支配不断积累的顶峰”[3]93。此外,他还指出,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由于异化的消除,人类不再局限于对狭隘的交换价值的追求,而是会基于人类的根本利益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因而支配自然不会造成生态危机。
格伦德曼正是在拒斥生态中心主义和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前提下,通过对理性、自然价值、需要等概念的分析以及对人类与自然之间辩证法的科学把握而把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阐释为现代的、扩展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从而实现对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辩护的。格伦德曼对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具体阐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三、格伦德曼对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辩护
第二,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扩展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具有本质差异,不会造成生态危机。所谓扩展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就是以人的需要和利益为唯一的价值尺度,否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在坚持对待自然的工具主义态度的同时,又对“工具性价值”进行拓展,将科学、美学、道德、环境等因素都纳入其中,从而超越了对狭隘的、短期的经济利益的追求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他认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之所以是扩展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就在于:其一,马克思扩展了工具性价值的内涵。格伦德曼指出,马克思虽然秉持工具主义自然观,主张为了人类利益而支配自然,但他又认识到自然不仅仅具有能以经济效率来衡量的经济价值,而且还包含经济标准无法衡量的价值,因此,他将科学、美学、道德、环境等因素都视为自然的工具性价值。其二,马克思承认自然的极限。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虽然反对马尔萨斯主义将人口过剩绝对化,将自然的极限视为一个涉及社会、历史、技术等因素的“复杂多变”的体系,但他并不否认特定历史阶段中的自然的极限的存在,因而强调如果人口增长确实影响到人类的整体繁荣,那么有必要采取相应的人口控制策略。其三,马克思关注未来世代的利益。格伦德曼提出,马克思不仅关心当代人的利益,而且关注未来世代的利益,他认为,作为世界居民,为未来世代留下状态更好的生态环境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马克思正是基于此而把美好社会设想为能够释放人的一切潜力的社会,把共产主义当作解放人的潜力的社会形式。总之,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对自然的工具性价值进行了拓展,考虑到了自然的极限,而且关切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是富含价值和意义的扩展的人类中心主义。
滚筒筛安装在距粉煤皮带落煤点10米左右位置,利用分煤器将粉煤截留进入滚筒筛中,经过筛分粒度大于1cm的部分落入滚筒筛后面,粒度小于1cm的经过滚筒筛底部皮带进入粉煤堆中。采用该种设计方案既能兼顾整体原煤筛分需要,又可以多筛出小颗粒块煤。同时采用这种布置方案,如滚筒筛出现故障时,可以随时停用检修,不会影响整体粉煤筛分。
总之,西方绿色思潮认为,马克思采取主、客二分的理性主义思维逻辑来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拒斥自然的内在价值,无视自然的极限,仅将自然视为相对于人而言具有工具性价值的存在物,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片面强调支配自然的生产力发展,对技术持盲目乐观态度,而忽视高风险技术所具有的酿灾潜势,具有生产力主义与技术决定论的倾向性,与生态危机具有内在关联。因此,他们主张生态危机的解决必须摒弃马克思的“支配自然”和人类中心主义观念。
总之,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超越了“不是人类支配自然,就是自然压制人类”[6]的二元对立立场,它以人类理性需要的满足为基础,以人类力量的完全释放为目标;同时又兼顾到生态环境的容纳力,坚持在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下利用和改造自然,因而是具有当代性的合理思想。
第一,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具有本质差异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生态危机没有必然关联。他认为,马克思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具有三点特征:其一,理性的独特性。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虽然深受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影响,但马克思所说的理性绝不同于凌驾于人类之上并造成人的异化的抽象理性。由于马克思以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为宗旨,因此,其理性是服务于人类目的并凸显人的主体性的真正理性。马克思对于人类整体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注足以表明其理性是复归理性本身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体。其二,自然价值的独特性。他认为,马克思虽然拒斥自然具有目的论结构的观点,否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主张以人的利益为参照点来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但同时又反对因自然没有内在价值而肆意破坏自然,因为正如诺顿所言,“就像我们不需要为了不破坏邻居家的财产而赋予它们内在价值一样,我们也不需要为了不破坏性地利用自然而赋予它内在价值”[3]26。其三,“需要”内涵的独特性。他指出,马克思虽然强调通过支配自然来满足人的需要,但他又意识到人的各种需要都与生态问题密切相关,并且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人的诸多需要之一,因此他并不主张肆意剥削自然以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而是强调有意识地控制自然,从而满足人的理性需要。简言之,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关于理性、自然价值及需要内涵的独特性表明,其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建基于近代主体性哲学基础之上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它超越了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近代机械论世界观,因此是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格伦德曼为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辩护是以其对生态中心主义和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判为基础的。他既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无法为分析和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合理的理论工具,又强调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与当前的生态危机具有内在的联系。他指出,生态中心主义存在致命缺陷,无法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理论指导,重返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前提。他强烈反对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当前盛行的生态中心主义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这是因为:其一,自然无法成为道德判断的参照点。他认为,生态系统的“正常”或“异常”状态都是以人为参照点而进行的道德判断,该判断背后隐藏着人的利益。生态中心主义者只是“假装仅仅从自然的立场出发来界定生态问题”,实际上他们并不能始终坚持该立场,因为任何“以生态为中心的方法”从根本上而言都是前后矛盾的,除非转向神秘主义[3]20。其二,生态中心主义并未超越近代二元对立的机械论世界观。格伦德曼认为,生态中心主义并未超越其所批判的那种将人类与自然机械对立的近代世界观,只不过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将人视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体,而生态中心主义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自然置于道德考虑的中心,本质上而言,两者都是将人类与自然机械对立的二元论的思维范式。其三,生态中心主义理论的抽象性。格伦德曼指出,生态中心主义还面临要么采取捍卫结核、艾滋等生物的生命权的激进立场,要么陷入偏爱高等生物、违反“生物平等主义”的悖论之中,这导致该理论缺乏现实观照力,只能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而存在。格伦德曼由此指出,鉴于生态中心主义所存在的上述理论缺陷,人类必须重返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人为参照点来协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是生态危机得以解决的基本理论前提。同时他又强调,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当前的生态危机虽然存在着联系,但不能像西方绿色思潮那样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第二,西方绿色思潮质疑马克思是生产力主义者和技术决定论者。在西方绿色思潮看来,马克思更为重视支配自然的生产力发展,他虽然也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力对人及自然的奴役效应,谴责其非正义性,但他却将其看作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先决条件,对其持乐观态度。西方绿色思潮正是基于他们所阐发的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及技术的盲目乐观态度以及生态危机与生产力及技术发展的内在关联,而将马克思看作是一个生产力主义者和技术决定论者,并强调马克思对待自然的这种态度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生态破坏。正如英国生态学家凯特·索普所指出的,马克思“将优先性赋予了‘生产力的发展’,以之为社会进步的尺度和目标,并向往一个共产主义的‘丰裕’时代,将重要性贴到发达的技术基础设施上,认为资本主义将会把这种技术基础设施留传给社会主义的后革命的重建力量”[1]78。索普正是基于此而将马克思看作一个信仰生产力和技术发展的“唯生产力论者”和“技术政治论者”,并强调其理论具有反生态性。
第三,格伦德曼强调,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会造成生态破坏。格伦德曼认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特性,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人对自然的生存依赖决定了自然的繁荣是人类繁荣的前提。他指出,在马克思看来,人既作为自然存在物而存在,又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与其他自然因素发生作用,自然属性是人的基本属性。由于人的自然属性要求利用自然所能提供的资源来解决吃、喝、住、穿等基本生存问题,因此,人类对自然具有基本的生存依赖,人类的繁荣必须以自然的繁荣为前提。另一方面,自然是物质财富的源泉,自然的繁荣是人类繁荣的基础。他提出,马克思认为,劳动并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自然与劳动一样也是物质财富的源泉。鉴于物质财富的丰裕是人类繁荣的物质前提,而自然又是物质财富的两大源泉之一,因此,“如果人类想要繁荣,这两个因素都必须繁荣。”[3]63总之,格伦德曼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不仅人类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自然所能提供的资源,而且人类的发展又必须以自然的繁荣为基础。马克思正是基于对人类利益的关注而将生态平衡纳入其理论思考之中,因为人类与自然休戚相关,自然的繁荣是人类繁荣的基础和前提,人类对自然的任何破坏都会危及人类自身的利益。格伦德曼提出,马克思正是基于此而强调以实践为中介的人类与自然的辩证法,反对肆意破坏自然。从这种意义上而言,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显然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四、格伦德曼对马克思自然观辩护的生态意蕴
格伦德曼以支配自然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切入点对马克思自然观的重新阐释,批驳了西方绿色思潮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诘难,阐发了马克思自然观所蕴含的生态思维,具有深远的生态意蕴。这不仅为发展生产力奠定了理论基础,维护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理论合理性,为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可行的理论工具,还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思维之间的有机联系,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生命力。
干线公路快速化改造关键线形设计指标研究……………………………………… 姜舟,丁健华,于斌(12-144)
第一,格伦德曼对马克思“支配自然”观念的辩护,否定了支配自然与生态危机的必然关联,为发展生产力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生态危机全球化发展趋势,西方绿色思潮对人类实践行为进行了反思,他们将人类支配自然的态度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在把生产力看作是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的基础上,将生产力发展与自然的繁荣对立起来,甚至提出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对此,格伦德曼首先从生存论的意义上论证了生产力发展的正当性。他认为,支配自然是解决人类生存的“必然性领域”的基本手段,而“必然性领域”的不可消弭性,决定了人类必须通过支配自然的生产力发展来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他进而提出,生产力发展本身与生态危机没有必然关联。他认为,生产力发展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指人类对自然的支配不断增加,二是指经济层面的生产力增长[3]4。西方绿色思潮之所以拒斥支配自然、反对发展生产力,就在于他们将现代生态危机的爆发归咎于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而忽视了现代生态危机的爆发是由于人类片面追求经济层面的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格伦德曼认为,生产力发展不仅要求经济层面的生产力的增加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而且要求人类不断增加对自然的支配,以确保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快乐来塑造世界。换言之,生产力发展内在地蕴含人类对和谐的生态环境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因此,它与生态危机没有内在关联。最后,格伦德曼还将支配自然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从而赋予了生产力发展以必要性。他指出,支配自然是人类获得自主性的前提,由于共产主义是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因此,共产主义是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达到顶峰的社会。鉴于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支配自然的生产力发展也就获得了必要性。这就有力驳斥了西方绿色思潮对生产力发展的诟病,为当代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格伦德曼对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辩护,维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合理性,为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理论工具。以生态中心论为理论基础的深绿思潮指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及其主导下的支配自然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因此而拒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提倡以生态为中心来处理生态危机。面对深绿思潮的诘难,格伦德曼首先通过指认生态中心主义既缺乏可行的道德参照点,又没有超越主、客二分的近代哲学思维逻辑,还存在无法消弭的内在矛盾,批判它缺乏现实关照力,无法成为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工具,从而为以人类为中心解决生态问题理论奠定理论基础。他又通过批判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对“理性”“价值”的狭隘理解及其人类沙文主义倾向而将其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区别开来,这既解释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因生态危机而倍受诟病的原因,又斩断了生态危机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在关联,从而维护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理论合理性。正是在此基础上,格伦德曼通过对理性、需要、工具性价值等概念的阐释以及对人类与自然之间辩证关系的把握,将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阐释为现代的、扩展的、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虽然仍然以人作为唯一的价值尺度,但由于它超越了近代狭隘的、短视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或者说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对经济利益的盲目追求,将生态效益也纳入到人类需要的范畴之中,因此,它不但不会造成生态破坏,反而是解决生态问题的一个很有前景的出发点,使“以人类为立足点来评估生态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成为可能”[3]5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工具。
第三,格伦德曼通过对马克思“支配自然”和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辩护阐发了马克思思想中所蕴含的生态思维,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西方绿色思潮以马克思秉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主张支配自然为由指责马克思没有生态思维,他们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并基于此而质疑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格伦德曼通过对马克思支配自然与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积极阐释而驳斥了这一谬论。他洞察到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人类在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主导下所采取的支配自然的特定方式,因此,他通过强调支配自然与支配自然的“特定方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本质差异,斩断了马克思的支配自然和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从而维护了人类以自身利益为参照来支配自然的合理性。格伦德曼还指出,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人类与自然休戚相关是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7],因此,其支配自然与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是奠基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辩证法之上的,早已超越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机械立场,扬弃了对自然的征服和奴役意识,蕴含整体主义和有机论的生态思维。由于支配自然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构成要素,生态思维也便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基于此,格伦德曼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虽然秉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强调支配自然,但它绝非像西方绿色思潮所指责的那样存在“生态空场”,而是蕴含丰富的生态思维,具有鲜明的当代性。
参考文献:
[1]特德·本顿:《生态马克思主义》,曹荣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2]克拉克:《马克思关于“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之命题》,《哲学译丛》1998年第4期,第61页。
[3]Reiner Grundmann, Marxism and Ec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1.
[4]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7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页。
[6]TedBenton,“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New Left Review,No.178,1989,p.75.
[7]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
中图分类号:B0
中图分类号: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9)03-000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专项课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阐释与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研究”(18VSJ013);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17AKS017)
作者简介:王雨辰,1967年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崔玉娟,1982年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朱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