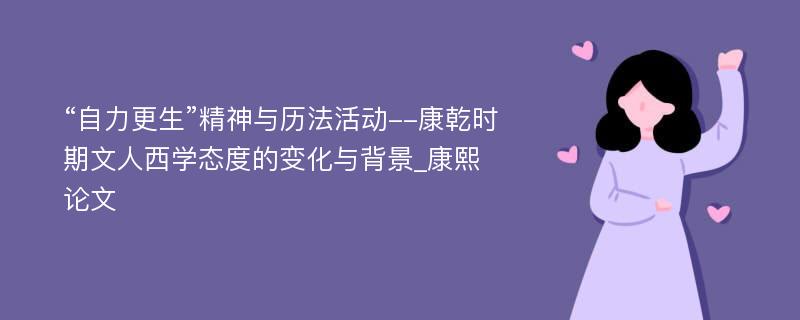
“自立”精神与历算活动——康乾之际文人对西学态度之改变及其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论文,自立论文,文人论文,态度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24(2002)03-0210-12
从明末崇祯改历开始,徐光启等人就借助耶稣会士,大规模翻译欧洲历算著作,试图达到“超胜”之目的;同时耶稣会士为能在宫廷立足,也要借重徐光启等高官的威望和力量,双方在历算方面的合作颇有成效。相比之下,康熙时代的历法改革则复杂得多:当时传教士已经在宫廷站稳了脚跟,并且控制了钦天监,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国籍不同,又牵涉到中国礼仪问题,因此他们之间就有冲突;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既久,信徒众多,耶稣会士、奉教天文学家和文人之间也引发了矛盾;此外,部分传教士为确保他们在科学方面的优势,又采取了留一手的策略。以上众多因素综合的结果促使康熙皇帝下定决心编制新的历法,以达到独立自主,亦即“自立”之目的,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嘉庆朝之后,影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从康熙到乾隆中期,文人对西学的态度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西学中源”说的盛行和对西学的拒斥(注:关于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及其和康熙、耶稣会士的关系,参见[16]、[21]、[22]。),这种转变进而影响了乾隆后期及嘉庆之后对西学的看法。本文试图结合中西文献,通过对当时科学、社会、政治、宗教诸因素的考察,探讨这一转变形成的社会原因,并透过对康熙帝、何国宗(?—1766年)、梅瑴成(1681-1763年)等人物的分析(注:关于梅瑴成对西学的看法,参见[23]、[24]、[18]。),阐述清初科学发展的社会背景,指出历算活动中自上而下的“自立”精神与传教士活动有密切之关联;进而考察康熙至乾隆时代文人对西学态度演变的内在理路,以及对后世产生的深刻影响。
1 康熙对西学态度的转变及其背景
17世纪60年代,杨光先挑起的反教案[1],是清初政治史、文化史、科学史上的重要事件,直接影响了西方宗教和科学在中国传播的进程。这一事件也使康熙幼小的心灵受到震撼,并导致了他日后对西学的浓厚兴趣,他曾回忆道:
“康熙初年,因历法争讼,互为讦告,至于死者,不知其几。康熙七年,闰月颁历之后,钦天监再题,欲加十二月又闰,因而众论纷纷,人心不服,皆谓从古有历以来,未闻一岁中再闰,因而诸王九卿等再三考察,举朝无有知历者,朕目睹其事,心中痛恨,凡万几余暇,即专志于天文历法一十余载,所以略知其大概,不至于混乱也。”[2]
由此可见,康熙开始对天文历法感兴趣,首先是因为“不知历”就无以息讼,这是他学习科学的直接原因。而杨光先和汤若望之间的历法之争,则使康熙认识到西法优于中法,这是他学习西学的重要因素之一。1672年,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开始为康熙讲授西学。1688年后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及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升(Tomé Pereira,1645-1708)相继向康熙传授西方科学知识。
康熙向南怀仁学习时还很年幼,他虽对西学感兴趣,所学却非常有限。法国耶稣会士(“国王数学家”)到达北京之后的一、二年内,天下承平,康熙年富力强,求知欲极其旺盛,频频把传教士请到宫中,传授西方历算和医学知识。此后的近20年间,他一直对西法深信不疑。直至1704年,他还断言“新法推算,必无舛错之理。”[3]在《圣祖实录》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谕钦天监,尔衙门专司天文历法。任是职者,必当习学精熟。向者新法旧法是非争论,今既深知新法为是,尔衙门习学天文历法满洲官员,务令加意精勤。”([3],卷62,804页)
这里明确表示“新法为是”,西法优于中法。故康熙不仅相信西法,爱屋及乌,也重用在宫廷供职的传教士。但值得指出的是,康熙对天主教本身并无多大兴趣。
1705年之后,围绕是否应禁止祭孔、祭祖的“礼仪之争”达到高潮。传教士各派为礼仪的争吵,使康熙对天主教愈发反感,但对西方历算却不改初衷。1706年底,熊赐履和李光地在向康熙皇帝讲完朱子书后:
“上令诸内官俱退,呼余(李光地)和孝感(熊赐履)近前,云:汝等知西洋人渐作怪乎,将孔夫子亦骂了。予所以好待他者,不过是用其技艺耳,历算之学果然好,你们通是读书人,见外面地方官与知道理者,可俱道朕意。”[4]
其时,适奉教皇使节多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出使北京,康熙的这段话是由“礼仪之争”引发的。为解决礼仪问题,康熙数次派遣传教士回罗马与教皇联系。由于使节迟迟没有返回北京,康熙甚为焦急,不时向传教士打听“西洋来的消息”,在奏折中,这样的记载屡见不鲜。由于时空的遥隔,大大阻碍了罗马教廷和康熙的及时沟通,加之使节均未能回来覆命,消息的阻塞使得“礼仪之争”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一些传教士出于传教利益的考虑,想尽量避免触怒康熙,有时封锁消息,隐瞒教皇禁教的旨意和有关信件,久而久之,终于露出马脚。这直接导致康熙对传教士失去信任。至迟在1711年,康熙对传教士的不信任感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称“现在西洋人所言,前后不相符,尔等理当防备。”[5]
同时,康熙也发现当时的西法计算有问题。因清初沿用明末编成的《崇祯历书》(改称《西洋新法历书》)采用的仍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折衷体系。1711年,康熙“发现”钦天监用西法计算夏至时刻有误,与实测夏至日影不符,于是对大臣说:
“天文历法,朕素留心。西洋历,大端不误,但分刻度数之间,久而不能无差。今年夏至,钦天监奏闻午正三刻。朕细测日影,是午初三刻九分,此时稍有舛错,恐数十年后,所差愈多,犹之钱粮,微尘秒忽,虽属无几,而总计之,便积少成多,此事实有证验,非比书生作文,可以虚词塞责也。”([3],卷248,456页)
就此问题,康熙询问了刚到北京不久的耶稣会士杨秉义(F.Thilisch,1670-1715),他用利酌理(G.Riccioli,1598-1671)的表计算,所得结果与钦天监的计算不一致,康熙这才知道西方已有新的天文表,而钦天监未用[6]。此事不仅使他对传教士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加深,而且也动摇了他对西法绝对优势的信心。打破传教士的垄断,让中国人能够独立掌握历算知识,便成为康熙晚年的重要目标。康熙的这种想法,在传教士的信件中便可得到印证。在钦天监任职的耶稣会士徐懋德(André Pereira,1689-1743)的信就很好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信这样写道:
“当今皇上的父亲,我们可以称他为欧洲人之父的康熙皇帝,对于在欧洲人面前无休止地辩论中国的礼仪终感厌倦。他预见到欧洲人不可能长期在他的帝国里呆下去。而且,他甚至可能最后向他们下逐客令。在这之前,他想尽可能地把他们拥有的科学和艺术转为己有,以传给他的臣民。为此目的,每当一位传教士从欧洲抵达北京,只要他在中国人所喜爱的科学或艺术上有所特长,康熙皇帝就马上派子弟随从学习。康熙这一努力终结硕果。中国今天在绝大部分欧洲科学艺术方面已培养出了杰出人才。”[7]
这恰好印证了康熙和李光地、熊赐履说的那段话。康熙晚年一直想让教皇派遣技艺之人到宫廷,这也是实现理想的重要步骤。为实现自己的旨意,他委派皇三子胤祉来组织宫廷的科学活动[8],而据耶稣会士的记载,胤祉在很大程度上是想摆脱传教士的指导,使中国人能独立胜任历算工作:
“多年的经验使皇帝确信,中国人主要或唯一对欧洲人的依赖是,如果没有欧洲人的帮助和指导,他们就无法正确地在天文学方面进行管理及准确无误地预告日蚀和月蚀。皇帝千方百计尽力铲除这一弊端,使中国人能够自立。为达到这一目的,皇帝不惜代价按皇室的排场建立起一所皇家数学院,诏命第三子为院长。此人担任这一职务是受之无愧的。因为他自幼就是我们神父的弟子,学习成绩斐然。皇帝还命其第十二子和十六子作为他的伙伴及继承人。皇帝还从各省召来全部数学家,扩大和加强数学院。这些被选拔的数学精英进行了16年的忘我工作,花费了庞大的开支,提高和发展了天文学,编纂了一本天文学著作。该书1725年以已故康熙皇帝的名义出版。”([7],104页)
“为了掩饰书(指《历象考成》)中的一切都是取材于外国人,著者添加了一些东西,即他们自己的一些观测结果。为此目的,他们的院士们曾奔赴各省作实地观测,这也是他们自惹麻烦的起因。他们期于一逞,信心十足地以自身的观测作为理论的依据和基础。但是,因这一依据和基础缺乏可靠及坚固性,他们建筑的整座科学和艺术大厦是立于流沙之上。
康熙皇帝具有非凡的才能,在数学上受过很高的教育。他非常熟悉我们的天文学和他们的天文学之间存有巨大的分歧。他明智地颁布法令,不准他们的院士发表任何未经欧洲人修改和认可的刊物书籍。倘若康熙皇帝能多活几年,他定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正是这样一本天文著作,令著者的名声随之远扬。不过,该书实际上是由我们的神父所著作并予加工,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供其使用而已。他们企图在数学上摆脱我们。”(注:Catherine Jami据其他史料指出胤祉摆脱传教士的努力,参见[26]。)([7],105页)
这封信提到的内容,是指1713年蒙养斋开馆前后,清廷进行的一系列科学观测活动([6],312-319页),如日月食的观测(以决定经纬度),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大地测量等。
既然已有钦天监这样编纂历法、预测天象的专门机构,为什么康熙要另外成立一个蒙养斋来进行历算编纂活动,而独立于钦天监之外?
看看钦天监的历史,就可以知道,自崇祯时代(1628-1644年)起,在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的支持下,耶稣会士进入钦天监工作,参与了西方天文学、数学著作的翻译,最终完成《崇祯历书》的编纂。但他们来华的使命是传授福音,把天主教义介绍给中国人,传播科学并非他们的本意。因和耶稣会士经常接触,许多在钦天监工作的中国天文学家受感化而皈依上帝。直至1700年前后,钦天监仍有大量奉教天文学家,他们在“礼仪之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7,28]。传教士不仅是他们天文学、数学的老师,更是信仰上的指导者。于是,钦天监不仅作为历算中心,也成为天主教的重镇(注:黄一农对清初钦天监天文学家的争斗进行了研究,见[29]、[30]。)。因此,皇三子胤祉在康熙支持之下,设立独立于钦天监之外的蒙养斋,直接负责历算著作的编纂,其目的正是从各种方面摆脱传教士的指导[9]。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熙对西学从信至疑的转变过程,以及对传教士由“用其技艺”,最后欲摒弃不用而“自立”的变化过程。这种转变的结果有二:一是蒙养斋的建立和一些历算著作的编纂等等“自立”科学活动的开展;二是对天主教进行了日趋严厉的控制。
1723年,雍正登基,他继续严禁天主教,下令驱逐传教士。除在宫廷供职之外,大多数传教士被逐到澳门,不得在内地传教。此外,由于雍正对西学毫无兴趣,故而和康熙时代相比,雍正时代的科学进步很小,显得黯然失色,无可称道,除《历象考成》表和《雍正十排图》的绘制之外,当时编纂的科学著作少得可怜,谈不上进行“自立”的科学活动。乾隆皇帝继位后,兴趣主要转向欧洲艺术,在继续奉行禁教政策之余,仍试图在科学上有所作为,编纂了《历象考成后编》、《仪象考成》,但其规模已不能和康熙时代相提并论。
2 文人对西学态度的演变
我们看到从康熙到乾隆,皇帝对西学的看法有很大的改变,那么一般的文人的看法又是怎样呢?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文人接触西学的氛围已产生了很大变化。杨光先反教案不仅直接造成了李祖白等奉教天文学家被斩的惨案,连时人提起天主教,都谈虎色变,如常熟儒童许嘉禄信教的经历,即为典型的例子,江南文人、教徒何世贞对此作了生动描述,称:
“方今杨光先流言煽祸,秉教诸铎德奉旨居广东,贵同宗之奉教者按察鹤沙公(许缵曾)以建堂被逮,御史青嶼公(许之渐)以作序见黜,汝得无虑于心乎?嘉禄曰:‘志已决,无他虑。’”(注: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藏书号Courant 1022。何世贞是比利时耶稣会士鲁日满的相公,曾著《崇正必辩》(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藏书号Courant 5002)对杨光先提出批评,关于何世贞,参见[31]。)
这段记载至少反映出杨光先教案在时人眼中造成的恐惧与不安。反教案之后,文人心有余悸,存有后怕,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及和传教士的交往,明哲保身成为心照不宣的处世哲学。明末文人和传教士多有唱和,传教士常请文人写序,而杨光先教案之后,特别是教皇特使多罗来华之后,此风几近消失。
实际上,前面所述康熙晚年提出的科学“自立”精神,在文人的著述中则早有反映。被时人誉为“南王北薛”的清初历算大家薛凤祚在《历学会通》序中曾这样写道:“中土文明礼乐之乡,何讵遂逊外洋?然非可强词饰说也。要必先自立于无过地,而后吾道始尊,此会通之不可缓也。”清初学者潘耒也曾表示了类似的看法,因他之劝,张雍敬赴宣城向梅文鼎学习历算,潘耒为此兴奋不已,在给张雍敬《宣城游学记》所写的序中,他这样写道:
“西人历术诚有发中人所未言、补中历所未备者,其制器亦多精巧可观,至于奉耶稣为天主,思以其教易天下,则悖理害义之大者,徒以中国无明历之人,故令得为历官掌历事,而其教遂行于中国,天主之堂无地不有,官司莫能禁。夫天生人材,一国供一国之用,落下闳、何承天、李淳风、一行辈,何代无之?设中国无西人,将遂不治历乎?诚得张君辈数人相与详求熟讲,推明历意,兼用中西之长,而去其短,俾之厘定历法,典司历官,西人可无用也。屏邪教而正官常,岂惟历术之幸哉?序之以为学历者劝。”[10]
潘耒序中称天主教为“邪教”,是当时文人的共同看法,他鼓励别人学习历算,其目的是达到“西人可无用也”,即达到“自立”之目的,和康熙的看法如出一辙。到了乾隆时代,一些文人仍怀有强烈的“自立”精神。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两个重要的人物:何国宗和梅瑴成,他们既是文人,又出自历算世家,参与了许多历算活动,在康乾之间对西学态度的转变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2.1 何国宗:家世、生平及反教背景
何国宗,字翰如,“顺天府大兴县人也(注:实际上,何氏家族原籍杭州,并非大兴县人。关于康熙时代钦天监官员的籍贯,拟另文探讨。)。何氏世业天文,故国宗以算学受知圣祖仁皇帝,钦赐进士,入翰林,官至礼部尚书。”[11]1712年成进士,后改庶吉士,在宫廷学习算法,1713年蒙养斋开馆后,负责《律历渊源》的编纂,与梅瑴成一起充当汇编官。雍正刚一上台就得到重用,担任起居注官,随伺皇帝达四年之久。从钦天监家族的低微出身,跃升到这一显赫的职位,极不寻常。此后,何国宗曾先后任乐部大臣、左副都御史、工部左侍郎、工部右侍郎、左都御史和礼部尚书,负责水利工程及《历象考成后编》、《仪象考成》的编纂,并率领传教士赴伊犁测绘地图[12]。乾隆时,他还负责了天文仪器的制造[13],试图借用徐光启“镕西方之材质,如大统之型模”的看法,来达到复古之目的[14]。至于他的家世,因文献所限,尚难细考。但从现存时宪书看,钦天监官员中有许多何姓,与何国宗多为一家[15]。
有意思的是,西方文献为理解何国宗的家庭背景提供了重要线索。在巴黎国立图书馆西文手稿部,笔者找到安多1688年9月8日在北京写给神父们的信,详细描述了南怀仁去世后钦天监的人事升迁及其矛盾。当时清廷曾派大臣向耶稣会士征询南怀仁的继承人问题,安多等人推荐了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1638-1712,他当时在欧洲),皇帝首肯了这一建议,但钦天监表示了别的意见,上疏推荐了另一位官员做监正,他是杨光先的学生。皇帝留中不发,宣布闵明我为监正,当他不在时,由宫中的两位耶稣会士代替,尽些责任(注:法国国立图书馆西文手稿部7485 n.a.F.)。
杨光先反教案后,钦天监内部权力斗争相当激烈,上面所引安多的信即说明了这一点。此信表明,虽然钦天监参与了监正的推荐工作,但决定大权仍由皇帝一手操纵。特别是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后,康熙对西方科学更为热衷,而且经常参与有关决策,对西方科学的学习和控制成为他政治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16]。有趣的是,中文史料对钦天监的人事变动也有记载,与安多信恰好可以互相印证。据《熙朝定案》记载,南怀仁去世后,监正之位空缺,于是礼部专门讨论了钦天监监正的人员安排,并向康熙作了汇报:
“礼部为请旨事,查得先因钦天监监正员缺,将监副胡振钺拟正,李光显拟陪等因题请。奉旨,历法天文既系南怀仁料理,其钦天监监正员缺,不必补授,钦遵在案。品级考内开钦天监监正员缺,由监副升任,监副员缺,由五官正等官升任等语。今南怀仁病故,补授钦天监监正员缺,或将监副鲍英齐拟正挨俸,将冬官正何君锡拟陪,移送吏部,或将通晓历法之人,令其治理,为此请旨。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题,本日奉旨,闵明我谙练历法,着顶补南怀仁治理历法,闵明我现今执兵部文出差,如有治理应行之事,着问徐日升、安多。”[17]
这里提到的鲍英齐是奉教天文学家,来自安徽休宁,自1664年到1667年担任五官司历,因受杨光先反教案的影响,曾有一段时间没有任职,1678年复出,担任右监副,一直到1686年,1687年起至1707年担任左监副[15],在“礼仪之争”中非常活跃(注:参见[27];拙文[28]对鲍英齐等钦天监奉教天文学家在“礼仪之争”中所起的作用,作了进一步论述。),他是由耶稣会士一手培养起来的,显然不可能是杨光先的学生,安多信中提到的绝不会是他。而礼部奏折指出另一位监正候选人是何君锡,由此可以推断钦天监推荐的正是此人,当无疑问。依据安多的信,又可知何君锡是杨光先的学生,被耶稣会士视为“敌人”。
从清初时宪书看,何君锡从1672年至1710年任钦天监冬官正、1711年至1714年任春官正之职([15],49-52页)。据记载:康熙“五十一年五月,驾幸避暑山庄,徵梅文鼎之孙梅瑴成诣行在。先是命苏州府教授陈厚耀,钦天监五官正何君锡之子何国柱、国宗,官学生明安图,原任钦天监监副成德,皆扈从侍直,上亲临提命,许其问难如师弟子。”([12],1668页)据此可确证何君锡、何国宗的父子关系。透过徐懋德的同一封信,还可看出耶稣会士和中国天文学家的严重冲突,为说明问题起见,现详细摘录如下:
“令我们的神父诧异不已的事还在于:中国人放出风声说,欧洲人将放弃数学这把交椅。如果预言成真,中国人对欧洲数学的依赖将告结束。在这个帝国传教的得以依靠的唯一根基将被拔掉。我们的神父惊慌不安确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一个姓何的贵族,院士,天主教的敌人,汤若望神父时期曾残酷迫害过我们的那个人的后代,他利用这一机会向皇上呈上一份请愿书。在书中他对皇帝说,鉴于中国院士们已完成了天文学的著作,欧洲人主持数学院并指导行星和日月蚀的天文记录似无此必要。该职位贵族院士梅氏即可胜任。他请求皇帝以梅氏取代欧洲人。此外,何还向皇帝说了其他一些事项。皇帝大动肝火,拒绝了何的要求,重申只有欧洲人才懂天文学,只有他们才能对天文学精确计算。”([7],106页)
这封信写于1732年11月20日,就当时参加天文学工作的情况看,这里提到的何姓官员是指何国宗无疑,而姓梅的则是指梅瑴成。徐懋德把何国宗看成是天主教的敌人、“汤若望神父时期曾残酷迫害过我们的那个人的后代”,实际上指出了何君锡在康熙初年的反教案时曾站在杨光先一边,这恰好说明了何国宗和传教士矛盾的根源,和反教的家庭渊源。遗憾的是,中文史料从未直接透露出何国宗对西学的态度,于是西方文献就显得十分重要。由此也可推断梅瑴成为什么对西方传教士非常反感的原因所在了,关于这点,后面将详加论述。
2.2 梅瑴成对西学的态度及其家学渊源
另外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就是梅瑴成,他在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康熙提出的“西学中源”说之所以能够在18世纪中叶之后广为流传,他起到了关键作用[18]。梅瑴成的反教倾向是人所共知的,但其根源可追溯到康熙时代,特别是与他的祖父梅文鼎对西学的态度有关。
梅文鼎作为清初历算大师,耶稣会士是如何看待他的,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笔者在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的信中找到一条有趣的记载,这封信是他在1734年写给法国碑铭和文学院院士弗莱雷(Nicolas Fréret,1688-1749)的,其中写道:
“我发现一本在康熙时AI写作成的书,由一位博士执笔,他是回回的朋友,并且实在是欧洲人的敌人;况且他非常能干;这位博士叫做梅,他对这个难题进行了考证,并且解决了它。”[19]
此信虽然主要讨论历法问题,但明确提到梅文鼎是“回回的朋友”,欧洲人的“敌人”,显然把梅文鼎归入反教派之列。宋君荣来华时,梅文鼎刚刚去世,而梅氏的《兼济堂历算全书》已由魏荔彤刊刻,宋氏对其著作显然是了解的,这一点当无疑问。关于梅文鼎是回回的朋友这种说法,也许来自前辈耶稣会士的看法。这封信不是空穴来风,完全有根有据,于是梅瑴成反教的“家学渊源”昭然若揭。作为梅瑴成的同代人,宋君荣、徐懋德的看法恰可作为佐证,说明梅氏家族反教、反西学的倾向显然是公开的事实。
实际上,梅文鼎对西学大体上采取的是折衷的态度,试图调和中西,缓解矛盾,他的言论,温和而不偏激,但内行人读之,仍可从字里行间体会到其中的反教倾向。并且在他的著作中,对杨光先颇致敬意,尊其为“杨监正”。
不仅仅耶稣会士的信件表明了梅文鼎的反教情结,即使在中文文献中梅文鼎和钦天监天文学家之间的恩怨和矛盾冲突,也可略见端倪。梅文鼎的友人毛际可及朱书,在他们所写的梅氏传记中,即已道破了这一点。毛氏的传记中称:“于是辇下诸公皆欲见先生,或遣子弟从学,而书说亦稍稍流传禁中,台官甚畏忌之,然先生素性恬退,不欲自炫其长以与人竞”(注:1699年,当梅文鼎和毛际可再次在杭州相见时,毛氏为梅文鼎作传,见《勿庵历算书目》附毛际可“梅先生传”(知不足斋丛书本)。)。这里提到的“台官”,即指钦天监官员而言。朱书在谈到梅文鼎时亦称:“辇下巨公人人欲一见勿葊,或遣子弟从游,勿葊书说稍流传禁中,台官甚畏忌之,而勿葊雅不欲以其学与人竞”(注:朱书《朱杜溪先生集》(光绪癸巳重刊本)卷2,21页。他和梅文鼎曾同在福建约一年。)。对这两个传记稍加比较,即可看出其中内容大同小异,由此说明二传均出自梅氏的自述,梅氏显然想把他与钦天监官员的矛盾公诸于世。事实上梅文鼎作为儒者,未必对钦天监的一官半职感兴趣,但是,他的能力毕竟对钦天监构成了威胁。前面已经指出,康熙时代钦天监的官员大都是耶稣会士和教徒,钦天监亦为天主教中心。这是否已向我们揭示钦天监反对梅文鼎的根本原因所在。
和梅文鼎有矛盾的人具体指谁,尚缺乏足够的证据加以说明。但有理由认为,这些人应该是指在钦天监工作的耶稣会士和奉教天文学家。从钦天监人事年表中,可以知道梅文鼎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内(1689-1693年),负责钦天监的是徐日升和安多,任左监副的是鲍英齐,任春官正的是孙有本,均是奉教天文学家,这些人当是毛际可、朱书传中提到的“台官”中的核心人物。
以梅文鼎之孙之故,梅瑴成受到康熙的特别恩赐,被赐与举人,参加殿试。分别在《御纂周易折中》以“翰林院庶吉士”、在《御制性理精义》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担任御前校对;以“翰林院编修”参与《历象考成》,担任“汇编”官。那么梅瑴成本人对西学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首先,他本人与传教士就有矛盾。当时任钦天监任监正的德国耶稣会士纪理安(Kilian Stumpf,1655-1720)在任期间,曾熔化元代的天文仪器,以铸造新的仪器,此事遭到了梅瑴成的强烈反对,在《操缦卮言》中他写道:
“康熙五十四年,西洋人纪理安欲炫其能而灭弃古法,复奏制象限仪,随将台下所遗元明旧器作废铜充用,仅存明仿元制浑仪、简仪、天体三仪而已。”[20]
除梅瑴成自己的记述之外,在清代官修的《大清国史天文志》中,我们也找到类似的记载:
“康熙五十四年,西洋人纪理安欲炫其能而灭弃古法,复奏制象限仪,遂将台下所遗元明旧器,作废铜充用,仅存明仿元制浑仪、简仪、天体三仪而已,所制象限仪成,亦置台上。……又臣梅瑴成于康熙五十二三年间,充蒙养斋汇编官,屡赴观象台测验,见台下所遗旧器甚多,而元制简仪、仰仪诸器,俱有王恂、郭守敬监造姓名,虽不无残缺,然睹其遗制,想见其创造苦心,不觉肃然起敬也。乾隆年间,监臣受西洋人之愚,屡欲检括台下余器,尽作废铜送制造局,廷臣好古者闻而奏请存留,礼部奉敕查检,始知仅存三仪,殆纪理安之烬余也。夫西人欲藉技术以行其教,故将尽灭古法,使后世无所考,彼益得以居奇,其心叵测,乃监臣无识,不思存什一于千百,而反助其为虐,何哉?乾隆九年冬,奉旨移置三仪于紫微殿前,古人法物,庶几可以千古永存矣。”(注:《大清国史天文志》(原抄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时编纂。《畴人传》和此段内容几乎完全相同。)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西洋人的极度不满。这段记载和梅瑴成《操缦卮言》的话如出一辙,很可能出自梅氏手笔。梅瑴成的观点能被采入官史,一方面说明其影响力之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可能直接参与其中有关章节的写作。
梅瑴成不仅继承其祖梅文鼎的反教倾向,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在《梅氏丛书辑要》序,表明了他对西学的看法:
“明季兹学不绝如线,西海之士乘机居奇,藉其技以售其学,学其学者,又从而张之,往往鄙薄古人以矜创获,而一二株守旧闻之士,因其学之异也,并其技而斥之,以戾古而不足用,又安足以服其心,而息其喙哉?夫礼可求野,官可求郯,技取其长,而理唯其是,何中西之足云。”
梅瑴成的目的是“以见西法之不尽戾于古实,足补吾法之不逮”,“将见绝学昌明,西人自无所炫其异”[18]。梅瑴成对耶稣会士“乘机居奇”的做法,有所批评。实际上,在乾隆年间这种做法还有所体现,上述徐懋德的信便是很好的例子。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乾隆年间为文人学者所认同的反教言论,早在康熙时代就已定调,梅瑴成等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影响了乾嘉学者的历算研究。钦天监与蒙养斋算学馆文人学者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梅瑴成等人对传教士的嫉恨,双方若即若离,爱恨交加。耶稣会士的“保留”政策固然不可取,但中国文人的自大情节,似乎也应负起一定责任。
3 结语
从利玛窦开始,耶稣会士就想通过历算来提高他们的荣誉,从而为其传教服务。耶稣会士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则通过寻找借口,减缓编历的进度来达到控制西方历算之目的。但在明末,文人还没能真正认识到传教士的保留态度。到了康熙时代,随着与传教士交往的加深,朝野对传教士的传教目的及对西学的保留态度才有真正了解,康熙从深信不疑到通过努力摆脱传教士对历算编制的控制,梅瑴成则公然指出西人不过“欲藉技术以行其教”,自炫其长,这种态度成为康熙时代西学传播的主线。
权力争夺构成了科学社会史的重要方面,透过中西方文献的对证,使这一观点得到了更好的诠释。从文中分析可看出,对西学的看法不仅涉及到科学本身的问题,而且涉及到钦天监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之间的明争暗斗。这不仅是科学的问题,也与宗教问题密切相关。雍正乾隆年间,由于《历象考成》在预测日月食方面不能达到预期目的,不得不再次依赖耶稣会士进行历法改革,编纂《历象考成后编》。自康熙皇帝开始倡导的“自立”精神,并没有取得胜利,历算“自立”运动也以失败而告终。
对乾隆时期文人的言行作一考察,就会发现对西学的看法,通过康熙皇帝影响到了像何国宗、梅瑴成这样的宫廷文人,继而通过他们影响了钱大昕等人。钱大昕作为乾嘉学派的领袖,深受梅氏祖孙著作的影响,同时在北京期间他又与何国宗有密切的交往,何国宗、梅瑴成等人对西学的看法无疑会对钱大昕产生深远影响。由于钱大昕后来从北京回到江南,于是对西学的看法完成了从朝廷向江南的转变,从而奠定了乾嘉时期对西学态度的基调,导致了乾嘉之后“西学中源”说之盛行,影响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阮元无疑受钱大昕影响最深,他从内心深处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大清亿万年颁朔之法必当问之于欧罗巴乎?此必不然也,精算之士当知所自立矣。”([11],卷45)这种看法代表了乾嘉时期文人的共同看法,是康熙时代“自立”精神的再现。
收稿日期:2001-12-14;修回日期:2002-04-23
标签:康熙论文; 传教士论文; 钦天监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中国历法论文; 清朝论文; 数学论文; 耶稣会论文; 历象考成论文; 天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