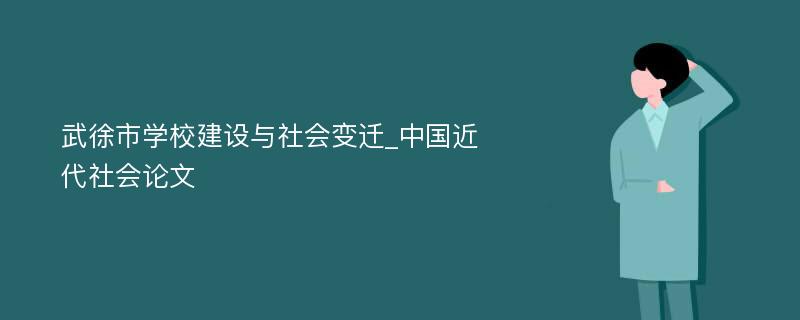
戊戌兴办学堂与社会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堂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主线是社会近代化。它是近代中国社会在与西方的冲突和交往中发生的封建社会日渐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日渐成长的过程,这既包括社会结构诸要素的转型,也包括社会文化和心态结构的变化,两个方面相互促进、相互激发,推动了近代化的发展。甲午战争之后,感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洋务运动的受挫,资产阶级维新派在他们的改革主张中将兴办近代学堂,主动向西方学习和吸收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和思想,改造国民意识作为重要的方面提出来,在实践上创办了一批维新学堂,开始从社会文化和社会心态结构方面推进近代化发展的努力。从理论和实践上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由洋务运动时期注重器物层次的近代化,发展到器物与精神并重,尤其侧重于人的知识文化结构、人的思想意识和人本身的近代化,在中国近代化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戊戌时期兴办学堂的理论和实践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和心态结构变迁的影响。
一
现代发展学证明: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和精神状态。19世纪中叶,中国人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企图靠引进西方近代工业生产技术实现自强和富裕,在不改变封建政治和文化结构的前提下实现近代化。洋务运动中遇到的种种挫折和失败宣告了这种理想的破灭。其后,维新派思想家们逐渐认识到传统的、由科举教育培养和维护的保守的文化心态,以及长期科举教育造成的愚昧陈腐的价值观念,已经成为向西方学习的严重障碍,不扫除弥漫整个社会的愚昧保守心态,就不可能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于是,开通民智、塑造新国民、实现人的近代化的课题,逻辑地上升为戊戌维新各种改革理论不可回避的主题。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发表言论,揭露科举教育的种种弊端,倡言改革教育,兴办学堂以开通民智,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兴办近代化新式学堂的序幕。
在戊戌维新时代,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教育仍然占据着社会文化的中心舞台。科举制度为封建国家培养符合统治者要求的、熟悉儒家经典的科甲人才,选拔封建官僚。这种教育制度使教育的对象局限于少数的地主阶级的后代,受教育面极其狭窄。梁启超曾指出:“夫近代官人,皆由科举,公卿百执,皆由此出……邑聚千数百童生,擢数十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为翰林……是使数百万之秀民皆为弃才也。”(注:梁启超等:《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页。)近代道咸两朝40年间共开会试20科,取进士4813名,平均每科240.6名, 有学者估计道咸40年间,全国共培养生员以上科甲人才100 多万人(注: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5页。 )。相对于一个4亿多人口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是非常小的。 由于科举制度限制了人口中的受教育人数,严重地制约着社会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给近代化社会变迁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其次,这种教育制度还将受教育者的出路限制在出仕做官的狭窄范围内,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弱,社会化程度非常低下。《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收录道咸朝有功名的谱主110名,其中有78名做到从知县到总督和侍郎的官僚,有26 人讲学,从事学术、文学和行医等职。他们中进士55名,做过督抚、侍郎、御史的31人,任知县、按察使和盐运使的18人,为学官的4人, 不仕讲学者2人;举人26名,做官的16人,从事教育学术的10人;秀才29名,做官的9人,从事教育、学术、文学的15人,不知职业者5人(注: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第385—386页。)。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弱,做官被看成是读书的唯一出路,设若不能做官,则一切都归于空虚和失望。“今人以功名为学问……设命中无功名,则所学者无可以自娱,无可以教子,不能使乡里称善人,士友称博学;当此时而回想数十年之功,何学不就?何德不成?今虽悔恨而无及矣,不已晚乎?”(注:王筠:《教童子法》,《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00页。)
科举的最大弊端在于其内容的陈腐守旧。经义诗赋、做八股文,讲究楷法,将文人士子的全部精力束缚在读经制义和诗赋贴括上。康有为痛诋科举“非三代之书不得读,非诸经之说不得览,于是汉后群书,禁不得用,乃至先秦诸子,戒不得观”。诸生荒弃群经,读书只守兔园坊本之陋说,解义只尊朱子,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但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注:康有为:《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37页。)不仅这样,科举教育灌输给士子的是陈腐的儒家伦常名教信条,其结果是教育的水平愈高,可能会使受教育者愈趋向于传统守旧的一方,而敌视任何近代化的新事物。19世纪60年代御史张盛藻宣称:“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子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何必令其学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注:《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页。)是科举不仅“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且它所塑造的数以万计的科甲人才,除极少数外,都是浸淫于封建伦常名教的守旧官僚,他们是封建保守势力的主力,成为近代化发展的最大障碍。
戊戌时期,维新派力主废科举、兴学堂,其目的首先在于以普遍的国民教育取代科举教育,以近代化的新式教育开通民智。梁启超强调“自强于今日,以开通民智为第一义”。他认为西方近百年强盛之原因在于其国民都有较高的素质。中国“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始”(注:《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41页。)。主张改革科举,兴办学堂,把教育的对象扩大到士农工商兵全体国民,使“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注:梁启超:《学校总论》,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康有为在写给光绪皇帝的《请开学校折》中,特别推崇普鲁士的“国民学”,吁请皇帝“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乞下明诏,遍令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令民七岁以上皆入学,县立中学,省府立专门高等大学,京师设立大学。“小学中学者,教所以为国民,以为己国之用,皆人民之普通学也。高等专门者,教人民之应用,以为执业者也。大学者,尤高等学也,磨之砻之,精之深之,以为长师,为士大夫者也。”(注:康有为:《请开学校折》,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页。)与洋务学堂不同的是,维新派在中国近代史上首先提出了建立普遍的国民教育取代科举教育的主张,广教育以成人才,使“中等学校小学校遍地”,举国男女,无不知书识字,解绘图,通算法,粗谙天文地理之人,“非独其为士者知学也”。他们要求冲破科举教育的狭隘性,使学校教育社会化、普遍化。“欲富强之自立,教学之见效,不当仅及于士,而当下逮于民,不当立于国,而当遍及于乡”,使士农工商兵皆有专门之学(注:康有为:《请开学校折》,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3页。)。
施行普遍的国民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知识水平,这在任何国家的近代化过程中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维新人士在这个问题上的识见既超过了“师夷长技”的思想,也突破了洋务学堂的狭隘和幼稚。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以近代化的教育内容取代陈腐的科举教育,对于推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变迁,实现人的思想意识和知识结构的近代化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其次,以近代化的教育内容取代科举教育,打破科举教育片面培养封建官僚的局限性,广开民智,造就农、工、商、矿、兵各个方面的专门人才。京师大学堂最初的功课设计,除了有经学、理学、诸子学等传统学科外,有逐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和英法俄德日诸国语言等普通课程;又有专门学,其列入专门学的课程有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法律学归此门)、高等地理学(测绘学归此门)、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归此门)等十种专门学。要求学生普通学卒业后,每生各占一门或两门专门之学以造就有用之才(注:《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第128页。)。 这一时期兴办的各个地方学堂也都把教授实用知识作为重点。江南储才学堂计划使学生“分习英、法、德、日四国语言文字,精通仿照汉儒专经,分治律例、赋税、舆图、翻书、种植、水利、畜牧、农器、化学、汽机、矿务、工程、各国商务、中国土货钱币货物诸学。”(注:《江南储才学堂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第204页。)湖南时务学堂功课分为普通和专门两等,其专门学包括公法学(宪法民律刑律之类为内公法,交涉公法约章之类为外公法)、掌故学和格算学(注: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第237页。)。事实上, 在戊戌维新的短暂时间里也不可能为学堂教育设计出一个科学完善的体系。但戊戌时期要求打破科举制度单纯讲求经义诗赋的陈旧格局,创设有利于开通民智发展民生事业的各种实学的理论,为其后壬寅学制的形成奠定了舆论和思想基础。
总之,“开通智慧,振兴实业”(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53页。)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也是戊戌维新时期社会文化近代化的总的方向。维新人士大力倡导兴办学堂,“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也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逸处而兴教于家庭。”(注:《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63页。)从发展学的角度看,普及教育和改革教育内容是一切国家跨越中世纪门槛,走向近代化的必由之路。19世纪中叶以后,科举制度已经不适应近代化发展的需要,并且日益成为近代化发展的严重障碍,以新式学堂取代科举制度,既是中国社会初步近代化的必然要求,又是推进近代化事业不可逾越的关键。维新人士以开通民智、振兴实业为中心,把改革教育内容和普及国民教育结合起来、力图建立一种符合近代化需要的新教育体制,对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变迁具有深远的影响。郭沫若评价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说:中国向日本学习,“既有助于打破中国古代的封建的因袭,同时又有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作用。”(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04页。 )这个评价用来说戊戌维新时期的文化教育改革也是恰当的。
二
受戊戌维新失败后政局变动的牵连,教育改革的实践也被迫中辍,京师大学堂硕果仅存,但也不得不受科举教育所禁锢。“大学生诵八股之声,比舍不绝。癸卯甲辰间,虽学风扬厉,然科举未废,大学生于校舍攻策论习殿白折者,亦所恒有,乡会试期届,校舍辄空其半。”(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959页。)
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1900年和1901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从义和团到八国联军的强烈震荡。1901年1月,在戊戌政变后两年零四个月时, 西太后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开始了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7月,刘坤一、 张之洞联衔发出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他们用几乎与维新派相同的口吻承认:“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以他们的识见,把改革科举、兴办学堂、培育新人作为重中之重提了出来。三疏的第一疏就论育才兴学,改革科举。其主要内容有四:(1)设文武学堂, 州县设小学及高等小学。童子八岁以上入蒙学,十二岁以上入小学,十五岁以上入高等小学。府设中学,年十八岁而于高等小学毕业者始得肄业。三年毕业后,再入省城高等学校,高等学校分7个专门学:经学、史学、 格致学、政治学、兵学、农学、工学、毕业后入京师大学。(2 )酌改文科以变通科举。(3)停罢武科。(4)奖励游学(注:张之洞、刘坤一:《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47—51页。)。现实给人深刻的教训,当年站在维新运动对立面的人也意识到革除科举兴办新学校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事关国家命运。 1903年,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废除科举,指出:“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不能进行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注:张之洞、袁世凯:《奏请递减科举折》,《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105页。 )基于这样的认识,20世纪初,全国掀起了一股创办新式学堂的热潮。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到1909年,全国有各级各类学校52939所,学生超过160万人,新式学堂系统开始形成。
“学堂之议,始于戊戌,成于壬寅。”中国近代化的学堂教育开始于戊戌维新,京师大学堂之外,维新人士在各地创办了以学会、学社、储才馆等名义出现的教育机构。1898年时全国有维新学堂58所(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0—406页。),到1909年的5万多所的规模,其速度之快世所罕见。
新式学堂的设立,对近代中国人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心态的近代化起到了启蒙和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首先,新学堂在广大民众中普及近代文化知识,促使中国人的文化知识结构趋向于近代化,中国学人的学术重心开始朝着近代化的方向转移。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总结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有以下诸大端: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及谱谍学、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这几乎概括了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基本知识结构和文化活动的主要方面。即使是那些以经世致用自励的学者,他们关注的致用之学也往往是河工、盐法、钱法、乡约、宗法、选举、学校等传统课题,其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从过去的经验中寻找答案。新学堂引进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极大地推进了知识分子文化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的近代化。1898年成立京师大学堂,中学与西学并重。1902年张百熙主持制定了《钦定学堂章程》,将大学堂分为预料、分科和大学院三级,规定分科大学分政法、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7科。 其中格致科下分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六目。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内容“现代科学是占最大成分的”(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960页。)。1902 年创办的山西大学堂分设中西两斋,中斋以文史为中心,西斋以数理化为中心,而中斋主课也为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和有关的其他科学(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1007页。)。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也大量进入学校教育。湖南时务学堂将《日本国志》、《各国交涉公法论》、《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欧洲史略》以及英法日等国律例作为教材和参考书(注: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第239—244页。)。广东时敏学堂中学书籍“但取有关经济者购之”,而西学之书则包括天算、地舆、格致、制造、政书、史志、交涉、公法、农矿工商兵刑诸书,“分类广购,以扩见闻而资讲习”(注:《广州创设时敏学堂公启》,中国近代教育我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第248页。)。学堂成为传播新文化的中心,学堂学生成为新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以全新的精神面貌给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其次,知识结构更新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使人的社会心态由保守趋向于求新,人们乐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思想和新的行为方式,对社会变迁保持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当19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上弥漫着陈腐守旧的心理的时候,人们视洋务为异途,学堂招生, 应者寥寥。 1867年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原拟招正途出身的进士举人贡生和五品以下京外各官,然而“浮言四起,正途投考者寥寥”。投考诸入,流品不一,勉强考试取录30人,“其中尚堪造就者不过数人”(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44—46页。)。山西大学堂初成立时,青年士子犹多存观望态度,不肯投入,尤其不肯入西斋,讥其数典忘祖(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1007页。)。河南、甘肃等省高等学堂不得不“强迫拨送新生,另给津贴以招徕学生”(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668页。)。 相对于受新知识和新思想感染较多的人群,社会心态形成强烈对比。1902年冬,京师大学堂开校招考新生,“各省材俊,一时并集。新奇环伟之风气,诡异之服饰,潮涌于京师,且集于马神庙一隅。”(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957页。)接受了新知识的学生, 精神面貌一扫守旧因循的故态。“后生初学,大率皆喜新厌故,相习成风,骎骎乎有荒经蔑古之患,若明习科学,而又研究经学者,甚难其选。”(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855页。)张百熙、荣庆、 张之洞在《学务纲要》中指责,“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舍熟求生不胜枚举。”(注:《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205 —208页。)学生成为社会上新风尚的首倡者。1912年8月20日《时报》载《苏州之士煞》一文,描绘学生的时尚装束:“绸伞高擎足踏革履之女界学生华丽煞,草帽高戴口衔雪茄之少年学生时髦煞”。
行为是思想的反映,新行为、新时尚是新的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新知识还是青年学生分析和改造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触媒。从康梁的改良主张到革命党人排满革命的思潮,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到西方新式戏剧,都经过学生向社会广泛传播。刚刚接受自由民权思想的学生,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改革现实社会的洪流,显示了巨大的力量。20世纪初年,各地掀起的“学界风潮”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1903年,《苏报》特辟“学界风潮”专栏予以报道,“稍有热诚者,咸引领张目而望之。”(注:《倡学生军说》,《苏报》1903年6月24日。 )人们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刚刚诞生不久的“学生社会”身上;中国社会“殆已有多数之绝望,乃于各种绝望之中而单有一种焉,浮影于热心家之脑中,而产生出一线希冀者,此何物也?吾必曰:学生社会!学生社会!”“盖学生者实能于各种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翕受新思想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社会主义方倒欧风倾亚雨而来,旁皇无所著,而直接承受之力,不得不以学生为之媒。”(注:《江南水师学堂之鬼蜮》,《苏报》1903年6月20日。)
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顽固势力“阻挠此举,妄造飞言恐吓,诸士多有震动者。至八日,则街上遍帖飞书,诬攻无所不至,诸孝廉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注: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第67页。)时隔数年,社会心态有如此巨大的转变,不能不说是开通民智的结果。
三
从心态史的角度来研究近代化,主要是把近代化看作是一种心理的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改变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结构或政治制度的转变。当一个社会的教育充斥着传统的道德训条,并且不允许学生有疑问和独立思考的机会,不给学生提供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文化和心态结构必然是保守的。这样的社会、近代化必不能得到顺利发展。因此,改革教育制度,彻底更新教育内容就成为近代化发展的决定性步骤。从这一角度看戊戌维新时期兴办学堂的理论和实践,重要的恐怕不在于他们兴办的学堂有多少,而是他们以“开通民智”为宗旨,革新教育,为中国社会文化的近代化指出了方向,为实现人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标签: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历史论文; 社会变迁论文; 科举制度论文; 中世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