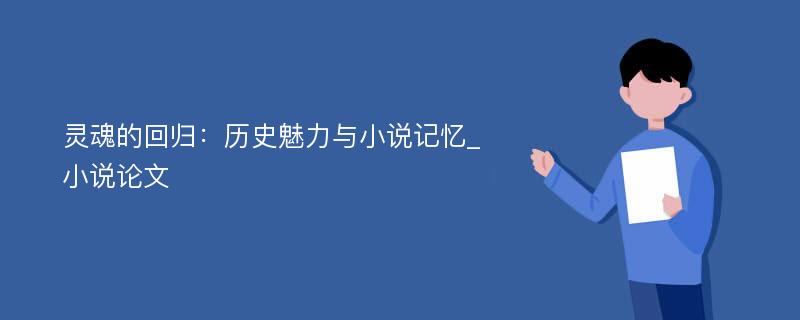
魂兮归来——历史迷魅与小说记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历史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明文人冯梦龙(1574—1646)的话本小说集《喻世明言》里,有一则《杨思温燕山逢 故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北宋亡于金人后的第三年(1129年)。那年的元宵灯节的 晚上,落籍于燕山(即北京)的杨思温偶遇一似曾相识的女子。就像许多宋亡后未能即时 南渡的北人一样,杨思温臣服异族统治,苟且偷生。杨在灯会上所遇的女子竟是他结拜 兄弟韩思寿的妻子郑意娘。从意娘处杨得知她和她的丈夫在东京(汴梁)失陷时被乱军驱 散,而她如今独在燕京韩国夫人府室中权充女婢。恰当其时,已经南迁的韩思寿随南方 朝廷的议和者重回故土。杨思温向兄弟韩思寿提及与意娘相遇,才大吃一惊地发现,意 娘其实早已死了。
故事自此急转直下。原来意娘落入金人之手后即自杀以明志,然而她却不能忘却人世 情缘。意娘与夫韩思寿重逢一景,成为小说的高潮。即使化为冤鬼,意娘也要还魂与夫 一诉前缘。杨思温问起与意娘一起出没的其他丽人,究竟是人是鬼,意娘叹道:
太平之世,人鬼相分;
今日之世,人鬼相杂。①
注释:
①冯梦龙:《喻世明言》,第376页,香港:古典文学出版社,1974年。此一故事出自 洪迈《夷坚志》,《太原意娘》南宋时期已衍变成为流行话本故事《灰骨匣》,元代沈 贺曾有杂剧《郑玉娥燕山逢故人》。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222~223,243~2 44页。台北:丹青出版社,1983年。
郑意娘的故事可视为中国古典鬼魅传奇中的重要母题:生当乱世,社会及天地的秩序 荡然无存,种种逾越情理的力量四下蔓延。死生交错,人鬼同途。《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源出于宋代话本《灰骨匣》,而《灰骨匣》又承自洪迈《夷坚志》①的记载。学者已经指出,这个故事对北宋覆亡后的民间实况,有相当生动的记录②。而通过对当年东京人情景物的追述,小说弥漫着故国不堪回首的悼亡伤逝情怀③。引人深思的是,小说之所以显得如此真实动人,竟是有赖于对鬼魅异端的渲染。所谓真实与幻魅的区分,因此变得问题重重。
意娘的鬼魂回到阳世,反而使仍健在的杨思温与韩思寿猛然惊觉,逝者已矣,生命的 缺憾再难弥补。国破家亡,他们的处境可谓虽生犹死,有如彷徨鬼魅。而他们的追逝悼 亡之举无异是魍魉问影、虚空的虚空。《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故”人因此不妨有一 新解:故人一方面意味故旧,一方面也指的是逝者。
有鉴于意娘对乱世中“人鬼相杂”的说法,我们发现古典中国叙事史中一个相当反讽 的现象。古典说部中充斥着怪力乱神的描写,无时或已。这似乎暗示历史上“太平之世 ,人鬼相分”的时代难得一见,反倒是“人鬼相杂”成为常态。鬼魅流窜于人间,提醒 我们历史的裂变创伤,总是未有尽时。跨越肉身及时空的界限,消逝的记忆及破毁的人 间关系去而复返,正有如鬼魅的幽幽归来。鬼在死与生、真实与虚幻、“不可思议”与 “信而有征”的知识边缘上,留下暖昧痕迹。正因如此,传统的鬼怪故事不仅止于见证 迷信虚构,而更直指古典叙事中写实观念游离流变的特征。
鬼魅叙述早在六朝时代即达到第一次高峰④,以后数百年间屡有创新⑤。迄至明清时 代,市井业者及风雅之人对谈玄道怪有共同的兴趣。文言传统中的“剪灯三话”《剪灯 新话》(1378),《剪灯余话》(1420),《明灯因话》(1592);《聊斋志异》(1679);《 子不语》(1781);《阅微草堂笔记》(1798);及《夜雨秋灯录》(1895),仅是其中荦荦大者。俗文学传统中的例子更为丰富,“三言”及“二拍”还有神魔小说都有佳作。 历来学者注意,尽管这些例子在文类、主题、风格、世界观等方面,彼此极有不同,但 越近现代,鬼魅小说愈显示其探讨人鬼、虚实关系的复杂特色。诚如鲁迅所言,明代神 魔小说流行之际,世情小说——描写现实人生点滴的小说——也大行其道。晚明与清初 的中篇小说颇多以糅合神怪与世俗为能事⑥;鲁迅更认为清代讽刺小说的源头之一,即 在于此⑦。
注释:
①《夷坚志》为《太平广记》后又一叙事说部集成,包括420卷,2700条故事;但现存 200余卷。这些故事为洪迈于1161—1198年所作,有关梦境、世俗及传奇事件,诗词探 源等。见William H.Nienhauser,Jr.,ed.,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 inese Literature,p.457,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6.
②胡士莹:《语本小说概论》,第223页。
③有关北宋南迁士人对故国及故都汴梁风物的追思见Pei-yi Wu,“Memories of K’al -feng,”New Literary History,25,1(1994):40—60.此文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为 例,讨论汴京当年的繁华及衰落及记忆。
④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奇幻的研究,可参见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4、8章,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李建国编:《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台北:文史出版社 ,1987。亦见Karl Kao,Introduction,Classical Tales of the Supernatural and th e Fantastic,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Kenneth De Woskin,“Th e Six Dynasties Chih-Kuai and the Birth of Fiction,”in Andrew Plaks,ed.Chin ese Narrative,p.25-52,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⑤见杨义,4、8、12、20章;陈平原:《中国小说试论》,收于《陈平原小说史论集 》,第1495~1506页,1533~154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程择中:《神 怪情侠的艺术世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30页,香港:青文书屋,1972。
⑦同上。
然而时至现代,此一传统戛然而止。五四运动以科学民主、革命启蒙为号召,文学的 任务首在“反映人生”。放诸文学,此一摩登话语以欧洲19世纪的写实主义为模式,传统的怪力乱神自然难有一席之地③。鬼魅被视为封建迷信,颓废想象,与“现代”的知识论和意识形态捍格不入。当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力陈《无鬼论》④,或当胡适整理国故,自膺为“捉妖打鬼”的健将时,传统的神鬼观自然无所遁形: 我披肝沥胆地奉告人们:只为了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 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客格斯德(Pasteur)发现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相信,虽然 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⑤
现代知识分子及革命者念念以驱鬼为职志,而此一姿态更在左翼政治、文学话语中大 显身手。三十年代曹禺、巴金各在《雷雨》及《家》中控诉传统家庭制度制造无数冤魂 怨鬼。四十年代延安文学有名的《白毛女》号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 人”⑥。五十年代何其芳编写“不怕鬼的故事”,而六十年代初孟超的新编京剧《李慧 娘》见罪当局,罪状正是提倡“有鬼无害论”⑦。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凡是有待 斗争的坏分子俱被冠以“牛鬼蛇神”的称号。
注释:
③事实上十九世纪的欧美现实/写实小说包罗各种题材,及于梦境及超自然现象。作家 凭藉文化、宗教、风俗或意识形态定义的“真实”标准书写这些令人信以为真的事物, 因构成“逼真”(verisimilitude)的准则,像福楼拜(Flaubert)的《圣安东尼的诱惑》 (The Temptation of St.Anthony)即为一例。
④周作人亦称不相信灵魂的存在,见《瓜豆集》第21页(上海,1937)。
⑤胡适:《国故与打鬼》,《胡适文存》3,第160页,台北:远流,1986。五四及五 四后学者文人对鬼魂的态度,见曾羽编:《聊侃鬼与神》,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 96。
⑥贺敬之等所改写《白毛女》的名句;见孟悦的讨论《白毛女演变的启示:论延安文 艺的历史多释性》,唐小兵编:《再解读》,第68~89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 93。
⑦戴家枋:《样板戏的风风雨雨》,第7~8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
这一驱妖赶鬼的语境强调理性及强健的身体/国体的想象,不在话下。然而时至八十年 代,不论雅俗文学及文化,妖魔鬼怪突然卷土重来,而且声势更盛以往,在台湾及香港 ,有关灵异及超自然的题材早已享有广大市场;司马中原或倪匡等作家的声势水涨船高 ①。其他媒体,从电视剧到电影,从广播到报刊,演述阴阳感应、五行八卦、神鬼传奇 无不大受欢迎。更值得注意的是,这股阴风也逐渐吹向大陆,连主流作家也趋之若鹜。 残雪及韩少功早期即擅处理幽深暖昧的人生情境,其他如苏童、莫言、贾平凹、林白、 王安忆及余华,也都曾搬神弄鬼。新中国的土地自诩无神也无鬼,何以魑魅魍魉总是挥 之不去?当代作家热衷写作灵异事件,其实引人深思。<杨思温燕山逢故人>里郑意娘的 话又回到耳边:“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我们还是生在乱世里 么?
识者或谓最近这股鬼魅写作其实受到西方从古堡式恐怖小说(Gothic novel)到魔幻写实主义的影响;更推而广之,后现代风潮对历史及人文的许多看法,也不无推波助澜之功。但我仍要强调,传统中国神魔玄怪的想象已在这个世纪末卷土重来。作家们向“三言”“二拍”、《聊斋志异》藉镜,故事新编,发展谊属自己时代情境的灵异叙述。我尤其关心的是,如果二十世纪文学的大宗是写实主义,晚近的鬼魅故事对我们的“真实”等观念,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如前所述,如果鬼魂多出现于乱世,为何它们在二十世纪前八十年的文学文化实践中,销声匿迹?这八十年可真是充满太多人为及自然的灾难,是不折不扣的乱世,难道中国的土地是如此怨厉暴虐,甚至连神鬼也避而远之?
一
就字源学考证而言,“鬼”在远古与“归”字可以互训,是故《尔雅》有言,“鬼之 为言归也”②。“归”意味“返其家也。”但这“返回”与“家”的意思与一般常人的 想法有所不同。归是离开尘世,归向大化。死亡亦即回到人所来之处。《礼记》:“众 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左传》昭公七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 归也。”③如果归指归去(大化),那么潜藏的另一义应是离开——离开红尘人间。通俗 的诠释则往往颠倒了此一鬼与归的意涵。鬼之所以有如此魅惑力量,因为它代表了我们 对大去与回归间,一股徘徊悬宕的欲念。我以为此中有深义存焉。有生必有死固然是人 世的定律,但好生惧死也是人之常情。鬼魅不断回到(或未曾离开)人间,因为不能忘情人间的喜怒哀乐。鬼的“有无”因此点出了我们生命情境的矛盾;它成为生命中超自然或不自然的一面。惟其如此,鬼魅反而衬托出生命想象更幽缈深邃的层面,仍有待探勘。
注释:
①从通俗文学角度两位作家都有值得注意之处。
②《尔雅·释训》3,第6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
③《左传·昭公七年》,第1291页,台北:展文书局,1963。《礼记·祭义》,第757 页,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
以《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为例,郑意娘回到世间,因为念念不忘夫君韩思寿,以及他 们当年在汴京共享的岁月。但意娘的“回来”却徒然提醒我们阴阳永隔,人鬼殊途。“ 故”人与“故”国再也不能唤回。所谓的夫妻团圆变成一场虚空的招魂仪式,一种迷离 幻境。因此意娘的魂兮归来与其说是欲念或相思的完成,不如说是凸显欲念与相思的缺 憾。生与死被一层神秘的时空缝隙隔开,而在此一缝隙间,不可思议、言传的大裂变— —国破、家亡、夫妻永诀——发生了。此生的纷乱无明与他生的神秘幽远何其不同,而 在两个境界间,但见新魂旧鬼穿梭徘徊,不忍归去,不能归来。
在二十世纪末期,“魂兮归来”的古老主题有了什么新的面貌?以韩少功著名的小说《 归去来》(1983)为例,这篇小说叙述文革期间下乡的知青在文革后重游故地的“神秘” 经验。主人翁来到一个村落,其中一景一物都似乎印证他当年下乡处的所闻所见,更不 提所有似曾相识的村人。但主人翁却无从确认这到底是他阴错阳差的幻觉,还真是他其 来有自的经历——毕竟所有村人都用另外一个人的名字称呼他。小说高潮,主人翁巧遇 据说是他当年“心上人”的妹妹,从而得知他的心上人已死去多时。
《归去来》常被当作伤痕文学或寻根文学来讨论。但此作也大可以放在鬼魅叙事的框 架中观之。《归去来》的题目当然遥指陶渊明(365—427)《归去来兮》的名作。但二十 世纪末中国作者的归家返乡渴望,不以回到故园为高潮;恰相反的,它是一种梦魇式的 漫游,以回到一个既陌生又极熟悉的所在为反高潮。如果运用佛洛依德式说法,我们可 说这一回归引发一种诡秘(uncanay)的症候,“家”及“非家”的感受混淆不清,因此 引起回归者最深层的不安①。韩少功的故事为此类诠释再加一变数。新中国社会的“家 ”曾以集体生活为能事,不只背离佛洛依德式的中产核心家庭观,也与传统中国的家族 结构相去甚远。韩少功的《归去来》到底“归”向何处,语意因此更为含混。
《归去来》并没有正面触及鬼魂人物,但读者不会错过故事中阴惨黯淡的背景。我们 所遭遇的一切都恍若隔世。迷离恍惚中,主人翁陷入对往事的追忆。但见事物影影绰绰 ,阴阳难辨。小说一再强调视线不清所造成的双重或多重视野,这一现象的暖昧感,加 上主人翁无所不在的命名渴望及命名错误,更显示全文再现、指涉(representational) 系统的崩溃。而也就在感官及认知功能的错乱中,幻想与现实交投错综、互为因果—— 造成鬼影幢幢。
注释:
①见如Anthony Vidler,The Architectural Uncanny(Cambridge,Mass:M.I.T.Press, 1992)的讨论。
韩少功以寻根意识见知文坛。《归去来》尽管充满乡愁①,韩少功的归属感却终必化 作幻影。“鬼之为言归也”,作为叙述者,韩少功所散发的鬼气,何曾小于他笔下的人 物?失落在历史与记忆的轨道中,他岂正是无家——那生命意义的源头——可归!
这一难题在知名香港通俗作家李碧华的作品里,有更不同的表现。李的畅销小说中以 《胭脂扣》最能搬演鬼事,而且古意盎然。《胭脂扣》中的女鬼如花曾为三十年代名妓 ,她幽幽回到世纪末的香港找寻当年爱人十二少②。两人曾相约殉情,十二少却死里逃 生。赶在九七大限前,如花还魂了却情债,却终于了解人事早已全非。她的痴情及彷徨 让我们想起了八百年前的郑意娘,她的结局却让人更无言以对。她找到了垂垂老矣的十 二少,即便如是,又能奈何?一切终归徒然。
注释:
①我曾以“想象的乡愁”一词讨论沈从文的小说,见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 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Mao Dun,Lao She,Shen Congwen,Chapter 7,New York :Columbia Univerisity Press,1992.
②对《胭脂扣》的评论,见Ackbar Abbas,Hong Kong: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p.40~47,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Rey C how Ethics after Idealism,P.133~148.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 98;李小良,《稳定与不稳定:李碧华三部小说中的文化认同与性别意识》,《现代中 国之文学讨论》,4(1995),第113~132页;也斯,《香港文化》,第6章,香港:香港 艺术中心,1995。
李碧华对历史记忆的反思亦可见诸像《潘金莲之前世今生》(1989)这样的小说。她改 写《金瓶梅》的高潮情节,想像潘金莲生在二十世纪末的香港,将会有何下场。与其他《金瓶梅》续貂之作不同,李的重心不在潘的生前,而在她的死后。故事开始 ,潘金莲已来到地狱门口,她拒绝喝下可以忘却前生的孟婆汤,一心一意要转世还阳, 重续孽缘——尤其是和武松的一段情。如此,其他人物如张大户、西门庆与武松、武大 ,都陪着她堕入轮回。
在李碧华的版本里,潘金莲名叫单玉莲,文革时曾是芭蕾舞团的尖子演员。她最擅跳 《白毛女》,这正是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好戏。玉莲貌美多才,为舞院张书记所 觊觎。文革之后,她随着一个猥琐商人武汝大来到香港,却与武汝大的弟弟武龙陷入情 网。
香港潘金莲于是旧戏重演,而且用李碧华的话说,把悲剧演成了荒谬的喜剧③。旧社 会纵有千般不是,香港的花花世界一样吃人不吐骨头;情欲的循环机器一旦启动,堕入 其中的男女就身不由己,一再重演自己的角色。也因此,小说并没有真正结局,因为这 些角色注定要在下一世重复彼此的冤孽。前面我讨论韩少功的《归去来》里“似曾相识 ”的(déjà vu)的荒谬感;李碧华的潘金莲另辟蹊径,处理“尚未发生,已成过去”( déjà disparu)的时间鬼魅性。用维理欧(Paul Virilio)的话说:“任何新鲜或特殊 的事物总已在尚未发生之前就已成明日黄花。我们总是面对陈腔滥调。”④潘金莲在故事开始之前就是鬼了,而鬼不再死两次。小说中的风风雨雨因此总已经是原该如此。
注释:
③李碧华,《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第218页,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3。
④引自Abbas,25。
历史的无常流变及鬼影般的记忆也在余华作品中屡见不鲜。我在他处已讨论过余华的 作品特征②,这里仅注重他的《古典爱情》(1988)。这篇小说顾名思义,灵感来自传统 才子佳人的主题,像书生赴京赶考,偶遇绝色佳人,一见钟情,共结鸳誓等。但小说中 段情节急转直下,当书生自京归来、再访佳人时,但见一片荒烟蔓草,佳人已缈。数年 后书生又来,斯地早成鬼域,饥荒蔓延,人人相食。书生最后见到了佳人,竟是在餐厅 的饭桌上——佳人已被卖为“菜人”,成了不折不扣的俎上肉。
余华如此残暴地改写传统,也许意在指出历史的非理性力量,随时蓄势待发,人为的 救赎难以企及。才子最后救了佳人,四肢不全,奄奄一息的佳人只求速死;故事的高潮 是才子杀了佳人。余华自承对巴他以(George Bataille)的《眼之色》(Eros of Eyes,L es Larmes d’Eros)中的色情与暴力观③着迷不已。但他小说中的暴力相衍相生,最终 变成一种定律,反让我们见怪不怪。在《古典爱情》的后半部里,我们看到书生旧情难 忘,在佳人的墓畔筑屋忏情。然后某夜佳人翩然而至,自荐枕席,遂再成好事。书生疑 幻疑真,终于掘墓观察佳人生死下落,但见枯骨生肉,几如生人。然而书生的莽撞,难 使佳人还阳回生的过程克竟全功;一场人鬼恋因此不了了之。
这一结局对熟知传统小说的读者并不陌生。它让我们想到了陶潜《搜神后记》的故事《李仲闻女》④,而《李仲闻女》正是汤显祖《牡丹亭》的源头之一⑤。《牡 丹亭》一向被奉为古典艳情想象的经典,余华的《古典爱情》将这一传统由内翻转颠覆 ,留给当代读者无限喟叹。
诚如杨小滨所言,余华世界中,“所有往事都分崩离析,如废墟、如裂片。时间消逝 ,历史理性退位,每一事件都仅在现时里昙花一现。”⑥余华小说中最令人可怖之处不 是人吃人的兽行,而是不论血泪创痕如何深切,人生的苦难难以引起任何(伦理)反应与 结局。在这一层次上,他比前述韩少功及李碧华都走得更远。
注释:
②王德威:《伤痕即景,暴力奇观》,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序论,第1~23页,台北 :麦田出版公司,1997。
③Xiaobin Yang,The Postmodern/Post-Mao-Dao-Deng History and Rhetoric in Chi nese Avant-garde Fiction,Ph.D.diss.,p.205,New Haven:Yale University,1996.
④陶潜:《李仲闻女》,《搜神后记》,收于李建国,第429页。
⑤汤显祖:《牡丹亭题记》,李建国,第433页。
⑥Yang,p.90.
二
二十世纪末文学里魂兮归来的现象,让我们重思曾凌驾整个世纪文学论述的写实主义 。写实主义曾被奉为唤起国魂,通透人生的法门,也是中国文学晋入“现代”之林的要 素。我在他处已一再说明写实主义的兴盛,不仅代表一种叙述模式典范性的变迁,也更 意味一代学者文人以“文化、思想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的文学例证。这一思维方式名为 革新,但在面对中国现代化千丝万缕的问题时,仍坚持以全盘的文化、思想重整,作为 改革的起步,其内烁一统的逻辑其实去古未远①。准此,不论是修辞上或观念上,写实 主义的出现都被视为反映并改造现实的妙著。用巴特(Roland Barthes)的话说,仿佛有 了写实主义,一种历史的向心力就能经书写而达成②。
写实主义论述的核心之一就是驱妖赶鬼。胡适“捉妖打鬼”的例子,足以代表时代的 症结。但我们如果仔细探究这些妖与鬼究竟何所指,立刻会发现歧义丛生。事实上,为 了维持自己的清明立场,启蒙、革命文人必须要不断指认妖魔鬼怪,并驱之除之;传统 封建制度、俚俗迷信固然首当其冲,敌对意识形态、知识体系、政教机构,甚至异性, 也都可附会为不像人,倒像鬼。鬼的存在很吊诡地成了必要之恶。
这个藉想象鬼域以厘清现实的写实法则,可以上溯至清代或更早。以叙事学而论,晚 明清初一系列的喜剧鬼怪小说,像《平妖传》③、《斩鬼传》(1688)、《平鬼传》(178 5)、及《何典》(1820),都可资参考。这些小说多半篇幅不长,它们延续了晚明神魔小 说的传统,敷衍怪力乱神。但与《西游记》或《封神传》相比,喜剧鬼怪小说无论在人 物、情节或主题上,都显示以往庞大的奇幻想象已经下滑,而沾染了越来越多的人间色彩。取而代之的,是对种种世态人情的尖刻嘲弄,每多黑色幽默④,鲁迅因此将其纳入讽刺小说的项下。
注释:
①Yü-sheng Lin,Crisis in Chinese Consciousness,p.26~33,Madison:Universit 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见我的评论,in Fictional Realism,Chapter 1.
②Roland Barthes,Writing Degress Zero,Trans.Annette Lavers and Coliln Smith .p.14,New York:Hill and Wang,1968.
③见胡万川,《钟馗神话及小说之研究》,第127~155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 0。
④见我的讨论:in Fin-de-siècle Splendor,第191~209页。
喜剧性鬼怪小说浮游神魔与讽刺、虚幻与世情的边际,确是名分飘忽不定的文学。这 类小说视人间如鬼域,嬉笑怒骂的写作形式,对晚清小说的写实观影响深远。我在专书 讨论晚清小说时,曾指出像李伯元(1867—1906)与吴趼人(1866—1910)等作家写尽人间 怪恶丑态,他们的灵感有可能来自早期的喜剧鬼怪小说。尽管作家的着眼点是现实,他们却明白除非诉诸魑魅魍魉的想象,否则不足以表达他们心目中的怪现状于万一。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10)开篇即点明历尽人生妖孽,叙述者只能自诩为“九死一生”①。小说的另一题名,《人间魍魉传》,也就令人会心微笑了。
晚清的谴责小说以夸张扭曲、人鬼不分为能事。作者似乎明白,在一个价值体系—— 不论是本源论、知识论、意识形态、或感官回应——四分五裂的时代,任何写实的努力 终必让人质疑现实的可信性。小说中充斥骗徒郎中、假冒伪善的角色,尔虞我诈,此消 彼长。但无论如何精力无穷,这些人不能算是巴赫汀(Bakhtin)笔下以“身体原则”颠 覆礼教的嘉年华狂欢者②。他们气体虚浮,在魅幻的价值空间游走,似假还真,以假乱 真。他们最多算得上是果戈里(Gogol)“死魂灵”(dead souls)的中国翻版。
五四文人一向贬斥晚清谴责小说作者,谓之言不及义,难以针砭现实病源。事实上, 我以为晚清谴责小说熔神魔、世情、讽刺于一炉,其极端放肆处,为前所仅见。作者所 创造的叙述模式不仅质诘传统小说虚实的分界,也更对行将兴起的五四写实主义,预作 批判。谴责作家惟其没有坚定信念,缺乏道德自持,对社会的罪恶“本质”,人性善恶 分野,就有更模棱两可的看法。他们的写实观中,因此有更邪恶且不可知的黑洞要钻研 ,而他们对正必胜邪的信念,也殊少信心。五四文人对社会堕落的挞伐虽然较晚清前辈 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的极端批评总是坐实了改造国是的信念,以及对掌握“真理” 、“真实”的自得。晚清作家“目睹”“怪现状”之余,终颓然承认在所“见”与所“ 信”之间,总有太多变数。他们的写实观最终指向一种价值的虚无主义;看得到的人间 恶行只是这一虚无的一部分。
五四主流作家以启蒙革命是尚,发之为身体美学,他们强调耳聪目明,以洞悉所有人 间病态。不仅此也,(鲁迅式)“呐喊”与“革命”成为写作必然的立场——仿佛真理的 获得,在此一举。写实主义小说容不下不清不楚的鬼魅。即便是有,也多权充为反面教 材。例如王鲁彦《菊英的出嫁》写冥婚;彭家煌的《活鬼》暴露寡妇偷情的丑闻。同样 吴组缃的《萧竹山房》也写了个寡妇面对性禁忌的荒凉孤寂,而罗淑的《人鬼和他底妻 的故事》明白控诉下层社会生活的苦况,人不如鬼。
正因写实小说以驱鬼为能事,强调光天化日之下没有不能合理化的人生,我们对偶见 的实验性小说,如徐訏的《鬼恋》写一浪漫作家与一装鬼女子的颓废勾搭;沈从文的《山鬼》写湘西迷离凄恻的超自然风习;钱钟书的《灵感》写一二流作家死后被打入地狱的闹剧,就更能引起会心的微笑。尽管成绩有限,这些作家显然不以创造有血有肉的角色为满足,立志要与鬼打交道。
注释:
①见我的讨论:in Fin-de-siècle Splendor,第200页。
②同上,第200~209页。
相形之下,戏剧界也有一二作品可资一提:洪深的《赵阎王》糅合表现主义剧场及传 统鬼戏方式,挖掘人的“黑暗之心”。白薇的《打出幽灵塔》揭露父权垄断的家庭,无 异是鬼气冲天的世界。乱伦、疯狂、死亡充斥其中,主要角色多半不得好死。此剧多不 为人所知,但日后曹禺情节相似的《雷雨》,亦安排了闹鬼的情节(似乎也得自易卜生 《群鬼》的影响),则成了经典名作。
在启蒙的光芒照映下,鬼怪看来无处肆虐。但新文学的背后,似乎仍偶闻鬼声啾啾。 事实上我们注意到一个吊诡:五四文人最迷人之处,是赶鬼之余,却也无时不在招魂。 最可注目的例子是鲁迅(1881—1936),现代文学的号手。评者自夏济安至李欧梵已一再 指出,虽然鲁迅极力抵制传统,他的作品有其“黑暗面”。丧葬坟茔,砍头闹鬼,还有 死亡的蛊惑,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梦魇。鲁迅对那神秘阴森世界的迷恋与戒惧,形成他作 品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自《狂人日记》的吃人盛宴、《白光》中的秘密致命的白光、 《孤独者》死后露齿冷笑的尸体中,可见端倪。“人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鲁迅的祥 林嫂(《祝福》)问着。而鲁迅的魅异想象在散文诗集《野草》达到高峰。
在《坟》的后记里,鲁迅写道:“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阳光一同早逝去 ,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我有时也想就此驱 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①在他清明的政治 、知识宣言之后,鲁迅不能,可能也不愿,摆脱那非理性世界的引诱。他逾越明白浅显 的“现代”化界限,执意回到古老的记忆中,啃啮自身所负载的原罪。他因而充满鬼气 。
夏济安特别提醒我们鲁迅对故乡目莲戏的兴趣。目莲戏的源头可溯至宋代或更早②。 融合了佛家道理及地狱轮回想象,目莲戏有其宗教意义,但表达的方式则熔“恐怖与幽 默”于一炉③。夏注意到尽管目莲戏内容荒诞不经,鲁迅对其抱持相当包容的态度。戏 里的鬼怪神佛就算无中生有,但其所透露的死亡神秘之美及生命的艳异风景,却让鲁迅 难以坐视。在他的笔下那些“千百年来阴魂不散的幽灵,又有了新的生命。”④
注释:
①鲁迅,《坟》后记。
②目莲戏的背景与发展,如见陈芳英,《目莲救母故事之演进及其有关文学之研究》 ,台北:国立台湾大学,1984;亦见湖南省戏剧研究所及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编辑 部编《目莲戏学术座谈会论文集》。湖南:湖南印刷,1985。
③T.A.Hsia,Gate of Darkness,p.160,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 68。
④同上,p.162。
但鲁迅不是新文学里惟一与鬼为邻的作者。站在光谱的另一端是张爱玲,四十年代上 海“颓废风”的代言人。半因家庭背景,半因个人秉性,张在描写死气沉沉的封建世家 ,或虚矫文饰的惨绿男女时,特别得心应手。这些故事虽然架构于写实观点之上,却显 得阴气袭人。张爱玲有言:“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了要证实自己的存在,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①
在张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少女葛薇龙初访她姑母的巨宅,仿佛进 入古代的皇陵②。小说以香港为背景,写葛薇龙的天真与堕落。但已故的唐文标直截了 当地指出,此作根本是篇鬼话,“说一个少女,如何走进‘鬼屋’里,被吸血鬼迷上了 ,作了新鬼。‘鬼’只和‘鬼’交往,因为这世界既丰富又自足的,不能和外界正常人 互通有无的。”③
张爱玲的鬼魅想象更由下列作品发扬光大:《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由怨妇变成如吸血 鬼般的泼妇;《秧歌》中受制于共产党的村民以一场扭秧歌——跳得像活见鬼的秧歌— —作为高潮;而《赤地之恋》更将此一想象发挥到极致,将上海这样的花花世界写成一 个失魂落魄的鬼城④。鲁迅的“鬼话”撇不去感时忧国的焦虑。张爱玲则似安之若素, 夷然预言你我一起向下沉沦的宿命;她成了早熟的末世纪(eschatology)见证。
五十、六十年代,鲁迅式的鬼魅题材人物横被压抑,张爱玲的所思所见却在海外大受 欢迎。我们甚至可以归纳一系列张派的“女”“鬼”作家。我在1988年的专论里,提出 像李昂、施叔青、苏伟贞、李黎、钟晓阳等人的作品都可据此观之。她们的才情感喟惟 有在书写幽灵般的人事,得以凸显。而我也问道:“鬼究竟是什么呢?是被镇压住的回 忆或欲望?是被摒于理性门墙之外的禁忌、疯狂、与黑暗的总称?是男性为中心政教社会 的女性象征?是女作家对一己地位的自嘲?是邪恶与死亡的代表?或正如巴他以所谓‘善 ’‘美’的言谈叙述外的‘恶声’,搔弄、侵扰、逾越了寻常规矩?”⑤九十年代以来 的鬼声方兴未艾,这一列作家尚可加入钟玲(《生死冤家》)、袁琼琼(《恐怖时代》)、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黎紫书(《蛆魇魂》)、黄碧云(《双城月》),以及前所提及 的李碧华⑥。
注释:
①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张爱玲文集》,第19~20页,台北:皇冠 出版社,1992。
②张爱玲:《沈香屑:第一炉香》,《传奇》,《张爱玲文集》,第8页,台北:皇冠 出版社,1992。
③唐文标:《张爱玲研究》,第56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
④见拙作《重读赤地之恋》,收于《如何现代,怎样文学》,第337~362页,台北: 麦田,1998。
⑤见拙作《女作家的现代鬼话》,《众声喧哗》,第227~238页,台北:远流出版公 司,1988。
⑥见《女作家的后现代鬼话》,《联合报》读书人专刊,1998年10月18日。
三
有鉴于写实主义已逐渐丧失其在现代中国文学的主导位置,我们可以探问鬼魅的叙事 法则如何提供一种不同的方式,描摹现实。有关文学写实主义的讨论已经多不胜数①,我所关切的是以往实写主义如何在重塑中国的“身体政治”(body politic)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五四以来的文人以写实为职志,因为他们希求从观察社会百态、搜集感官、知性材料入手,重建“国体”、唤起国魂。历史的实践正在于现实完满的呈现。
随着此一写实信条而起的,是我所谓“体魄的美学”(aesthetics of corporeality) 。坚实强壮的身体是充实国家民族想像的重要依归。尤其在中国的革命论述及实践里, 自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到文革时期的集体劳动改造,我们可以不断看见意识形态的 正确往往需由身体的锻炼来证明。反讽的是,革命论述每每暗自移形换位,将体魄的建 构化为语意的符号的建构:锻炼身体的动机与目标,毕竟是为了精神的重整。所以有了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有名的宣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 ,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 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学。”②
学者王斑描写此一将体魄形上化的冲动,名之为“雄浑”符号(figure of sublime)的 追求。这一雄浑喻意指的是“一套论述过程,一种心理机制,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符号 ,一个‘身体’的堂皇意象,或是一个刺激人心的经验,足以让人脱胎换骨。”经由“ 雄浑”的机制运作,“任何太有人味的关联——食欲、感觉、感性、肉欲、想像、恐惧 、激情、色欲、自我的兴趣等——都被压抑或清除殆尽;所有人性的因素都被以暴力方 式升华成超人,甚至非人的境地。”③
注释:
①关于中国写实主义的研究,见Marston Anderson,The Limits of Reali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Wang,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②鲁迅《呐喊》自序。
③Ban Wang,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 th-Century China Stanford:p.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正是在对应这种雄浑叙事观的前提下,幻魅的写实手法可被视为一种批判,也是一种 谑访。作为文学方法,写实主义不论如何贴近现实,总不能规避虚构、想像之必要。观 诸五四以来的种种写实流派,已可见一斑。二十世纪末的幻魅写实手法则一反前此“文 学反映人生”的模拟信念,重新启动写实主义中的鬼魅。这样的辩论仍嫌太附会形式主 义(formalism)的窠臼。我以为当代华文作家所经营的幻魅观是将写实主义置诸“非实体的物质性中”①,这正是傅柯“鬼影论”(phantom)的看法。对傅柯而言,“鬼影必须被允许在身体边界范畴活动。鬼影反抗身体,因为它附着身体,自其延伸,但也因为鬼影接触身体、割裂它,将其粉碎而予畛域化、将其表面多数化。鬼影同样在身体之外活动,若即若离,产生不同的距离法则。”②
注释:
①Michel Foucault,“Theatrum Philosophicum,”Language,Counter-Memory,Power,Trans.Donad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p.170,Ithaca:Cornell Universit Press,1 981。
②同上,p.169~170。
“雄浑”的传统今非昔比,世纪末华文作家在历史的废墟上漫步。他们“归去来兮”的渴望——回返到已经丧失的革命、真理、真实的源头的渴望——已经堕落为一趟疑幻疑真的幽冥之旅,就像韩少功《归去来》一作所示。这些作家也来到了当年让鲁迅进退维谷的“黑暗的闸门”前,但不像鲁迅,他们执意要开启闸门,走了进去。跨过门槛,他们发现了什么?可能是张爱玲式的“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古老的记忆比未来的瞭望更明晰、亲切。面对那个世界,这些作家更可能为之目眩神迷,而以为自己从来没离开过。以这样的姿态回顾过去,这些作家顾不得“模拟(写真)的律令”(order to mimesis),转而臣服于海市蜃楼(simulacrum)的虚拟诱惑③。
当代作家一方面揭穿写实主义的述作,难免自外于非写实因素的“污染”,他们也同 时思考古典神魔作品中,所隐含的写实因素。我们可以询问,在二十世纪末写作鬼魅, 是否仍可能导生古典说部中的说服力?他们又如何营建一套属于自己历史情境的、能让 人宁可信其有的虚构叙事方法?换句话说,就算作家把古典的怪力乱神搬到现时环境里 ,他们仍必须辨别哪些因素可以让今天的读者“信以为真”,或哪些会被斥为无中生有 。诚如我以“幻魅写实”一辞所示,古典与现代、人间与鬼域、相互交错琢磨,互为幻 影,使写实的工作较以往更具挑战性④
在台湾作家林宜沄的《捉鬼大队》里,一个小城因谣传鬼来了而人心惶惶。目击者是 一个跳脱衣舞的舞娘;某夜中场时分她正在方便,猛地瞧见一张白脸,外加一尺长的舌 头,正在窗上偷窥。这位舞娘吓得跌进粪坑里。她活见鬼的消息立刻传遍全市,警察也 忙着成立了捉鬼大队。民众热心检举他们认为有嫌疑的鬼:精神病患者、“匪谍”、江 湖郎中、弃妇、不良少年、无业游民、甚至梦游症患者都一网打尽。同时社会文化批评 家与群众的捉鬼热相辉映,藉媒体发表专论,大谈鬼之有无。他们的论点自“父系社会 受压迫的女性”到“集体潜意识的投射”,无所不包,好不热闹。
小说至此看得出林意在讽刺社会假“鬼”之名,奉行其图腾与禁忌之实。他也必然预 见(如本文般)连篇谈神道鬼的学术“鬼话”,干脆先发制人,予以解构。而故事进行至 中段更有一逆转:原来“真”的有鬼。“真鬼”来到小城,深对全城热中自行想像的鬼 不以为然;它要一展身手,显显正牌的鬼才。但事与愿违,没人怕它。我们最后看到全 城为捉到鬼而盛大游行。但这鬼其实是装鬼;而且是警察捉鬼大队为了交差而出的鬼点 子。
我们可视林宜沄意在揶揄一个社会自以为是的理性力量。但更有趣的是小说的人物、 布局大有晚明、晚清喜剧鬼魅小说的影子。而林别有用心,他要点出在我们这个诸神退 位的时代,就算没有鬼,也得“装”个鬼。而既然鬼原已是个迷魅,“装”鬼其实是鬼 上加鬼,愈加不可捉摸。但就在这疑神疑鬼的过程中,所谓的社会“真实”的论述得以 向前挺进。
注释:
③我引用Christopher Prendergast’s的立论,见The Order of Mimesis:Balzac,Sta ndhal,Nerval,Flaubert,chapters 1-2,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④这可与德勒兹的观察互相印证;见他论叙事的鬼影Loguique du sens,quoted from J.Hillis Miller,Fiction and Repetition,p.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1982。
类似的辩论可以运用到大陆作者苏童的《仪式上的完成》(1988)上。在这个短篇里,一个民俗学家来到一个小村中,找寻已经失传的赶鬼仪式。这个仪式的高潮里,村民共聚一处抽签选出一个鬼王;选中鬼王的被其他人乱棒打死。民俗学家请求村民为他重演此一仪式,殊不料自己抽中鬼王签。神秘事故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村民假戏真做,几乎要把人类学家打死;后者侥幸逃过乱棒,却在离村的途中被机车撞死。民俗学家的死也许纯属意外,也许是他触动天机,真把一个古老的仪式唤了回来。他的学术追求其实为的是后见之明,而且不无做戏成分,却好似命中注定,在劫难逃。他原本意在重现一个已逝的场景,结果惹鬼上身。他既是死亡仪式的执行者,也是受害人。
这两个故事为我们提供相关的角度,审视幻魅的写实主义如何颠覆以往的写实观。林 宜沄的故事加插了一个奇幻的成分——“真鬼”,却能见怪不怪,把它视为现实里的 当然。我们因此必须再思“现实”的多重可能。另一方面,苏童的小说中的鬼则仅止于 一种迷信或风俗。小说叙述的表面毫无不可知或不可思议的现象或角色,但是每每投射 了现实的对应面,产生鬼影。民俗学家是抱着致知求真的心情审理赶鬼风俗;他是否弄 假成真,引鬼上身始终是个谜团。作为散布鬼话者,苏童总栖居在一个鬼影互为牵引的 迷离世界中。林宜沄及苏童两种看待幻魅现实的角度,都威胁到前述“体魄的美学” ,也再次解构了模拟写实主义念兹在兹的政治动能性。一片恍惚中,写实典范中的两大 知觉反应,说(呐喊)及看(眼见为证),都必然受到冲击①。
在杨炼的《鬼话》(1991)里,一个孤独的声音在一幢空荡荡的屋子里喃喃自语,惟一 的回应是自己的回声。这是谁的声音?杨链曾是八十年代大陆诗界新秀,六四前后远走
他乡。他的故事也许是人在海外,有感而发,但小说没有,也并不需要,明白的历史表 述。生存在后现代(postmodern)的时代里。
朱天心的《古都》(1997)更是变本加厉。九十年代初以来朱即发展出一系列“老灵魂 ”式的角色。老灵魂生年不满半百,却常怀千岁之忧。他们不只感时爱国,更对生命本 然的不确定性,作出形上深思。识者或谓他们杞人忧天,但对朱天心而言,那种世事晦 暗,是非不明的切身之痛,只有自己扪心自知。在这方面,她让我想起了鲁迅《墓碣文 》中自啮自心的腐尸。
注释:
①见如惹内的研究,对惹内而言十九世纪写实主义小说特重声音与视角(观点);Narra tive Discourse,Trans.Jane E.Lewin,p.212-214,Itha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26.
《古都》以一个中年台湾女子赴日重会早年同学未遇开始。提早回到台湾机场,这一 女子将错就错,伪装成日本观光客,拿着导游手册,“观光”她原以为熟得不能再熟的 城市。穿街越巷,这女子不禁油然而生悲戚,台北“古城”哪有什么古迹可资纪念?一 切在不断的毁坏中,从清廷到日本,从日本到中国,从中国到中华民国在台湾,但见历 史的游魂四窜,却再没有安身立命之地。行行复行行,伪观光客来到淡水河边,彷如屈 原(!)行吟江畔。但昔时一缕诗魂而今安在?浊水涛涛,老灵魂不禁掩面痛哭。朱天心的 悲伤及死亡想象不可等闲视之。她让我想起米歇德色妥(Michel de Certeau)所述,在 一个“现代的符号的社会里”,找寻“丧失的幽灵声音”真是难上加难①。朱的故事,或杨炼的故事亦然,企图运用一种幻魅的,旁敲侧击的边缘声音或身影,拼凑现实碎片,清理历史残骸。而此举正印证了中国后现代性的异声、异形本色。
与上述写实主义所强调的声(声音)与色(视象)的写实基础相对抗,我们又在苏童、莫 言等人的作品得见更多的例子。苏童的《菩萨蛮》写一个父亲眼见子女堕落,亟施援手 ,却忘了自己已经死了。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写一个军人的浪漫邂逅,未料对方非 我族类,穷追他至死而后已。两作都可以附会于心理学中,看与被看,幻想与象征,爱 欲与死亡的辩证②。
更进一步,黎紫书、王安忆等作家也有意地把鬼魅与历史——个人的、家族的、国家 的历史——作细腻连锁。马来西亚的黎紫书以《蛆魇》赢得评者注意。故事中的叙述者 娓娓追述家中三代的爱欲纠缠,令人惊心动魄,而叙述者洞悉一切,无所顾忌的灵魂来 自于她的身份——她已是自沉的女鬼。王安忆的《天仙配》以1949年以前,中国一个村 落的冥婚为背景。一次国共血战后,一个共产党的小女兵重伤死在村中。村人不忍见她 成为孤魂野鬼,为她找了个地下冥配。多年后,女兵当年的情人,如今垂老的高干,找 上坟来,要开棺移尸,永远纪念。
注释:
①Michel de 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p.131~132。
②Jacques Lacan,“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Ecritics:A Selection of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两造对小女兵遗骸的争执正触及了两种记忆历史与悼亡方式的冲突。尽管小女兵为“革命”而死,村人却坚持以“封建”方法安顿她,甚至为此又发明一套新神话。小女兵的旧情人却要挪走她的骨骸,由国家来奉祀。毕竟共和国的基础由她这样的先烈以血肉筑成。王安忆描写双方的谈判之余,似乎有意提醒我们,小女兵的冥婚也许是荒唐之举,但把她摆到革命历史殿堂中接受香火,就算合情合理么?在村俚迷信及国家建国神话间,故旧情人及“地下”丈夫间,小“女”兵的骨头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但她的“魂”归何处,岂能如其所愿?王安忆因此不写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式“国族寓言”的发现,而写它的失落。幽灵徘徊在历史断层的积淀间,每一出现就提醒我们历史的不连贯性①。
到了莫言的《战友重逢》,国家与鬼魂的辩证,更充满反讽性。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 述者在返乡过河途中,突遇大水,攀树逃生。在树上他遇到昔时中越战争的同胞,聊起 往事,不胜唏嘘。一个接一个当年战友加入谈话,直到叙述者心里发毛,暗忖莫不是见 到了鬼。但如果别人是鬼,他自己呢?先前他在大水中见到一个军官的浮尸,现在想来 ,原来那个浮尸就是自己!
注释:
①Fredric Jameson,“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 talism,”Social Text,15(1986):p.65-87。对此文的批评,见Aijaz Ahmad,“Jameson ’s Rhetoric of Otherness and the National Allegory,”Social Text,17(1987):3 ~25。
莫言的英雄角色们为国捐躯,正所谓“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但殉国后的日子 阴森惨淡,漫漫无际。还有的战友战争后死于琐碎意外,更为不值。在群鬼的对话中,我们的感慨是深远的。大历史不记载这些鬼声,惟有小说差堪拟之。叙事者自己原是鬼魂,他对同僚的哀悼竟也及于自身,而他因意外而死,死得真是有如鸿毛。小说的写实架构终因此一连串的鬼话嫁接,而显出自身的虚幻。失去的再难企及,语言的拟真及历史“实相”的追记形成一种不断循环的悼亡辩证②。
四
回到首节的引言,“鬼之为言归也”。我提及“鬼”及“归”二字所隐涵的复杂意义 ;“鬼”/“归”是古字源学中的归“去”,也是通俗观念中的归“来”。鬼在中国文 化想像中浮动位置,由此可见。在本节里,我再以数篇当代小说作为例证,说明文学传 统经过一世纪“捉妖打鬼”,启蒙维新的冲击后,如何又悄悄渗入世纪末小说的字里行 间。永恒的忘却以及偶存的记忆间,鬼魅扮演了媒介的角色,提醒我们欲望与记忆若有 似无的牵引。
注释:
②参考Eric Santner,Stranded Objects:Mourning,Memory,and Film in Postwar Ger many,chapter 1,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以台湾作家钟玲的中篇小说《生死冤家》(1991)为例。此作的源头是宋代话本《碾玉观音》①;明代冯梦龙改写的《崔待诏生死冤家》的本子,尤其脍炙人口。原作中玉匠崔宁以手工精巧、擅雕观音见知咸安王,并蒙其赐婢秀秀为妻。某夜王府着火,崔宁为秀秀鼓动逃走。两人于澶州另立门户,但不久即为亲王侍卫所执。崔宁于流放途中与秀秀重逢,日后获释回京重拾旧业。两人又被前此缉捕他们的侍卫撞见,后者大惊,因为秀秀早已在崔宁流放之前被亲王处死。
冯梦龙版的崔宁故事虽忠于宋作,但已将焦点大幅移至市井男女的恩怨动机上。此由 故事题名的改变——从《碾玉观音》到《崔待诏生死冤家》——可以得见。两作中的叙 事者都善于控制情节,创造悬疑。因此,当秀秀是鬼的真相曝光,现实呈现,我们惊觉 生与死、人与鬼间的穿梭来往,是如此在意料之外,又发展的在情理之中。
在钟玲的处理下,传统作为叙事者的说话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秀秀的声音。女性 主义者可以说这一安排凸显了女性——即使作了鬼的女性——强韧的立场②。但另一方 面,秀秀的话毕竟只是“鬼”话,不能当真。但我对钟玲处理爱情与死亡的方式更有兴 趣,而其媒介点正是玉匠崔宁碾玉的工夫。与宋明版本相较,钟玲在描写崔宁与秀秀的 要命关系时,又多了一份情色魅力,而这样激烈的爱情只能以死为高潮。所以在原作中 崔宁被秀秀强索共赴黄泉,钟玲的崔宁则是被秀秀色诱而死,作鬼也风流。秀秀的还魂 了结了一段孽缘。然而钟玲的用心仍不止于此。她尤其强调崔宁与秀秀都是技巧精致的 手艺人。秀秀的刺绣府内知名,她之所以倾慕崔宁,主要因为他的玉雕工夫了得。
注释:
①小说出处与发展,见胡士莹,第200~201页。
②见陈炳良为《生死冤家》写的序,第1~7页,台北:洪范,1991。
钟玲自己是有名的玉石赏玩家。她不会不知道王国维把“玉”与“欲”等量齐观的论 述③;另一方面,玉与死亡及殡葬的关联自古有之。随着故事发展,玉的象征愈益复杂 ,崔宁与秀秀的生死恋成了有关“玉”与“欲”的寓言。如果秀秀爱恋正对照了一个世 代昏昏然似假还真的(鬼魅)风情。
我下一个例子讨论《聊斋志异》对世纪末作家的影响。《聊斋》堪称古典鬼狐说部登 峰造极之作,自十八世纪以来即成为日后作家效法的对象。诚如学者所谓,《聊斋》的 魅力不仅及于描述玄异世界而已,而更能藉谈狐说鬼的异端论述,投射“异”之所以若 是的“常”态规范,人间道理④。蒲松龄自命为异史氏,其实明白他的《聊斋》所从事 的是“另类”的历史(history of alterity)。藉着狐鬼魑魅,蒲松龄记起了一个异样 的过去,因此成就正史之外的异史。
注释:
③我指的当然是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有名的辩论。
④Judith Zeitlin,Historian of the Strange:Pu Songline and the Chinese Class ical Tale,chapter 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世纪末的作家里,莫言的《神聊》(1994)显然是踵事《聊斋》的有心之作。莫言以《 红高粱家族》等作享誉,自承好谈“鬼怪神魔”。这样的风格也许其来有自;莫言的老 家山东高密与蒲松龄故里淄博同属一境之内①,而他对蒲氏影响也一向念兹在兹。当我 们读到像捕鱼人夜晚与女鬼的艳遇(《夜渔》)、专吃铁器的铁孩(《铁孩》)这类故事, 蒲松龄的身影幽然得见。但我以为莫言是类小说也许太有刻意为之的意图,因此成绩不 能超过他前此的作品。
相形之下,马华作者黄锦树的实验就更为可观。《新柳》(1997)中黄锦树讲述了一个 迷离曲折的《聊斋》式故事:书生鞠药如梦中来到一神秘境界,受托于一位瞎眼老者探 究人生命运。鞠惊醒,却发觉自己名叫刘子固,娶妻阿绣;但他也证得在别的前世中他 曾名唤彭玉桂、宫梦弼、陈弼教、韩光禄、马子才等。熟悉《聊斋》的读者当然会体认 出来,这都是蒲松龄笔下的人物②。黄锦树积累这些不同故事中的人物,创造了一个无 限延伸的虚构中的虚构,啼笑恩怨,纠缠不已。小说最后,刘子固又跌入鞠药如的现实 里,而他又遇到一位名叫蒲松龄的老者。
注释:
①莫言:《好谈鬼怪神魔》,杨泽编《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第345页,台北:时 报出版,1994。
②见《聊斋志异》卷十二《鞠药如》;刘子固出现于卷九《阿绣》中。
《新柳》出虚入实,既似向《聊斋》致敬,也似对前人的谐仿。黄锦树安排鞠药如与 蒲松龄相见,也托出自己的创作心事。他的蒲松龄力陈笔下角色虽然玄奇,却也无非是 历史人物的反照,他几乎像是呼应卡尔维诺(Calvino)或博赫斯(Borges)的创作观。真 正令人感动是,(黄的)蒲松龄自述创作动机有如鬼神相寻,不能自已,而且他的创作前 有来者。溯源而上,蒲松龄其实刻画了一个“异史”的谱系学。这一异史谱系与正史相 互对应:“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崔宁的原初动机是爱玉 /爱欲,那么这个故事也基本不只是恋人,也是个恋物故事。什么是恋物?恋物无非是原 欲对象的无限挪移置换,以物件暂代鬼影般不可捉摸的原欲③。此一替换原则正是一种幻魅的机制。当宋代的女鬼进入钟玲的世界,她已沾染了这一个世纪末的颓废风习。
我第二个例子是贾平凹的小说《白夜》(1995)。贾平凹在八十年代崭露头角,以乡土 寻根式作品得到好评。1993年他因《废都》的性描写成了话题人物,而小说记述世情方 面的成绩,反而为读者所忽略。《白夜》延续了贾对俗世庶民风采的好奇,在架构上则 另抒新机。如贾所言,《白夜》的灵感得自1993年他在四川观看目莲戏的经历。他为目 莲戏贯穿死人与活人、历史与真实、演出与观众、舞台与人生的戏剧形式感动不已④, 因有《白夜》一作。
注释:
③Sigmund Freud,“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in Peter Gay,e d.,The Freud Reader,p.249~250,New York:Norton,1989。
④贾平凹,《白夜》,第3页,台北:风云时代,1995。
目莲戏的渊源及丰富面貌,我们当然不能在此尽述①。但不分时代、区域及演出形式 ,此戏以目莲僧下地狱救母为主题,发展出繁复的诠释形式。《白夜》的主人翁夜郎是 个文人兼目莲戏演员。通过他的四处演出,他见识到了社会众生相,无奇不有,同时他 的感情历险也有了出生入死、恍若隔世的颠扑。小说以一神秘的“再生人”出现,自称 为街坊齐奶奶的前世丈夫而起,一股宿命气息即挥之不去。随后重心移向夜郎的演出及 爱情经验,其间贾平凹并加插种种民间艺术。这些艺术体现了日益消失的民间风情,有 如“活化石”②,而目莲戏正是集其大成者。如贾平凹所述,目莲戏之所以可观,不只 因为它的故事穿越阴阳两界,更因它的形式本身已是(死去的艺术)起死回生的见证。它 渗入到中国庶民潜意识的底层,以其“恐怖及幽默”迷倒观众。而夜郎如此入戏,他的 生命与爱情也必成为不断变形转生的目莲戏的一部分。
就此我们不能不记起鲁迅七十年前对目莲鬼戏的执恋。对大师而言,目莲戏阴森幽魅 ,鬼气迷离,但他却难以割舍。九十年代的中国,目莲戏居然卷土重来,以其光怪陆离 、匪夷所思的形式又倾倒一批后摩登的读者。何以故?目莲戏百无禁忌,人鬼不分,岂 不正符合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③小说横跨昼与夜、现在与过去,吟而成癖。自鸣天 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集腋为裘 ,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④小说终了,蒲 松龄递给鞠药如一支笔,嘱他“以独特的笔迹,填满剩下的所有空白。”⑤
注释:
①见陈芳英。
②贾平凹,第3页。
③同上,第7页。
④见Zeitlins的讨论,chapter 2。
⑤黄锦树:《新柳》,《乌暗冥》,第157页,台北:九歌出版,1997。
我们可以看出黄锦树的用心所在。抛开令人目眩的后设小说技巧,他有意重开幻魅历 史的叙事学,作为赓续“异史”的最新传人。而在廿世纪末写异史,他发现真正令人魂牵梦萦的题材不在大陆或台湾,而在他的故乡,东南亚的华人群聚处。这些早期华人移民的子孙注定是正统中土以外的飘流者。尽管他们心向故土,在海外遥拟唐山丰采,竟至今古不分,他们毕竟去国离家日久,渐成化外之人。时空的乖违,使这些华族后裔宛若流荡的孤魂。当他们落籍的新祖国厉行归化认同政策时,他们非彼非此的暖昧身份更二度凸显出来。
因此在他得到大奖的短篇小说《鱼骸》里⑥,黄叙述了一个年轻旅台马华学者寻根的 奇诡故事。这位马华主人翁来到台湾,一心要追求华族文化的源头。然而从马来西亚到台湾,从一个(中华政治地理)的边缘到另一个边缘,他岂能实践他的情怀?这位学者专治上古甲骨文字学,治学之余,他自己居然效法殷商祖先,杀龟食肉取甲,焚炙以窥休咎。他甚至考证出四千年以前,仅出产于马来半岛的一种大龟即已进贡中土。当“深更人定之时,他就可以如嗜毒者那般独自享用私秘的乐趣,食龟,静聆龟语,暗自为熟识者卜,以验证这一门神秘的方术。刻书甲骨文,追上古之体验。”⑦我们还记得,现代中文里的“龟”音同“归”。如果“鬼之为言归也”,那么黄锦树的“归”去之鬼已化成归去唐山的“龟”。如此,主人翁寅夜杀龟卜巫之举在在令人深思。在焚炙龟甲的缕缕青烟中,他重演殷人召唤亡灵的仪式。而他最难忘怀的是他哥哥的鬼魅;多年前在马共暴动中,哥哥为了遥远的唐山“祖国”牺牲一切,最后在围剿中失踪死亡。故事中的主角抚摸鱼骸,也是余骸之际,可曾有如下之欢:世纪末在台湾的马籍华裔可仍在梦想那无从归去的故土?如果如前所述,韩少功等大陆作家写《归去来》,已把寻根归乡化为此路不通的鬼魅之行,像黄锦树这样的海外游子孤魂,又能如之何?黄的主人翁企图重演三千年前的招魂仪式,其时光错乱处,岂正如苏童《仪式的完成》中,那个召请鬼王的民俗学家?但弄假可以成真,请鬼容易送鬼难。黄的主角刻书龟甲,徒然地追求神秘的天启
神喻。而黄自己呢?客居台湾,写作一个回想故土不再,神谕消失的故事,他对自己的离散身份,能不有所感触?这一铭刻龟甲/书写小说的努力,最后会变成一种恋物仪式——就像钟玲《生死冤家》中的两个角色那般;或是一种超越的幻想——就像黄的《新柳》中的蒲松龄一样?中原与海外,文化命脉与历史流变,千百年来的华族精魂何去何从?
回到本文的开始,郑意娘的鬼故事还没说完,她的魂魄依然没有归宿。意娘与丈夫韩 思寿重逢后,韩答应把她的骨灰匣带到南方,朝夕供奉,永不忘怀。韩后来遇到个还俗 的女尼,她的丈夫也在靖康难中被金人所杀。两人一拍即合,旋即成婚。婚后一个月异 象即出现,不断侵扰他们。为了躯鬼,一个道士建议韩思寿把意娘的骨灰从坟中挖出, 倒于扬子江中。韩照办之后,鬼祟乃平。数年后,韩及妻子泛舟扬子江上,突然之间, 两个厉鬼,一男一女,从江心窜起,各捉拿韩氏夫妇,掷入水中溺死。人的记忆有时而 穷,鬼的记忆天长地久。魂兮归来!
收稿日期:2001-10-27
注释:
⑥《鱼骸》为1996年《中国时报》小说奖首奖作品。
⑦《鱼骸》,第267页。
标签:小说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归去来论文; 白毛女论文; 胭脂扣论文; 韩少功论文; 夷坚志论文; 古典爱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