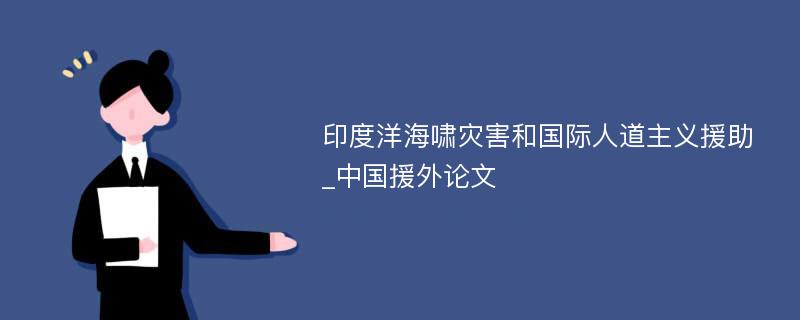
印度洋海啸灾难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道主义论文,灾难论文,印度洋海啸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围绕海啸灾难进行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几个特点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啸发生之后,东南亚与南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七个国家遭受了重大海啸灾难。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乃至个人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截止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围绕此次海啸灾难所进行的赈灾和援助灾后重建行动仍在积极进行。事实上,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评价的那样,国际社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面前,的确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反应”,在过往的世界历史中,似乎还没有哪一次比这一次灾后救援有着参与更为广泛、及时和数量巨大的国际救援。离海啸灾难的发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透过对一系列国际救援事件与现象的解读,可以得出此次国际社会人道主义援助的如下几个特点:
1.作为海啸灾难援助主体之一的西方大国围绕此次海啸救灾展开了权力的博弈,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旌幡下的更高道德原则仍经受着质疑。国际援助是战后国际关系、尤其是南北关系中的一个历久而又常新的重要方面和内容,属于传统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范畴的国际赈灾,其本身就是传统国际援助多种形式之一。(注:对外援助一般包括对外发展援助、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军事援助等不同性质的援助。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曾经将对外援助细化为人道主义援助、生存援助、军事援助、名望援助、贿赂、经济发展援助六种基本的对外援助形式。See Hans Morgenthau,"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56,2.June 1962,p.301.;另一研究对外援助的知名学者澳拉乌·斯多克则专门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依据一种“国家内部因素外化理论”将其界定为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激进主义的三种国际主义。在斯多克那里,人道主义的国际主义从人道关怀出发,感到对于国界以外的人类苦难负有责任,希望福利国家的理想与实践能够跨国界延伸;现实主义的国际主义不主张干预他国内政,主张为了本国的私利而提供发展援助;激进主义的国际主义主张通过外援,积极输出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意识形态,从而保证外援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为扩展国家利益服务。See Olav Stoke(ed.),Western Middle Powers and Global Poverty,The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Uppsala,1989.)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摩根索和沃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各主权国家政策制定者的任务就是使用各种政策工具保护或者促进民族安全与主权、抵御国际环境中的敌对势力、促进和保护国家利益、谋求建立霸权和安全体系,对外援助、即便是看上去非政治性的对外人道主义援助,也只不过是保护与推进国际力量对比和大国进行竞争和获得霸权的政策工具。(注:Hans Morgenthau,"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56,2.June 1962,pp.301-309;Ken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Random House,1979,p.200.)实际上,从研究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功用的角度看,大多数研究集中于研究援助者的动机、国际格局与制定外援政策以及对外援助与国际影响三个方面。从此次海啸灾难救助中关、日等国的行为来看,事实上都验证了前述理论与视角的客观适用性。
就美国而言,布什政府一开始应对灾难并不积极,与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理应承担的人道主义灾难救助责任大不相称,在受到国际社会及联合国人道事务办公室官员、乃至美国国内舆论的批评后,美国才不得不分别在2004年12月29日、30日和2005年初的月份里大幅度增加救援资金来平息国际社会不满;同时,在最后一次呈几何级增加援助数额之际,布什政府着重展现美国的“领袖形象”并试图控制国际救灾的主导权。布什总统本人与白宫其他官员多次对外宣称,美国将在全球动员救灾工作以及随后的重建过程中,担当和扮演一个“领导角色”和“主要贡献力量角色”,国务卿鲍威尔和布什总统的弟弟杰比·布什以及前总统老布什和克林顿也先后前往海啸灾区开展“赈灾外交”;(注:"Bush's Remarks on Tsunami Relief",Los Angeles Times,January 3,2005.)布什政府在采取行动的同时,却绕开和“冷落”联合国,并将中国、欧盟以及东盟各国等排除在外,而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组建了一个所谓赈灾“核心集团”来“协调行动”以应对救援。虽然由于“核心集团”运转的不力、国际社会的疑虑而导致国际社会协调救灾的复杂化,其“主导”赈灾功能在雅加达会议上被终止,但美国仍表示出于担心联合国的“快速行动能力”,美国持有“部分的保留”,并认为在此次国际救助中,联合国的角色将仍“不是惟一的领导角色”。(注:Paul Richter and Don Lee,"U.N.Gets Leading Role in Tsunami Aid Effort",Los Angeles Times,January 7,2005.)无独有偶,在美国大幅追加捐助数额后不久,《洛杉矶时报》2005年1月2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在对布什政府应对因南亚海啸所引发的东南亚、南亚人道主义自然灾难态度及行动上的迟缓提出委婉批评后,不仅建议美国应该对此次海外自然灾难做出“积极大胆的行动与反应”、“重塑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而且敦促布什“尽快提出一个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亚洲战略”。社论声称:美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将提升美国与作为美国“发展民主”对象的印尼、斯里兰卡、泰国、印度四国的“天然盟友”关系,“削弱印尼人对恐怖主义者的同情”,抵制遍布穆斯林世界的反西方鼓惑。并指出,“南亚各受灾国家进行重建所需的资金,只是伊拉克战后重建所需资金近2250亿美元的一小部分。这项投资毫无疑问将是一个明智之举,美国将会在此后的反恐战争中收益良多。”(注:EDITORIAL:"A Marshall Plan for South Asia",Los Angeles Times,January 2,2005.)
就日本而言,其在海啸发生后近两周的时间里保持着世界最大海啸灾难援助数额承诺者的身份;东京在此次海啸救灾中另一项惹人注目的举动,是乘联合国允许各国军队参加海啸灾难救援的机会,派出海陆空自卫队前往苏门答腊岛北部进行救助活动。此次日本派往印度洋海啸灾区的军队不仅规模超过1000人,而且是日本自卫队海陆空三军首次同时开往海外从事紧急救援。分析家们普遍认为,日本于2004年末刚刚出台“新防卫计划大纲”,将自卫队的国际活动定格为“本来任务”,并把其提升到与“国土防卫”的同等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根据其《国际紧急援助队派遣法》,派出如此规模的海、陆、空自卫队,不仅是为了验证与实施“新防卫计划大纲”的所谓“本来任务”、配合美军控制马六甲海峡运输线、测试自卫队危机快速反应与物资投射能力,而且是为了进一步实施与推进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达到其长久追求的政治与军事大国地位身份的战略目标。对美、日围绕此次南亚海啸灾难救助所展开的上述“海啸外交”能否达到其上述外交与战略目标,目前尚难得出全面评估结论,笔者在此也并不想否认此次美、日等大国海啸救灾中所固有的人道主义救助之真义,但在东南亚出现相对权力真空和长期成为大国权力搏弈之场所、美国全球与东南亚“反恐”以及对外援助历来作为美国“战略工具”、东南亚长期作为日本在国际政治角逐中的“基盘”、日本对东南亚关系转型(由冷战时期以经济关系为主转变为冷战后以政治关系为主)和外援政策转变的大背景下,人们也不能否认海啸救援已成为美、日等西方大国获得地区权力与影响力、推进国家安全战略、改善与加强国家形象的工具。事实上,从此次海啸灾难救助中美、日、德、澳大利亚、欧盟捐款数量的“比拼”,到澳大利亚军队所牵动的东南亚受灾国的神经,都反映了此次海啸灾难救助背后不可避免的“援助政治学”,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旌幡下的更高道德原则仍经受着质疑。
2.联合国体系在此次海啸救灾中展现的主导作用、协调功能与公信力具有不可替代性。此次海啸灾难发生以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随即与印度尼西亚等受灾国领导人进行了电话交流,了解受灾各国的援助需求,强调在国家、地区和国际等层次协调救援努力的必要性。其后,他于2004年12月29日中断休假返回纽约联合国总部,以加强对联合国各机构在海啸灾区开展的救援活动的领导和协调。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次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安南呼吁国际社会对亚洲海啸受灾国的救援努力进行协调,以便更好地帮助受灾国应对海啸灾难造成的近期和长期影响,并号召这场“史无前例的全球灾难”需要国际社会做出“史无前例的反应”,强调联合国在协调国际救援方面的主导作用。在具体的协调方面,安南于12月30日上午召集了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署(UNDHA)、联合国儿童基金(UNICEF)、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粮食计划署(WFP)、世界银行等与人道救援有关的联合国机构的负责人举行了会议,并会见了印度等12个受灾国的常驻联合国大使。此外,他还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以及美国倡议成立的“国际(救灾)联盟”“核心集团”其它成员国的代表举行了电视会议,并于当天下午与欧盟国家的代表举行了会谈。随后新加坡呼吁的东盟国家灾区救援紧急会议的倡议以及2005年1月6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召开的国际海啸峰会,乃至后来于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捐助国会议,相当大程度上都应被视为对上述联合国机构敦促与呼吁的回应,而随后1月7日西方七国集团财长于伦敦宣布的“一致同意”冻结遭受地震海啸灾害的国家偿还债务以及各国海陆空三军的紧急海外救灾行动也是对联合国主导下的国际救灾呼吁、协调与具体实施的产物;在建立海啸预警机制与系统方面,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主任萨尔万诺·布里塞尼奥在2004年12月29日就呼吁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应该在一年以内建立海啸预警系统,并敦促该地区建成一个允许各国对地震情况进行交流和快捷地向有关地区发布警告的国际与国内机制,从而达到分享经验、提高该沿海地区对地震海啸认识的能力。联合国负责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扬·埃格兰随后在12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为防止海啸灾难重演,联合国灾害防范部门将帮助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在明年年底之前建立海啸预警体系。在雅加达国际海啸峰会召开的第二天,联合国还表示将在联合国机构中成立一个“国际预警计划署”,并致力于将太平洋海啸预警模式在全球推广。在监督救援捐款的流向方面,据2005年1月11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CNN)报道,联合国表示,它将借助一家会计公司,协助跟踪南亚海啸灾难捐款的运用情况,以确定南亚海啸灾难捐款运用情况细节。在各国政府、救援组织与民间团体保证提供的大约40亿美元捐款中,目前约有27亿美元正由联合国通过其网站跟踪其运用情形。以上事实都说明了,在此次印度洋海啸灾难援助体系中,联合国体系在呼吁、协调、建立相关海啸预警机制以及监督国际救灾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主导性的功能与作用。
3.在此次海啸灾难国际援助中,非政府与非官方国际组织、社会团体与国际社会中个体公民作为援助主体的地位突出,传统的对外援助体制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长期以来,在国际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体系中,主权国家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由于其自有资源与援助体制一直占据着几乎垄断性的地位。在此次海啸灾难中,由于海啸所造成的灾难的巨大危害性和跨国性,全球化时代国际资讯与传播的发达与便捷和全球相互依存观念的加强,加之海啸遇难者身份的多国籍性,可以说,此次海啸灾难在各国民众中所引发的心灵震撼大大超过既往,各国普通民众与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基于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人道援助、人道责任没有国界的时代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涌现出对印度洋沿岸灾区的援助热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认为,在此次灾难援助中,在美国和西方社会因特网甚至成了“最基础和最有效”的捐款手段,并认为美国的捐助文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注:Peter Grier,Faye Bowers,and Amanda Paulson,"Profound Shift in U.S.Culture of Giving",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January 5,2005.)实际上,从巴黎到北京,从纽约到柏林,从香港到伦敦,从设在咖啡屋的捐款箱到因特网电子媒介,再到音乐人的大型赈灾义演,各国与全球的非政府组织、慈善团体、宗教组织、音乐人和广泛意义上的作为个体的世界公民,都积极通过自己的方式,在不同的地点,组织参与赈灾活动,为援助海啸灾区筹集资金,在主权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外起到了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积极补充作用,并使得此次海啸灾难救援中的非国家主体化以及“超越国家中心”的现象十分突出。
从对外援助的现实功用的视角看,对外援助被视为能够以很少政府支出形成较大国际影响的政策领域,而援助资金也总是可以被转化成各种力量的。长期以来,作为受援主体的南方国家和作为援助主体的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由于存在着力量的不对等,掌握了资源的发达国家就获得了一种超越传统主权国家的政治力量筹码,使得其可以对受援国家的政策,甚至政治进行干预,或使用少量的外援资金投入作为杠杆在援助国俱乐部中倡导与推行某种政策目标,并在缺少国际监督的情况下,成为其有力的战略与私利工具。而南方不发达国家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国际援助的客体,出于资金匮乏等各方面的原因,都经常会愿意得到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资金,甚至甘愿为之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上述西方主导的传统外援体制在此次海啸救援中遭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抵制。在此次海啸灾难中,基于在寻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敏感时刻,和试图通过对灾后重建援助做贡献来树立自立、充满活力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作为受灾国的印度不仅断然拒绝了外国政府的援助,相反还积极对邻国斯里兰卡与马尔代夫展开积极援助,并在美国总统布什的建议下,同美、日、澳一起第一次在关乎地区稳定的问题上同其他有影响的大国进行合作;同样,另一受灾国泰国为了避免影响其外交权益,拒绝接受国外现金援助,其是在强调自立的同时,更担心一旦接受外国的金钱援助,将来自己在自由贸易协定与关税谈判等外交谈判时,难免缩手缩脚和被迫让步,从而影响泰国长远的外交权益。应该说,印度与泰国的上述态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外援体制由上世纪80年代的强调“外援经济条件”到冷战结束后以来更为强调“外援政治条件”的大背景下,不能不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上述国家在此次海啸灾难救助中的举动也不能不说是对传统外援体制“北强南弱”的一次不大不小的“颠覆”。
此次海啸灾难国际援助中的一个“亮点”是中国的举动令人注目和赞赏。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援助舞台上向来“低调”,但在此次国际援助中,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援助,在联合国主导下的国际救援行动中,通过一致性原则,增强了在国际援助中行动的力量。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援助计划中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阿富汗战争后,中国向阿富汗提供了1.5亿美元的重建援助,前不久向海地派遣了维和部队。此次灾难发生后,中国政府很快就承诺为亚洲海啸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总理温家宝出席印尼雅加达救灾峰会,并充分展现中国“全力救灾”的“实效”与“诚意”;高达8300万美元的政府捐款更是一个新的“突破”;中国医疗队迅速进驻灾区服务;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向受灾地区空运数量庞大的援助物资;普通老百姓和民间机构也纷纷解囊;中国香港更是创下单一城市捐款额全球记录,成为全球“最具爱心城市”;同时,中国政府还在2005年1月25日由外交部牵头组织了“中国—东盟海啸预警研讨会”。对于中国在此次海啸灾难援助中的举动,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相当正面的反应,纷纷给予“善意”、“更加慷慨”、(注:Peter Grier,Faye Bowers,and Amanda Paulson,"Profound Shift in U.S.Culture of Giving",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January 5,2005.)“真情救灾”、“实效”等评价,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以及联合国相关机构其他官员以及驻华代表都高度赞扬中国在此次海啸灾难救助中的“积极”、“全面”反应。可以认为,中国在此次灾难救助中的举措不仅展示了中国“安邻”、“睦邻”、“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友好关系,还极大地充实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国国际和外交战略的内容。
二、思考与启示
长期以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援助,不仅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国际政治战略的缩影。冷战期间,美国和西方主导下的传统外援体制中主体性的发展援助实质上成为冷战与发达国家从政治、经济以至军事上控制受援国的工具。冷战结束以后,西方提供的包括发展援助在内的整个外援数量一度下降,到了世纪之交的科索沃战争及更近一点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美国等西方国家与国家集团又开始逐渐重新重视外援,外援再次成为战争的后续与补充行动;与外援从相对“沉寂”到走向“复活”的同时,美、日等西方国家与国家集团的外援政策中的主题与对象也经历了一次全面的调整。(注:随着国际关系与主要国际性议题的变化,美、日等西方国家与国家集团的外援政策中的主题与对象的调整大致如下:在有些不发达国家(尤以非洲国家为典型)由于失去往日在冷战中的地缘政治地位而不再成为援助对象的同时,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政治条件不断增强,更加强调外援中的政治理念与社会价值,从以往外援中一般性地强调军事安全、“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制度等内容细化为“良好治理”、“保障人权”、环境保护、跨国犯罪与反恐怖主义等具体条款,很多过去是主权范围内的政策,如环境保护、人力资源发展、健康和控制犯罪等等,此时也成为对外援助政策的主题与对象,其中反恐怖主义在“9·11”事件后更是得到了普遍的关注,明显成为发达国家对外援助政策中的重要考虑。)客观地说,在调整后的西方外援政策的主题与对象中,有关瘟疫、环境、自然灾害等侧重全球治理与人道主义援助的内容与地位得到了大大提升,但与上述外援政策中主题与对象的调整相伴随的,是外援受政治驱动与基于地缘政治和安全战略考虑的不变。在上述变化中,就日本来说,其对外援助政策的变化主要是由冷战结束前的“发展援助”向冷战后的“发展援助”与“战略援助”的混合型转变;(注:可参看金熙德:《日本:战后的外援与外交》,载周弘主编:《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258页。)就美国而言,在笔者看来,调整后的外援政策不仅是更加侧重政治条件,而且同样重视安全战略。在“9·11”事件与美国外交“单边主义”色彩非常严重的今天,功利主义以及对联合国体系主导下的国际多边机制的漠视与冷淡也势必会体现在美国对外援助政策中。这也再一次说明了,虽然此次海啸救灾属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范畴,但美、日等西方大国围绕救灾所展开的权力与战略安全的博弈,以及美国在此次救灾中,绕开联合国体系拉上其安全与战略上的伙伴单独组建所谓的“国际(救灾)联盟”实在不属于什么意外之举。事实上,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对外援助的现实功用以及对外援助政策理论的研究两个方面。在笔者看来,前者实际上解决的是研究对象的拟定;后者则是针对上述研究对象所提供的研究视角,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彻头彻尾渗透着西方、特别是“美国中心主义”。由此观之,即便在当今互相依赖的全球化时代,向那些由于不可抗力而产生的严重事故或自然灾难而处于困境的人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每个人的道德责任,其所蕴涵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体现了为保障所有人最低生活水平的国际社会的集体责任原则,但在类似于此次海啸救灾事件中超越“美国中心主义”,实现前文所述的斯多克的真正“人道主义的国际主义”国际社会恐怕仍然任重而道远。
就联合国救援体系而言,目前在联合国机构中,就重大自然灾害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范围主要由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UNHCR)、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调整。长期以来,联合国体系由于其自有资源一直是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领域中的强大力量。在此次海啸灾难救援中,联合国体系所发挥的上述功能与作用,证明了其主导下的救援以及通过其对外援物资的筹集、组织协调与整合而形成的超国家的理念与政策,以及组织外援资金转移的普遍合理性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功能;而美国单独组建的“国际(救灾)联盟”最后不得不让位于联合国的主导,也间接证明了联合国体系与机制在应对此类国际灾难与问题时的不可或缺性。但同时也必须承认,此次海啸灾难救助中大国援助与捐款的竞争和比拼的事实,以及完善的国际救灾机制、成熟的预警机制和善后协调机制的事实上的不足,都表明了在现有国际组织与国际体系尚无立法与行政能力解决司法不足、参与不足、激励不足与约束不足的前提下,联合国国际组织体系权威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与困境。而这可能是今后联合国体系本身以及国际社会所要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长期问题。同样,此次在全球范围内涌现出对印度洋沿岸灾区的民间援助热潮,的确值得肯定,因为相比于主权国家与现有政府间国际组织,民间援助考虑的更多只是单纯的道义原则,而这事实上正弥补了现有世界体系下全球治理的不足。不过,在全球化时代下的各种国内力量开始绕过传统的国家利益代言人,和国外的机构、集体乃至个人发生着直接的沟通与交往,并实现着自己的利益与价值取向的时候,也难免同时出现一个多元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为者追求不同的目标而产生的混乱局面,而这恐怕也是国际社会今后所要面对的一个局面;而对正在积极开始参与国际援助实践的中国来说,了解、关注包括人道主义救助在内的有关国际援助的理论、政策与运行机制也属当务之急。
标签:中国援外论文; 海啸论文; 日本海啸论文; 日本地震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社会援助论文; 联合国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