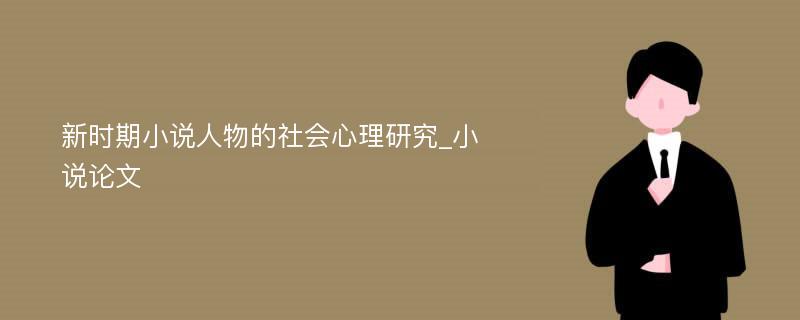
新时期小说人物的社会心理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学论文,新时期论文,人物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就社会心理的二重性和社会心理特征两个方面,对新时期各种类型特别是性格小说中人物的社会心理特征和丰富内涵,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分析考察,探寻了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演变的趋向和线索。
对新时期小说人物进行的社会心理学考察,是立足于开阔的文化视野,依赖于活跃的思维方式,着眼于考察对象的自身的特质。八十年代以来小说作家们认为,以表现事件为主的小说,事件是它的着眼点,事件的发生、发展、结果便是小说的结构形态,人物成为附加品,成为串联全篇的道具,这样的小说其价值是会受到影响的。与此相反,许多小说家崇尚性格小说,即以刻画人物性格为目的并以性格发展线索来结构小说。在这种小说中作家们广泛地借鉴各种艺术手法,诸如原发性联想、梦境、内心独白、弥漫的情绪、打破时空秩序等来拓展人物心理活动的空间,使小说人物的心理内容空前地丰富多彩。在这些小说中虽然人物性格心态各异,但是人物的心理内容绝非是个体性的。新时期小说家们虽然重视性格小说和人物的心理活动,然而传统文化养就的文学理想和取材思维方式,必然会使他们更多地着眼于社会性的心理内容。于是,社会成员之间心理上的相互影响,包括自己的心理对他人和他人的心理对自己的影响,还有自我与他我这种个体自我意识领域的影响等等,就在人物形象中广泛地呈现出来。这就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新时期小说提供了最丰富多样的艺术客体,开拓了文学研究的空间。
新时期小说人物的社会心理学考察可以从社会心理内涵和社会心理特征两方面展开。
一
社会心理既是内在心理过程,又外现为社会现象,这是社会心理不可分割的双重属性。社会心理的内在过程中包括社会认识、社会情感、社会动机和社会态度等。其中的社会情感以特殊的与文学有着天然联系的性质进入小说创作,渗透在小说人物的心理世界中。其他心理过程都是在社会情感的掩盖影响下进行着。新时期小说创作中人物社会情感的表现有这样一些方面和特点:
1、借助人物的社会感情来建立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示丰富、深刻、有着文化意蕴的背景。一些作家意识到,社会感情对人际关系起着纽带作用。建立人际关系靠沟通(信息传递),又靠人际纽带。感情纽带作用比信息沟通更深入牢固可靠。言传、身传和媒传,是有声有色的、表达式的,侧重于表现;心传,虽然无声却能传出深情,传出心意,心传是深沉的、深入内心的,能通达灵魂。借助心传建立人物的关系自然而深刻。张承志《黑骏马》中的索米娅、白发额吉是世代生活于草原上的人们,他们对人诚实、善良、宽厚,注重人情,这是草原的宽阔质朴以及独特的生活方式培养起来的感情,是最典型的草原人民的社会情感,这种情感构成了白音宝力格告别草原而后又回来寻觅某种失落了的东西的背景。白音宝力格的社会感情则是他在另一个文化氛围中建立起来的,其中更多一些理性的成分,因而,不同质的社会感情联结着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的关系,他们既相融汇又相冲突,产生了浓厚苦涩的人生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李顺大这个普通农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有着真挚朴素的感情,他善良、正直,这是那个特定的年代造就和培植起来的社会感情,这种社会感情构成了李顺大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使得李顺大这一形象更坚实可信。新时期之初相当一些充满使命感、责任感、旨在以小说揭示出振聋发聩的社会问题的作品,都极为重视人物的社会感情所联结的人际关系。这种现象本身就表明,作家是从群体的角度分析、考察社会问题,观照人物的。此外这种视角由于重视人物社会情感及社会情感所联结的人际关系,也恰恰符合传统小说中人物相互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以推动情节波澜起伏地向前发展的要求。
2、重视小说人物民族感情和信仰感的价值,并对其加以深入开掘,使之成为小说人物的本质特征,并且影响到作品的整体性风格。社会感情的存在形态可以从纵横两个角度看。从横的方面看,有短期起作用的情绪状态和持续起作用的感情状态两种,两种状态相互贯通,在实际过程中相交叉。从纵的方面看,是个由不同层次构成的感情系统,包括内心感情、人际感情、群体感情、民族感情和信仰感情等。民族感情和信仰感情是这个系统中的最高层次。民族感情沉积于小说中的性格独特的人物心灵世界中,往往会使人物产生悲壮的色彩,并弥漫于整篇作品。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中的范汉儒虽然备受政治上的不公正待遇,但他对祖国的爱却始终如一,并水乳交融般地汇入他的血液之中,决定着他的人生选择和命运。在炼狱中他结识了陶莹莹,并且深深地爱上了她,可是当他得知陶莹莹曾有过“叛国”的记录时,就断然地割舍了这份爱情。对范汉儒来说,什么都可抛弃,唯独祖国不可抛弃,民族情感是神圣而不可亵渎的。范汉儒终究没有寻找到爱情,他的民族感情是悲壮而真诚的,而他的命运则是凄凉的。这种神圣的民族感情不仅造就了范汉儒这个人物,而且将整篇小说都涂抹上悲剧色彩。其他如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谌容《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等人物的民族感情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新时期以民族感情为主导色彩的人物大多出现在对知识分子命运“反思”的小说中,在这些作品中,知识分子是以“弱者”的面貌出现的,他们或者受到非人的对待,人生之路坎坷而悲惨;或者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但在物质利益和精神报酬上,却未曾得到相应的报答,或者虽然身陷囹圄,处于逆境,但在威逼利诱面前却大义凛然,不为所动。作家的创作意图是在为知识分子恢复“本来”面目,也是为了博取人们的同情,于是在人物创造中民族感情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和诗意化,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真实感。同时也向社会提出了一个涉及文学又涉及社会政治的尖锐问题:人格完善了,就能解决社会历史问题吗?这是一切关心知识分子命运的人们值得思索的①。无论怎样,民族感情在人物创造中的作用是作为当代文学发展中一个有深度研究价值的问题。
信仰感是社会感情的最高层次,信仰是人们对非现实力量的无限尊崇和信服。注重信仰感在人物心灵中的底色,是理想主义文学的基本前提。在“十七年”的文学中曾有过一些这样的人物,他们的信仰感压倒了一切人类其他感情,成为人物精神世界的全部,失去了血与肉的真实感。新时期小说中这类人物已经销声匿迹了,但人物精神世界中的信仰感依旧存在,并与其他感情浑然天成地融为一体,以各不相同的性格体现出来,读者接受了人物性格的时候,也就自然地接受了人物的信仰。这种现象出现在一些成功的作品中。《都市风流》中的市长阎鸿唤性格独特,他有过人的智慧和果断,又有锐意改革的精神和求实的作风,他的一系列决策和行动都是他这种性格和作风的体现:将女设计师徐力从市政局长的位置上解脱出来,让她重操桥梁设计的本行。徐力以自己最后的生命设计了光明立交桥。阎鸿唤还将原市政公司的建筑队长杨建华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杨建华的优秀品质显示出潜在的人民力量是改革有希望和前途的必备条件。阎鸿唤对生活和未来、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就渗透在这些决策和行动中,渗透在他的性格中。阎鸿唤的信仰感决定了整部作品的饱满、充实、积极向上的美学风格。信仰感不仅包括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还有人生信仰、人格信仰等。一些人物正是以他对人生的独到理解和对这种人生的执著追求而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的人生故事在小说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他有农民的底色:善良、勤劳、质朴,富于同情心,珍视友谊等。但是他更多的是接受了外部世界和现代意识的影响,自觉地扩大了自己的生活天地,进入了另一个社会的大世界。他有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和追求:“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又要从我们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就是凭着这个信仰,孙少平从双水村走出来,经过县城、地区包工队生活的磨炼,终于走向煤矿工业。自觉地抛弃传统农民人格中的弱点,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念,追求更丰富充实的人生。从孙少平新人格的建立,从独具特色的信仰感的角度,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物是路遥对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3、从人物的社会感情到情绪的转移,是新时期小说人物创造中的趋势。在一些小说人物的社会感情产生着艺术魅力并影响到作品风格的同时,另有一些作品在人物创造中侧重捕捉和再现人物的情绪,并有愈来愈强化的趋势。感情世界主要是由情感和情绪构成的。情感和情绪是两种有区别的感情现象。与情感侧重从认知方面体验和感受不同的是,情绪侧重欲求方面,它少理智和评价,而多自发性和欲求性。从个体水平的心理过程来看,情感过程同自我意识更多地联系在一起,有明显的强烈的自我感,情绪过程同本能、无意识有更多的联系。从社会水平的心理过程来看,情感基本上与高层次社会精神现象相联系,情绪则同低层次的社会精神相联系。情绪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属于社会感染现象。此外,情感是深入内心的过程,情绪则是由内向外的外现过程。新时期以来,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题目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情绪的概括。小说表现了作家对生活的敏锐发现:充满了种种生活裂变的时代必然产生的一种痛苦,即一种急剧的现实变化带来的精神世界的“浮躁”情绪。金狗是小说中最能体现这种精神浮躁的人物。一方面他具有正义感和初步的历史使命感,另一方面在许多方面又幼稚脆弱。在复杂强大而严峻的现实面前,费尽心机,有时还有小小的狡猾,但还是不能拯救他所面临的那种世俗意义上的颓势。作为一个农民(或一个船工、或一个记者),他要改变现存的生活方式,抵抗邪恶,伸张正义,但他的力量与能耐实在是太渺小了,于是他往往不能战胜自己而不可避免地产生浮躁情绪。这些浮躁情绪“向我们诉说着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烦难艰巨,诉说着一个富有传统的民族在锐意进取的道路上必然会领受到的种种来自进取者本身的束缚与制约,诉说着农民的命运在急剧变迁的时代机遇中不能不产生的千姿百态的缓慢转变,以及那种潜在的观念更新——也诉说着他们的忧患和信念”②。近几年的新写实小说和前几年出现的新潮小说,人物大多是以情绪特征为基本底色的。当然两种小说中的人物情绪的处理与表现是有所区别的。新写实小说刻意追求生活的原生态化,追求小说的原滋原味。按说这种近乎于自然主义的创作观念是不会注重人物的情绪内容和特征的。但是绝大多数的新写实小说家却认为,生活流中的人物,他们的生存境况、情感欲望和生命搏动,他们的艰难和困惑、努力与挣扎也必然活脱脱地毫无矫饰地表现出来,小说人物心理中多方面潜在的无法言说的欲求也必将会得到真实而充分的表现。新写实小说中人物的情绪都生活化了,似乎是本能地任随生活的左右。这个特征使我们似乎捕捉不到人物的情绪内容,但是揭开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后,情绪就显现出来了。赵本夫的《走出蓝水河》中渗透于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中的,是野蛮与文明的交错,历史前进的迂回曲折以及人在文明与野蛮的撞击、消长中的痛苦。小说中的野孩表面看是随着命运的支配颠簸流浪,但是在他的人生轨迹中却分明有一条情绪线索:对一切伤害过自己的对象施以报复,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欲望。他的人生是悲惨和富有戏剧性的,欲求却是值得思索的。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塑造了庸庸碌碌、被种种烦恼所缠绕的小林和小林老婆的形象。小林被琐碎而烦人的生活打磨得完全失去了朝气和棱角,剩下的就是无可奈何地任随生活裹挟着前行的情绪。小林的情绪是作家刘震云情绪的投射,正如作家在《磨损与丧失》一文中谈到创作这篇小说的思想底蕴时所阐述的,他认为生活是严峻的,严峻的是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单位、家庭、上班下班、洗衣做饭弄孩子,对付保姆,还有如何巴结人搞到房子,如何求人让孩子入托,如何将老婆调进离家近一点的单位。每一件事情,面临的每一件困难都比刀山火海还令人发愁。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得与人打交道。我们怕人,于是我们被磨平了③。
二
社会心理特征是对新时期小说人物社会心理考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社会心理特征是融社会群体心理和个体心理为一体的。我们的考察是从人格的角度切入的。人格的概念起源于拉丁文的“面具”,用于演员等戏剧人物,与角色有相似的意义,经过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反复应用,人格概念已有不少变化。从文化(文化环境)对个人的影响作用看,人格是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成熟起来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之总和。人格特点和文化类型是一致的。从社会个体的社会心理过程看,人格是个人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的总和。心理特质是隐藏于内的,性格特点是内在因素的表现特点,属于表现在外的东西。人格是各种心理过程的统一,统一于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强弱与否,是人格成熟与否和人格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新时期小说人物的心理特征表现为从人格与文化类型相一致到人格与文化类型的关系渐趋模糊;从人格的鲜明突出到不甚鲜明突出乃至人格的消失。
1、从人格与文化类型相一致到人格与文化类型的关系渐趋模糊。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等等作品中,人物的人格与文化类型基本是一致的。文化类型成为人格产生和表现的背景,人格是特定的文化类型的个体化表现。任何人格的表现都可以追溯到它的社会化过程和文化类型的某些特征。如《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靳开来是个人格高尚、性格独特的人物,就表面看,他外在的性格特征与他的人格是矛盾的,非一致的,但是当这个人物走完它的人生历程,将他的性格展示完毕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高尚的人格与从外表看来随便、玩世不恭、牢骚满腹的性格特点的内在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恰恰是与靳开来由农民成为一名战士,由农民文化的质朴、纯厚、随便和军营文化的献身精神相一致的。或者说,他的人生经历背后的文化氛围就是他人格的凭证。何士光的《乡场上》的冯幺爸的人格由委琐、软弱、忍气吞声到大胆地表示自己的愤怒与抗议,性格的跨度恰恰是农民由贫困到自给的经济变化的幅度,同时也是传统农业文明的隐忍观念发生变化的形象投射。冯幺爸的形象可以说是农民人格变化的缩影,这个形象不仅具有它自身作为一个人物在小说中的意义,而且具有唯物主义即物质决定精神的认识意义。《李顺大造屋》中李顺大的性格特点是勤劳质朴。祖祖辈辈农民生活培育起来的置房、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心理具体化为他的造房子的目标,为此他展示了一个农民人格的全部可贵和可怜。这个人格是我们解放以来至新时期开始的极左政治气氛和文化环境的产物,是与农业文化类型相一致的。与文化类型相一致的人格与社会性格也是一致的。所以由这种人格也能考察出社会性格的特征。在上述小说中人物的人格都与特定时期的社会性格相近或相同,人物是那个时期社会群体中普遍性格的代表,而后来的新潮小说中的人物,其人格难以与某种文化类型相联系,呈现为模糊不清的特征,与社会性格丧失了同一性。洪峰《奔丧》中的“我”是一个奔丧的儿子,他本应对父亲的去世悲伤痛哭,而他却游离于对父亲的感情之外,并且对姐姐的身姿表示出异性的兴趣。就人格来说,这是低劣而无情无义的。那么是怎样的文化类型培植了这种人格呢?阅读中无法获得答案。再如格非的《迷舟》中的那个“箫旅长”,是怎样的文化引导他陷入那场置他于死地的情欲呢?难以回答,可以得到的唯一回答是:他的生物本能和神秘的超人的力量使然。形成上述人格趋向的原因何在?首先是由于作家们主要是从个体视角而非群体视角来创造人物。他们不认为人的个体人格与社会文化和群体的社会心理有怎样必然的联系。其次是他们对文本意义中的真实和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独特理解。例如余华曾认为,现实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的事物。而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他认为,在他的精神世界里面,“很早很早发生的事情跟昨天发生的事情是同时存在的”,他觉得它们非常整齐,非常真实可信,把握它们也更真实④。既然这样,那么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对现实世界的依赖就不存在了,人物的人格只要在小说世界中能成立就可以,它不需要与现实世界的文化类型和社会性格相一致、相联系。也许这会使小说世界乃至小说人物孤立,与现实世界相脱离,然而这恰是新潮小说家们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2、从人格的鲜明突出到不甚鲜明突出乃至人格的消失。人格的鲜明突出是传统小说刻意追求的效果。人格的鲜明突出能够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引来读者的情感投入,也易于在小说文本之内建立起和其他人物的关系从而推动情节的发展。在新时期相当数量的小说中,有许多这种人格鲜明突出的人物:高加林(《人生》)、安然(《没有钮扣的红衬衫》)、香雪(《哦,香雪》)、陈奂生(《陈奂生上城》)、谢惠敏(《班主任》)等等。但是在后来的一些新潮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模糊不清,崇高与卑劣,纯洁与污浊,善良与邪恶,都没有打上明显的印迹。如前所曾列举过的洪峰的《奔丧》中的“我”,他的人格可以概括为低劣与无情无义,但这种人格在小说中并不明显,在低劣与无情无义的后面更本质的东西应该说是麻木不仁和随遇而安。马原的《虚构》中的“我”,是小说中的主人公,“我”走进了一个麻风病人居住的村子——玛曲村,并且与一个女麻风病人产生了性爱。“我”这个人物没有任何人格特征,有的只是任凭感性需要随意的行动,对这些行动无法进行人格评价,因而这个人物真实性只存在于小说文本所呈现的虚构意义中,与这个人物相联系的是小说所表述的故事也是不真实的,它的虚构意义来自对现实的否定。上述小说人物现象缘于作家们重视文本意义,即虚构意义。他们认为现实生活的意义对文学是不重要的。小说所做的就是把平日不易觉察的意义形式在虚构环境里加以组织和改造,变成新的意义形式而突出出来。由于单项事物所处的环境和位置不同,所包含的意义也不同。单项事物的位置一旦在虚构世界里被确定,它本身的意义以及和它同一系统中的其它单项的意义、系统整体的意义也就产生了。那么作为小说的一个单项的人物,他的意义是在虚构世界里被确定下来的,倘若虚构世界不予评说现实世界的人格,那么人物的人格色彩在虚构世界中也说自然可以模糊乃至消失。追求人物“谜”一样的色彩,也是人格模糊乃至消失的原因。清晰的人格可以使读者在阅读中看到人物的底蕴,而这恰好是新潮小说所忌讳的艺术效果。他们努力造成人物的“迷”一样的色彩,使阅读不易把握。人物的“谜”可以向读者提供这个人物的多个意义,并且多个意义复杂地交错在一起。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就常常具有这样的效果。例如托马斯的《白色旅馆》、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橡皮》和《吉娜》、托马斯·品欣的《第四十九街的呼叫》,这些作品中的情节是永远不能理清楚的,人物也永久地以“谜”样的色彩呈现给读者。除上面论及的重视文本意义即虚构意义的原因之外,这些小说还依赖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不明确的意义传递是永恒的常数:交流活动总是从一个确定无疑的信息发送者到一个同样确定无疑的信息接受者。并且意义传递活动总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而语境本身不可能是充分的和没有缺陷的。意义总是不完全的,任何语境中的任何意义传递,总有一个意义的剩余部分是我们无法掌握的,错误与废话、意义确定的不可能性,已深嵌入每个意义成分和交流的本质中。困难的在于这些意义本身不确定,那么,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就必然被罩在迷雾之中。我们在新潮小说人物“谜”一样的特征中看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和相应观念的影响。毋庸置疑,新潮小说在这方面的探索是可贵的,但同时也值得进一步思索,经受审美接受的检验。
注释:
①参阅洪子诚《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第120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②周政保《〈浮躁〉:历史阵痛的悲哀与信念》,原载《小说评论》1987年4期。
③参见刘震云的《磨损与丧失》,原载《中篇小说选刊》1991年2期。
④参见余华:《我的真实》,原载《人民文学》1989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