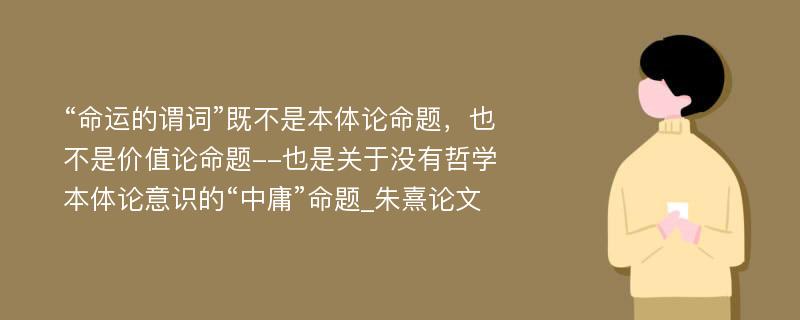
“天命之谓性”既非本体论亦非价值论命题——兼论《中庸》并无哲学本体论的自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价值论论文,中庸论文,天命论文,命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5-0008-07 一、学界对“天命之谓性”的误解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微,莫显乎隐,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首章》) 现代不少人都紧跟在宋儒后面“接着讲”(冯友兰语),认为首句“天命之谓性”是融本体论与(道德)价值论为一体的命题。冯友兰说,“盖天为含有道德之宇宙的原理,而性则天所‘命’于人,人所‘分’于天者也。……以为吾人行为之意义及价值,并不在行为之外,而即在行为之自身,《中庸》与此人生态度,以形上学的根据。”①牟宗三认为,天命乃作为创化原理或生化原理的形上实体,天命之“性”是指与禽兽之性有本质不同的超越意义之性,价值意义之性,体现了儒家从天道下贯而言的道德理想主义之色彩。②劳思光说:“其中‘天命之谓性’一语,表示心性论及形上学两种立场之混合。”③徐复观说,“天命之谓性的另一重大意义,是确定每个人都是来自最高价值实体——天——的共同根源”,“而其根据则为‘天命之谓性’的天。天即为一超越而普遍性的存在。”④杜维明认为,天是人的内在道德性的超越的本体论基础,“人性受命于天表示了一种使人性与天的实在性得以合一的本体论基础。”⑤李宗桂认为,“天命之谓性”认定了“人之‘性’是‘善’的”,表明了“道德本来是先天禀赋的”,“使原先在孔子那里仅属于主体的道德理想的追求获得了存在论的支撑”。⑥杨国荣解释首章说:“要而言之,以‘性’与‘道’的辨析为出发点,《中庸》既肯定了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的统一,又联结了本然与当然,而内在于其中的基本视域,则是本体论与价值论的统一。”⑦ 虽然价值论是来自西方的学术术语,但其实把所谓的天命之“性”与道德直接关联的解读,至少早在东汉末年郑玄就已开始了。只是郑玄虽然认为此“性”中包含仁义礼智信,但并未认为性仅指五常之德。可是朱熹在解“天命之谓性”时,却说“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⑧这就是认为天命所赋予人之“性”,仅仅是指仁义礼智信五德。⑨这样,“性”本身就成了道德的标准,而现代人“接着讲”,自然就认为“天命之谓性”是个价值论命题。再加上把“天”视为超越的形上实体,这句话同时就又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本体论命题。 但实际上,“天命之谓性”这句话,在《中庸》文本中,既不是本体论命题,也不是价值论命题。虽然从东汉至宋明,儒学内部大多数人都把它当作具有道德规范意义的命题,但从来也没有谁合理地证明过它的道德规范性,后人只是代代因袭前人的解释,而前人的解释却从来没有建立在严谨的论证之基础上。至于所谓的本体论,虽然朱熹等人的解释已隐约有此倾向,但却并非立足于《中庸》本身的根据,而现代学者也没有接着朱熹等人进一步提出令人信服的论证。 二、“天命之谓性”非价值论命题 如果《中庸》可以成为一部相对独立的儒家文献,而且可以根据这一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献本身的内在思路,对它里面的某些章——如首章的含义,做相对独立的解读,那么,我们可以说,“天命之谓性”这句话,不是个明确的价值论或包含价值意味的命题。甚至可以说,它没有表达任何道德价值倾向。 那么“天命之谓性”如何会被认为具有价值意味乃至成为一个价值论命题呢? “天命之谓性”接下来就是“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字一出场,价值意味才始出头。但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倾向,也还并不十分明确,因为所谓的“率性”之“道”,既可能是指本能地顺从天生的生理本性,如“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之类,也可能是指自觉地遵循其他具有道德意味的天命之性。如果是后者,“道”当然具有道德价值意味;若是前者,则价值意味轻些,甚至根本就无所谓价值意味,而纯粹是一种对事实的描述。否则就不用紧接着再说“修道之谓教”。 郑玄认为,经过修治广大之后,“道”始可为人仿效,这整个过程就是“教”。⑩既如此,则可知郑玄并不否认,“率性”之“道”,既不仅仅是指本能地顺从天命的生理本性,也不仅仅是指自觉地遵循其他具有道德意味的天命之性。否则,如仅指前者,亦即食色之类的本能性行为,人人皆会,何须待“修”而成教化呢?如仅指后者,则人们直接遵守未经修治广大之“道”就已经是一种道德行为,何必再“修”而成教化呢?正是因为“率性”也可以指本能地顺从天命的生理本性,而人又不能不对此类行为有所节制,并同时加强“率性”中所包含的具有道德性的行为,所以要成教化,就必须先“修道”。如此“修道之谓教”这句话,才显得必不可少。朱熹因为只把人之“性”规定为五常之德,因而使得“率性”之“道”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道德,百姓直接照着这个“道”做就是有德,从而使“修道”对教化而言成为画蛇添足。虽然朱子抬出“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11)来解释“修道”即品节道的必要,但这除了显示他自己的理论建构之外,丝毫也无助于消除他把“性”狭隘化给《中庸》本文所带来的前后矛盾。 “道”要经过修治或品节之后才能让人仿效,可见并非所有率性之“道”都具有儒家所看重的道德价值意味,或者说其道德价值意味不是自然现成的。“道”虽然离不开“性”,但并非直接成于“性”,而是成于以“性”为对象之主体行为“率”。如果只有“性”而无“率性”,则不可能产生“道”。“性”乃先天之自然,而“率性”乃主体后天不背离性之行为。可见,就人道而言,《中庸》认为只有人后天的行为发生之后才有所谓“道”。这与庄子所谓的“道行之而成”(《庄子·齐物论》)之义若合符节。(12) 因此,如果不接着宋儒,或者根本就不接着儒家讲,不以“天”为道德的至上权威或终极根源,那“天命之谓性”倒是表达了某种价值规范性。《淮南子·齐俗训》云:“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可见,在此处的道家看来,即使“绝仁弃义”,也照样可以保住“天性”的价值权威。此论入手处虽与老庄原始道家有异,但与老庄仍是灵犀相通。在他们看来,天固然不是仁义之类道德价值的根源,但却是比仁义价值更高的另一种价值的根源。这种价值就是因应自然或顺乎本性,它们高于仁义礼智之类的道德价值。而天在他们看来,本身就代表或象征着自然。但《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之宝典,我们自然不能借他山之石来建立“天命之谓性”的价值圣殿。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继续追问,为何“率性”之后还要“修道”方可成“教”?我们越是深入细致的剖析这个问题,就越是发现,不但“天命之谓性”离价值意味越来越远,而且就连“率性”之“道”的价值规范性其范围也越来越小。“率性之谓道”乃就个体而言。作为个体的人,人人各率己性而成己道,不可能率他人之性而成道。每个人的天性都具有与他人不共的特殊性和与他人相类或相共的普遍性。因此每个个体率性之“道”,如果其所率之性乃属于特殊性,就只对每个个体自己具有规范性,而不可能规范他者;只有当其所率之性恰好属于普遍性,才具有公共的规范性,而不仅仅单独规范其本人。当属于前一种情况时,每个个体的率性之道,就难免与他人的率性之道或万物之道相互产生冲突,因此就可能威胁或妨碍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相处,从而最终有害于“成己成物”(《中庸·25章》)之实现。于是需要“修道”成“教”,以消除各个个体之道之间的相互冲突,乃至个体之道与物之道之间的相互冲突,达到所谓的“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30章》),做到“致中和”,从而最终实现“万物育”、“天下平”(《中庸·33章》)的最高理想。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郑玄解释说,“道”就是道路,是人出入行动之所由,不可或缺。虽然行动着的人所依赖的一切条件并非同等重要,而是存在着即使暂时离了它也不影响当下行动的条件,但这种可以离开的条件——哪怕是暂时性的离开,肯定不会是道路。(13)郑玄在这里用“道路”解“道”,乃取其本义用法。这种解释虽然并不违背语境,但却纯粹是从字面上解释词义,根本就没有触及这三句话的深层意蕴。而朱熹的解释——“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14)——虽然颇具本体论之意味,但却脱离语境,完全是自说自话。因为如果像他这样解释,这里的三个“道”,就与上两句的“率性”、“修道”之道,所指就如同风马牛,前后文就成了毫不相干的七拼八凑。 实际上这三句与上两句密切相关。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就每个孤立的个体而言,是指每个人的生存都不能违背扭曲各自天生的人性,因为“率性之谓道”;就每个处于社会共同体和自然等关系之中的个体而言,人人都不能背离修道而成之教化,否则社会不宁,万物不育。因此,所谓不可须臾离也之“道”,既包括率性之道,也包括修后之道,而并非指朱熹所谓的“无物不有”的本具之道。当然,这个道可能包括朱熹所谓的“礼、乐、刑、政之属”,只要它们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可以“为法于天下”。(15)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16)这里用表因果关系的“是故”一词承接前文,可见文本作者认为,君子戒慎恐惧、慎独等修身的道德行为,是在前文所讲道理的影响下而产生的结果。修身之君子固然不可须臾离道,但既然“率性之谓道”,而率性却本无须人监督,为何君子还要戒慎恐惧乎无人闻睹之时,慎独隐微之地?为了消除此困惑,我们就必须承认,文本在此对一个前提性的事实秘而不宣。此前提性的事实即是,如果缺乏他者或众目睽睽的监督,人们可能会姑息或放纵自己,背离修道而成的教化,迷失于天性之中消极阴暗之一面,或自封于一己之小道,从而不利于修身,乃至最终危害平天下、育万物之大业。既然如此,那么凡修身之君子,在无人闻睹时就应戒慎恐惧,在隐微之处则应慎独。慎独与戒慎恐惧乃修身立德之必需。 如上所述,虽然道产生于率性,但既然其规范性不是决定于“率性”,而是决定于“修”,那么,“天命”之“性”本身就并非必然需要带有道德性,更不必像朱熹那样认为人性仅仅是指五常之德。天生的人性完全可以是指人天生本具的一切本能、机能和倾向性。 这样界定人性不会像郑玄、朱熹等人那样,在解读文本时总是顾此失彼,漏洞百出。相反,如果人之“性”的内容不包括人天生本具的一切本能、机能和倾向性,而仅仅包括朱熹所谓的五常之德,则非但引起上文所提到的矛盾——“修道之谓教”成为多余,而且紧接着“故君子慎其独也”之后出现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这句话,就会显得很突兀,让人感觉,虽然同在首章之内,但这一句却似乎与章首的“天命之谓性”毫无关系。但如果“性”的内容本来就包括人天生本有的一切本能、机能和倾向性在内,那这一句就与章首遥相呼应,因为喜怒哀乐等感情正是人生而具有的本能或机能对外界的反应。朱熹认为喜怒哀乐之情未发时叫做“性”,(17)可是,如果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人之“性”只能是指五常之德,那它们发出来怎么就会变成喜怒哀乐之情呢?(18)这是朱子把“性”狭隘化给文本带来的另一个矛盾,而且这一次他也给自己的解释链造成裂缝。 如果“喜怒哀乐”之情本身就属于首句所谓的天命之“性”,那么接下来所说的“发而皆中节”,则与开篇所谓的“率性”、“修道”,无论在文气与文义上都遥相呼应。“发”呼应“率性”,“中节”呼应“修道”。率性而不修道,则喜怒哀乐发而不中节。(19)“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则“发而不中节”谓之失和。率性而不修道,则人无教。人无教,则不知如何节制情欲。不知如何节制情欲,则人与人、人与万物皆不能和谐相处,亦即失和。失和,则天地不位,万物不育。唯有“致中和”,方可“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亦即唯有率性且修道,方可天地人三才和合,“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30章》)。这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可见,把天命之“性”理解为人天生本具的一切本能、机能和倾向性,整个首章都气脉通畅,条理连贯。 事实上,“天命之谓性”这一命题,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只是对“性”做了内涵或形式的规定,并没有对其外延或具体内容做任何限定。如果文本本身的语境允许把人天生本有的一切本能、机能和倾向性都归之于天命之“性”,那就不必像历史上已有的做法那样,各自根据自己的理解及其时代的具体需要,对“性”之内容各做脱离文本语境的割裂取舍。郑玄用五行说,认为“性”中包含仁义礼智信。本来《中庸》开篇即言“天命之谓性”,这与“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论语·公冶长》)的夫子,旨趣已有所异。而郑更采用邹衍、董仲舒以来的五行说解性与五常,则又与由四心或四端言性与仁义礼智的孟子,更行更远。至朱熹则进而用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之说,认定“性”对于人而言仅指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当然与孔孟之旨更大相径庭。 直至18世纪中叶,戴震看不惯主张“性即理”(20)和“存天理,灭人欲”(21)的程朱一派的理学家,把所谓的“以理杀人”(22)的血帐,莫名其妙地扣到他们头上,并跳出来说,“性”就是血气心知,人欲和心知一样,也属人天生本有之性,天理、仁义即在人欲之中,舍人欲即无天理、仁义。性本身并非五常之德,顺乎性、遂乎欲才会产生仁义等五常之德。(23)这才近乎还了《中庸》天命之“性”的本来面目。 熊十力、钱穆、劳思光等人都对戴震如此论“性”深为不满。他们认为,如果像戴震这样,认为人性本身既非道德亦非道德之标准,那么儒家的道德就没有客观可靠的内在保障,进而《中庸》本身所谓的“修道”、“中节”也就不知以何为标准。其实,这只是后人的偏见。当这种偏见幸遇康德的伦理学并以之为后盾时,就显得更加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事实上,《中庸》本身为道德标准确立了很清晰的来源。这种标准来自于人之心对“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这些儒者所要实现的目标、所欲达到的境界的认知。借助经验并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中庸·20章》),总结出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达到上述境界的道理,此道理即可作为道德乃至治国之标准。《中庸》所谓的天之“诚”,表达的就是对这种标准的认知。因为所谓天之“诚”,就是指天地“生物不测”(《中庸·26章》)以及人和万物皆生生不息的现实。凡是有助于达到“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物生生不息的道理,就是修道和中节所应该遵循的标准,因此“君子诚之为贵”(《中庸·25章》)、“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中庸·23章》)。可见,并不需要以人性为道德或直接以之为道德标准,而只需借助人性所固有之心知,在经验中认识到可让人和万物生生不息之道理,就能确立道德乃至治国的标准。另外,天命之“性”当然不排斥孟子所谓的作为道德之萌芽或可能性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但即便如此,率“性”之“道”也未必就必然具有道德规范性,如果这三心之所发因缺乏认知能力的引导而投向错误的对象,并因而有碍于天地正位、万物化育、天下太平的话。 如下文将要论证的,“天命之谓性”只是从万物生成的角度描述了一个自然事实。而《中庸》首章却把这种自然事实当做人的一切生命活动的一个事实前提,因此它也就成为人的道德修养行为的一个事实前提。先发生的事实虽然为后来行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或对后来行为形成各种各样的限制,但其一,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必须认定先发生的事实对我们后来的行为具有道德规范性,因为任何事实都不能直接成为道德规范,任何道德规范都是人后天自觉选择的结果;其二,这更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把天高捧为形上的道德根源或位格神,道德规范才能成立并赢得我们的尊重,这就像我们即使不把生养万物的天高捧为形上的道德根源或位格神,也无碍于我们自觉尊重禾苗的生长习性而不揠苗助长一样。 三、“天命之谓性”非本体论命题 “天命之谓性”根本就无所谓本体论命题。因为“天”与“性”之间,只是被看做一种生成和被生成的关系,而并没有同时被看做本体与现象或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天”也并没有被视为万物的内在构成要素或生成原理,所以这里对“天”与“性”之间的生成与被生成关系的叙述,根本就没有表达任何一种可称之为本体论的观点,而只是在纯粹描述一种自然而非人为的事实——即人性是天生的,(24)而这就犹如说人的四肢乃是天生就有而非后天人为安装的那样。 而且,如前文所述,既然“道”的道德规范性取决于“修”而不取决于“性”,那么“天命”之“天”就并非必得被认定含有道德的形上根源之意味。其实天很朴实,就是指与大地相对而言的苍天,人和万物皆生长于这样的天地之中。《中庸》里的“天”大多是这种用法,如十七章“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之“天”,又如首章“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天”,以及十二、二十二、二十六、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等章中的“天地”并用或与地对用之“天”。(25) 《中庸》有时把圣人之道或德与“天”的化育万物之功德相比拟,但即使这样,“天”作为苍苍之天的意味也丝毫未减。如,“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中庸》27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中庸》31章)“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中庸》32章)这些地方的“天”都明显能看出其作为苍苍之天的意味。 事实上,在《中庸》里,“天”直接在宗教或道德意味上来使用的情况,并不多见,只有很少的几处。直接在宗教意味上使用的,如“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中庸》29章)“《诗》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必受命。”(《中庸》17章)而后一例中“天”的宗教意味显然是从《诗经》带来的。直接在道德意味上使用的,如“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中庸》20章)但即使这里的“天”,也未尝不可同时当做生物之苍天来理解。(26)因为天生而成的人性虽然本身并非道德亦非直接就是道德的标准,但修养道德却必须以人性为基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说“思修身”最终“不可以不知天”。 另外,当《中庸》把“天之道”与“人之道”对比使用时,“天”更具有与人为相对的“自然”之意,转而与道家之旨相通。如“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20章)一直以来,人们多把“诚者天之道”解作“诚是天道或天德”,把“诚”当做形上本体,从而这句话就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可是如果这样解,与后面紧接着的“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就难免断裂。其实,所谓“诚者”、“诚之者”,指的是两种不同的实现诚的能力和方法。“诚者天之道”指圣人的能力和方法,唯圣人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犹如自然天成,故谓之“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指常人的能力和方法,常人需要经过后天的努力和学习,“择善而固执之”(《中庸》20章)才能实现诚,故谓之“人之道”。(27) 总之,《中庸》里的“天”,很少脱离自然之天的本色,从未隐藏它“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的本来面目,其偶尔所散发出的宗教或道德气息,也是立足于其自然功能,通过隐喻或象征所引起的暗示或联想而来。它根本就没有被升格为任何意义上的位格神,没有被升格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体,根本就不具备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超越性,因而根本就无法担负起道德形上根源的角色,无法合理地成为道德价值确立的根据,根本就不具备成为道德的超越本体之资格。 如果“天命之谓性”可以算作一个命题的话,那么它只不过是从万物生成的角度描述了自然人性形成的事实。 四、《中庸》并无哲学本体论的自觉更无本体论与价值论融合的自觉 即使“天命之谓性”这句话可能不自觉地隐含着某种本体论的观点,但至少《中庸》并未对其中可能隐含的本体论观点做自觉的理论探索和具体论证,可见《中庸》并无哲学本体论的自觉。因为只有能以概念和逻辑思辨的方式,自觉探索本体与现象或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自觉探索万物的内在构成要素或生成原理,并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方可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尽管先秦儒家有关于万物发生或生成的不成理论体系的零星的看法,但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亦即第一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ontology),在中国上古思想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成形。(28)《中庸》并未把“天”视为“性”之内在构成要素或生成原理,亦未把二者视为本体与现象或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因此对二者关系的描述根本就与哲学的本体论无关。 自从休谟认为“是”推不出“应当”、事实推不出价值以后,西方哲学家就很严肃地反省他们自古希腊以来在这方面所隐含的问题。而我们一些从事传统思想研究的人,不但没有因此激起对我们传统思想的理性反省,反而激发出自以为是的激情,认为我们古人从来就没有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对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做分辨,而是本然与当然、本体论与价值论融为一体,因而我们的思想中不存在休谟难题。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不能分辨事实与价值问题之差别而混沌地一锅煮,与能分辨同时又能合理地从事实判断推出价值判断,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他们也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休谟所批判的正是前面一种做法,而同时又否认后一种做法的可行性。 之所以那么多学者都自觉地以形上学、本体论、存在论等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解读《中庸》首章从而不自觉地陷入误区,不是因为他们缺乏西方哲学的基本知识,而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都主观地认定《中庸》是孔门最具哲学味和形上色彩的经典,都想把它按照西方哲学的样子来诠释,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没有真正像西方哲学所要求的那样,对文本做细致严谨的哲学分析,对文本本身存在的矛盾给出合理的解答。同样,因为他们缺乏对文本的细致的哲学分析,再加上儒家思想本身重视道德的传统,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认为“天命之谓性”是个价值论命题。 注释: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6页。 ②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4-61页。 ③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卷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8页。虽然劳思光这里用的是“混合”而非融合一词,但说明他还是认为“天命之谓性”这句话既包含了价值论(心性论),也包含了本体论。 ④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04页。 ⑤杜维明:《〈中庸〉洞见》,段德智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3、95、97、99页。当然,杜维明所谓的德着重指诚。 ⑥冯达文、郭齐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上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页。所引内容乃李宗桂撰写。 ⑦杨国荣:《中庸》释义,见《诸子学刊》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3页。 ⑧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7页。 ⑨朱熹为了对应前文“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中庸章句》),而不得不以“健顺五常之德”为性,似乎除了以五常之德为性之外,还以健顺为性。但这与我们说朱熹仅以五常之德为性并不矛盾。其一,朱熹认为,就不夹杂阴阳之气的天命之性本身而言,亦即就作为理的本然之性而言,性乃纯善无恶,因此可谓性仅指五常之德。其二,“健顺”这两种性在朱熹处本与道德义相通。“健顺”乃就阴阳而言,而朱熹认为仁礼属阳,义智属阴,信就是实有仁义礼智,故以阳健阴顺为性,与以五常之德为性,实质上可相通,只是表达的角度不同而已。参见《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二(第4册)及卷第十七(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490、374页。 ⑩参见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87页。 (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7页。 (12)其实,钱穆早就指出,《中庸》受了道家老庄思想之影响,乃汇通儒道之作。参见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13)参见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87页。 (1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7页。 (15)(17)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7、18页。 (16)郑玄注云:“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也。”(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87页。)由此注可知,郑玄把“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中的“不睹”、“不闻”,分别解作“不见睹”、“不见闻”,这不仅仅符合词法——因为上古文献中,本身并不表被动意的动词被活用来表达被动之意的现象较常见,而且在前后文义的贯通上,这种解释也比以朱熹之注为圭臬的宋儒更妥帖。 (18)当然,这种看法并非朱熹的发明,至少在孔颖达等人的《礼记正义》中,就已有此观点。“被色而生,既有五常仁、义、礼、智、信,因五常而有六情。”见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88页。 (19)如果“率性”之“率”不训“循”而训“统率”,则“率性”几近“发而皆中节”之义,而且由“率性之谓道”人们可以兴奋地联想起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中所谓的“长性者道也”之说。 (20)参见《二程遗书》卷22上及《朱子语类》卷4。 (21)参见《朱子语类》卷12、13。 (22)(23)参见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第10、1-10、25、187页。 (24)参见陈柱:《中庸注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25)“天地之大,人犹有所憾。……及其至也,察乎天地。”(12章)“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叁矣。”(22章)“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26章)、“建诸天地而不悖”(29章)、“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30章)、“天之所覆,地之所载”(31章)、“知天地之化育”(32章)。 (26)其实,当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他所谓的“天”也一样,虽然可以把它与宗教性和道德性关联起来,但同时丝毫也无碍于把它理解为生养万物的苍苍之天。 (27)有学者早已对此做过精当的辨析,参见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5页。 (28)这里所谓的本体论乃与宇宙生成论相对而言,而非与认识论相对而言。如果西方哲学所谓的认识论转向之前的本体论包括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在内的话,那我们先秦也有类似于自然哲学的一些讨论,但也主要是集中在《老子》、《庄子》书中,而非儒家文献中。标签:朱熹论文; 本体论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中庸论文; 君子慎独论文; 四书章句集注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国学论文; 人性论文; 礼记正义论文; 郑玄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