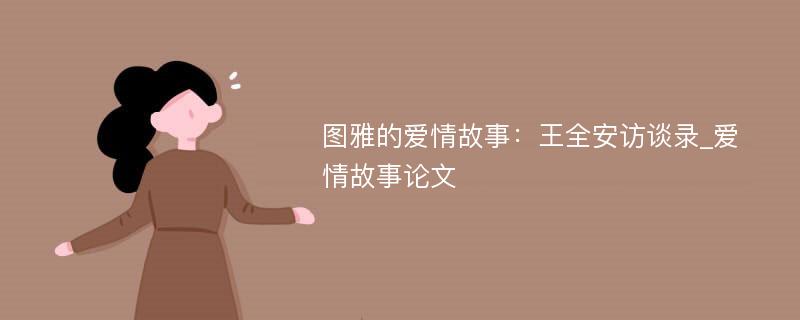
图雅的爱情故事——王全安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情故事论文,王全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吴:这个片子得奖很有意思,之前谢飞老师得金熊的《香魂女》是女性题材,再之前张艺谋得金熊的《红高粱》是民俗电影。你这部片子好像有点集两片之特点,既是女人的故事,又有民俗的东西在里面,不知道国外的评论怎么样?
王:我当时没有想到会得大奖,以为会有一个单项奖。得了大奖以后,电影节主席的助理讲了几句话,挺逗的,他说,这个奖给你,给这种电影,也许可以让其他中国电影感觉到,以后好好拍电影就行了,不要想太多电影之外的事情。《图雅的婚事》(以下简称《图雅》)其实不是一部处心积虑的作品,它是一部转折性,或说转移性的作品。《白鹿原》在那儿卡了两年,很郁闷。但这时候我对电影的认识有了一个变化,我要拍一个东西,把我对有效的戏剧性叙事的理解和技巧融到一部电影中去,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效果,有为《白鹿原》未来的电影气质做点试探的愿望。电影节的选片人看完也很意外,和过去中国艺术电影的感觉不太一样。他们过去看中国的艺术电影,首先要沉下来,然后在里面琢磨出点儿文化的东西,而且是相对远的,不太好明白的,也是比较抑郁的。现在的中国艺术电影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气质,我们也都知道它是怎么来的。看了《图雅》之后,他们首先在观感上受到了一定的刺激,没意识到看一部中国艺术电影会很畅快,会被剧情牵着走,各个元素都很饱满,而且里面还有点幽默感,这是他们的感觉,其实就是气质变了。原来我们艺术片里的人之所以会成那个样子,是因为导演对里面的人物是怀疑的,导演觉得他的人物应该过另外一种生活,成为另外一种人。而我对《图雅》里面人物的看法变了,她是有毛病,是活的很郁闷,但人生就这样,你没什么可惭愧的。这样一来,影片的趣味就不一样了,人物形象就有意思了。国外报纸评价这是一部可以在欧洲院线,甚至在北美院线放映的电影。原来我们的电影可能把文化意义放在电影之上来看,现在我们不能再这样做了,因为你的文化毕竟要通过电影来表述,你要尊重电影本身的规律,至少你要平衡这两件事情。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可能目前的创作环境不够理想,不够完善。但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哪儿的环境是理想和完善的?哪儿都不完善!因为电影注定是个性和体制有冲突的,谁都要平衡这件事情。所以,哪儿的电影导演都会遇到问题。而目前中国的环境已经足以让你用一个正常的心态去对待电影。
吴:在你前一部影片《惊蛰》中,有大量你所谓的东方化的东西,比如完整的婚丧嫁娶的场面,而且非常细节化,它们不是叙事过程而是仪式。《图雅》这个发生在内蒙草原嫁夫养夫的故事,很容易又让人想到这种被无限放大的仪式化的细节。事实上,在影片的结尾还是出现了内蒙古族的婚礼场面。但类似的东方奇观在《图雅》中占的篇幅好像少了。
王:有一个外国记者采访我说,我以前喜欢中国电影因为它是东方的,人是东方的,景也是东方的,我不能理解,但很神秘,所以我喜欢。而看你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忘了自己是在看一部中国电影,我为里面人物的命运和感情而激动,你觉得失去这个东方色彩,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听了这个问题之后,我特别感慨!我说,听了你的话我很欣慰,我们终于可以在谈中国电影的时候,不用再谈那些乏味的事情,我们终于可以丢掉东方电影的帽子,电影可以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进行交流。比如说为什么要生活?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生啊死啊,这些东西。我就是想回到最简单的问题,一部电影本身应该产生的力量。剧作的结构,电影元素的饱满,有色彩地刻画人物……只有这些东西饱满了,你才能突破前面说的那些局限。在拍《图雅》之前,我对自己的电影到底是个什么样,或者说我们为什么喜欢那样拍所谓的艺术电影有疑虑。别忙活半天,发现这是有先天缺陷的东西,白白浪费自己的精力。到了《图雅》,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把所有的东西放在电影里面来解决,而不是在电影之外去贴这个,贴那个。
吴:内蒙古这个环境会不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他们不会很快地直接进入人物,而可能愿意在环境中找他们理解的东西。有没有想过把这个故事放到大多数观众都熟悉的环境中?
王:其实我不介意观众进入故事速度的快慢。这个过程看似是慢的,但很稳健。其实我拍第一部电影《月蚀》的时候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月蚀》在当时的电影环境中,有点太超前了。当时大家都还在纪实的时候,你去做一个虚的东西,里面却裹胁了一个很现实很残酷的部分。那是一种很讲究的讲述方式,但那是8年前,如果现在再出来这样的电影可能相对就好一些。这里面还存在一个衔接的问题,我是希望一开始大家能在这个电影中找到大家以前习惯的东西。首先你要有一个坐标,然后再变化。比如说,我会花一些时间在一开始呈现出中国艺术片典型的气质和场景,然后在这个里面做变化。
吴:你的意思是说,《图雅》的纪实和民俗的部分是在照顾到今天大家对一部艺术电影的习惯认知?
王:我是指这部影片的实际效果,这样的影片在今天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果。你要客观地照顾到中国电影创作的实际环境。有些时候妥协并不意味着丧失。当然,选择这样的环境当时也有一个考虑,就是这个环境让我对人性激赏和认同的东西带来一种解放。如果放到城市里面,给观众这样的故事,观众很快就会进入道德分析中去。为什么我没有放到青草蓝天那样的草原上?这是一个道理,那样的环境不给你提供一种极致的困境,你故事的可信度就弱了。道德分析很讨厌,我根本就不想让观众在“嫁夫养夫”这样的故事里面,再去分析什么道德不道德。图雅这么做是一种无意识的,不是什么理智的选择。故事的关键是人在这样的故事里面都经历了什么。就是人的生命力嘛,生活都变成这样了,她依然能够生存。图雅也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什么不正常,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尽管围巾裹住了余男多一半的脸,但掩饰不住这个人物的美感,这是很迷人的一种气质。如果不放到这样的环境,我觉得我做不到。如果选择汉族的环境,我觉得我没有力量突破一些东西,会背离我对人性的认同,会显得图雅这个人太特立独行了,而削弱了对于生命力的感觉。
吴:问题不在于是不是选择老少边穷的环境,而在于这样的环境对故事是否是有意味的。简单的环境,简单的人物关系让图雅所面临的困境很纯粹。
王:而且,表现与我们大多数人有一定距离的故事,包括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我们能够相对冷静地把握住它,理解它。城市离我们太近了,变化也太快了,我们有时候很难了解到底我们是怎么回事儿。
吴:外国观众对内蒙古环境没有提什么问题吗?
王:他们觉得这样的故事放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理解。关键是影片的讲述魅力。不管你讲什么故事,你又怎么可能再现生活呢?你拍的只是一部电影,所以要看电影有没有吸引人的魅力。
吴:我接触的一些年轻观众觉得,《图雅》是一部中规中矩的电影,很工整,看不到导演的追求。
王:他们可能希望在这样的电影中看出寓意来,看到标签。之前的很多艺术片都在靠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走捷径。为什么说我愿意回到电影本身,就像是严密的古典音乐,为什么会百听不厌,就因为它严密,不会有简单发挥的东西,这么做会破坏整体性。我所要做的是经过多少年证明,是最易于被观赏的方式。既有生活的质感,又有戏剧性的东西在里面支撑着,这才能形成强烈观感的东西。电影很难拍好,难就难在这个上面了。《图雅》这个电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就是森格帮图雅运草,半路翻车那场戏开始,那是个门槛儿,从这儿开始,《图雅》就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纪实的艺术电影了。这个场景很写意,里面有一种很隽秀的东西。
吴:你怎么理解戏剧性?
王:情节剧是有一定程式的。这种程式要求具备高度的感性和高度的理性。艺术片是跟着导演的感觉走,高度感性。你对着白墙拍十分钟,只要你觉得有含义,没有任何问题都是对的。一旦要有高度理性的戏剧性叙事的时候,那么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情节的进入它都要承担叙事功能。而作为艺术气质的电影又要有文化表述,那么,这样的表述能否融到情节叙事里面去,就是判定电影成功与否的标准。你脱离这个,节奏就不对了。比如刚才你说的《惊蛰》里面的问题,可能你迷恋那种文化形式感的东西,但它已经脱离叙事了,不是很高明。把寓意单独拿出来表达,本身还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我现在意识到一点,真正让电影有力量的其实就是快感,不一定都是快乐,痛苦也一样,它是很明确的。这种快感是观众不能拒绝的,而且是能传递的东西。电影如果不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证明你在导演方面没有职业能力。
吴:从电影元素的角度来说,这种快感传递的手段是什么?
王:我觉得最好的手法还是戏剧叙事。因为戏剧化是凝练的,它不是生活化的幌子能搪塞过去的。我们看一部电影的动力是什么?除了生活和文化之外,大部分人还是想看故事。
吴:你说的这种电影有没有范例?
王:《教父》,当然这是简单地说。或者是《阿拉伯的劳伦斯》。
吴:中国电影呢?
王:这不是一个概念或者是一个愿望所能完成的。能够把欧洲电影刻画人的深度和美国电影讲故事的技巧完美结合,是件很难做到的事情,不光中国,世界上这样的电影也很少。我是希望我未来的电影能够达成这样一种风格。包括电影里的文化命题,包括和观众的关系,如果能结合在这样一种度里面,那才是真正复杂的好电影。《图雅》的格局虽小,但已经做了一点试探,已经顶破了一些局限。至少我们逾越了中国电影局和国际电影节这样的两极状态。他们为什么会有同一种观感,就是我们相信电影本身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够突破隔膜而不是制造隔膜。有时候,我觉得有人是在故意制造隔膜,然后在一种对抗中显示一些价值,但这不是电影最好的价值。
吴:谈戏剧性的时候,往往会谈冲突,冲突的本质是价值观的冲突,所以传统戏剧性的电影里都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图雅》的冲突是什么呢?
王:我的戏剧性是指有足够相反能量的东西。它不一定是我们原来的那种外化的好人坏人,它是更复杂更微妙的东西。比如说《图雅》,它里面可能没有外化的对立面,但人欲本身确是件太复杂的事情。“嫁夫养夫”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是以女人做牺牲来成为道德楷模,一个高尚的牺牲者。但当爱情产生的时候,这个女人可能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假公济私者,“嫁夫养夫”可能就成了背叛。这种力量本身也是戏剧冲突。而且戏剧性的东西他要求你把你要的东西清楚地再现出来,不能模糊。
吴:《图雅》的戏剧性来自于人欲的矛盾性。
王:对,包括这两个男人,他俩要是和图雅一点儿爱情没有,那就没冲突。可一旦爱情来了,马上两人的关系就变了。
吴:爱情有爱情的规则,婚姻有婚姻的规则,你现在把他们拧到一块去了。如果遵守婚姻的规则就是我们熟悉的“主旋律”,如果遵守爱情规则,可能就是—欧洲电影。
王:是,现在我让他们和谐地在一起。
吴:这两个男人的作用就很重要,不光是丈夫和情人那么简单。
王:是,这种关系毕竟我们都没有经历过,你没有办法给出一种答案。等剪完了,我回头看,才意识到,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爱情故事。图雅非常非常喜欢丈夫巴特尔。这个家伙是那种内心比较有力量的男人,让女人觉得安全。而且这个演员的选择也比较准确地体现了我对这个人物质感的定位。片子中的这三种男人没有好坏之分,是给观众带来不同愉悦的三个人物。像森格这种人,看上去很飘逸,很活分,但他内心的坚定与沉稳显然不如巴特尔。而宝力尔这样的男人,很软弱,十几年前他怎么失去图雅的,今天还怎么失去。和那两个男人比起来,他相对有点自私。宝力尔的所为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富人为富不仁,他不是这个概念,他是个性的问题。比如说一个人的软弱,那在关键时候就是致命的。我对每个人物的态度是明朗的。最后我感觉到,人生这个东西是很诡异的,图雅做了好多事情,她甚至都以为自己爱上森格了,其实不过是绕着弯子还想和她丈夫在一起生活。这让我很感慨。像遇到这些问题,我和编剧芦苇就谈不到一块儿,因为我们对人的理解不一样。比如森格和图雅老是在一起呛来呛去,我说这就是爱情。生活比你想象得要高明得多。当我们真的遭遇困境的时候,嫁夫养夫可不是一个选择呀,它是惟一的办法。拍电影的人,你只能去理解这些东西,而不是去指教什么。
吴:艺术家所要表现的就是现实规矩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在现实中有合理解决方案的事情对艺术来说没有意义。
王:没错,艺术要表现困境,通过这种极致的表现,可以让你有一个考验人性的机会。
吴:除了余男,其他演员好像全部都是业余的吧?
王:对,都是。巴特尔是典型的牧民,连旗里都没去过。制片人去采风,拍了一批照片回来,其中有一张他的,我一看,他就是主演了。其实,这个选择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在他那张典型蒙古男人的脸上有我认为巴特尔最重要的气质,眼神很忧郁,很无奈。你就知道这个无奈的背后有原因。他来的时候,我一看,他腿有点瘸,他在家里的处境和他的经历与巴特尔没有什么区别。据说当年也曾经有十几个女朋友,是个骑手,腿摔断了两次还要骑,最后终于摔得不能骑了。知道这些后,我一下就明白他忧郁和无奈的原因。这正是我要的巴特儿。这个人物放在那个环境中,他可信呀!角色和演员一下就重叠了。演员的气质为整部戏的戏剧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品质,剩下的就是表演上的一些连贯的东西,那是导演的事。我是到了《惊蛰》的时候,才体味到什么叫艺术形象,就是人物的某个瞬间让你难忘。之前对这个没有什么意识。到《图雅》这部片子,艺术形象的意识在我脑子里进一步明确了。而且我们有能力在银幕上创造和现实中牧民形象一样有魅力的艺术形象。现在看来,我们的想法多少有所体现,图雅这个人物不是平扁的。大家看完,还是要把图雅当作一个艺术形象来接受。
吴:森格这个演员从名字上看像是汉族人,选择他也有你特别的考虑吗?
王:他其实也是一个骑手。我当时考虑,森格这个人物除了要是牧民,还要有一张吸引人的脸,那张面孔能够让异性有好感,当然不是很成熟的好感,而是一种表面的浅的异性好感。我是在赛马场看见他的,当时,他和他老婆在一起,他老婆是一个特胖特剽悍的女人,特厉害。他老婆刚一离开,他马上就和旁边年轻的女广播员又搂又掐,亲热得简直不行。他做这一切很自然。一会儿,他老婆回来了,他一点都不尴尬,依然谈笑风生。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天生的处理男女关系的禀赋,善于处理那种复杂的关系。我觉得他肯定能演森格,没事就来找图雅磨叽。
吴:你是演员出身,后来做了导演,你觉得电影表演是一种什么状态的表演?
王:电影和电影也不一样。电影中,人物的价值是最高价值,这里面包括表演。一切的努力都是为这个来服务的。但造成表演和导演之间的问题,根本原因是编剧。剧本提供给演员的东西和生活不一致,是造成表演不顺畅的真正原因。表演的难题在于,我要把一个我认为不正常的事情演得很正常。这是造成虚假表演的根本。甚至可以说,这是惟一的问题。当你要求他完成和生活逻辑不一致的事情的时候,这个虚假就已经注定了。所以,一般遇到表演障碍的时候,我都会停下来,看看剧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问题。
吴:在你的作品中,你是怎么处理导演技巧和表演技巧的关系?
王:我觉得首先是导演的审美决定的。反过来,也要看演员身上是否具备某种东西。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演员的品质。真正感人的艺术形象必须是和演员的人格相一致的。人格魅力是演不出来的。余男本身秉性里就有这种东西,而且她没有太多受现在演艺界气氛的影响。没有磨去她身上一些单纯的东西。当表演技巧上升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种魅力就会产生一种力量。
吴:你和余男有没有分歧的地方。
王:基本上,越往后分歧越少,只是看我们能跳多高。
吴:我的意思是说,《惊蛰》和《图雅》在人物形象上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一个好演员往往不愿意重复同样的角色,她自己有没有想跳出来的东西?
王:其实这种角色,在余男每一次完成的表演里面,显而易见都有她自己的秉性在里面。这里面有我对她的了解,我知道什么东西是和她不拧巴的。余男本身就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她其实一直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即使在演艺圈,她也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工作环境和工作关系。
吴:拍摄的时候,你排戏的时间长不长?
王:我拍戏从来不长时间地排戏,长时间排戏很可怕。作为导演要尽量保护演员最新鲜的感觉。而且这与编剧有关系,你编的东西是不是和人物以及生活的逻辑契合。如果不契合,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导演、演员可能就不踏实。如果你编的台词和节奏是可以理解的,那一下子情绪就出来了。越是重场戏,我越不排练。你比如医院的那场戏,在场的工作人员都镇住了。其实那一瞬间既表现了图雅的强悍也表现了她的软弱。
吴:每场戏都不排练吗?
王:尽量少排练,就是走走机位。我觉得越是业余的演员,你的机位变化就要越少,给他造成一个宽松的活动范围。而且除非很强的戏剧叙事,一般我喜欢用更简练的,镜头内部的变化来完成。光彩的瞬间只有一个,没有很多的瞬间,最好的表演肯定只有一条。所以我一般就拍3条,如果到第3条还有问题的话,我就会换一种方法。不能让演员有那种受挫感。演员要尽可能晚地进入现场,最不能消耗的就是演员在现场的精神。你要让演员迈出表演那决定性的一下的时候,要越轻松越好。我也最怕讲戏,即使是最剧烈的戏也是生活场景,有什么理解不了的呢?所以导演应该学会化繁为简,给演员的指令越直观越好。至于什么内心活动,那是戏剧舞台赋予的,生活本身并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有些业余演员有时候也会呈现一种有节奏感的表演。
吴:可不可以说,你的戏剧性就是在艺术片里加一点戏剧冲突?
王:当然,我是要用情节剧的方式去叙事,而不是拍情节剧。我肯定还是要拍我感兴趣的问题,依然要有我自己的表达,但是要把它负载在一种什么工具上。这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你自己,一个是电影。过去我们把自己举得太高了,而电影做得太少了。《图雅》只是为电影多考虑了一点。我把《图雅》拍完,才意识到情节剧的厉害,做好真正的情节剧太难了,我现在只能说摸到一点儿门儿。情节剧所有设定的东西,你必须按照设定的目标完成,不能有任何变化,你必须要达到那个质感,才能完成叙事,要不然讲不下去,讲不清楚。表演不到位不行,拍摄不到位不行,而且还要保持一种灵动感,这真不简单。
吴:从影片的影像风格看,其实《图雅》不具有戏剧性。很客观冷静,摄影机没有更多的表情,也没有介入到人物的戏剧动作中去。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还会削弱戏剧性的感染力。
王:严格来说,《图雅》依然是艺术片气质的电影,这是本质的东西。戏剧性地讲述只是用来支撑这样一种气质,它是一种故事的内在结构,而不是表面的动作。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戏剧性、道德思想都不能过那个度。它是以真切、自然、有生命气息的气质作为这种电影的底线。而且戏剧性也不简单是我们知道的那几种方法,它有很多种方法。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影像风格之类的事情。但每部影片出来,影像风格基本上还很统一,自然的,纪实的。
吴:德国籍的摄影师在影像方面没有给你什么建议?
王:我觉得国外摄影师有一个特点,他们对电影概念的理解比较完整。他们会先理解导演想要传递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给你提供很多种方案。他不会只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卢茨从这个角度讲是真正过硬的。而且,德国人拍东西有一个特点,他的东西出来比较冷静,不花哨,而且能在即兴的创作中保持一种完整性,在即兴调整的时候,随时能够把构图调整好,而且很从容,这绝对是功夫。
吴:做完这部片子有没有你很遗憾的地方?
王: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可能还是叙事不够老辣,不够细腻,还是再靠一股气推着。比如影像可以再冷静一点儿,但这就意味着你的结构要更精巧。现在的片子里,图雅和她丈夫的线,展开的不充分。因为已经没有空间了。在剧本里我还写了一些她和巴特尔因为家庭琐事争吵的戏,比如因为孩子上学的事,也拍了,拍得也很好,但总觉得和整部片子的气质有点儿游离,显得拖沓,就给删了。但图雅和丈夫之间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东西,真正维系了他们之间那种深刻的关系,没有讲清楚。现在拍摄用的剧本,是我在开拍前7天改出来的,很匆忙,所以片子的层次不够丰富。还有一点就是,没有空间展开图雅独处时的内心状态。
吴:就像片子开头和结尾,图雅一个人在蒙古包中哭的状态。
王:对。如果再从容一点儿,应该表现她的更复杂的状态。她到底怎么看森格,怎么看巴特尔,这些有点不够。当然这种东西是无止境的。有时候,拍现实题材的电影,那种拍摄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和焦灼状态,倒让你离你自己的人物近了。我很愿意置身到这样的状态中去。
吴:有的评论认为,现在年轻导演的作品有泛主旋律化的倾向,没有揭示真实复杂的社会矛盾中人的挣扎状态,你怎么看?
王:我觉得考虑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是有问题的。当我觉得社会比我高明的时候,我还批判什么?当你对自然的敬畏油然而生的时候,其实你的那些批判只是站着说话腰不疼。打个比方,如果你不到真正的战场上去,你真的不知道生死是怎么回事儿。当图雅嫁夫养夫是她惟一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还怎么批判呢?没有什么客观的东西,电影最擅长的也不是这个,它的特性不在这上面。如果说电影能够唤起某种真实的东西,那只在某种特定的状态下,感情上的真实,真实应该是指这个。比如我听到一些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的评语,这部电影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生活。我觉得这话只说了一半,一些电影最重要的东西哪儿去了?而且,在今天,把电影当作娱乐产业,我觉得电影一下子找对了位置。你的电影是否能够给人提供一种高品质的快感?即使是艺术片,它也应该是更高级的娱乐,你必须有这些东西,而不是打着什么主义的招牌就能解决电影的问题。什么体制内地下,我不太去想这些事情,这些解决不了电影的品质问题。即使是拍“主旋律”,你依然可以看出一个导演有没有电影才华。电影的价值应该通过观赏快感之类的东西来实现,那才是电影艺术。而且现在已经到了该为电影本身做点什么的时候了,不能再浪费时间。
吴:接下来的片子还是余男做主角的女性题材吗?
王:我已经把一生做电影的时间大概做了一个盘算。因为我知道最终我要拍的电影是什么样的,知道它的复杂程度,知道这中间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去充实。《月蚀》也好,《惊蛰》也好,都是在我自己的储备和试探里面。我的电影肯定是越拍越复杂,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人,那种内在的力量会更巨大。我其实一直在找我的电影的品质概念。到了《图雅》之后,我才基本没了那种困扰和犹豫,基本弄明白了我要做的电影是什么。
王全安作品
《图雅的婚事》(2006)
第57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
《惊蛰》 (2003)
《月蚀》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