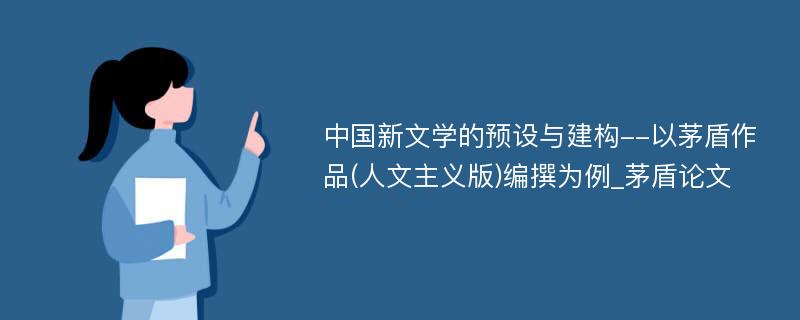
新中国文学的预设与建构——以《茅盾文集》(人文版)的编纂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新中国论文,茅盾论文,人文论文,文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在1950年代,该出版社共出版发行一部全集、六部文集(全集为《鲁迅全集》,文集分别为《瞿秋白文集》、《沫若文集》、《茅盾文集》、《巴金文集》、《叶圣陶文集》、《郑振铎文集》),其中部分文集在1960年代出齐,而《叶圣陶文集》和《郑振铎文集》则一度中断。这些是新中国文学建设中的重大工程,同时也为该时期文学的模式与标准做出了诸多潜在的规定。这无疑为我们研究新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角度。
查阅茅盾1958年《致作协办公室》的书信,我们可以得知出版《茅盾文集》并非茅盾之意。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楼适夷同志再三来说”,而人民文学出版社最初之意,是重印茅盾全部旧作,“重印是使读者看到一个作家的发展”,茅盾则持不同意见。因为茅盾此前已出版过《蚀》和《子夜》的修改本(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茅盾认为当时的修改基本上是对的,并没有改变原作的思想内容,故坚持以修改本为底本进行编纂。值得注意的是,1954年的修改也并非茅盾之意,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建议,茅盾当时处于两难之境:“我觉得不改呢,读者将说我还在把‘谬种流传’,改呢,那就失去了本来面目……当时我主张干脆不再重印,但出版社又不以为然。”①最后,茅盾决定采用执中的方法,即在不改变原作思想内容的前提下,对其中的字句作或多或少的修改,以《蚀》三部曲为例:“《幻灭》和《动摇》改的少,仅当全书的百分之一或不及百分之一,《追求》则较多,但亦不过全书的百分之三。”②由此可见,《茅盾文集》的出版,并非出版社或作家的单方面行为,而是双方协调互动的结果,是建国后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学生产上的具体操作表现。
根据1957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出版说明,《茅盾文集》“收辑了作者三十多年以来创作生活中的大部分文学著述。按照小说、戏剧、散文、文学论文等体裁和著作年代编次。作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以及多年在从事杂志的编辑工作中所写的部分带有时间性的文章,都不收入在内”。出版说明还指出,所有收辑的作品均由作者亲自校阅、修订。茅盾在1958年《致作协办公室》的信中也说:“现在整理,并不是要将旧稿修改,而是校改排印上的错误,及编排次序(此指短篇小说及散文而言)。”综观所上,我们可以得知,这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文集》在编纂上有三个特点。第一,部分文集的底本为建国后的修改本(这里的部分文集,特指《茅盾文集》的第一、三卷。即《蚀》和《子夜》);第二,部分文集的底本仍为建国前的旧版本(这里的部分文集特指《茅盾文集》的第二、四、五、六、七、八、九、十卷);第三,部分文学著述并未被收入《茅盾文集》(从编辑部出版说明中的“收辑大部分文学著述”即可得知)。需要指出的是,《茅盾文集》中以建国前版本为底本收辑的作品,往往卷后都有后记、部分篇后则有附记以作说明。从茅盾作品的版本源流上看,人民文学出版社十卷本《茅盾文集》在建国前版本基础上,分别作了改收、漏收、注收(后记、附记收)的处理。这显然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学对旧作所提新要求所致,或者说,茅盾旧作中部分作品已不符合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要求,必须要对其作修改、修饰、省略的处理,使其符合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范。而从这些被修改、修饰、省略中,我们不难看出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生产的预设与建构。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简称“第一次文代会”),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队伍胜利会师,大会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由此进入当代文学的阶段。第一次文代会确定了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讲话》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所接受。《讲话》的中心阐释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及如何服务的问题。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中,《讲话》强调作家要深入工农兵中,要熟悉工农兵的生活,“先当工农兵的学生,再当工农兵的”,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使之符合革命大众的要求。在如何为工农兵服务中,《讲话》强调要格外重视文艺的普及,要多创造工农兵熟悉的、喜闻乐见的作品,在普及的基础上再进行提高。作家对工农兵要慎用讽刺暴露的方法,对一切反人民反革命的势力则要坚决揭露批判。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及如何服务的中心出发,《讲话》顺理成章地得出文艺的评价标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为工农兵服务,有益于抗战与革命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否则就是有害的作品,如果作品政治上错误,则艺术成就越高危害也越大。当然,不能机械庸俗地理解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不能人为割裂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因为只有艺术上越成功的作品,它的政治效果才能越深入人心,相应地它的艺术生命也更为持久,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对照毛泽东的《讲话》,茅盾在1952年开明版的《茅盾选集》自序中,沉重地检讨了他的作品《子夜》未能深入工人群众的生活,未能表现出那时候整个的革命形势。《幻灭》等三部小说,则问题更多:“表现在《幻灭》和《动摇》里面的对于当时革命形势的观察和分析是有错误的,对于革命前途的估计是悲观的;表现在《追求》里面的大革命失败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也是既不全面而且又错误地过分强调了悲观、怀疑、颓废的倾向,且不给以有力的批判。”对于短篇小说,茅盾坦白地承认:“选在这本集子里八九篇小说都是‘瑕瑜互见’乃至‘瑜不掩瑕’的东西。而且这八九篇的题材又都是小市民的灰色生活,即使有点暴露或批判的意义,但在今天这样的新时代,这些实在只能算是历史的灰尘,离开今天青年的要求,不啻十万八千里罢?”众所周知,《幻灭》三部曲是茅盾的成名作,茅盾借此走上职业作家的道路。而《子夜》更是茅盾的代表作,当时曾风行上海,人们争相传阅,据当时《晨报》的消息,某书店一日内售出《子夜》一百余册,当时鲁迅与瞿秋白也给予《子夜》较高评价。茅盾的短篇小说中不乏精品,建国前曾多次再版。为什么建国后茅盾对这些作品作出如此低的评价呢?显然,茅盾按照《讲话》的要求来评判自己的作品:《子夜》未能突出工农兵方向,不熟悉工人运动和农民斗争;《蚀》着重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趣味,与工农兵的审美隔膜太大;短篇小说大多刻画小市民的灰色生活,同样与工农兵方向相冲突。而且以上这些作品在政治标准上,因为未能昭显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兵必然胜利的合理诉求,而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事实上茅盾多次申明要从头向群众学习,彻底改造自己。查阅茅盾1958年致《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书信,可以得知他当时正在创作一部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材的小说,可惜因事务太忙、身体违和而中断。
伟大的小说家都有一个世界——经验世界,经验世界改变,小说也要修改。这或许可以解释茅盾1954年修改《蚀》和《子夜》的主观原因,正如艾略特所说:“现在也会修改过去。”③茅盾正是用“现在”的《讲话》去修改“过去”作品的“错误”,于是《蚀》和《子夜》出现了迎合性的修改。据学者统计,1954年《蚀》人文版在初版本基础上修改多达900余处。“其中《幻灭》120余处,《动摇》350余处,《追求》450余处(处次的计算最小以逗号隔开的半句为单位,半句中无论修改几处均按1处计算。两半句前后语句调换的只算1处。其他增、删的句段连续成片的算1处)”。④而1954年《子夜》人文版在初版本基础上改动600余处,“修改最多的是第十五章(160处),最少的是第十九章(3处)。这些修改包括对初版本误植的订正、标点符号的增加和改换、字词的改换、句子和段落的删改”。⑤综观所上修改,一共有五种类型:(一)涉及性内容的删改,(二)涉及工农革命国共斗争等政治话语的修改,(三)涉及汉语规范化的词语置换修改,(四)涉及少数晦涩语段的删改,(五)涉及个别语句精益求精的润色修改。前两种可看成文本中的内容修改,后三种可看成形式修改,其中修改量最大的是性内容的删改。在茅盾的早期小说《蚀》、《虹》、《子夜》中,诸如乳房、屁股、身体曲线和肉感等性语句屡见不鲜。国内有学者认为,茅盾是高举文学的社会性大旗而建立起写“性”说“欲”的合法性。⑥胡风在当时曾直言不讳地批评茅盾的早期小说:“那形象是冷淡的,或者加点刺激的色情,也没有普通人民的真情实感的生活。”⑦此类说法虽不免偏激,但也是有事实依据的。茅盾早期小说受自然主义的影响,认为性是人生内容和社会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丝毫不能以之为秽亵。但事实上,茅盾早期小说中的性话语并非单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除了男欢女爱的自然本能欲望之外,这些性话语还有革命激情、女性(权)解放与自由、女性身体的商品化等诸多隐喻之意,茅盾为了获得这些隐喻之意,难免不夸大女性的性征体态,这往往成为人们诟病的理由。对于一般的工农大众读者来说,他们对这些过量过分的性内容所阐释的隐喻之意难以理解,同时,这些性话语也容易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其实在建国之初,涉及性内容描写的作品(非“五四”以后的一般新文艺作品及一般谈情说爱的“言情小说”)往往被看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文学旧艺术的残余势力,被看成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腐朽思想和下流无耻生活方式的代表。周恩来在1955年7月22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的指示》:“一部分人民群众,尤其是有些青年、少年、儿童,因为受到这类图书的毒害,思想堕落,身体败坏,生活腐化,学业旷废,工作消极,甚至做出殴斗,盗窃,奸淫,凶杀等犯罪行为……凡内容极端反动的书刊和描写性行为的淫书淫画,一概予以查禁。”茅盾作品显然与淫秽无关,但早期小说存在大量性话语却是事实。同时,这些性话语往往产生在特定的都市语境中,作品人物也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经验情趣,与普通工农大众的审美隔膜较大。故茅盾作了大量删除或简化的修改,既不改变作品的情节结构,也适应了工农大众的欣赏水准。《茅盾文集》采用修改本作底本,实质上是肯定了这种修改的正确性。
对涉及工农革命、国共斗争等政治话语的修改,实质是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诉求所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旧的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已被摧毁或受到很大限制,新的人民大众的经济基础已经或正在建设中,新的经济基础必然产生新的上层建筑,新的上层建筑的改变必然导致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的改变,反映到具体文学作品上,其旧的意识形态必然被新的意识形态所取代。《蚀》的创作时期,正处于大革命失败阶段,新的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立,中国共产党及工农武装的前途到底在何方,当时并不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反映在《蚀》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观、怀疑、颓废恰好是客观事实,茅盾非常准确地把握了他们的思想动态,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辩证性与复杂性。同样,《子夜》的创作也是作家认真调查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的结果,《子夜》中纺织女工的罢工失败及党在领导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脱离群众的简单粗暴的“命令”作风,因为没有从一个“革命神圣化”的角度来“预设”事物的发展,所以这些被认为“错误”的东西才得以保存下来。而通过这些所谓的“错误”,我们非常可贵地看到事物发展的某种原生态。而在建国后新的历史语境中,这些有损工农革命者和党的形象的“错误”大都被修饰或删改。
涉及汉语规范化的词语置换修改和涉及少数晦涩语段的删改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广大工农读者的阅读需要,另一方面也是1950年代汉语规范化的客观要求所致。词语置换指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用语换成1950年代的规范用语,诸如“马将”换成“麻将”、“看护妇”换成“女护士”、“汽车夫”换成“司机”、“利害”换成“厉害”、“年少”换成“少年”、“餐间”换成“餐厅”,等等。晦涩语段的删改是将一些文艺性太强、不易理解的语段作简化删除的修改。《动摇》结尾中方太太在尼庵中出现幻觉:“……在这中间,有一团黑气,忽然扩大,忽然又缩小,终于弥漫在空间,天日无光……”而原文为“……在这中间,有一个黑心,忽然扩大,忽然又缩小,终于是不息的突突的跳!每一跳,分生出扩展出一个黑的圈子来,也在突突的跳。黑圈子一层一层的向外扩展,跳得更快,扩展的也更快,吞噬了一切,毁灭了一切,弥漫在全空间,全宇宙……”涉及个别语句精益求精的润色修改,是作家继续锤炼雕琢作品的结果。
《茅盾文集》的第二、四、五、六、七、八、九、十卷并没有作出修改,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一方面,茅盾时任中国作协主席、文化部部长、政协常委,又兼《中国文学》和《译文》的主编,事务非常繁忙。另一方面,其时茅盾身体违和。正是精力及身体不济等方面原因,茅盾不可能对其他旧作作出像1954年人文版《蚀》和《子夜》的修改,但他通过选编作品和附录、后记、附记的方式完成了与修改本相同的政治效果,使之力求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范。
在《茅盾文集》第七卷《后记》中,他说:“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三年间,我所写的短篇小说,不只是现在这本集子所收的十八篇,还有五篇,即《自杀》、《一个女性》、《泥泞》、《陀螺》、《光明到来以前》,我以为应当‘割爱’,这样办,倒不是想把青年时代的蓬头赤脚光屁股的照片隐藏一部分,而是为了节约纸张和读者的时间。”这显然是茅盾的自谦之辞。那么,茅盾为何要舍弃以上五篇短篇小说呢?《自杀》讲述环小姐追求婚姻自由与少年男子偷尝禁果,整日处于孤寂怨艾中,在得知已怀身孕后她在深夜上吊自尽。而那个少年男子在骗得她的处女身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据说为了多数人的幸福而奋斗了。整篇小说充满神秘荒诞的色彩,读后让人感到压抑窒息。小说最后借环小姐之口对“五四”倡导的“婚姻自主”观念提出了批判。《一个女性》的情节凄婉而悲凉,美丽的琼华小姐出身望族,父亲是名流,她因善于交际而成为一乡的女王,不幸家道中落,她父亲在火灾中烧死,母亲病重,她自己也被火烧伤面颊,留下指头大的红疤。她的昔日追求者离她而去,在人们的冷眼嘲笑中,她不幸得了女儿痨病死,死前怀念着那个被家乡人排挤走的“遗腹子”少年张彦英,整篇小说书写人性的冷酷虚伪残忍,气氛沉闷凝重。《泥泞》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黄老爹因帮着农民协会写“花名册”而被穿灰色军服的兵拉去枪毙,他的大儿子也一起遇难。而枪毙他的军队与要他写农民协会“花名册”的军队居然旗帜相同(只不过号数不同罢了)。《泥泞》中关于“共妻”的描写令人困惑。农民把参加农民协会当成要“共妻”,不许村里的婆子与姑娘露脸,单身的农民却想共那些穿灰色军服的女兵。最后,穿灰色军服的士兵撤走,农民们内部却盗抢四起。整篇小说跳跃性较大,逻辑条理也不清楚,对农民的批判犀利,对照新中国工农兵文艺方向,这篇小说显然有严重的“政治错误”。《陀螺》叙述了小资产阶级女子五小姐与徐女士之间絮絮叨叨、琐碎冗长的对话,韶华不再的五小姐对恋爱持怀疑悲观的态度,但有男士为她送礼物时,她却又迅速由凄然变为兴奋了。小说情节发展过于缓慢,卖弄知识地介绍Gilgamesh(吉尔伽美什)和W·Hausenstein(维廉·霍善斯坦因),显然不符合工农大众的欣赏口味。《光明到来以前》与其说是一篇小说,不如说是一首散文诗。全文以对话连缀而成,意象飘忽不定,象征色彩浓厚。幽禁在黑暗牢笼中的两人隐约感受到裂缝中一道光线:“红的、绿的、黄的、小小的、圆圆的、尖角的,在那里跳!跳!”两人努力想打碎这牢狱,地震和火山爆发了,还有轰隆隆的雷声,年长者因为外面燃烧的烈火和炫目的光线而不愿意离开牢笼,年青人却勇敢地离开了。“火也就要烧过来了!哈!来罢!烧毁了旧世界的一切渣滓!来罢!我要在火里洗一个澡!”这篇小说的主题虽是追求光明,但从艺术形式上看,浓厚的象征色彩和晦涩的表达显然妨害了工农大众的阅读欣赏,茅盾于是“割爱”了。综观以上五篇作品的舍弃,茅盾一直以《讲话》中“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作品,凡政治上有损党和工农兵形象及艺术形式上晦涩沉郁或小资产阶级色彩过浓的作品均被“剔除”。同样,《茅盾文集》第八卷中有意漏收《牯岭之秋》和《烟云》两篇小说,其理与之相同,这里不再赘述。
注收(后记、附记收)是编纂《茅盾文集》时采用的主要收录作品方式。以《腐蚀》为例,茅盾在后记中指出他未作任何修改。但当时有部分读者质疑为什么要给赵惠明这样一个满手血污的特务以自新之路?茅盾说赵惠明之徒的本质显然是坏的,虚荣心很重,不明大义,敌我界限不分,尽管也反抗着高级特务对她的压迫和侮辱,但她的反抗是个人主义的、不彻底的。那么,为什么给她自新之路呢?因为正是通过对赵惠明的描写“暴露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只是日本特务组织的‘蒋记派出所’,暴露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的不少青年分子是受骗,被迫,一旦陷入而无以自拔的,那么,为了分化、瓦解这些胁从者(尽管这些胁从者手上也是染了血的),而给《腐蚀》中的赵惠明以自新之路,在当时的宣传策略上看来,似亦未始不可。”⑧这里,茅盾巧妙地将阶级敌人的问题转换为抗战策略的问题。正是为了暴露抗战中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这也符合对阶级敌人专政的理论)才塑造了赵惠明的自新之路,但同时,“如果考虑到日记体裁的小说的特殊性,而对于赵惠明的自讼、自解嘲、自己辩护等等不作正面的理解,那么,便能看到这些自讼、自解嘲、自己辩护等等正是暴露了赵惠明的矛盾、个人主义、‘不明大义’和缺乏节操了”。⑨显然,茅盾通过自己对作品的解读完成了对赵惠明这个阶级敌人的批判。尽管在作品中赵惠明令人同情且走上自新之路,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并不能放松对特务的警惕,这是茅盾的言外之意,和整个1950年代的历史语境也是相契合的。当然,其他并不让读者产生“误读”的作品,茅盾在后记中一般只交代作品的创作及发表情况等相关背景知识,以方便读者阅读。
附记是《茅盾文集》第九卷和第十卷中采用的一种编纂方式,专收散文、杂文和游记。其中第九卷有5篇附记,分别附在《风雪华家岭》、《西京插曲》、《秦岭之夜》、《太平凡的故事》、《新疆风土杂忆》篇后。第十卷也有4篇附记,分别附在《学步者之招供》、《永恒的纪念与景仰》、《归途杂拾》、旧体诗《渝桂道中口占》篇后,以上九篇附记的时间均注明为1958年11月,显然,茅盾在该月完成了对九、十卷的编纂整理。这九篇附记共分四类。一类是讴歌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伟大成就。前者有《太平凡的故事》和《归途杂拾》篇后的两则附记,均追述了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及地下工作者抢救香港沦陷区文化人的盛举。后者有《风雪华家岭》的篇后附记,热情讴歌了共产党在大跃进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华家岭本是西北兰西公路上的必经之路,因为经常雨雪霏霏,这座海拔五六千尺的高原山岗极难行走,1940年作者乘汽车途经此处时恰逢雨雪,车陷入泥泞而受尽折磨,而现在(1958年)华家岭却“旧貌换新颜”:“我愿意提醒读者,今天的华家岭完全不同了。本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人民日报》有一篇通讯是这样写的:‘现在岭上已经满山梯田,园林连片……这是通渭、定西、会宁和静宁四个县三万七千人大战十一天的结果。从十月十二日起,十一天内,共修成山顶公园二十二个,梯田二十八万四千六百亩,植树种草三千二百二十亩,结合修梯田深翻地十二万六千六百亩……在华家岭的工程上,各兵团的党团支部一面开办工地党校、红专学校,一面整党整团整社,政治文化教育也搬到了工区。1958年11月17日作者记。’”时隔半个多世纪后,我们重新审视这段热情洋溢而又“注水”严重的《人民日报》通讯,一方面对这种浮夸风的虚假报道深表遗憾,另一方面,对当时人们的冲天干劲深感惊叹。茅盾此处的附记,契合了当时人们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激情。或者说,这正是国家意识形态赋予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学在文本上的必然反映。第二类附记对国民党解放前的文网制度及反革命措施进行了批判。有《秦岭之夜》、《西京插曲》、旧体诗《渝桂道中口占》篇后的三则附记。以《西京插曲》为例,作者在篇后附记中追述:“此篇发表时被国民党的检查官删削了不少。原稿早已遗失,现在记不清那被删削的是些什么内容,只依稀记得,那是用讽刺的笔调,点明那华侨慰劳团之所以被‘请’到华山去住,表面上为了安全,事实上是怕慰劳团和群众接触,慰劳团的团长是陈嘉庚。1958年11月13日作者补注。”此则附记一方面批判了国民党的文网制度,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国民党脱离群众的官僚作风。第三类附记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有《学步者之招供》篇后一则附记。茅盾当时写此文之意是批判美国的霸权政策“握有月球,可轰炸地面上任何一地点”(美国火箭协会主席法恩斯渥斯宣传)。想把月球作为未来称霸世界的战略基地,这简直是希特勒的“学步者”,在1958年11月的附记中,茅盾在继续批判这个战争狂人后指出:“十二年以后的今天,美国的吹得震天响的牛皮,完全破产。在苏联放出了三个人造卫星以后,美国几经出丑,这才勉强放了一个山药蛋大小的卫星……纸老虎已经戳破,东风将永久压倒西风。”不仅赞扬了苏联(当时两国处于友好合作时期)的伟大成就,而且以毛泽东的话语作结,旗帜鲜明地强化了国家的意识形态。第四类附记阐释了青年如何学习罗曼·罗兰。有《永恒的纪念与景仰》篇后附记一则。茅盾指出,学习罗曼·罗兰,不是学习约翰·克利斯朵夫个人主义的反抗,而是学习《动人的灵魂》中人民大众的社会革命,要学习罗曼·罗兰怎样从一个个人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针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分析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几篇文章,茅盾一方面认为“大概算是大大地消毒一番了罢”,但同时他又担心“副作用又产生了:不少青年把罗曼·罗兰视为一文不值,甚至还把他当成反动文人”。在这则附记中,茅盾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和新中国文艺官员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宏观把握出发,阐释了如何批判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艺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是很有远见的。
早在20世纪初,葛兰西在《社会主义和文化》中已经提出这样的观点:无产阶级要重视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文化工作是取得革命工作合法性的基础,对文化工作不能采取自发和自然主义的态度,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领导工作。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重视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讲话》中开篇即强调“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新中国建立前夜,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到会讲话,郭沫若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在报告中郭沫若指出,新中国的人民文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文艺工作者要更广泛地和人民大众结合。这其实已为新中国的文艺定调: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兵的大众方向(艺术品位及美学追求)。大会也成立了“专管文化艺术部门”的组织机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9月分别改名为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由此也标志着新中国文学进入全国性的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设与建构阶段,而非之前的部分地区存在的自发与自然状态。
综观所上,我们可以得知:新中国文学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学生产上有计划有组织地参与预设与建构的文学。这种预设与建构不仅体现在诸如《鲁迅全集》、《沫若文集》、《茅盾文集》等的整理编纂上,而且也体现在作协各分会的建立、重要作品的组稿制度、对作家创作路线加以“规范”等机构设立及意识形态的控制上。从《茅盾文集》的编纂来看,其所收作品绝大多数在建国前已整理成集出过单行本,许多在当时曾多次再版,被读者视为经典。《茅盾文集》通过对茅盾旧作的改收、漏收、注收(后记、附记收)的方式,事实上完成了茅盾作品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再经典”工程。
注释:
①②茅盾《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茅盾文集》第1卷第433—434、4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③[英]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著、李赋宁译《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第3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④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第20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⑤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第1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5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⑦李继凯《关于胡风与茅盾的交往、冲突及比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⑧⑨茅盾《茅盾文集》第5卷第306—307、307—3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