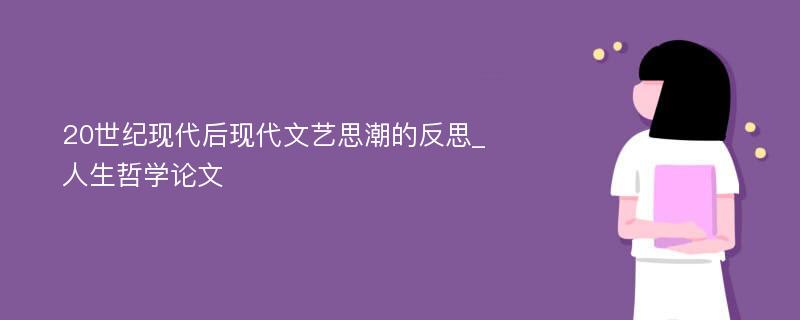
二十世纪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后现代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低迷暗淡的文艺时代
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是: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的文学艺术笼罩着一层低迷与暗淡的情绪,再也没有了十九世纪那般显赫的声势,再也没有出现像托尔斯泰、雨果那样举世公认、雅俗共赏的一流文学大师。代之而起的现代、后现代派,虽然不乏在学术界获得很高评价的作家作品,但对于社会大众,却缺乏真正属于艺术的吸引力。难怪美国文学评论家诺门·勃多列兹早就著文指出:现代派无异于文学的死亡。另一位美国文艺理论家威尔逊也早在三十年代就这样声称:诗成了“即将死亡的技巧”[①]。连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思想家海德格尔也这样惊呼:“伟大的艺术连同其本质已离开人类;近代艺术正在经历慢性死亡。”[②]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主体理性的无限膨胀,在一些激进的作家、艺术家那儿,几乎所有的艺术规则都遭到了粗暴践踏,艺术终于陷入了令人迷茫的困境。
这是一个破坏的时代。
破坏,几乎是现代、后现代主义的性质之一。现代主义一出世,似乎就挟带着一种破坏的冲动。请看现代主义的早期派别“未来主义”的宣言:
我们的诗歌中最重要的成份将是勇气、大胆和反叛。
除了在斗争中以外,没有什么美。
我们想讴歌战争——使世界健康化的唯一手段——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毁灭一切的手臂,杀生的优美思想,对妇女的蔑视。把图书馆的书架子点上火!……改变河道,让博物馆的地下室淹在洪水里吧!……哦!愿这些壮丽的油画毫无办法地在水中漂荡!……抓住鹤嘴锄和榔头!去破坏那些古老神圣的城市的地基![③]
这听上去,很像是我们当年的“文化大革命”。
这种破坏欲望落实到实际的文学艺术创作领域便是:蔑视艺术规则,追求极端化的创作自由。特别是那些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作家、艺术家们,他们以更加激进的反叛姿态,故意把小说弄得不像小说,诗不像诗,绘画不像绘画,音乐不像音乐。如被看作后现代主义代表作之一的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微暗的火》,由“前言”“诗篇”“注释”“索引”四部分组成,看上去更像是学术著作。巴思的《迷失在开心馆中》,充满了文学理论及标点符号使用法之类内容。在戏剧领域,出现了不再像“戏剧”的《等待戈多》、《秃头歌女》等作品。在音乐领域,出现了斯托克豪森的《一周间》、凯奇的《4分33秒》这样一些要“把音乐从音符中解放出来”的“概念音乐”;在美术领域,出现了在沙滩、荒漠上堆筑、挖掘而成的“大地艺术”,用人体或画家自身作为材料的“行为艺术”,用废品组装而成的“集合艺术”等等。这类艺术,不仅破坏了某类艺术的基本规则,甚至也否定了作家、艺术家自身,使作家、艺术家与一般人没有了根本的区别。
遗憾的是,在西方现代文艺史上,这种破坏性,不仅没有受到必要的遏制,反而受到了同样激进的一些理论家的高声喝彩。如被我们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著名理论家阿多尔诺认为,这是新型的“反艺术”,这些作品越是不被社会接受,就越出色,反之就越低劣。马尔库塞说得更为激进:“艺术作品按照它整个的结构来说,就是造反”“艺术本身就有一种破坏性的潜力”“永恒的美学颠覆——这就是艺术的任务”“艺术就是政治事件”。这对于破坏性的现代主义的恶性发展,无异于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与破坏性相关,这是一个虚无的时代。
与十九世纪的作品不同,在现代主义作品中,往往难以见到自信、光明与希望。作家、艺术家们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生,对自己,均失去了信心。反讽与戏谑,自贬与嘲弄,悲观与失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调。乔尹斯说:“历史是一场恶梦”;卡夫卡说:“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萨特说:“社会理想,究竟会不会实现?对这一点,我就一无所知。”德国艺术家乔治·葛罗兹说:“对我们来说,无神圣可言。……我们唾弃万事万物,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象征是乌有,是真空,是空虚。”[④]
众所周知,这也是一个嗜丑的时代。
从现代主义先驱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开始,人类的文学艺术便似乎开始了一个审丑的时代。蛆虫代替了鲜花,污浊代替了圣洁,乱伦、同性恋代替了爱情,恶作剧般的亵渎代替了严肃的艺术创作,一只小便器居然可以随意置于神圣的艺术殿堂。正是面对如此的文艺现实,英国美学家李斯托威尔发出惊叹:“那么多的当代艺术,就因为对丑的病态追求而被糟踏了。”[⑤]
这又是一个蔑视大众读者、背叛大众读者的时代。
在许多现代、后现代主义作家心目中,审美愉悦不再是文学艺术关注的价值目标,不再顾及读者的审美娱乐需求,而是力图通过作品,唤起读者的厌恶与痛苦,甚至悲观与绝望。而且,将其视为艺术价值的正常嬗递。卡夫卡在致布洛德的信中说:一本书的作用,就是在人们头上猛击一拳,让人惊醒,“使我们读到时如同经历了一场极大的不幸,使我们感到比死了自己心爱的人还要痛苦,使我们如身临自杀的边缘,感到因迷失在远离人烟的森林中而彷徨。一本书,一本有影响力的书,应该是一把能够破我们心中冰海的利斧。”[⑥]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艺术品就不是让人舒舒服服享受,像在沙发上睡大觉那样,真正的艺术品就是随时让你感到不舒服,因为恰恰在你不舒服的时候,这里才有真实性。”[⑦]法国学者让-皮埃尔·理查也这样指出:“今天,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文学的功能已远远超过了它过去仅供消遣、颂德或点缀的作用。人们惯于认为文学表现的是个人存在深处的选择、困扰和难题。”[⑧]人生本已充满着不堪与重负,又有多少人愿意在饱纪现实的磨难之后,再抱起书本,去忍受痛苦的精神煎熬?
事实上,正是由于审美愉悦价值与可读性的丧失,许多现代艺术不再是供社会大众欣赏的“艺术对象”,而成了象牙之塔中的小圈子艺术,成了主要供学术界分析探讨的“研究对象”。比如被奉为现代主义小说典范的乔尹斯的《尤利西斯》,真正感兴趣,真正当作“文学作品”欣赏的又有几人?美国当代文学理论家米勒的说法大概不会是别有用心的诋毁:乔尹斯的作品是专门写给教授读的。美国作家辛格说得更为尖刻:“他写得深奥难懂,好让别人一直解释他的作品,采用大量的脚注,写出大量的学术性文章。在我看来,好的文学给人以教育同时又给人以娱乐。你不必坐着唉声叹气读那些不合你心意的作品,一个真正的作家会叫人着迷,让你感到要读他的书,他的作品就像百吃不厌的可口佳肴。高明的作家无须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所以研究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的学者寥若晨星。但乔尹斯的门徒就需要具有学者的风度。或者说要具备未来学者的风度。”“乔尹斯把他的聪明才智用来造成让别人读不懂他的作品,读者要读懂乔尹斯,一本字典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借助十本字典。”“大概读他作品的人都是博士学位获得者或是在攻博士学位论文的人。他们就喜欢搞一些晦涩难解的谜。这是博士们的特权。”[⑨]
也有一些现代或后现代作品,之所以丧失了艺术美,令读者敬而远之,一个重要原因是:表面上的“非理性”,骨子里却是强硬的理性。如后现代主义的大地艺术、行为艺术、废品艺术等,常常是某种“巧智”、某种“创意”的产物,而不是独特的审美创造。如萨特的小说与戏剧,虽然获得了学术界的极高评价,但作为艺术作品,却缺乏真正的吸引力,有的甚至不堪卒读,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其作品,主要是他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图解。
二、哲学尴尬与艺术困境
在西方,形形色色的现代及后现代文艺思潮的产生,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是与西方社会自身的历程,特别是精神发展的历程密切相关的。
一是人性哲学的深入发展。二十世纪以来,人类严酷的生存现实,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终于彻底粉碎了文艺复兴以来一些善良的思想家关于人是“万物之灵”,人是“天使”之类的美丽梦幻。于是,“非理性”似乎便成了人类对自身本性的重新确认。二是思维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一些敏感的思想家愈来愈痛切地感到,必须对传统理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进行批判与否定,正是日趋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概念,删削规范了世界,导致了人的生命的枯燥化,世界的干瘪化。前者表现为对人性的失望,后者表现为对人生的失望。
从文化哲学意义上来看,这无疑是深刻的。这里特别应该提及符号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弗洛伊德、荣格“精神分析”等哲学思潮的贡献。它们在更深的层次上使人类认识了自我,它们开拓了文字、符号的功能空间,打破了几千年来一直束缚着人类思维的单向因果及追求概括性、统一性、稳定性、终极所指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但毫无疑问,由于激进的思维方式,致使许多思想家本人,始非所料地陷入了尴尬,使构成人类精神指向的文化,陷入了令人忧虑不安的迷途。
那些激进的思想家们,虽然要彻底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但他们心里当然应该清楚,人类正是凭依规范性文字符号和形而上思维方式,使自己得以提升,由动物而生成为“人”的。不论怎样打破,忍受文字符号对感性世界的删削,忍受形而上思维方式对感性生命的束缚,怕是人类不幸却又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那些激进的思想家们,眼睛太毒,也太阴鸷了些。他们把人生和世界看得太透了,把人性、人生的真相彻底揭穿了,这势必也就动摇了人类生存的精神支柱,将人类推进了虚无主义的深渊。实际上,文艺复兴以来日趋强盛的理性权威固然压抑了人的自由本性,但如果任凭非理性本能的自由泛滥,也注定不可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寻找一种和谐与平衡,才是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秩序的明智选择。人,总要以“人”的姿态活着。人生,既需要源于自然生命的本真状态,但也不能没有信仰、道德之类虚饰成分。正如人的裸体是真实的,但却不能没有衣饰一样。人生,可以了然生存状态的尴尬,但也的确需要一种庄子所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旷达胸怀,需要一种理想的支撑与精神的抚慰,尽管这支撑与抚慰可能是虚妄的。
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学艺术,本应部分地承担化育人类德行,抚慰人类精神的使命,本应清醒地保持与以求真为鹄的哲学的距离,独立地开辟人类的精神空间。但在二十世纪的西方历史上,文学艺术,却不怎么顾及社会大众的文化欲求,而过分紧密地胶着于玄妙高深的哲学:或者本身就是某种哲学思想的衍生物;或者无视哲学的尴尬,一直在盲目地为其推波助澜。其结果是,许多作品,只是写尽了人生的失意与悲哀,丑陋与龌龊,但却失去了人类统驭丑的自信;只是热衷于宣泄某些本能意识,但却丧失了应有的价值判断;只是为社会提供了某种哲学意义的研究对象,但却丧失了应有的审美趣味。文学艺术,终于被推进一个晦暗的时代,日益更大范围地失去了读者。对于这种状况,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的一段话也许是值得深思的,他说:“艺术家如果成了职业性专家,不是为人类同胞,而只是为专家们著述的话,艺术确实不会有什么成绩的。照我的见解,这种东西已不是为艺术的艺术,只不过是为人的艺术而已。从这一意义看,我认为,文学也好,或者科学或者学问也好,如果只为少数人所有,那才是真正的不幸,并且是社会弊病的兆候。”[⑩]
文学艺术,当然可以写丑,但本世纪出现的许多此类作品,由于片面注重于丑的客观展示,缺乏对丑的主体统驭,往往只能唤起令人厌恶的如同实际生活一样的生理刺激,而难以得到艺术性质的审美体验。在文艺学著作、美学著作中,当然也需要谈丑,但如果仅从丑的角度谈“丑”,甚至将“丑学”作为“美学”的一部分,总叫人感到不伦不类。
文学艺术,当然可以写虚无,可以高深莫测,但如果缺乏理想之光的照耀,一味宣泄,或故弄玄虚,只能徒增人生的迷茫与烦恼。
文学艺术,当然需要不断创新,不断破坏,但作为艺术创造,毕竟又需要建构。究竟怎样才是文学?才是艺术?才是诗歌?才是小说?总该有一定规则。若过于自由与随意,也就毁灭了艺术。且,不论怎么创新,总该要有诱人耽读品评的趣味性,即首先要设法满足人们的消遣娱乐需求。否则,又怎么谈论其审美价值?这一点,即使在当代西方理论界,也是早就受到关注的重要问题。法国文学理论家、小说家乔治·杜亚美这样指出:“作品的趣味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仅有趣味当然还不是好作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严肃的评论家不应该考虑趣味性问题;这也不意味着,为了对抗不良的艺术趣味,我们应该对所有能使我们消遣的作品,抱着一种高傲的蔑视态度。”这位理论家还特别强调:“任何作家的首要任务,特别是长篇小说家的首要任务,是用自己的主人公吸引住读者。我们有权要求一部长篇小说至少不能比它所描写的实际生活更枯燥。”(11)
文学艺术,当然需要自由,需要率性而为,但某些根本规则、基本质素,则是不能随意改变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某类艺术了。如绘画总该有色彩、线条,总需要画纸、画布、画板之类,总该要有空间造型;音乐总是要有音符,总是要构成一定的音符系列;小说也总该写人写事,如像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人所主张的那样,果真“将音乐从音符中解放出来”,怕也就没有音乐了;将人体表演看作是绘画艺术,那也就没什么绘画可言了,倒不如干脆叫作“小品”更加名副其实;把小说写得像议论文、像学术著作,那干脆就叫论文、叫学术著作好了,何必仍叫小说?这正如酒必须要有乙醇、衣服首先要蔽体一样。如果不含有乙醇,可以是别的什么饮料,而不必再称之为“酒”;可以是别的什么装饰品,而不能独立作为衣服。
与二十世纪以来的大多数作家相比,美国意第绪语作家辛格,也许显得守旧和背时了些,他对那种时髦的反人物、反故事、反情节的现代创作思潮甚为不满,公然声称:“把讲故事从文学中取消,那么文学便失去了一切。文学就是讲故事。当文学开始力图以弗洛伊德的学说、荣格的学说或艾德勒的学说来分析生活,它就变得乏味和没有意义了。”他曾抱怨说:“讲故事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了一种被遗忘的艺术。”并表示:“我自己则尽力设法不要患上这种健忘症。”他认为“短篇小说是比长篇小说短的故事。长篇小说是长的故事,而短篇小说是短的故事。”(12)辛格正是凭他那些传统味十足的、重在讲故事的作品,照样博得了全世界许许多多读者的喜爱,并于1978年,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
可见,文学创作,形式创新固然重要,坚守传统也不见得没有出路,关键要看达到的艺术高度。如果有人老老实实地以曹雪芹的传统笔法,写出一部当代内容的《红楼梦》式的作品,大概照样会成为杰作。相反,如果没有什么真货色,只是一味地标新立异,玩花架子,怕也不可能赢得读者。
三、西方现代思潮与中国当代文艺
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可谓世界近代史上最为多灾多难的民族之一。强寇入侵,文化沉沦,政治失误,造成了一次次沉重的心灵阵痛。“国家不幸诗家幸”,从文学艺术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应该产生“巨著”而至今却不见“巨著”的时代,这是一个应该出现“大家”而至今依然罕见“大家”的民族。更为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当代文坛,正在失去应有的刚健骨骼和血性气质,正在加速自身的精神瘫痪症。一大批本应是民族之魂、社会良心、历史旗手的诗人们、小说家们,已经越来越淡漠了作为中国当代作家应有的现实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越过了我们的现实,浮着在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泡沫上,搅动起了肤浅的文艺浪花。他们或迷恋于超前消费的先锋意识,或困扰于无可奈何的生存状态,或热衷于纯技巧的摹仿与卖弄。
有一些作家,写出了一些看上去莫测高深,颇具哲学气度的作品,然而仔细考究,就会发现不过是某些现成哲学观念的套用或图解。如对于被称为“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的小说,评论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作者以独特的敏锐性,对深刻地贯穿于当代中国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提出了质疑。不断强调和说明的,是人在语言中的无能为力,语言成了控制和压抑人的东西,人,沉溺于自己所创造的符号秩序之中,无可奈何,找不到出路。余华的小说中,或许不乏这种语言哲学的意味,但却不过是对西方某些现代哲学观的图示而已。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早就指出:“只要我们粘着文字和它的含义,我们便无法接近物象本身。”这种现象,倒正如我国著名作家汪曾祺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许多作者,“竭力要表现哲学意蕴。这大概是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和青年评论家的怂恿(以为这样才‘深刻’)。作者对自己要表现的哲学似懂非懂,弄得读者也云苫雾罩。我不相信,中国一下子出了这么多的哲学家。我深感目前的文艺理论家不是在谈文艺,而是在谈他们自己也不太懂的哲学,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哲学’是‘抄来’的。我不反对文学作品中的哲学,但是文学作品主要是写生活,只能由生活到哲学,不能由哲学到生活。”(13)有一位作家,在一篇文章中竟这样得意地告诉读者,当他从法国新小说派那儿发现了一部理想范本(米歇尔·布托尔的《变》),从中“找到了一种新的角度——你!”“看见了一种新的起码在当今中国文坛还未曾出现过的结构形式”之后,居然“差点按捺不住山呼‘万岁’”,“整整啃了二十一遍,当作自己心中的《圣经》摹仿起来。”(14)
八十年代后期,中国诗坛兴起了以消解意象,亵渎文化,反叛诗美,追求“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为特征的“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先锋诗派。实际上,这些诗派的作品,从形式技巧到创作意旨,也不过是在步法国超现实主义,美国黑山派、奥地利维也纳派、德国新主体意识派等西方一些后现代诗派的后尘。这些作品,除了引人怀疑和反叛传统的“诗”之成规之外,本身却很少是成功的艺术。诸如“你见过大海/你曾想象过/大海/你想象过大海/然后见到它/就是这样/你见到了大海/并想象过它/可你不是/一个水手/就是这样/你曾想象过大海/你见过大海……”(韩东《你见过大海》)“祭司的预言爬满虎皮/麦子随之而来从没见过的麦子/黑色的麦子紫色的麦子/那一年尼罗河茂盛/成群结队的鱼在街头抛锚……水里浸过三遍火里烧过三遍/水深火热的麦子有坚硬的牙齿……”(周伦佑《埃及的麦子》)“隔着一堵墙/你和她同时/退下裤子和裙子/两岸便有声音/淅淅沥沥”(张锋《你和一个女人同时上厕所》)这样的诗,无论背后有着怎样深刻的哲学,无论理论家们怎样阐释其中的微言大义,作为诗,怕是很难让读者感兴趣的。相反,这种步趋洋人,亵渎文化与艺术的时风,可能会诱使许多涉世未深的年轻人陷入歧途,正如诗人、诗歌理论家郑敏在一篇文章中十分痛心地讲过的:许多青年诗人的诗令她不安,为作者浪费他的才华而不安,而且他们往往用“先锋”的字样解释自己语言的不必要的扭曲和内涵的虚假,以“反诗美”作为特点。这些诗,除了新奇,似乎没有其它的意义。但新奇本身不等于艺术。“反诗美”的追求,当它最初被用以撼动伪装的诗美时,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一旦被超常度使用,作为以“丑”代替“美”的同义词时,也就失去振聋发聩的效果了(15)。
在我们的文坛上,虽然,由于某些圈子内的相互趋奉与吹捧,由于某些时髦批评家们不时发出阵阵喝彩,造成了文学繁荣的某种假象,但真正耐品的诗,可看的小说实在不多。连金克木这样著名的学者都曾这样慨叹:“从前有‘闲书’可看,可是现今小说都成了高深研究的对象。”(16)绝大多数普通读者更不肯买账,纯文学刊物、书籍销量的锐减便是明证。国外的反映也不像某些国人那样自视甚高。日本有学者认为:往日的《红岩》《暴风骤雨》《李双双》虽有某些不足,但在日本却曾大受欢迎,因为它们有着“对时代风云直接体验的迫力”,“能够打动多数同时代人的社会理想”,“而新时期文学则相对缺乏这种魅力。”(17)美国普利策评奖委员会也这样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散乱,看不出构架,很多作者描绘的是无意义的东西,作者群体有落伍意识,人们无法从中国当代文学中了解中国当代社会(18)。
其它艺术门类的情况同样令人丧气。以美术界而论,如青年画家们1985年在杭州举办的“新空间展”,1986年在厦门举办的“新达达画展”以及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美展”,虽轰动于一时,但除了“火烧作品”“枪击作品”之类新奇“事件”(对于中国人而言)一时引人注意之外,也似乎并没有为美术史提供多少艺术价值。且,其创新之“新”,也不过是对西方人现代艺术试验的摹仿;其理论支撑,也不过是西方人的“现象学”“解构主义”之类哲学。
想想这些,对于那些不满现状,意欲创新的中国新潮诗人、作家、画家的敬佩之余,却又不能不令人顿生一种悲哀,——为我们民族自身创造力的低下而悲哀。在简单趋奉西人的背后,我们还会看到一种更为可怕的民族自卑心理。的确,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整个世界文学艺术格局中,我们的民族没有赢得应有的地位,很少有作品获得世界性的声誉。实际上,即使我们数千年以来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西方人亦知之甚少。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除了西方人自高自大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汉语本身的障碍之外,经济与现代科技的落后怕是最关键的原因。显然,在此情况下,我们的民族要想卓立于世界,首先是自身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同样,作为文学艺术,也只有牢牢立足于民族文化和我们特定的社会现实,才有出路。如果过分步趋西方,只能进一步丧失民族自尊。
四、理性建设与文艺理想
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与兴盛,当然也是有其深刻的时代及历史原因的,这就是借助于历史的机缘,一个自我个性久遭压抑的民族,从西方人那儿,从尼采、弗洛伊德、萨特等人那儿,找到了反叛权威,寻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但在社会基础、历史条件等方面,我们与西方人又有许多根本的不同。西方社会是以现代理性压抑了人性的,而我们是以非理性压抑了人性的。在我们的历史上,从“君主意志”到“个人崇拜”,从照般苏联模式到“十年动乱”,骨子里都是“非理性”的。与西方人相比,我们根本没有体验过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自信,我们跨越了一个建立规范和完善秩序的时代,这就使我们对非理性的肯定与西方人不是在同一个基点上,对准的不是相同性质的目标。西方人是源于对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度发达的科学理性和过分严密的社会理性的怨恨,我们则主要是源于对缺乏理性秩序的封建性的权威意志的不满。
由于文化背景和文化结构不同,在西方,本是有意义的东西,到我们这儿,便极有可能发生质变。
二十世纪的西方,“非理性”思潮虽一直在波翻浪涌,但同时却又受到了这样三种强硬的理性力量的抗衡与制约。一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对人生价值、个性价值有着正确把握的人文主义思想;二是精神自慰、精神信仰意义上的现代宗教;三是严明健全的法律制度。在这样强固的理性氛围中,“非理性”可以在调谐理性的过于严酷方面产生积极意义,而不论怎样张扬,却终不至于泛滥。
而在我们这儿,本应是与道德律令、社会责任相关联的个性主义,却很容易质变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本应是与肯定自我,尊重人权相关联的人性解放,却极易异变为兽性本能的发作。因为中国人骨子里没有宗教,没有上帝,也没有经过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相当一段时间的人文主义文化的熏陶。而可以成为抗衡与制约兽性本能力量,近乎于宗教的儒家学说,从“五四”运动以来,则已被当作封建垃圾,给予了彻底的批判与否定;而多年以来确立的,作为中国人精神支柱的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觉悟,由于历史进程的缓慢与曲折,特别是由于商品意识的突然兴盛,也已受到了严峻的冲击;我们的法律制度也一直极不健全。可以说,我们是在反叛了封建意识,但却没有新的坚实的理性依托和精神保障的状态下,饥不择食地突然接受了西方现代派思潮的。这就难免有买椟还珠之憾。
在西方,不论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是基于对人类理性的失望,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不满。而对于以直觉思维见长,习惯于权力崇拜的中国人而言,形而上的思维方式不是多余,而是不足。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真正的理性一直被掩抑在“非理性”的阴影中。至今,权大于法,长官意志,个人崇拜,法制意识淡漠,这本来就是“非理性”的产物。因此,在当今中国,更需要的是真正的理性建设,而不是“非理性”的过分喧嚣。
与西方人相比,我们面临不可偏倚的双重任务:感性解放与理性建设。
特别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今中国,在人文精神失范,法制力量依然薄弱,物欲极易恶性膨胀的社会条件下,我们既需要感性的解放,同时又需要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建设。我们的任务要比西方人艰巨复杂得多,绝不是简单照搬西方人的文化就能解决我们千头万绪的问题。与之相关,作为与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文学艺术,同样不应该只是简单地趋奉西人,尤其不能盲目地陷入“非理性”、“玩文学”之类的小圈子里。文学艺术,说到底,总是要和人生发生密切关系的,因此就一定离不开时代性、功利性和思想性。概念化无疑将致文学艺术于死地,但概念化不等于思想性,一个没有思想的作家、艺术家,很难成为一个真正有成就的大作家、大艺术家。我们反对概念化,不是不要思想。只是主张:一、这思想应是个人创造性的,而不是轻易挪移自报刊、广播,或政府文件;二、这思想应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与社会人生密切相关的;三、这思想应化为作品中的艺术血肉,而不是马克思所批评的“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文学……就其本性来说,它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不能不是时代思想的表达者。……只有那些在强大而蓬勃的思想的影响之下,只有能够满足时代的迫切要求的文学倾向,才能得到灿烂的发展。”(19)针对我国目前的文艺状况而言,我们深感有重申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一论断的必要。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中国的文学艺术界,整个文化界、思想界,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承认西方现代文化思潮深刻性的同时,也要切实认识到:那些痛苦而又激进的欧美思想家们,虽然敏锐地意识到了社会问题的严重,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找到文化拯救的妙方。许多有识之士,已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投向中国。许多人断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显然不仅指经济,也包括文化。因此,我们必须总结历史的经验,做出正确的选择,这就是:既不该盲目自大,不分青红皂白,重新沉迷于传统文化,更不能急功近利,不顾现实,完全被动地适应外来文化,而是要积极地,在综合吸取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并以此促进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健康发展。“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风骨,也应是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风骨。
注释:
① ③ 参见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67、64-67页。
② 杨荫隆主编《西方文论大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
④ 参见陈慧著《西方现代派文学简论》,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1、116页。
⑤ 转引自《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第36页。
⑥ 参见鲍维娜、王梅著《小说:作家心理“罗曼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214页。
⑦ 何帆等编《现代小说题材与技巧》,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05页。
⑧ 让-皮埃尔·理查著、顾嘉琛译《文学与感觉》,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1页。
⑨ 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127页。
⑩ 阿·汤因比、池田大作著、荀春生等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76页。
(11) 见王忠琪等译《法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1-102页。
(12) 参见《现代小说题材与技巧》一书。
(13) 汪曾祺《小说陈言》,《小说选刊》1989年第1期第111页。
(14) 见《怎么写》,1987年6月27日《文艺报》。
(15) 参见郑敏《我们的新诗遇到了什么问题?》,《诗探索》1994年第1期。
(16) 见《金克木小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
(17) 参见《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2期第34页。
(18) 转引自《作品与争鸣》1992年第4期第29页。
(19) 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文学理论参考资料》,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01-402页。
标签:人生哲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艺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哲学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