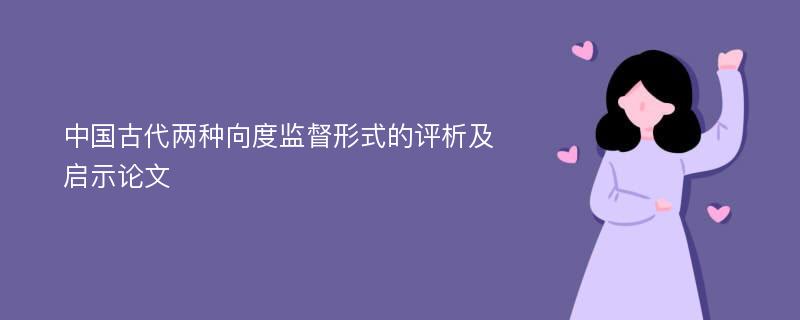
中国古代两种向度监督形式的评析及启示
于 学 强
(聊城大学 廉政研究中心,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 中国古代监督思想强调异体力量对权力制约,由此衍生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监督两种向度迥异的监督形式。自上而下的监督在中国有雄厚的历史根基,具有绝对性、全方位性的特征,受到普遍关注。相比而言,自下而上的监督在事实上往往被忽视,呈现定位虚高、手段多样,但成效不佳的状况。中国古代监督思想为现代监督提供有益启示:监督要靠监督者的自我觉悟,更要靠制度力量;自上而下的监督较自下而上的监督更有成效。汲取中国古代监督思想的合理成分,推进中国当下监督制度建设,既要重视自下而上的监督,也要关注自上而下的监督。
关键词: 古代;监督形式;巡视;启示
中国古代监督思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了深厚的监督思想,不同时代的统治者往往汲取其中有利于统治的成分加以发挥和实践,建立特定时代的监督制度,有效地推进了本朝代政治生活的有序化。中国古代监督思想内容丰富,不仅对于特定时代的政治发展有积极作用,对今天完善监督制度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中国古代两种向度监督形式的评析
中国古代监督思想强调异体力量对权力制约,商鞅最早论及异体监督,提出“夫事同体一者,相监不可”(《商君书·禁使》)思想,并由此衍生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监督两种向度迥异的监督形式。为了巩固和维护家天下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古代非常重视自上而下的监督形式。相比而言,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往往被忽视。
(一)自上而下的监督:根基深厚、特征突出、影响广泛
自上而下的监督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国家建制之前。夏之前的尧舜禹时代,就已经萌生了一些朴素的治理思想,其中内含自上而下的监督理念。任何组织的存在,都以个体遵循组织设置的规矩为前提的。为此,加大对组织个体遵循规矩的监控是保障组织规矩落实、确保组织存在和富有生命力的重要条件。中国古代人已经具备这方面智慧,不仅在社会实践中形成惯例约束,还形成相对制度化的监控手段。如根据史书记载,舜时便形成“五载一巡狩”(《尚书·舜典》)的巡察惯例,还设有专司收集民情的官员,逐渐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巡视思想。自国家建立以后,这一思想得到贯彻、发展和不断完善,并通过健全制度加以落实。
自上而下的监督在中国有雄厚的历史根基。任何政治思想都是建立于特定政治架构的设计理念之上,中国古代监督思想也是如此。自夏以来,禅让制为世袭制取代,伴随周朝宗法制度的建立,中国政治社会开始走上依靠血缘辈分的自然序列形成的秩序,从而进入家国同构的时代。所谓家国同构,就是家与国,尤其是君权与父权相互为用,即国家的统治秩序是家的伦理秩序的延展,国内部关系是家内部关系的推广与应用。在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荀子曾言:“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杆头而覆胸腹也。”(《荀子·议兵》)韩非子同样讲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这样,每个‘家’内的家长对成员的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为‘家天下’专制皇帝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在每个家庭内生了根,找到了它的对应物,从而产生了认同、归属感,使它的统治者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1]周初统治者提出君王对诸侯和百官进行监督控制的思想,“诸侯不命于天子,则不成为君”(《诗经·唐风·无衣》),强调诸侯只有经过周天子的册命才能获得权力与地位。进入封建社会之后,皇帝更是将君臣父子关系应用于治国理政之中,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君父,所有黎民百姓都是他的子民。同时。统治者还将家中之孝与国中之忠联系起来,达成对臣子与社会的层层控制。所以,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之中,以上对下以监督控制为主,下对上则主要只有服从的份儿。“由于强调上对下的绝对控制与役使,使上级权力相对而言无限广大,同时缺少来自平行和下级的监督,权力往往不受约束,很容易造成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甚至敲诈勒索。”[1]
中国古代自上而下的监督具有绝对性、全方位性的特征。“封建时代的监察监督制度,不是人民对政府官吏的监察,更不是人民对最高权力的拥有者——皇帝的监督,而是皇帝对臣民的监视。”[2]皇帝对于臣民的监视主要通过法律的、武力的和教育的手段,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层次:一是皇帝对于大臣们的监视;二是皇帝对于子民的监视。察吏为求治之本。“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吕氏春秋·知度》)。在中国古代皇权社会中,非常注重对官吏的控制,并由此建立起一整套纠察百官善恶与政治得失的监察体系。皇权对官员的监视又可分为两类,首先是皇权对官员的直接监督,即通过皇帝公开到地方巡视工作,或者隐蔽性的微服私访来了解下属官员对自己的忠诚度,以及他们的政绩情况;其次是皇权对官员的间接监督,即皇权通过利用其掌握的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对官员进行监督,这些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既包括受皇权规制的庞大的监督体系,也包括一些底层鸣冤渠道的设置,以及利用百姓对官员的不满来制约官吏。皇帝治民方式多样,为了统治需要各种治理监视手段多以爱民教民姿态呈现,如倡导“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诸身,赋敛如取于已,此爱民之道也”(《文韬·国务》),“民,有孝慈者爱敬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文韬·盈虚》)等。
中国古代强调自上而下的监督,弱化了自下而上的监督。在家国同构理念下,中国古代赋予了家长与皇帝无限的权力,而家长制在国家体制中的集中体现是皇权至上和政治结构中的以官为本、以官为尊、以官为贵和以官为上的官本位思想。再加上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性善论的影响,在政治制度设计方面强调皇帝与官员的自我修养,将他们假定为有仁德之人,从而也为其权力不受监控找到了理论基础。由此,在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中,皇权至上从根本意义上讲就是皇权不受约束。虽然,在不同朝代曾设置过谏诤之官,针对皇帝过错加以控制。但是,这种控制受制于两方面影响:一是皇帝是否愿意受制于人,是否清明;二是谏诤者有无勇气。如杨广曾放言:“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新唐书·吴兢传》),结果“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贞观政要·求谏》)。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开明皇帝也难以保证谏诤的有效性,比如相对开明的唐太宗也曾萌生扑杀强谏之人魏征的念头。所以,从历史实践来看,谏诤之士的设置无以控制皇权,根本就形不成对皇权的控制。同样,官本位思想盛行也使得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僚权力在同级中或民众中得不到有效监管。“‘官本位’就是指包括人们的思想意识、行为取向和制度安排在内,一切都以官为中心,以官为出发点和归宿。”[3]基于儒家伦理政治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且“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常要求,以及“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化,导致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固化。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官员自身有绝对的优越感,其权力除了受制于上之外,社会和民众对权力的监督基本上不存在。
(二)自下而上的监督:定位虚高、形式多样、效果不佳
古代自下而上的监督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政治体制之内的下级对上级,乃至皇权的监督;二是民众对于各级官吏的检举与讨伐。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之中十分注意下对上的批评与建议,尤其是针对皇帝和决策机关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承担这种职责的主要是谏诤之官,并由这类官员与御史监察配合形成比较封闭的监督体系。“谏诤制度可以理解为一种监督权的体制内共享,以规正君主不当决策或不妥行为为己任的谏诤官或谏官或言官能够分享一定的监督权力,这是一种内部分权制度。”[7]结合自下而上的监督,尤其是中国古代谏诤制度看当时的监督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9]〔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历史法学派的基本思想[M].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实际上,中国古代不是完全漠视自下而上的监督,在其庞大的监督体系中也存在这种监督形式,而且开明人士甚至皇帝对这类监督的定位较高。管仲早就提出以民为本的观点,认为帝王统治必须体现合乎民心。为此,帝王应广开言路,听取臣民意见与诽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管仲·小称》)君主只有“以天下之耳听”(《管仲·九守》),才能使政策合乎民心。后来,魏征针对君主治国提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思想。而同时代的唐太宗亦要求自己“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同时要求群臣“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贞观政要·求谏》)。
“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监督与控制,没有监督与控制的权力必将导致专制。”[4]543总体而言,“在中国古代,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对权力的监督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监督,缺少自下而上的监督,同时也缺乏横向的、对等的权力实体之间的平等性监督。”[5]109从社会稳定发展的视角看,“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那么不论‘治官’制度如何发达,它都不可能从源头上控制腐败。这是由人的本性及其固有的局限性所决定的。纵然高层领导有意愿消除腐败,他们仍然有极大的困难弄清楚哪些下级官员是贤明的而应受到提拔。”[6]385—386
无疑,将自我监督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是靠不住的,这正如西方将政治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一样。从社会实践来看,人性的善恶不可僵化地予以认识,不能说一个人生来就是善的或恶的,更不能讲一个人的善恶是伴随一生的。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对恶人加以改造,也没有必要开展各类德育活动以培养和引导人们向善。从中国古代政治实践来看,由于将人性善作为政治制度设计的理论假设,导致对好人政治和清官政治的依赖,而忽视了制度对于限制恶人的考量,结果导致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中出现带有悖论性的政治现象:“主张人性本善的中国人,却让绵延几千年的封建皇权制度为自己造出了一个非常缺乏人道,非常不善的官场化社会。”[11]3这种非常缺乏人道、非常不善的官场化社会表现在很多方面。《中国丑史》从叛乱史、政界史、皇家史、刑部史、黑帮史、青楼史、婚俗史、食人史、古墓史十个大的方面全面呈现了崇尚人性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丑陋的一面,尤其是为了夺取权力可以不顾亲情,如曹氏兄弟相争,雍正杀兄害弟;为了巩固权力可以实施铜热炮烙、剖心掏腑、烹人煮肉、铁钩抽肠等,根本谈不上性善,更谈不上以性善为假设的制度架构能够带来良政。[12]1—787
采用SPSS19.0对本文涉及到的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及处理,本次研究中的计数治疗采用n及%表示,并用t值进行检验,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修建智慧楼宇,实现绿色校园 在很多高校,智慧楼宇可将建筑物的电力、照明、空调、排水、消防、弱电和安保等自动化地进行集中监视、控制和管理,为用户提供安全舒适、便捷高效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改变以往的教学楼使用效率不高,有时拥挤、有时闲置,中央空调、照明、电器等能源没有得到及时合理控制,造成很大浪费的情况。通过建设智能教学楼,使整个系统和各种设备处在最佳的工作状态,并保证系统运行的经济性,以及管理的现代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实现能耗的有效控制,减少能源浪费,实现绿色校园,提升和改善师生的校园生活品质。
刘莉在清理到一个巨大的纸箱时,发现了异常。寄存牌上标识:201207014335,注明:衣物。寄存时间3天。按时间计已经过了1天,这个纸箱放在行李架的第二层。但最奇怪的是,纸箱的底部都湿了,还在滴滴答答地流出液体,将放在一层的一个行李箱都滴湿了,流到地上,形成一滩难看的印迹。刘莉拿起拖把去拖,却又在瓷砖地面上形成了一道暗红的痕迹,更要命的是阵阵恶臭扑面而来。
除了体制内对于皇权的各类监督之外,中国古代开明人士也重视民众对于各级官吏乃至皇帝的检举与讨伐,开明君主也注重倾听民众的呼声。周召公就曾针对周厉王不能容忍百姓提意见和发表政论看法,甚至对于妄议国政的人大开杀戒提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国语·周语上》)。儒家思想代表孔子强调民众监督的正当性,如“子路问事君。子曰: 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提出“可与言而不与之言, 失人,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的思想。孟子不仅强调民众进谏的必要性,而且表达进谏的态度也应“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从政治实践来看,所谓登闻鼓、邀车驾、设匦函、立肺石等都是为民众的检举讨伐开辟路径的做法与制度。这种思想与对应的制度设置,虽然解决了民众的一些冤情,但总体上也不能普遍反映民众的心声,不能实现对于上面权力的真正监控。
二、中国古代两种向度监督形式的启示
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监督思想可以发现,与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相比,中国古代社会强调政治主体个人的道德约束而非法律约束,关注自上而下的监督而非民主监督。中国古代监督思想体现出来的特点影响了古代政治发展,也为现代监督提供有益启示。
(一)监督要靠监督者的自我觉悟更要靠制度力量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人性善”。基于此,在政治思想与相应的制度设计中特别强调君子施政,以德治国,认为统治者都是善良的,具有自我觉悟与反思能力,能够通过自我修养、自我反思造就良好的政治生态。“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是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9]6所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0]1,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监督力量变得不怎么重要,如果说有监督,也是更多地体现在统治者自我反省这个方面。
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沉思“自我觉悟—自律”与“制度力量—他律”的辩证关系。自律是基于内心的认同,但是一个人的内心是个变量,基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和自身认识水平的提升,一个人对同一事务的态度可能出现不同,这种变化既体现在同一时期对同一事务的态度的变化,也体现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事务态度的转变。所以,一个人可能经过自省自律使自己的认识、态度和行为与社会发展要求同向;也可能经过所谓自省与自律走向社会的反面。同时,自省与自律是柔性的,不同的人不尽相同。所以,自省与自律无论是对一个人,还是对社会上的所有人都不可作为社会发展的完全依赖。相反,特定时期的制度设定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和期待的,而且制度与自省自律相比是硬性的、一贯的,无论对于什么样的人,无论在什么时期,只要制度没有发生变化,其约束力就是公平且实在的。所以,监督要靠自我觉悟,但是,这种自我觉悟的方向性需要制度引领和规约,同时制度的刚性特点显示,依赖制度监督较之自觉自律更加可靠且可行。当今民主政治条件下,需要好人政治与好的作风,需要强化政治人的道德约束和自省自律,更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形成好的政治生态环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进而在政治领域进一步规约好人和规避坏人。
首先,中国古代历代明君非常重视吸纳建议,给自下而上监督很高的定位。中国古代强调对下级的控制,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力,也注重保障下属建议献策和一定监察督导之权。商汤不仅认识到,“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尚书·汤诰》),也提出“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史记·殷本纪》),要求自己与官僚群体都要接受来自臣民的监督。而后,中国古代关于民众监督对于王权支撑的认识更加自觉,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的思想。中国历史上的朝议、谏诤制度就体现这种自下而上的监督思想。秦汉时期确立了朝议制度,“朝议在制度上为政治决策过程安排了一个相对理性协商、多人互动的环节,使大臣有机会对君主提出不同的意见,有助于弥补君主政体中个人政治决策的不足,是一种避免皇帝重大决定或决策出错的防范机制。”[7]而唐代封驳制度使有封驳权的中书舍人或门下省,可以对出现问题的诏书予以驳回,即所谓“不经凤阁鸾台,何谓为敕”(《新唐书·刘臣道篇》),更是直接体现了对皇权的一种监督。与朝议制度与封驳制度相比,中国古代的谏诤制度以及对这一制度的重视更加凸显。一方面,最高统治者认识到谏诤的重要意义,给予谏诤者较高的政治地位。“尧、舜、禹、汤、文、武,此六君者,天下盛王也,莫不从谏以辅德,询众以成功。”(《奉天论前所答奏未施行状》)所以,古代提出“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官”(《官制门·台谏》),认为“士逢有道之君,则顺其令;逢无道之君,则争其不义”(《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敢谏君之过、禁君之非,才是“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荀子·臣道篇》)。另一方面,要求最高统治者要有虚心接受谏诤的胸怀,应“任贤良,受谏诤”(《贞观政要·政体》)。朱元璋提出,“人主治天下,进贤纳谏二者,真切要事也。”(《明天祖实录》卷150)因为皇帝“不能无过举”(明天祖实录》卷254),需要“有献替之臣,忠谏之士日处左右,以拾遗补阙”(《明天祖实录》卷100)。对于谏诤者,要“待之以礼,煦之以和,虚心以尽其言,端意以详其理”(《奉天论前所答奏未施行状》),要“谅直者嘉之,讦犯者义之,愚浅者恕之,狂诞者容之”(《兴元论解姜公辅状》)。
中国古代监督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制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主张。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性善论,强调伦理道德的力量,古代政治也打上深深的伦理色彩,尤其是突出政治领域中人的自我反省能力,强调统治者内圣而后外王。内圣以道德理性为前提,强调道德的自我力量,外王以社会价值为导向,突出道德力量的外在表现和社会影响。对于统治者而言,古人认为善政之人本身也是道德高尚的人,符合内圣标准,这是他们从政达到外王的前提要件;同时,这些有道德情怀的人在从政之后,也容易通过自我道德规约达到善政。古人曾结合道德自律倡言君子何以达到修己及人的目标:“夫古之君子,进则救民,退则修己,其心一也。盖修己者必能救民,救民者必本于修己”。(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一《与戴太守》)从具体修身手段的选择方面,古人非常重视慎独,注重严格自律的作用,并将慎独作为一项道德要求和道德修养,也视为一种道德境界,指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慎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见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中庸》)。“人心内重,内重则外轻。苟内轻,必外重,好名好利,无所不重。”(《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即保持内心不受外物影响,才能符合道德要求。
(二)自上而下的监督较自下而上的监督更有成效
中国古代王权社会,与现代民主政治社会性质完全不同,人的政治素养也完全不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统治者为了维系自身的政治地位,强调上对下的监督和控制,在思想意识与制度设计方面,自上而下的监督比自下而上的监督更受重视,也更健全。从监督的政治效果来看,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条件下的自上而下监控,不仅有效地维系了王权统治,确保统治集团内部的等级地位及尊严,也有效维护了统治者的权威,保障了社会的相对稳定。
其次,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不同时段呈现自下而上监督手段多样化的思想。黄帝和尧舜禹时期就有重视自下而上监督的表达,如黄帝曾设“明台”采纳民意;“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吕氏春秋·自知篇》);夏禹“悬钟、鼓、铎、磐、靶”五种乐器,都是听谏工具。进入皇权社会之后,伴随御史监察制度的发展完善,西汉时期开始关注自下而上的监督,尤其是对皇帝本人的监督并开始设置谏官,后代尤其是唐朝,谏官得到重视并予以较大的职责。比如唐代谏官有如下职责:一是谏议之责,谏官对于时政的得失、皇帝的奢侈,以及滥施刑罚等都有权提出意见,予以制止。二是封驳之责,谏官对于皇帝的诏命、有关部门制定的政策措施,以及大臣的奏章等,如认为有不妥,均有权予以驳回,建议予以改正。三是知起居事之责,谏官通过记录皇帝的言行,以皇帝与大臣对国家大政的讨论,监督皇帝与大臣。“武则天时期还于朝堂设置四匦(箱子),用于接受臣民议论时政、陈诉冤屈、治国谋略等方面的投书,由谏官负责每晚收集奏报。”[8]131唐朝的繁荣不能说与谏官制度无关。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提出正确对待谏诤的方法:一是谏当则赏,不当亦不罚。指出“言而是也有褒奖之美,言而非也无谴责之意”(《明天祖实录》卷100)。二是对进谏内容予以保密。他担心人有后顾之忧而不敢进谏,下了一道诏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朕前”(《明天祖实录》卷113)。但是,中国古代谏官制度因是否遭遇明主而呈现不确定性和非常态性,总体来看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它不仅出现得晚,而且消失得也早,从宋、元开始,谏官制度逐渐衰微,直至完全取消。
同时,古代监督体制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自上而下的监督方面,中国古代不仅在监督内容上基本实现了全覆盖,而且创新了监督手段与机制,特别是创设了各种各样的巡视监督。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督一方面有效地控制了下属,另一方面也容易培植特定的监督群体,使这些人的权力成为超乎特定范围内权力的最大权力。同样,如若对这种监督控制的权力缺乏有效监控,也容易衍生新的腐败。从古代巡视监察实践来看,一些巡视监察官员借助上层赋予的极大的权力,一朝权在手,便将令来行,鱼肉巡视客体,公报私仇的情况并不鲜见。虽然,当初上层赋权可能是基于对他们忠诚度或能力的信任,但一旦这些人走上工作岗位,就可能尝到权力的甜头,对皇权的忠诚往往会让位个人利益的诉求。这样,他们便会将上层赋权的问题丢到一边,甚至为了捞取个人利益,完全违背设置他们这些官僚机构的上层初衷。另一方面,作为被巡视监察的官员,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往往也比较积极地笼络或贿赂这些巡视监察人员,甚至将这些人员中的清廉之士拉下水,形成一种对上阳奉阴违、曲意逢迎,对下颐指气使、沆瀣一气,一并侵占皇家的便宜或侵吞百姓的利益。
真人秀是电视娱乐节目为提高收视率与知名度,通过邀请体育明星、娱乐明星等参与录制的节目,像《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中国星跳跃》等,都属于真人秀的体育参与方式转型范畴,即“从直接参与变为间接吸引参与”、“从单纯的运动员参与变为名人代言参与”、“从中规中矩的体育变为时尚有序的娱乐”、“从个体参与变为亲子参与”等,将体育搬上荧屏,使得体育更加生活化。在观看真人秀体育节目时,大众能够潜移默化地感受到参与体育活动的乐趣,有助于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其次,自下而上的监督方面,虽然在思想理念与制度设计方面关注到了这种监督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甚至针对皇权提出了“纳谏为圣, 拒谏为昏”的命题,“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 而不责其辩。”(《淮南子·主术训》)但是,总体而言,这类监督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设计中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并且从根本上讲,这种对自下而上监督的重视是建基于维护上方的统治,而不是对于下级权利的尊重。比如,民众对于权力的监督要有成效,不仅是取决于监督客体的意愿,能够创造条件使监督主体敢于监督。因为民众监督是对统治者权威的挑战,如果没有在制度方面创设好的条件保障监督主体的利益与权利,就难以真正动员他们积极主动地从事监督。从古代政治实践来看,民众主动监督较为鲜见,除非有重大冤情,民众是不怎么去告官的,因为缺乏制度保障下的告官成功机率甚小。同样,下级对于上级权力的监督如果缺乏相应保障条件,下级监督的动能也不大,即便有动能也不一定真正有效。又如,民众监督的前提不仅需要有自身权利保障与利益保障问题,也需要监督对象公开权力行使的立意、过程与成效。如果在制度方面没有政令公开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公开,民众与下属官员对上级的监督都无计可行,因为不公开就无以形成对错的判断依据,不知对错就无以监督和纠偏。
汲取中国古代监督思想的合理成分,推进中国当下监督制度建设既要重视自下而上的监督,也要关注自上而下的监督。从社会性质来讲,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国家,从最终意义上讲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源泉,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和体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监督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十分重视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来完善和提升民主监督的层次和效果,保障民众政治权利的实现。另一方面的现实是,在当今中国政治条件下,就某一特定政治权力授受关系来看,大部分政务人员的权力在事实上还是来自上一层级。这样,在最终意义上对人民负责的权力,在现实中的体现是对上级领导负责,且受制于上级领导的监督。由于政治主体对于权力授受现实关系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其最终意义的关注度,最终导致上层权力的监督力量和效果远远大于民众监督。
正是由此,在现实意义上讲,我们推进中国政治监督制度的科学化建设,一方面要强化民主监督,以此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上级监督以在现实上强化权力运作的有序性,同时又利于进一步推进民主监督的发展。所以,加强巡视制度建设科学化,既是强化自上而下监督的需要,也是推进民主监督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
在数学实验课上,学生是在新的情境、实验材料下进行推断、创新并且运用,成长的是思维、信念、好奇心等属于个人的隐性知识。因此,教师在课堂中不需要多引导,也不需要特别的课堂教学艺术,学生巴不得教师少讲话,自己早点动手。事实上,学生往往还能玩出更多新花样,常常令教师自叹不如。在实验课上,教师也不用过多判断结果对不对,这由实验结果说了算。因此,对于数学实验课我们主要采用两条原则性的教学策略。
参考文献:
[1]谢长征,李敏.论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与腐败的关系[J].广西社会科学,2003,(11).
[2]袁刚.封建皇权和中国古代的监察监督[J].法学杂志,2000,(3).
[3]李成言,肖俊奇.社会性官僚政治:中国官本位传统之源[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4)上.
[4]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上)[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5]丁以升.法治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6]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7]岑树海.传统中国朝议、谏诤和巡视:三种监察机制探究及其现代启示——基于内向分权与外向分权的解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8,(1).
[8]吴晓玲,等.中国法制史新编[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9]朱哲.中国文化讲义[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10]乌恩溥.四书译注[M].长春:吉林出版社,1990.
[11]黎鸣.中国人性分析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曹金洪.中国丑史[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
An Analysis of the Two Forms of Dimensional Supervis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Its Modern Enlightenment
YU Xue-qiang
(Anti -Corruption Research Center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China )
Abstract : The ancient Chinese supervising thought emphasizes the restriction of power by the foreign body, which is derived from the top-down supervision and the bottom-up supervision. Top-down supervision has a strong historical foundation in China, and it has absolute and all-round characteristics and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contrast, bottom-up supervision is often overlooked in fact, leadng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 positioning is high and the means are diverse, but the results are not satisfactory. The ancient Chinese supervision thoughts provide us with 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modern supervision: supervision relies on the supervisor's self-realization and depends on institutional power; top-down supervision is more effective than bottom-up supervision. To draw on the rational elements of China's ancient supervision thought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current supervision system,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both bottom-up supervision and top-down supervision.
Key words : ancient times; supervision form; inspection; enlightenment
收稿日期: 2019- 03- 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DJ036)
作者简介: 于学强,男,山东茌平人,聊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 D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5957( 2019) 03- 0045- 06
标签:古代论文; 监督形式论文; 巡视论文; 启示论文; 聊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