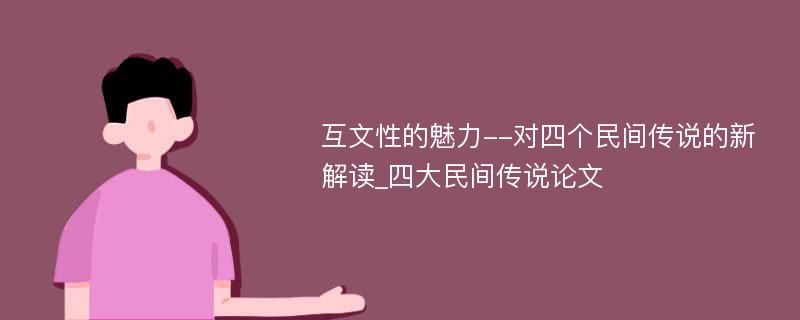
互文的魅力:四大民间传说新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间传说论文,魅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4)04-0205-10 本文为《四部古典小说新论》的姊妹篇。[1](P162)按照中国民间文学界的共识,四大民间传说包括《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与《牛郎织女》这四个故事。 如果说四大古典小说之间存在着令人诧异的结构相似,那么四大传说更像是一个天然契合的有机序列。像四大小说一样,四大传说也有其共同的深层结构,用列维-斯特劳斯的模式来表述,或许就是“镇压/反抗”与“禁锢/自由”这样两组相互对立的范畴。但本文无意重作冯妇,以四大传说为对象再作一番深层叙述结构的追踪剖析,因为民间故事本身就是一目了然“透明见底”的。真正值得深入研究的,我认为还是四大传说之间的“间性”。 “间性”又称“互文性”(transtextuality),这里指的是单个故事与所属故事群中其他故事之间的差异与相似,亦即故事“家族”成员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哈罗德·布鲁姆说“文本的意义取决于文本间性”:“为要解释一首诗,你必须解释它与别的诗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该诗生气勃勃地创造意义的地方,这是一种家庭的差异,一首诗正是借此差异来抵偿另一首诗的。”[2](P31) “间性”这个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不难接受,因为我们从小就习惯了“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之类“互文见义”的表述,把握“互文”的关键在于将分开来的表述当成一个整体,这样我们就不会以为“东市”才有“骏马”,“西市”才有“鞍鞯”。同理,把握四大传说的关键在于洞察其“间性”——将四个故事看作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序列,唯有让这四个故事彼此印证,相互映发,其隐含的意义才能真正被召唤出来。从“间性”这个角度观察,四大传说之间的配合相当默契。它们固然是四个不同的故事,但是由于那些复杂微妙的“异中之同”,它们给人的印象就像是同一故事的不同变体。这就是四大传说的“互文见义”功能。它们之所以能从浩如烟海的民间故事中脱颖而出,或者说为什么中国的四大传说偏偏是它们而不是别的什么故事,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一个被“间性”牢牢吸附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为了更好地说明“间性”,本文不得不先对这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逐一讨论,然后再从“见木”回到“见林”状态上来。当然“见木”与“见林”也并非绝对相斥,在集中剖析一个传说时,也不妨让其他传说保持一种若隐若显的“在场”状态。 一、《白蛇传》——药物与变化 白蛇传说中弥漫着浓郁的药香。现代文论把故事的讲述比喻成织物的“编织”。“编织”中需要有东西来穿针引线,白蛇传说中起这种作用的就是药物。故事的大部分事件发生于药店,许仙的身份是药店学徒,白素贞因服用药酒(雄黄酒)而露出蛇精原形,后来又寻来药草(灵芝草)让吓死过去的许仙恢复生命。如果没有药物在其中充当道具,故事的许多事件无从演绎与推进。丁乃通对蛇女型故事的来龙去脉有过详细考论,认为“这个故事首先在纪元前后流传于西亚或中亚的一个不崇拜蛇的民族中”,传入中国后“经过了重大的修正,以适应中国的文化”。[3](P15)药物因素的添加显然属于他所说的“重大的修正”,因为中医药是典型的中国国粹,我们是世界上最善于以植物、动物和矿物入药的民族。在中药的采集、炮制与使用过程中,贯穿着万物相互依存的思想,中医相信恰当地使用这些药物,能够激发人的生命活力,改变身体内部的各项机能。 雄黄酒和灵芝草的药理功能正好相反。雄黄的主要成分为硫化砷,是提炼砒霜的主要原料,据《抱朴子》和《本草纲目》等记载,雄黄能杀毒驱邪,对夏日多见的蛇虫之患尤为有效。故事中法海在端午期间唆使许仙逼妻子饮下雄黄酒,目的是为了“以毒攻毒”,使蛇精的变化之术失效。灵芝的难能可贵之处是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临床使用有健神强心、延缓衰老、提升免疫能力等效果,因此在古代传说中,灵芝成了一种浓缩生命精华的药物,它不仅能使神仙长生不老,还可以让凡人起死回生。除了“有毒”和“无毒”之外,雄黄和灵芝还有更深一层的区别:如果说有毒的雄黄能使美女变回丑物,那么无毒的灵芝可以美化容颜——《山海经·中山经》提到帝女死后“化为瑶草”(灵芝又名瑶草),“服之媚于人”。通过这棵可以美容的瑶草,白蛇传说响应了古代文学中著名的巫山神女故事——《太平御览》卷二九九引《襄阳耆旧记》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台,精魂依草,为茎之,媚而服焉,则与梦期,所谓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虽然故事中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表明白素贞服用过灵芝草,但从许仙惊厥后她立即想到寻找药草这一反应看,这位在大自然中修炼得道的蛇精应该非常熟悉这种药物,她的神通与灵芝草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然的联系。 雄黄酒和灵芝草的迥然相异,衍生出故事中一系列矛盾对立与斗争。法海用雄黄酒让白素贞露出怪物的丑形,没想到却使许仙由生入死;白素贞为救丈夫不惜冒死盗取灵芝草,这一事件使其被蛇精身份遮蔽的善良获得现象学所谓的“绽放”机会,从而改变了人们对她的印象。药物之为药物,在于它能带来肉体和精神上的某种改变。与雄黄酒扮演的负面角色不同,灵芝草在故事中起着一种“正能量”的作用:对许仙来说它有起死回生之功,对白素贞来说它又有化丑为美之效——白素贞的本相固然是面目狰狞的异类,但其心灵美却因“盗草”的执着而大放光彩,此举感动了灵芝草的主人南极仙翁,也使死而复生的许仙对她有了新的认识。在这场由雄黄酒和灵芝草引发的冲突中,生与死、美与丑、善与恶、正统和异类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各自都实现了向自己对立面的转变。 按照经典叙事学的理论,决定冲突胜负的应当是故事世界中的仲裁者。南极仙翁在故事中充其量只是一个次级仲裁者,因为他只能决定灵芝草的归属,对于“盗草”之后的事件进程他已无能为力。南极仙翁属于道教人物,按说他也是正统队伍中的一员,但其法力远逊于法海背后的佛教大人物。《西游记》等故事已经告诉我们,道教出身的孙悟空可以大闹天宫,却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无论是太上老君还是玉皇大帝都不能与佛祖平起平坐。就此意义而言,法海在故事中是代表“正统中的正统”向异类宣战,不管白素贞如何通过“水漫金山”之类的手段奋起反抗,法海后面的仲裁者最终一定会出手干预,因此故事的结局必定是蛇精伏法,被仲裁者用强力镇压于佛塔之下。不过,法力的胜利不等于道德的胜利,这一结局明显违背了佛教本身的“众生平等”原则——作为蛇精的白素贞也有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任何生灵的心灵自由都不应该遭到如此粗暴的践踏。 或许是由于此种考虑,国人在讲述白蛇传说时多半还会添上一个尾声,这就是让法海变成人人得而食之的丑陋螃蟹。公道自在人心,善恶报应不爽,“故事外”的这种绝妙安排体现了更高的伦理取位,原先扭曲的价值轴至此被拉直,美与丑均获得自身的安顿。与此同时,故事的动物语义也因这一尾声而臻于平衡:外表骇人的蛇精升华成心灵美丽的女性,道貌岸然的法师变形为面目可憎的螃蟹。民间故事其实只是看起来简单,在“蛇→美女”/“僧→螃蟹”这对变化范畴中,隐藏着生命不断循环的深刻思想:人与万物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众生之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本体论界限。 以上讨论已于无形之中由药物转到了变化。再重要的道具也只是道具,药物在白蛇传说中的作用就是为了引出变化,如果说药物是故事中的引子,那么变化便是故事的关键——诺思洛普·弗莱说“传奇中标准的逃脱手段是身份转变”[4](P152)。变化不仅出现于《白蛇传》中,在其他三大传说中也有程度不同的存在:祝英台先是女扮男装,后又与梁山伯一道化蝶;织女开始隐瞒了自己的天女身份,后来又与牛郎双双变为星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孟姜女传说中,女主人公生于葫芦之中,投海殉夫之后又变成白鱼逃避进一步迫害。这些变化的共同之处,是人物变成日常生活中的司空见惯之物。它们体现了民间传说的普世性质,其“易见性”又有助于传说本身的流行与传播。世世代代的故事讲述人正是利用这一点来为故事“起兴”,例如,到了把酒持螯的时节,准备讲白蛇传说的爷爷会用筷子指着餐桌上的螃蟹对孙子说:“你知道这东西是怎么来的吗?” 不过四大传说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解释事物的由来。人物的变化实际上是身份或状态的变化,发生这种变化为的是跨越形形色色的鸿沟:蛇精变形跨越了人妖之隔,祝英台易服跨越了男女之隔,孟姜女投海跨越了生死之隔,织女下嫁跨越了仙凡之隔——她与牛郎变星还跨越了动静(瞬间与永恒)之隔。我们在后文中还要提到,四大传说全是爱情故事,故事中行动的主动方均为追求变化的女性,她们或希望获得与对方平等的身份(白素贞、祝英台和织女),或是要进入与对方同样的状态(孟姜女以死殉夫),这类“趋同”的愿望不啻是事件演进的驱动器。而对变化所做的这种“集体讲述”,包括反复讲述与多角度讲述,构成了叙事语义中的“互文见义”,四大传说的“间性”从中可见一斑。 如果把考察范围放大,还会看到“互文”关系不只存在于四大传说之间。我们的古人特别喜欢讲述诸如此类的“趋同”故事,故事主人公的原身既有动物(鸟兽蛇虫)和植物(花精树魅),也有地下的鬼魂与天上的神仙。在这些被称为人妖恋、人鬼恋、人神恋的故事当中,无一例外都有变化发生,变化成了异类与人交往的先决条件。而将变化演绎得最精彩的当属白蛇故事,没有哪个故事能将变化呈现得如此不可思议:故事的“妖氛”到最后被稀释殆尽,外部形骸的可憎可怖彻底让位于内在心灵的可爱可亲。至此我们明白,白蛇传说能够进入四大传说之列,全仗成千上万同类故事的“顶托”,四大传说的产生乃是无数同类故事自动筛选淘汰的结果。 二、《梁山伯与祝英台》——翅膀与自由 梁祝传说中也有变化,这变化不像白蛇那样由异类变成人,而是到最后由人变为异类——一对翩翩飞舞的蝴蝶。蝴蝶最吸引人之处是其翅膀,没有翅膀就没有无拘无束的自由飞翔。 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提出了困扰女主人公的身份问题:祝英台身为女性不能上学,被剥夺了像男性那样的受教育权利。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是乔装打扮,穿上男性的衣衫之后,祝英台顺利实现了自己的意愿。但是接下来又有新问题产生,祝英台对同窗共读的梁山伯产生了感情,解决这个问题可不像女扮男装那样容易——没有父母之言与媒妁之命,旧时男女要实现自由结合难于上青天。在故事的大部分时间内,梁山伯一直处于不明真相的状态,等他明白过来已经是噬脐莫及。故事的最后场景是男女主人公一在坟外一在坟内,然而幽明之隔阻挡不了爱情的力量,一对有情人最后通过化蝶获得了比翼齐飞的自由。 白蛇传说中引起变化的是药物,梁祝传说中反映变化的则为长出了翅膀。作为由爬行动物进化而来的地面物种,人类总是用羡慕的目光注视着天空中振翼翩飞的生灵,长有翅膀的鸟类与昆虫似乎享有比其他物种更多的活动自由。世界各民族的先民大多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转移,他们骨子里都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拥有其他物种的本领。《山海经·北山经》说“炎帝之少女”女娃死后变为精卫,这个神话故事说明我们祖先很早就萌发了凌空御风的想象。不过精卫展翅是为了“衔木石以堙东海”,梁祝化蝶却是为了坚贞不屈的爱情。古代文学中有许多让人物插上翅膀“飞”抵爱情彼岸的故事,它们与梁祝传说之间的关系,就像人妖恋故事之于白蛇传说,也就是说它们乃是“顶托”这两个故事的“群众基础”。《孔雀东南飞》与《搜神记》“韩凭夫妇”故事的结尾几乎完全一样——男女主人公的坟头均出现连理枝与鸳鸯,但两者都未说明鸳鸯是由人物变化而来。李商隐的《咏青陵台》中人物终于长出翅膀——“莫许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据此可认定化蝶结尾定型于汉唐之间。化蝶与化鸟从性质上说属于一类。古代文学中但凡涉及“爱而不得所爱”的叙事,都倾向采用“在天愿为比翼鸟”之类的譬喻。今天的人们在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时,往往也会产生“愿依此日生双翼”的幻想冲动。 故事需要美感,与其他三大传说一样,梁祝传说讲述的也是凄美的爱情。刘再复曾说从《诗经》到当代文学存在着一个不断重复的母题,这就是“爱而不得所爱,但又不能忘其所爱”。[5]梁祝传说极其有力地证明了人是情感的动物,男女主人公的殉情显示出爱情的不可阻挡,故事的全部魅力来自这种“之死靡他”的坚贞与决绝。与梁祝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悲剧也是用年轻人的殉情来彰显精神的自由与爱情的永恒,它们的主题都可以用“爱的战胜”来概括。由于比《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了一个化蝶的结尾,梁祝传说把真爱不朽的思想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美好的事物不会真正死去,自由值得以生命为代价来换取,死亡在爱情面前显得是那样无能为力。 或许是出于这一原因,死后比翼齐飞被认为是极富中国神韵的叙事安排。西方人在向我们学习制瓷技术时,也把一个浪漫的东方爱情故事画上了他们的瓷器,这就是瓷绘界著名的柳树图案故事(willow pattern story)。瓷绘的作者大概通过某种途径听过梁祝传说并为之感动,于是产生了这个引发广泛效仿的创意。由于语言不同造成的阴差阳错,瓷绘上的细节与梁祝传说有所不同,尤其是男女主人公死后不是化蝶而是变为鸽子。但画面上那两对大得不成比例的翅膀完全不像是鸽子所有,这种夸张的处理说明传播过程中局部环节虽有错讹,但故事的精髓——翅膀代表的自由追求并未失落。① 三、《孟姜女哭长城》——眼泪与抗争 药物是白蛇传说的道具,翅膀是梁祝传说的标志,而孟姜女传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女主人公的眼泪。 眼泪代表悲伤,悲伤源于苦难。其他传说中自然也有哭泣,但只有在孟姜女传说中,眼泪被置于如此突出的地位。这或许是因为孟姜女遭遇的苦难太过深重,别的女主人公皆有背景——织女为天孙,白素贞有法力,祝英台出生于大户人家,唯有孟姜女是地地道道的民间女子。役夫之妻的社会身份决定了她的命运要比别人更为悲惨,送寒衣事件透露出她的孤苦无助,所以听到丈夫死讯后她除了痛哭之外别无他能。与其他传说相比,这个故事似乎更具悲剧意味——万喜良的死意味着一切希望都已破灭,因为男女主人公都是既无背景又无神通的普通人,他们生聚的可能性至此不复存在。孟姜女传说的正式名称为“孟姜女哭长城”,其他三个传说的标题都只有人物之名,唯独它多了一个代表主要事件的动词——“哭”。标题是高度浓缩的叙事,这个“哭”字凝聚了故事的精华,强调了它的主题是受苦受难。 讲述孟姜女的苦难,也就是讲述中国古代所有“思妇”的苦难。徭役、战争与饥荒,使多少怨女旷夫处于天各一方的分离状态,可以与孟姜女传说“互文见义”的是历史上那些反映“所思在远道”的篇章,《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如此写道: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古代文学中这类作品为数不少,它们大多遵循“温柔敦厚”的诗教,称得上“怨而不怒”或“哀而不伤”。孟姜女传说与它们不同,女主人公对命运的安排不是逆来顺受地默默流泪,而是用痛彻心扉的啼哭发出抗议。孟姜女之哭最能体现民间文学的格调,草根民众的情绪反应不像上层阶级那样含蓄,他们没有必要控制自己的情感,当背负的苦难沉重到无法继续忍受时,他们会用翻江倒海、惊天动地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痛苦。 被孟姜女哭声崩倒的是长城。长城是隔断的象征,秦始皇当初修建长城,意在用人造屏障隔断北方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侵扰,但在孟姜女传说中,长城的功能是在男女主人公之间形成隔断。其他三个传说中,我们也能发现这种起隔断作用的“负能量”:白蛇传说中的雷峰塔、牛郎织女传说中的银河以及梁祝传说中的坟墓。这些隔断都只是貌似强大,四大传说有一个共同的故事逻辑,这就是主人公最后总能以某种形式战胜这些“负能量”。长城的崩倒在四大传说中最不可思议,因为长城是由海量物质堆积而成,它占据的空间和绵延的长度在地球上无与伦比,卡夫卡有篇小说就把长城写成权力意志的象征,但这样一座建筑巨无霸竟然会因一名民女的啼哭而轰然倾圮!有意思的是,很少有聆听者对这一“不可能”表示过怀疑,这不仅是出于“姑妄言之姑听之”的特定心理,还因为人们在潜意识中确实相信,孟姜女恣情一恸形成的巨大冲击力非长城所能抵御。孟姜女身上汇聚了所有时代一切薄命女子的痛苦,似乎有无数个声音跟着她一道同声悲哭,用《红楼梦》第五回的话来说就是“万艳同悲”和“千红一哭”,因此这哭声具有摧毁一切障碍的神奇力量。 孟姜女传说因其悲剧性质,很容易被纳入所谓“泪水叙事”的范畴,本文认为有必要特别指出,该故事强调的不是诉诸视觉的泪水,而是诉诸听觉的哭声,它从呱呱坠地起就是一个声音事件,其成长和衍变都与听觉有关。“哭夫”的前提是“夫死”,据顾颉刚等人考证,“夫死”最初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关于杞梁妻的一段记述,《礼记·檀弓》想当然地为女主人公增加了“哭夫”行动,接下来《孟子·告子》顺理成章地赋予其“善哭”的本领,而《说苑·善说》则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让其哭声崩倒了齐国的城墙。[6](p2-20)沃尔夫冈·韦尔施认为西方文化是由听觉文化逐步过渡到视觉文化②,马歇尔·麦克卢汉说中国文化仍然是听觉主导的精致文化③,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准确,起源于春秋时代的孟姜女传说称得上听觉叙事的一个早期标本。《说苑·善说》说杞梁妻的哭声产生了“隅为之崩,城为之阨”的地震般后果,我们无法认同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这一叙述透露出古人的听觉敏感,以及他们对声音力量的崇信。即便是在今天,女性的痛哭也是一种颇为有效的抗争武器。 四、牛郎织女传说——银河与怅望 与孟姜女传说不同,牛郎织女传说是一个需要视觉配合的故事。它适宜在夏秋之际的星空之下讲述,这时横亘天际的银河为故事讲述人提供了天然的道具,而聆听者的目光则为银河两岸的牵牛星与织女星牢牢吸引。 由于视觉的原因,银河的隔断作用在这个传说中呈现得最为直观。《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称牛郎织女的处境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四大传说虽说全为“爱而不得所爱”,但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不幸者均有其独特的不幸,这个传说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男女主人公几乎总是处在可望而不可即的怅惘状态。钱锺书在论及《诗经·秦风·蒹葭》的“在水一方”时,曾将怅望状态归入“西洋浪漫主义所谓企慕之情境”,并借清人之语反映怅望者所受的煎熬——“夫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悦益至”。④古往今来不能团圆的有情人太多,用脍炙人口的牛郎织女故事来指代其境况最为相宜,故“牛郎织女”在汉语中又成了“两地分居”的代名词。郑板桥曾说:“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他不知道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牛郎织女”最初的男耕女织内涵已被时光冲淡,后人使用这一成语时主要指涉男女的分离。汉语中大部分成语后面都有一个故事,用到这些成语时相关故事便被“激活”于交流背景之上,汉语因之成为特别适合叙事的美丽语言。 仔细推敲“牛郎织女”一词,我们会发现它还有一重指涉,这就是有情人并非绝对不能聚首,而是这种机会太少太珍贵。织女毕竟是天宫的金枝玉叶,这里的隔断较之其他传说中多了一点弹性,或许是由于王母娘娘用发簪划出银河时没有用尽全力,或许是值守者曲意奉承网开一面,银河上居然每年一度会有鹊桥铺通。婚姻之被称为爱情的坟墓,乃是因为终日厮守带来的审美疲劳,这种情况导致聚少离多的牛郎织女反而成为某些人的羡慕对象。秦观在《鹊桥仙》中说他们的聚首是以少胜多——“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并由此发出“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感叹。从维护爱情的角度看,怅望者所受的煎熬恰恰是情感的“保鲜剂”,被隔断的男女更容易维持彼此之间的美好印象,也不可能像普通的柴米夫妻那样为鸡毛蒜皮之事发生龃龉。所以纳兰性德会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柬友》) 牛郎织女变为隔河怅望的双星,让人想起梁祝传说中比翼齐飞的蝴蝶,两个传说都以变形收尾,不同在于变形后的一静一动。这种差异化的故事处理,体现的正是具有互补意义的“间性”。许多人可能倾向于让有情男女在故事结束时团圆,哪怕是死后化作比翼鸟与连理枝,但牛郎织女最后的隔河怅望更是民间故事天才的神来之笔。每次抬头看见那两颗始终不渝、脉脉无语的星辰,我们心头都会泛起一股酸楚之情。英国浪漫诗人济慈如此讴歌希腊古瓮上的石雕画面: 树下的美少年啊,你无法中断 你的歌,那树木也落不了叶子; 鲁莽的恋人,你永远、永远吻不上, 虽然够接近了——但不必心酸; 她不会老,虽然你不能如愿以偿, 你将永远爱下去,她也永远秀丽 画面上的美少年一直享受着接吻前的甜蜜期待,虽然他总也吻不上恋人的嘴唇,那位年轻的少女也永葆青春与美丽,虽然她注定不能与近在咫尺的情郎执手相牵。这种情况就像镶嵌在天宇之上的牛郎织女,由于瞬间已经变为永恒,他们的爱情花朵永远不会凋谢。 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前述三个传说中的隔断,无论是注定会倒塌的佛塔,还是已经崩裂的坟墓与长城,全都阻挡不住爱情的力量,牛郎织女传说中鹊桥飞架银河,同样突出了“爱的战胜”这个共同主题。按照四大传说的叙事逻辑,有隔断就会有跨越,至于怎样跨越,则是每个传说需要完成的具体设计。不过这些设计也有其必然性。如前所述,四大传说由人和动植物共同演绎而成,万物相互依存的思想在许多民间故事中都有流露,似此让会飞的鸟儿搭起空中的天桥,应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安排。这还不是故事中的动物第一次对人施以援手,牛郎所牵之牛就对主人有过许多帮助,对牛郎来说它已从劳动工具变为亲密伙伴。如果说牛郎与老牛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在织女和鸟儿之间也同样存在。我们不要忘记织女当初就是凭借鸟儿的“羽衣”飞临人间的池塘洗浴,牛郎是按老牛之计窃得羽衣后才得以与织女喜结良缘,⑤所以鹊桥在故事最后出现并不让人觉得突兀。 五、合论:从“见木”回到“见林” 以上四节系对四大传说分而论之,即前文所说的以“见木”为主,本节则对四大传说进行以“见林”为主的合论。如前所述,四大传说虽各有其苦难内容与解脱方式,但它们的共性非常明显——所讲述的都是鹣鲽情深和棒打鸳鸯,其深层冲突皆涉及“身份与变化”、“禁锢与自由”、“镇压与抗争”和“隔断与跨越”。不仅如此,四大传说的相互契合还有如下表现: (一)情节动力均来自女主人公 情节动力与人物愿望关系密切,因为没有愿望就没有行动,愿望像发动机一样推动着故事情节不断朝前演进,导致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四个爱情故事中,全部都是女主人公在主动追求,她们比男主人公更有勇气,而男主人公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白素贞几乎是强迫许仙接受自己的爱,祝英台在男女之情上可谓“先知先觉”,孟姜女千里迢迢为丈夫送去寒衣,织女纡尊降贵下嫁凡夫俗子。这四位女性都有美丽而又坚强的心灵,她们敢于突破身份禁锢,奋起追求自由,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与强大的正统力量抗争,虽然从结果上说这种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但她们对爱情的执着不由人不肃然起敬。这些魅力四射的形象使男主人公显得稍逊一筹,甚至被反衬得黯淡无光:许仙缺乏男子汉应有的气概,梁山伯长时间被蒙在鼓里,万喜良在故事中几乎只是个符号,牛郎的命运完全因织女的到来而改变。当然,男性之力一旦调动起来可能更具能量,但四大传说中女性处于无可置疑的掌控位置,故事中着重展示的是女性的追求,男性在故事中的作用主要是配合与跟从。 由此我们想到歌德《浮士德》结尾的“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弗·雅·普罗普对民间故事的特征有过精辟归纳:“一方面,是它的惊人的多样性,它的五花八门和五光十色;另一方面,是它亦很惊人的单一性,它的重复性。”[8](P18)女性在四大传说中的引领功能,是对这种“单一性”和“重复性”的最好说明,至于为什么四大传说都以“永恒之女性”为主旋律,答案应在叶舒宪等人倡导的女神文化研究之中。[9]早在鸿蒙初辟的旧石器时代,世界多地的人类就用石头和玉器打造出丰乳鼓腹的大母神形象,以此向担负生育与繁衍重任的母亲表示崇敬。迈入文明时代之后,人类的成长仍然离不开母亲温暖的怀抱,女性的厚德载物永远是男性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撑,西方的维纳斯情结自不待言,在我们的女娲、西王母甚至观音故事中,也能察觉到大母神崇拜留下的印痕。据此而言,四大传说中不约而同的女性引领,似乎是由世代传承的文化基因所决定,史前时代的“元叙事”对后世叙事产生的影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小觑的。 (二)伦理取位均与正统观念相悖 与《三国演义》等小说中的宏大叙事不同,四大传说站在民间立场上进行私人叙事,采用的是社会底层的视角,诉说的全为细民百姓的悲欢。四大传说的伦理取位处处与正统观念相悖:佛门不允许异类与人来往,白素贞执意要与许仙结为恩爱夫妻;儒家宣传男女授受不亲,祝英台乔装打扮与男子同窗共读;道教人士希望长生不老悠游自在,织女偏偏向往男耕女织的人间生活;封建帝王以修建长城为宏伟业绩,孟姜女却把它看成邪恶与压迫的象征。四大传说中流露的是一种颠覆性的伦理观念:那些维护既有秩序的等级藩篱与类别屏障,不管是人妖之分还是男女之大防,不管是仙凡之隔还是尊卑之别,在叙述中全都成了被冲击的伪善堤防。那些貌似正确的行为,如拯救被蛇精蛊惑的男子,避免两性交往失慎以及构筑维护帝国安全的城墙等,突然间暴露出违背人性的丑陋一面;而那些在其他叙事中显得冠冕堂皇的人物,如佛门长老与王母娘娘等,在四大传说中不但丧失去其神圣光环,甚至变成了被嘲弄的对象。 这样的伦理取位当然并非仅见于四大传说,在以往的戏文说唱、稗官野史与私家笔记中,也存在着无数诸如此类的颠覆性叙事,它们讲述着比“钦定正史”更为真实的历史故事。这类私人叙事的功能在于补宏大叙事之失,将居高临下的伦理取位拨正为平视与细观,使得被正史忽略的民间呻吟获得关注,放大成像孟姜女哭声那样的振聋发聩之音。宏大叙事的最大弊端在于漠视普通人的痛苦,他们为历史进程付出的代价没有理由不在叙事中得到体现,只有将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相结合,我们才能认识历史的全貌。四大传说的伦理意义体现于此,聚合在一起的四个故事最为鲜明和集中地反映了普通人的欲求,故事中主人公并没有奢望太多东西,四对男女只不过希望此生能长相厮守,但即便是这样的愿望也得不到满足,无怪乎从古到今的听众都会为他们的命运而唏嘘叹息。 (三)传说结尾均有一抹亮色 中国古代戏曲多以喜剧收场,普罗普研究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大都在“婚礼”的钟声中结束,弗莱如此归纳传奇故事的普遍规律: 大多数传奇故事结局圆满:它自身份脱离开端,以身份恢复结局。即使是那些最具现实主义色彩的故事也往往流露出这样的痕迹:开头有明显的下沉,结尾又有反弹。这意味着大多数传奇显示出了一种循环的推进;先是沉入到夜的世界,然后又回归到田园的世界,或者通向田园世界的某种象征,如结婚。[4](P59) 我们的四大传说由于有神奇因素,也在弗莱所说的“传奇故事”之列,但它们都不是以“回归”和“恢复”告终,因而在世界文学中属于异数。 不过如前所述,四大传说中虽然没有大团圆式的结局,留给人的印象却不是一味悲苦,故事背景到最后都会出现一抹亮色。白蛇传说中,白素贞虽然被镇于佛塔之下,但“雷峰塔倒,西湖水干”的谶语暗示了她总有复出的一天;梁祝传说中,男女主人公虽然死去,但他们的精灵至少还能在一起同飞共舞;牛郎织女传说中,男女主人公虽然被银河分隔,但毕竟还有每年一度的鹊桥相会;孟姜女传说虽然以女主人公投海为结局,但按鲁迅关于悲剧与喜剧的定义——“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10](P192-193),故事中“有价值的东西”固然被毁灭,造成这种毁灭的长城也被崩倒。似此四大传说结尾都提供了情绪的宣泄口,它们就像隧道尽头的一线光明,作用在于驱除听故事者心头的郁结。这种处理似在告诉人们,镇压带来反抗,隔断呼唤跨越,禁锢不可能长久得逞,自由的愿望总有一天会以某种方式获得满足或释放。与廉价的大团圆收场相比,“镇塔”、“化蝶”、“崩城”与“变星”的结局更能产生曲终奏雅的效果,这也是四大传说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悲剧的长处在于深入人心,又会造成挥之不去的伤痛,因此那些懂得讲故事奥秘的人,常常在悲剧中羼入一丝喜剧的色调,以免形成过于压抑的气氛。《红楼梦》中贾府的下场无疑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过故事的未来若真是如此毫无悬念,那么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将会一直紧皱眉头,因此小说中又预设了“兰桂齐芳”这一影影绰绰看不分明的远景。把某种可能发生但不一定就要在作品中实现的未来放在“故事外”,可以说是一种相当高明的叙事策略,即便是在遨游虚构世界的精神旅行中,我们也会下意识地憧憬道路尽头能有令人惊喜的风景。一个故事是悲是喜其实取决于观察角度,四大传说既是受苦受难的故事,也是冲破牢笼的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男女主人公双双死去,但这出悲剧并不让人太过伤感,因为两人的爱情烈焰融解了双方家族的世代仇恨,这种情况就像崩倒长城一样给人一丝胜利的喜悦。传奇故事中的死亡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没有“爱的战胜”,没有希望与光明。 (四)人物身份对应士农工商 四大传说的男主人公皆为普通人,封建社会将平民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四民”⑥,有意思的是,梁山伯为读书人,牛郎为农夫,万喜良为役夫,许仙为药店学徒,他们的身份恰好与“四民”分别对应。 这种对应似非完全出于偶然,四大传说作为一个有机的故事序列,其筛选机制应当带有分殊与“间性”的要求,不然难以解释为何单单是这四个故事被挑选出来,更无法说明为何它们能契合得如此亲密无“间”。中国是文明古国,儒家文化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四大传说中自然需要一个关于读书人的故事;中国又是农业大国,稼穑为立国之本,没有农民的故事对四大传说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还是一个疆土辽阔的帝国,修建长城之类的工程需要从各地征调大量役夫,这一庞大的流动人群势必又会推出自己生离死别的故事;“商”在重农轻商的古代被列为“四民”之末,但无“商”不成“市”,城市生活也有权在四大传说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是按先来后到排序,白蛇传说在四大传说中也应“叨陪末座”,但这个故事在今天的“重述率”比其他故事要高得多,究其原因,应当说与其对应的城市生活背景有很大关系。 有了这样的“分工”,故事讲述中就有了乡村、道路和城市,有了书堂、店铺和寺庙,有了边关、山川与大海。四大传说从内容上说并不复杂,故事线索也很简单,但其牵涉的社会阶层相当广泛,上场人物来自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其中还不乏“天地君亲师”方面的代表。就地理空间而言,四大传说涉及中华大地的东西南北,孟姜女不远万里从秦国走到海边,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共读于教育昌明的中原,牛郎织女故事中的洗浴和窃衣带有楚地民俗色彩,白素贞与许仙邂逅于美丽的西子湖畔。白蛇传说虽然起源于域外,但西湖和中药等因素已经使这个故事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其他三个传说中也有像中药这样的“国粹”,如梁祝传说中的书堂,牛郎织女传说中的男耕女织以及孟姜女传说中的万里长城等,这些来自“士农工商”的标志性事物,赋予四大传说鲜明的中国叙事特征。 (五)故事时间覆盖春夏秋冬 时间在四大传说中也参与了叙述。就故事持续的时间长度来说,四大传说均不止一次地跨越了四季,但在人们印象中,每个故事似乎都只对应某个季节,或者说故事的主要行动各有其发生的季节。梁祝传说是春天的故事,那里有成双成对的蝴蝶飞舞;白蛇传说为夏天的故事,许仙与白素贞在端午节同饮雄黄酒;牛郎织女传说为秋天的故事,有情人聚首在金风送爽的七夕;孟姜女传说为冬天的故事,女主人公顶风冒雪为丈夫送去寒衣。有春夏秋冬之分,就会有物候、节令与天象之别,所以故事背景有时蝶舞翩翩,有时洪水滔天,有时星汉灿然,有时北风凄凉。 除了主要行动的季节属性外,四大传说中的爱情也分属不同的季节:梁山伯与祝英台从未获得真正亲近的机会,他们纯洁的爱情就像含苞待放的春天花朵,离繁花似锦的夏天和果实累累的秋天还很遥远;白素贞到端午时腹内已有爱情的结晶,如果不是爱得太热烈太盲目,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喝下那杯让自己出乖露丑的雄黄酒;牛郎织女之爱因银河隔断而趋于深沉,要是不沉下心来耐心等待,鹊桥相会之前的日子将会无比难熬;孟姜女到最后已成形单影只的孤鸿,在长城边看到丈夫尸骸的那一刻,她的内心一定因绝望而变得冰凉彻骨。故事当然是没有“体温”的,但四大传说之间确实存在着微妙的爱情“温差”:其中既有初恋、暗恋和苦恋,又有热恋、痴恋与绝恋;既有情窦初开、浓情蜜意与深情厚谊,又有一见钟情、两地相思与始终不渝。 四大传说与四季的对应,和它们与“四民”的对应一样,显示出这四个故事确实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序列。如果说“士农工商”这四大人群都有自己的故事,那么每一个季节也应该有最适合讲述的故事,例如秋天的夜晚银河呈现得特别清晰,这时坐在豆棚瓜架下面讲“鹊桥相会”便很应景。与此相似,化蝶的故事适合在春回大地时讲述,饮雄黄酒的故事适合在气温升高时讲述,送寒衣的故事适合在冰封大地时讲述。如此看来,我们的祖先在推出顶尖故事时一定考虑到了它们的季节属性,以便自己的子子孙孙一年四季都有故事可听。 民间故事是知识的宝藏,四大传说合起来是一部袖珍版的百科全书。任何叙事都有传授知识的功能,四大传说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相互补充而做到无远勿届无所不包,其覆盖范围之广胜过了许多鸿篇巨制。我们在聆听故事中经历四时八节,走过北国南疆,往来天上人间,巡游各行各业。这种“巡游”带有走马观花的性质,但就是这种体验让我们了解世事人生的基本格局,获得相互联系的整体印象。不仅如此,四大传说流传至今还与其承载的教化功能有关。这些故事实际上是在进行伦理教育,它们携带古人对生命的理解与对爱情的诠释,告诉我们什么最有价值,什么最有力量,什么最有意义,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就是在这样的爱情学校与人生课堂中接受启蒙。《毛诗序》在论“诗”之功效时,使用了“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等表述,四大传说和“三百篇”一样来自民间,其特点亦可用“思无邪”来概括,底层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中华文明的薪火传承。 ①“欧洲陶瓷工人利用这一色调模仿中国的装饰技巧,设计了至今还流行的柳树梢头两只鸽子,这种表现出安详而美丽色调的图案,与那些在东印度公司时代早期来中国的经商人的想象相吻合。”路易·艾黎:《瓷国游历记》,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第35页。“柳树图案最初在1849年的英国杂志《家庭朋友》上出现,后来在欧洲被广泛翻制,最多时有200多家瓷厂烧制这种图案。在当今欧美,50年以上的柳树图案瓷具已属价值不菲的藏品。”傅修延:《瓷的叙事与文化分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②“最初,西方文化根本就不是一种视觉文化,而是一种听觉文化。……在荷马笔下的贵族群里,听觉是头等重要的。视觉的优先地位最初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初叶……到了柏拉图的时代,已完全盛行视觉模式。”(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14页。 ③“中国文化精致,感知敏锐的程度,西方文化始终无法比拟,但中国毕竟是部落社会,是听觉人。”(加)马歇尔·麦克卢汉:《古滕堡星系:活版印刷人的造成》,赖盈满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④“陈启源《毛诗·古编·附录》论之曰:‘夫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悦益至。’二诗所赋,皆西洋浪漫主义所谓企慕(Sehnsucht)之情境也。古罗马诗人桓吉尔名句云;‘望对岸而伸手向往’(Tendebantque manus ripae ulterioris amore),后世会心者以为善道可望难即、欲求不遂之致。”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3-124页。 ⑤羽衣仙女传说为亚非欧三大洲广泛传播的民间故事,其源头在西晋郭璞《玄中记·女雀》(东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四有相似记载)中,牛郎织女传说与该传说有交织之处。 ⑥“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石民”此处意为柱石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