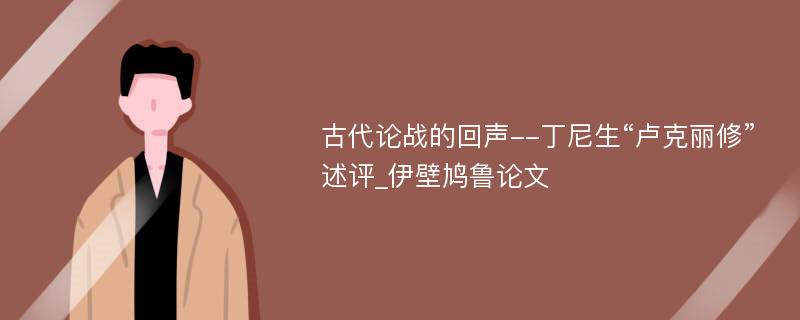
古代论争的回声——评丁尼生的《卢克莱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莱论文,回声论文,古代论文,评丁尼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丁尼生1865年创作的《卢克莱修》是他以疯狂为题材的戏剧独白诗之一,这首诗与其他疯狂题材诗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维多利亚时代那样一个注重道德的时期,它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情欲的题材。情欲的毁灭作用是丁尼生对理性与信仰关系思考的一种折射。卢克莱修被情欲所困扰,并且发疯自杀,这是丁尼生对古罗马文学史中一段存疑的历史记载进行的改造,他希望以此表明在缺乏信仰的尊重的情况下,人的欲望会失控,并造成灾难。
一、作为唯物主义诗人的卢克莱修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卢克莱修热”
《卢克莱修》中的同名主人公是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著名诗人,他的代表作《物性论》阐述了原子论思想和伊壁鸠鲁主义的伦理学,在当时实验条件还非常低下的情况下,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思考,得出了对世界本质的唯物主义观点。卢克莱修认为,世界是由不同种类的原子构成的,同时自然里存在虚空,以作为原子可以运动的条件。原子的数量是无限的,无生无灭,它的永恒运动造成了世界的变化。卢克莱修并没有否定神的存在,可是他认为神和灵魂也由原子构成,只是构成神和灵魂的原子更为细腻平滑,因此神也没什么值得崇敬的地方,更不是道德与灵魂不死的保障,而由原子构成的灵魂在人死之时就会飞散,不复存在。
卢克莱修在古罗马一度受到推崇,维吉尔的《农事诗》就有向他借鉴模仿的段落,①距卢克莱修时代不远的古罗马帝国黄金时期,不少作家也盛赞卢克莱修。②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几乎被大众遗忘,这与古罗马帝国盛行带有泛神论色彩的斯多葛主义有关系。古罗马是一个尊崇神的城邦,斯多葛主义肯定神的存在,认为整个世界都带有神性,因而鼓励人们注重精神上的修养,轻视物质上的享受,得到了不少上层社会人士的推崇,包括西塞罗、马可·奥勒留,而宣扬唯物主义的伊壁鸠鲁主义由于否认神的神性,则相对没能得到那么广泛的接受。再加上斯多葛派对伊壁鸠鲁主义哲学的快乐原则进行了歪曲,使它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受到了歧视。③《物性论》同样因为否定神和宣传伊壁鸠鲁主义而被古罗马的大多数读者所忽视。中世纪时期,卢克莱修的著述更是被排斥在欧洲人的视野之外。但在古希腊原子论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以及伊壁鸠鲁没有十分完整的哲学著述留存的情况下,在文艺复兴以后,卢克莱修的相关论述成为系统阐述原子论和伊壁鸠鲁主义哲学的古代经典,受到重视科学与理性的欧洲知识界的关注。
在维多利亚时代,卢克莱修成了英国知识界关注的热点。无论是科学界还是文化界的人士都表示出对卢克莱修的兴趣,还出版了不少相关著述。19世纪60年代,英国就出版了好几个版本的《物性论》。1860年,英国出版了《物性论》的拉丁文版,1864年和1866年出版了英文版。维多利亚时代著名诗人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认为,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流露出来的抑郁、沮丧的情绪使他显得更像是19世纪的人而不是古罗马人。其他一些作者的文章更充分地体现了维多利亚人关注卢克莱修的原因。塞勒(W.Y.Sellar)指出,卢克莱修代表了古代思想对探索万物起源与演化、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努力,而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同样也在探索这些问题。拉丁本《物性论》的评注者芒罗(H.A.J.Munro)称赞卢克莱修使人免于“对死亡和神的恐惧”,使人获得幸福和思想的自由,而跟宗教有关的作者们对卢克莱修的关注就带有更强的目的性,他们是要把卢克莱修与当时的科学家联系起来。对于他们来说,卢克莱修对宗教和神的攻击,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发现对宗教冲击的一次预演,但卢克莱修对宗教和神的抨击在历史中被证明是无效的,他的观点只是宗教发展过程中从外部使宗教变得更为纯粹的助力,不能对宗教产生真正的威胁。④
卢克莱修在维多利亚时代受到关注,是维多利亚人把当时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投射到卢克莱修的作品上的结果。不仅维护宗教的人士乐意这样做,科学界人士也乐意这样做。物理学家丁达尔认为在历史上宗教一直起着阻碍科学的作用,他把卢克莱修引为反宗教的同道,认为他掌握了古代世界的科学,是迷信的反对者、自由科学的先驱。⑤
丁尼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的声誉在他身后曾有起伏,而这正是与人们对维多利亚时代评价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这也说明了丁尼生与维多利亚时代思想结合之紧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经济和文化发展变化之大,给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丁尼生的诗歌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而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密切关注的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也是丁尼生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虽然是一位诗人,丁尼生一直密切关注当时的科学进展,在读大学时,他就喜欢研读天文学著作,后来还被选入英国皇家科学院,成为荣誉院士。乔治·奥威尔说,丁尼生是“没有机械才能但能看到机械的社会潜力”的作家。⑥托马斯·赫胥黎说,丁尼生是自卢克莱修以来最了解科学的诗人。⑦丁尼生本人由于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的关系,对保障了人的短暂生命的意义以及维系社会道德和秩序的宗教,有不能割舍的感情。所以,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与宗教的论争,丁尼生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虽然他站在科学的业余爱好者的立场上对卢克莱修所宣扬的自在自为的物质和理性表示理解,但他最终不免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指出理性的局限性。
二、丁尼生处理卢克莱修之死的题材:既同情又批评
关于卢克莱修的生平,后人了解得不多,有关他的死因,更是存在着争议。卢克莱修的生卒年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是生活在导致古罗马共和国终结的内战之前,并且在他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苏拉的统治。关于卢克莱修去世的原因,古罗马三大拉丁教父之一圣杰罗姆(St.Jerome,又译圣哲罗姆)在尤西比乌斯《编年史》的注释中说,是因为卢克莱修误服了春药,因而发疯死去。⑧圣杰罗姆对卢克莱修的论述,被后世的古罗马文学史家指出存在不准确之处,如塞勒在《罗马共和国诗人》中指出,杰罗姆关于卢克莱修的生卒年的说法不准确。⑨圣杰罗姆关于卢克莱修死因的说法也缺乏旁证,更有人指出,杰罗姆的这一说法是基督教人士对持异教学说的卢克莱修的有意贬损。⑩由于关于卢克莱修的存世资料很少,所以虽然有人怀疑他的说法,但也无法真正证伪此说。
丁尼生的《卢克莱修》描述的就是卢克莱修发疯自杀的事件。由于卢克莱修醉心于对科学和哲学的研习,冷落了自己的妻子卢奇利亚(Lucilia),于是卢奇利亚从女巫那里拿来春药让不知情的卢克莱修服下,导致后者发疯自杀,最终卢奇利亚追悔莫及。
诗中作为现实人物的形象出现的主要是卢克莱修、他的妻子和古罗马历史传说中导致古罗马王政时期结束的卢克莱提娅(Lucretia)。诗的主题部分是卢克莱修的独白,丁尼生化用了《物性论》的许多观点和诗句,让卢克莱修表述了他的原子论观念以及对宗教的态度。这一部分是深思的哲理部分。卢奇利亚的部分作为一个框架,描写了她的猜疑和最后失去丈夫的悲痛。有研究者指出,卢奇利亚的部分所涉及的女巫以及卢奇利亚悲痛时的表现,其风格与主题部分的沉郁深思有很大的区别,显得夸张、超现实。这种对比是为了表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待疯狂病症的夸张和戏剧化态度,表明了丁尼生对严责人们恪守道德责任的维多利亚社会的不认可。(11)但实际上,诗歌刚刚出版的时候,不少读者没有责怪放弃丈夫责任的卢克莱修,反而同情他,并责怪卢奇利亚的愚蠢,认为是她给卢克莱修带来了不幸。(12)
丁尼生虽然采用的是对卢克莱修不利的传说,但他对诗中主人公的理性思考还是持同情态度的。他虽然不赞同卢克莱修的结论,但他对卢克莱修关于自然和神的关系的反思有很多共鸣的地方。丁尼生让卢克莱修在诗中以大段的独白酣畅地表达出自己的看法。卢克莱修在诗中提出对神的质疑:责怪神置身于人类世界之外,对人类的苦难不闻不问,让人独自承受自然给个体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这些指责与丁尼生自己在《悼念集》中质疑神漠视自然的残酷非常相像。戏剧独白诗是维多利亚时代两大诗人丁尼生和勃朗宁都喜欢采用的一种形式。丁尼生的独白诗创作虽然无法与勃朗宁的斐然成果相比,但也有其独特的形式。评论者给丁尼生所使用的戏剧独白另起了一个名称,即独白剧(monodrama)。霍恩(R.H.Horne)就曾经提到,丁尼生的《圣西蒙·斯泰赖茨》(Saint Simeon Stylites)是“强有力的独白剧”,而《精选评论》(Eclectic Review)(1849)中一位评论者也说:“(勃朗宁的)整首诗可以说是戏剧性的,而丁尼生的诗就完全是独白剧。”(13)勃朗宁的戏剧独白诗重点强调的是独白者的讲述与阅读者的理解之间的反讽距离,而丁尼生的独白剧则突出了独白者意识层面的表述与他无意识中揭露的自我之间的冲突。(14)换言之,两者都有两种声音的冲突,但勃朗宁的戏剧独白诗是让读者在独白者的讲述中读出作者设置的言外之意,从而构成对独白者的批判,而丁尼生的独白剧则是要揭示独白者自身的冲突和挣扎,因此,独白剧的作者对独白者更有一种同情。但是,如果丁尼生对卢克莱修的态度只是同情,那就不会有这首诗的创作了。在诗的最后部分,当卢克莱修举刀自刺而倒地,卢奇利亚冲过去表示哀恸的时候,卢克莱修说了一句话:“有什么关系?”表现的仍是伊壁鸠鲁信徒对生死无谓的态度。《卢克莱修》后来再版时,丁尼生把这句话改为“你的责任?什么是责任?”瑏瑥更强调的是维多利亚社会要求个人对他人应承担的责任。卢克莱修沉浸于自己的思想,先是沉迷理性思考,后是出于情欲破坏个人尊严,放弃作为一个人的社会责任。。
三、丁尼生认为对理性的迷思使卢克莱修陷入疯狂,导致毁灭
诗中和历史上真实的卢克莱修都坚持原子论,认为除了原子和虚空之外别无他物,一切都是原子运动、碰撞的结果。研究者指出,卢克莱修在描写原子论基础上物质不停地转化时,突出强调的是物质的生成,而不是它的毁灭,(16)突出的是原子论比较乐观的一面。根据原子论,人在这个物质世界中,与其他物质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卢克莱修详细地分析了灵魂的构成和在人的身体里的分布状态,最后的结论是,灵魂作为更平滑细微的原子,稀薄而均匀地分布在人的身体中,随着人的死亡,会离开人体,以原子微粒的形式消散在空气中。在阐述了人的灵魂并不比肉体更神圣,也不会永恒存在之后,卢克莱修进一步消解神的神圣性。由于人能够掌握宇宙的规律,而神不过是由同样的原子构成,所以人完全不必对神顶礼膜拜,更不需要对神和宗教有什么敬畏,甚至这种敬畏对人和社会都是有害的,使人做事畏首畏尾,甚至做出违反道德的事情。在《物性论》开头,卢克莱修歌颂维纳斯,请她赐予灵感,不过他的歌颂只是半心半意的,在诗的主体部分,卢克莱修指出神居于世界之外,过着自己平静的生活,根本不关心这个世界和人类,而人对神的崇奉只会给人带来死亡的恐惧,因为人为逃避冥府的恐怖而做出很多背德败行的事情。分析神的性质,从而消除人对神的惩罚和死亡的恐惧,让人能过上平静幸福的生活,这就是《物性论》向人们介绍原子论和伊壁鸠鲁哲学的目的。《物性论》中提到,如果我们把欲念的痛苦去掉,就能与朋友一起,在草地上、树荫下,“开怀行乐养息身体”。(17)《卢克莱修》中也借用了同样的情景,歌颂“伊壁鸠鲁式的生活”。但是,伊壁鸠鲁的快乐哲学也有消除不了的痛苦。《物性论》以雅典瘟疫流行的悲惨场景结束,在瘟疫中,无论有德者还是逃避责任者都遭受瘟疫的痛苦而倒毙。不过,伊壁鸠鲁主义的有效之处就是,它表明了对客观存在之物的恐惧是一种新的痛苦,所以它告诫人们遵守自然的必然性,接受必死的命运,并告诉人们,更长的生命也不会带来更多的快乐,也不会有更大的意义。在接受必然性之后,平静的心境能给人带来最少的痛苦和最大的快乐。卢克莱修不是让人只满足于最低限度的自然欲望的犬儒主义者,他在分析人能够认识自然规律,消除对神灵的恐惧的同时,又表现出人的智性上的骄傲,因为这是人通过理性认识到的自然规律,是在文艺之神的指引下,在喝彩声中取得的一顶光荣的桂冠。(18)把世界仅看作由自然规律支配,认为人虽由物质构成,却以其最高的智慧认识了这个世界,这样的观点显然是注重灵魂和信仰的丁尼生难以认同的。虽然研究者认为丁尼生夸大了卢克莱修的理性与欲望之间的冲突,但卢克莱修对理性的高度推崇确是事实,可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性崇拜互相参照。
按卢克莱修的论证思路,神既然已经失去了神圣的属性,那么掌握了自然规律的人就具有了神圣性。除了诗中卢克莱修对神的嘲讽之外,诗的开头还写到卢克莱修醉心伊壁鸠鲁哲学,把老师视为神圣。《物性论》本身并没有从道德的角度对神和宗教进行评判,而《卢克莱修》中的主人公指责神冷漠对待世界中的苦难,但这种从道义上对神的指责在古希腊罗马宗教体系中是没有的,是基督教出现后的产物。到了18世纪以后,在福音运动和康德道德哲学影响下,道德成为宗教的一个重要属性。《卢克莱修》中描述的神带有丁尼生作品中常见的伊壁鸠鲁主义隔绝者的特征:远离人世,对人世的一切责任无动于衷,保持心灵的平静。作品中的卢克莱修指责这种不关心人类的神,但他又希望人能够过上伊壁鸠鲁式的生活,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是人对神的嫉妒和觊觎。丁尼生描述卢克莱修这种对神既嘲讽又欣慕的矛盾态度,其实就表现了他的狂妄态度掩盖下的不稳固的平静。丁尼生早在少年时期很可能就已经读过《物性论》,(19)1865年他重新关注它,并创作《卢克莱修》,当然不仅是再现《物性论》的观点而已。他关心的是宗教与科学、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诗中的卢克莱修把唯物论当作新的神明,追求人的理性的纯粹,然而这种神圣很容易被击败,它本身也蕴含着本质的矛盾,卢奇利亚的春药就轻易毁掉了卢克莱修的理性和尊严。
在《卢克莱修》中,卢克莱修的发疯,首先是因为药物在物质层面上影响了卢克莱修的身体,进入他的血液,损坏了他的细胞,继而影响了他的神智。研究者指出,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肯定人可有适当的欲望,而《卢克莱修》中的主人公醉心理性,忽视欲望,导致妻子的猜疑,才酿成这一后果。(20)但是,对丁尼生来说,物质本身可有生灭断续,但它的多变无序是不可撤销的本质特征,正是物质的毁灭性本质导致了卢克莱修的精神崩溃和死亡。在《卢克莱修》和丁尼生的其他一些诗中,神、灵性与天空的意象结合在一起,而物质、变化则与大地相联系。卢克莱修在服下春药后做了三个梦,一个比一个狂乱。第一个梦中卢克莱修见到天地变色,闪电划破天空,大雨倾注,原本干燥的山谷中狂暴的水流倾泻。天空和大地失序,尤其是大地的面貌起了巨大的变化。水会带来生机,但纯粹的物质变化最终带来的是混乱。所以卢克莱修在回忆这个梦境时感叹道:
……可怕啊:看起来
自然中产生了虚空。她的束缚
全溃裂了。我看到闪耀的原子流
和她广大宇宙的洪流
在无尽的虚空中流动,
飞起来彼此撞击……(21)
这段描写符合卢克莱修原子论对虚空和原子运动的描述,但在丁尼生的表述中,自然的束缚溃裂以及原子的流动、撞击都显示出主人公和作者对原有秩序瓦解、混乱的恐惧。在第二个梦中,大约与卢克莱修同时代的古罗马统治者苏拉屠杀时洒下的鲜血溅到地上,但它并不像卢克莱修所期待的,如同希腊神话故事里卡德摩斯杀死毒龙、播种龙齿那样,从地里生出建城勇士,而是出现了一群代表着肉欲的妓女,紧紧围绕着卢克莱修,还围拢上来,吓得卢克莱修大叫起来。在第三个梦中,欲望的形式更强烈,海伦的酥胸吸引了卢克莱修的注意力,一把剑上下盘旋,最后伊利昂的大火结束了这个梦。研究者指出,海伦的酥胸和剑分别是女性和男性的性象征,而大火象征着肉欲导致的毁灭。(22)在接下来的幻想中,卢克莱修见到了古罗马神话中象征淫欲的林神在追逐林间女神,而卢克莱修对这一场面的描述充满了自身被压抑的欲望和表层意识中对这种欲望的厌恶。
与《物性论》强调物质的生成性特征相反,《卢克莱修》强调的是物质的毁灭性本质。卢克莱修在自杀之前,提到了名字与卢克莱修相近的卢克莱提娅的自杀。同样的自杀,卢克莱提娅的自杀是共和国的开端,而卢克莱修则眼见共和国处在内战的边缘,很可能就此终结。诗中提到自然是“一切的子宫和坟墓”,肯定了物质生成与毁灭的功能,但《卢克莱修》中提到的基本上是物质毁灭的一面,即使是事物的开端,也都是“盲目的开端”,毫无目的,终将陷入混乱和毁灭。丁尼生在诗中提到,当精神与原子结合起来时,大量的原子挤入,就像一群暴徒撞破大门,涌入庄严的大厅。研究者指出,关于暴徒破门的描写可能是因1865年改革法案讨论引起的骚动而联想到的,它也可以与罗马共和国末期社会秩序的混乱相联系。(23)正因为如此,在诗中,紧接共和国诞生的就是卢克莱修预见到的共和国的灭亡。诗歌结尾处卢克莱修的自杀,其实在诗歌的开头已有预示。卢奇利亚作为诗中物质和欲望的代表,在丁尼生的描写中与大地和死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诗的开始部分,卢奇利亚每天仔细聆听丈夫回来时踏在地上的脚步声,注意到丈夫的思想总是埋在沉重的思考之中,她的春药最终摧毁了他。
因此,卢克莱修虽然自诩能够通过对自然的了解而像神一样“安稳地生活,/没有淫欲、狭隘的嫉妒、低劣的恶意,/没有野心的疯狂、贪婪……没有什么可以损害理性的尊严/来自安定甜美的伊壁鸠鲁式的生活”,但他马上就感觉到“似乎看不见的怪兽用它/巨大肮脏的手攫住了我的意志,/扭曲成与它同样,破坏了我/存在的神圣”。(24)在丁尼生看来,在不稳定的物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性,很容易就被导向欲望和死亡的物质所毁灭。因此,追求“神圣的平静”和“理性的尊严”的卢克莱修不可能忍受失去了这一切的“永恒地狱”的折磨,最终以自杀来解脱自己。在永恒精神不存在的情况下,人只能用消灭自身这唯一的办法来战胜欲望,虽然战胜的结果对这一个体已经没有意义:“于是——于是——灵魂飞散,消逝于空气之中。”
作为赫胥黎所说的自卢克莱修以后最了解科学的诗人,丁尼生其实在自己的诗中也表达了与卢克莱修的自然观相近的科学认识。在发表于1850年的《悼念集》中,他就写道:
“难道我关心物种吗?”不!
自然从岩层和化石中呼喊:
“物种已灭绝了千千万万,
我全不在乎,一切都要结束。
你向我呼吁,求我仁慈,
我令万物生,我使万物死。
灵魂仅仅意味着呼吸,
我知道的仅止于此。”(飞白译文)
但是,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世界并没有道德属性,外在于人所生存的自然界的神也没有道德属性,他们并不关心人类。对于丁尼生来说,他可以承认自然世界的变化、事物的生长与消亡,但这个世界无法保证个体存在的意义和意志自由,退一步来说,这个世界本身如果没有系统之外的外力保证,必然会陷于混乱和崩溃。有学者指出,《卢克莱修》关注丁尼生对疯狂色欲的恐惧、对没有神明的世界以及强大而盲目的宇宙的恐惧,而丁尼生否定卢克莱修哲学,坚持宗教信仰,并不是要否定卢克莱修所推崇的理性,而是因为卢克莱修哲学体系中的理性虽可傲视神明,却屈从于个体死亡的必然性和自然的混沌。在丁尼生看来,人类的理性是可贵的,但只有在超越自然的神的保证之下,个体的理性和自由才能真正实现。
注释:
①(15)詹姆斯·尼古拉斯:《伊壁鸠鲁主义的政治哲学》,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16,27,28页。
②③⑧王焕生:《古罗马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113,114,102页。
④⑤Frank M.Turner,“Lucretius among the Victorians”,Victorian Studies,Vol.16,No.3 (Mar.,1973),pp.330-335,p.337.
⑥乔治·奥威尔:《奥威尔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279页。
⑦Patrick O’Neill,“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and the Productive Reader of Victorian Poetry:Tennyson’s‘Lucretius’Among Victorian and Contemporary Critics”,Victorian Poetry,Vol.29,No.4 (Winter,1991),p.386.
⑨W.Y.Sellar,The Roman Poets of the Republic (Oxford:Clarendon Press,1881),p.275.
⑩(19)A.A.Markley,Stateliest Measur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4),pp.141,p.140.
(11)(20)Roger S.Platizky,A Blueprint of His Dissent (Lewisburg: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p.88,p.69,p.74.
(12)(16)Patrick O’Neill,“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and the Productive Reader of Victorian Poetry:Tennyson’s‘Lucretius’Among Victorian and Contemporary Critics”,Victorian Poetry,Vol.29,No.4 (Winter,1991),p.394.
(13)(14)A.Dwight Culler,The Poetry of Tennyson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p.195,pp.195-196.
(17)(18)卢克莱修:《物性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62,347,356页。
(21)(22)(25)Karen Hodder ed.,The Works of Alfred Lord Tennyson(Hertfordshire:Wordsworth Poetry Library,2008),p.657,p.661,pp.338-339.
(23)Henry Kozicki,Tennyson and Clio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9),p.163.
(24)Christopher Ricks,Tennyson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9),p.274.
标签:伊壁鸠鲁论文; 原子论论文; 维多利亚时代论文; 克莱论文; 莱修论文; 物性论论文; 卢奇论文; 古罗马论文; 毁灭世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