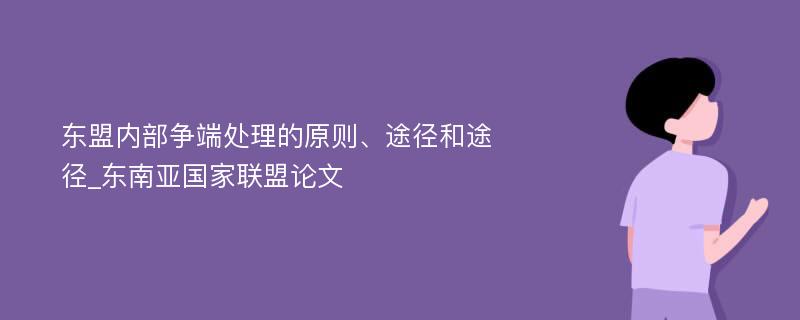
东盟处理内部争端的原则、渠道和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争端论文,渠道论文,原则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8-6099(1999)03-0066-05
一般来说,组建区域性国际组织,旨在加强区内国家间的合作,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这一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首先取决于各成员国能否以整体利益为重,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妥善处理它们之间的分歧和争端,更取决于组织本身能否为成员国之间化解争端,保持团结统一创造一种适宜的机制和氛围。二战结束以来,区域性国际组织大量涌现,但有些由于在协调内部关系上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而导致内部纷争不断、步履维艰。与许多政府间国际组织一样,东盟内部也存在着诸如国家利益相左、领土主权纠纷、经济水平不一、宗教文化差异等矛盾甚至争端。然而,东盟30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它不仅经受住了由于内部争端而出现的危机和考验,而且还调和、淡化了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增强了凝聚力并不断发展壮大。抛开东盟所取得的成就和发展势头不言,仅从其内部关系的稳定和协调上看,笔者认为,该组织是成功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成员国恪守共同确立的处理相互关系的各项原则,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符合各成员国实际并带有本地区特色的处理分歧与争端的方式。因此,对该问题做一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东盟的认识,而且也会对我们处理与该组织及其成员国的关系有所裨益。
东盟处理内部争端的原则和渠道
东盟问世之前,该地区一些国家相继进行过两次组建区域合作组织的尝试,一次是1961年由马来亚(1963年9月后改称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泰国组建的“东南亚联盟”;另一次是1963年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组建的“马—菲—印尼联盟”(又称“马菲印多”)。前者由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国在沙巴主权归属问题上出现尖锐争端而长期陷于瘫痪,后者则由于印尼和菲律宾强烈反对马来西亚于1963年9 月成立包括沙巴、沙捞越和新加坡在内的马来西亚联邦而很快就名存实亡了。不过,东南亚区域主义步伐并未终止。从60年代中期起,随着该地区局势的日趋缓和以及上述国家关系的改善,一个新的、包括该地区五个国家在内的区域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应运而生。
东盟在成立后的头八年里,由于主要致力于调整内部关系,加之组织机制和合作举措尚不健全,成员国之间的隔阂与猜疑又很深,致使其发展受到严理阻碍。有鉴于此,东盟于1976年2 月在印尼的巴厘举行了第一届首脑会议,会上签署了三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即《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协调一致宣言》和《最后公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是东盟最高决策层制定的旨在规范成员国关系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该条约确定的宗旨是“促进缔约国间人民的持久和平、永远友好和合作,以及为各国力量的增强、团结和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作出贡献。”为达此目标,条约还为缔约国处理相互关系确立了六项基本原则,从而成为东盟国家之间解决争端、协调关系的法律依据。这六项原则是:
(a)各国相互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平等、 领土完整和民族特性;
(b)每个国家都有维护其民族生存、反对外来干涉、 颠覆和强制的权力;
(c)互不干涉内政;
(d)用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
(e)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
(f)在缔约国间进行有效的合作。
为了实现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条约第十四条建议成立一个“由各缔约国的一个部长级代表组成的高级委员会,来负责受理已经出现的而且有可能破坏地区和平、和谐的争端或情况。”条约第十五条规定该委员会有权“向有争议的各方建议适当的解决办法,诸如斡旋、调停、调查与和解”;可以“直接斡旋,或者在争议各方同意的情况下建立调停、调查和调解委员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该条约提议在东盟框架内设立一个高级委员会作为专门负责处理争端的组织机构,但实际上该委员会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另外,条约中有关该委员会的规定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其一,条约没有限定高级委员会中的代表必须是律师,倘若是有政界人士组成,那么它所采用的方式则只能是政治性的,而非法律性的;其二,条约规定高级委员会只是“在争议双方无法通过直接谈判达到解决的情况下”才进行工作。如果争议双方尚未直接谈判或是尚未达成解决,高级委员会则无权在处理争端中采取主动举措;其三,条约既没有强制规定争议各方必须诉诸于高级委员会,也没有规定对争议各方实施制裁的手段[ 1]。
条约中的上述局限性反映了东盟国家在选择处理争端的途径和方式上的自愿性和灵活性倾向。从法理上看,这种自愿性、灵活性或曰非强制性降低了国际条约的法律效力,但这正是东盟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和成员国的关系的实际情况所做出的恰当安排,因为这种安排考虑到了东南亚国家的差异和意愿,简化了处理争端过程的复杂性,并使争端更易于解决。另外,这种安排还包含着“公正”的成份,因为在东南亚,除老挝、柬埔寨和缅甸之外,几乎每一个国家都与马来西亚之间存在着边界、领土或领海争端。倘若由高级委员会处理这些争端,有关各方围绕该委员会代表的组成问题势必会发生新的争执,即使该委员会得以组成,它所作出的处理结果的公正性也难以得到保障。
既然《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对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方法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而且作为负责处理争端的唯一机构也一直没有建立起来,那么,东盟国家处理彼此争端的渠道和方式只能在东盟的组织框架之外来寻找。事实正是如此,自东盟成立以来,不曾有哪一个成员国将其与另一成员国的争端提交给东盟这一超国家机构,它们对分歧和争端的处理基本上都是在国家关系的层次上通过双边渠道进行的,东盟只是为其成员国协调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总的指导原则和组织框架[2]。例如, 东盟一些成员国为了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所成立的一些联合委员会(诸如马来西亚—泰国边境委员会、马来西亚—印尼边境委员会和马来西亚—菲律宾双边合作委员会等)都是在双边基础上运作的,而不属于东盟组织内部的特设机构。另外,当某些成员间之间发生争端时,虽然也会有别的成员国或是主动出面或是经东盟指定充当调停者,但它们的斡旋并不是以东盟组织的名义而是以非争端国的身份进行的。
笔者认为,东盟国家这样做的一个重要考虑在于,它们把加强区内团结与合作、建立东南亚共同体视为东盟事业的根本目标,而东南亚国家之间矛盾和争端较多,其中有些事关国家根本利益,最终解决难度很大。因此,如果由东盟组织出面对各个争端实行统一管理,势必会转移东盟的工作重心,削弱东南亚一体化进程。反之,如果把争端留给有关各方依据均可接受的方式自行解决,东盟只对此做原则性安排,则不仅有利于保持东盟组织的完整性和培养成员国的集体意识,而且也会给解决争端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并体现东盟所强调的成员国之间无论大小强弱绝对平等、友好协商的原则。东盟的发展历程表明,尽管其内部争端不断,有些至今未获解决,但成员国间没有因此而发生过战争或武器冲突,东盟在推进政治和经济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是举世瞩目。这不能不说是该组织的另一大成功之处。
东盟处理内部争端的方式
如前文所述,东盟国家之间的矛盾较多,最为突出的莫过于边界领土纠纷。由于此类问题涉及国家主权,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让步。有鉴于此,东盟处理内部争端时主要着眼于避免争端升级、缓和紧张关系、防止其危及内部的团结稳定。为达此目标,东盟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如下避免和缓解争端的方式。
一、广泛协商、寻求一致
从决策角度看,政府间国际组织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协调成员国的立场,统一它们的意见。这是因为,国家利益具有多维性,虽然说若干国家聚合在一起的基础在于它们之间某些利益和目标的相同或相近,但不可能达到完全的一致与调和。因此,如何求大同、存小异,寻求成员国之间态度、立场和意见的结合点,便成为国际组织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若处理不当,则会引起纷争,加深内部分化。为了避免此类现象发生,东盟坚持把“广泛协商、寻求一致”作为其决策和处理重大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
所谓“协商一致”,就是通过协商达成一致从而作出决定。它原是古代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一些农村社会的一种议事方式,现已被东盟广泛采用,并有所创新。根据东盟的实践,东盟成员国在每一次决策之前以及决策过程中,都要频繁地进行双边或多边磋商,寻求一致意见,以使决策尽量实现所有成员国的目标和意愿。在寻求一致的目标短期内难以达到时,东盟往往退而求其次,在多数同意的情况下通过某项决议,同时又允许持不同意见的国家保留自己的意见,并给其将来参与决议的时间和机会[3]。
东盟的这一方式有三个内涵和特点:首先,它强调的不是通过决议时必须得到全体成员的赞同,而是必须未遭到任何成员的反对。这使东盟在两方面受益,一方面,它可以确保每个成员都对议案拥有否决权,从而能够有效地维护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它可以增加各成员在不同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因为在各成员国彼此分歧较大的情况下,使它们都不反对某议案显然比使它们都支持该议案要容易些[4]。其次, 它强调作出正式决议前成员国间的非正式磋商[5]。 由于非正式磋商具有形式多样、方式灵活、回旋余地大等优点,因而使成员国能够通过充分交换意见来增进理解、减少分歧。再次,它不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即不是靠强制某个成员放弃自身立场,而是靠求同存异和相互妥协。因而,这种妥协和存异之后的一致所达到的通常不是矛盾的解决,而是矛盾的避开。上述特点所反映出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既有助于决议的通过和实施,从而保证东事业的发展,也可以使持少数意见的成员坦率地表明自己的意见而又不被持多数意见的成员所支配,从而促进成员间的相互尊重与平等。
“广泛协商、寻求一致”方式不仅体现在东盟的每一次重大决策当中,而且还广泛地被运用于处理成员国之间的各种争端。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在马六甲海峡问题上的争端就是通过该方式解决的。马六甲海峡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要冲,对于沿岸的新、马、印尼具有极其重要的商业和战略价值。随着国际法对领海主权范围的不断扩大,这三国的领海范围便由3海里增至12海里, 从而产生了“领海重叠”问题。为了解决这一争端,上述三国进行了多次友好协商,终于在1977年签定了一个马六甲海峡交通独立的协议,使争端得到初步解决[6]。
二、搁置争议、待后解决
由于东盟国家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其中有些并不是经过短时期的磋商就能够获得解决的。因此,为了避免争议使各方的正常关系受到影响,保持东盟的团结与合作,有关各方往往通过默契将一时无法达成一致的问题或无法化解的争执暂时搁置起来,留待以后时机成熟时再寻求解决。
这一方式主要地被运用于处理争议较大的问题。例如,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国在沙巴主权归属问题上的做法就是典型的例子。沙巴争端始于1962年菲律宾政府对该地提出主权要求,此后两国关系便陷于破裂,并成为东南亚联盟夭折的主要原因。东盟成立后,虽然两国围绕沙巴主权不时地发生新的争吵和对立(严重的如危及东盟存在的科雷吉多事件),但每当危机时刻,双方都能从改善双边关系、维护东盟整体利益的大局出发,采取了淡化矛盾、搁置争议的做法,直至1987年东盟在马尼拉举行第三届首脑会议之时,菲律宾新任总统阿基诺夫人主动作出重大让步(即表示菲律宾愿意单方面采取行动正式撤回关于沙巴主权的要求)之后,两国在该问题上的争端才得到较大程度的缓和。目前,尽管距最终解决该争端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两国的经济联系与合作正在因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以及东盟“东部增长三角”的建立而不断加强。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围绕沙巴主权的矛盾已不像以前那么突出了。
三、自我克制、互谅互让
“自我克制,互谅互让”是东盟国家为了防止彼此矛盾过分激化,损害东盟组织的统一而形成的另一个外交传统。东盟的“自我克制、互谅互让”不仅意味着在发生纠纷时不强制另一方外交传统。东盟的“自我克制、互谅互让”不仅意味着在发生纠纷时不强制另一方接受自己的意志,不以胁迫、颠覆、支持反政府骚乱和攻击领导人等方式干涉别国内政,也意味着对另一方采取宽容、尊让的态度,兼顾另一方的利益要求,考虑本国的政策和行为对别国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这在其成员国关系出现危机以及在重大问题上调和彼此分歧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东盟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成员国采取自我克制的结果,因为当时在菲、马、新、印尼和泰国五个创始成员国当中前四个国家由于领土主权纷争尖锐而彼此怀有很大的敌对情绪,而且它们对组建区域集团所抱的态度和意图也各有不同。“自我克制,互谅互让”还体现在东盟处理同区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关系以及协调各成员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方面。每当涉及此类问题时,各成员国通常向在有关问题上利害关系最大的那个成员国所持的立场靠拢,因为在此方面有重大利益的成员,为了维护其基本利益,所持立场难于改变,为了突出东盟“整体团结”和“一致对外”的形象,其他成员国只有多作妥协。
新加坡与印尼之间发生的“海员事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东盟“自我克制、互谅互让”的认识。1965年,正当印尼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采取“对抗”(Konfrontasi)政策期间, 新加政府逮捕了两名潜入其领土“从事阴谋破坏活动”的印尼海员。印尼和马来西亚领导人曾多次呼吁新加对这两位印尼人以予以减刑,但新加坡拒绝了这一请求,于1968年10月将这二人处以绞刑。据分析,新加坡此举是想向其强大的邻国表明,刚刚获得独立的“袖珍小国”绝不会屈从于外部压力[7]。 两名印尼人被处死的消息传入印尼后,印尼舆论一片哗然,并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新加坡示威游行,新加坡驻雅加达使馆被捣毁,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新加坡与印尼关系的恶化使已经因菲—马沙巴争端受到伤害的东盟面临新的瓦解的危险。为挽救濒临崩溃的东盟,泰国主动充分调停者,分别对新加坡和印尼进行劝说。同时,印尼和新加坡双方都保持了比较克制的态度,印尼总统苏哈托虽然颁布命令限制同新加坡贸易,但拒绝采取其幕僚所建议的报复、断交等一些更为激烈的行动,印尼外长马立克发表低调讲话,设法缓和公众的情绪,印尼政府还率先公开表示愿意同新加坡实现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新加坡也比较克制,对印尼的贸易抵制没有采取报复措施,避免了事态进一步加剧。两周后印尼国内的反新加坡浪潮得到平息,几个月后印尼解除了对新加坡的贸易限制,两国关系恢复了正常。据分析,印尼在这场冲突中保持克制,除了维系东盟的存在的考虑之外,也有体谅新加坡维护自身安全和赢得领国尊重这一需要的因素[8]。
四、利用第三方从中调解
东盟十分重视通过内部的调解活动解决成员国间的争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提议的“高级委员会”虽然没有建立起来,但利用非争端国对争端进行调解的做法贯穿于东盟发展的全过程。这方面的成功事例不胜枚举。例如,前文提到的马来西亚与菲律宾之间关于沙巴主权的争端,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印尼之间关于马六四海峡的争端,新加坡与印尼之间的“海员事件”,以及后来新加坡与菲律宾之间的“女佣事件”等争端的缓解,都是与东盟内部非争端国的积极斡旋密不可分的[9]。
近年来,对于某些长期悬而未决特别是涉及领土、领海问题的、在双边层次上很难解决的争端,争议双方表现出了通过正式的调解渠道谋求解决的趋向。例如,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之间围绕柔佛海峡中的PedraBlanca 岛主权归属的争端, 以及马来西亚与印尼之间围绕沙巴附近的Ligitan和Sipadan岛主权归属的争端,已经提交给国际法院裁决。由于这一解决争端的方式是通过东盟机制之外的法律渠道进行的,因而对于不宜以组织名义处理内部争端的东盟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由于领土争端的最终解决往往导致“零和”状态(即一国利益的增长引起另一国利益的削减),所以,上述新动向意味着东盟已经在处理内部争端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
收稿日期:1999—03—12
标签: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菲律宾总统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矛盾处理论文; 合作原则论文; 关系处理论文; 新加坡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