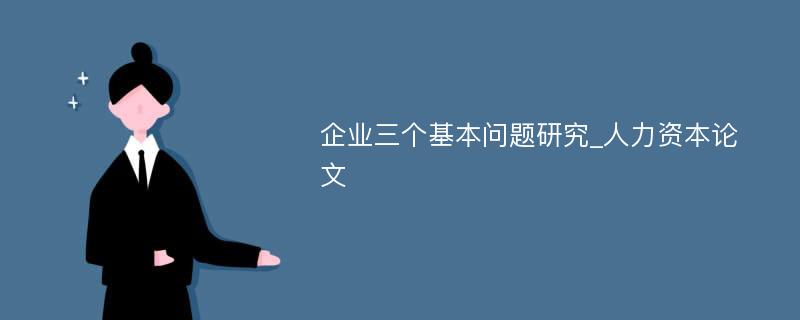
企业三个基本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27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06(2001)03-0009-02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和基本载体,在中国,企业的这种主体地位和载体力量十分虚置。20余年的经济改革,贯穿着从宏观到微观的思径取向,至今尚未建立起明晰、健康的企业成长制度。实践的错位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理论导向的错位。就学术研究而言,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至今没有把企业成长制度的分析放在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研究的核心地位,理论突破和系统成果都十分缺乏。因而在理论与实践上,中国也就没有很好解决关于企业的性质、成长和制度演进这三个问题。
一、企业性质的研究
企业的性质是什么?有关企业性质研究的著作虽然很多,但迄今没有明确、合理、科学地回答出这样一个基础性的、企业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既有的三种流行理论模式均具有自己内在的悖论性:物质资本模式认为企业是(物质)资本与劳动的合约,其最大缺陷,是没有对企业经济增长起源的合理解释。人力资本模式认为企业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合约,但说企业家拥有人力资本,而把职工(包括各种技术专家、中层管理经理人才)说成不拥有人力资本行不通。交易费用模式把企业说成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是节约交易成本的组织。但在历史实证过程中,随着企业规模扩大,企业交易费用并没有出现减少现象。
现在,中国企业性质研究现实表面的繁荣,同时正好映射了既有研究成果对实践缺乏透视力,从而对政策的制定缺乏指导性。这种说法,并不囿于一个很高的学术分析层面,在一个普通的思维与实践层面,亦是如此。除了困惑,和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或者所谓的原理,既有的企业性质理论并不能给学者和企业实践者,乃至政治决策者,提供一些鲜明而有力的指导性建议,即使是方向性的;除了思辨,还是思辨,一切仅此而已。
北京大学前校长陈佳洱院士指出过,中国的学术研究,即使是基础性研究,也是跟踪的多,原创性的少。将这句话套用到中国的企业理论研究上来说,再适合不过。迄今中国的企业理论研究,尤其是企业性质研究,的确是跟踪的多,原创性的极少。但是,中国的企业与国外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发展上存在巨大的环境差别:1.起点不同。中国的企业发展,现在是站在原点上,就面上的情况和主导性的政策而言,企业的本质问题并没有解决,主要的问题是,把很多政府的下属单位,或派生单位,或变相的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当成了企业,甚至是企业的发展形式。2.基础不同。中国的企业发展,在基础,尤其是制度基础与政策基础(注:制度基础与政策基础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硬性的,后者是软性的。)上是不自由的,具有极大的外在强制性或曰外在主导性,不具有市场、社会与历史的主导性,自身非常被动,内在主动性受到极大的削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中国经济学家对企业性质的研究必须有原创性的突破,以指导理性思维主导下的、以促进企业发展为目的的改革运动。
二、企业成长的研究
现今的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企业管理的成果很多,而研究企业运动、尤其是企业成长的成果很少。突出表现在:1.研究就业问题的多,研究创业问题的少;2.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多,研究民营企业成长问题的少;3.以外部介入的方式研究企业问题的多,以内部剖析研究企业问题的少;4.从横断面调研企业问题的多,从纵向跟踪企业问题的少;5.采用归纳法研究企业问题的多,采用演绎法研究企业问题的少。
由于存在几十年企业实践的历史空档,中国的企业家,和研究企业的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大多没有对企业运作的感性认识与经验,而是在一张白纸式的经验与思维基础上,来演绎企业的实践与思辨;盲人摸象,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基本的思径取向。因此,站在已有的全球企业实践的经验基础上,运用最新的企业理论,勾勒企业成长的理论与政策体系,其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无论怎么说都不过份。
对“企业是如何成长的”的命题的研究,有两种基本的途径:其一,从历史和国际比照的角度进行实证性的演绎,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但对中国企业的实证演绎,有力的研究成果至今尚不多见。其二,从企业机理的角度进行研究,尤其是从企业产权、组织和资本等制度层面进行研究。后者是笔者研究的基本定位。(注:可参见本人著述的《企业的起源——从人力资本、企业家和企业合约角度对企业性质、成长与制度演进研究范式的重构》,待版。)
三、企业制度演进的研究
制度演进(InstitutionEvolution)是指制度深化、拓展与发展的自然过程。为什么不提制度改革而提制度演进呢?这主要是突出制度改变的内生性。为什么不提制度变迁而提制度演进呢?这主要突出制度改变的继承性。笔者特别欣赏汪丁丁提出的演进的普遍主义(Evolutionary Universalism)这一说法。
研究制度演进而不是制度变迁,方法与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分野在于:制度的运动必须使企业成为自为的客体、企业家成为主导制度运动的主体、(注:在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多个层面上都是如此。)遵循企业各方合约的原则。与制度变迁相比,制度演进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合约性。合约是制度变迁的基本手段,无合约基础上的制度变迁只能是内乱或叛乱。2.渐进性。制度不能飞跃。埃格特森指出:“契约形式的变化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如果缺乏实际材料来显示一项安排是否最适合于新的环境。一旦有了成功的实践,竞争的力量就会建立起新的均衡契约。同样,给定人们认识契约安排的知识状态,给定产权基本结构状态,在此基础上,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社会在技术稳定、价格稳定情况下,可以寻找到具体的契约形式,这种契约将使各生产单位的生产成本最小化。”[1]3.生长性。制度演进没有终止期,也没有终止地。4.方向性。制度演进具有明确的理性演进方向,这是经济学可以分析的关键依据。5.实践性。制度演进首先是实践的产物,而决不应该首先是理性的产物。
从制度演进的角度观照中国的企业制度,关键的一点就是:没有让企业成为自为的客体,而是反过来让政府成为了自为的客体;没有让企业家成为主导制度运动的主体,而是反过来让政府官员成为了主导制度运动的主体;没有遵循企业各方合约的原则,而是反过来困循企业某个方面单向强制的原则。(注:在任何企业内部,始终存在着三对矛盾:企业职工与资本家之间的劳资矛盾,企业职工与企业家之间的管理矛盾,企业家与资本家之间的代理矛盾。矛盾是企业合约的基础。)结果,诸多制度运动的起点是空茫的,结果是虚置的!(注:起点的喜剧并不代表终点的喜剧。社会与人生经常有这样的悖论。)
从强调制度演进的角度出发,中国国有企业的研究与改革需要进行思路的转换。为什么20余年的研究无突破,改革无进展?一句话,原因在于定向思维。这种定向思维有3个突出特点:1.是政府思维而不是企业家思维:在中国既有的改革研究和改革政策中,凸显的都是政府的影子,企业家何在?这导致传统思维的主体存在错位。2.是计划经济的思维而不是市场经济的思维:不是研究我们“只能怎么办”,而是研究我们“应该怎么办”?整个中国,理论界与政策界现在成了一片方案的海洋,围绕着实践的孤岛,而这实践的孤岛上现在冷冷清清。这是一种改革标的的错位。3.是自上而下的思维,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思维:理论界和政策界一个劲地让实践界只能怎么做,不能怎么做,实践界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创造的机会、发展的可能,改革的活力和创造性何在?这是一种手段的错位。在这3个特点主导之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目前陷入两难境地。
[收稿日期]2001-0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