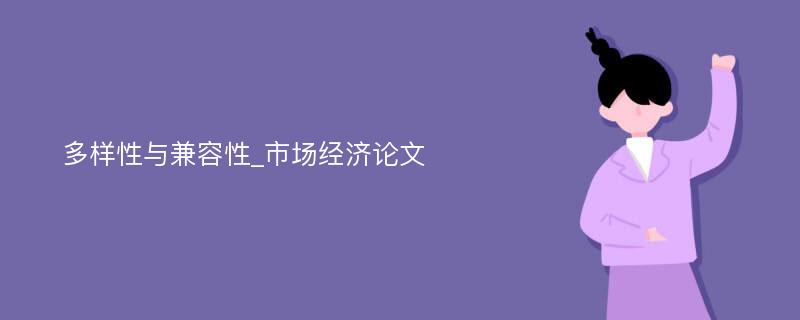
多元与兼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论百家
多元观念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现代意识
何西来(以下简称“何”):首先,多元作为文学观念、精神,是一种现代意识。它是针对过去文化上的独断、专横,文化上的舆论一律、“大一统”等各种形态的文化专制主义而提出的。
多元正是人们在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中,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中,逐步形成的。新时期以来,把它作为一种文学观念,最早提出来的是刘再复的《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一文。
杜书瀛(以下简称“杜”):这篇文章好像是1985年初在《读书》连载的。当时很引起文艺界的关注。
何:对。他的这篇文章指出,在当时的文学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四个大的趋势。从一到多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这样解释的:“由一到多,即由单一的、单纯从哲学的认识论或政治的阶级论角度来观察文学现象转变为从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精神现象学等多种角度来观察文学,把文学作品看作复杂的、丰富的人生整体展示,这样就用有机整体观念代替了机械的整体观念,用多向的、多维联系的思维代替单向的、线性因果联系的思维。”与之呼应的是王蒙,他在许多场合,肯定了刘的这篇文章。王蒙接受了这个观念,于是后来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文学三元》,从此成为“左”派们攻击的靶子。甚至硬往政治的“纲”上扯,必欲置之于死地。其实王蒙讲的,只是文学,而根本不是政治,再说,他也仅讲了“三元”。而文学的复杂功能系统所包括的却远远不止三元,甚至也不止三十元。童庆炳教授就曾提出过文学五十元的观点。在这方面批王蒙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就是在《光明日报》和《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同时发表的那篇,认为王蒙反对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一元论。翻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谁也没提过那样一个出于杜撰的所谓“文学一元论”。抱着这种所谓“文学一元论”观念的人,是说什么也不能容忍拓展思维空间的,不能容忍带有开放特点的多元文学观念的。
邵燕祥(以下简称“邵”):他们需要的是“鸟笼经济”以及与之配套的“鸟笼文化”。
白烨(以下简称“白”):还有一个是,怕多元了之后,失去了自己的文化霸主地位。
何:文学的多元竞争、多元共生、多元互补,是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文化思想。“双百”方针我们提了几十年,基本上是停留在口头上、纸上,甚至有人把它变成一种“阳谋”、一种钓饵。这个口号到“文革”中就完全变成了张春桥所说的“百家争鸣,一家做主,最后听江青的”。这里的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只是达到由“四人帮”极左派“一家做主”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手段。认真来讲,“双百”方针的这两个“百”,就是多的意思;只有一,还哪里会有“百花齐放”,会有“百家争鸣”?因此,只有多元意识和多元观念,才能真正把“双百”方针变成现实,从而促进科学和文化的繁荣。另外,多元的问题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与宽容、兼容、艺术民主、艺术自由等问题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对之进行一次比较集中、比较全面的探讨还是很有意义的。
杜:多元化和市场经济很有关系。以自由竞争为根本原则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多元。市场经济带来的是学术上的多元化,而且不仅是学术上的。因为市场经济是与开放、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相联系的。
白: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多元经济的竞争。
何:没有多元,怎么竞争得起来?只有一元,是无所谓自由竞争的。至少得有二元以上,才有竞争可言,经济才见活力,社会生活才显活相。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艺术,也才会出现蓬勃的生机。
杜:对。市场经济是崇尚多元,反对一元的。崇尚多元的市场经济,我认为它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是反权威的。因为权威常常是与一元联系在一起的。它意味着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地位和威严,意味着芸芸众生对它的臣服和顺从,意味着众星拱月之势,也就意味着对民主和平等的威胁和侵袭。在这样的氛围下,怎能有平等自由的竞争。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是多元的局面,而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还远远不够。
何:市场经济也有权威,这权威首先是市场本身,你的货色如何,受不受欢迎,能占有多大的份额,获取多大的效益,都必须在市场上接受检验。适者生存。要么被淘汰出局,在前面等着的便是破产;要么争得主动,先站稳脚根,唱着凯歌前进,执市场之牛耳。其次,完整的市场经济要有一整套规则,要有相应的立法保障,这规则和立法,也带有不可争议的权威性,进入市场进行经营的人,都必须遵守,不得例外。再次,企业的经理、董事会、董事长,均按其职分,在其管辖范围内有一定的权威。市场经济破坏的是专断权威,权大于法的权威,不顾经济规律和市场运行法则而一味蛮干的权威。
刘心武(以下简称“刘”):书瀛的结论挺好,但他发言当中对市场经济的拥抱有点太热烈了。热烈到褒扬市场经济“反权威”了。大何讲得有道理,市场经济如果没有任何权威,就会一片混乱,市场经济怎么可以没有权威呢?
钱竞(以下简称“钱”):要求统一市场,而不分割市场。
何:市场经济的发展,肯定会有利于多元观念的确立,和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但多元和权威并非绝对排斥,更非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事实上即使在多元格局中,只要各元的关系是互补的、有序的,而不是对抗的、无序的,就必然会有权威存在。不过这是一种新的,与多元共生、互补的观念相对应的权威罢了。
白:从一般的科学民主的意义上讲,也是必然要求多元的。所以我们在没搞市场经济之前,也应该是多元的。
杜:是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没搞市场经济之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百”不起来,最后还是只有两家,而其中一家是受批判的,所以还是一家。
白:多元意识,多元观念已成为了共识,个别人想反对反不了。但他们现在的策略是不讲一元而讲主元,要占主导地位。现在是不能不让步了,但从科学意义上讲依然不够,因为这其中没有主次的问题,也不存在老大老二的问题。
何:正因为如此,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有必要再讲一讲。因为,第一,“一元论”的受益者至今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一元化,而且还在攻击多元观念。第二,提出人文精神的朋友中也有少数人有这种倾向,认为你的多元就容忍了面向俗世的东西的存在,就有同流合污之嫌。因而,现在只是在学理的论证中才好像真正出现了多元共存的局面,其中有一些“元”并不是被承认的“元”,而某些元则有扩展自己话语霸权的倾向。
白:是有这种倾向,就是要把他的那个“元”,变成主控元,霸主元。
何:对!,不过,从学理上说,在多元共存的情况下,如果由这些元组成一个统一的格局,形成某种有机系统,则多元在系统中的地位当然不可能都是半斤八两,毫无主次之分,轻重缓急之分。
刘:因此在当前人文精神论争中,想做“主控元”本无可厚非,但那种焦躁和对其他……
宽容释义
何:对其他诸元不能容纳,不加宽容就不行了。为什么提出了宽容问题?因为有人拒绝宽容。作为一种理论主张,出于种种具体的考虑,倡言反对宽容,是可以的。但指望把这种理论进入可操作的领域,不宽容就不行了。王蒙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这是在80年代初那种特定情况下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也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种反叛。不能老是打“落水狗”,老是把好人当落水狗打;打了多少年了。是不是该讲点宽容了。另一个是对于提倡宽容者的宽容,认为讲宽容就是堕落,因而自己就是不宽容,这未必可取。
杜:我特别赞成宽容,汲取“文革”中无辜群众间“你死我活”的惨痛教训,更觉宽容之可贵。文化上、学术上更应提倡宽容。当然,宽容绝不是取消学术争论、学术讨论,也绝不是把不同意见“宽容”掉,而是说对不同意见的理解、尊重。对于正常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者互相关系来说,要把过去的那种“你死我活”变成“我活你也活”。要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并给予充分的尊重和理解。这是“宽容”的最重要的含义。
何:顺便说一句,关于宽容的概念,我是认同于燕祥的说法的。他对于谈宽容曾经很有点厌恶。我也不怎么主张用“宽容”的概念,而主张用“兼容”。
白:好像这两个概念不一样。“兼容”是指你自己是不是可以吸收他人的东西。而“宽容”则是指我根本不喜欢你的东西,但我可以容许或容忍你的存在。
邵:要加以区别。一个是我们希望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环境,政治文化环境:多元的,宽容的。另一个,我作为个人,比如鲁迅至死不宽容他的论敌,这是他的自由。这与我们要求什么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不一样。
刘:个体生命对他人不宽容,可以个案处理。这无损于对世界的理解。
邵:心武在这个问题上是宽容的,他不要“我的敌人不能成为你的朋友”。
何:我总觉得宽容者对被宽容者会有一种凌驾感,优越感。因为宽容的主动权不在被宽容者手里,而在宽容者手里。今天他高兴了,可以宽容你;明天他不高兴了,则要“灭了你”。怎么办?因此,我主张兼容,你我都是平等的,你别来宽容不宽容的那一套。
刘:宽容当然是居高临下的。掌了权以后的宽容就尤其可贵。
何:权力者身处高位,手控生杀,言出法随,宽容确实十分难得。我理解这种做为个案处理的宽容,如伏尔泰曾写过《论宽容》的文章;房龙专门写过一本叫做《宽容》的书;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在抨击加尔文专制的同时,也可以认为提倡着宽容。当然,茨威格的现实锋芒是指向纳粹的,指向德国当时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政治专制主义的。
邵: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以死捍卫你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
众:这就对了,这是对宽容的最确切的认识。
邵:从个人经历上讲讲我为什么对“宽容”非常讨厌,因为我从来没有宽容别人的权利,老是别人宽容或不宽容我,而且从来没人宽容过我,总是越逼越紧,直到把我逼到墙角。在干校时,专案组要结案了,就逼着我交代“活思想”,我说:“我的活思想就是:我已经没有活思想了,怎么办?”还有一次开会时让我交代“活思想”,我说:“我觉得我变成小炉匠栾平,能说的话只剩下一句‘请求宽大处理’。”所以我对宽容有反感和恶感。最近看董乐山的文章,他认为TOLERANCE这个词,最初是对他人不同于自己的信仰、思想和行为的容忍和承认,后来引申为不得侵犯他人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宽容说白了就是容忍执不同见地者。
邵:在知识分子思想文化领域的人际关系中,作为文化人的一种修养,可以提倡一下“和而不同”。但是“和而不同”也是一个高标准的要求。
杜:“和而不同”。这就是“多元共生”,承认“多元共生”、允许“多元共生”、提倡“多元共生”就是一种宽容精神、宽容态度。
白:“宽容”是最基本的底线了。多元是一种观念存在的形态,而宽容则是一个学术风范上的问题。它尤其在目前的情况下更带有必要性和紧迫性,现在有许多争论实际上是由不宽容引起的。它和“理解”不同,现在各业都讲“理解万岁”,但相互理解是一种相当高的境界,进入这个境界也更难。一时理解不了那就宽容一下,这是最起码的了。
钱:“理解”是最高层次上的东西,理解不了就“沟通”,沟通都不行了,就宽容一下好了。
刘:宽容是在不理解的,讨厌的,乃至极其厌恶的前提下,还允许它存在。如果你能理解它、喜欢它、同意它,就无所谓宽容了。
众:这样一分,问题的层面就清楚了,对了。
邵:因意见相左而发生抵牾时,可以正面交锋,也可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钱:而不是曲解原意,罗织罪名,恶意相向等等。
邵:那种人本来就不该进入文化学术领域。
不宽容的沉重记忆
何:我们几十年间的学术争论,特别是在“文革”及其以前,除了50年代有关美学的争论这样个别的例外,其他几乎所有学术界的争论在学理的探究与推进上都很少,双方用力最多的地方往往不是学术而是争夺政治主动权。谁掌握了政治主动权,就可灭了对方。那办法是请最高的领导仲裁,一仲裁,你是错的!不是说你承认错了便罢,便可以了。不行!要么,你就是胡风集团,或者是右派,要么,你就是机会主义,或者是“胡适派唯心论”,或者是别的什么,总之,就得“灭了”你。
刘:所以马寅初虽然什么也没给他定,但他一辈子就再别说了。
白:那个时候往往由学术论争开始,常常以政治判决作结。
杜:这个和东方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是连在一起的。
邵:这是宗教改革以前的那一套。
钱:对!宗教裁判所。
何:在极左的观念下,连只提一下宽容都是不行的。那会有阶级调和、阶级投降的嫌疑。流毒所及,到了新时期,提倡宽容的人,也不是没有人“裁”下去。
刘:大何说得很对,很沉痛。过去的学术争论,不说政治家怎么想的,只说参与的文人双方往往就有一种卑微的心理,他不是去调动读者的真理认知,也不是启发、唤醒对方的认错意识,而是吁请官方,吁请权力用其所设定的框架来使对手低头认罪。这是一揽子的解决,实际的解决,这可怕极了。
何:宽容可以有几个层面:为了能有一个更为宽松、宽和、适宜于文艺、文化、学术发展的外部环境,以便让其自由健康地发展,吁请领导、政府,即有权调节社会环境的管理者、组织者,应当有一种宽容的胸怀、宽容的方针、宽容的政策,是很必要的。
白:应立法而不能只是吁请。
何:你说得有道理,当然应该有完备的体现宽容精神的文化立法。但在这个法还没立起来,还不完备时,我们只能吁请或提建议,希望有关方面重视知识分子为了促进学术发展在这方面的要求。
白:还有一个层面是文化人自身要“志平气正”,行为方式上要避免走极端。
刘:另外,还要不断拓展民间的文化空间,只有这样有些东西才不请自来。
何:你拓展,他不停地吹哨子,亮黄牌,怎么办?
刘:我们应该公正地评价现在的文化环境。与过去相比,文化人思想的空间还是大多了,自由度也大多了。意识形态的淡化是有一个理性指导的过程,不是未经深思熟虑的。事实上,对于学术的行政干预正逐步地减少。即使出现问题,也是化为个案处理,而不是动不动就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那种办法被送进了博物馆。
白:你们两人有职业上不同的感受。从事理论批评的感到干预更多、压力更大,不能不有些顾虑。而作家则不一样,从创作上讲,他的自由度更大一些。
何:作家们面对的是形象世界,形象具有多义性,其常用的象征、比兴等手法,更往往难于一句话说清楚。同一形象,也可以有不同解释,马上下不了结论。而理论家们所面对的却是概念世界,概念要求含义确定,必须明晰,一旦明晰,就常常不能不多所顾忌。
钱:这就是形象大于思想。所以理论批评就更要讲宽容。
何:对。要我来说是“兼容”。大家在学术面前一律平等,可以争论,可以说你这个错,那个错,甚至说你全错。我同意邵燕祥引述的董乐山的意见,互相之间应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另外,因为争论的双方都不是权力,不是政权,因而即使我不宽容你也不存在对你采取实际行动、采取制裁措施的问题。
刘:我再把我的观点说明白一点。如张炜在《柏慧》的最后说他决不宽容。我同意他的作法,即把自己的这一看法在小说中直书出来,因为他是个作家,他这是作品,他可以有这样的看法。要求文艺作品中没有偏激情绪这是没有道理的,作为美学家,你可以表明自己的美学观点。你可以讨厌偏激,他偏激了你可以给他定位,说他美感差一点,说你喜欢更美的。这他可以理解,也可以拒绝。但作为他,他有这个自由。
何:作家更多是情感型的,有时由于偏激而更见真情,更显可爱。如果他完全用清明的理性权衡一切,大约也就没有了艺术创作。
白:所以作家往往比较更有自己的个性。
刘:现在有一些人利用作家的这种本可以理解的情绪性语言、情感型的偏激文字,将其引出作品之外,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宣谕,并试图进行实际操作,甚至有吁请权力介入的架式,这是我所反感的。因为这类事以往多有发生,历史的教训不应遗忘。例如有那么一位诗人,1964年自己参加了剧协的春节晚会,领了小食品回家,又一想不对头!不对头,那你可以写文章公开发表,也可以写信给当事人,他却不,而是直接上书举出一些所谓“格调低下”、“胡闹”的例子,这就超出了观点争鸣和美学讨论的范畴。这应该属于打“小报告”,或“大报告”。结果引出了毛主席关于文艺界的第二次批示,整个文艺界就基本上定性为“裴多菲俱乐部”了,于是要“砸烂”,要“打倒”了,为此,文联死了很多人。这当然是那位诗人也始料未及的。他原来可能只不过是想表现一下自己如何正确。但这种唯我正确并企盼权力介入加以肯定的思路和作法,显然是永不可取的。
对张炜、张承志,人家认为他们的理想不错,我没意见。但如果认为:“中国作家领导中国人民堕落”,“搞痞子运动”,如果又因此而吁请采取措施,并且真的采取了,目前多元格局和开始呈现的百家争鸣的趋势就会彻底丧失。到这时,我就不宽容了,我就要严肃、认真地花点力气争一争,发出我的声音,而不能让他们成为文艺界唯一的声音,把别的声音都哑灭掉。
从“三大文化冲突”谈到新儒学的实践及其评价
刘:有一个问题,在前面提得很少,我们作为一个文化人,对亨廷顿提出的三大文化冲突,应当做出回应,我建议讨论一下。
白: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试图对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格局作新的描述。他断言:“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将成为未来的战线”。他把文明之间的差异看成是一切矛盾的根源,指出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有可能联合起来抗衡西方文明。这个看法在西方有相当的代表性,也在东方引起广泛关注。
何:这是一种把文明的,即由某一文化传统而形成的精神差异极端化、绝对化的观点。事实上,即使是文明的冲突,那背后都会有非常实际的利益、利害的权衡。文明的差异,只有与现实的利害关系裹挟在一起时,才会导致激烈的冲突。
钱:一个是他,另一个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已翻译成十六国文字,他是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身份,讲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在经历了苏联解体以后,得到最后的胜利。因此,它是对西方极乐世界来了一个玫瑰色的大描绘。这在西方内部也引起了很大的回应,特别是在青年学者中有一种反抗声音。我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有两个前途:一个是民族主义的前途,相对应的是一套民族主义话语。中国已经有这种迹象。民族主义情绪抬头,各界都有,包含不祥之兆。还有一个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并不是我们走过来的那些号称社会主义的东西。19世纪酝酿出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对资本主义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成主要批判力量的伟大思想,是否还可以作为我们今后的精神资源?或者,还是跟着西方人讲:冷战结束了,马克思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统统玩儿完,等等。
杜:我插一句:据说这位美国人(福山)最近又在《民主》季刊上发表文章,主张学习儒家文化以救西方文化之弊。
钱:所谓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是在这个含义上的,其中有新的可谈的理论。我们曾经起过呼吁、鼓励市场经济形成的作用,现在也还是支持赞同。然而,一旦市场经济形成之后;知识分子就要继续扮演其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进行批判角色,就要继续对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严厉的批判,没有这个,就不成其为跨世纪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
刘:这就是话语错位的根本原因,内部、外部乱做一团的根本原因。
钱:实际上这是很现实、很要紧、涉及面很大的问题,我们许多青年学者认为,它是一种文化策略,你要从正面回答就恰恰中了他的圈套。似乎人要批判现代西方文明的弊病,就会自动站在儒家的或伊斯兰的立场,而不可能是别的例如社会主义的立场。因为他们是政府知识分子,是为美国政府,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的。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主题话语,把它转变成三个文明冲突的话语,恰恰是一种概念的偷换。
邵:中国周边的国家是否可用儒家文明来概括?至少现在我是反对用儒教文明来统一中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按这样的设计,就会不知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了。
白:韩国儒教学会的副会长赵骏河在一篇文章中就把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和亚洲“四小龙”统称为“儒教文化圈”。许多中国学者对这个看法都表示认同,并加以呼应。这些都对意识形态中心不能不发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