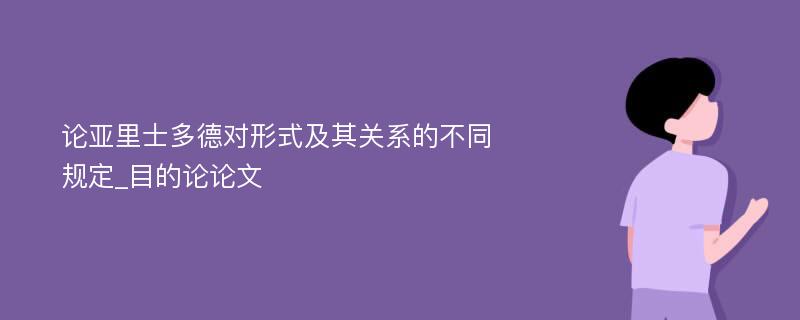
论亚里士多德对形式的不同规定及其相互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里士多德论文,相互关系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2.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3)05-0041-07
“形式”(eidos)(注:这是按汉语拼音方案拼写的希腊文,二者的对应关系见苗力田 先生主编的《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后记”。)一词源于动词idein(看见或观看),它可以表示用肉眼所见到的一物之外观或形状(shape),也可以表 示用灵魂之眼所见到的一物之内在结构或本质(essence)。另外,形式也有逻辑学上“ 属”(species)的意思,与“种”(genos)相对应(注:这里的“属”和“种”采用了苗 力田先生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依据希腊文原义的译法,即“种”的外延比“属 ”大,它与其他逻辑学著作及一般教科书中关于“种”、“属”的译法刚好相反。)。 其中,shape意义上的eidos与另一希腊词morphe(形状)同义,essence意义上的eidos则 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专门术语to ti en einai(其所是的是)。但在行文中,这两种意义 上的形式往往合在一起(如《形而上学》1029a30-32,1044b24,1045a24等处),因而区 别不大,我们可以把它们合称为form(形状或形式)意义上的eidos。由此,重要的区别 就在于form意义上的eidos和species意义上的eidos之上,这一区别构成了亚里士多德 实体学说的分水岭,他经常从这两个不同方面来讨论实体。认清这一区别从而看到亚里 士多德从多角度、多层次述说同一问题的写作风格和思想特点,对于理解他的形式概念 及其实体学说至关重要。本文主要以亚里士多德实体学说为限,清理他对形式的不同规 定,并试图分析这些规定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以澄清对他的一些误解。
一、形式之为“其所是的是”
“其所是的是”即希腊文中的to ti en einai,这个术语为亚里士多德所独创,它的 奇特之处在于其中的en,en是一种过去未完成时态。余纪元先生把它称作是一种“哲学 过去式”的用法,认为该词的英文直译为“what it was to be”或“what the‘to be ’was”,中文直译为“一个事物的过去之‘是’是什么”,他自己则主张直接译为“ 恒是”[1]。但在通行的译法中,英译者往往依据拉丁译法essentia直译作essence;汉 译者中,吴寿彭先生将它译为“怎是”(注:参见吴寿彭先生译《形而上学》,商务印 书馆,1981年。“怎是”这一译名非常精当,它从动态的角度凸显出了“是”的时间之 维,这让人不由想起了海德格尔的大著《存在与时间》(或《是与时》)。),常见的译 法则依照essence简化为“本质”,苗力田先生先后采用了“何以是”、“是其所是” 、“其所是的是”三种译法[2]。本文所采纳的是苗先生的最后一种译法。
从学者们对to ti en einai一词的翻译情况,我们不难看出它与eidos一词的内在联系 。因为eidos的其中一种含义也是essence。亚里士多德正是基于这一点而将形式等同于 其所是的是,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证明。
首先,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三,亚里士多德列举了四种实体:其所是的是、普遍、 种和载体;紧接着他又区分了三种载体:质料、形状(形式)和由两者构成的东西。在他 考察完质料载体并将组合体暂时悬而不谈时,他在该章末尾处说:“应该考察的是第三 种实体,这是最大的难题。”[3](1029b1)如果跳过随后的一个插入段,第四章应接过 上一章的话头而考察“第三种实体”(即形式实体)。可是,亚里士多德在第四章中却只 字未提形式,而是转过去讨论其所是的是。由此,余纪元推测,他在此实际上是将形式 等同于其所是的是[1]。
我们认为上述推测是合理的,因为亚里士多德在否定质料为最优先的实体时依据了两 条标准,即“可分离和‘这个’看来最最属于实体”[3](1029a30)。这两条标准恰好适 用于除了质料以外的两种载体,也就是说由两者所构成的个体(组合物)是分离的,但它 不是最为严格意义上的(即第一实体意义上的)“这个”。因为“当此物述说彼物时,它 并不是个这个,正如白净的人(即偶性的个体——引者注)不是个这个一样,因为这个只 属于实体。”[3](1030a3-5)另外,形式则是个“这个”,但它又不分离存在(纯形式除 外)。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称谓是某一形式,或某一这个。”[3](1049b1-2)同时,“ 这个只属于实体”,只属于其所是的是。这就构成了一个三段论推理:大前提为“形式 是一这个”,小前提为“这个即其所是的是”,因而结论就为“形式即其所是的是”。
其次,亚里士多德还多次直接宣称形式即其所是的是。如他所说:“动物的灵魂,就 是理性实体,是形式,是特定身体其所是的是。”[3](1035b15-17)他在用“四因说” 探讨何为人的形式时也说:“他的形式是什么?是其所是的是。”[3](1044b1)类似的地 方还有很多,如1032b1-2、1032b13-14、1035b32等处。当然,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下去 ,那么就将发现形式与其所是的是的等同并非完全的等同,两者也不是可以互相替换的 同义词,它们之间还有一些细微差别。在这点上,中世纪《形而上学》的伟大注释家托 马斯·阿奎那认为,形式与本质(即其所是的是,拉丁文译本将to ti en einai转译为( essensia)之间的差异在于:1.“形式是一物之本质的一部分”,形式与本质正如灵魂 与人性的关系;2.“形式使一物成为实现的,它与质料相关。而本质则与主体相关。” [4](591-592页)所以,我们可以把其所是的是当成是形式的一个规定,而不能将二者完 全等同。
“形式之为其所是的是”是亚里士多德对形式的一个最重要的规定,其他规定大多由 此引申而来。此规定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通过“这个”为桥梁来沟通形式与其所是 的是。“这个”(tode ti)是实体的代名词,尽管亚里士多德实体观前后有所变化,但 “实体是这个”的说法从未变更。但什么是“这个”呢?“这个”在很多场合即指个别 事物(the individuals),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中关于第一实体的提法[5](2a11-13) 更加深了这一看法。但这只是它的一种含义,如果继续把这种含义带到对于“形式是一 这个”的理解中,就将产生重大误解。此处的“这个”不再指代个别事物,而是指其所 是的是,指本质意义上而非主体或载体意义上的实体,偶性的个别事物在上面1030a3-5 处的引文中,甚至连实体都算不上(但这也只是一个极端的观点)。澄清这一片面理解对 于认清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实体观的转变及定义理论等问题 。
二、形式之为“这类”
从字面上看,这一规定似乎与前一规定相矛盾。在前面,亚里士多德把形式规定为其 所是的是,形式是一“这个”(a this),而此处形式又与“这类”(toionde,the such )纠缠在一起。这个“矛盾”实际上是形式理论乃至整个实体学说内部巨大张力的表现 。
亚里士多德说:“形式所表示的是这类,而不是这个。它既不是这个也不受限制,但 是人们却从这个制作出、产生出这类来,然而一旦被产生了,这个类也就存在。”[3]( 1033b24-26)必须指出的是,此处“形式不是这个”中的“这个”和“形式之为其所是 的是”意义上的“这个”含义不相同。如前所述,其所是的是意义上的“这个”不是指 作为偶性而存在的个别事物,而是个别事物的本质或形式;相反,上面引文中的“这个 ”却正是指个别事物,所以,“形式之为这类而不是这个”并未推翻“形式之为其所是 的是(即这个)”这一既成论断。但是,也必须指出,此处的“这类”又确实有“普遍” (universal)之意,因为形式也是某种普遍[3](1036a29)。那么,这又是否会危及形式 作为实体的既有地位呢?
普遍在亚里士多德笔下几乎就是柏拉图理念的别称。在《范畴篇》中,作为种属的普 遍曾被当作是第二实体,《形而上学》卷七章三也在列举意义上将普遍算作实体中的一 员,但在该卷章十三、十四、十六三章中,亚里士多德又反复论证普遍不是实体。其理 由在于:1.实体为个体所独有,而普遍则是共同的且依存于他物;2.实体是主体而非主 体的述词,而普遍则是对主体或载体的述说;3.普遍只是一种属性,如果普遍是实体, 那么1)属性将先于实体,2)定义将无法成立,3)将导致“第三者”的论证,4)实体也不 可能构成。这些理由又可归结为一点:“普遍只能表示这类而不表示这个。”[3](1039 a15-16)而实体一直都是一“这个”,如果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也是这种理念意义上的普 遍或这类,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实体。
但是,就在同一个地方,他又提出了赞成普遍是实体的观点,他说:“尽管普遍不允 许作为其所是的是,但它们仍然寓于其中,正如动物寓于人和马之中……因为普遍仍然 是某物的实体。”[3](1038b19-22)这真让人大惑不解。同是普遍,同在一章的内容中 ,亚里士多德居然得出如此对立的两个观点!这是否又是一个矛盾?我们认为这并不矛盾 ,因为两处的“普遍”含义各不相同。当普遍作为一种共同属性时,它就不是实体,例 如,在“苏格拉底是个白净的人”这句话中,“白净的人”只是一个普遍述词而非实体 ;而当普遍作为属或类时(如《范畴篇》中所指的那样),它就是实体,例如在“苏格拉 底是人”这句话中,“人”就是苏格拉底的实体,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为什么既否定又肯 定普遍是实体的原因。与此相关联,在“形式之为这类”的规定中,如果“这类”指属 性意义上的普遍,那么形式就不再是实体;如果“这类”指属种意义上的普遍,那么形 式“仍然是某物的实体”。从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论述(上引1033b24-26)来看,“这类” 恰好是属种意义的普遍,正如“人”是苏格拉底的属一样。所以,形式仍然是实体。与 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特别防止一种普遍流行的错误倾向,即把作为“这类”的形式和具 体的个别事物之间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因为形式虽然 有其抽象性,但这种抽象并不是一种与具体和个别截然对立的抽象,它是“这个这类” 。当它指代“其所是的是”时,它恰恰就是一种最具体最个别的东西。两者之间的关系 正如著名哲学史家文德尔班所说:“类就是个别实体中自我实现的共相……类之存在只 是由于类作为个别事物真正存在的本质而在个别事物中自我实现……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类也有权利得到作为本质的形而上学意义。”[6](第193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第一,“形式之为其所是的是”(即“这个” )与“形式之为这类”两个提法并不矛盾。第二,两种提法中形式一词的含义各不相同 。前一个形式是用哲学分析方法解剖具体事物而得到的结果,它是本质意义上的形式; 而后一个形式则是用逻辑概括方法抽象众多事物而得到的结果,它是属意义上的形式。 此处的抽象即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分离,但它又不是如柏拉图那样代表事实上的分离, 它们不是在现实中而是在思考之中进行的分离[3](1027b29-30)。
三、形式之为“内伏的是因”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提出了五个衡量实体的标准,其中第五个标准为:“实体 具有这样的特点。它既在数目上保持同一,而且通过自身变化而具有相反性质。”[5]( 4b17-18)学者们普遍认为,亚里士多德通过这一标准而挽救了在自身内部发生矛盾变化 的现象实体(即个体)。举例来说,苏格拉底由白的人变成黑的人,这并未否定苏格拉底 本人的存在,苏格拉底作为苏格拉底而存在的本质也即其内在形式并未发生变化。此处 “通过自身变化而具有相反性质”这一标准也为亚里士多德后来实体观的转变(即由主 体转为形式)埋下了伏笔,它暗示了实体自身的一大特点——能够由自身而发生变化。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形式当作是一物“内伏的是因”,它使一物由潜在变为实现 。
“内伏的是因”一说是借用了陈康先生的译法,他说:“所谓‘内伏的是因’即是‘ 相’(‘埃多斯’的另一义)。”[7](258页)亚里士多德在解释实体时说:“内在于那些 不述说主体的东西中,是存在原因。例如灵魂对于动物。”[3](1017b15-17)这里作为 动物存在原因的形式实体,就是陈康先生译作“内伏的是因”的东西。
把形式规定为事物“内伏的是因”是亚里士多德较为常见的一个说法。如他的“四因 说”中就有所谓“形式因”的说法;其次,他在解释原因时也说:“(原因的另一个意 思)是形式或模式,也就是其所以是的原理。”[3](1013a27-28)最后,他在探讨一物生 成的原因时也说:“把潜在的球形变成现实存在球形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正是每一个的 其所是的是。”[3](1045a31-32)这里其所是的是即形式,形式是一物得以实现的内在 “是”因。
亚里士多德对形式的这一新规定充分反映了其哲学中具有生存论特征的一面。生存论 研究的是世界万象何以“一个否定一个,处于辩证的不安中”,研究“生命的自我否定 与超越的矛盾”。[8](36页)生存论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秘密诞生地,黑格尔也以此 来解读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他说:“柏拉图的理念一般地是客观的东西。但其中缺 乏生命的原则,主观性的原则,而这种生命的原则、主观性的原则却是亚里士多德所特 有的。”[9](289页)一般的观点大致认为柏拉图哲学辩证法意味浓厚,在他的著作中时 时跃动着诗人内在不安的思想火花;而亚里士多德似乎显得更为平和、冷峻,充满哲人 深沉睿智的静观冥想。黑格尔的评价却与此相反,倘若我们细读《形而上学》卷七章七 、八、九和卷八、九,我们将不得不诚服于黑格尔的上述论断。在这些部分中,亚里士 多德着重从动态的生存论角度与潜能——实现学说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其实体学说并尤 其强调了形式在其中的地位。著名研究家谷思里(W.K.C.Guthrie)由此而认为,对于亚 里士多德的形式,最为重要之处在于它与功能(function)的等同,形式并非一种静止的 状态,而是一种不断的实现活动[10](232页)。形式的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实体 与属性、形式与质料之间的对立,也充分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哲学辩证综合的内在特性。
形式之为“内伏的是因”也反映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具有“努斯”(nous)精神的一面。 努斯精神与逻各斯精神同为希腊哲学的两大构成要素。逻各斯精神集中表现为从早期自 然哲学以来对万物本原和本质的不懈追求,亚里士多德对形式的前两个规定即是这一精 神的内在体现。努斯即是阿那克萨戈拉的“心”或理智。“在万物之中,它是最精粹和 最纯洁的。它有对万物的一切知识和最大力量。”[11](146页)万物的分离、旋转运动 都是由“理智”所推动、所安排的,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来源于对万物运动原因的考察 。此后,恩培多克克勒以“爱”、“恨”作为万物的推动力量;德谟克利特以虚空来解 释万物的运动,并把由精细原子所构成的灵魂或心作为运动的根源;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又进一步将努斯精神内化为内心的“灵机”(或灵异)和灵魂的“回忆”。在此过程中, 努斯精神逐步向主体回归,亚里士多德则一方面把与质料相结合的形式作为事物“内伏 的是因”;另一方面又把纯形式作为万物之外的第一推动力量,纯形式的推动作用是由 于万物皆有内在的追求“好”的本性,而自动地趋向于纯形式这一最终目的(最大的“ 好”)。
四、形式之为目的
目的学说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一个极富特色的组成部分,它可被划分为自然目的论、 技术目的论和理性目的论三部分[12](129-142页)。其中技术目的论主要涉及一般产品 和艺术品(在希腊语中,技术和艺术统称为技艺tekhne)的制作。在一般产品的制作中, 亚里士多德习惯于举铜球的例子,制作铜球即是把球形这一形状(形式)制作到作为质料 的青铜之中[3](1033b10-12)。因此形式既是铜球的“是因”又是青铜(质料)所要追求 的目的。在艺术品如诗歌、舞蹈和雕塑等的创作活动中,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强调 艺术对于声音语音、动作和颜色图形等艺术形式的摹仿[13](1447a14-30),艺术所摹仿 的对象——灵魂中的形式——就成为艺术创作的目的。所以,技术活动即是对形式的摹 仿,技术目的论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自然目的论,因为技术追求形式即是以追 求自然为目的[14](199a16)。相比于技术目的论,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目的论和理性目的 论着墨更多,而且也提出了“形式之为目的”这一相同结论。
尽管亚里士多德曾对“自然”(phusis)一词做过多种不同规定,但《物理学》中较为 常见的说法是将自然等同于质料和形式[14](194a14,199a32-33)。在质料和形式二者中 ,他又更倾向于把形式当作自然。如他所说:“自然就应当是在自身中具有运动本原的 事物的形式和形状,这种形状或形式除了在理性上外,不与事物相分离。而且形式比质 料更是自然,因为每一事物在其现实地存在时被说成是这个事物更为恰当些。”[14](1 93b4-9)在潜能——实现和质料——形式的类比学说中,形式即实现,质料即潜能,这 是“形式比质料更是自然”的根本原因。作为自然的形式只能在理性上(即在思想上、 原理上和定义上)而不能在存在上与质料相分离。另外,自然目的论也意味着自然本身 就是目的,“‘何所为’和目的与达到目的的手段是同一的,而且自然就是目的和‘何 所为’。”[14](194a27-29)对上面两个结论作一简单归纳就是:1.形式是自然;2.自 然是目的;所以3.形式就是目的。亚里士多德也说:“形式就是目的,其他一切都是为 了这目的的,那么,形式就应该是这个‘何所为’的原因。”[14](199a33-34)并且, 由于作为目的的形式内在于质料中,目的与达到目的的手段一致,所以,亚里士多德的 目的论乃是一种自满自足的内在目的论,而不是那种机械的目的与手段相割裂的外在目 的论。
在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中,我们可以把《物理学》中的实体论当作由《范畴篇》过 渡到《形而上学》的中间环节,它基本上还是主体和载体意义上的实体[14](185a31-33 ,190b1-5)。但它更着重从运动角度来说明实体,这就必定促使其实体观由载体朝形式 方向发展,因为形式或自然“是在自身之内具有运动本原的事物”[14](193b5)。同时 ,对物理运动的探讨又促使他去寻求一个最初的第一动者,第一动者是自身不被推动的 运动者,而且是唯一的,“永恒的,是其他事物运动的本原或始点”[14](259a13-14) 。但亚里士多德又特别强调第一动者“不是作为运动的目的,而是作为运动的本原”[1 4](243a3),它只是运动的动力因而非目的因,第一动者还不是万物运动所要朝向的最 终目的——最高的善,至善乃是专指理性目的论中的纯形式。可见在自然目的论中,亚 里士多德并未过多地强调作为目的的形式所具有的形而上的超越性意义。
对亚里士多德理性目的论的探讨必须先从两个相关概念入手,它将引导我们从另一方 面揭示形式与目的之间的内在等同。在希腊文中,energeia(实现)是由前缀en-(在…… 之中)和ergon(功业、辛劳)合并而成,表示运动过程,也可译作实现活动;entelekheia(现实)则由en-和词根telos(目的、终极)的变化形式合并而成,表示运动 结果,有“达到目的”、“圆满完成”之意。所以实现和现实都与运动有关,“运动就 是能被运动的东西作为能被运动者的实现”[14](202a7-8,202a14)(原译文为现实,现 依苗先生笺注本改译为实现——引者按)。实现与运动的区别在于,运动只是达到目的 的手段,实现则是寓目的于其中的运动,实现活动本身就是目的[3](1048b29-36)。所 以形式作为在质料中的实现,也是目的。从目的这方面来看,我们也可得出“目的即形 式”这一相同结论。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并非僵死不变之物,它是具有自我实现力量 的能动的目的,万物皆由其内在目的之推动而实现由潜能到现实的转化,目的就是事物 的内在形式或本质。黑格尔就习惯于把亚里士多德的eidos(形式)直接转译为目的[9](2 93页)。形式与目的的等同或许正是其“三因合一”(运动因、形式因和目的因)的理论 前提,“三因合一”也表明希腊哲学中的努斯精神和逻各斯精神在“形式之为目的”这 一规定中实现了统一。作为目的的形式不仅是努斯冲动的安息之所,而且也是逻各斯言 说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对形式的前三个规定均在“形式之为目的”这一 新规定中实现了完满的统一。
在构成可感实体的质料与形式这两者中,质料由形式推动而发生变化,变成形式;而 形式相对于更高一级的形式又成为质料,它也要向着更高级的形式变化。但这种变化不 能无限地进行下去,否则将陷于黑格尔所谓的“恶无限”之中而不能自拔,因而“必然 要有个停止”[3](1070a4)。根据这一“无穷倒退不可能”原则,亚里士多德从逻辑上 推出了一个最初动者的存在,它推动万物而本身不动,它作为万物之初,“是永恒、是 实体和实现活动”[3](1072a27)。这一永恒的实现活动就是无质料的纯形式,即所谓的 “隐德来希”(entelekheia之音译),万物的最高目的——至善,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心 目中的神。要注意的是,此处的最初动者(也即纯形式)不同于《物理学》中末两卷的第 一动者,它们的区别在于:1.第一动者是从寻找最初的动力因角度而推导出来的,而纯 形式则是从质料——形式与潜能——实现的类比学说角度,通过寻找最高的目的因而推 导出来的;2.第一动者可最终归结为一种内在的实体,它与世界密切相关,而纯形式则 可最终归结为一种超越的实体,它就其自身而言是一个绝对分离存在的最高实体,与世 界毫无关系。
五、上述各规定间的内在联系
以上我们只是简单地、平面式地清理出亚里士多德在其实体学说中对形式的四个不同 规定,下面我们还要进一步探讨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在下文中 分别将形式之为“其所是的是”、形式之为“这类”、形式之为“内伏的是因”和形式 之为目的这四个命题简称为A命题、B命题、C命题和D命题。
首先,让我们返回到A、B两命题。如前所述,它们分别对应于形式一词的两层含义,A 命题中的形式是本质意义上的形式;B命题中的形式则是属意义上的形式。但由这两个 不同规定,就引出了关于形式到底是特殊还是普遍的长期争论。如R·阿尔布里顿(R·Albriton)认为形式并非共相,而是为每个个体所特有的东西[15]。也就是说形式是特 殊的,而没有什么普遍的形式。D·K·莫杰克(D.K.Modrak)则批评这一看法,他认为形 式并不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因为1.形式为同一属内成员所共有,各成员之间的差别并不 取决于形式,而取决于质料;2.如果形式为个体所特有,那么形式将如同属性一样成为 个别的东西,但形式乃是实体而非属性。由此他认为形式是一种普遍,但又不是属性意 义上的普遍[16]。另外,M·L·吉尔(Mary Louis Gill)也从定义的对象——即普遍的 形式——角度批评了特殊形式之说[17](33页)。罗斯(W.D.Ross)则徘徊于两者之间,认 为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很成功地解决这一“矛盾”[18](211页)。
在上引各观点中,我们倾向于赞成D·K·莫杰克的看法,但要对它作出一些补充。因 为当形式作为定义所要揭示的对象时,形式是一种种属意义上而非共同属性意义上的普 遍;当形式作为个别事物的内在本质时,形式与个别自身“完全同一”[3](1031b20), 它恰恰又是一种最具体最独特的东西。所以,对形式的理解不必仅仅局限于普遍与特殊 的对立模式中,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A命题中的形式侧重于从 存在论层面揭示实体之为实体的内在根据;B命题中的形式则主要是从定义层面也即知 识论层面来述说实体。论述角度不同,对形式的规定也不同,但不同的两个方面并不是 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撇开普遍与特殊的对立不谈,我们就可认为B命 题中的形式如同A命题中的形式一样,也是本质意义上的形式。例如,在“苏格拉底是 人”这个命题中,“人”作为属意义上的形式就恰好揭示了苏格拉底的本质。所以,两 种形式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分别从存在论和知识论层面共同揭示了一物的内在本质。
其次,“本质”之义不仅是A、B两命题中形式的共通之处,而且也是亚里士多德对于 形式所有规定的共同纽带。既然形式就是本质,那么它也就是事物的内在原因和根据, 也即其“内伏的是因”。并且一物之所以成其为自身,就在于它实现了其本质,因而本 质又是事物所要追求的目的。这样,亚里士多德就通过形式一词的“本质”之义而将形 式的诸多不同规定串通为一,从而使其形式理论成为一个较为融贯的整体。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A、B、C三命题最终皆以D命题为归宿。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 在D命题中完成了他对形式的论述,也使其实体学说达到了最终的统一。因为A、B、C三 命题中的形式归根结底只是一种内在的形式,它们不能和质料相分离,而是内居于可感 实体之中。而D命题中的形式则可以作为纯思的逻辑设定而成为一种超越的形式,它可 与个别可感实体相分离,这种纯形式即至善,至善既是“三因合一”的交汇点,又是万 物所要追求的最高目的。这样,亚里士多德就在“形式之为目的”这一规定中达到了所 谓可能性、现实性和“隐得来希”的高度统一,哲学由此而上升到了一个“普遍的环节 ”[9](294-295页)。对此,谷思里也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最终在其对目的论 的再次强调中达到了顶峰,他曾用这种目的论来解释自然——正如在各种技艺中一样。 ”[10](218页)另一位杰出的亚里士多德专家耶格尔(Wemer Jaeger)也说:“形而上学 ……最终达到了那最高的、无质料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一种“超越的目的”(a transcendent end),“它是这个世界一切可见的运动所直接指向的目的。并且,由于 它,自然现象也得到了‘拯救’。”[19](272页)
收稿日期:2003-05-30
标签:目的论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文化论文; 范畴篇论文; 苏格拉底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