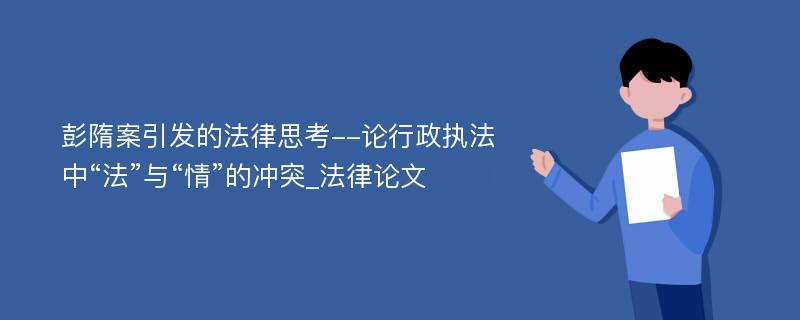
由“彭萃案”引起的法律思考——谈行政时效及行政执法中“法”与“情”的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效论文,行政执法论文,冲突论文,行政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074(2000)06-0007-05
据报道,彭萃是四川新龙县龙桥镇的彭先忠、黄万如夫妇于1992年2月在成都市青龙场(彭、黄在此经营一皮鞋铺)捡到的一名弃婴(当时出生只有1个多月),遂收养。1999年6月彭黄夫妇带着彭萃回到新龙县龙桥镇后不久,当地计生部门以四川省《计划生育管理条件》中“收养他人子女期满6个月,未按规定办理收养手续,又无正当理由的,视为计划外生育”的规定,决定向彭、黄夫妇征收计划外怀孕费、生育费共计6840元,彭没有在规定之日交款,龙桥镇计生办申请法院执行,彭仍未按法院的要求交纳款项,法院遂强制执行,将彭萃移交给县民政局。[1]
该案经新闻媒体报道后,引起较强列的反响,很多读者对计生部门、法院的行为不理解,同情彭、黄夫妇。按现有的法律规定看,计生部门、法院是在依法办事,而结果则得不到大多数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笔者由此案想到以下法律问题。
一、公共权力的行使,尤其是与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公共权力的行使应否有时效限制
时效是一项基本的法律制度,指法律确认的某种权利超过法定期限而不行使时,权利即归于消灭。刑事法律上有犯罪的追诉时效、行刑的时效,民事法律上有取得时效、消灭时效、诉讼时效。行政法律上也有一些时效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第18条、《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第7条,等等。
从行政法律上的时效规定来看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没有把时效作为行政法的一项原则确定下来,二是已有的关于时效的规定对行政相对人的约束比较严,相对人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某一行为或不完成某一行为,他即丧失了应有的权利或受到处罚,而对行政主体的约束较少,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时间宽泛,自由度很大。这种状况造成如下不良后果:
1.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由于行政主体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没有时效的限制,一方面使行政相对人应该得到的权利长时间得不到,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行政相对人得到了不该得到的利益,进行了不该为的行为,由于没有行政主体撤销该行为的时效规定,使相对人对该行为或该利益处于一种长时间的不稳定状态,经过较长时间后才被撤销,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如果及时撤销,损失就可避免或减少。如及时撤销彭、黄夫妇的收养行为,就可以避免彭、黄夫妇财产上的损失,避免伤害该夫妇与彭萃因长时间扶养而产生的父母子女之情。
2.影响行政主体的办事效率。行政具有广泛性、直接性和紧迫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迅速、高效是行政的一项基本要求,孟德斯鸠就断言:“行政贵乎神速”。所以,对行政行为没有时效的限制是与行政的效率原则不相符的,它无形中放纵了行政主体的拖拉和不负责任,促成了行政主体的“老爷”作风,使法律、法规、政令得不到及时贯彻,损害了国家、社会的利益。
3.给我国的法制建设带来负面影响。依法行政是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依法行政要求法律对象公共权力行使这样的既涉及国家权力又关乎百姓利益的行为作出明确的规定:哪些该为哪些不该为,该为的如何为,在什么时间内为,按什么程序为,法律后果如何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行,才能保障公民权利得以实现。然而,由于现时生活中行政行为无时效的规定,使得行政相对人该得到的权利长时间的得不到,只得寻关系、走后门,拜门子,从而不旦滋长了掌权者的腐败,更摧毁了人们对法律的认同感,权大于法的观念根深蒂固,严重阻碍着法制建设。
造成这种状况的基本原因是民主观念还未深入人心。从立法者来说,行政法律思想还比较陈旧,对法律治理国家的功能认识充分,而对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的功能认识还不够,因而立法中注意对行政主体行政权的保护,比较忽视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护。当然这里有客观的因素,即由于法制建设步伐加快,立法任务艰巨、繁重,立法者的精力放在了那些亟须出台的法律上,而来不及就各种行政行为立法。然而,我们欣慰地看到《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已在保护相对人权利上迈出了突破性的步伐。我们有理由相信,法律的触角将会伸进行政时效这一领域。从行政主体看,承袭传统的行政管理观念,注重自己的管理功能,忽视自己的服务功能,注重权力的行使,忽视职责的履行,认为行政就是代表国家治老百姓的,老百姓就得服我管,自己是管老百姓的官。从行政相对人来看,权利意识比较淡薄,对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无可奈何,不能通过各种正当途径表达自己的意愿,因而在全社会难以形成约束行政权力的气氛。
然而,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全社会的民主思想、权利意识普遍增强,约束权力、监督权力的呼声愈来愈高,因此,完善行政时效制度势在必行。
完善行政时效制度首要的就是要把行政时效作为行政法的一项原则确定下来。这项原则的具体内容应包括:(1)一切行政法律规范和行政规章不溯及既往,法律法规特别规定对行政相对人有利的除外。(2)对一切能导致权利取得和义务消灭的行政行为均须规定时效。(3)导致权利取得的行政法行为,过了一定法定时间,权利自然取得。行政法行为既包括行政行为,也包括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如行政机关内部下级向上级的请示报告,凡日之内不批复即视为同意;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报告几日之内不答复即视为同意。(4)导致义务消失的行政法行为,过了一定时效,义务自然消灭。这里的行政法行为同样包括行政行为和相对人的行为。(5)超过时效的行政行为无效。(6)因超过时效带来损失的,应追究行政主体或其直接责任人的相应责任。[1]
在这些内容中,可能有人会对第(4)项提出异议。行政主体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行政相对人的义务即是国家应享有的权利,就因为过了一定的时间,相对人的义务消灭,这不明摆着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吗?的确,这个问题确实存在。问题是如果不因一定法定时间而消灭义务,则势必侵犯相对人的利益。在国家权力与公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保护谁,这不是笔者在此要讨论的。笔者注重的是造成两者冲突的原因何在?责任主要在谁?很显然,相对人是有责任的,他应尽义务却没有履行,然而我认为主要责任在行政主体,指引、评价、教育、督促、强制相对人履行义务是你的职权,同时也是你的职责,尤其是在相对人由于各种原因不知自己的义务或不知如何履行义务时,义务的履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主体采取积极的行为。正是因为你失职,义务人没履行义务,才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要追究责任的话,理所当然应追究行政主体或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而不应使相对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彭萃案发生时如果有以上时效制度,彭、黄夫妇收养彭萃而未履行相应的申请、登记等手续的行为就可能因过了法定时间(从收养之日起算已有7年零4个月了)而消灭相应的义务,收养发生法律效力,行政主体不能再对其进行处罚。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则应追究当时(成都市青龙场所在地)的有关部门的责任,因为他们疏于管理、失职。
二、如何处理执法中“法”与“情理”的冲突
“法”与“情理”的矛盾冲突是执法中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严格执法,其结果将有悖情理,令人难以接受,甚至引起老百姓对法律,对执法机关的不满,影响法律实施的效果;依情理,又有损国家法律的尊严,经过不懈努力,好不容易才获得的一些法律权威,执法中又要以“情”代“法”,岂不弊大于利吗?
处于这种两难境地,执行者应如何处理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找到“法”与“情理”冲突的原因。笔者认为在我国“法”与“情理”的冲突是由如下原因造成的:
1.法的相对稳定性与社会发展的不间断性的矛盾。法是对一定社会关系的调整,社会不断发展,社会关系不断变化,而法则不能随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而变化,法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朝令夕改的法无法给人们的行为作出指引,无法让人们预测自己该如何行为以及行为的法律后果,因而不是法。即使法律中有预测性条款,一方面数量有限,另一方面也可能预测不科学、不准确而与发展的社会关系不相适应。因此,用“不变”的法和预测可能不科学的法去调整变化的社会关系,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法”与“情理”的矛盾。
2.立法者认识的局限性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的矛盾。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一方面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另一方面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要受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科学技术手段等约束,作为我国的立法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国务院等虽然能克服个体的认识上的局限,但作为人的集合体,它同样受人的认识的局限所影响,正如徐国栋先生所说:“历史已经证明立法者并非万能,他们不过是推到立法者位置的常人,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他们同样可能预料不到。我们的认识有什么局限,他们可能有同样的局限。”[2]因此,它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并不都是客观实在的真实反映,并不全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是千疮百孔的。”[2]这样的法律、法规在客观现实中实施,当然会产生与“情理”的冲突。
3.法的价值取向与“情理”的价值取向的差异性。本文所说的“情理”有二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指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准则,以上两个方面的“情理”都是从这个层面来说的。二是指社会公众依他们对公平、公正的理解而形成的对事物评价的一种标准。以下两个方面的“情理”是从这个层面来说的。
法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站在维护统治秩序的高度所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具有国家意志性,而“情理”则是民众对具体事物是否公平合理所作的评价,它带有很浓的感情色彩。尽管在我国国家与民众之间没有根本利益上的冲突,但毕竟两者所站的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因而评判的标准就有所不同,对同一事实自然就会有不同的判断。
4.法的相对抽象性与社会关系的复杂多变性的矛盾。法律规范有的明确、具体,有的则较原则、较抽象,即使是明确、具体的法律规范,相对于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而言它总是抽象的,它必须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不可能、也没必要对每一具体的行为作出规定。因此,用这种相对抽象的法来调整复杂具体的社会关系时,难免会有不符“情理”之处。
找到了矛盾产生的原因,执法中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尽量解决矛盾或尽量缓解冲突。
如果是法律本身的问题,包括法的相对滞后性(即前面所说的稳定性所带来的结果)、立法时的局限所留下的不科学之处以及法的相对抽象性,则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办法来解决:[3]:
第一,解释法律。执法机关在执法中遇到由于法律本身的问题将会引起与“情理”的冲突时,应及时向有关有权解释法律的机关提请法律解释,将自己对该案的处理意见附上,有权机关根据法的精神和基本原则,结合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或具体的实际情况,对该法律条款进行合理解释。“解释并不是被动地、消极地去发现立法者的未曾明显表述过的意图,而是由解释者从法律的目的和法律规定之间的逻辑关系出发,去阐明法律中应该包括的意图。[2]因此,解释法律可能改变被解释条款的愿意,赋予新的内容,从而解决矛盾。
第二,执法者自由裁量。自由裁量方法又称衡平方法,指执法者有权根据个别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据公平、正义原则作出处理,避免因机械适用法律而使处理有失公正。法学家梅里曼是这样论述衡平方法的:“衡平原则表明,当法律条文的一般性规定有时过严或不适合时,当某些具体问题过于复杂以至立法机关不能对可能发生的各种事实的结果作出详细规定时,法院运用公平、正义原则加以处理是必要的。因此,凡有类似的问题发生,最好是由法官根据衡平原则作出判决。”[4]梅里曼在这里虽然讲的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扩大到执法者,因为行政机关等执法部门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完全可以碰到法官在审判案件中出现的以上情况,而且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比法官的审判活动更复杂、更琐碎、涉及面更广,影响更大,因而更需要自由裁量权。然而我特别要强调的是,自由裁量权一定要在公平、正义的框架内行使,离开了公平、正义的自由裁量就根本不是法律上所讲的自由裁量,而是执法者的随心所欲。尤其是行政机关中,由于行政执法的监督还不象法院司法那样比较完善,因此执法者公平正义的裁量更显得重要。
第三,适用一般原则方法。一般原则方法是指将某一法律条款适用于解决某一特定情况时将会造成明显的不合“情理”的后果,或某一特定情况找不到恰当可用的法律条款时,执法者可引用指引该条款的一般原则来解决问题。一般原则方法在不少国家早已被采用。《意大利民法典》规定:“如果一条明确的规定不足以解决争议,可以适用同类案件或相类似案件的规定;如果仍不够清楚,则根据国家法律秩序的一般原则进行判决。”《瑞士民法典》第一段这样写着:“法官在缺乏可适用的法律规定时,可根据习惯判决,无习惯法时,则根据其作为立法者所确定的规则来判决”。勒内·达维也说:“在西班牙,引用这样一些原则是有法律根据的,西班牙民法典第六条在可能有的法源中列举从西班牙各法典与法律中推论出来的普遍原则。”[5]我国学者也认为一般原则(或称基本原则)既是行为的准则,也有审判裁决的功能。
如果是“法”与“情理”的价值取向不同而造成的矛盾,执法机关应严格执法,决不能以“情理”代法,作出与法相违背的事情。这一点非常重要。由于长期的封建意识的熏陶,长时间的缺乏法制教育,民间的一些认识和做法是违法的,如把抓到的小偷打伤、打残,甚至打死认为是在“情理”之中;与强奸犯“私了”,认为他也“血”(指钱)弥补了被害人的损害就合“情理”了,司法机关不能再“法办”他了;出嫁了女儿不能回娘家继承父母的遗产;嫁出去的妇女即使没迁走户口,没在男方所在地分得责任田也不能再在原籍保留责任田,等等,甚至一些被奉为美谈的如父母把自己大罪不犯,小事常犯,经常骚挠邻里的儿子除掉的“大义灭亲”之举,与法律的精神相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执法机关如果迁就当事人去寻找合乎“情理”的结果,实际上就是蔑视法律,是在破坏法治。这在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花了很多精力才有了初步法制的今天是非常有害的!甚至可能前功尽弃。当然,同样重要的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执法机关应利用各种手段,采取各种方法向当事人及其周围的人宣传法律,解释法律,使他们懂得法律,并逐步支持法律,用法律来规范、衡量自己的行为。
联系到彭萃案,在还不能运用时效制度解决的情况下,执法部门(这里指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可以向上级部门请求解释法规:彭、黄夫妇未按法律程序办理收养手续是否有“正当理由”。上级部门可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认定有“正当理由”,本案结果将是皆大欢喜;如果上级部门认为无“正当理由”,执法部门就应执行法律,但在罚款的数量上是否可以“自由裁量”减少数量,一方面向社会警示了该做法是不合法的,应受处罚,另一方面对彭黄夫妇又显得公平些。
此外,要指出的是本案法院在执行中将执行对象搞错了,应执行的对象是彭黄夫妇的财产,而不应将彭萃强制移交民政部门。
本案给我们带来的另一个思考就是如何抓好农村的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农村是普法的重点,农民的法律意识如何,法律知识怎样,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法律建设。没有农村的法治,没有农民的法律觉醒,我国的法制就无从谈起。同时,农村又是普法的难点,农民的文化水平以及各方面素质偏低,农民人数众多,农民组织松散,居住分散,以及外出务工的流动性等,都给普法工作带来了困难。如何切实有效地抓好农民普法工作是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的一项艰苦的工作,也是法律工作者应该重视的一项课题。希望这项工作不久将会有突破。
标签:法律论文; 行政相对人论文; 行政主体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行政法基本原则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行政执法论文; 行政立法论文; 社会法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行政诉讼法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