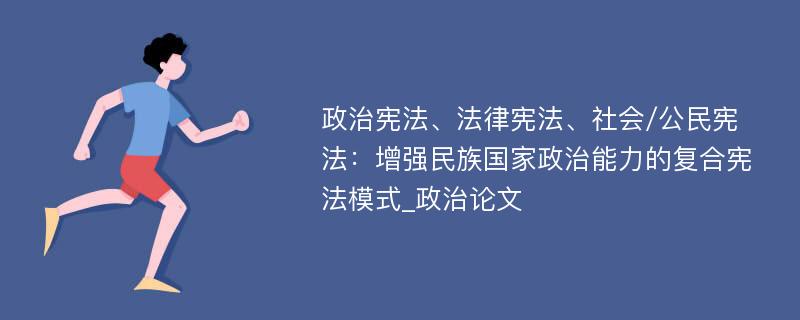
政治宪法、法律宪法、社会/公民宪法——民族国家政治能力增强的复合宪法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法论文,政治论文,公民论文,民族论文,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掀起了一股摆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然而自获得独立后,有很多国家出现了政治动荡、军人专政、政治衰朽的局面。以亨廷顿为首的一批政治学家对政治不稳定的现象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并提出了加强政治制度化的理论(注:亨廷顿提出了衡量制度化水平的四组对应的标准,即制度的适应性/刻板性、复杂性/简单化、自主性/从属性和内聚力/不团结。参见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一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此后,关于民族国家政治稳定、政治秩序和政治能力等问题成了政治研究的热点。与这种侧重于从政治制度视角的研究传统不同,本文试图从宪法建设与发展的角度,探讨在利用与整合现有宪法资源的前提下,增强民族国家政治能力的途径,并根据宪法在法理性质上的三重性或宪法的三种不同的发展形态,提出一种政治宪法、法律宪法和社会/公民宪法的复合宪法的政治能力提升模式。
一、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
对于政治能力这一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取罗伯特·杰克曼的分析框架(注:Robert W.Jackman,Power without force:the political capacity of nation-states,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1993.)。杰克曼认为,政治是因利益和价值分配引起的冲突,因此,政治能力就是政府解决冲突的能力,政权用政治手段解决冲突的过程,也就是权力实施与贯彻的过程。这一分析框架的优点是:不仅仅把国家的政治能力理解为一种单一的政治权能——一种政策贯彻能力或以资源提取能力为核心的国家能力(注:参阅施雪华:《政府权能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更解释了为什么民族国家会具有这种政策贯彻的能力和资源提取能力,以及为什么这些国家在这些能力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政治能力体现在两个维度,或者说,它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制度与合法性。在制度层次上,政治能力体现为制度的能力,这又具体表现为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国家的实际年龄和实行宪法以来的代际更替年龄。他认为组织生存的可能性会随着组织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已经定型化,组织行为的一般模式得到稳定,个人和组织的角色被固定下来了。因此,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年龄越长的国家,它对环境的调适性也就越强,因而它的生存能力和政治能力也就越强;组织代际更替年龄越长的国家,它的政治能力也越强。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权威主要是克里斯玛型权威,而这一权威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把自己的权威制度化,但新秩序的制度化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其中,第一届领袖的顺利继承和继承规则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成功孕育成功的机制下,随着时间的流逝,领袖职位的继承将更可预见,日后的继承过程也将更加惯例化和制度化。因此,代际更替年龄越长的国家,由于这一惯例和制度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在领袖继承问题上会更加稳定。
政治能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合法性。他认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是权力的实施与贯彻。合法性又体现在领袖和政权激发同意和服从的能力。人们在关注组织意义上的制度之外,还必须关注政治领袖激发同意和服从的数量和能力。因为合法性的反面是积累起来的对政治秩序的挑战,而公民通过非正常渠道来挑战政治秩序表明,他们不相信正常渠道能为他们追求自己的政治利益提供一个有效的机制,因为根据理性人的假设,正常渠道外的挑战,意味着他们估计到,他们有机会来获得更高的利益,以抵消非正规政治行为的高成本,而且这种行为说明了,在参与者看来,正常渠道的无效性恰恰表明政权对他们的挑战无能为力,政权也不堪一击。因此他的具体指标是国内冲突的多少,或者说,通过非正常渠道参与政治的程度(主要体现为暴力挑战既存政治秩序的程度)。这样,政权有效地使用政治手段解决冲突(即不需暴力就能解决政治冲突)的能力也就是政治能力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政府越依赖暴力手段来解决冲突,就越会损失自己的合法性,它的政治能力也就越低。
由此可见,以宪法为核心的宪政制度是杰克曼的政治能力分析框架的基础,宪法与宪政制度,也就成了提升政治能力的途径。然而,在这些新兴国家普遍缺乏一种宪政民主的历史传统,因此,思考在一个缺乏宪政传统的社会如何利用固有资源建设宪政,并因而增强自己的政治能力的问题就成了政治学家们的理论任务。在学术史上关于宪政的起源与成长有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是强调历史演化的社会学观点,它强调妥协与商谈,以及在不断的妥协中向宪政制度进化着;与这种渐进的观点相比,第二种观点更加强调意识形态和制度的自觉设计,强调理性的作用。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制度的设计就像是在汪洋大海中修造轮船,一方面,他们只能运用手头现有的材料来进行制度设计;另一方面,他们不能忽视对短期效应的考虑。如果忽视制度设计的直接的即时的效果,一味地着眼于长远的、最终的设计,这就可能要导致制度之轮很快就有被大海吞没的危险(注:Jon Elster,Claus Offe,and Ulrich K.Preuss,Institutional desig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这样,整合现有的宪法资源,以建设宪政制度提高政治能力就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首选。
二、宪法的三种发展形态
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后,一般都会制定一部宪法,然而有了一部成文宪法,并不等于就建立起了一个宪政制度和宪政政权。莱温斯坦从本体论的角度把宪法分为规范性的宪法(normative constitution)、名义性的宪法(nominal constitution)和语义性的宪法(semantic constitution),只有第一种宪法即规范性的宪法体制才称得上是宪政体制。要解释一个成功的宪政政权,我们会遇到两个独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宪法制定的问题,即在第一代人要成功地制定宪法,第二个问题是宪法实施的问题,即在未来的若干代人中,能成功地利用它去指导和制约政府。如果把宪法的生命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宪法的制定阶段与宪法的实施阶段,我们便可以看到三个层次上的宪法,或三种形态的宪法,或宪法在法理上的三重属性:宪法首先是政治的,即宪法是政治的宪法(political constitution),这主要体现在立法过程中,它强调的是宪法目的及内容的政治性;宪法其次是法律的,即宪法是法律的宪法(juridic constitution),这主要体现在司法过程中,它强调宪法作为一种高级法的法律实施;最后宪法是社会的,即宪法是社会/公民的宪法(societal/civic),这主要体现在执行过程中,它强调的是宪法与社会和公民的互动性。这三种宪法分别体现着宪法发展的三个不同的形态与水平。从政治宪法,到法律宪法再到社会/公民宪法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低到高、由简到繁的演化过程。(注:Karl Loewenstein,Political power and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pp.123—163.)
(一)政治宪法
在性质上,宪法首先是政治的,它是政治的宪法。这个意义上的宪法所对应的词应该是" constitution" ,突出的是其" constitute" 的功能。政治性是宪法的生命所在,是它存在的一切依据和基础。从宪法的制定动因看,政治动因是宪法制定的最主要的动力,它要解决的都是当时的一些结构性的或原则性的政治问题,宪法的批准与通过正是政治冲突的规则化的解决。里默教授认为,宪法的制定与批准就表明它在政治上有了一种创造性突破(比如美国宪法制定时就在宗教自由的问题上进行了彻底的解决),而这种创造性突破就意味着“对麻烦问题的成功解决”(注:[美]肯尼思·W·汤普森主编、张志铭译:《宪法的政治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5页。)。
宪法是因某种原因而制定出来的,同时,它也要因某种原因而生存下去。正如沃尔特·墨菲指出,宪法承担着以下几种职能:它是政治共同体的一面旗帜,它掩盖着或体现着政治生活的真正现实;它是政府的组成章程;它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卫士;它还是一份契约,一种象征和一个抱负(注:Walter F.Murphy,Constitutions,constitutionalism,and democracy,in Douglas Greenberg and Stanley N.Katz(eds.),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transi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3—25.)。内森·布朗依据宪法的最主要的目的,把宪法划分为两种类型,即服务于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与非服务于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在他看来,第二种宪法的目的主要有:象征性(symbolic),这表示国家已经建立,这是一种主权的象征(注:Nathan J.Brown,Constitutions in a non-constitutional world:Arab basic laws and the prospects for accountable government,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pp.10—13.),正如惠尔指出的,各国起草和通过宪法是因为人们希望就其政府制度范围内有关问题的声明有一个新开端(注:惠尔(Wheare,K.C.)著,甘藏春、觉晓译:《现代宪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意识形态性(ideological),这时宪法主要是在对外宣示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大政方针;效率性(enabling),这时它起的作用主要是强化政权的执政能力,是要使得政府更加稳定和更具有政治效率。
宪法是一幅权力地图(注:Ivo D.Duchacek,Power maps:comparativ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s,American Bibliographical Center-Clio Press,1973.)。它规定着规则的选择与规则下的选择。它构架着(structure)权力体系,它通过自身的建构性条款(constitutive clause)搭建起一座权力大厦,并规定着谁有资格进入这个体系,由谁分别占据着这个体系中的不同的权力位置,由谁获得相应的权力数量。它的这种权力分配体现在纵向和横向两个层次:在纵向上,它规定着政府的层级,并更主要地在权力体系的中央与地方各个层级上进行着权力的分配与界分。同时,它还在中央层次上进行着权力的横向划分,规定着由谁行使着什么权力并明确地划清它们之间的界线;它把这个权力体系的各个部分有机地组织起来(organize),规定着各权力之间的分工与配合,让它们和谐与协调地共同完成着这个权力体系的使命;它给各个权力部分提供着运行规则(regulative clause),通过否定性的条款,指导并规制着(regulate)它们的运行,以不让它们越出权力的轨道。
此外,它预先规定着纠纷的应对机制。这样当各个部门与各个层级发生权力纠纷时,它就能在宪法框架内提供着解决冲突的机制,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种如布坎南提出的“作为危机防范机制”的宪政体制。(注:布伦南、布坎南著,冯克利、秋风等译:《宪政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哈贝马斯认为,危机是指疾病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将决定身体的自我康复能力是否足以使人恢复健康。(注:尤尔根·哈贝马斯著,刘北成、曹卫东译;《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因此,宪法机制应对着各种危机的到来,宪政制度的真实存在也就意味着机体本身具有一种高强的自我康复能力或自疗机制。
总之,宪法的制定,为现行的体制提供着合法性的基础,从法权的角度论证着这个权力结构的正当来源。通过这部宪法的指引,这个权力体系就像是一部高度精密的机器在有条不紊地运行着,一切权力都按部就班地持续着,工作着。
对于宪法发展的三个层次而言,政治宪法是其第一个层次,也是最低的一个层次。对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要结束它们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获得政治能力,它们就必须首先恢复这种政治宪法的顺利运行,并为这种运行创造着良好的外部条件。而这首先又体现为政治格局中的精英们恪守宪法作出的关于权力分配与运行的规定,如果宪法规定国家实行议会制,那么总理或首相就应该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拥有最高的行政权力,而且这种认识应为各精英一致遵守与服从,如果宪法规定国家实行总统制,那么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总统就应是真正的最高行政长官,这种规定也应为各个精英一致遵守与服从。政治宪法的这种顺利运行,表明着各政治力量对游戏规则的接受,并在政治游戏中共同创造着政治的可预期性与稳定性。政治力量格局的发展是无法预测的,所以在制宪时各政治力量都尽力按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通过今天的政治行动能够预期明天的结果、防止自己明天受害的原则,参与宪法制定过程。针对制宪时的无知之幕,普热沃斯基指出:“在力量格局和力量关系并不明朗时采纳的制度,是最有可能在各种条件下持续生存下去的制度。”(注:Adam Przeworski,Democracy and the market: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88.)
宪政制度的最大优势不在于它能在经济上创造什么惊天奇迹,而在于它能缓解经济和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压力,可以给共同体带来一种可预期性与稳定性。通过宪法的否定性条款,宪政把自我约束的理念适用于政府,然后适用于它在任何地方可能发现的重大权力机构。所以有了政治宪法上的平稳运行,这种尊重宪法的理念就可以一直扩散和渗透下去。只有实现了政治宪法的真正的运行,才能为实现宪法的第二个阶段奠定基础。
总之,政治宪法是提高民族国家政治能力的最基本的途径。
(二)法律宪法
法律是不断成长的,作为法律之一种的宪法也是不断成长的。(注:本杰明·N·卡多佐著,董炯、彭冰译:《法律的成长》,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只不过这种成长是通过司法过程的法律成长。宪法经由司法的成长过程,是一个把宪法请下神坛、并且把它具体化的过程。从宪法实施的角度来看,宪法是一种法律,只不过它是民族国家内的根本法、高级法或最高法。因此,作为法律的一种,法律宪法是宪法发展的第二种形态。这个阶段的宪法,其对应的词是" constitutional law" ,这时强调的是" law" 的属性,只不过这时它是一种有自身特点的高级法而已。宪法作为一种高级法,它具有法的形态,因而也应该具有法的特性。实体法的最明确的特性是它的可司法性和可解释性。如果说政治性是宪法的生命的话,那么,可司法性就是它的灵魂。这种可司法性与可解释性体现在宪法案件的裁定、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上。
各种实体法都可以看成是一种权利规定。比如劳动法,就可以看作是对劳动者法律权利的规定,以及对侵害这种权利时所应受到的责罚或这种权利受到侵害时的一种救济;而合同法,也可以看成是对缔约双方权利与义务的一种规定,以及对侵害这种权利时所应受到的责罚或这种权利受到侵害时的一种救济。法律宪法也像各种实体法一样,可以看成是一种权利规定。只不过这种权利是一种作为公民的由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它是其他一切权利之母。因此,一旦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了侵害或公民侵犯了别人的宪法权利,他们就应该相应地受到责罚或获得救济。
无法在法庭上审理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而缺乏救济手段的权利也不是真正的权利。只有能接受法官审判的宪法才是真正的宪法(constitutional law),也只有能获得救济手段的公民的宪法权利才是真正的权利。当布朗夫妇因地方公立学校拒绝接收其儿子入学而起诉托皮卡地方教育委员会时,联邦最高法院给了他儿子以公民权利的救济;当美国现任总统小布什在2000年总统选举因佛罗里达州选票重新计票问题而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起诉,以违反平等保护条款为由,请求终止佛州的重新计票时(注:参见拙文《论美国宪政历史中宪政正义的转变》,载《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他的宪法权利也得到了救济。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活着的宪法。
正如德沃金(注:罗纳德·德沃金著,信春鹰等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中文版序言,第3页。)指出的,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争端,人们就会不再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的一个工具而加以依赖,他们就将寻找其他的办法来解决争端,法律将日益成为与社会和经济生活无关的事情,政府也会再次失去它的引导该社会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如果宪法发展到了法律宪法的形态,真正成为法庭上的宪法和公民手中的宪法,那么这种宪法就获得了最大的权威。
除了宪法案件的审判之外,宪法的成长还可以经由司法解释与司法审查和宪法修正的途径来实现。法律是不断发展与不断成长的,虽然法律条文可能不变,但可以对它们作出适应形势的新的解释。因此,宪法及其理论应该适应时势与环境的变化,不同时代应该有不同的宪法及宪法理论。W.I.詹宁斯指出,“宪法是一种转变中的事物,像万花筒的色彩一样变幻不定;对宪法运作的研究包括对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考察,正是这些力量造成了民众及其社会各阶层的观念、愿望和习惯的变化。一个公法法律家如果不理解宪法的这些方面,就不会理解宪法。——的确,我们可以断言:法律家只有了解法律产生的社会条件以及法律施加于受治者的后果,才可能理解法律”(注:W.Ivor.詹宁斯著,龚祥瑞,侯健译:《法与宪法》第一版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宪法修正与解释,一方面可以归因于宪法制定时的漏洞,这可能源于制宪时的条件限制;另一方面可以归因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从宪法制定的角度看,影响宪法制定者的最初的两大因素是,他们对现在与将来实质结果具有的偏好;他们对体现在宪法中的规则将如何影响这些结果的预期。这两大因素影响着宪法的制定,也就必然会影响着宪法在日后的运行及随之而来的解释与修正。
罗伯特·利普金认为,美国制度的设计采用的是一种二阶段设计模式,对多数决定必须有一个反思与审查的过程。在他的宪法革命理论中,司法审查就作为一种赋予审慎过程以反思或第二次思考的能力的机制在发挥着作用。(注:Robert Justin Lipkin,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s:pragmatism and the role of judicial review i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Preface,IX—XIII.)通过二阶段模式,一个使谬误暂时通行的判决必定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被推翻,这正如1954年沃伦法院审理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注: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347 U.S.483(1954).)推翻了1896年的普莱西诉福格森(注:Plessy v.Ferguson,163 U.S.537(1896).)一案,又如1937年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罗斯福总统有了法院改组方案的动议后对洛克纳诉纽约州(注:Lochner v.New York,198 U.S.45(1905).)一案(虽然在当时不能说那一案的多数意见和判决是一种错误的判决)的推翻,从而结束了实质性正当程序的洛克纳时代。
宪政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司法维系,是政治问题的司法解决。如果没有这种宪政制度,如果政治冲突不是在议会或法庭上来解决,那它就必然要通过其他非正常的渠道来解决。所以说,通过司法化给宪法规则提供了一种历史性的合法性,这是宪法固有的不确定性的定期的解决。但是正如约翰·芬恩(注:John E.Finn," The civic constitution:some preliminaries" ,in Sotirios A.Barber and Robert P.George(eds.),Constitutional politics:essays on constitutional making,maintenance,and chan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p.41—69.)指出的,法律性的宪法意味着要把政治争论置于法律的语言和修辞之中。但是只有法律家才具备这种法律语言和修辞的知识,因此尽管表面上通过解释性的实践活动,大众参加到了宪法的维系与变革中来,(注:布鲁斯·阿克曼着,孙文恺译:《我们人民,宪法变革的原动力》,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但是宪法维系与发展的使命还是实质性地落在了法律家们的肩上。
一旦我们把宪法维系不单看成是争论规则的适用,更确切地说,一旦我们把宪法看成是宪法规范与价值在一代又一代人中间的维系、传递和延续,那么很明显,宪法解释就只是宪法维系这一伟大事业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尽管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总之,法律宪法是实现民族国家政治能力提升的最有效的途径。
(三)社会/公民宪法
宪法应是法律宪法,但又不应当止于法律宪法,它还应该上升一个层次,即社会/公民宪法,充分体现出它的第三个特性即社会性。这种社会性又体现在它与公民在政治生活与市民社会中的密切关系。社会/公民宪法是宪法发展的第三个形态,也是其最高阶段。
在市民社会中,公民们往往把宪法看成是一种契约,而契约要求的是合作;或者把宪法看成是需要其他制度支撑的一种制度(注:Stefan Voigt,Explaining constitutional change:a positive economics approach,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9.)。卡尔·多伊奇也指出:“使得事物前进的力量的是合作的习惯,而不是威胁。”(注:Karl W.Deutsch,The nerves of government,New York:Free Press,1966,p.123.)在这一阶段,宪法已经完全融入了公民的社会生活,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次事件中,公民们在与公共权力进行政治对话并实施政治行为时,总是受到一种宪法思维的自觉指导。可以这么说,一个社会的自治与自组织能力越强,程度越高,它就越是能依据宪法或法律来与国家进行交流,也越是能用法律手段制约着国家并守卫着自己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正如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公民的参与和实践,美国公民已经培育出一种民主合作的传统,同时经由公民的法律意识及宪法的司法化,美国宪法也就真正成了保护公民权利的最有力的救济手段。
通过对英国普通法的发展历程的分析,20世纪初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在《普通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有两个重要因素,在整个法制史里抗衡着经济的压力和阶级的利益,并且已经使每一个时代法律的发展免于为经济力量和阶级冲突所左右。这两个因素就是:第一,坚持法律是从现行的规则和学说的类推中有逻辑地发展;第二,努力使法律表达人们向往的永恒不变的理想。(注:罗科斯·庞德:《普通法的精神》,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法律从现行的规则和学说的类推中有逻辑地发展,就是指法律是从公民在市民社会中、在经济活动中、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一切习惯向法律的深化与层次的提升,因而最终发展成了" common law" (" common" 一词本身就有习惯的意思)。
在市民社会中,组织的多元化、文化的多元化与差异性等等,都要求建立一个非权威主义的、用社会整合取代社会控制的社会秩序。文化承认政治提出的问题、社会公民的身份认同的问题,都对宪法提出了承认的要求,要求从合作(注:David Sciulli,Theory of societal constitution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而不是从控制的角度来思考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团体、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要求宪法是一部能承认与容纳文化差异的宪法,这也就是要求发展出一种社会/公民宪法。
正如芬恩指出的,在公民宪法下,宪法问题得到了更多的表达机会(注:John E.Finn," The civic constitution:some preliminaries" ,in Sotirios A.Barber and Robert P.George(eds.),Constitution al politics:essays on constitutional making,maintenance,and chan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p.41—69.),而政治体系也在这种宪法问题的公开的表达与争议中,在不断积蓄着宪法的合法性和体制改革的合法性。总之,社会/公民宪法是防止宪政衰朽的最有力途径,也是民族国家政治能力提升的最深入持久的途径。
三、提高政治能力的途径:复合宪法模式
宪政民主制度是一种多元化的制度,是一种充满着制度性宽容的制度(而宽容与信任是弥补宪法共识不足的有力工具),宪政的精髓在于法治、程序和责任。因此,宪政制度是迄今为止最能提高杰克曼意义上的政治能力的制度。
如何在利用和整合现有宪法资源的前提下,维持与增长政治能力,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面临的现实课题。虽然宪法不能等同于宪政制度,但宪法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民族国家在获得独立后,多数国家已经有了一部成文宪法。它们之所以还深陷在政治不定的泥潭,经常发生宪政挫折(注:参见拙文:《宪政挫折的分析框架》,载《新视野》2004年第6期。),最直接的原因是没有实现第一层次上即政治宪法意义上的宪政。与非洲、拉美国家相比,一些阿拉伯国家政治要更为稳定,这正是因为它们的宪法已经发展到了政治宪法的阶段。(注:Nathan J.Brown,Constitutions in a non-constitutional world:Arab basic laws and the prospects for accountable government,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
有了政治宪法,就具备了获得政治能力的最基本的途径。为了让政治能力的发展具备制度性动力,民族国家还必须具备法律宪法意义上的宪法,这样宪法问题就能化解为日常政治问题,让公民去感受,并为宪法体制找到一种合法性和惯例化的渠道。法律宪法是民族国家获取政治能力的最有效的途径。
然而,最重要的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宪法形态是社会/公民宪法意义上的宪法,通过市民社会中的公民意识的增长,通过社会与国家的界线的界分,法律和宪法成了公民穿在身上的用来保护自己的外套。这种宪法已经融入了公民的生活当中。
在这三种宪法形态中,法律宪法高于政治宪法,而社会/公民宪法又高于法律宪法与政治宪法,在政治宪法和法律宪法概念框架下公民都无法参与到法律中去,只有在公民宪法下才能完全发挥公民的作用。综观既有的宪法理论,法律家们强调的往往是某种形态的宪法,或者至多是强调政治宪法与法律宪法的结合,而忽视了社会/公民宪法这个层次的宪法形态,更不用说借助它,乃至通过它与政治宪法和法律宪法的整合,来获得民族国家政治能力的源自根基的不竭之源。
如果说政治能力获得途径有三种由低向高发展的途径,即第一种途径,单一的政治宪法途径;第二种途径,政治宪法与法律宪法结合的途径,以及第三种,政治宪法、法律宪法、社会/公民宪法复合途径,那么在不同的途径下,政治能力的增强幅度也会呈现层次上巨大差异。通过单一的政治能力提升途径,是一种力量单一、缺乏后劲的途径,不足以为民族国家带来政治能力的系统性复合性提升。只有通过一种系统性的、复合性的、全方位的途径,才能为民族国家培育出一种力量最为深厚、根基最为扎实的政治能力。
比较言之,第一种途径的政治能力最低,第二种途径居中,第三种途径下的政治能力最高,也最为恒久,因为通过这三种宪法形式的复合形式,民族国家可以得到一种制度性稳定,宪政框架下的政治稳定,而这正是民族国家政治能力的直接体现。第三种途径,即在利用与整合现有宪法资源的前提下,政治宪法、法律宪法、社会/公民宪法的复合宪法模式,是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政治动荡局面、实现制度性政治稳定、获取与增强政治能力的最有效的现实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