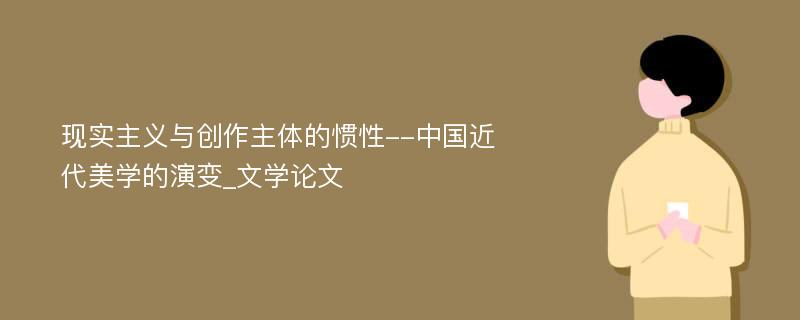
现实主义与创作主体的惯性——审美在现代中国之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惯性论文,中国论文,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实主义作为创作主体表达现实世界的一种创作方法,是创作主体按照现实生活的具体状貌及其本来特征,通过形象的真实描写揭示生活内在特征的一种创作方法。古今中外的现实主义,虽然在总的原则上相同或相近,但由于不同地域、国家、或历史阶段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运用不同,使得现实主义在不同时期,表现出它的不同的内涵。
现实主义的概念自“五四”从西方进入中国以来,它如同忠实的情人,伴随着中国文学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在不同的历程中,它虽然以不同的风貌出现,然而我们还是能在各种文学思潮中和文学理论里遇到它。并且还为此不断地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激烈的论争。乃至当下在经济转型之际的各种思想观念交汇中,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坛上,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仍然是最引人瞩目的一波。
为什么现实主义能在中国文坛上处于如此特殊的位置,而且始终成为文学理论界争论的焦点,这正说明了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实用性”和“投和性”。因为现实主义所负载的内容适用于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需要;这种“投合性”又恰好切合了中国文人所特有的儒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的传统的审美心态。所以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坛上,现实主义已形成一种惯性审美的方式。如果说“五四”、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是“革命”选择了现实主义,那么文革前的文学是“政治”选择了现实主义。而文革后的“伤痕”反思文学是“人性道德”选择了现实主义。进入80年代中期,现实主义虽然被西方各种思潮的“新鲜”感所代替而暂时失宠。然而到了90年代现实主义又以多种表现方式,再一次在文坛上显示出它强劲的生命力。
一
“五四”时期中国从西方引进了各种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但真正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倾向的仍然是现实主义。因为现实主义直而现实的文学指向,正切合了当时的“五四”社会批判的需要。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鲁迅为代表的创作者们,广泛地使用现实主义这一最直接的表达现实的形式。在那个时期的主要作品除了最有代表性的鲁迅《狂人日记》以外,还有叶绍钧、郁达夫的小说,郭沫若的新诗,以及冰心、欧阳予倩等人的剧作。他们在作品中,通过对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讴歌;对农民、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的主人翁的描写,以新的思想内涵和新的表现手法来批判封建制度,启蒙民众心智。
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君主专制,然而人们的思想仍还处在混沌愚昧的封建制度的状态之下。“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却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危机。从而表现出中国文坛上前所未有的现实主义的“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注:陈独秀:《新青年》,1917年《文学革命论》。)“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注:陈独秀:《新青年》,1917年《文学革命论》。) “ 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注:陈独秀:《新青年》,1917年《文学革命论》。)以此形成了中国式的批判现实主义。而且由此形成的“五四”文学主潮几乎又贯串着整个三十年新文学的始终,使得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在创作主体的审美心理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趋向性和专注性。
随着马克思主义自“五四”在中国的传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成为当时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基本依据。所以,作家面对现实,用“现实主义”这一形式来反映现实是无产阶级文人们当时根本的一个创作原则。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与阶级性的理论也被介绍到中国。例如1934年9 月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定义作了如下表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成为当时左翼文坛开展文艺论战中的重要思想和理论武器。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虽然出现了一些像茅盾《子夜》那样的现实主义艺术品味很高的作品。然而就整体来看,当时文坛上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与其说是作为人类高级审美活动与审美对象的产物,不如说是作为一定社会与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表征,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与武器而存在的。
虽然如此,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那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政治斗争压倒一切的岁月里,这种现实主义以它特有的“适用性”、“战斗性”发挥了别的文学倾向所难以企及也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到了40年代,现实主义这种文艺创作审美方式,在当时历史时期的现实土壤中,沿着它的自然朝向,更加稳固并自觉不自觉地“惯性”发展。例如,无论是在“国统区”或是“解放区”,创作主体虽然在表现上内容不一,但在形式上却都追求直而现实的表达方式。当现实主义走进解放区时,它脱下“批判”的外衣,唱着《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的陕北民歌,形成了歌颂“工农兵”的现实主义。正如周扬在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说到:“从斗争和工作中开始熟悉了体验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这就是解放区文艺所获得健康成长的最根本的原因”。“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而现实主义走进“国统区”表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文学的理论,都更注重表现普通民众的不幸与混乱时代的阴暗,带有批判现实主义的浓重意蕴。如巴金的《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北京人》,钱钟书的《围城》,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以及胡风及其七月诗派的理论与创作。
同一现实主义,在不同的“统治”地区,表现出不同的风貌。由于特定的环境所孕育的不同的文学作品的原因,在国统区,你不能唱着《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去反映法西斯统治下的现实;去揭露封建制度的黑暗。反之亦然,在解放区的创作者们也写不出《寒夜》和《四世同堂》。所以,无论现实主义的前缀如何变化,现实主义作为文学艺术反映现实的一种方式,它总是要体现出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总是随着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自己。不仅现实主义是如此,现实主义创作主体也是如此。例如,当时国统区许多以抒发个人感情为主要创作内容的作家,到了解放区,都转换作风,以主要的篇幅去再现人民群众在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中的历史功绩。丁玲的由《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转换,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二
在全国解放后的一个时期里,因受制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越来越成为通行的现实主义创作准则。一次又一次地“政治运动”,使社会生活日益政治化。而此时的文学,也以政治性的强化和艺术性的淡化走上了坎坷的道路。虽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与流行观念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如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陈涌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黄秋耘的《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等,强调现实主义要写“真实性”,要敢于揭露现实的负面,在创作上也出现了一批“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土地上》等。然而这些好的苗头刚一露头,就又由于“反右斗争”和“反修防修”的政治现实的需要,被“政治化”的现实主义所代替。
到了60年代,党的文艺政策再一次调整,使得现实主义精神在文学中有所恢复,如邓拓的《燕山夜话》,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电影《早春二月》《兵临城下》,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然而“文革”时期更为左倾的社会文学思潮扑面而来,不仅中断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且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十年动乱”和文学领域的黑暗。
检省十几年间的文学,不难看出,尽管在“政策调整”的“宽松”时期,现实主义创作者们,在题材、体裁上都有所拓展,但在创作方法上仍然比较单一。或是“批判”或是“揭露”的主题,也没有离开中国文人“忧国爱君”的传统审美心理。例如,最有代表性的是王蒙《组强部新来的年青人》。虽然他是在当代文学中第一次闯进了一个文学题材的禁区,正面揭露了我们党内的一些病变。然而在文中充满着“对党的赤诚的爱”,“尝试着把自己的幼稚的观察和思索的果实交给党。”(注:《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
从创作者们对现实主义方式的惯用,到现实主义精神的表现来看,现实主义这种惯性审美在他们的审美心理活动中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
三
粉碎“四人帮”专制统治的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得以复苏,并且以各种倾向表现出新的拓展。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反封建、反官僚、反特权;写改革、写知青等等。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以直面人生、说真话,抒真情、为人民代言,为真理呐喊,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的生命力。
应当说在新时期之初,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仍然显得主题趋同,方式单一。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些同样的创作倾向,可用一个“共名”来概括本身,便说明了这一问题。虽然在70年代末,王蒙的“意识流”的小说创作使文坛上大为惊奇,如《夜的眼》、《海的梦》、《春之声》、《布礼》等,使得中国文人惊讶地感到:文学还有这样的表达方式。这如同乡村里的孩子第一次进城见到摩天大楼一般,非常新奇。可见,由于中国长期的封闭,使得中国人传统的审美心理得以传统下去,这必然形成中国文人审美惯性的思维定势,使得文学创作形式形成了单一性。随他之后,尽管许多作家的创作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突破了那种不能颠倒的时间观念;突破了那种顺序的情节模式。如《爱是不能忘记的》、《人到中年》、《在同一地平线上》等等,都表现了结构与叙事的灵活性,并进入了人的内心世界的描写。然而这些尝试,还仅仅局限在文学的艺术表现方式上,局限在叙事方式上,并没有脱离现实主义的轨道。只不过是拓展了现实主义的空间,使现实主义摆脱过去那种单调的艺术表现能力而已。
文学发展到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多样化的经济发展,以及西方文学思潮的涌进和现代派、后现代派作品的大量译介,为文学艺术洞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一种强烈的新鲜感,激发着中国文人在文学创作上,开始了多种可能性的探索试验,文学的创作方式也出现了多样相竞的局面。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一批又一批具有先锋精神的文学作品的出现,使得中国文坛上出现从来未曾有过的百花齐放的新景观。虽然如此,由于“现代主义”的尝试,把形式的意义推到极端,便又走火入魔地进入了文学自娱的怪圈里。那种荒诞的意识流的描写和以反传统“性爱”的审美观的组合,使它们成为不似“现实主义”,也不似“现代主义”的“伪先锋”文学。虽然这期间出现了一些上乘之作,然而与同时期出现的现实主义的守望者们的作品相比,这些“上乘之作”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却显得黯然失色。而“守望者们”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炜的《古船》,黎汝清的《皖南事变》等作品,却更引人注目。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的缘由,和长期受现实主义作品的熏陶,在广大读者的潜意识之中,也形成了一种惯性审美。所以,对所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类的作品,暂时还消化不了。
这批“守望者们”虽然沿用了现实主义这一表现方式,然而却在创作上超越了以往的现实主义的“政治现实观”。他们很少以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去判断与取舍已经非常复杂化了的现实存在。作家多从社会、历史、道德、文化的角度观照生活,表现了创作主体对现实存在的广阔观察与包容态度。在经济转型这一特定历史现实中,表现出一种开放的现实观。现实主义历经风雨后,仍然显示出它的魅力和后劲,这恰好说明现实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然而这一“适用性”正是来自于它随着社会现实的演变而不断地更新和发展,以至于进入90年代,现实主义再一次地在文坛上展现出它的强劲的生命力。
四
80年代的后期,中国社会呈现出了非常复杂的局面。原有的经济体制的价值观念已经解体,人们普遍地失去了原有的心理平衡。空前的活跃和空前的紊乱,使整个社会笼罩着一种困惑、迷惘。现实的发展似乎越来越超出了普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想象能力,使人们越来越被推向一种尴尬无为、无可奈何的境地。面对这种现实,刚刚走进90年代的创作者们,并没有选择“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之类的先锋新奇手法,而是惯性地选择了现实主义。以池莉的《烦恼人生》(1987年)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以现实“还原”方式的现实主义,来描写“小我”在当下的各种真实心态。以一种平民化的审美追求,使现实主义再现活力。同样,《北京文学》从1994年第1 期起连续推出的“新体验小说”,更以创作主体生活亲历的写实描述,使现实主义逼近人民当下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
虽然“新写实”、“新体验”等在文坛上只是匆匆过客,然而这种意义大于行动的新尝试,在一定意义上,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出现起到了铺垫的作用。
进入90年代,从“新写实”到“新体验”乃至当下被称之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现实主义以它独有的惯性审美,再一次在文坛上显示出它的活力、魅力和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定势。这也是当前以谈歌、关仁山为首的作品为什么能在文坛上引起激烈的争论,并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根本所在。
谈歌等人,站在传统的儒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高度,通过写困境中苦苦挣扎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不仅“原生态”地写出当下百姓生活的艰难状况,而且以极大的胆量,尖锐地揭露出一批腐败分子的丑恶心态。并且在揭露中,通过《大厂》中的吕建国、袁工程师,章老师傅,《分享艰难》的孔太平,《苍天在上》的黄江北和反贪污局长等不同层次人物的塑造,反映出中国传统儒家“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民族精神,而且写出了中国在当下经济转型时期艰难中的希望和力量。
每个民族都有她的传统精神作为支撑点。以社团为本位的整体主义的儒家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核心,也是中国文人所特有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根本所在。
我们对现实主义文学,结合它的演进过程,和创作主体的惯性审美与中国文学的内在缘结的探究,并不是为了否定现实主义,而是为了更内在地认识它的特点,使之更好地面对它。对于任何事物来说,“特点”即是它的优点,又是它的缺点。所以,对于现实主义乃至由此体现出来的中国文人与现实主义所特有的内在缘结,既不能强调它的优点,也不能诘难它的缺点,只能随着社会现实的演变,让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去自我调节。
本文于1997年11月23日收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