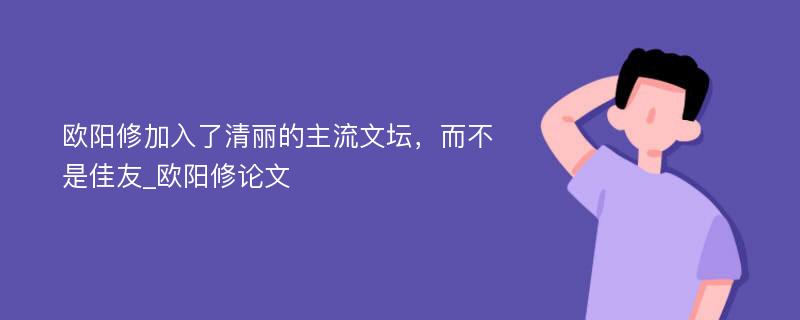
欧阳修入主文坛在庆历而非嘉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而非论文,欧阳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阳修在北宋文坛和中国散文史上有着公认的崇高的地位,其文学活动对宋文和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嘉祐二年(1057),欧知贡举,力挽狂澜,扭转时风,使古文运动获得重大的胜利,历来学者对此论述颇多。有一种模糊的认识,以为欧是在知贡举后被公认为文坛领袖的。事实是这样的吗?欧阳修究竟是何时入主文坛的呢?
学界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并不多。王水照先生认为:“从景祐元年(1034)到庆历五年(1045),是欧阳修政治道路和文学道路上又一个重要时期。”“欧阳修在文坛的地位也日益提高,终于成为公认的领袖。”(见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欧阳修散文选集》之序言),从“终于”看来,欧阳修之“成为公认的领袖”,当在这一段时间的下限——庆历。孙望、常国武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则作如下表述:“如果以庆历年间的《朋党论》、《醉翁亭记》等作为欧阳修散文创作高度成熟的标志,那么,嘉祐二年(1057)他主持礼部贡举时所采取的有关措施,则是利用科举考试来扭转科场文风的成功尝试。欧阳修主盟文坛以来所作的出色贡献,使宋代古文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里所说的“欧阳修主盟文坛以来所作的出色贡献”,显然包括庆历创作的成熟和嘉祐贡举的成功,则“主盟文坛”的时间上限也是在庆历。
把欧阳修“主盟文坛”或“成为公认的领袖”定在庆历年间无疑是正确的。我以为,欧阳修的文学活动大致可分为天圣起步、庆历奠基、嘉祐辉煌三个阶段,前者乃入主文坛之准备,中者见盟主地位的确立,后者显一代宗师的伟绩。本文拟以有关的资料和分析,进一步论证,欧阳修入主文坛应在庆历,而非嘉祐。
一
欧阳修于天圣八年(1030)进士及第,此前,朝廷多次下诏书,“欲矫文章之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 他步入仕途与文坛之日,恰是“学者变革为文”(《欧阳文忠公集·试笔·苏氏四六》)之时,时代为他提供了机遇,他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抓住机遇,一展身手。
在天圣八年礼部试前,欧阳修就认识了苏舜钦、苏舜元昆仲以及石延年等人。与欧同年及第的又有蔡襄、刘沆、孙抃、田况、石介、孙甫、尹源、张谷、刁约、王畴、王素、张先等;同年中制科的还有余靖、尹洙和富弼。在“最盛于文章”(欧阳修《上随州钱相公启》)的西京钱惟演幕府,欧又结交了诸多友朋,其中不乏后来从事政治革新和文学革新的志同道合的伙伴。西京的文学气氛极为浓厚,欧阳修与梅尧臣、尹洙尤为友善,相与创作诗歌古文。尹洙学古文在欧阳修之前,欧“服其简古”(《邵氏闻见录》卷8),以之为师,后来居上, 以致尹有“欧九真一日千里也”(《湘山野录》卷中)之叹。叶涛《重修(神宗)实录(欧阳修)本传》云:“是时,尹洙与修亦皆以古文倡率学者,然洙才下,人莫之与。至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为之唯恐不及,一时文字,大变从古,庶几乎西汉之盛者,由修发之。”西京这块文学沃土为新苗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欧阳修能充分利用有利的条件,广结文友,勤于切磋,不甘人后,刻苦创作,加上天资聪颖,因而很快超越先于他作古文的柳开、穆修、苏舜钦、尹洙等,令人刮目相看。韩琦《故崇信军节度副使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尹公墓表》云:“文章自唐衰,历五代日沦浅俗,浸以大敝。本朝柳公仲涂始以古道发明之,后卒不能振。天圣初,公独与穆参军伯长矫时所尚,力以古文为主次,得欧阳永叔以雄词鼓动之,于是后学大悟,文风一变。”范仲淹于庆历八年(1048)所作的《尹师鲁河南集序》,在肯定尹洙创作的成就后写道:“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文风一变”亦即欧在《试笔》中所说的“学者变革为文”。叶涛谓尹洙“才下”,韩琦称欧阳修有“雄词”,观尹、欧两家文集,高下判然而别。范仲淹说欧阳修“大振之”,足见欧水平之高、力量之强和影响之大。
西京任满,召试学士院,任馆阁校勘以后,欧阳修的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坛上的声誉鹊起、名望日盛,是与他在政坛上的敢说敢为、奋不顾身密切相关的。当石介因议论朝廷录用五代及诸国后嗣之事而被免召御史台主簿时,欧阳修作《上杜中丞论举官书》,为石介鸣不平;当范仲淹因指责权相过失,贬知饶州时,欧阳修压抑不住愤慨之情,作《与高司谏书》,痛斥其诋毁仲淹,落井添石,因而被贬为夷陵令。欧阳修的仗义执言、不怕丢官,赢得士大夫和舆论的广泛同情,韩琦、蔡襄、苏舜钦、梅尧臣等均赠诗相慰。欧离京及舟行途中,送行及看望问候者甚众,欧的声名随着他“沿汴、绝淮、泛大江”、赴贬所的经历而远播各地。
贬官夷陵是欧阳修遭到的第一次政治挫折,他没有消沉。离开京都,深入民间,接触社会实际,大大开阔了眼界。他勤于吏事,养精蓄锐,期待着重返政坛,再显身手。他也有了更多时间,以更为专注的态度投入创作。如果说在西京幕府时,欧阳修在文坛上已崭露头角的话,那么谪宦夷陵时荆南乐秀才及吴充、祖无择等皆登门或发书求教,可知欧阳修已有不小的文名。
欧阳修在文学道路上迈出坚实可喜的步伐,不仅表现在他已写出了日趋成熟的作品,如《上范司谏书》、《李秀才东园亭记》、《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夷陵县至喜堂记》、《峡州至喜亭记》、《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等,而且表现在正气凛然的《与高司谏书》和忧念国事的《读李翱文》以感慨淋漓、曲折尽致的文笔,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雄厚的创作实力,另外还表现在他发表了诸多创作见解,已形成了令人称道的文道观,对宋文基本特色的奠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明道二年(1033)作《与张秀才第二书》、景祐元年(1034)作《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景祐二年(1035)作《与石推官第一书》、《与石推官第二书》之后,景祐四年(1037)在夷陵,欧阳修又写了《与乐秀才第一书》、《与荆南乐秀才书》、《答祖择之书》,此后,还写了《答吴充秀才书》,对文道关系等作了明确完整的论述。事实表明,这位古文大师关于道须易知而言须易明、事信言文而不为怪异、中充实而发于外者辉光、骈文浮薄然亦有可取之处、文士不可弃百事不关于心等重要的理论观点,已形成于明道、景祐年间。换言之,庆历之前,欧阳修不仅从友朋的联络和散文的创作上,而且从散文理论的建树上,为此后的入主文坛做好了积极的准备。
庆历元年(1041),曾巩入太学,作《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称欧文“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说“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他奉欧阳修为韩愈的继承者。庆历二年(1042),曾巩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又称欧之“文章、智谋、材力之雄伟挺特,信韩文公以来一人而已”,足见欧阳修文坛地位之隆。
强至“以文学受知韩琦”(《宋史》卷356), “琦上奏及他书记,皆至属稿”(《宋史翼》卷26)。强至于庆历六年(1046)登进士第,后颇有文名,神宗皇帝看到韩琦的一份奏书,说:“此必强至之文也。”足见其文之不同寻常。皇祐二年(1050),他为韩琦所作的《代上新知南京欧阳龙图状》,以“主道吾盟,于变文章之淳”,称扬欧阳修的文学功绩;后又作《代上南京欧阳龙图状》,谓欧“文章大淳,坐复古道。制作一出,立为人模。”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同时代人很早地明确地尊欧为文坛盟主的记述。以韩琦的地位、强至的文笔给欧阳修加上文坛盟主的桂冠,应该是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自然是不容置疑的。
元祐策试时为苏轼所激赏而名列第一、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并擢馆职的毕仲游,在所撰《欧阳叔弼传》(欧阳修中子棐,字叔弼)中写道:“本朝庐陵文忠公起于天圣、明道间,主天下文章之盟者三十年。”由欧阳修逝世的熙宁五年(1072)上溯三十年,为庆历二年(1042),可见欧大致在庆历初已确立了文章盟主的地位。在欧逝世后五年出生的叶梦得也指出:“庆历后,欧阳修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避暑录话》卷上)文章盟主的令人倾服,于此可见一斑。
二
庆历初入主文坛的欧阳修,在而后的岁月中牢执文坛牛耳,地位越来越巩固,这主要表现在从政、交游和创作上。
首先,欧阳修对政治活动的积极投入不断提高着他的声望。
身为谏官,欧阳修全力支持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呈进大量献可替否的奏章,遇挫折而不气馁,奋不顾身地捍卫改革而不动摇。新政遭敌对势力的诽谤,欧阳修针锋相对地写了《朋党论》,劝仁宗皇帝“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当范仲淹、韩琦等相继以党议罢去时,欧“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干一人难犯之颜”,慨然上书,力陈仲淹等为“可用之贤”,谓“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这种极言直谏、无私无畏的举动在当时和后世都有不小的影响。庆历二年(1042),苏轼七岁始知读书时,即闻欧公之名。(见苏轼《上梅直讲书》)庆历三年(1043),石介《庆历圣德诗》传至乡校,苏轼从旁窃观,对欧公之为人不胜仰慕。(见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庆历五年(1045),苏洵至京师,亲见新政受挫、欧阳修等被贬,十分痛心。(见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曾巩亦为新政夭折、欧遭诬陷感愤不已,献书鸣不平。(见曾巩《上欧蔡书》)欧阳修遭到第二次沉重打击——贬官滁州,但他的人格却闪耀着光辉,声望不但没跌落,反而更高。韩琦在《祭少师欧阳公永叔文》中深为敬佩地写道:“公之谏诤,务倾大忠。在庆历初,职司帝聪,颜有必犯,阙无不缝。正路斯辟,奸萌辄攻,气劲忘忤,行孤少同。……人畏清议,知时不容,各砺名节,恬乎处躬。二十年间,由公变风。”至和二年(1055)冬,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派皇叔、北宰相等四贵臣陪宴,他们对欧阳修说:“此非常例,以卿名重。”(见欧阳发等撰《事迹》)庆历以后欧阳修声望之高竟然使异邦亦如此倾倒。
其次,欧阳修与朋辈后学的广泛交流继续扩大着他的影响。
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赞叹欧公为“大贤长者,海内所师表,其言一出,四方以卜其人之轻重”,又引欧公的话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由这句话可知仰慕欧之为人与为文者甚众。
在“环滁皆山”、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仍有诸多后学前来拜访求教。庆历七年(1047),曾巩至滁州拜见欧公,徐无党兄弟来谒,欧有《怀嵩楼晚饮示徐无党无逸》诗。前一年,有章生、孙生先后来访,欧均以诗相赠,《送章生东归》为“子以一身千里来”而感慨,《送孙秀才》则记下了孙生“迟迟顾我不欲去”的深情。刚刚进士及第的魏广也冒着风雪,远道来见欧公,欧作《送荥阳魏主簿》诗。从以上诗作不难看出门生后学对欧的钦敬、急于求教之心和欧对他们的关切之情。
欧阳修还通过文酒诗会、书信往来、作序铭墓等保持着与友朋密切的交往,在文坛上发挥自己的影响。汴京东园、滁州丰乐亭、扬州平山堂、颍州聚星堂、南京留守司府邸,是欧阳修与同僚宾客、门生故旧饮酒赋诗、畅叙情怀的地方。《寄题丰乐亭》之诗,从滁州寄向各地,苏舜钦、梅尧臣、 蔡襄等人的和诗又从各地寄往滁州。 作于庆历六年(1046)的《梅圣俞诗集序》,继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之后,提出著名的“穷而后工”之说。作于庆历末与皇祐初的《尹师鲁墓志铭》和《论尹师鲁墓志》则是碑志文的佳作和古文大师难得的经验之谈。欧阳修的文学活动涉及文坛和政坛的众多人物,他以刚直不阿、敢说敢为、笃于友情、乐于助人、虚怀若谷、好客荐士而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他的文章与道德、文学魅力和人格魅力紧密交融,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再次,欧阳修以成熟作品的不断涌现充分展示了他的实力。
庆历年间,欧阳修的创作获得丰收,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均诞生于这一时期。包括《朋党论》在内的大量谏章奏议之外,还有《释惟俨文集序》、《释秘演诗集序》、《梅圣俞诗集序》、《送曾巩秀才序》、《送杨置序》、《画舫斋记》、《王彦章画像记》、《醉翁亭记》、《丰乐亭记》、《菱溪石记》、《黄梦升墓志铭》、《尹师鲁墓志铭》等佳作问世,欧文已形成自己成熟而稳定的艺术风格。委婉曲折、一唱三叹、韵味无尽的欧文,以其独具的“风神”深深地感染着读者并受到他们的喜爱。以《醉》、《丰》二记为代表的传世精品展现了无穷的艺术魅力,《曲洧旧闻》卷3有“《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 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的记载。皇祐年间,欧阳修的创作精力仍十分旺盛,除完成《新五代史》外,还写出了《真州东园记》、《苏氏文集序》、《祭资政范公文》等好作品。
笔者曾泛览南宋以来诸多古文选本,如陈亮的《欧阳文忠公文粹》、茅坤的《欧阳文忠公文钞》、归有光的《欧阳文忠公文选》、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储欣的《唐宋八大家类选》、林云铭的《古文析义》、吴楚材等的《古文观止》、高步瀛的《唐宋文举要》等,并以欧文的入选情况作了统计。若取前十八篇的话,入选次数最多的篇目依次为《五代史伶官传序》、《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纵囚论》、《释秘演诗集序》、《五代史宦者传论》、《上范司谏书》、《送徐无党南归序》、《祭石曼卿文》、《岘山亭记》、《朋党论》、《梅圣俞诗集序》、《送杨置序》、《醉翁亭记》、《张子野墓志铭》、《秋声赋》、《苏氏文集序》、《释惟俨文集序》。这样,前文所列的欧阳修在庆历、皇祐年间创作的佳篇多数都在其中了。(《纵囚论》和《张子野墓志铭》写于改元庆历的前一年,即康定元年;《送徐无党南归序》写于皇祐五年的后一年,即至和元年。)十八篇佳作中写于嘉祐及以后的仅有《泷冈阡表》(其初稿《先君墓表作于皇祐年间)、《祭石曼卿文》、《岘山亭记》、《秋声赋》四篇。
综上所述,如果因欧阳修嘉祐二年知贡举,扭转时风,影响巨大,而认定其文坛主盟即在嘉祐,是不正确的。欧阳修入主文坛,或者说文坛盟主地位的确立,应在庆历而非嘉祐。
标签:欧阳修论文; 庆历新政论文; 宋朝论文; 梅圣俞诗集序论文; 醉翁亭记论文; 韩琦论文; 范仲淹论文; 文学论文; 朋党论论文; 古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