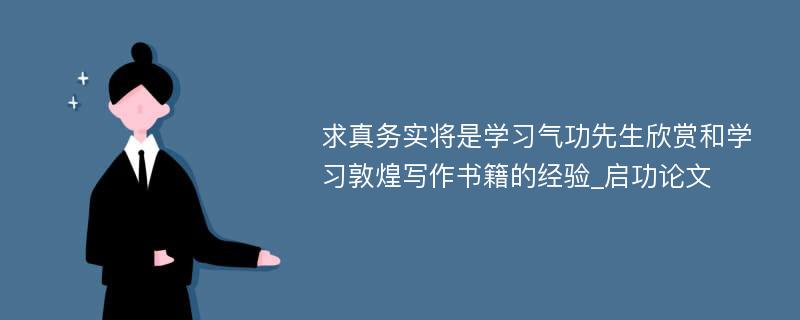
求真求实会于心——学习启功先生鉴赏与研究敦煌写本的体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写本论文,求实论文,于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2)03-0034-06
敦煌学界最早知道启功先生对敦煌写本的研究,大概是在1957年8月《敦煌变文集》[1]出版之后。《敦煌变文集》由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六位先生录校而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为收录最为完备的敦煌变文总集。启功先生不但负责迻录并主校了其中的《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欢喜国王缘》、《秋吟一本》和《苏武李陵执别词》五种写本,而且以其深厚的文献学修养与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为全书的校勘作出了宝贵的贡献。遗憾的是,该书出版不久,启功先生便被“派入右”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几乎被剥夺了教学与科研的资格,当然也不可能接着发表相关的论著了。
其实,启功先生对敦煌写本的研究,并不始于也不局限于对变文的整理。早在启功先生的青年时期,他在名家指点下鉴赏古代书画作品的同时,就已经观摩了大量的敦煌写卷,并以其科学的治学精神与特殊的鉴赏眼光,认识到敦煌写本在研究中国字体演变史和书法史上的重要价值。对于他个人经眼或购藏的敦煌写本,启功先生主要以题跋的形式,表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精审而独到的见解。本文即以启先生的几个题跋为主要依据,结合他的《论书绝句》、《古代字体论稿》等著述所体现的学术思想,来谈谈自己肤浅的学习体会。
一
目前我们见到的启功先生关于敦煌写卷的题跋,有《唐人写经残本四种合装卷跋》、《唐人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卷跋》、《唐人写经残卷跋》三则及《武则天所造经》、《米元章书〈智慧清净经〉》中相关部分,均已收入《启功丛稿·题跋卷》[2]。前三则原文不长,为便于叙述,不妨先将它们全文录引并略加说明如下:
唐人写经残本四种合装卷跋
右唐人写经四段,都百九十六行。己卯春日,偶过厂肆,见装潢匠人,裁割断缺,将以背纸作画卷引首,谐价得之,合装一卷。其一使转隽利,体势肥阔,疑出开元、天宝以后。其二字画古劲,犹存六朝遗意,“世”字“愍”字皆不缺笔。避讳缺其点画,始自高宗之世。此段纵非隋写,亦在显庆以前。其三格兼虞、褚,与昔见永徽年款者相似,惟圆润之中,骨力稍薄。其四结体生疏,非出能手,当是衲子之迹。而乱头粗服中,妙有颜平原法,不经意处,弥见天真。余结习难忘,酷耽书翰,凡石渠旧藏,私家秘笈,因缘所会,寓目已多。晋唐法帖,转折失於勾摹;南北名碑,面目成於斧凿。临池之士,苟不甘为枣石毡蜡所愚,则舍古人墨迹,无从参究笔诀。其确出唐人之手,好事家不视为难得之货者,惟写经残字耳。此卷饰背既成,出入怀袖,客座倦谈,讲肄暇晷,寂寥展对,神契千载之上,人笑其痴,我以为乐也。昔董思翁以唐写《灵飞经》质於陈增城,陈氏私割四十三行以为至宝。余今所得,四倍增城,而笔法之妙,不减《灵飞》,古缘清福,不已厚乎?赞曰:羲文颉画,代有革迁。真书体势,定於唐贤。敦煌石室,丸泥剖矣。吉光片羽,遂散落乎大千。晴窗之下,日临一本,可蝉蜕而登仙。人弃我取,尤胜据舷。信千秋之真赏,不在金题玉躞;濡毫跋尾,殆自忘其媸妍也。[2](P95)
跋中所述“己卯春日”为公元1939年春,是时启功先生还不满27周岁。“厂肆”指北京琉璃厂书肆。启先生尚记得此敦煌石室所出唐写本合装卷中有一段为《金刚经》残卷卷头,有一段为唐经生摹写颜体字的写经。该合装卷启先生珍藏了若干年,在1949年前经由东北书店雒君之手卖出,今不知流入何处。
唐人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卷跋
右唐人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首有断阙,尾损十五字,书体精妙,与世行影印邵杨(阳)李氏宝墨轩本相似,而笔势瘦健,殆尤过之。行间有朱笔句读,是曾经持诵者。己卯秋日,得之燕市海王村畔。用宝晋题子敬帖韵为赞。赞曰:虹光字字腾麻纸,六甲西升谁擅美。李家残本此最似,佛力所被离水火。缓步层台见举趾,日百回看益神智。加持手泽不须洗,墨缘欲傲襄阳米。[2](P297)
此卷启功先生亦于1939年得诸北京琉璃厂,后以之与同好交换藏品,今归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编为“北大D014号”。用原件跋语对照,“邵阳”排印误为“邵杨”;“行间”二句,原为“行间句读,朱墨灿然,是曾经持诵者”;赞后落款为“庚辰残腊元白启功书”,并钤“启功之印”、“元白居士”二印章,可见此跋语为1940年所作。该卷又有沈兼士、顾随、秦裕、贾鲁等四人的题跋。
唐人写经残卷跋
右唐人写《妙法莲花经》卷一《序品》后半《方便品》前半,共二百二十九行。硬黄纸本。前有“大兴乐氏考藏金石书画之记”朱文印。余以重值得之遵化秦氏。以书体断之,盖为初唐之迹。世字已有缺笔,当在高宗显庆以后耳。此卷笔法骨肉得中,意态飞动,足以抗颜欧、褚。在鸣沙遗墨中,实推上品。或曰:此经生俗书,何足贵乎?应之曰:自袁清容误题《灵飞经》为钟绍京,后世悉以经生为可大,虽精鉴如董香光,尚未能悟。夫绍京书家也,经生之笔,竟足以当之,然则经生之俗处何在?其与书家之别又何在?固非有真凭实据也。余生平所见唐人经卷,不可胜计。其颉颃名家碑版者更难指数。而墨迹之笔锋使转,墨华绚烂处,俱碑版中所绝不可见者。乃知古人之书托石刻以传者,皆形在神亡,迥非真面矣。世既号写经为俗书,故久不为好事家所重,而其值甚廉。余今竟以卑辞厚币聘此残卷,正以先贤妙用,於斯可窥;古拓名高,徒成骏骨耳。赞曰:墨沈欲流,纸光可照。唐人见我,相视而笑。[2](P298)
此《法华经》写本为启功先生珍藏的敦煌残卷中尺幅最大者,先生曾数次出示我一同观赏。先生另藏有一小段《妙法莲花经》残卷,前几年中国印刷博物馆正式建成,武文祥馆长向启功先生征集展品,先生遂将该卷无偿捐赠。
启功先生收藏的敦煌写卷,我还见过数件,其中有一册子装为几十个写本碎片合裱者,大概不为一般收藏者看好,故购入时价格甚廉,其实因为汇集了各时代、各字体的写本残片,甚具参照价值;有一为道经写本(卷背有僧人杂抄),书写精妙;另有三件系几年前从琉璃厂中国书店购进。这些因均无题跋,又待正式刊布,此不详述。
上录三则题跋言简意赅,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论断独到精彩,既涉及中国字体学和书法史上的关键问题,也体现了启功先生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
二
启功先生的题跋明确地指出了唐人写本真迹在我国字体学、书法史研究上的珍贵价值,可谓独具只眼。正如启先生在《古代字体论稿》中所指出的:所谓字体,即是指文字的形状,它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指文字的组织构造以至它所属的大类型、总风格。其二是指某一书家、某一流派的艺术风格。而前代对此的研究,所依据的多侧重于古代文献的记载和某些著名法书字迹。近现代由于考古发掘的发达,出现了较多的古代文字实物资料,丰富了研究对象。但是,可以说绝大多数的研究者,有的只是关注甲骨卜辞、钟鼎铭文、简牍记事、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内容,有的只是单纯欣赏某些“书法精品”,而不能从认识碑铭字迹与简牍及纸本墨迹的区别着手,透彻地解决字体、书法发展史上的根本问题。而在我国敦煌学界,从60多年前即已开始,真正从字体学、书法史角度来研讨敦煌写本的,启功先生实为第一人。
求真指伪是文物鉴定与研究的第一目标,启功先生正是以“真”为标准来探讨写本与碑版之区别的。先生告诉我们,对古代字体与书法的研究来说,“求真”的涵义并不只限于判定这些有文字字迹之载体(如甲骨、竹简、器皿、石鼓、碑崖、绢帛、纸本等)的真假,还必须判别那些字迹之间的差异与流变。过去人们临帖练字,往往重碑版而轻墨迹。启功先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晋唐法帖,转折失於勾摹;南北名碑,面目成於斧凿。临池之士,苟不甘为枣石毡蜡所愚,则舍古人墨迹,无从参究笔诀。”[2](P295)又断言:“(唐人经卷)墨迹之笔锋使转,墨华绚烂处,俱碑版中所绝不可见者。乃知古人之书托石刻以传者,皆形在神亡,迥非真面矣。”[2](P298)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语!古书家墨迹上石勾摹,经匠人凿刻,神气已失许多;若再捶拓成纸本,又有若干变化;如再加翻刻印刷,则全失其本来面目矣。启先生说:“余尝以写经精品中字摄影放大,与唐碑比观,笔毫使转,墨痕浓淡,一一可按。碑经刻拓,锋颖无存。即或宋拓善本,点画一色皆白,亦无从见其浓淡处,此事理之彰彰易晓者。”[3](P24)又说:“惟古碑传世既久,毡捶往复,遂致锋颖全秃,了无风韵。”[3](P48)清代翁方纲一生固守化度寺碑,字模划拟,几同響拓,启先生遂嘲之为刻舟求剑。启功先生在题跋赞语中所宣称的“人弃我取”,就是舍形似而求神契,这才是“求真”的真谛和精髓所在。启功先生平生临过的名帖可谓不计其数,但他最看重的还是临写敦煌写经原卷,甚至讲:“余遂求敦煌石室唐人诸迹而临习玩味,书学有所进,端由于此”[3](P38),宣称自己是“半生师笔不师刀”[3](P196)。我想,这大概可以视作他的一个“秘诀”,先生自谓“出入怀袖,客座倦谈,讲肄暇晷,寂寥展对,神契千载”、“晴窗之下,日临一本”、“日百回看”,达数十年而不倦,若将他收藏的敦煌写本称之为“随身宝”恐亦不为过也。
对于敦煌唐人写经,启功先生又特别注意将它们放在字体流变的背景里进行鉴赏与研究,并不以“雅”、“俗”来定真伪。敦煌写经,有许多是当时一般信众为做功德而请人抄写的,写经者多为文化程度较低的“经生”,若与朝廷专门颁发的“标准经卷”相比,似可目之为“俗写”,艺术水平会有高下之分;但重要的是它们非但不伪,反而常常不乏真率可爱之趣。启功先生《论书绝句》第十一首云:“乳臭纷纷执笔初,几人雾霁识匡庐。枣魂石魄才经眼,已薄经生是俗书。”又自注曰:“唐人细楷,艺有高下,其高者无论已,即乱头粗服之迹,亦自有其风度,非后人摹拟所易几及者。”[3](P24)所以,启先生始终认为,即便是从书法的角度看,这些唐代“经生俗书”亦弥足珍贵。先生每每强调:古代字体嬗变,皆有缘故;钟繇虽古而风致尚未极妍,六朝称壮而变化容犹未富;发展至唐,则点画万态,骨体千姿,字字精工,丝丝入扣,可谓瓜熟蒂落,达于大成。尤其是“真书体势,定于唐贤”。因此,唐代饱学之士的“雅写”诚然可贵,下层文人或经生的“俗书”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二者就统一在一个“真”字上。对敦煌学界有的研究者自设雷池,以某几个“标准写本”为框框定真伪的做法,启先生向来十分反对。1996年10月,启功先生曾带领一个专家组赴美、英、法等国考察与鉴定中国古代书画。在伦敦大英图书馆东方部,吴芳思博士(Dr.Frances Wood)请启功先生看一些被某国权威指为“伪卷”的敦煌写本,启先生明确判定这些其实均是晚唐五代经生俗写,完全不伪,于是提笔写了一段话:“一九九六年十月十日下午獲觀館藏敦煌逕卷,其中有晚唐、五代寫生拙筆所書者,聞有妄人指寫偽作,因寫志此,以奉告典藏諸君,自古法書有真有偽,而此輩妄人囈語切莫聼也。”并与一路同行的王世襄、傅熹年等专家一起,在这段话后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更能启人心智的,是启功先生在雅、俗之间求“实”求“通”的鉴赏眼光与研究方法。启先生曾声明:“平生不喜雅俗之说,文字尤难以雅俗为判。”[3](P80)在前录敦煌写经的题跋中,他称赞衲子经生之迹“乱头粗服中,妙有颜平原法,不经意处,弥见天真”,其上品更是“笔法骨肉得中,意态飞动,足以抗颜欧、褚”,并且举出袁清容误题《灵飞经》为钟绍京而董其昌不能辨的例子,说明经生之笔足以当书家,雅、俗之间实可相通,难以截然为别。上世纪初敦煌写本面世后,文史研究者对其中的“俗文学作品”(如变文、俗赋、民间曲词歌辞)和“世俗及寺院文书”格外关注,关键就在于它们可以补正传世典籍之阙失;然而,欣赏与研究“敦煌书法”者,则较多青睐他们认为的名拓古帖和一些“精品”,很少用汇通的观点来探究雅、俗关系,进而肯定经生俗写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依笔者体会,如果从个人鉴赏的角度讲,书法的雅、俗之分,虽有一点粗、细的客观因素在内,却始终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因此不仅常随个人之好恶而见仁见智,而且也会因鉴赏者的学养、能力、水平的高低而不同。例如有些书家津津乐道的“现代派”(乃至“超现代派”)书法,以笔画扭曲形似图绘为尚,写字以让人看不懂而自我陶醉,你以高雅自诩,我看俗不可奈(如启先生所云“人不能识,斯真俗不可医者”)。其雅乎?俗乎?另一方面,从书法史与字体史的角度看,如果真有雅与俗、正与俗之分,也是同源共流,相通互联的。在漫长的汉字字体发展的过程里,文字在流通应用中“雅”随“俗”、“俗”成“雅”、“俗”变“正”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道理很简单,因为“文字贵在通行,符号取其共识”[3](P80)。书法的“实用性”标准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若就艺术风格而言,“雅”的东西若孤芳自赏,自我封闭,便必然会失去生命力而渐趋凋敝;反之,若受社会喜爱而推广,大众普遍仿习,便一定成为通俗而流行。在书法史上,名家法书也不一定称“雅”才算好,启先生曾提及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唐朝韩愈以石鼓文的篆籀为“雅”,就说王羲之的真书行书为“俗”(《石鼓歌》:“羲之俗书趁姿媚”)。启功先生评价唐写本《法华经》残卷尾题“字体精严,雅近欧书《皇甫诞》、《温大雅》诸碑”,堪称“当时之首选”[3](P133-134),岂非雅乎?就字形而论,六朝的碑别字,敦煌写本中的俗字,有不少后来成了公认的正体字,有些则被淘汰了;而曾经通行的正字,后来变成异体俗字的,也不在少数。由于敦煌写本绝大部分是实用、应用的写经与文书,它们的写、作者又大多为下层文人、僧尼、学郎、官吏,字体、风格丰富多样,其差异之大,虽难以划一,却利于求通,因而就更具探究价值。总之,不囿于传统的书史材料,“信千秋之真赏,不在金题玉躞”,从而抛弃成说,不重虚名,用敦煌写卷来探究书法的体势之变、雅俗之通,求真求实,这确是启功先生的高明之处。
三
人们在叹服启功先生鉴赏古代书画的眼光、功力时,往往偏重于赞许他的天赋(包括聪慧、睿智)与创新精神,而忽略了后天的勤奋努力,尤其是忽略了造就深厚学养的“物质条件”——大量经眼古代书画真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古AI写作卷,十有六七已流散海外,劫后余珍留存国内者总数约两万件(号),唐人写经占十之八九。对这部分写本,除研究佛教典籍的专家较为重视外,一般的研究者关注不够;当然,由于各种原因,能够接触大量原件的人也很少。而启功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有志亦有缘,得以不断观摩并收藏敦煌写经。先生在《论书绝句》第八十三首的自注里有这样一段话:“先师励耘老人每诲功曰,学书宜多看和尚书。以其无须应科举,故不受馆阁字体拘束,有疏散气息。且其袍袖宽博,不容腕臂贴案,每悬笔直下,富提按之力。功后阅法书既多,于唐人笔趣,识解稍深,师训之语,因之益有所悟。”[3](P168)于此亦可见陈垣老校长的教导对启功先生影响之大。我记得大约20年前,有人曾建议启功先生带书画鉴定的研究生,先生没有同意。启先生说:“学书画鉴定必须能够看到大量的原件,现在没有这个条件,实际的东西看得少,架空讲理论,架空传授别人的经验,那是要害人的。”当时我听了这话,还不十分理解,后来有机会常常观察启先生的鉴定实践与聆听他的教诲,才开始明白先生揭示的道理。启功先生少时即拜书画名家为师,受家庭及周围环境熏陶,加上自己的勤奋好学,得以亲眼观摩大量的古代书画真迹与赝品,又有自身的创作实践,积数十年的经验体会,才能炼就“火眼金睛”,做到得心应手。
鉴赏与研究敦煌写卷,又不能局限于光看敦煌卷子本身,除了要通晓各类文献典籍外,还必须谙熟与字体书法相关的文物。启先生自述一方面“生平所见唐人经卷,不可胜计”,另一方面“酷耽书翰,凡石渠旧藏,私家秘笈,因缘所会,寓目已多”,奠定了做鉴定与比较研究的扎实基础。我们读启先生的敦煌写经题跋,于字里行间处处可以感受到他在这方面的深厚学养与丰富经验。十多年前,敦煌研究院要选一些敦煌写卷到日本去展出,两位研究员先拿了几个卷子到北京来,让我带他们去请启功先生鉴定。有一个写卷刚展开一半,启先生就说这是某朝某代所写,而且马上列出了好几条具体的证据,待展到卷子末端一看尾欸,果然不差。另一个带卷轴的写经,还未打开,先生就说这种装裱肯定不是敦煌所出,而是日本某代某人的写经,千万不要当敦煌写本拿到日本去展览。打开之后,先生看我们似有疑惑,便从里屋找出一册印有日本古写经的图录来对照,证据分明,真让我们心悦诚服。启功先生研究汉语规律,并不迷信“葛郎玛”,而是从语言现象入手,名之曰“现象论”,这里虽有先生自谦的成分,但同时也完全符合辩证逻辑,因为既是“现象”,就不等于事物的个别、单纯“存在”,所以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启功先生研究敦煌写卷的字体、书法,也正是从大量的书画“现象”(而非个别“存在”)入手,找出本质属性,并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所以说,鉴赏书画文物要达到望而即知这种炉火纯青的境界,必须见多识广,而且日积月累,烂熟于心,进而做到融会贯通。
启功先生鉴赏、研习敦煌写卷已经六七十年了,虽然他专门为此写下的著述不多,却是他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好地体现了他求真、求新、求实、求通的治学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学习领会。“墨沈欲流,纸光可照。唐人见我,相视而笑。”我想,只有像启先生这样眼观万卷,学富五车,才能心会百代,神契千秋,与圣贤哲人相视而笑。
标签:启功论文; 书法论文; 书法欣赏论文; 书法字体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灵飞经论文; 论书绝句论文; 书画论文; 敦煌博物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