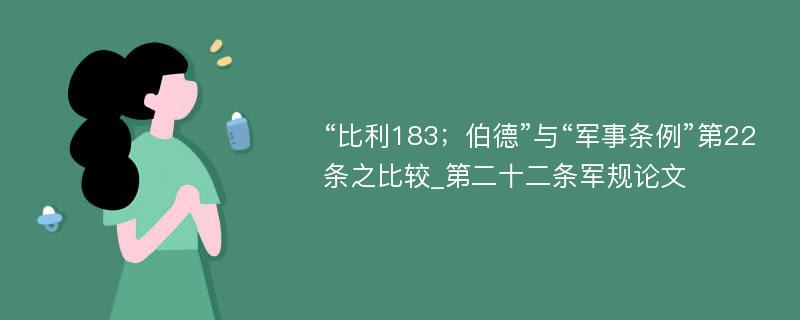
《毕利#183;伯德》和《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伯德论文,军规论文,十二条论文,毕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赫尔曼·梅尔维尔的《毕利·伯德》和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经常被美国战争小说评论家和史学家双双列入美国战争小说代表作书单。虽然两位作家相距近百年,写作的内容、风格、方法等有诸多不同,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许多相通和相同之处的。对它们作一些比较研究,对于了解美国战争小说的传统与特点、长处与不足也许会有裨益。
引发我写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原因是最近读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写的一本书。亨廷顿近年来因他的“文明冲突论”而备受世人注目,声名藉甚。实际上,他的名声并非始自今日,早在50年代他就已是一位在国际政治理论方面颇有影响的学者。1952年他发表的专著《军人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和政治》(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一书就是他对战后国际形势和美国对策的调研报告,观点鲜明,独树一帜。他认为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美苏对峙,美国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为此美国应在国内采取军事极权主义,实行独裁统治。他把美国的西点军校作为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他说在那里可以找到一种“有序的宁静”(ordered serenity)。那里的营房和人员都严格按照等级划分,各就各位,个体隶属整体。人们的性格和地位象征着他们的贡献,高级军官住砖石房,低级人员住木屋。亨廷顿说,当“集体意志取代个人的随心所欲时,人们就可获得和平和安全”。他进而引出结论:“社会有四大支柱:军队、政府、大学和教会。宗教为了神的缘故,教人俯首听命于上帝;军事生活要求人们为了社会的缘故,服从义务。军人社会就其严厉、规范和纪律而言,与宗教团体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现代人可以在军中找到他们的寺院。”(注:
Samuel P.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Cambridge,Mass,1958.p.465.引文为笔者自译。)这样,他给美国政府乃至现代人类社会开出了一帖“济世良药”——军事极权主义。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美国作家笔下的美国军队组织或军人生活究竟怎样,人们是否真的在那里找到了“有序的宁静”,或者说找到了他们的“寺院”。这里我选择了《毕利·伯德》和《第二十二条军规》这两部小说。梅尔维尔被公认为美国战争小说史上一位重要的创新者,他最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军队中普通人的命运上。在他的笔下,没有高大的英雄形象,有的是“反英雄”。他最先把军队作为权力主义国家的微型来分析,开创了把战争小说作为一种载体来表达对美国政治和社会问题思考的先河。他还把讽刺的因素,特别是反讽,引入美国的战争小说中来,与着力赞美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美国传统的战争小说和历史小说背道而驰。可以说,梅尔维尔和他的杰作《毕利·伯德》在美国战争小说史上具有开创意义。而约瑟夫·海勒及其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则把美国战争小说的反英雄与反讽的传统发挥到了极致,把讽刺的矛头直指腐败的军事官僚主义机构,同时把存在主义哲学和荒诞派戏剧的写作手法移植到小说中来,成为“黑色幽默”小说的先驱,在美国战争小说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说来凑巧,《第二十二条军规》是1961年问世的,而海福特-塞尔茨版的《毕利·伯德》发表于1962年,紧随其后。这样就在无形中拉近了两部作品的距离,发人深思,劝诱人们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
当然,梅尔维尔的《毕利·伯德》并非是作者写的第一部战争小说,也不是他最典型的战争小说。在该小说之前,梅尔维尔还写了两部战争小说:一是《白外套》(White—Jacket,1850),一是《伊斯雷尔·波特》(Israel Potter,1855)。二者都以美国独立战争为背景,但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作家如库柏等人写的战争小说不同,他以军队作为社会与世界的缩影来探索社会问题。《白外套》的副标题就是“军舰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舰长作为一舰之主,是这个小王国的独裁者,他的话就是法律,操纵与决定着手下人的生死荣辱。他手下的各级军官对他惟命是从,因为他们都求他封官赐禄。舰上的陆战队员就是他的宪兵,士兵就是他的奴仆。作者一再把舰船比作社区、比作城镇、比作国家。它的建构完全是一个极权的、摧残人性的政权的缩影。《伊斯雷尔·波特》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倒是一位名叫莱昂·福伊希特威格(Lion Fenchtwanger )的德国学者在一本评述历史小说的书中大声疾呼,梅尔维尔的这部小说“被大大地低估了”。他强调它与传统的历史小说形成的鲜明对比,伊斯雷尔·波特这位默默无闻的老战士才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真正英雄。波特为了国家的独立,英勇作战,不幸被英国人俘虏,送往英国。他设法逃跑,在颠沛流浪期间仍不忘祖国,从事秘密活动,奔走于伦敦和巴黎之间,为革命效力。其间他遇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保罗·琼斯和伊桑·艾伦等人,并参加了跟英国军舰“塞拉匹茨”号的海战。最后,他在离乡背井近50年之后回到美国时,已年老体衰,贫病交加,而政府却拒绝给他发放养老金,最后波特含恨死去。小说的突出之处是作者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而对那些所谓的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却频频反讽讥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梅尔维尔是美国战争小说史上第一个把讽刺成功地引进了战争小说的作家。他生前未及整理出版的小说《毕利·伯德》把他前期的两部战争小说的主题思想与写作技巧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思想更深刻、更凝炼;写作技巧更娴熟、更简约。研究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和学术专著很多。根据杰西·里特统计,仅在美国以它为题目撰写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就达500余篇。
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周珏良教授于1987年把《毕利·伯德》译介给我国读者,并写了一篇题名为《〈毕利·伯德〉的一种读法》的评论文章。文章对如何理解这部小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应对“全书作为一个整体的艺术效果进行研究”。(注:《周珏良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96页。)他强调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机整体,作品的各个部分,如情节、人物、思想、语言等都会对作品产生不同的感情效果。周先生的文章不仅对我们深入理解《毕利·伯德》这个具体的作品很有帮助,而且对于如何阅读文学作品也有很深刻的指导意义。周先生运用他的“合成原则”对作品进行了具体、准确的分析后又补充说:“此外本书中有许多地方充满反讽意味,”他在举了两个例子后又说,“这本小说中的反讽是很可以作为专题研究的。”(注:《周珏良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108页。)他言辞恳切,使一般读者对小说中存有反讽确信无疑。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即这部小说的语气是否是反讽的,曾在美国评论界引起过一场大论战,而且争论双方还都是名家。持否定意见的一方阵营强大,有F.O.马西森、J.E.米勒、D.E.S.马克斯威尔、F.B.弗里曼、查尔斯·韦尔等。他们认为梅尔维尔的态度只是承认必然,接受现实,并无反讽之意。持肯定观点的一方阵营也不弱,有理查德·蔡斯、哈里·莱文、艾尔弗里德·卡津、默林·鲍恩、约瑟夫·希夫曼等。而据说在这一方的背后,还有一位影子人物,也是这场争论的发难者盖伊·威尔逊·艾伦。据说他曾对希夫曼说过:梅尔维尔很可能有意将反讽贯穿于《毕利·伯德》全书(注:Wayne Charles Miller,An Armed America:Its Face in Fiction,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0,pp.43—44.)争论的双方都发表了不少文章,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裁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不是本文的要旨,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仅从技术上来说,就有一个版本问题。一般认为梅尔维尔是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创作该小说的,但直至1891年他逝世时也未定稿。手稿尘封多年,1924年始由雷门·魏弗整理出版。以后又有根据不同编辑原则出版的另外一些版本,如1948年弗里曼的版本和当前广泛使用的海福德-塞尔茨1962年版本。版本不同必然会影响到对作品的解读。就论战双方发表的有关文章的时间来看,大多集中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也就是在海福德-塞尔茨版发表前后,距今已有40多年了,这期间无论对梅尔维尔的研究,还是对《毕利·伯德》的研究都有了较大的进展。虽然至今还没有看到有谁对这场争论写出总结性的文章,但尘埃落定,结果不言而喻。周珏良教授的文章就可以说是一个例证。
有趣的是,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发表后,在美国评论界也围绕对它的评价问题,特别是它的幽默和结构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人批评它“混乱不堪”、“陈腐平庸”、“感情用事”,甚至说“多数评论家因难以将它归类,而可能嗤之以鼻,一掷了之”。(注:Wayne Charles Miller,An Armed America:Its Face in Fiction,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0,p.241)但是,也有一些有远见的批评家指出海勒与塞缪尔·贝克特有许多相似之处,认为小说批评的矛头不仅指向军队的官僚机构,还指向社会和整个西方文明。海勒的观点超越了任何具体时间和地点的荒诞,成为“黑色幽默”的典型作品。最近美国兰登书屋“现代文库”编辑部公布了三张分别由文学编辑、大学生和学者选出的本世纪最优秀的100 部英文小说的调查表。《第二十二条军规》在三张表中都名列前茅,可以说是对这本小说的最好评价。它的巨大成就之一就是把荒诞引入了小说,从而也给美国战争小说的讽喻传统作了一个完美的总结。
著名文学理论家诺思罗普·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对“讽刺”和“反讽”的关系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反讽和讽刺的主要区别在于,讽刺是一种激烈的反讽,它的道德准则相对而言较明晰,它假定了衡量什么是荒诞可笑的标准。”(注: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Princeton,New Jersey,1957,p.223.引文为笔者自译。 )这个论述为我们界定了反讽、讽刺和荒诞。接着,他又说:“对于讽刺来说,最重要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建立在幻觉或荒诞不经感觉上的机智或幽默,另一个是攻击的对象。”他进一步指出,没有幽默的攻击或纯粹的谴责是讽刺的端线之一,而讽刺的另一端线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幽默,属传奇。(注: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Princeton,New Jersey,1957,p.225.引文为笔者自译。)弗莱对讽刺本质的论述告诉我们,反讽和荒诞属于同一个范畴之内。把这两部各具特色的美国战争小说作一比较,无疑会加深我们对反讽和黑色幽默的了解,帮助我们认识美国战争小说的发展过程。
我们的比较不妨从“攻击的对象”开始。《毕利·伯德》和《第二十二条军规》讽刺的矛头指向许多地方,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可以说被亨廷顿称之为社会四大支柱中的军队和教会都是两位作家揭露和鞭挞的重点。本文限于篇幅,仅以这两点作为比较的重点。
《毕利·伯德》中叙述维尔舰长召集军事法庭,审判伯德的那几个章节,是全书的高潮,也是全书最精采的部分。梅尔维尔通过这些章节,不仅对军纪的严峻、军法的威力、军队中长官意志的至高无上和战争的残酷无情作了深刻的揭露,而且在反讽的运用上也达到了驾驭自如的地步。
维尔舰长在目睹青年水手毕利情急之下不意打死纠察官克莱加特之后,情绪异常激动,大声叫道:“哎哟,这是上天对亚拿尼亚的判决!”“被上帝的天使打死的,天使却要受绞刑! ”(注: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2nd ed.,Norton,New York,1985,p.2404.笔者在引用时参考了周珏良先生的译文,稍有更动。)显然,他认为毕利是使徒彼德、是天使,而克莱加特是骗子、是毒蛇,欺骗上天,死得其所。但是,他还是决定立即召开军事法庭来审判毕利。组成军事法庭的三名军官是他一手指定的,而他自己虽不是法官,却“作为最终负责人保留监督权和在需要时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干预权。”(注: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2nd ed.,Norton,New York,1985,p.2407.笔者在引用时参考了周珏良先生的译文,稍有更动。)实际上,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他既是提出起诉的检察官,惟一的见证人,又是真正的大法官。他大权独揽,一个人说了算。在他作证完毕后,上尉法官问毕利:“维尔舰长说得对还是不对?”毕利回答道:“维尔舰长说的句句是真理。他说得对,纠察官说得不对。我吃的是皇上的粮,我效忠皇上。”(注: The NortonAnthology ofAmerican Literature,2nd ed.,Norton,New York,1985,p.2408.笔者在引用时参考了周珏良先生的译文,稍有更动。)在舰上,在毕利的心目中,舰长就是皇上。整个审讯过程,从开始作证到最后判毕利绞刑,都是维尔一人在说,在起作用。梅尔维尔在审判结束后意味深长地提及1842年美国双桅战舰“索默斯号”判决三名军官绞刑的案子后说,“有理无理,都是一个样。”这整个审判过程和审判的结果给人一种强烈的压抑感,叫人心烦意乱,迷惑不解。人们不禁要问,在这艘军舰上,还有没有公理、公道、公正,或者就如维尔舰长说的:“虽然大海属于不可冒犯的开天辟地就有的自然界,虽然它是我们在上面活动,使我们成为水手的物质,但作为皇上的军官,我们的职责还能在一个相应的自然范围内吗?一点也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接受任命之际,就在最重要的方面已不再是自然的自由人。……不管法律怎样无情,我们都得遵守和执行。”(注: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2nd ed.,Norton,New York,1985,p.2411.笔者在引用时参考了周珏良先生的译文,稍有更动。)维尔振振有词地对军官们说,作为军官已经没有了良心,没有个人的良心,只有服从制定成法律的国家的良心,依法行事。因此,为了执行军法,尤其是战时的军法,无辜的毕利必须判罪,必须绞死。我想,读了这几章,谁都会感受到强烈的反讽意味,而且是那种按罗杰·福勒对反讽分类中的悲剧性的反讽。(注:Roger Fowler,A Dictionary of Modern Critical Terms,revised ed.,Routledge & Kegan Paul,New York,1987,p.128.)如果说这里的反讽主要是通过情景来实现的话,那么在小说结束前,作者还假借海军部正式出版物对这一事件的报导,来进一步揭露军方颠倒是非,歪曲事实的恶劣行径,即通过文字来实现反讽。声称“用诚实态度”写成的这篇报导,完全与事实不符,说什么当克莱加特当着舰长的面指控毕利阴谋发动哗变时,“伯德忽抽出鞘刀寻衅,将其穿心刺死。”更为可笑的是对克莱加特品德的描述,溢美之词令人肉麻,说正是他的拳拳爱国之心惹人嫉妒,惨遭杀害,从而驳斥了约翰逊博士的危言:“爱国心者实小人之最后口实也。”(注: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2nd ed.,Norton,New York,1985,p.2426—2427.笔者在引用时参考了周珏良先生的译文,稍有更动。)军方这种恣意捏造事实、诬陷好人、美化恶人的行径已到了令人啼笑皆非、荒谬绝伦的地步。
《毕利·伯德》中的审讯场景使人自然联想起《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类似的一个审讯场景,受审的是一个名叫克莱文杰的年轻人。表面上看,他在许多方面跟毕利·伯德不同,他不像毕利那样英俊漂亮,而是长得瘦长难看;毕利没有文化,目不识丁,而他是哈佛大学的高才生,绝顶聪明;他口齿伶俐,绝不会一紧张就犯口吃讲不出话来。但他跟毕利·伯德一样有一股子傻劲儿,不通世故,是“一个战斗性颇强的理想主义者”,政治上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毕利因不慎在甲板上泼撒了汤,引起纠察官克莱加特的不满与仇恨,被诬告企图率众闹事,而克莱文杰却只是因为“颇有头脑”。沙伊斯科普夫要指控他,“惟一缺少的,就是以什么罪控告他。”同样,由三名军官组成了一个裁定委员会,他们是留着粗浓八字胡的上校、沙伊斯科普夫中尉和梅特卡夫少校。滑稽的是,沙伊斯科普夫中尉既是法官,又是起诉人。“克莱文杰有一名军官替他辩护, 但那个军官还是沙伊斯科普夫中尉。 ”(注:Joseph Heller,"Catch—22",Dell,New York,1985,p.77.笔者在引用时参考了译林出版社杨恝等人的译本,稍有更动。)读者可以想象这样的审讯会是怎样,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但有意思的是,当克莱文杰不承认自己有罪,说自己“忠于正义事业”时,上校一听到“正义”两字就惊愕不已,接着还发表了一通对“正义”的宏论。克莱文杰当然被判有罪,原因很清楚,裁定委员会的人仇恨他,“那种赤裸裸的残酷无情的仇恨。他们仇恨一切人。”(注:Joseph Heller,"Catch—22",Dell,New York,1985,p.83.笔者在引用时参考了译林出版社杨恝等人的译本,稍有更动。)
通过对这两场审讯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那个被亨廷顿称作具有“有序的宁静”的世界里,是非是如何被颠倒,人性是如何被扭曲,公正是如何被践踏的。两者的差别只是在讽刺的手法上不同,前者用的是反讽,后者用的是荒诞。
宗教也是这两部小说攻击的对象。约瑟夫·海勒认为,基督教和上帝是造成这个荒诞世界的罪魁祸首,他对上帝的讽刺挖苦几乎到了亵渎和谩骂的地步。这里有一段淋漓酣畅的描述:尤索林在一个感恩节夜晚,在跟沙伊斯科普夫中尉的太太调情做爱后,讨论有什么事情值得人们感谢上帝。尤索林认为上帝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地方,他根本没有工作,一味玩耍,不关心人们的痛痒。尤索林把上帝骂得使不信上帝的中尉太太坐立不安,竟挥动拳头痛打他的脑袋。尤索林提出了一个妥协办法,要求“让咱们多一点宗教自由”,“你不信你想信的上帝,也不会信我想信的上帝。”(注:Joseph Heller,"Catch—22",Dell,New York,1985,p.185.笔者在引用时参考了译林出版社杨恝等人的译本,稍有更动。)这不是彻底否认了上帝的作用和作为西方文明重要基础的基督教吗?
海勒在小说结束之前意味深长地写了随军牧师塔普曼被绑架受审的事件。他被控的罪行之一就是不相信上帝。一个牧师不信上帝,这不是大逆不道吗?一个参加审讯的上校故而建议,把牧师的脑壳敲开。这不是要彻底摧毁人们对上帝、对基督教的信仰吗?再想想尤索林在看到他的同伴斯诺登受重伤,炸得五脏六腑都流了出来时,他感到冷,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惊呼“人没有了灵魂,就变成了一堆垃圾”,(注:Joseph Heller,"Catch—22",Dell,New York,1985,p.450.笔者在引用时参考了译林出版社杨恝等人的译本,稍有更动。)而这堆垃圾恰恰是上帝造出来的,其寓意之深就不言自明了。
《毕利·伯德》对上帝的批评则要含蓄得多,它主要是通过象征的手法,含沙射影,旁敲侧击。据说在小说里,基督教的典故多达三四十处。但是梅尔维尔并不想把它写成一个宗教故事,而只是为了达到某种艺术效果。恰恰相反,作者竭力贬低宗教的作用。舰上的随军牧师在毕利受刑之前去看望他,毕利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平静,牧师对此十分感慨,“觉得带着天真无邪去接受最后的审判甚至可能胜于宗教。”在毕利临刑前的最后一刻,他嘴里喊出的最后的、也是惟一的一句话就是:“上帝保佑维尔舰长!”此时全船上下异口同声地喊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上帝保佑维尔舰长!”可是上帝并没有保佑舰长,“战威号”在返航途中碰上了敌舰“无神论者号”,维尔舰长中弹身亡。小说的反讽意味到此可谓“登峰造极”。
这两部小说可以比较的地方还很多。从它们抨击军队司法和宗教的几段叙述中,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亨廷顿所向往的“有序的宁静”,找到的倒是喧哗和骚动。我们也很难找到亨廷顿指点人们去寻找的“军中寺院”,反倒在《毕利·伯德》第21章中找到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但是真正的军官在某一点上颇像真正的僧侣。前者对军事责任的忘我忠诚决不下于后者对寺院戒律的一心坚守。”而正是“对军事责任的忘我忠诚”这个美丽动听的词句,成为维尔舰长滥用权威的借口,成为科恩上校和卡恩特上校制定22条军规的绝好理由,也成为亨廷顿的军事极权主义或新权威主义今天一心要坚守的戒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