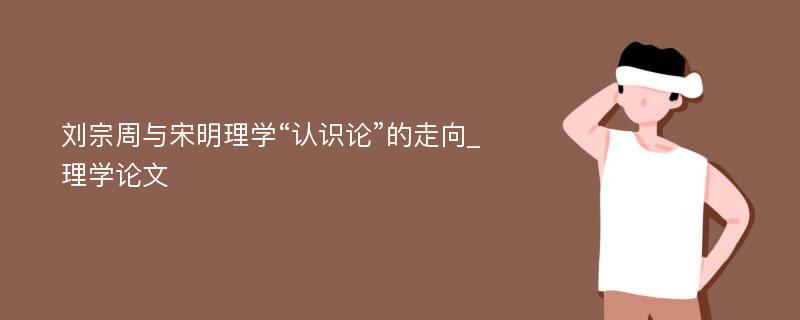
刘宗周与宋明理学“知识论”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走向论文,知识论文,刘宗周论文,宋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12)01-0061-09
一
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理学”至少在北宋时代尚非儒家主流,讲求心性的“理学”要到南宋以后始占据重要学术地位。北宋时,儒学宏阔,周、张、二程的义理尚不过是儒学的一支而已。刘彝在答复宋神宗询问胡瑗和王安石孰优时,曾对儒学有如下的界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①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解释,任何宗教传统或道德传统或文化传统,一定有它一套基本文献,文献怎么处理,如何解释,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至少在北宋时,除了少数人讲心性以外,还有更多的儒家学者讲其他的问题,如经世问题、政治改革问题等等。下逮南宋,儒学始偏重于体的方面,而且是偏于体的哲学方面,或者说要建立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体是永久性的、绝对的,不是暂时的、相对的。要确定这种永久性、绝对性,便不得不从形而上方面着眼。总而言之,南宋以后,儒家注重体甚于注重用②。
对于宋明理学主流诸家来讲,“心性”问题是他们思考问题的重点,甚至是非主流的“新学”、“蜀学”和“婺学”,亦曾为“心性论”作出过各自的贡献③。关于宋明理学的这个特点,张立文先生在给“宋明理学”下定义时,即有所揭示:“概括地说,宋明理学是指在外来印度文化哲学与本土道教文化哲学挑战下,将元典儒学作为滞留于伦理道德层次的心性之学,从形上学本体论层次给以观照,使传统儒学以心性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价值理想(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建构在具有理性力度的形上学本体论思维之上,通过诠释心性与本体、伦理与天道的连接以及人与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系,使儒家道德学说获得了形上性和整体性的论述,传统儒学内部的逻辑结构、价值结构、道德结构等经此调整,获得了新的生命。”④就此而言,宋明理学重“心性义理”之学而轻“经世致用”之学。当然,宋明理学论学侧重“心性义理”之学,并不是没有“经世致用”之学,只是在这一方面的论述不够发达而已。
南宋以后,儒家重“心性”而轻“事功”,越到理学后期,这种情况就越严重。黄宗羲曾深刻指出:“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程、朱之辟释氏,其说虽繁,总是在迹上;其弥近理而乱真者,终是指他不出。明儒于毫厘之际,使无遁影。”⑤黄氏之论表明,宋明理学探讨问题之侧重,“心性”之学盖过了“经世致用”之学,尤其是明代在心性之学上更有突出的贡献,把“心性”之学领域内的各种境界开拓到了一个极致⑥。明清之际的士人在反思明亡的教训时也往往感慨儒者、书生的无能,表达出对明儒重义理而不重事功之行为取向的不满。明末忠烈、蕺山弟子施帮曜殉国之际吟诵绝命诗云:“惭无半策匡时艰,惟有一死报君恩”⑦,正是当时儒家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明末儒士于国难当头之际,毫无半点应对之策,假道学之虚名,反误了卿卿性命。李塨曾指出:“当明之季,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恕谷集·与方灵皋书》)朱之瑜也说:“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既为尘羹土饭,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而国家被其害。”(《舜水遗集·答林春信问》)顾炎武则把批判的锋芒直指王阳明的哲学,认为王学末流的弊端在于“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日知录》卷7《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王夫之更是把明朝的一切罪恶和流弊直接归于王阳明本人和其学之下,说:“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张子正蒙注·序论》)这些都是明朝遗民痛定思痛总结明亡教训的愤慨陈辞。黄宗羲曾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这种琐琐小儒只谈心性而轻事功之“偏固狭陋”的弊病:“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⑧梨洲之论,引人深思!
二
明末大儒刘宗周(字启东,号念台,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蕺山,后世学者尊其为蕺山先生)在探求严密的道德心性义理之学的同时,不废事功,实现“学术”与“经济”的有效统合。他在《论语学案·君子儒》中明确指出:“学以持世教之谓儒,盖素王之业也。”⑨儒者的本质是“世教”,“既为儒者,若定要弃去举业为圣学,便是异端”⑩。蕺山从“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关系上挺立“学术”与“经济”的圆融性。他在1637年所写《答右仲三》的书信中指出:
至于德性、闻见本无二知,心一而已,聪明、睿智出焉,岂可以睿智者为心,而委聪明于耳目乎?今欲废闻见而言德性,非德性也;转欲合闻见而全德性,尤未足以语德性之真也。世疑朱子支离,亦为其将尊德性、道问学分两事耳。夫道一而已矣,学亦一而已矣。一,故无内外、无精粗。与其是内而非外,终不若两忘而化于道之为得也。(11)
蕺山认为“心一而已”,因此,“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亦只是“一”,若以之为“二”,自然将“心”分而为二,故他有“德性、闻见本无二知”之论。此外,“聪明”与“睿智”同是“心”,同为“心”的机能与属性,不能“以睿智为心,而委聪明于耳目”。“聪明”即是“闻见之知”,“睿智”即是“德性之知”,“聪明”与“睿智”同为心,则“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自然非二心可知。圆融“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既不会偏于“德性”,只重本体,又不会偏于“闻见”,只重工夫。本体与工夫合一,才是“心”之生生自然之道,方是天理自然如此。
蕺山1641年《答嘉善令》论簿书、钱谷问题时,亦深切表达了他融“事功”与“心性”为一体的思想。他说:
承谕求放心之说,至矣哉。簿书、钱谷皆放心之地,亦即是求心之地,此居官者当以学问为第一义,而不可不日加之意者也。夫心非一膜之心,而宇宙皆足之心也。故善事其心者,无有乎内外、显微、动静之间,而求其所谓本心者,亦曰仁义而已矣。“生生之谓仁,时措而宜之之谓义”是也。其不善言心者反是,内外、显微、动静皆成两胖,于是日置其心于一膜之地,而遗其所谓宇宙者。卒亦以其心为血肉之心,槁焉而不灵,奚有乎生生之妙?真鸡犬之不若矣。求之于静,失之于静;求之于敬,失之于敬;求之于觉,失之于觉。静也、敬也、觉也,皆似之而非者也,不得其说,皆死道也。放固放在一膜之中,求亦求在宇宙之外,既不免以其放者为求,又安得不以求者为放?簿书、钱谷之皆心者,为其有以寄吾之生心也。君子生其心以生人、生百姓,一簿书焉而生生,一钱谷焉而生生,则学问之道又孰有大于此者乎?(12)
簿书、钱谷系求达社会安定和发展的致用之学。在蕺山视域下,这些事情是“求心之地”,是“生生之心”的必然表现,能够实心实意、真心诚意地完成社会事功,是“心”的当然要求,故而“学问之道”并不外乎此。蕺山立论如此,其为人为事亦是如此。蕺山铿铿从事于事功,从无丝毫懈怠,虽崇祯帝斥之为“迂”(13),实是其“真学问、真经济”的真切体现。在蕺山的信念里,“一心也,统而言之,则曰心,析而言之,则曰天下、国、家、身、心、意、知、物。惟心精之合意、知、物,粗之合天下、国、家与身,而后成其为心。若单言心,则心亦一物而已”(14)。蕺山从“心”之所想出发,认真完成每一件自己认为“应当如何”的“事”,是他诚正无欺、认真踏实、自觉体悟人生之刚直情操的显现。
蕺山通籍四十五年,实际立朝仅四年,而被革职为民凡三次,历仕神宗、熹宗、思宗、福王四朝,在中央吏部、工部及都察院皆有任职,官至正二品;在地方则做过顺天府尹,且被民众呼为“刘顺天”,可见其行政能力为上级及民众所普遍肯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刘蕺山集提要》曾这样评价蕺山:“立朝之日虽少,所陈奏如除诏狱、汰新饷、招无罪之流亡、恩义拊循以收天下泮涣之人心、还内廷扫除之职、正懦帅失律之诛诸疏,皆切中当时利弊。一厄于魏忠贤,再厄于温体仁,终厄于马士英。而姜桂之性,介然不改。卒以首阳一饿,日月争光。在有明末叶,可称皦皦完人,非依草附木之流所可同日语矣。”詹海云先生则评价蕺山曰:“刘氏一生治学之基调不是专在纯学术上,而是在‘学以致用’的经世实学上。”(15)
就心性义理之学的阐释而言,蕺山堪称是阳明之后宋明理学中最能自成体系的哲学家。他把宋明心性义理之学发展至极致,对阳明后学猖狂纵恣之躐等之弊作出最有力的反击。梁任公曾言:“凡一个有价值的学派,已经成立而且风行,断无骤然消减之理。但到了末流,流弊当然相缘而生。继起的人往往对于该学派内容有所修正,给它一种新生命,然后可以维持于不弊。王学在万历天启间,几已与禅宗打成一片。东林领袖顾泾阳(宪成)、高景逸(攀龙)提倡格物,以救空谈之弊,算是第一次修正。刘蕺山(宗周)晚出,提倡慎独以救放纵之弊,算是第二次修正。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惟蕺山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16)将蕺山归结为“王学后学”或“阳明学的修正者”,非无可商榷处,但是梁启超所说,又非无客观性。明清之交,学风渐趋健实,一反阳明后学之蹈空之弊,蕺山功不可没。黄宗羲即曾深刻指出:“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盖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反身理会,推见其隐,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渐之所衣被也。”(17)
蕺山之后,最能传蕺山之学的当是黄宗羲。姚明达《刘宗周年谱》在阐论蕺山“学术渊源”时指出:“刘宗周之学,推本于周敦颐及二程,而与朱、陆皆有龃龉。得源于王守仁,而为说又异。受教于许孚远,而其学非许氏所能范围。切磋于高攀龙、陶奭龄,而其思想迥非高、陶能和同。传其道者,惟黄宗羲最正,邵廷采则其再传嫡派也,而恽日初、张履祥之流不与焉。”(18)但是吾人当知,梨洲最大的学术成就是在经史方面而不是在心性学上,他的心性学对刘宗周学说只有继承,并没有进一步发展(19)。即便是梨洲经史圆融思想,亦不能不说受蕺山的影响。蕺山论学不仅“学术”与“经济”相统合,而且“经学”与“理学”、“经学”与“史学”相圆融。
三
明代哲学以理学为主,心性论发达,经学衰微,且经学与理学分途。“经学在新的方法、新的社会需要确立之前,已经很难再有发展。”(20)而且,明代史学亦不发达。正因为无儒家经学之根,无儒家史学之根,有学者称明代学术思想为“无根的一代”(21)。明代思想的无根性乃是基于正统儒家的经学观和《春秋》史学观所作出的评判,正如陈永革先生所说,明代思想之所以无根,正在于其思想中并不突出“古”与“圣”的权威性。古则以三代为高,圣则以周孔为尊。复古当力究诸经,尊圣应效法诸经(22)。在蕺山这里,经学已然涵蕴了新学之发展方向,不仅经学与理学有机融通(23),经学与史学亦和合通贯,这正是尊古崇圣思想的开显。蕺山在心性义理的阐释中,由对天人和性命问题的思考而走向对史学问题的思考,“言性命者必究于史”(24)。何柏丞先生便有此论:“吾国学术思想至北宋末造就一番融贯之后,大起变化。……初开浙东史学之蚕丛者,实以程颐为先导。……故浙东史学自南宋至明初,即因经史文之变而日就衰落。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一个时期。迨明代末年,浙东、绍兴又有刘宗周其人者出,‘左袒非朱,右袒非陆’,其学说一以慎独为宗,实远绍程氏之无妄,随开浙东史学中兴之新局。故刘宗周在吾国史学上之地位实与程颐同为由经入史之开山。”(25)无论是就浙东学术史、浙东史学发展史而言,还是就宋明理学发展史言,蕺山心性学所开出的经史之学当为吾人所重视。这种新学方向恰恰是“健实”之学风最真切的体现。
蕺山“经史相融”的学术品格可由其晚年“凡三易稿”的《人谱》得以透视。中国传统史学是重人不重事,以人为主,以事为副,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历史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它能把人作中心。”(26)在传统历史观看来,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在历史发展中起支配作用的往往是“圣人”、“贤人”,他们才是历史的主体、文明的创造者、人伦道德的象征。《荀子·解蔽》曰:“圣也者,尽伦者也。”《礼记·中庸》云:“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梁启超曾言:“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如何?佛学界失一道安……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渊,失一王阳明……其局面当如何?此等人得之名曰‘历史的人格者’。”(27)圣人、英雄人物是历史的主宰,作为其化身的道德精神在历史发展中也就起着主宰作用,这就是道德决定论,而它便构成了中国历史精神。钱穆先生曰:“中国的历史精神,也可说是一种道德精神。中国的历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杰性的。”(28)所以,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那些既无权又无钱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始终为人所尊重,就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历史的评价标准,在参与历史的同时又塑造着历史,中国史学撰著多以褒贬笔法为主的纪传体为主要体裁就是一个明证。因此,杜维明先生指出:“在中国传统之中,历史也就逐渐成为在政治势力、社会影响以及经济权威之外的一个独立的评价标准。”(29)刘蕺山《人谱》对道德哲学、心性论不吝笔墨的论述,正是要极力构建一种新型的道德价值体系来应对王学末流躐等之弊。他对工夫论的重视,对道德主体主动性、能动性、自觉性的体认,目的正是要培养至上的道德精神,重建以道德品性为准绳的人物评价体系。这正体现了中国史学的精神。
《人谱》既是对王学末流蹈空之弊的回应,又是对社会发展中道德评价准则的提炼;既是对那个特定的时代生活体验的总结,更是以一种普适性态度对人类社会道德发展模式的设定。蕺山以《人极图说》收摄《太极图说》,濂溪所设计的宇宙论图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时间性和衍生性的道德精神现象。正如蒋年丰先生所说,刘宗周把时间性展现于道德精神自身的辩证发展过程中,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着眼,刘宗周的这种时间观乃是真正从精神主体内在地扣到历史意识(30)。张高评先生亦指出:“(刘宗周)《人谱》一书,统贯性命德性之理,推寻古人言行,附丽排比以成类记,是其虽倡理学,要亦有得于史也。”(31)当把《人谱》和蕺山未竟的《人谱杂记》结合起来看时,《人谱》所开显的心性义理之学与人之历史发展颇相契合。中国传统儒家哲学讲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如若个体没有成熟的道德理念(内圣),他就不能在修齐治平的外王事业中有所成就。历史就是由有着绝好道德修养的人创造出来的,《人谱杂记》所选择的嘉言懿行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真切把握。《人谱杂记》可看作是一部小小的人物传记,这种人物传记,以人物的道德精神为中心,历史的意义也就体现于人们体道的过程中。刘宗周除了写作《人谱》和《人谱杂记》这样的理论著作外,还写下不少人物传记与墓志铭,其写作的重点集中于对人物道德的评价上,他的此种写作方法直接影响了后世学者的写史方法。蒋年丰先生深刻地指出:“自有《史记》以来,中国史学即重列传。但经过刘蕺山与黄梨洲之影响的列传,即强调为体道的人格列传。换句话说,经此影响,列传转型为‘仁人志士的列传’。历史真理表现在仁人志士的节操之中。这种史学思想乃是新的发展。”(32)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写道:“浙东之学……绝不空言德性……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33)章学诚所指出的浙东学术“绝不空言德性”,与蕺山所开启的“人格列传”的写法密切关联。蕺山论“知”是与“行”密切相合的,“即知即行,知行合一”。他在《人谱》中说:“夫知有真知,有常知。昔人谈虎之说近之。颜子之知,本心之知,即知即行,是谓真知。常人之知,习心之知,先知后行,是谓常知。真知如明镜常悬,一彻永彻;常知如电光石火,转眼即除。”(34)真知即是“即知即行”,即知自然行,所行自然有其知,知与行并无间隔,非先知后行者。而且,蕺山所主张的“真知”必须落实于“身”,他在《问答》中指出:“为学不得悠悠泛泛,须实落着在吾身上,方有进步可言。”(35)“真知”之自然落实,便是圣贤人格的彰露。《人谱杂记》描述、引用圣贤人物的方式,恰好正是以史论理、以史明鉴。正因如此,杜维明先生才说《人谱》的道德形上学彰显出“经史相容、亦经亦史”(36)的史学价值方向。
蕺山六十八岁作《中兴金鉴录》,通过历代中兴帝王治国方略的得失与个人道德品行的评价,总结出一套他自认为可以使弘光政权迁延明祚的治国之道,包括中兴目标、中兴方略和中兴之主所应具备的道德品行等,其本质是在宣扬以虞廷“十六字心传”之“心法”为“治法”的道德史观、心性史观。是书最大的特点是坚持了道德判断和历史判断相统一的历史评价准则。历史的运动往往是这样: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君子,而控制历史运动的是小人,小人与君子共同缔造着历史。为了凸显人类的进步,为了张扬人类的文明,我们总是喜欢对历史上的贤人君子褒扬有加,但若仅限于此的话,这样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历史总是在矛盾运动中进行,有君子必然就有小人,有君子的善行就会有小人的恶动。能够看到善行的同时也关注恶动,才能从历史那里真正得到启发、教训和经验,这才是符合历史本来法则的正确态度。客观的历史事件总也抹不去这两种人的活动轨迹,因此褒善就是在惩恶。所以当我们用“善”的准则评价历史事件时,还要运用“意义”评价准则。《中兴金鉴录》即是这样逻辑地把小人与君子统合在同一历史事件中,公正、理性地分析他们各自存在的意义,从而实现了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的圆融。道德判断是对一个人的行为,考察它是否依“当然之理”而行,是对历史主体行为之动机的探究,表明的是历史事件背后历史主体的出发点究竟是否符合道德的准则。历史作为人类活动的时间轨迹,它不可能完全是正义的,因此,“光只道德判断固足以抹杀历史,然就历史而言,无道德判断亦不行(道德在此中不能是中立的)。盖若无道德判断,便无是非”(37)。所以要正确了解历史事件的“历史性”,在进行道德判断的同时还须进行历史判断。历史判断是一种辩证的鉴别,它打破了认识主体单纯的主观性,从而要求主体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历史发生的客观事实,并辩证地接受和体悟它们。在《中兴金鉴录》中,经验与教训同样重要:道德判断往往得到经验,历史判断往往得到教训,两方面的融合通贯才能更好地评价历史。蕺山对历史判断的提升和重视,下启梨洲之经史之学以及船山道德判断历史判断兼重双美的历史哲学(38)。
总之,无论是蕺山的经世致用之学还是他的经史之学,都与他的心性义理之学圆融通合。宋明儒“体、用、文”分途,蕺山使之复合,三者互蕴互涵、经史圆融、心史相通。蕺山言心性义理,即心即性、心性圆融;言经世致用,则学术与经济圆融;言经史之学,则经史圆融。正因如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语学案提要》赞蕺山曰:“宗周讲学,以慎独为宗。故其解‘为政以德’及‘朝闻道’章首揭此旨。其传虽出姚江,然能救正其失。其解‘多闻择善多见而识’章有云:‘世谓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有二,予谓聪明睿知非性乎?睿知之体不能不穷于聪明,而闻见启焉。今必以闻见为外,而欲隳明黜聪求睿知,并其睿知而槁矣。是隳性于空,而禅学之谈柄也。’其针砭良知之末流,最为深切。”蕺山圆融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观念正是对宋明儒重心性义理而轻经世致用思想的纠偏。故而余英时先生指出,蕺山的阐论实预示着新时代的来临,“是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的清楚指标”(39)。由此可说,蕺山之学是宋明理学“知识论”演进的新阶段。
注释:
①[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1《安定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页。
②⑥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30、299页。
③参见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9页。
④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第17页。
⑤[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页。
⑦[清]黄宗羲:《弘光实录钞》,《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⑧[清]黄宗羲:《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0册,第433页。
⑨《刘宗周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47页。
⑩《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526页。
(11)《刘宗周全集》第三册,第336页。
(12)《刘宗周全集》第三册,第368—369页。
(13)如1629年,蕺山五十二岁时曾有《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批评崇祯刚愎自用,建议行尧舜之道。“疏入,上惮其直,又心以为迂,竟不听。下旨云:‘这所奏不无迂阔,然亦忠荩。’”(姚名达:《刘宗周年谱》,载《刘宗周全集》第6册,第321页)
(14)[清]黄宗羲:《子刘子学言》,《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册,第286页。
(15)詹海云:《刘宗周的实学》,载钟彩钧主编:《刘蕺山学术思想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第440页。
(1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17)陈祖武点校:《清儒学案》,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3—94页。
(18)《刘宗周全集》第六册,第212页。
(19)参见刘述先:《黄宗羲心学的定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20)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导言第1页。
(21)转引自赵令扬:《无根的一代:从明代思想谈起》,载汤一介编:《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一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388页。
(22)陈永革:《儒学名臣——刘宗周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页。
(23)蔡方鹿先生指出,刘蕺山将“慎独”与经学相结合,强调“六经”之教皆以阐发人心之蕴。他融会经学、理学及心学,对宋明理学加以系统的总结和融会贯通,在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蔡方鹿:《刘宗周“慎独”说与经学相结合的思想》,载《天府新论》2008年第5期)。詹海云先生亦说:“在经学上,《大学古文参疑》是考据与义理的融合。而《礼经考次》一书,宗周之用心是一方面厘清经书之面目,使孔子之旨复明于世。一方面表彰仪礼,以其乃周公所以佐周以致太平之书,欲其与‘易、诗、书、春秋并重不朽’。而《礼经考次》中的《古学记》是匡正当时学者浸淫佛老,谈玄说虚,不重修身之弊。”(詹海云:《刘宗周的实学》,载《刘蕺山学术思想论集》,第454页)
(24)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3页。
(25)《刘宗周全集》第六册,第201—202页。
(26)钱穆:《中国史学发微》,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84页。
(2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28)钱穆:《中国文化丛谈》(1),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147页。
(29)《杜维明学术专题访谈录——宗周哲学之精神与儒家文化之未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30)蒋年丰:《从朱子与刘蕺山的心性论分析其史学精神》,载氏著:《文本与实践(一):儒家思想的当代诠释》,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49—277页。
(31)张高评:《黄梨洲及其史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页。
(32)蒋年丰:《从朱子与刘蕺山的心性论分析其史学精神》,载氏著:《文本与实践(一):儒家思想的当代诠释》,第271页。
(33)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523页。
(34)《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19—20,356页。
(35)《杜维明学术专题访谈录——宗周哲学之精神与儒家文化之未来》,第129页。
(37)牟宗三:《历史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38)参见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台北,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221—269页。
(39)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336—3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