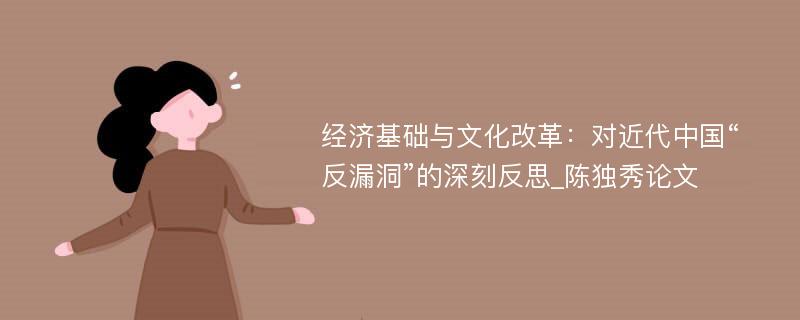
经济基础与文化变革:中国近现代“反孔”的深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基础论文,中国论文,近现代论文,深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1-0067-06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显著成就是动摇了以儒家为轴心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把孔子推下了神坛,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彻底解决孔子问题推到了极其突出的位置。与此同时,通过陈独秀等人的反孔实践,也给后人留下了总结经验、汲取智慧的丰厚文化遗产,从中可以提炼出很多富有哲理的教训和发人深省的启示。诸如,解决孔子问题是用政治和革命的手段,还是用学理的文化方式;不考虑或较少考虑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单纯去变革孔子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能否行得通;对孔子文化的改造,是着眼于过去,还是立足于现实和现代化进程。这些问题实质上涉及中国古典文明的现代转化,非一篇文章所能胜任。故而,从一定意义上讲,本文提出的问题多于探讨解决的问题。
一
实质上,孔子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对文化问题,只能用符合文化本身发展规律的方式来解决。五四反孔着眼于政治上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大批判,淹没了最初设定的文化式的学理解析,其结果是,思想震撼有余,持久的文化积累不足,圣人的光环仍在。
按照梁启超的观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发生,是近代中国人引进西方文化逐步深化的能动反映。他在1923年撰写的纪念《申报》创办七十周年的文章中认为,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学西方,第一阶段是学器物;第二阶段是学制度;第三阶段,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是学精神文化。梁启超解析陈独秀一代优秀知识分子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逻辑思维是:中华民国成立后,“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1](P39、43—45)。陈独秀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并非要搞政治运动,而是像梁启超所分析的那样,革新“旧心理”,打造新“人格”。1916年来临之际,陈独秀即撰文呼吁国民尤其是青年,要发扬“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气概,“动心忍性”,来一番国民性格的彻底改造,为铸造新文明,建设新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满怀激情地写道:从1916年开始,“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民族,以新家庭”。“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2]胡适则“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3](P330)。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文学改良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旧传统,为现代新文学奠定了根基。特别是白话文运动,从根本上解决了几千年书面语言和行为语言的矛盾,改变了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和文化追求,釜底抽薪地改造了传统,创造了新文明。这种平和、理性、学理式的文化改良,就是胡、陈二人所期待的样板,也就是在除旧布新的过程中,为建造新文明铺路搭桥。在对待孔子的问题上,陈独秀等精英们也曾经运用这种方法,解析儒学,剖析圣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果。
在政治文化方面,揭示了皇帝这个最高的权力代表和孔子这个最高的思想权威之间的相互利用。如李大钊称皇帝和孔子为“大盗”、“乡愿”,他认为:“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做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做不成圣人。所以我说,真皇帝是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4](P125)。易白沙则指明了孔子专制思想的具体表现,即“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5]。这些评论虽然还过于简单,缺少学理的深度,但无疑打开了认识孔子的新思路。
在伦理文化方面,陈独秀一代对孔子的“礼教”进行了全面抨击,“吃人的礼教”、“奴隶的道德”成了那个时代的流行语。陈独秀指出:
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2]。
陈独秀还特别指明孔子的思想学说与民主、科学以及现代生活相矛盾,其称: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6]。
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7]。
综合陈独秀的这些言论,可知他是在鼓吹人格独立、个性张扬、民主科学,这种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现代社会的民主与科学,大大提升了批判孔子及其学说的水平,展现了一种新思路。
陈独秀一代哲人批孔的智慧源泉和理论指导基本是西方天赋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思维方式和逻辑推理也充满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评判精神。理论和方法的更新,使他们在清算孔子及其儒学的过程中新意迭出,新人耳目。孔子这个在传统社会根本不成问题也绝对不许成问题的问题成了问题;孔子这个和皇帝并驾齐驱的思想政治权威发生了动摇;孔圣人的说教成了批判的对象;以孔圣人为理论根基的专制集权文化和宗法伦理文化更需要来一番彻底改造。总之,在近世的工业文明社会出现后,在农业文明状态下沿袭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出了“大问题”,不改造中华文明就无法进入人类工业文明时代。这犹如在思想文化界刮起了飓风,沉寂的死水掀起了万丈波澜。但是,孔子文化早已积聚成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流淌着其血脉,对这样的文化加以清理改造,时日之长是起码的一个条件。诚如胡适、陈独秀所设想的二十年甚至几个二十年的时间,同时还需加上经济与社会同步变革等其他必备的基本条件。遗憾的是,随着陈独秀一代政治意识的加强和五四革命风暴的突起,清理孔圣人及其代表的传统文化变得政治化、革命化,一蹴而就的急燥态势已难以改变。
陈独秀一代虽然极力从西方寻求解决孔子问题的智慧和力量,但关心现实、关注民生、“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传统,仍是他们发起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挥之不去的精神力量。孔圣人文化的传统因子随时会在他们身上发酵。儒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和政治的紧密结合,逐步使政治“泛化”。“泛政治化”是孔子及其儒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喜欢孔圣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只有将政治泛化,什么都成了政治,政治就变成了一种“专制”,构筑专制集权即如风行水上,顺理成章。结果是,人人都关心政治,全民受政治控绑。迷信权力,追求权力,成了社会的核心价值。权力拥有者则借之引诱民众,为所欲为,专制统治便大行其道。迷信权力的最典型表现就是“学而优则仕”,“内圣外王”,演变到极端则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意识特别浓厚的国度里,想让政治不统帅一切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陈独秀一代很难完全摆脱这种传统价值取向的束缚。如此,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过程就变成了陈独秀等人政治热情异乎寻常高涨的过程。他明确讲:“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8]又说:“吾人既未能置身政治潮流以外,则开宗明义第一章,即为抉择政体良否问题。”[9]显然,陈独秀一代的反孔要由最初的学理层面转向政治,并伴随着五四风暴,转向革命。
毫无疑问,孔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封建社会绝对维护专制及其政治。孔子文化政治色彩之丰富,是其他任何学说难以比拟的。按常理讲,如此浓厚政治色彩的孔学,就应该运用政治或革命的手段去解决。但是,即使孔子及其学说政治意识极其强烈,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思想,一种文化,是为政治服务的,还不等同于政治,仍然属于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何况,孔圣人的东西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骨髓里,这不是动用任何政治手段甚至政治运动所能解决的。即使是暴力革命也威力有限,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政治手段或暴力革命对孔圣人已经无可奈何,有时甚至适得其反。“文化大革命”正是因为变成了一场政治大革命,结果文化没有新生,反倒“革”了文化的“命”。在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是靠轰轰烈烈的政治大革命能够解决的。
历史地看,从政治或者革命的角度去解决孔子问题并不科学。一般情况下,政治手段或暴力革命较多地被运用于解决政权的更迭和权力的分配。如果以之去解决思想文化问题,可以轰动一时,表面上看颇有成效,但风头一过,深层次问题仍不能解决之。
回观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一代最初所抱定的远离政治、专注文化的批孔方针,是很有见地、合乎文化变革内在规律的,但陈独秀一代骨子里对政治的一往情深以及五四政治风暴的突起,亦促动他们运用轻车熟路的政治革命手段。方法的欠佳,削弱了反孔成果的积累;路径的错位,阻碍了文化的创新。孔子问题的真正解决和孔子学说的现代升华,只能留给后人。
二
孔子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经济社会的进步,孔学积聚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和经济社会基础的变革是同步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超越经济社会基础的孔子“革命”,无论走多远,还要还原到起点。这是从五四运动以及近代反孔归纳出的一条最宝贵的经验。
陈独秀一代批判孔子的重要依据就是孔子的思想和学说不符合现代生活,为此他专门写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从不同侧面论述孔学缺少共和理念、民主意识、自由精神,尤其是伦理纲常束缚人的个性发展,影响国家振兴和民族崛起。文中还突出阐明了思想理论和经济社会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其云:
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学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7]。
陈独秀在这里强调的,一是思想学说和社会生活状态的一致性;二是人格独立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协调性。正因为孔子的理论学说和人格自由发展相冲突,和现代社会生活格格不入,所以必须反孔。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认识完全一致。他说:
他(即孔子)的学说所以在中国行了两千多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缘故。现在经济上发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10]。
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理论推导及逻辑思维十分严密,无隙可击。但是,陈、李二人所讲的“现代生活”、“现代的社会”并不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态,而是西方的欧美,欧美才是他们一切立论的参照系。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国家混乱,民生凋敝,民族危机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所谓的共和国较之前清少有实质性的进步。所谓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只是一帮无知文人的鼓噪。陈独秀说:
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就带君主专制臭味;不过胆儿小,不敢像筹安会的人,堂堂正正的说将出来,其实心中见解,都是一样[11]。
应当说,陈独秀对当时国人认识水平的估价是得体的,其主流是筹安会一样的帝制思想。遗憾的是,陈独秀没有更深入地去研究造成这种共和国号、帝制思想二元矛盾格局的深层原因,仅仅是归结为反孔力度不够。事实上,不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共和国体的新思想永远不可能成为国人的共识。在一个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国度里,简单地去套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反对集中代表小农经济社会的孔子学说,不能讲没有成效,但不可能最后成功,风潮一过,就会反弹回来。五四运动后的孔子思想学说仍然弥漫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社会经济生活没有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多数反孔的结局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陈独秀一代的悲剧是整个中国社会经济没有现代化的悲剧。百年来的反孔,基本上没有走出这种误区。火候不到就揭锅,馒头总是生的。
太平天国的反孔较陈独秀一代更严厉。洪秀全称孔子为“妖魔鬼怪”,命令将士砸孔子牌位,推倒孔子神像,焚烧孔庙,还将儒家经典全部烧毁。在南京,太平天国将孔庙改为屠宰场,把孔子牌位扔到马厩、猪圈里。凡私藏和阅读儒家“妖书”者,斩!时人描述当时情景时称:“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12](P386)“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13](P735)如此激烈的反孔,除了为树立皇上帝的思想权威和洪秀全的专制权威外,在思想文化上毫无建树。没过多久,太平天国又恢复了儒家经典的地位,孔子照样无法打倒。以小农经济衍生的专制理论和思维方式去剔除以小农社会为根基的孔学,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自我设定的文化循环怪圈。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反孔”与洪秀全不同,为了变法维新,他偷梁换柱,把孔子改造成一位改革的思想家,孔子俨然成了维新变法的鼻祖,康有为的变法正是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变法主张。康有为等维新派实质上是把孔子作为传播他们维新变法思想的载体,表面上尊崇和弘扬孔子,实际上重新塑造了一个满载他们变法意愿的“新孔子”。“假孔子”在真维新中却发挥了意想不到的积极效应。但是,将西方社会运行的人权、立宪、市场经济理论等嫁接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权威孔子身上,无异缘木求鱼,必然失败。何况戊戌变法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状况依然有利于孔学立足。康有为后来迅速变为死心塌地的尊孔旗手,和他戊戌时期的造假失败不无关系。
辛亥革命时期,对孔子及其儒学的冲击具有新特点。革命党人和康有为拉孔子做大旗来推行其维新思想不同,他们是直面孔子,旗帜鲜明地予以抨击;也和洪秀全的焚书砸孔庙有别,他们是运用民主革命的理论,从学理上批判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封建主义本质。邹容在《革命军》中系统而深刻地批判了孔子为中国历代封建皇帝所利用,成为推行专制集权的思想政治工具,儒学把国人都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唯唯诺诺的“奴仆”,要想中国进步,首先要打倒孔子。章太炎则批评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是“忠君”的“伪学”,专“以富贵利禄为心”,败坏了整个社会风气[14](P289)。还有革命党人深刻指出:“君主无圣人,则其压制臣民较难,惟有圣人而君主乃得操纵自如,以济其奸。”[15]总之,虽然他们批判的规模有限,深度也很不够,但毕竟开创了在理论上抨击孔子及其儒学的先河,为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封建帝制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但由于承载思想文化变革的深层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没变,随着革命成果的丧失,尊孔之风猛烈回潮。陈独秀一代不得不再次发动新的反孔运动。
回过头来看,无论是洪秀全、康有为的反孔,还是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前后的排儒,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用,但却没有留下传之久远的经典的文化成果,开创性的文化奠基作品难以寻觅。倒是1930年代前后新儒家学院式的“返本开新”的儒学研究,留下了一批经得起推敲的可以传之久远的代表中华民族文化水平的成果。冯友兰、汤用彤这些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有深厚的古典文化积淀,对西学也有透彻的了解,既不泥古不变,也非食洋不化,他们在振兴儒学的过程中,创新性地改造了儒学,将孔子向现代拉了一小步。从广义上讲,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反孔”。这正是陈独秀、胡适一辈在发动新文化运动初期所盼望的。美中不足的是,这些富有积极意义的学院式的成果没有通过大众媒体转化为民众意识,其影响力主要停留在学术界。
从太平天国到五四时期,所有的反孔都没有真正成功。核心问题就在于孔学赖以成长的“土壤”即经济基础没有根本改变,社会本体不变,却反复发动意识形态的革命,超越了经济社会的许可,当然难以成功。李大钊在五四时期写的一篇文章中说:
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16]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讲经济基础决定一切;后半部分是强调通过阶级斗争来推进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一个是基础,一个是手段,二者相辅相成,协调发展。但五四运动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则似乎忘却了前半部分,很少讲或基本上不讲经济基础决定一切,而一再强调阶级斗争决定一切。这就造成了近百年来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革命,毫不在意经济基础的许可。处于这种认识水平的批判和清除孔学运动,负面的东西不言而喻,陈独秀一代的“打倒孔家店”也没有逃脱。马勇在编辑五四启蒙史料集前言里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他认为:
当中国社会经济尚未达到陈独秀所期望的“现代”标准时,理论观念的提前转变势必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失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以来不是中国旧有的观念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滞后于意识形态的变迁。换言之,包括五四在内的近代国人在精神上的追求远远超过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遂使意识形态不是为社会的稳定与有序服务,而是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失范[17](P6)。
三
文化变革,是渐进的、改良的,非革命的。从五四反孔实践所提炼出的评判的态度、学理的研究、国民性的改造,是解决孔子问题的合理途径。孔子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文化自觉和文明再造的过程。
文化变革,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价值观更新。而价值取向的提升,不是靠强迫的,只能是自省自觉的;不是一朝一夕的,只能是日积月累的。革命和战争的强制行为,不能说对文化的变迁不发生作用,但从根本上解决文化问题,只能靠一天一天的时代进步与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就像人的知识积累和人类文明的创造一样。胡适在总结五四新思潮包括反孔经验时讲:
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18]。
胡适在这里一口气用了四个“一点一滴”,显然是强调文化和文明创造的长期性、渐进性,也是对五四后期学术界、文化界浮躁情绪滋长的不满和批评。与文明的创造相比,传统文化的更新,更艰更难,更须从一点一滴来做起。孔子文化承载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讲中国传统,孔学是核心。所以,中国新文化和新文明的建造,必须要对孔圣人的传统进行根本的改造,进行一点一滴的和平改良。而改良的重点,不是过去,而是面向现实。传统表面看是历史的,实质上也是现在的。任何传统都是通过现实而展示的。孔子的文化传统渗透在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存在于国民的头脑里和日常生活当中。诚如梁漱溟所概括的:“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19](P214)思想观念民主科学了,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现代化了,孔子及其学说中隐含的封建主义传统就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存活了。禁止尊孔读经、砸烂孔庙,只是形式,是末;根除人们头脑里和生活里的孔圣人,才是实质,是本。本末倒置,就很难完成孔子文化的现代转化。一般情况下,治末容易治本难。所以,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出的一点一滴去改造传统、创造文明的主张难以变成现实,而砸孔庙、禁尊孔的“革命行动”则反复出现。这种本末倒置的历史教训值得铭记,而被历史证明行之有效的更新孔子文化的方法必须提倡。至少,以下三条可以参考:
其一,评判的态度。这是胡适对五四新思潮的高度概括。其云:
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2)对于古代遗留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这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18]
这里所阐释的评判的态度,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具有自信、怀疑、创新等独立精神,渗透着追求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的近代人文主义理念。以这种精神去剖析孔子及封建儒学,本身就是对其人伦道德中奴隶主义和封建等级关系的背叛。如果再进行深一层评判,对传统孔学的清理不可能不见硕果。诚然,评判的态度必须要有新的理论方法做指导,有新的参照系做标尺,故而胡适提出了“输入学理”。总之,只要不盲从,社会就会有活力,独立自信的民族精神就可能铸就。
其二,学理的研究。任何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都有可以立足的理论支撑、哲学根底和社会基础,何况孔子文化已延续了两千多年,中间又经过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汲取佛学的多次创新与再造,其内涵之丰富,理论之深厚,哲理之缜密,基础之广博,在世界文化园林中是屈指可数的。对如此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进行改造,没有长期的学理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五四时期那样的反孔也就是吹吹风,真正让孔学来一个创造性的转换,主要还靠长期坚实的学理研究。胡适在总结五四新思潮缺少学理研究的教训时指出:
我希望新思潮的领袖人物以后能了解这个教训,能把全副精力贯注到研究问题上去,能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能把一切学理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种种切要问题上去;能在研究问题上面做输入学理的工夫;能用研究问题的工夫来提倡研究问题的态度,来养成研究问题的人才[18]。
胡适之所以如此关注学理的研究,是因为学理问题是文化的核心。孔子文化的核心问题不解决,仅触及皮毛,用处不大。如果从学理上阐明了孔子及其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完成了孔学的现代升华,孔子文化自然会向新文明逐步转换。当然,经院式的精深的学术研究,有—个向社会和大众转化的过程,也就是由体到用的链接。如果链接得好,就有可能出现一场成功的思想启蒙。
其三,国民性的改造。从某个角度看,中国人都有孔子性格的影子。孔子性格是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孔能否成功的最后标志,决定于这种民族性格的改造程度。这一点,五四先哲确实看得很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先知先觉先思先行者一再强调封建礼教的核心是使中国人失去了自我,养成了奴隶的性格,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他们尤为特别号召要进行伦理的变革,包括政治伦理和生活伦理。陈独秀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9]只有实现了伦理的革新,才可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2]。人格即人性,延伸到民族和国家,就是国民性。从国民性中彻底铲除了孔子及其学说的专制主义的封建毒素,釜底抽薪,孔子文化才可能从本质上具有现代性。国民性的改造,与反孔密切相连。在这方面,鲁迅主张最力,行动最烈。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都是对孔子文化的抨击,对国人奴隶性格和“吃人的礼教”的深刻揭露和鞭打。终其一生,基本致力于民族性格的解剖和民族劣根性的批评。令人惋惜的是,鲁迅难以找到一条提升国民性的途径。这可能是其一生郁闷的—个重要原因。
当然,国民性的改造需要多种因素交织互动,是一种社会综合功能,是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样态的转化。当—个民族和国家向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自由民主、平等和谐逐步迈进的时候,国民在安居乐业中就会逐步提升自身素质,“阿Q”一辈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洗掉孔子文化制约下的劣根性,成长为现代公民。而国民的饮食起居、行为举止、思想品格一旦完全步入现代社会,孔圣人也就变成了现代生活和现代文明中的孔夫子。那时,既不需要批孔,也不必打倒“孔家店”,反而需要弘扬孔子文化,为提升国民素质服务。至于尊孔读经,自然不必强禁,孔庙当然亦须保留,现代文明的核心是尊重一切先人的思想资源,造福于人类精神和谐家园。
[收稿日期]2009-10-20
标签:陈独秀论文; 孔子论文; 儒家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胡适论文; 国学论文; 反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