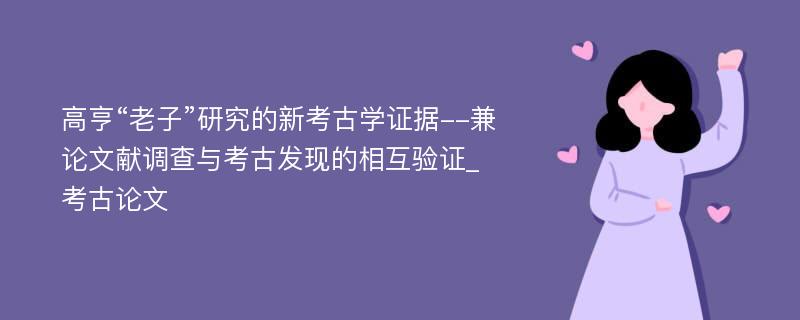
高亨《老子》研究的考古新证——兼论文献考察与考古发现的互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子论文,考古发现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839(2001)05-0016-08
老子问题曾经是学术界的一大公案。当年在许多学者对老聃及其著《老子》提出诸多疑问时,高亨先生曾凭借对文献的悉心考察,成为肯定者中的代表。近年郭店战国楚简《老子》的出土,解开了关于老聃与今本《老子》关系的一些疑问,正可视为高亨先生关于老子及《老子》判断的新证。其实,也只有将高亨先生的文献考察与考古发掘的新材料结合起来,互相生发,才能对老子及《老子》有一个更接近事实的认识。由此,我们有必要对文献考察与考古发现的互证问题予以重申,并给以新的理论说明。
一
老子谜团,是太史公在《史记》老子本传中为后人留下的。在这篇不长的传记中,他首先记述了“姓李氏,名耳,字耼”的老子,即春秋末年孔子曾问礼的老聃,并明言老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无疑,在太史公那里,是基本倾向于老聃著《老子》的说法的。问题是,在这同一篇传中,太史公又提到了与孔子同时的老莱子和战国时代的周太史儋,并提到“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也莫知其然否”,这就为后来关于老子及《老子》的研究和判断,留下了很大的缺口。
从宋代疑古思潮开始,直到近现代乃至当代,都不乏对老聃及其著《老子》持怀疑或否定态度者,而且这种否定的声音曾渐趋强烈,一时间几乎成为老子及《老子》研究的主流。归纳起来,其思路大致有这样几种:
第一,从外围的各种迹象判定,认为老子应是战国时人。比如宋陈师道提到“孟子辟杨墨而不及老”(《理究》),言外之意是孟子时代老子还没有出现。清代汪中就太史公所记老子出关遇关尹、并为之著《道德经》上下篇之事,指出与关尹同时的列子被杀于孔子殁后八十二年,为关尹著书的老子自然不会是春秋时的老聃;又指出函谷关置于献公之世,知“遂去至关”的老子是秦献公时人。此人正该是战国时的周太史儋(《述学补遗》)。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一文,更通过统计“《吕氏春秋》的作者……简直把五千言的三分之二都吸收进去了,但始终不吐出这是取材于《老子》的”,大胆假设“在《吕氏春秋》著作时代,还没有今本《老子》存在”[1]。
第二,从老聃与《老子》的思想矛盾方面分析,认为世传《老子》与春秋时代的老子在思想倾向上有所不同。比如针对《老子》非礼与《史记》、《礼记·曾子问》载孔子问礼于老聃的情况,宋叶适就曾指出:“然则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必非礼家所谓老聃,妄人讹而合之尔”(《习学记言》)。汪中更明确点出史称孔子问礼于老子,而《老子》书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述学补遗》)。梁启超也说《曾子问》所载老子的谈礼,和《老子》书相反[1]。
第三,从《老子》一书本身的观念和用词方面分析,认定该书乃战国所作。梁启超就称老子有许多太激烈太自由的话,不像春秋时人说的。《老子》书的“王侯”、“侯王”、“王公”、“万乘之君”、“取天下”、“仁义”字样,也不像春秋时所有。顾颉刚说老子痛恨圣智,实在因为战国后期,社会上受游士的损害重极了,才有这种呼声[1]。
第四,从《庄子》、道家、杨朱与老子的关系着眼,论证老子是《庄子》创造的或《庄子》之后的产物。清人崔述就认为关于老子之说来源于“战国时,杨墨并起,皆托古人以自尊其说。儒者方崇孔子,为杨氏说者因托诸老聃以绌孔子”(《朱泗考信录》)。梁启超指出《史记·老子传》本于《庄子》,《庄子》是寓言。孙次舟《跋古史辨第四册并论老子之有无》则根本否认老子的存在,称“老子本无其人,乃庄周之徒所捏造,藉敌孔丘者也。”证据是:《论》《墨》《孟》都没有称及老子,至《庄子》始忽有老子;《庄子·德充符》述无趾老子对语,称孔子学于老聃。“后世关于老聃之重重演化,皆基于此。”不知“无趾者,无足也;老聃者,大耳也。”至《老子》书的产生,则是“庄周后学一面虚造老子之事实,一面复收庄周以还研究所得之精理妙义,著之篇章,题为老子,以实其人也”[1]。
第五,从肯定太史儋或分老聃与李耳为二人的角度,否定老聃即著《老子》的老子。梁启超指出据史载推之,老子的八代孙与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罗根泽进而认定老子八代孙不能与孔子十三代孙同时,太史儋的八代孙则正可与孔子十三代孙同时。另外,罗根泽还指出了老聃与太史儋事迹重合的两点。一是老聃为周柱下史,太史儋也是周之史官。二是老子出函谷关,太史儋入秦也必出函谷关。由此断定,太史公所记的关于老聃的传说,实际上都是太史儋的事迹,太史儋才是著《老子》的老子。刘汝霖分老聃与李耳为二人,称教孔子者是老聃,辑《老子》者是李耳。老聃“说了许多格言,却没有书行世。”至战国的李耳,始编辑成书,所以“就带了战国时代的色彩”[1]。
正是在这些置疑的基础上,罗根泽先生作了一个近乎定案的总结。他在《历代学者考证老子年代的总成绩》一文的《跋》中指出:“文中希望老子的年代问题能得到大体的解决,好据作他方面的研究,总算实现了。在这以后,它已不再是各家写专文争论的问题,而是在各种史书上,一般的都排在孔墨之后,不再排在孔墨之前。1944年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7年《中国思想通史》,均把《老子》列于孔墨显学之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也把《老子》放在孔墨后、孟荀前。他说‘著道德经五千多字,号称老子’的,是‘生在孔子死后一百多年’的李耳。1954年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更说《老子》一书‘不仅成于战国时代,且成于战国时代的庄子之学大兴以后’。1955年杨宽《战国史》把《老子》放在孟子之后……。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称‘大体上推知老子本人在春秋时代,《老子》一书成于战国晚期’”[1]。
由此不难看到,对老聃著《老子》之说的否定,一时间几乎成了定论。
二
尽管如此,高亨先生根据自己对文献的悉心爬梳和研究,还是自始至终坚持了老聃著《老子》的观点。
当然,对上述老聃否定说持反对意见的并非只有高亨先生一位。实际上还有不少学者作为老聃肯定派,在讨论中都曾针对否定论者发现的问题,寻找论据或理由予以回复。如张煦据《论语》“窃比于我老彭”之语,认为老即老子,以证孔子并非没有提过老子,据《论语》所引“以德报怨”之语,见于《老子》,证当时已有《老子》之书;唐兰据儒家的《礼记·曾子问》也记孔子见老聃,证此事并非出于道家的虚构;黄方刚据《孔子家语》《列子》《战国策》《吕氏春秋》《韩非子》及《庄子》所引老子语,“考订《老子》书之年,至迟当于庄子生时已传于世。”至于作者,则据《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鸿烈》及《贾子新书》,知是老聃。老聃是老彭,不是李耳,老子书成于孔子存时。马叙伦据《吕氏春秋》载子产见壶丘子林,《庄子》载列子见壶子,证列子与子产同时,进而与列子同时的关尹子为春秋末年人[1]。只是这些论证大多集中在对于老聃最初传授《老子》的肯定上,而对于《老子》的写定和成书,在论争后则显得犹豫起来,或大多断在了战国中期。比如胡适1933年发表的《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在分析了冯、梁、顾、钱诸人的证据后说:“我不反对把《老子》移后,也不反对其他怀疑老子之说,但总觉得这些怀疑者都不曾举出充分的证据。”唐兰先生1929年发表的《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尚肯定“老聃就是《道德经》的著者,至少其中一部分的传授者”,“《道德经》是老聃的遗言”;而在1934年发表的《老子时代新考》中,虽仍肯定老子即是与孔子同时的老聃,但又据老子说到“万乘之主”,并“仁义”连用,把《老子》书的撰成时代定在与《墨子》、《孟子》同时,此外,郭沫若一方面主张《老子》乃老聃的语录,一方面认为集成这部书的是学黄老之术的环渊,即关尹,年代大约与孟子同时[1]。总之,他们都无法回避今本《老子》中战国色彩的问题,也就只好折其中了。
高亨先生关于老子和《老子》的研究,见于1934年发表的《史记老子传笺证》[2]、1956年出版的《重订老子正诂》[3]、1979年发表的《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4]等著述。应该说,他的论证,是在吸收已有的老聃肯定说所列举的诸证的基础上进行的。上述比较有力的证据,诸如战国各种典籍对《老子》的征引,在他的论证中都被综合采纳和借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他通过文献考察所提供的新证据、新研究和独立性。
第一,与老聃否定论者不同,与大多数老聃肯定论者也不同,高亨先生是自始至终肯定老聃著《老子》的论者之一。在《史记老子传笺证》中,他提出《道德经》决为老聃所作,并举六证以明之。在《重订老子正诂》中,他也感到老子问题目前还没有充分证据来下结论,并承认《老子》一书有些部分一定是战国的产物;但仍认为其中的思想内容有些部分是春秋末期的产物,也就是说,是老聃所为。后来在《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更在新研究的基础上肯定了早期的论断,即“《道德经》一书是老聃所作”,只是书传之后又“有战国时人增益的文字”。这和其他肯定论者所称该书集成于战国中期的观点是有所区别的。
第二,他不独详尽列举了战国诸书引《老子》一书语句的材料,还特别发现了其中许多书提到老子或老聃的证据。如他指出,《庄子·寓言》曰:“老子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见《道德经》四十一章。《天下》称:“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见《道德经》二十八章。此二处径作“老子曰”、“老聃曰”矣。《天下》一篇,绝无寓言,最为可信。他还指出,《吕氏春秋》虽不称“老子曰”,但在《不二》中云:“老耽贵柔。”吕氏此言,必非无据。察老聃贵柔之旨,具在《道德经》中,则发此评者,盖尝见《道德经》矣。这就比一般的引用战国典籍材料,论证更加充分,而且证明了战国诸书均认定著《老子》者即老子,或即老聃,而非太史儋。
第三,在据文献考察论证《老子》书早出时,他又发现了新的十分有力的证据。这就是与《孟子》大约同时的《墨子》已经引用过《老子》。这正是他断《道德经》决为老聃所作六证中的第一证:“《太平御览》五百十三卷引《墨子》曰:“《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见《道德经》四章。今本《墨子》无此文,《御览》所引当在阙篇之中。是墨子或其徒已见《道德经》明矣。其证一也。”上述关于诸子百家引《老子》的证据,都只能证明《老子》并非战国末年之作,却并不一定证明是春秋末或战国初之作;而用《墨子》引《老子》的材料,证明此点就增加了极大的可能性。
第四,高亨先生在对战国及秦汉各种典籍征引《老子》的材料全面排比后发现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就周秦两汉人所引,知周秦传本与两汉不同,两汉传本又自不同。”这对于理解《老子》一书的复杂情况及战国色彩,也是十分重要的(详后)。
第五,关于老子世系问题,高亨先生也分老聃与李耳为二人,李耳很可能即战国时人太史儋。因为所谓“老子者,姓李氏名耳”之说并不见于先秦著述。并推测李耳或即老聃之后,见于《战国策·魏策》的段干崇(《史记·老子传》称段干宗)当是李耳的儿子。这样就解决了老子八代孙与孔子十三代孙同时的问题。只是与否定派分二人正相反,高亨并不因此认定《老子》为李耳所作。
第六,也是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高亨先生通过对文献的发掘和考证,揭示出了老聃一段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从而为孔子见老子的时机、老聃著《老子》的思想基础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极为有力的佐证。高亨先生的这一发现来自对《左传》中一条关于老阳子的记载的释疑。《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冬十月……甘简公无子,立其弟过。过将去成景(甘成公、甘景公)之族。成景之族杀甘悼公(即甘过)而立成公之孙,杀……庾皮之子过,杀瑕辛于市,及宫嬖绰、王孙没、刘州鸠、阴忌、老阳子”。一个“及”字,给人的印象是包括老阳子在内的五人都在这场周贵族的权力纷争中被杀。然而《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又记在周王子朝争位失败后“阴忌奔莒以叛”;《昭公二十一年》记伶州鸠评论周景王,《国语·周语下》记周景王二十三年(鲁昭公二十年)伶州鸠与景王两次对话。高亨先生认为伶州鸠与刘州鸠当是一人,伶是官名,刘是姓。这里阴忌与伶州鸠二人的事迹都发生在上述所谓被杀事件之后,总不至于是死而复生。这只能说明,上引所谓被杀一段的文字一定有问题。高亨先生由此断定,其实五人并没有被杀,“及”应是“反”之讹,“反”是“召回”之意。也就是说,上述那段记载应是说成景之族杀了甘悼公、庾过、瑕辛,召回了此前因某种原因而逃往别处的五位朝臣。据情理推之,这五人应是因受甘悼公或甘简公迫害而逃亡的。从文献来看,“及”与“反”因字形极近而致讹的情形并不少见,高亨先生就列举了《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反”字误作“及”的两条材料以证之。令高亨先生对这一发现感兴趣的是它证明了老阳子的没有被杀,进而就可以把他和老聃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了。老阳子与老聃同时,都姓老,都在周王朝供职;老聃又有字伯阳之说(注:高亨先生称,老聃字伯阳一说,由来已久,今本《史记·老子传》:“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索隐》本作“名耳字聃”,司马贞注:“有本字伯阳。”是唐本《史记》也有老子字伯阳之说。老聃、李耳并非一人,所以“名耳字聃”之说根本是错误的。考刘向《列仙传》(《文选·反招隐诗》)李善注引)、边韶《老子铭》(《隶释》卷三)都说老子字伯阳,足证老子字伯阳乃汉人相传的说法,应该有其来历,不是汉人所捏造,是可以相信的。),因此,这位老阳子很可能就是老聃。而且,联系到《礼记·曾子问》中孔子在巷党见老子的记述,高亨先生推知,老阳子当时去周后所至之国即鲁国。这一发现解决了《礼记·曾子问》所提孔子问礼的时间和地点问题,更可据此理解老聃著《老子》。应该说,老聃的“贵柔”和“无为”,他老成的政治经验,当与他这段受迫害的经历,与他看清了政治的险恶,不无关系。这样一位博学而又经历坎坷的人,作出《老子》一书,就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了。
从上述关于老子及《老子》一书的研究讨论看,怀疑或否定论者提出的一些问题,大多都被高亨先生等肯定论者所解释,从而深化了人们对老子的认识。但《老子》书究竟成于何时,特别是《老子》书中显而易见的战国内容,以及其中的“非礼”所表现出的诸子论争味道,的确仍是个不小的问题。对于前者,高亨先生虽举《墨子》引《老子》,因《墨子》本身成书尚有早、晚之说,终难成为《老子》早出的铁证;对于后者所提出的“后人增益”说,确是个合理的推断,但终因是推断而不能成为定说。它们都有待于新的发现来证明。
三
近年考古有几次出土文献的重大发现,其中所见《老子》的传本,正在陆续证明着高亨先生的推断。先是长沙马王堆西汉前期墓中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与今本《老子》不同,可知不是一个传本;同墓出土的甲本和乙本,它们又有不同,也不是一种传本。后来是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其中的简本《老子》与帛书本和今本又有明显的不同。这首先便证明了高亨先生在文献考察时所发现的《老子》有多种传本的事实。既然有多种传本,论战国色彩为后人所加,就不是没有根据的了。
最关键的还是郭店楚墓简本《老子》的出土。据考古专家介绍,这座墓墓葬位置在楚国郢都外墓地范围之内,这一带楚墓的序列已经排定,足以说明郭店一号楚墓属于战国中期后段。具体来说,这座墓最接近离它不远的荆门包山一号、二号墓,包山二号墓所出竹简有一个纪年可确定为公元前323年。比包山二号墓晚的包山四、五号墓也是地道的楚墓,应早于公元前278年郢都被秦人占领。因此,包山一、二号墓及郭店一号墓估计都不晚于公元前300年。这个时间起码证明了《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期之前。因为就常识而言,墓中所出竹简的抄写时间应该早于下葬时间。而且,墓中出土有刻有“东宫之币(师)”字样的漆耳杯,证明墓主当是楚国宫廷某位太子的老师,这些典籍应是他生前所用,其时间更应早一些。要知道,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在典籍需要辗转传抄的情况下,《老子》一书之流传至楚国,是需要相当时间的。这就把书的作期起码推到了战国中前期。这个时间段对于已近战国中期的李耳或周太史儋作《老子》的说法是十分不利的,而对于高亨先生所坚持的老聃撰《老子》的说法,却是十分有利的证明。佐之以《墨子》以及《战国策》中战国中期之前的记载已经有征引《老子》的内容,《论语》中“以德报怨”一语很可能出自《老子》,老聃作《老子》之说就更增加了几分砝码。
更为重要的是,简本《老子》本身也证明了它的早出,且证明了它极可能就是春秋末年老聃所著《老子》一系的传本。因为对照今本《老子》,有研究者已经发现,简本《老子》应是《老子》原始本,而今本《老子》乃是在此基础上的增修本。其论据比较重要的有这样几点。其一,简本没有与儒家伦理观念针锋相对的文字,今本中那些明显否定儒家伦理观念的段落在简本中皆有异文或文字上的增减。今本十八章的“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在简本中为:“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臣?”[6]一字之差,意思完全相反。今本十九章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在简本中为“绝智弃辩”、“绝伪弃诈”[6]。今本其他与儒家伦理观念相抵触的几章也都恰恰不见于简本。其二,先秦古籍后来增补的部分常常被放在原始部分之后。今观简本《老子》,其内容分见于今本的三十一章,据查全在六十六章之前,而今本六十七章至八十一章这整整十五章,在简本中没有任何踪影。总之,简本内容皆见于今本,这说明今本将简本悉数纳入。这样,问题就相当明晰了。简本应是今本中最原始的部分,今本则是后人在简本的基础上进行改造、重编、增订而成的。另有学者通过语言考察发现,简本多用虚词“也”,且用“亡”而不用“无”,这也说明简本时代比较早。
简本的发现,解决了老子及《老子》研究中最令人迷惑的问题,这就是战国色彩和诸子论争的问题。也就是高亨先生所推断的肯定有后人增补的问题。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原始本《老子》并没有一定是战国时代才能有的内容,今本《老子》中的“万乘之主”等等战国的词汇和内容,的确是后人增补时所带,所谓“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之类明显与儒家针锋相对的语句,也不见于简本,这就为肯定该原始本《老子》为春秋末年老聃所作,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佐证。至于其中的“绝智弃辩”、“绝伪弃诈”,并不一定是针对纵横家才会有的内容,因为孔子就十分讨厌辩巧之人,所谓“巧言令色,鲜矣仁”。简本不言“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而言“绝智弃辩”、“绝伪弃诈”,这恰恰说明它们很可能是与孔子大致同时代的产物。
四
用荆门郭店简本《老子》,印证高亨先生通过文献考察所得出的关于老聃及《老子》的认识,或者反过来,用高亨先生的文献分析,佐助对荆门郭店楚简本《老子》的指认,无疑使老子及《老子》问题的解决,得到了突破性进展。由此使笔者想到了文献考察与考古发现互相印证的问题。
当然,这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王国维就已经明确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的观点,即1926年他在《国学月报》第二卷发表的《古史新证》中的《总论》中指出的,“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9]前辈学者们也已经运用二重证据法,解决了许多学术上的疑难问题,或推进了问题的研究。只是人们更多的还是处于解决具体问题的阶段,对考古发掘与文献考察的互证关系,似乎尚缺少系统的总结。而且,当时乃至今日,人们更多的还是出于对新发现文献的兴奋,论“二重”实更偏于对考古发现这“一重”在解决疑难中的决定作用,而较少注意文献考察的意义。
首先应该指出,考古发掘对于古代某些学术问题的研究,其意义的确常常是决定性的。上个世纪学者们曾花过很大精力论证许多先秦典籍为后代所作,诸如上述顾颉刚论《老子》为《吕氏春秋》之后的作品,还有如吴则虞论《晏子春秋》为秦统一后一段时间内所作(《晏子春秋校释》)等等,战国中期荆门郭店楚墓简本《老子》的出土,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用战国字体抄写的《晏子》的发现,使这些论证不攻自破。学术界因此而热烈欢呼考古新发现是很自然的,有人甚至对以往考据方法的价值发生怀疑,一切都想等待新文献的出土来作结论,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考古发现对于考察古代学术问题并不是万能的。第一,地下考古发现多是出于墓葬,原本在对古文献的保存方面就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像郭店楚墓,因为墓主人是一位学者,师长,所以我们有幸见到了当年的部分典籍,而其他一些楚墓,像十分著名的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湖北江陵楚墓等,虽也都出土有竹简,但多为卜筮文字和遣策之类,并未见到今传的典籍。很显然,今日的发掘,并非我们需要什么就会发掘什么,学术研究是不能完全依赖它的,甚至可以说不能主要依赖它。第二,考古发掘对于论证古代学术问题,有其特点和偏重。比如出土文献作为尘封在地下的古本,对于考证书籍的出现年代、文字用词、借以检验其他典籍的讹误等有其特别的功效,比如上述《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赖银雀山汉墓手抄本《晏子》的出土得以解决,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一句“左师触龙言愿见,大(太)后盛气而胥之”,解决了今本《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中的“触詟”当为触龙的问题等等。但出土文献对于考证作者就比较麻烦,因为古书多是不署名的;对于了解作者的情况,更无从谈起。还有第三,具体到不同的发掘内容,对于考据问题,情况也不尽一致。其中有的属于铁证,或曰一锤定音之证。像地下出土的秦代错金甬钟上刻有“乐府”二字,对于论证乐府并非建于汉武帝时代,就是铁证。有的属于模糊论证,像银雀山汉墓出土的首简背面上端刻有“唐革(勒)”二字的简文,对于论证宋玉赋大多并非伪作,就仍还属于推论性质,它只能说明凭着汉初的时间,凭着刻有“唐革(勒)”字样的这篇文(赋)的水平、形式,题为宋玉作的那些赋作已经有可能是宋玉所作,但却不能确定一定是宋玉所作,更不能说这篇简文一定是宋玉所作,毕竟这上面刻着的是唐勒而非宋玉。还有的出土文物对于论证某些问题可以说是铁证,对于论证号一些问题又只能是模糊论证。就以荆门郭店楚简本《老子》而言,它对于论证《老子》非战国后期所作,更非《吕氏春秋》后所作,确是铁证,但对于论证《老子》是春秋末或战国初之作,就还需要借助其他手段,仰仗文献论证。毕竟该墓下葬已在战国中期偏晚的时代。
这说明,无论考古发掘有多大进展,文献考察都是不能丢的。正因为有高亨先生等诸学者通过文献考察得出的老聃作《老子》的结论与考古发掘正相印证,郭店楚简本《老子》对于论证《老子》的作年才由模糊变得清晰;还因为有高亨先生关于老聃生平事迹的发现,我们才能有对考古发掘所没能反映的作者情况的了解。
总之,文献考察与考古发现是相得益彰的,是需要相互印证的,所以是不可偏废的。
收稿日期:2001-05-05
标签:考古论文; 出土文献论文; 国学论文; 庄子论文; 战国策论文; 道德经论文; 孔子论文; 晏子春秋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