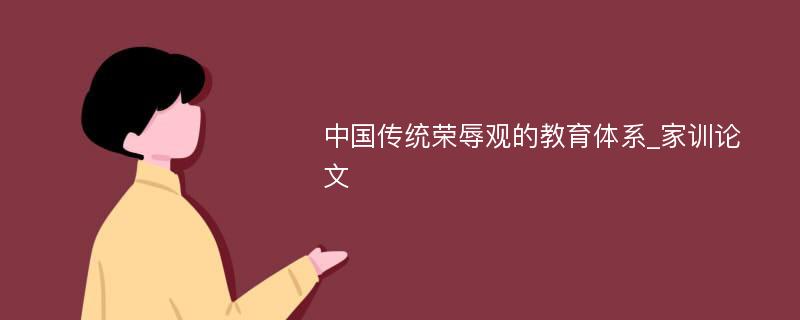
中华传统荣辱观的教化系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论文,荣辱观论文,传统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7)10-0018-05
任何一个民族的荣辱观,都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体现于现实,根植于历史。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一脉相承。作为中华文明内容之一的荣辱观,也是前后相续,环环相扣。今天的荣辱观,既与历史上的荣辱观有所不同,有其时代性、变异性,也有很多相同、相似、相通之处,有其连续性、稳定性。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治乱兴亡,代有不同,中华民族的荣辱观在不同时代的具体表现有所不同,但始终赓续不绝。考其原因,在于历史上荣辱观的教化系统、传承系统的有效性。具体地说,这一教化系统可以分为国家训导系统、榜样示范系统、制度保障系统、日常化育系统、宗教警戒系统。
从国家训导系统来说,中国有君师合一的传统,君主、皇帝多重视教化问题,包括教育君主的接班人(太子之类)、官僚与普通百姓。传说帝舜为天下共主时,他任命东夷族首领皋陶为士,掌治刑法,惩治邪恶,又任命契等八个贤人为官,称为“八元”,让他们推行五教于四方,这五种教化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契等贤人的工作很有成效,结果内平外成,百姓亲和。契推行教化的方法,是将五种教化的要义悬挂在高高的象阙上,让民众来看,并加以解说。这种教化方式被后人称为“契敷五教”。西周的教化更为系统,大司徒将教化内容在王畿内外广为发布,内容包括祭礼、阳礼、阴礼、婚礼等。秦汉时期均设三老职位以负责教化,了解百姓的善恶。以后各代教化系统越来越发达,教化内容越来越具体。
自汉以降,尽管有的朝代崇佛,有的朝代尊道,但儒家荣辱观一直是国家倡导、训育的主流荣辱观,是意识形态的主体部分。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从公元元年(汉平帝元始元年)被封为“褒成宣尼公”以后,历代帝王都褒扬孔子,给予各种各样的封号,封号中用的最多的字是“圣”,包括“先圣”、“玄圣”、“至圣”等,特别强调的是其道德。尊孔就是尊崇儒家荣辱观。历代统治者都提倡忠孝,西汉标榜以孝治天下。朱元璋在执政之初,资助了一场广泛的善书出版运动,洪武三十年,他亲自制订、颁布《教民六谕》,一称《圣谕六言》,要求人民“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转变和道德教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许多家训中都有要子弟家人恪守这六条“圣谕”的内容。高攀龙在家训中写道:人失学不读书者,但守太祖高皇帝圣谕六言,“时时在心上转一过,口中念一过,胜于诵经,自然生长善根,消沉罪过”。姚舜牧在家训中叮嘱家人,“凡人要学好,不必他求”,只要遵守太祖的圣谕即可。①
康熙即位后,提出了“尚德缓刑,化民成俗”的社会教化方针。他拟订了有关齐家治国的《圣谕十六条》,即“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银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其所倡导的道德,包括孝悌、和睦、节俭、守法、热爱劳动、重视教育等方面。雍正对《圣谕十六条》逐条解释,每条六百字左右,形成《圣谕广训》,共一万多字,使《圣谕十六条》更加周详、显明、易懂。有些地方官员为了宣讲需要,编写了《圣谕广训》的解读本,包括直解、注解、广训、衍义、俗解,边远地区的官员还将《圣谕广训》翻译成满、蒙等文本,在少数民族中推行。清朝政府对于灌输《圣谕广训》倡导的道德,有一整套措施,包括乡约宣讲、地方官宣讲、宗族宣传、通过学校与科举考试贯彻。清代的乡约制度,一是宣讲圣谕,二是惩恶扬善。乡设约正、约副为讲解人员,由乡人公举60岁以上,行履无过、德业素著的生员担任,若无生员,即以素有德望、年龄相当的平民担任,每遇朔望,进行宣讲,并将乡人善恶表现,登记簿册,分别奖惩。为了使宣讲取得理想效果,有的地方在约正、约副之下,还特别选择声音洪亮的少年宣读上谕。康熙时有不少讲约的著名官员,于成龙任黄州知府、汤斌在江苏布政使任上都厉行乡约制度。雍正年间将《圣谕广训》颁发各省学政,刊刻印刷,分送各学,朔望宣讲。嘉庆朝倡议义学,要求一乡一里,分别延师,使儿童在一开始接受教育时,就学习《圣谕广训》,受到道德教化。道光时规定,学政到任,将《圣谕广训》刊印,颁行各学生童,令人人诵习。雍正以后将《圣谕广训》列为童生考试内容,要应试童生默写《圣谕广训》部分内容。对于不识字的人,包括妇女、儿童,有些地方官员则编辑《圣谕像解》,用生动的图画、浅显的文字,将《圣谕广训》倡导的道德灌输到从城市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从官员到民众的各类人群。②
从制度保障系统来说,历代教育制度、选官制度、奖惩制度,都将选拔对象的道德品质放在首位,将教育内容、选官标准与维护儒家荣辱观统一起来。
《礼记·王制》曰:“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其实质就是以制度为道德提供保障。
东汉光武中兴,诏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材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公廉之行。[《文献通考》(卷三十九)《选举考十二·辟举》。]所谓“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孝悌公廉”,强调的都是道德。东汉俗尚清议,重视乡评,故至魏晋行九品中正制,亦重德行,强调所用之人要“德充才盛”。中正向朝廷提供的推荐资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世;二是状,即现实表现;三是品,即综合家世、表现而定的等级。所谓表现,就是看德与才。
从隋唐至明清均实行科举取士制度,所考的重要内容是经义,即儒家的经典,同时将学校教育与科举相结合。历代表彰的节妇贞女、忠臣义士、清官循吏,也都是旨在从制度上保障道德教化的有效性。
虽然道德教化是面向全体官民的,但在道德实践中,却有公认的道德楷模,这个楷模就是士绅。
传统中国的国家统治权力只到县级,县以下的权力空间由士绅来承担。所谓士绅,就是有功名、知识、受人尊敬的人。从西周开始,国家就要求当官的既是行政管理者,又是道德实践者、示范者。《周礼·春官·宗伯》载:“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
秦汉以后,历朝对于道德高尚的人都有奖赏,或授予官职,或在其死后立祠祭祀。《后汉书·百官志》记载乡一级政权的职掌:“凡有孝子顺孙、贞女节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三国时,孔融任北海相,对于那里已经去世的德行高尚的人,立祀表率,这是表彰乡贤的肇始。此后,全国各地、各个朝代,不知道表彰过多少忠臣烈士、善人义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不知道立过多少牌坊牌楼,建造牌坊牌楼的资金多由州县官库发给。
建立牌楼属于旌表的范畴。旌表是政府行为,比较正规,有整套程序。与旌表类似而不那么正规的是由政府或民间将匾额给予某个有善行的家庭或个人,以示表彰。这在汉代就有,属于乡一级政权的职掌,以后历代相沿。完颜绍元在《千秋教化》中对这一制度有具体介绍,表彰的对象包括孝子顺孙、贞女节妇、让财救患、家族和睦、兴办教育、热心公益、拒绝贿赂等。1725年(雍正三年)秋,河南巡抚田文镜一次就表彰一百四十余人,包括致仕官员、举人生员、老农乡耆、城镇市民,根据每人情况分别拟定匾书。
明清时代,每逢春季二月和夏季五月,州县衙门各举行一次奖励德行的活动,令各地公举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无愧者一人,上报官府,由州县主官或佐贰向受表彰者敬酒,赐以花红。每逢秋季八月和冬季十一月,各举行一次惩治奸恶的活动,令各地公举不孝不悌、不忠不信、无礼义廉耻者一人,上报县署核准,由官员或训斥,或罚款。[1](p.150)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的士绅,也自觉地担当道德载体、道德卫士的角色。诚如张仲礼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绅士有卫护传统纲常伦纪的职责,他们积极地从事传授和阐明这些纲常伦纪。[2](p.67)
日常化育系统,包括家训、遗规(如《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等)、乡规民约、蒙学课本、小说、唱本、楹联、格言、善书、功过格、民谚、口头禅等,内容相当广泛,研究成果甚多,本文择其要者,作一略述。
中国历史上的家训对化育道德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北齐士族颜之推为了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写下《颜氏家训》二十篇,涉及子孙教育、兄弟相处、勤俭持家、待人接物、谦虚勉学等方面。这部家训在其后的一千多年里广为传诵,影响极大,被推为家训之祖。宋朝司马光、欧阳修、朱熹,明朝王夫之,清朝郑板桥、曾国藩,都留有家训。与家训类似的还有许多形式的家规、家书、教子诗等。雍正年间做过扬州知府等职的张师载,将汉唐以来著名的“型家正俗之篇”编辑成册,题名《课子随笔》,共收八十四篇家训、家规、信札。张师载在序言中指出:风俗之厚薄,不惟其巨,其端恒起于一身一家,所以极为重要。此书在乾隆年间出版,后又多次刊印,广为流传。
家训灌输的重要内容是儒家荣辱观。关于重德,朱熹在《家训》中指出:“有德者虽年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他认为进德修身就如同“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朱熹还重复刘备的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要子孙积善去恶。关于节俭,《朱柏庐治家格言》说:“一粟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一丝一缕,应念物力维艰”,此语传诵广远。有的家训还具体规定了宴会、衣服、嫁娶、丧葬、祭祀等的标准。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强调“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再怎么幸运的家族,都不可能每一世都做大官,何况落拓不羁的世家子最容易败坏先人家业,因此骄奢习气是绝对要不得的。曾国藩也有类似家训,他告诫家人: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故“切不可贪爱奢华”,要求子侄“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关于清廉,多数官宦家训都有此内容,最典型的是包拯嘱告家人:“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关于读书上进,《颜氏家训》写道:“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
诚如颜之推所言,“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父兄的教诲、祖上的遗训,远比朝廷的谕旨、儒生的文章更亲切,更有针对性,更容易入耳入脑。在这些家训、家书、家规中,儒家的礼义廉耻、勤俭、好学、宽厚等美德,被一遍又一遍地强调与重复,成为许多家族的传家美德。
蒙学课本是化育荣辱观的重要载体。传统蒙学课本,如《三字经》、《千家诗》、《小儿语》、《弟子规》、《增广贤文》、《蒙求》、《名贤集》、《二十四孝图》等,都特别强调儿童优良道德品质的养成。
比如《增广贤文》、《名贤集》,教人重义轻利:“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教人和睦相处:“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常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两人一般心,无钱堪买金,一人一般心,有钱难买针”;教人善良:“积善有善报,积恶有恶报”,“劝君莫作亏心事,古往今来放过谁”,“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教人忠恕诚实:“心要忠恕,意要诚实”,“万事劝人休瞒昧,举头三尺有神明”;教人淡泊:“黄金浮在世,白发故人稀,多金非为贵,安乐值钱多”;教人大度:“饶人不是痴,过后得便宜”,“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教人惜时努力:“长江一去无回浪,人老何曾再少年”,“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教人知足安命:“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命好心也好,富贵直到老,命好心不好,中途夭折了,心命都不好,穷苦直到老”。
至于《格言联璧》,几乎全是教人修身养性、知荣免耻的,比如教人正确对待贫富:“贫贱时,眼中不著富贵,他日得志必不骄。富贵时,意中不忘贫贱,一旦退休必不怨。”教人正确对待权势:“君子之事上也,必忠以敬,其接下也,必谦以和。小人之事上也,必谄必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人争求荣乎,就其求之之时,已极人间之辱;人争恃宠乎,就其恃之之时,已极人间之贱”。劝帮助他人:“施必有报者,天地之定理,仁人述之以劝人。施不望报者,圣贤之盛心,君子存之以济世。”教育官员清廉不贪:“居官廉,人以为百姓受福,予以为锡福于子孙者不浅也,曾见有约已裕民者,后代不昌大耶?居官浊,人以为百姓受害,予以为贻害于子孙者不浅也。曾见有瘠众肥家者,历世得久长耶?”
民谚涉及许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关于官场风气、官员品行的评价,因其生动形象,简单易记,极易流传,形成所谓官员口碑,无形中对官员品德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比如《清官雅趣录》所载一钱太守、二不尚书、三汤道台、四知先生、五代清郎③ 等,就是老百姓对清官的赞誉。
至于楹联,内容则更为丰富。《七修类稿》记载:明弘治年间,吏部尚书王恕作官署楹联:“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仕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嘉靖年间,藩司参议钱嶫自撰一联,使所属衙门皆帖,句云:“宽一分民爱一分,见佑鬼神;要一文不值一文,难欺吏卒。”表达的都是拒绝贿赂的意思。近代蔡云万认为,对不同程度的人进行道德教育须用不同方法,教育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因果报应最有效。他举所见到的一副对联说:“教人之法与规友之道,对上等人可讲道德,对中等人须说因果,对下等人只有谈谈报应。各县均建有城隍庙,士民信仰敬畏之心,群认为冥漠中佑善罚恶之唯一主宰,当时确能辅助官治与教育所不及。……曩岁赴淮安府应试,偶游府城隍庙,见有砖刊联语,砌于二门左右墙内,句云:‘为人果有良心,过节逢时何须烧香点烛;作事不循天理,三更半夜谨防我铁缧钢叉。’虽凶恶之徒见之,亦不能不有所儆惕也。”[3](p.153)
历史悠久、名目繁多、数量巨大的道德化育资源,使得儒家荣辱观成为舆论,化为习俗,世代积累,广泛认同,沦肌浃髓,深入人心,成为集体无意识,形成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质。
以宗教警戒系统而论,佛教之轮回说、道教之报应说,在今日的唯物主义者看来,自是无稽之谈,但在警戒作恶、劝人行善方面,却有难以估量的影响。比如,民间流行的道教的《文昌帝君阴骘文》,所说各种报应,诸如救蚁中状元之选,埋蛇享宰相之荣等等,今人看来自是天方夜谭,但其所劝人守的各种美德,劝人行的各种善事、不昧良心事,如矜孤恤寡、敬老怜贫、斗称公平、宽恕奴婢、舍药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烦、点夜灯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济人渡、勿唆人之争讼、勿坏人之名利、勿倚权势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穷困,对他人、对社会都有益无害。
道教的功过格,原为道士逐日登记行为善恶以自勉自省的簿格,后来流行到民间,变成用分数来表示行为善恶程度,使行善戒恶得到具体调节的善书。这类善书列功格、过格两项,用正负数字标示,功格用正数记善行,过格用负数记恶行。奉行者每夜自省,两相对照,给善行打正分,恶行打负分,只记其数,不记其事,月底小计,年底总计,累积之功过,可转入下月或下年。这种功过思想起源很早。《易经》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教认为,天地、灶神、司命等神,会监察人的善恶并给予应得的奖惩。葛洪《抱朴子》中有丰富的功过思想资料,其《对俗》称: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无求玄道无益也,“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当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故善不在大,恶不在小也”。此后经历代发展、演变,至宋代以后形成功过格一类善书。功过格是修行者实践道德的指导书,像店主在账簿上记账一般,故有学者称之为“道德记账法”。
尽管任何教化的功能都是有限的,任何教化的方式也都受到其时代的限制,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传统的道德教化有其相当成功的地方。以上五大系统各有侧重,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国家训导不足则辅之以日常化育,榜样示范不足则辅之以宗教警戒,硬的一手有制度,软的一手有教化,或雷霆万钧,或春风化雨,生前有君亲师,死后有阎罗王。在教化方面,儒、释、道相互补充,诚如清人钱泳所说:“天地能生人而不能教人,因生圣人以教之。圣人之所不能教者,又生释、道以教之。故儒、释、道三教并行不悖,无非教人同归于善而已。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盖圣人之教但能教中人以上之人,释、道不能教也。释、道之教但能教中人以下之人,圣人亦不能教也。”[4](p.601)
纪晓岚有类似的看法,“帝王以刑赏劝人善,圣人以褒贬劝人善,刑赏有所不及、褒贬有所不恤者,则佛以因果劝人善”。鲁迅亦说,儒家的三纲五常,本来不容易说服人,“而佛教轮回说很能吓人,道教炼丹求仙则颇有吸引力,能补孔子之不足”。这样,就形成了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道德教化网。
注释:
①姚舜牧:《药言》,《丛书集成初编》(第333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版,第18页。
②关于《圣谕广训》的研究,参见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常建华:《论〈圣谕广训〉与清代孝治》,《南开史学》1988年第1期。
③一钱太守。后汉刘庞任会稽太守,为官廉明。离任时,当地百姓筹资千钱相赠,刘再三推辞,见百姓长跪不起,盛情难却,只得拿一钱留作纪念。他感叹:“为官之道,舍一分则民多一分赐,取一文则官少值一文钱!”故世人称他为“一钱太守”。二不尚书。明朝工部尚书范景文为官廉洁,不开后门不受礼,在门口张贴“不受瞩,不受馈”六个大字,广为告之。百姓称他“二不尚书”。三汤道台。汤斌任清朝岭北道台,为官多年,两袖清风,生活简朴,老百姓称他为“三汤道台”。三汤,指的是豆腐汤、黄连汤、人参汤,意谓其从政如豆腐汤那样清白,生活如黄连汤那么清苦,对于社会如人参汤般具有滋补益处。四知先生。杨震历任后汉刺史、太守、太常、司徒等职。有一次途经昌邑,县令王窑趁夜色蒙蒙以十金相赠,说:“夜幕之时无人晓。”杨震当即严辞拒绝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王窑只得怏怏而去。杨震拒贿的美德,赢来“四知先生”美誉。五代清郎。袁聿修身经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五个朝代,为官五十余载,但清贫为本,始终如一,从不接受别人馈赠,因此获得“五代清郎”之美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