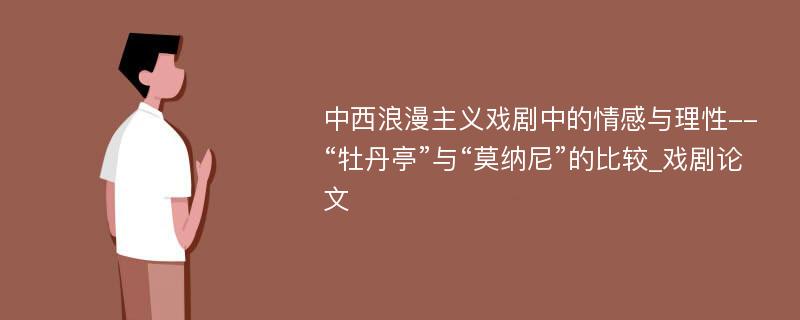
中西浪漫主义戏剧中的情与理——《牡丹亭》与《欧拿尼》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漫主义论文,中西论文,戏剧论文,牡丹亭论文,欧拿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1598年)和19世纪法国雨果的《欧拿尼》(1829年),是中西浪漫主义戏剧的巅峰之作。它们以人性之“情”反对封建主义之“理”,让觉醒了的具有“自我”个性的人,冲决各种阻力,勇往向前。这两部浪漫主义剧作,昭示了新兴社会力量的无穷生命力,有其社会的和戏剧艺术发展的必然性。
一、“情”胜“理”的两种形态
与不同历中阶段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相适应,也受各自戏剧艺术传统的影响,《牡丹亭》和《欧拿尼》在表现情与理的冲突斗争时,体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形态。《牡丹亭》向人们展示梦幻的境界,细腻描绘人物柔婉曲折的心理,以动人心魄见长;《欧拿尼》则直接描写现实中人物尖锐的矛盾冲突,以决绝悲壮的风格取胜。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热烈地讴歌“情”胜于“理”的伟大力量。作者在《牡丹亭记题词》中申明创作主旨道:“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剧中杜丽娘因追求爱情生梦,因梦而病而死,表现了封建礼教对人的摧残。历来的戏曲小说在写“情”时,多安插父母反对、小人使奸作为阻力,但杜丽娘纯粹由于对爱情的渴求而死,其批判的矛头直指“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剧作还以浪漫奇幻的想象表现爱情的巨大力量,杜丽娘终于为情死而复生,并同柳梦梅同结连理。围绕着杜丽娘的生生死死,剧作揭露了晚明社会封建礼法的罪恶,塑造了杜丽娘这个光辉的叛逆形象。
《牡丹亭》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在它问世不久,就出现了“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注:沈德符《顾曲杂言》。)的盛况。《牡丹亭》的艺术魅力,与作者以细腻热情的笔触,深入地描写人物独特的个性心理有关。杜丽娘青春觉醒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喜悦和惊惶、热烈执著和沉重艰难的矛盾历程。她比历史上反抗封建礼教的女性所受到的束缚更严厉沉重得多,她甚至连自己家里的后花园也不能随便踏足流连。因此,当她在游园中观赏到旖旎动人的自然景色,在赞叹、惊喜和入迷的同时,萌发了对爱情的追求,就是很自然的了(《惊梦》)。试看曲子〔步步娇〕:“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此曲景语蕴含情意,把一个长期禁锢闺房、因春光感召而情窦初开的少女的独特心理情态,描摹得生动传神。
杜丽娘在游园中看到春色满园无人问,不由得引发无限感慨和忧伤。她唱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里不单是把景物作强烈的对比,也是人物身世遭遇的鲜明写照。像鲜花那样“姹紫嫣红”的不正是杜丽娘的青春之花吗?但她却被锁闭在不见天日的深宅大院之中。睹景伤情,她发出感叹和责问:天赐如此美好春光景色,有赏心乐事的又有哪一家呢?伤春惜春之情见于言表,深沉感叹中包含对封建礼教和怨恨和控诉。
杜丽娘被无边春光勾起对烂漫多彩生活的向往,沉睡的情在觉醒,接着是梦情人、寻梦境、写花容、入冥府、魂幽媾、返阳世等生死往复的情节,其中无不贯串着“情”字。杜丽娘就是“情”的化身,“情”作为驱动力使她战胜“理”。这一切都是通过现实与幻想两种境界的交融、细腻地刻划人物的情感心理而实现的。
雨果的《欧拿尼》是浪漫主义戏剧彻底战胜古典主义戏剧的奠基之作。它也以情与理冲突的展开构成戏剧情节,但由于结合着具体历史事件中人物的冲突和斗争,使剧作产生一种令人回肠荡气的激情。剧本叙述16世纪西班牙一个贵族出身的强盗为父复仇的故事。主人公欧拿尼本是西班牙贵族,他投身绿林,伺机向国王卡洛斯报杀父之仇。欧拿尼与吕古梅公爵的侄女素儿彼此热恋着,但国王和公爵也觊觎素儿的美色。一个夜晚,国王及其侍从前来劫夺素儿,欧拿尼及时营救了素儿。后来欧拿尼被国王率领的卫队围困在吕古梅家的城堡中,吕古梅遵从不出卖宾客的侠义观念,拒绝交出欧拿尼。为感谢吕古梅的掩护,欧拿尼将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力交给了对方。后来卡洛斯当上了日卫曼帝国的皇帝,恢复了欧拿尼简武安公爵的爵位,并同意他和素儿结婚。新婚之夜,吕古梅吹响了催命的号角,欧拿尼和素儿只得自杀,吕古梅也自戕而死。
欧拿尼和素儿的殉情,也谱写了一曲自由纯真爱情战胜封建主义理性的浪漫主义之歌。由于雨果在创作中贯彻“美丑对照”的原则,使情胜于理的冲突得到更鲜明集中的表现。雨果在著名的《〈克伦威尔〉序》中曾指出:“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注:《雨果论文学》第3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雨果这一论述是针对古典主义戏剧崇尚理性、把帝王贵族作为赞美的描写对象而发的。他认为艺术描写不应排斥生活中平凡粗俗的形象,“自然中的一切在艺术中都应有其地位”。他是想通过对照的原则,使崇高的更加崇高,使优美的益显优美。
在美丑对照中使事物发生碰撞和冲突,必然激发出火花,产生出激情。雨果正是以这种美丑对照的原则,对当时在剧坛仍占有统治地位的理性原则作最后的冲击,最终使高尚的情感压倒并战胜封建主义的理性。《欧拿尼》一剧在情节内容、矛盾冲突和人物性格等方面的对照是很鲜明的。从情节线索所形成的矛盾冲突上看,欧拿尼与素儿之间以生死许诺的纯真爱情,同卡洛斯国王企图利用权力占有美貌少女,以及正向坟墓走去的吕古梅公爵仍厚颜无耻地要同侄女结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在性格上,欧拿尼的高尚豪侠、光明磊落、义无反顾,与国王躲在壁柜偷听、想趁夜晚劫掠素儿的卑劣委琐,以及吕古梅公爵吹响号角置人于死地的狠毒,又是一重对照。
作者还遵从生活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进行人物本身性格的对照。欧拿尼虽然报仇心切,但当国王不愿意决斗时,他却要像贵族那样体面地放走国王。他明知吕古梅是自己的情敌,却把处置自己生命权力的号角交给对方。同样,吕古梅在古堡家里掩护情敌欧拿尼,国王宽容地赦免谋反的贵族并成全欧拿尼与素儿的婚事,都和自己的主导性格形成对照。这种美丑对照原则的运用,多侧面多角度地肯定了真挚美好情感的力量,批判了封建专制之理的荒谬。首先,它使卑贱者、被压迫者的品德情操和精神境界得到肯定和赞美,也使地位显赫的统治阶级在对照中暴露其卑鄙龌龊;其次,对照原则带来剧本情节的错综曲折,起伏跌宕,产生令人回肠荡气的激情效应;最后,美丑对照原则否定了古典主义从“理性”出发的关于人物性格定型化和类型化的理论,并在情感的驱动下驰骋想象,通过人物富有个性特点的斗争行动充分展示性格特点。
《欧拿尼》的激情产生于美丑对照的矛盾冲突之中,《牡丹亭》动人心魄的感情产生于大自然感召下的心理觉醒之中。前者始终贯穿着人物的行动和斗争,后者以细腻的心理刻划见长。《欧拿尼》创作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的王政复辟时期,雨果说:“浪漫主义其真正的定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已。”(注:《雨果论文学》第92页。)他把文学上向古典主义争取创作自由和政治上向复辟王朝争取社会自由联系起来,因而让他的人物为爱情和理想而行动和斗争,直至献出生命。《牡丹亭》创作于晚明时期,当时虽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社会和人性都还处在觉醒的时期,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东西,只好到梦幻境界中去寻觅,并在幻想的过程中实现。中西两大浪漫主义剧作在表现“情”胜“理”斗争时的差异,体现了各自在特定历史阶段反封建斗争的特点。
二、内形式与外形式的纷争
充满激情、崇尚想象、向往自由的浪漫主义文学,不单在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上要反对封建主义之“理”,而且在表现形式上要破除旧形式的种种束缚,以争得反映表现生活时更大的自由。形式规模所体现的创作法则、规范也是一种“理”,这是创作中形式规律之“理”。文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在文学内容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往往随之出现对形式的重大突破。《欧拿尼》的成功上演,冲破了古典主义僵化的内形式的拘束;《牡丹亭》问世以后,也引发汤显祖与沈璟之间关于外形式的争论。浪漫主义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也可看作是情与理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形态。
艺术作品的形式一般可以区分为内形式和外形式。内形式指作品内部的结构方式,和作品的内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文学作品来说,内形式指情节、环境、场面的构思安排,人物关系的处理,及从中体现出来的巧妙独特的组织结构。如欧洲古典主义戏剧对情节、时间、地点的整一性作严格规定的“三一律”,就是一种内形式。外形式则和传达内容的物质媒介直接相关,它在主要诉之于视觉、触觉的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门类中显得特别重要,讲究色彩、线条、形体、质料等物质材料所呈现出来的外形式的美,是这些艺术类型的重要特点。文学的特质媒介是语言,语言艺术主要诉之于欣赏者的想象。因此外形式在文学中的表现不是那么鲜明突出。作为文学的物质媒介的语言,包含有意义和声音两个层面,而文学的外形式就是指语言声音层面所形成的声调、韵律和节奏感的美。
作为中西浪漫主义戏剧代表作的《牡丹亭》和《欧拿尼》,都要求突破繁琐僵硬的形式的束缚,以使情感在宽松自由的条件下得到更充分的表现。这是主情的浪漫主义戏剧的共同特点。但在形式问题上引起争论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牡丹亭》引起外形式的争论,《欧拿尼》则在内形式上有重大的突破。产生差异的原因既耐人寻味,又有深刻的内涵。
17世纪在法国兴起的古典主义是当时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适应政治上巩固专制一统的王权的要求,对文艺从内容到形式都提出了种种规范化的要求。其中“三一律”要求剧本的情节、时间和地点必须完整一致,即每个剧本只能写一个故事,事件始终在一个地点,并于一天内完成。“三一律”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情节整一律”。1545年意大利学者琴提奥提出了“时间整一律”。后来,意大利的卡斯特尔屈维罗又提出“地点整一律”。到了17世纪古典主义时期,法国法兰西学士院负责人沙坡兰和剧评家多比雅克神父,将三个“整一”合在一起,借亚里士多德之名正式提出了“三一律”(注:《雨果论文学》第5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地入古典主义的全盛期,布瓦洛1674年发表了对古典主义理论作全面总结的《诗的艺术》,进一步对“三一律”作出规定:“我们要注艺术地布置着剧情发展;/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注:布瓦洛《诗的艺术》第三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对此,马克思曾指出:“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08页。)
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是崇尚理性原则在艺术形式规律的表现。按照布瓦洛的说法,它能使戏剧创作“永远只凭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注:布瓦洛《诗的艺术》第一章。)无庸讳言,“三一律”如果运用得好,将有利于剧作情节结构的紧凑、集中,但它并不适用于一切题材,也不适用于一切戏剧形式。就整体而言,“三一律”刻板僵硬的规定,限制了戏剧舞台更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扼杀了作家蓬勃的创作生机。当时著名的剧作家高乃依和莫里哀,都为勉强遵守这些规定而深感苦恼。高乃依的《熙德》于1936年上演后受到普遍的欢迎,普希金也说:“我觉得《熙德》是他最好的悲剧”。(注:转引自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233页。)但却因违犯“三一律”而遭到围攻批评。
古典主义戏剧的创作法规对18世纪启蒙戏剧也产生巨大在的影响。像伏尔泰、狄德罗等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作家,毕生都没有完全摆脱古典主义戏剧对他们的影响。伏尔泰一生戏剧创作颇丰,被誉为“伏尔泰就是18世纪的全部悲剧”(注:朗松《法国文学史》第652页,转引自吴岳添《法国文学流派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55页。)。但他所能做的只是用旧瓶装新酒,在“三一律”等古典主义法规的限制下宣传启蒙的思想内容。正因为这样,伏尔泰对莎士比亚表现了既肯定他具有“卓绝的天才”、又贬斥他“断送了英国的戏剧”的矛盾态度。(注:《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第347页。)
浪漫主义的兴起,形成了对古典主义的猛烈批判和冲击。雨果于1927年发表的《〈克伦威尔〉序》被称为浪漫主义的宣言,而1930年《欧拿尼》上演成功,则被看作是浪漫主义戏剧乃至整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胜利。在《〈克伦威尔〉序》中,雨果对“三一律”等僵死戒条的批判是深刻的。他指出,“地点一致”的条规总是使剧情“发生在过道、回廊和前厅这类公式化的场景里”(注:《雨果论文学》第49-52页。),戏剧中的许多行动场面,都只好到后台去进行。而“时间一致”的规定“把剧情勉强纳入24小时之内”,就像“一个鞋匠给大小不同的脚做同样大小的鞋,岂不好笑”。如果两种“一致”同时向戏剧创作提出要求,那就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他说:“关在‘一致’笼子里的,常常是一具枯骨。”(注:《雨果论文学》第49-52页。)从这种认识出发,雨果在《欧拿尼》一剧中彻底突破了“三一律”的束缚,剧情时间远远超过24小时自不待说,地点也随剧情的进展不断变换,五幕剧是五个地点,第四幕的场景甚至跨越西班牙的国境到了普鲁士的夏倍尔城。这种时间、空间上的突破,为剧作家在处理情节、驰骋情感想象、追求理想等方面,提供了更大的自由。
《欧拿尼》以突破“三一律”而在内形式上对古典主义的戒律进行反拨,但《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却和吴江派的沈璟在语言的音韵声律即外形式上发生一场论争,表现了中西浪漫主义戏剧在形式追求上侧重点的不同。
沈璟是著名的戏曲声律理论家,他强调戏曲文辞“合律依腔”的重要性。他说:“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注:沈璟《词隐先生论曲》。)对曲词声腔的音韵格律要求,是适应舞台演唱的需要,也是戏曲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地方。沈璟对这方面的强调是合理的、必要的。但他常常为恪守形式规律而忽视了情感意蕴等内容因素。他曾说:“宁协律而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为中之之巧。”(注:王骥德《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这已有为形式而形式的意味了。汤显祖则较能正确处理情感意蕴与格律声韵之间的关系,他看到了后者对前者的依附关系。首先,他认为“时势”的变化决定歌曲的长短和字句的音节。他说:“上自葛天,下至胡元,皆是歌曲。曲者,句字转声而已。葛天短而胡元长,时势使然。(注:汤显祖《答凌初成》。)”“时势”的变化,决定社会生活、词曲情感内容的变化,最后决定音律的变化。其次,音律的急促舒缓要适应不同地域人们表现感情的需要。他说:“南歌寄节,疏促自然。五言则二,七言则三。变通疏促,殆亦由人。”(注:汤显祖《再答刘子威》。)前者从社会发展的纵向看,后者从不同地域的横向看,都表明格律声韵应从属于情感意蕴的表达。尽管汤显祖说过“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注:汤显祖《答孙俟居》。)之类的过头话,但他在创作实践中并不是按照这种意气用事的话行事,他的矫枉过正的话,传达了浪漫主义情感要求突破声律束缚的迫切愿望。
汤、沈的争论表现了戏曲的情感意蕴要摆脱外形式束缚的抗争,而雨果的《欧拿尼》则直接向扼制情感的内形式发起冲击。是中西戏剧性质、特点的不同所造成的。从戏剧情节的结构看,西方戏剧强调冲突的强烈集中,形成板块连接式的结构,每一幕是一个板块,纵横交织的情节线索以网状的形态挤压在板块之内,使冲突在板块内酝酿生成,并通过板块的连接逐步推向高潮。试看《欧拿尼》的第三幕。故事发生在亚拉岗山区吕古梅公爵家的城堡中,吕古梅的逼迫素儿小姐与他举行婚礼,素儿准备以死殉情。此时欧那尼装扮成过路香客前来借住,欧拿尼与素儿的恋情暴露,引发了欧拿尼与吕古梅的激烈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卡洛斯国王率领卫队追捕欧拿尼也来到城堡,但吕古梅认为保护客人是他的职责,拒绝交出欧拿尼。最后卡洛斯国王把素儿当作人质带走了。在这一幕中,四个人构成的五条冲突线成网状交织在板块里,情节跌宕起伏,冲突尖锐扣人,而这一切全赖内形式对情节组织安排的结构作用。它突出地显示了西方的冲突型的戏剧侧重于对内形式的关注。
中国戏曲是叙事性的戏剧,虽有冲突却不尖锐,有的甚至只有矛盾而无冲突,但叙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却是它的鲜明特点。著名导演焦菊隐说:“咱们戏曲讲究从一开头就连贯到底,不让断气。这一点是咱们戏曲的好处。”又说:“咱们戏曲就是明场交代,什么戏都要明场交代,暗场交代很少。”(注:《焦菊隐戏剧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连贯性和明场交代,使戏曲形成线性叙事的特点。“场”可以有大场、小场、过场、圆场等的区分,以适应明场叙述事件的长短大小的需要,且场数往往很多,如《牡丹亭》就多至55场。这些“场”形成线性的排列,叙述一个有头有尾、体现因果关系、连贯发展的生活故事。与西方戏剧强调冲突的板块艺术相对照,人们称中国戏曲为叙事性的点线艺术。由于中国戏剧在结构情节时有叙事型和冲突型的不同;中国戏曲和叙事体相适应,内形式比较自由;西方戏剧与表现冲突相适应,对内形式有更严谨的要求。
中国戏曲虽然在内形式方面有较大的自由,但在外形式方面却因追求形式美而形成种种规定和限制。由于把音乐舞蹈这些表现性艺术的因素交融于其中,所以中国戏曲有强烈的情感表现的特色。戏曲吸收了音乐舞蹈因素,形成了舞台表演程式的形式美,诸如声腔美、旋律美、姿态美、动作美等等,这些均有利于剧情内容抒情性的表现。这些形式美有其相对独立的欣赏价值,所以戏曲的内容不宜过分复杂,以免影响形式美的表现。而西方的戏剧以比较复杂的生活内容取胜,直接打动观众的就是曲折复杂的情节内容,不宜太过强调形式来限制内容。
标签:戏剧论文; 牡丹亭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杜丽娘论文; 诗的艺术论文; 法国作家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新古典主义论文; 三一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