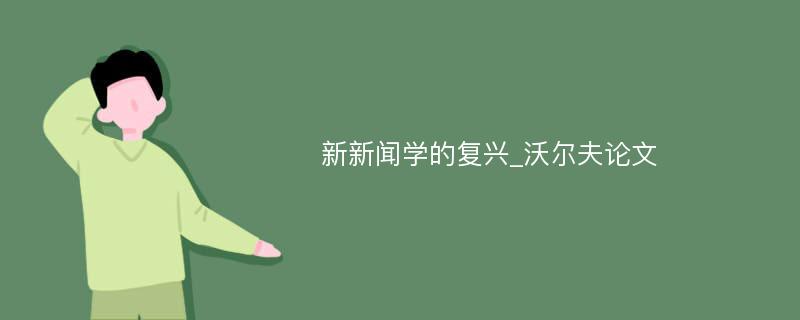
新新闻主义的复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风靡一时的“新新闻主义”曾为批评界所猛烈抨击,一度销声匿迹。然而,到九十年代“新新闻主义”却奇迹般地重新兴起。“新新闻主义”为什么能够卷土重来?围绕着它的复苏,又引发了什么样的争论?刊于《美国新闻评论》杂志1994年10月号的一篇文章对此作了分析。现编译出供读者参考。该文作者查理斯·哈维曾是《华盛顿时报》的记者,现在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任职。
二、三十年前,报章曾公开嘲笑“新新闻主义”的中心人物汤姆·沃尔夫只具有蚂蚁的社会良知,完全不懂新闻还有真实这一说。在当时,谁要是预言“新新闻主义”有朝一日还会卷土重来,一定会被视为有点异想天开。
尽管如此,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象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城报》。
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新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特点:用描写手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
复兴的原因
《巴尔的摩太阳晚报》工作时曾两获普利策奖的琼·弗兰克林,如今是俄勒冈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新闻学教授。他认为“新新闻主义”的复兴是读者兴趣“钟摆效应”的结果。八十年代,以《今日美国》为代表的一派报纸曾试图以“强刺激、大信息量、数字统计”特色吸引读者重新捧起报纸。然而,随着九十年代的到来,读者对“描写手法”的兴趣再度高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1993年的一次研究证实:与许多其他类型的新闻报道样式(包括传统的倒金字塔式)相比,“描写性新闻”可读性更强,甚至传播信息的能力也更强。
波士顿大学的新闻学教授马克·克莱默认为很多新闻报道的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了人情味。例如当劫案发生时,没有报道告诉读者抢劫犯的人品究竟怎样。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新闻学教授诺曼·西姆斯则批评报纸只对反常的丑闻进行报道,而忽视了发生在人们身边的日常生活。他们认为“新新闻主义”复兴是这种读者需求长期未得到满足的结果。
其他媒体的竞争也是“新新闻主义”复兴的重要原因。《俄勒冈人报》的高级编辑杰克·哈特说:“我们的竞争对手都是极难对付的高手。电视、好莱坞电影,如今又多了交互式的电脑游戏。它有主角、挑战者、行动、故事,甚至还有大结局,无怪乎人们玩得无法自拔。”美国报纸联合会的报告最近披露,成人阅读日报的比例已从1970年的78%下降到了1993年的62%。独立撰稿人唐·富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编辑会登载任何能把读者重新吸引回来的东西。
“新新闻主义”也确有吸引读者的地方。与倒金字塔式的新闻不同,它让读者自己在阅读中寻找答案,从而不断给读者带来知识和趣味。波因特学会搞媒介研究的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人一般总是用“描述”去获知、去理解、去记忆、去寻找意义。因而,“描写性新闻”更符合读者的思维习惯。
引起的争论
“新新闻主义”的复兴同时也再次引起了广泛争论,争论焦点仍然集中在消息来源和新闻准确性上。
反对者们认为文学技法有歪曲历史和失去读者信任的潜在危险。他们说,沃尔夫式的“描写性新闻”经常直接写出人物的内心思想,真不知道记者是怎样深入别人的内心的;有时甚至整个会议、场景都能“再现”,也没有任何提示告诉读者它的新闻来源。
“新新闻主义”的支持者也承认“描写性新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技法。他们承认“性格化”是无法证实的,对话也经常是无法证实的,依赖这些东西的“文学性新闻”本身有很多不可知因素。
不过,琼·弗兰克林等人辩解说:采用“描写性新闻”写作的记者们并不见得比采用倒金字塔式写作的记者们更有可能伪造引文或隐瞒事实。事实上,有机会写“描述性新闻”那样长篇作品的往往是一些老资格的记者。他们艰苦奋斗赢得了诚实的名誉,不大可能再去伪造或修饰事实。波士顿大学的马克·克莱默说:“毕竟人们不会因为你采用了‘描写性手法’就视你为英雄。”
支持者们还强调“描写性新闻”的写作要比一般新闻的写作多花两倍、三倍甚至是四倍的时间,因为他们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去核对事实、场景、对话以保证其准确性。《华盛顿邮报》杂志的撰稿人沃特·哈灵顿说:“基本前提是你必须比一般新闻更严格要求自己。一个报道有可能要花上几月或几年的功夫,因为有太多的层次要报道。”《华盛顿邮报》时尚版的撰稿人辛西娅·高妮在撰写一部关于人工流产的书。为了解释一个天主教产科医生的信仰,她将自己沉浸入医生的世界。她和医生进行长时间、多角度的交谈,读他曾读过的一些书,包括他在读大学那个时代的一些道德教科书和一种天主教医生的期刊。高妮是如此投入以至最后简直象是在天主教学校里长大似的。
在“新新闻主义”的新生代中,对技法和标准的要求并非完全一致。《华盛顿邮报》杂志的沃特·哈灵顿认为只有某人亲口告诉过记者他想的是什么,记者才可以写某人在想什么。《纽约时报》的编辑主任小尤金·L ·罗伯茨和独立撰稿人唐·富莱认为记者有时必须在文中向读者提供消息来源。
但其他一些人则在描写人物思想和感觉方面走得更远。《华盛顿邮报》的辛西娅·高妮曾把撰写好的稿件念给医生听,医生指出了与他实际思想有细微差异的几个地方,并说高妮写得基本正确。鲍勃·伍德沃德与斯科特·阿姆斯特朗在他们合作撰写的一本关于最高法院的书《兄弟们》中,曾描写过一个首席大法官的内心思想。他们根本不可能与这个法官有过交谈,又怎能自信地写出他想的是什么呢?伍德沃德说:“这个大法官曾将心里所想的告诉给16个人,我们与其中的15个或16个人进行了交谈,从而得出结论。同时,他的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琼·弗兰克林认为“再现”记者没能亲耳听到的人物对话确实是异常困难的;然而如果能得到当时在场并愿意谈谈情况的几个人的帮助,又掌握一些实用的心理学知识,这并非毫无可能。如果回忆的是结婚、参加父母葬礼等激动人心的时刻,人们也往往可以记起多得惊人的细节。为了保证这种回忆的准确程度,琼·弗兰克林会问采访对象一些他能事后检查的细节,他说:“如果这些细节经核对后是真实的话,我倾向于相信他的其他回忆。否则我就会怀疑。”
然而,对“新新闻主义”新生代的这些作法,《洛杉矶时报》的媒介评论员戴维德·肖表示反对。肖认为仅仅采访知情人中的一部分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谈话发生在私人场景,比如两个在卧室内的谈话,记者就必须和这两个人都交谈过。记者也必须在文中说清楚信息来源,并指明文中的对话仅是对当时情况的回忆。肖还认为记忆也往往是不可靠的。对同一句话,有人只听见表面意思,有人则听出了弦外之音。《纽约时报》的小尤金·L ·罗伯茨则认为报上发表的“创造性非虚构写作”应比在书上发表的同类文章有更严格的标准。因为当读者买一本书时,他知道买的是一本个人作品,书的权威性不会超过这个程度。报纸却被读者视为一个通晓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机构的产品,而且这个机构的信誉也与之紧密相连。
为历史翻案
在为“新新闻主义”的具体技法辩护的同时,也有人为“新新闻主义”的历史翻案。
很多人认为“新新闻主义”由来已久。波因特学会的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以前。他认为汤姆·沃尔夫等六、七十年代的“新新闻主义”者并不是因为在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而出名,而在于他们利用这种手法更自觉也更频繁。麻省大学的诺曼·西姆斯说他可以指出至少两打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本世纪作家,这中间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
对汤姆·沃尔夫的评价也有所不同了。沃尔夫在《新新闻主义》里曾经说到“新新闻主义”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作品中,沃尔夫以小说家的眼光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收入历史,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他以大量采用长段对话、观点和内心独白为快事,他随意动用省略号、分隔号、破折号、感叹号。1972年的一期《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曾因此嘲笑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
然而今天,《纽约时报》的小尤金·L·罗伯茨说, 人们应多注意沃尔夫观察事物的方法,而非学他用标点符号的方法。他认为沃尔夫将一种新的观察问题方法带入新闻界,如今有许多报纸用他们以前从未用过的方法来观察亚文化群,他说:“沃尔夫对此是有功的。”独立撰稿人唐·富莱说:“沃尔夫和‘新新闻主义’者开辟了崭新天地。在他们之前的50年代,报上只有单调的事实。”波因特学会的彼得·克拉克说沃尔夫描绘了他的工作方法,这成了新一代新闻记者的指南。
评论界曾讽刺“新新闻主义”不仅在结构上借用了小说手法,内容也是虚构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1966年的一期曾指责沃尔夫关于《纽约客》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完全失实。曾在《纽约客》任编辑的克莱·富尔克最近说他不认为沃尔夫的这篇文章完全是错误。他说:“文章所以激怒了人们只是因为它描述了一些真相。如果有人不喜欢文章的主题,他就说文章失实。然而历史证明汤姆是正确的。”
1981年,《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杰妮特·库克在她的特写中编造了一个儿童吸毒者的形象,并凭此骗取了普利策奖。丑闻被揭露后,对“新新闻主义”的新一轮攻击随之而来。《洛杉矶时报》的戴维德·肖指责库克掉进了典型的“新新闻主义”陷阱,他说:“库克写得太棒了。她写得如此之棒以至于她忘了自己是个记者,而不是个小说家。”
诺曼·西姆斯最近说:“杰妮特·库克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从未有人称她为‘新新闻主义’者。然而一旦她写了一篇失实的文章,她就突然变成了‘新新闻主义’者。可她的文章中没有‘性格化描写’,没有精致的结构,更没有对话。”她的失实文章用的是标准新闻写法,为什么人们不指责它撒了谎呢?”
对“新新闻主义”最近的攻击则指向《华盛顿邮报》负责调查事务的助理主任编辑、曾在水门事件大出风头的鲍勃·伍德沃德。批评说伍德沃德能深入别人的思想,却从不引用消息来源,从来不说是怎么搞到这些东西的。伍德沃德为自己辩解时说,人们应该知道他是个记者而不是文学撰稿人,所以应该对他的作品保持信赖。这也包括他的书,如《面纱:中情局秘密战》、《最后的日子》、《总统班底》。伍德沃德说他写书时遵循的是与在报道新闻时一样的标准。他指出当书中在某些章节在报上刊载时,他还加入了对技法的说明。在介绍他最近的新书《日程》时, 伍德沃德说为了写这本描写克林顿政府的书他采访了不下250个人。书中所有经“再现”的对话都至少出自一个在场者、一份备忘录或一个在场者的日记或笔记。如果书中说某人在想什么或感觉到什么时,这种描写也得自本人或他曾亲口告诉过的某个人。所省略的只是这是谁说的,在谁的日记,在哪本备忘录里。
发展的趋势
尽管引起争议,“新新闻主义”的复兴势头却仍在发展:
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如今有一个“创造性写作”计划,1994年秋天将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
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如今正试图办一份新闻杂志。执行制造人克雷格·李克说他将会采用一些“新新闻主义”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
1994年1月,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会在佛罗里达举行, 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
波特兰市的《俄勒冈人报》在报社内部刊物中详细介绍了“描写性新闻”的技法。
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新闻编辑主任汤姆·麦克纳马拉介绍说,《今日美国》上的文章平均长度已从1982年9月创刊时的14 英寸到了今天的15英寸,25—30英寸的文章并不鲜见,50—60英寸的特长文也出现过。《今日美国》甚至还登载过第一人称的文章。
很多记者认为由汤姆·沃尔夫推进的“描写性手法”将来会是报纸上的一种式样,但只是一种而已。将来的报纸上会有更多样化的新闻式样和篇幅,这全得看哪种式样和篇幅更适合新闻报道的需要。简短的倒金字塔样式对那些时限紧的新闻仍然是需要的。《纽约时报》的小尤金·L·罗伯茨说:“倒金字塔式新闻仍然会是报上的一种样式, 但不应再是全部。八十年代我们曾因试图将《今日美国》的新闻风格搬入所有的版面而面临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