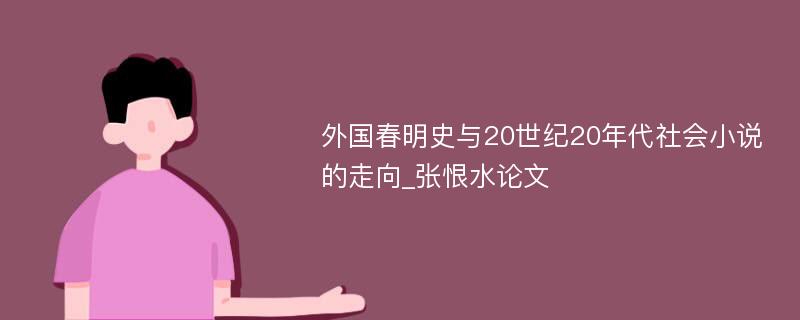
《春明外史》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社会小说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史论文,二十世纪论文,社会论文,春明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5)04-042-08
在张恨水的众多小说作品中,名气最大、影响最广的三部长篇应该说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春明外史》是张恨水的成名作,发表的当年在读者中引起轰动,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据张恨水子女回忆,这部作品也是作者自己最偏爱的。然而,只要读过张恨水作品的读者都知道,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春明外史》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是根本无法与《啼笑因缘》和《金粉世家》相比的,无论是小说的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文学描写的手法。这三部小说中,笔者认为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啼笑因缘》,女主角的形象刻画颇有深度,风格上也非常接近新文学作品。《金粉世家》有“民国红楼梦”之称,不论在题材、结构还是人物没置上,处处都有学习《红楼梦》的痕迹,也算得上一部优秀的小说。而《春明外史》却完全不同。首先,小说根本没有统一的结构,人物来来去去,除了两三个主人公之外,其他众多人物都像走马灯一般,随时出现,又随时消失。就如鲁迅评价《儒林外史》所说,“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1](P221)小说中占大半的人物和故事,都和主人公的生活没有任何联系。除了杨杏园和李冬青这对男女主人公之外,其他的人物都谈不正性格表现和塑造。那么这部小说在当时能够风靡一时,而且还始终得到作者本人的偏爱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随着笔者对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新旧文学交替的文学环境的了解,随着对当时的社会小说潮流的背景以及对作者张恨水的文学背景等多方面的逐步了解,逐渐得到了解答。这个问题应该分两个步骤来回答:一,这部小说当时为什么吸引了那么多读者,获得了那么大的名气;二,作者自己为何特别喜爱这部小说。
首先应该从社会小说的发展谈起。自晚清开始,随着梁启超等人所提倡的“新小说”运动的兴起,小说类型划分法开始出现。“科学小说”、“政治小说”、“社会小说”以及“侦探小说”等名字开始广泛流行。自1902年《新小说》创刊,在小说的目录前,开始加上类型的标签,比如1903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样描写社会现状的小说,标题旁边就写着“社会小说”。但是这个名字在当时众多的小说类型中并不突出。直到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当言情小说、黑幕小说的浪潮滚滚而来,社会小说的浪潮也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起来。1919年李涵秋完成《广陵潮》到1924年张恨水开始写《春明外史》这段时间,正是社会小说最为繁荣的时期。《广陵潮》的出现,引发了一大批以“潮”命名的小说,如《歇浦潮》、《人海潮》等等,都是社会小说,但是其中多少都有些言情的情节,所以也可以称为社会言情小说。这些小说在当时大量涌现,非常受读者欢迎,当时几乎所有的小报上,都在连载社会小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都市社会成长起来的张爱玲,还能记得当时社会小说的盛况,而且她自己和家人亲友,也多半都是这些小报和小说的热心读者。
社会小说的广泛流行,有着作者和读者两方面的原因。从小说家这边来说,从晚清开始的社会小说创作,发展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成了非常大的一股潮流,有着相当可观的作者队伍、发表阵地,并已形成传统。从读者方面来说,自从晚清的新小说运动以来,随着小说的地位向文学的中心位置转移,随着小说报刊的繁荣,培养了相当一大批热衷于阅读小说的读者。二十年代的这批读者,正是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些小说开始培养起来的。这些社会小说,以实录为特点,广泛记载社会现象,搜罗各种社会奇闻,养成了一大批以“新奇”为趣味的读者。本来,在中国的传统文学观中,小说就是一种消闲的文体,在二十年代,除了一部分具有启蒙思想的新文学家和新文化拥护者之外,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仍然是抱着传统的小说观。新文化阵营的知识分子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大量的批判。1923年陈望道就曾以“晓风”的笔名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著文批判:
近见各家书店的小说广告,依然把“情节离奇”四字做他“不可不看”的证据。大约文学革命闹了这几年,一般人还同先前一样,爱看所谓“情节”的壳子,爱看所谓“出乎意表之外”的“离奇”的壳子;这就难怪一班最乖的小新闻编辑,每晚死命地找那“情节离奇”的“趣事”,赚取了几个一笑卖给读者们了。我们的知识原来告诉我们:小说重在描出“情状”,不重叙些“情节”;重在“情状真切”,不重“情节离奇”,情节只是壳子罢了,取譬荔枝,情节就像荔枝的壳,情状才是荔枝的肉。而因文艺植根于真,故亦不贵乎离奇,而重在真切。现在他们对于这以真切为生命的文艺也还要求着离奇,那真难怪那些卖笑的小新闻死找些离奇的趣事来充篇幅了。但我颇疑问小说的读者倘爱“情节”又爱“离奇”,那又何不简直多找些小新闻来看呢?[2]
事实上,一般读者就是把社会小说当小新闻来看的。张爱玲就曾经说过,她喜欢看社会小说,并不是为了艺术,而是读一点有趣的新鲜的事实,把社会小说当成社会纪实文学来看的。所以当时的社会小说,多数都有很强的新闻化的特点。而社会小说的很多作者,同时也具有报人的身份,这是一个传统,如晚清社会小说的作者李伯元、吴趼人等,本身就都是报刊工作者,本身兼具报人和小说家两种身份,而这两种身份,又是彼此密切相关的。这个传统,张恨水也继承了下来。他在整个民国时期,都始终是兼具这两种身份的。作为报人,有机会广泛接触各种社会生活和人物,并得到许多新闻和内幕。在二十世纪初的一、二十年内,“黑幕小说”的流行,也是社会小说的一大特点。一般人喜欢阅读社会小说,喜欢它们提供的各种社会新闻趣事,但并不是任何方面的社会生活都是他们所喜爱和关心的,一般人所喜爱的,都是名流政客或名伶、名妓或姨太太等人的内幕,至于一般工农大众的生活,则少人关心。这种黑幕流行的风气,新文学阵营曾经对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18年9月《东方杂志》第15卷第9号,载《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小说家勿再编写黑幕一类小说函稿》。文中说:“近时黑幕一类之小说,此行彼效,日盛月增。核其内容,无非造作暧昧之事实,揭橥欺诈之行为。名为托讽,实违本旨。况复辞多附会,有乖写实之义;语涉猥亵,不免诲淫之讥。此类之书,流布社会,将使儇薄者视诈骗为常事,谨愿者视人类如恶魔。”罗家伦在《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中,也指斥黑幕小说的恶劣风气:“这一种风气,在前清末年已经有一点萌孽。待民国四年上海《时事新报》征求《中国黑幕》之后,此风遂以大开。现在变本加厉,几乎弥漫全国小说界的统治区域了!推求近来黑幕小说发达的原因,最重要的有两个。第一是因为近十几年来政局不好,官僚异常腐败。一般恨他们的人,故意把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庭,描写得淋漓尽致,以抒作者心中的愤懑。当年《孽海花》一类的小说是这类的代表;不过还略好一点,不同近日的黑幕小说的胡闹罢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近来时势不定,高下二等游民太多。那高等多出身寒素,一旦得志,恣意荒淫。等到一下台,想起从前从事的淫乐,不胜感慨。于无聊之中,或是把从前‘勾心斗角’的事情写出来做小说,来教会他人(上海确有这种人);或者转看这种小说,以味余甘,——所谓‘虽不得肉过屠门而大嚼’的便是。那下等游民,因为生计维艰,天天在定谋设计,现在有了这种阴谋诡计的教科书,为什么还不看呢?从这两个大原因,于是发生出许多的黑幕小说来。诸位一看报纸就知道新出的《中国黑幕大观》《上海黑幕》《上海妇女孽镜台》等不下百数十种。《官场现形记》《留东外史》也是这一类的。里面所载的,都是:‘某某之风流案’‘某小姐某姨太之秘密史’‘某女拆白党之艳质’‘某处之私娼’‘某处盗案之巧’等等不胜枚举。征求的人,杜撰的人,莫不借了‘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招牌,来实行他们骗取金钱教人为恶的主义。诸君!世上淫盗之事,谁不知道是不好的?何必等这类著小说的人来说一遍?”[3]
就是在旧派通俗小说阵营内部,他们自己也承认,包天笑在1918年7月1日《小说画报》第14期发表的《黑幕》这篇小说中,借人物之口说:“现在除非是黑幕的稿子才收,其他一概不收。……世界上事事物物哪一样没有黑幕,中国的黑幕更多,中国的上海的黑幕更加多。……上海的黑幕人家最喜欢看的是赌场里的黑幕,烟窟里的黑幕,堂子里的黑幕,姨太太的黑幕,拆白党的黑幕,台基上的黑幕,还有小姐妹咧,男堂子咧,咸肉庄咧,磨镜党咧。说也说不尽……”
从上面正反两个阵营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是当时黑幕小说的广泛流行,如罗家伦所说,“几乎弥漫全国小说界的统治区域了”。说明黑幕小说很受欢迎,很有市场。二,在罗家伦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孽海花》和《官场现形记》也被划进黑幕的范围。这正是我要说的:几乎所有的社会小说都具有几分黑幕的性质。黑幕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就是社会小说的近义词。仔细看来,不论是《广陵潮》、《歇浦潮》,还是《人海潮》、《春明外史》,任何一本社会小说,哪一本里没写姨太太、妓院、私娼、烟窟?哪一本里没写男女“调膀子”、拆白党?这几乎是他们通行的题材,也是他们共有的资源。
《春明外史》里面,就有很多可供人猜测的材料,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笑鸿在《春明外史》重版代序里说:
说来已是半个世纪以上的事了。《春明外史》在《世界晚报》连载不久,就引起轰动。我们亲眼见到每天下午报社门口挤着许多人,等着买报。他们是想通过报纸的新闻来关心国家大事么?不!那时报上的新闻受到极大的钳制,许多新闻是无中生有,涛张为幻,而副刊有时倒可能替老百姓说几句话,喊叫喊叫。尤其是小说,有人物,有故事,往往能从中推测出不少政局内幕来。有时上层人物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社会上都传遍了,可是从不见诸新闻。而小说却能影影绰绰地把这些人和事都透露出来,使人一看,便心领神会。于是小说便成了“野史”,所谓“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读着带劲,细按起来更是其味无穷。当然,并非所有报上的小说都是如此,不过恨水的《春明外史》确是这样。小说情节是虚构的,可并非完全出于幻想,作为“野史”的小说更不是毫无根据的胡诌。……
《春明外史》中的很多故事,够上年纪的人一读就能联想到当时的社会。不过,考证也考不完,索隐也索不了,时间久了,连我这当年最年轻的“小兄弟”都过了八十岁了,如果按图索骥,“春明旧梦已模糊,今日惟存此一珠”,那可无法一一交待。不管怎么说,这部小说的确是“野史”,而并非只谈男女关系等等。其所以能够流传久远,道理即在此。
这段话把《春明外史》受到欢迎的原因交代的很清楚。排队等着看小说的小市民们,他们所要看的,就是小说里“影影绰绰”的透漏出来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能够从小说里“推测”出来的那些“政局内幕”。就是这些,使当时的读者们“读着带劲,细按起来更是其味无穷”。张恨水做了多年的记者,他对各种消息、秘闻确实掌握很多。从他的《春明外史》看得出来,是考虑了读者口味的,各种当时社会小说流行的题材要素,他小说里一样都不少,除了南北通行的姨太太、拆白党、堂子私娼、赌场之外,还有北方京城特有的遗老名士,名公巨卿,以及这些人所捧的坤伶、小旦等等,实在是非常丰富。所以说,《春明外史》当时的轰动,是因为它投合了当时流行的阅读口味。流行的特点,就是具有特定的时效性。所以,当社会小说的潮流过去之后,《春明外史》也就不再有当年的风光了。
第二个问题,张恨水自己为什么特别偏爱《春明外史》。我认为,除了这部作者给他带来了声誉之外,最大的原因,就在于这部小说里面,有着作者本人很多的寄托。张恨水曾经说过,他自己早年是个十足的礼拜六的胚子,他迷恋风花雪月的旧小说,迷恋《花月痕》式的才子气的小说。在二十五六岁上,他还迷上了词章,吟风弄月,写诗填词。当1924年,张恨水开始写《春明外史》的时候,他还是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人,正是他自身具有浓厚的名士气才子气的时期。他写《春明外史》,不同于后来的很多小说,往往是出于应付稿债或者出于金钱目的的功利之作。这是他初次写长篇小说,具有尝试性质,功利色彩不浓,他是凭着兴趣来写的。这部作品继承了《花月痕》那种以诗词炫耀才学的传统,同时也继承了那种怀才不遇的名士气和浓重的伤感气氛。应该说,这是包含作者自己的本来性情、气质最多的一部小说。《春明外史》中很多地方,尤其是恋爱的情节和诗词唱和,充分地表达了作者自己的名士气和伤感的气质。作者自己是个“礼拜六的胚子”,而小说的主人公杨杏园,也同样是个礼拜六的胚子。所谓“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第一回的开头,就介绍他有许多的号,绿柳词人、沧海客、困庐等等,这是典型的鸳鸯蝴蝶派旧文人的习气。主人公杨杏园这个形象的塑造,其中有着浓厚的作者自况的意味。另外,据说这部小说中还包含了作者自己的爱情经历。“我们仅仅知道,张恨水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曾经隐隐约约地提到他到北京后曾经有过两次不成功的恋爱,它们后来都经过了艺术加工,写进《春明外史》,成为杨杏园与梨云和李冬青的两次恋爱。”[4]也有当时的读者认为主人公杨杏园就是作者张恨水自己。为此张恨水还认真的反驳过,其中的一条反驳理由,就是小说里杨杏园死掉了,而他还好好活着。说杨杏园就是张恨水,自然是不确切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作者与杨杏阅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主人公身上确实有着作者的影子。比如他们都是安徽人,都出身于败落的旧家。都是孤身做客京都,都是新闻记者,都爱写诗,也写小说,等等。至于气质上,也是非常相似的。都有一种旧文人的诗酒风流、伤感多愁的气质。同时,张恨水也不止一次说过,这部小说每一章的回目,都是他精心撰制的,其中包含了他无数的心血,务求所有回目既工整切题,又华丽典雅,这也是作者引以自傲的。所以,张恨水对《春明外史》具有深厚的感情和偏爱,山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春明外史》算不上是出色的作品,然而却是一部有特点的小说。不论在张恨水个人的创作中,还是从民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历程上来说,都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还是应该重点分析一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春明外史》和《广陵潮》是十分相似的。首先,它们都是捏合了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两种成分而成的社会言情小说。从结构上来说,都是以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为线索,串起许多社会小说的内容。这种结构,是从晚清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继承来的。把主人公作为一个串线人物,同时给主人公安排了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作为小说的主线。其实,小说中的很多情节、人物和故事,与主人公完全是彼此游离的。
但是,《春明外史》又有自己独特的特点。首先,从言情的路径来讲,这两部小说就完全不一样,虽然,主人公的恋爱对象,都是一为妓女,二为闺秀派的佳人。《春明外史》的言情情节,分为前后两段,由主人公的两次不幸的爱情故事组成。而《广陵潮》则是一个多妻主义的主人公同时与几个女子的婚恋纠葛。同时,《春明外史》的言情故事,受到《花月痕》的相当大的影响。从小说的言情部分来说,主人公杨杏园与妓女梨云的一段悲惨动人的感情故事,几乎就是《花月痕》中韦痴珠与妓女秋痕的悲剧故事的翻版。小说的前23回,描写了孤身客居北京的诗人、记者杨杏园,是个清高孤傲的名士才子,偶然的机会被同事拉去北京的胡同(妓院)游玩,认识了妓女梨云。梨云活泼天真,小鸟依人,在杨杏园眼里,丝毫没有青楼中人的习气,一缕情丝由此萌生。梨云对杨杏园也是一往情深。两个人之间,产生了一段非常真挚缠绵的感情。然而,梨云毕竟不是自由身,她的鸨母因为杨杏园的清寒,暗中不允许梨云和他交往。每次杨杏园去看梨云,她不但在一边虎视眈眈的监视着,而且总是旁敲侧打,向杨杏园要钱。因为鸨母的暗中干涉,使他俩产生了不少的误会,彼此都很痛苦。至于替梨云赎身,对杨杏园来说,那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贪婪的鸨母把梨云视为奇货可居,其代价是杨杏园一介寒士绝对无法筹措的。在这种无望的痛苦感情中,两个人备受煎熬。最后梨云郁郁成疾,香消玉殒。杨杏园伤心欲狂,大病一场,身心都受到巨大创伤。
在小说中,主人公杨杏园也几次引韦痴珠的诗句以自比,确实,杨杏园的超人的才华,漂泊的身世,落拓的名士气质,都与韦痴珠非常相似。同时,他与梨云的一段遇合,彼此的缠绵痴情与悲剧的结局,也是与韦痴珠、秋痕几乎完全一致,甚至连悲剧的原因都是相同的,都是因为男主角的经济困难,而虽然所恋的青楼女子痴恋对方,但是鸨母却十分凶狠贪婪,遂使有情人无法终成眷属,酿成悲剧。主人公最后惨死的结局也是相似的。作者张恨水当时十分沉醉于《花月痕》,在这部《春明外史》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以张恨水本人的缠绵悱恻的名士气和诗歌才华,他把杨杏园和梨云的一段恋爱故事描写得非常哀艳动人。这给小说增添了不少的文学性质和风雅的气质。
后半段,在梨云死后,杨杏园又经历了一次恋爱。这次的恋爱对象是一个才女。这段爱情故事,既有传统的才子佳人的性质,又是写实的,描写了在五四运动后的北京,半新不旧的过渡时代的两个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对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心理,颇有细致的反映。从23回开始,杨杏园在同事家中,遇到女主人公李冬青,展开了小说后半部分的言情线索。作者对这一段恋爱的描写,是很用心的。虽然是才子佳人色彩的恋爱,但是,作者抛弃了常见的“一见钟情、郎才女貌”的俗套写法,而是详细描写了两个人慢慢的相遇、相知,互相了解、互相吸引的恋爱过程,比起当时一般的社会言情小说,要精彩得多。作者先从杨杏园无意中得到李冬青失落的藏书中读到了李冬青的诗词写起,引出了一段文字因缘。经过一两次偶然的相遇,杨杏园知道了李冬青就是那本书中夹着的诗词的作者,而李冬青也知道了杨杏园就是她素所敬佩的著名诗人。原来他们在见面之前,彼此都已经拜读过对方的作品并大为赞许。可以说,他们的文字因缘在他们相遇前就已经结下了。随着交往的进一步加深,他们对彼此的了解和倾慕也在逐步加深。他们好像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己一样,灵魂的契合达到了非常深刻的程度。然而,当杨杏园向李冬青表达自己的感情时,李冬青却一再地拒绝了。杨杏园又一次受到失恋的痛苦。原来李冬青生来就有暗疾,无法成家。所以,她把自己的一个女友史科莲,介绍给杨杏园,希望史科莲能够代替她,给杨杏园以幸福。但杨杏园钟情于她,无法移情,史科莲知道杨与李彼此的感情,不愿意介人他们之间,并且毅然离开他们,只身前往上海。继梨云之后,杨杏园又一次受到毁灭性打击,他的病弱的身心终于崩溃,一病不起。终于象《花月痕》中的韦痴珠一样,为情而殉,结束了短暂而飘零痛苦的一生。
在这段爱情故事中,男女主人公多数是通过诗词唱和来交流的。这表现了主人公的才子气,也反映了这个恋爱故事的才子佳人色彩。但是,故事的结尾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最后的“李代桃僵”的情节,与《玉梨魂》的情节如出一辙。应该说,作为民初言情小说鼻祖的《玉梨魂》,对后来的社会言情小说的影响,是十分深远而且明显的。这个恋爱故事最好的部分,就是开始的时候他们慢慢交往、互相了解,并且互赠诗词的那个阶段。那个阶段非常美好温馨,是作者理想中的恋爱。女主人公李冬青,是张恨水理想中的女子,是他为主人公杨杏园塑造出来的另一个自我,是一个女性的杨杏园。“无疑,品貌出众而又富于才华,带有一点旧式女子风度,又能与杨杏园互相唱和的李冬青最符合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佳人’形象,使杨杏园式的‘才子’为之倾倒。”[4]但是,张恨水所描写的这一对“才子佳人”的恋爱,完全超越了民初“礼拜六派”的小说那种“某生,一日遇某女,惊为天人”的模式,而是采取了更为写实的方式。他们是在多次交往中逐渐的开始彼此倾慕的。如小说中描写他们在朋友家门口第一次见面时,杨杏园只是感觉这个女郎很素雅文静。第二次见面,有了进一步交谈,“这一次会晤,给了杨杏园一个很大的印象。他觉得这位女士,于幽娴贞静之中,落落大方,蔼然可亲,绝没有小家子气象,却是在少年场中少遇的人物,很是佩服。”同时,小说中所塑造的李冬青这个形象,又绝不仅仅是封建时代的“佳人”的翻版,作为一个二十世纪的才子张恨水心目中的理想淑女,李冬青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她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立自强、奋发不息的独立坚强的性格,而不是古典佳人们那种多病多愁。她曾经发表议论,认为在这个时代,说谁是“林黛玉”,并不算是正面评价,像林黛玉、杜丽娘那样整天吃了饭不做事,只会唉声叹气是非常无聊的。因而她不但自己能独立,而且还负担着奉养母亲和照顾弟弟的责任,完全靠自己的工作。这样的现代“佳人”,也许是与现代才子杨杏园们的身份有关。杨杏园既不是贾宝玉,也不是张君瑞或者柳梦梅,既没有豪华的家世,也没有中状元的可能,所以,即使世上还有“林黛玉”或“杜丽娘”,那也绝对不是杨杏园们的理想对象。杨杏园理想中的佳人,就应该像李冬青这样,既有平民色彩,而且还有经济自立的能力。至于梨云,是那种“小鸟依人”、“我见犹怜”的类型,可供士大夫赏玩,是杨杏园这样的旧文人才子们的另一种理想,所谓“红袖添香夜读书”。对旧式的才子来说,与妓女发生爱情,不但不是不名誉的事情,反而是一种“韵事”,是士大夫的“诗酒风流”。发生在杨杏园身上,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一部《广陵潮》式的社会言情小说,《春明外史》在言情方面有着自己的特点,有关主人公爱情的情节确实也是全书中最打动人的部分。应该说这部小说作为言情小说是成功的。不足之处就是小说后半段写杨杏园与李冬青的恋爱,在最后的几十回里,显得过于分散,断断续续不够集中。作者用大量的远远超过主人公所占的篇幅来叙述不相关的别人的故事,社会小说的成分大大冲淡了言情的成分,使这个言情故事的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
同样,这部小说作为社会言情小说,它的社会小说的性质表达得也相当充分,它也是一部成功的社会小说。“外史”这个名字,本来就是典型的社会小说的名字。作者为了吸引读者,才加进了主人公的恋爱故事,所以张恨水的朋友称他拿恋爱故事来绕人,是个好办法。所以这部小说的重点仍然在揭露社会弊端方面:
它犹如一架广角镜,对着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社会各个层次各种侧面,一一加以扫描。……上至总统、总理、国会议员,下至妓院、游艺园、跳舞场,无论是官场、军界,还是教育界、新闻界、戏剧界,三教九流,在小说中都有所反映。作品包容的社会面是如此之广,描写的又是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这在当时小说中还是十分少见的。……张恨水混在新闻界里几年,看了也听了不少社会情况,新闻的幕后还有新闻。达官贵人的政治活动,经济伎俩,艳闻趣事也是很多的。这使《春明外史》具有近代‘社会小说’的两个特点:一是人物大多可以索引,不难一一考出他们的原型;一是小说带有较强的新闻色彩。
仅据笔者粗略考证,就可指出小说中下列人物的原型:时文彦(徐志摩)、胡晓梅(陆小曼)、任放(王赓)、鲁大易、关孟纲(张宗昌)、魏极峰(曹锟)、姚慕唐(张敬尧)、姚慕虞(张敬舜)、姚慕商(张敬禹)、姚慕周(张敬汤)、余兰痕(徐枕亚)、黎殿选(刘春霖)、杨毅汉(杨宇霆)、曹祖武(杨度)、乌天云(禇玉璞)、王泰石(李景林)、苏清叔(吴景廉)、庞爱山(彭允彝)、舒九成(成舍我)、章学孟(张绍曾)、秦彦礼(李彦青)、闵克玉(王克敏)、韩幼楼(张学良)、胡春航(张弧)、金善予(王敏芝)、陈伯儒(高凌凌)、何达(胡适)、谢碧霞(碧容露)、小翠芬(小翠花)、周西坡(樊增祥)、金士章(章士钊)等等。不仅人物,就是事件也大都有着原型。[4]
所以说,《春明外史》就它的反映社会来说,是一部相当典型的包罗万象的社会小说。我们今天的人回头来看《春明外史》,不仅可以通过小说了解当时的政局、风俗等等,还可以通过张恨水的描写,了解新旧过渡时代人们的社会和文化心理。
当时的社会小说家,强调社会小说反映社会的功能,常以“镜子”自命。但是,这面镜子和普通的镜子不同,它是经过于作者主观意识的折射,然后反映出来的。《春明外史》看上去是“有闻必录”的新闻化、纪实化的写作,但是从中却仍然折射出作者的主观意识。比如,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有一种模式化的特点。如小说中出现的坤伶,表面上和捧角的人很亲密地应酬着,但毫无真情,都是专门敲竹杠的。小说中出现的妓女,倒大多是有情有义的。官僚政客、国会议员都是荒淫腐败的。还有很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小说中出现的新派人物,几乎都是反面的,至少也是作者讽刺的对象。大学生被描写成“拆白党”,骗有钱的姨太太的钱。作者借人物之口说:“这一班青年猎艳家,和窑子里的妓女一样,外面风流儒雅,见了妇女十二分温存体贴,实在他的心比毒蛇还恶……”演文明戏的演员和学生,骗到钱就去逛妓院。他们所演出的话剧,名字都叫做“一只狗”、“老妈子的恋爱”、“倒粪夫的婚姻”等等,十分夸张地表达了作者的讽刺态度。
从小说中所描写的恋爱故事更可以看出作者的态度。小说中除了主人公的前后两段恋爱之外,还描写了许多次要人物的恋爱事件。这些人物,多半都是新派的人物。如小说中的“爱美戏剧学校”里的几对恋人。有陈国英与陆无涯的师生恋,双方都有配偶,他们恋爱并且怀孕,惹起一场丑闻风波,并波及学校的名誉。有女学生贪慕虚荣,抛弃穷情人,嫁给有钱有势的姐夫。还有思想激进的女学生,同时是妇女运动积极分子的厉白女士,却宣称嫁人的宗旨是“第一要他有钱”。作者描写这些男女大学生的恋爱,充满了肉欲和金钱的气息。厉白在被男友抛弃之后,想道:“他虽然用了我几个钱,他也小小心心陪着我住了许多天,我也不上当。”这些新人物的恋爱,和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的恋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旧式人物的恋爱,冰清玉洁,可歌可泣,一边是新人物的恋爱,猥亵不堪。最典型的是小说中时文彦、胡晓梅的恋爱故事,影射生活中的徐志摩、陆小曼的故事,何达影射胡适:
她这里刚坐下去,头一个何达博士掀帘子进来了,嘴上一撮小胡子,笑着都会活动起来。他就在胡晓梅下手椅子上坐了,笑嘻嘻地叫了一声“密斯胡”。第二个就是李如泉先生,第三个就是赵维新先生,第四个就是汪爱波先生,第五个章如何先生,第六个就是关增福先生,都进来了,都笑嘻嘻地叫了一声“密斯胡”。胡晓梅在家里是一肚皮的气,如今看见许多翩翩少年围着她,心花怒放,什么忧愁也忘了。这些人越发凑趣,这个请胡晓梅按钢琴,那个请胡晓梅唱英文歌,后来还是胡晓梅自己决定了,唱一段昆曲《尼姑思凡》。她这样一说,大家都鼓掌,说这是想不到的事。何达先生的博士资格,也牺牲了,当起临时听差来,连忙就倒了一杯茶给胡晓梅润嗓子。又不辞辛苦的要去请教昆曲的来吹笛子。李如泉拦住道:“不!不!我们在这儿玩,用不着他,我来吹,我来吹。”胡晓梅也道:“何先生你别忙,就让密斯脱李吹笛子罢。”何达一时高兴,不料倒碰了这样一个橡皮钉子,只得勉强露着干笑,坐在一边……
偏是这样巧,胡晓梅去了没有五分钟,时文彦就来了。他一进来,就到小客厅里去。这屋的前后两边门,都垂着帘子,空气不很十分流通。他坐在绿色的沙发椅上,靠着鸭绒的椅垫,忽然闻见一种香味。他仔细一闻,不是檀香,不是麝香,不是花香,却是美人身上的脂粉香。时文彦是一个谈爱情的人,又是一个新式风花雪月的诗家,这种香味一触到他鼻子里去,他还有个什么不明白的道理?他料定胡晓梅一定到这里来了,这种香味,就是她身上落下来的香气,还未散尽。旧诗上不是说得有“重帘不卷留香久”吗?这时何达先生进来了,他看见时文彦一人坐在这里发呆,问道:“你又在这里做什么,要做诗吗?”时文彦道:“我问你,密斯胡刚才来了吗?”何达道:“来了,她的昆曲越发进步。”时文彦道:“你怎么知道她的昆曲有进步?”何达道:“刚才她在这儿唱一段《尼姑思凡》。字正腔圆,的的正正是昆曲,一点儿不含糊。”时文彦见他夸奖胡晓梅,心里也是好过的,不觉得微微一笑。何达道:“她这样一个花枝般的美人,又能唱,又能舞,真是解语之花,我们天星社里有了她,真是出色得很。”时文彦见他如此夸奖,笑嘻嘻地说不出所以然来。何达道:“我想我们社里,一定有几个人的心被她燃烧着。”时文彦微笑道:“虽然有许多人的心被她燃烧着,我想也只有一个人被燃烧得最厉害吧?你猜这人是谁?”时文彦说完,含着微笑,静等何达博士满意的答复。何达道:“这没有别人,一定是李如泉。”时文彦很不以为然,勉强问道:“你在哪一点上看出来的呢?”何达道:“这有凭据的,刚才密斯胡唱《思凡》,就是密斯脱李吹笛子啦”。时文彦一听这话,心里一阵难过,两眼发直,说不出话来。何达见他晕了过去,也慌了,连忙问道:“怎!怎!怎样了?”说着,用手摇动他的身体。时文彦半晌才说出一句话,说道:“我的心弦动了。”何这才知道并不要紧,不然何以出口成章,还没有改掉诗人的吐属呢?
徐志摩、陆小曼和王赓的一段恋爱婚姻故事,在新文化圈子里,是一桩佳话。徐、陆对爱情的执著追求,王赓的大度,胡适的赞同,都是为人们所传诵的。但是,同样的一件事,放到张恨水的笔下,就成了这样的一副面貌。在张恨水的心目中,新派女子贪慕虚荣,作风轻浮,行为放荡,一无可取。在他心目中这些新派女子甚至不如妓女。看他在小说中塑造的两个妓女形象,梨云和花君,都是可敬可爱的女子。一个痴情苦恋,为情而死;一个极有主见,宁愿拿出自己的私蓄来为自己赎身,嫁给何剑尘后成为一个很好的贤妻良母。可见,张恨水对自己的文化定位,完全是站在旧文化的一边。新文化阵营认为的佳话,在他这里就成了丑闻。总之,《春明外史》这部小说,完全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它的成功与它的缺陷,都与当时的文学潮流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透过对这部小说的分析,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学史上的一段缩影。
收稿日期:2005-10-14
标签:张恨水论文; 小说论文; 春明外史论文; 文学论文;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论文; 杨杏论文; 花月痕论文; 金粉世家论文; 啼笑因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