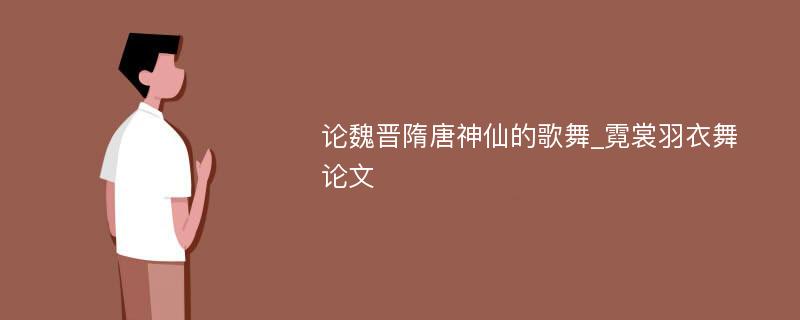
魏晋至隋唐时期神仙题材歌舞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隋唐论文,歌舞论文,题材论文,神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魏晋南北朝流行的歌舞艺术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清商乐》。这是一种与宫廷正统雅乐雅舞相对应的民间通俗乐舞,在三国曹魏时期正式确立此名称,并成为一种独立的歌舞形式大行于世。本来,雅乐舞和俗乐舞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乐舞艺术早已有之,两汉时期还曾分别设立专门的官署来掌管。如管理和演奏雅乐舞的机构西汉时称“太乐署”,东汉时期改称“太予乐署”;管理和演奏俗乐舞的机构西汉时名为“乐府”,至东汉改称“黄门鼓吹署”。由于宫廷雅乐舞主要是沿袭周代乐舞而来,虽然用于郊庙祭祀及宫廷盛大的礼仪场合有其庄重肃穆、威仪森严的规模和气派,但对于满足统治阶级现实生活中的歌舞欢娱需要来说并不合适。因此在更多情况下,他们所喜好的还是那些属于通俗乐舞中的精彩表演,以及能令观者大开眼界的所谓角抵百戏,而这恰恰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间通俗表演艺术的发展。如果说历史上的周王朝曾出现过雅乐舞文化的高峰,那么两汉时期则算得上是一个俗乐舞文化的高潮。表演规模宏大的角抵百戏(其中即含有大量的乐舞表演)及乐府、黄门鼓吹署所排演的众多通俗乐舞节目,构成了一个时代通俗乐舞文化发达的重要标志,也从一个侧面生动形象地体现了汉代大一统国家的规模和气势,以及国力的强盛和繁荣。由于“黄门鼓吹署”所演奏的《相和歌》、《鼓吹曲》、《杂舞》等通俗乐舞中含有不少属于平调、清调和瑟调(即宫调、商调、角调在当时的俗称)的歌曲,故时人也因之将这些乐曲称作《清商三调》,或简称为《清商乐》。及至汉末三国时期,曹魏父子对于《清商乐》皆酷爱无比,据《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载:“太祖(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1]他不但生前清商女乐不离左右,而且死前还留下遗令,命其婕妤伎人居住在铜雀台上,“每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1]63。曹丕于公元220年废掉汉献帝正式建立魏国后,干脆把《清商乐》独立出来,正式设立以女乐为主的“清商署”,用以取代“黄门鼓吹署”,专门负责为宫廷演奏清商乐舞。曹操、曹丕、曹植等人还依照清商三调的乐曲节奏填写了大量适于歌舞的诗歌,如《魏书》所载,曹操“登高必赋,乃造新声,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清商乐》就这样由于曹魏统治者的特殊偏爱获得了极为有利的发展机遇和条件,并很快成为社会上最受推崇的艺术表演形式。其后的西晋武帝司马炎对清商乐舞也情有独钟,他不仅继承和保留下了曹魏时期的“清商署”,而且灭吴后还将收纳的五千名多才多艺的美貌吴姬补充到“清商署”中,进一步加强和壮大了清商乐舞的表演实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东晋政权的南迁,《清商乐》传播到了南方,并对江南的民间乐舞《吴歌》与《西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形成了南朝的所谓“新声”。这样,《清商乐》所囊括的内容也就越来越宽泛了,既含有汉魏以来北方流行的“中原旧曲”,又包括江南地区发展起来的“新声”。后魏孝文帝曾组织音乐机构对流行于不同地区的清商乐舞加以采集整理,有关史料记载:
初高祖(孝文帝)讨淮、汉(493年),世宗(宣武帝)定寿春(500年),始收其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舞曲》、《公莫》、《巾舞曲》、《白鸠》、《拂舞曲》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2]。
可知在南北朝时期,世人所称《清商乐》实际上是对汉魏以来的《相和歌》、《相和大曲》、《清商三调》和《吴歌》、《西曲》及诸《杂舞》等流行通俗乐舞的总体称谓,内容变得非常丰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当时最受社会上层欢迎的通俗表演艺术。
二
由于古代乐舞的一个重要源头是来自原始宗教祭祀及巫觋娱悦神灵的表演,因而其内容多有与神祇仙人相关的成分,这个传统自然也会影响到《清商乐》的表演题材。比如在两晋南北朝清商乐舞中影响最大的《白紵舞》,其最初即是源于巫降神的一种歌舞表演。从晋代该乐舞的歌诗结句“清歌徐舞降祇神,四座欢乐胡可陈”[3],便不难了解其大致内容。这样的诗句一直到南朝刘宋时期的《白紵舞》中还保留着,可见人们在通宵达旦地欣赏这类精妙乐舞表演的同时,对于其中所表示的娱悦神灵的内容也是乐于接受的。
六朝时期流行于江南地区的《清商乐》新声,在宋人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中被划分为六个类别,即《吴声歌曲》、《西曲》、《神弦歌》、《江南弄》、《上云乐》和《雅歌》。其中与神仙题材有关或属于泛神仙题材,值得我们关注的有《神弦歌》和《上云乐》二种。前者是巫觋祀神的表演,即后人所称谓的“婆娑以乐神”之类,而后者则是直接表现神仙事迹的乐舞。
吴声歌曲中的《神弦歌》[3]683,是一组表现巫觋祭祀神灵的歌舞曲,产生于以建业(南京)为中心的江南一带。它共有11首曲辞,与先前屈原所作《九歌》在内容和体式上都有些相似。组歌第一首《宿阿曲》是用来迎神的乐曲:“苏林(神仙)开天门,赵尊(神仙)闭地户,神灵亦道同,真官今来下。”迎神曲以下第二首至第十首开始描述多路神灵陆续前来,逐一通过载歌载舞的表演在观众面前展示自己的风采。第二首《道君曲》:“中庭有树,自语梧桐,推枝布叶。”曲中语意不甚明了,大致应该是表现一个与树有关的神灵。第三首《圣郎曲》:“左亦不佯佯,右亦不翼翼,仙人在郎旁,玉女在郎侧。”被称作“圣郎”的是何方神圣不得而知,但陪侍在其身边的仙人、玉女是两位仙女却是无疑。这一节应是三位神灵同舞。第四首《娇女诗》,所表现的是一位河中女神。第五首《白石郎曲》,表现的是河畔白石头神。第六首《青溪小姑曲》,表现的是一位青溪神女的传说故事。第七首《湖就姑曲》,表现的是赤山湖畔的两位姐妹神女的事迹。第八首《姑恩曲》:“明姑遵八风,蕃谒云日中。前导陆离兽,后从朱鸟麟凤凰。苕苕山头柏,冬夏叶不衰。独当被天恩,枝叶华葳蕤。”从曲辞的内容来看,此曲所表现的是一位御风的女神,而且舞蹈中还杂以多种禽兽假形的表演,如神女引导着前边的陆离兽,后面还跟随着麒麟、凤凰等吉祥动物。这种由演员装扮起来的拟兽表演,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汉代平乐观前百戏节目中《鱼龙曼延》的热闹表演场景。第九首《采莲童曲》:“泛舟采菱叶,过摘芙蓉花。扣楫命童侣,齐声采莲歌。东湖扶菰童,西湖采菱芰。不持歌作乐,为持解愁思。”乐舞所表现的应是一群在湖中采莲的天真可爱仙童形象。第十首《明下童曲》:“走马上前阪,石子弹马蹄。不惜弹马蹄,但惜马上儿。陈孔骄赭白,陆郎乘班骓。徘徊射堂头,望门不欲归。”这里所表现的是一群骑马的仙童。最后一首《同生曲》有两首曲辞,其一:“人生不满百,常抱千岁忧。早知人命促,秉烛夜行游。”是从《古诗十九首》演化而来。另一首“岁月如流迈,行已及素秋。蟋蟀鸣空堂,感怅令人忧”取自《子夜吴歌》。这里配合两首曲辞表演的应该是一段祝福的歌舞曲,同时也是整个《神弦歌》的送神曲。
《神弦歌》所祭祀的神灵,不像《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云中君那样属于著名的天神,而是一些自然界的普通神祇,甚至还有活泼可爱的仙童居于其中,从整个乐舞出场的不同身份的神灵和歌词的描述来看,舞蹈的场面结构富于变化,内容也比较丰富,是那个神仙道教背景浓郁的时代,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形象反映。
较之《白紵舞》、《神弦歌》之类泛神仙题材的乐舞表演,《清商乐》中所列举的《上云乐》(又称《老胡文康》),则可称之为一部专门演述神仙变化的歌舞剧。此剧产生于南朝梁代,内容是表现一个名叫文康的西域老胡人,带着一班门徒和驯养的狮子、凤凰等动物来到中国的大梁,为帝王进献祝寿歌舞的故事。如此剧情的表演之所以在梁代出现并得以流行,除了南北朝时期社会上佛教、道教广为流行的大背景外,还由于当时的梁武帝萧衍特别热衷于仙佛,迷信所谓天意祥征,如建康出现凤凰、秣陵县获得灵龟之类,皆被视为天神降福于世间的帝王。老人星见本是一种很普通的自然现象,而在梁武帝的本纪中,却每年都要特书其事,甚至与他国贡献方物联系起来,作为国家祥瑞的标志。可见对于这位帝王来说,他最大的愿望无外乎仙佛能够降临,给他带来长久的快乐和享受。他亲手制作的《上云乐》歌舞曲,今存于《乐府诗集》卷五十一。该乐曲前的解题引《古今乐录》的记载说,梁武帝制作这七曲《上云乐》,为的是要代替《西曲》。七支曲子的名称分别是《凤台曲》、《桐柏曲》、《方丈曲》、《方诸曲》、《玉龟曲》、《金丹曲》、《金陵曲》。共中除《方丈》、《金陵》二曲外,另五支曲子均有和词。如《凤台曲》和云:“上云真、乐万春。”《桐柏曲》和云:“可怜真人游。”《方诸曲》和云:“方诸上,可怜欢乐长相思。”《玉龟曲》和云:“可怜游戏来。”《金丹曲》和云:“金丹会,可怜乘白云。”七首曲辞都不算太长,所表现的也主要是神仙思想,对仙界仙人的倾慕与颂扬。如果仅就梁武帝《上云乐》七曲的内容来看,似乎与《老胡文康》所表演的故事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只是这种游仙诗似的东西跟这个神仙题材的乐舞表演还勉强可以配合。但《乐府诗集》在保留《上云乐》七曲的同时,还保留了同时代人周舍所作咏赞该歌舞表演的《老胡文康辞》,并特意注明:“《上云乐》又有《老胡文康辞》,周舍作,或云范云。”由于周舍的这篇辞赋意在铺陈歌咏《上云乐》的表演情况,而不是用作歌舞表演时的伴唱歌辞,所以他笔下的描述颇为详细具体,有利于了解这部早已失传的歌舞剧的内容。该诗上来就直截了当点出了故事主角身份:“西方老胡,厥名文康。”使人们明确知道了这位来自异域神秘人物的名字、籍贯和大致的年龄。继而作品便从各个角度很全面地介绍了此老仙胡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遨游六合,傲诞三皇。西观蒙汜,东戏扶桑。南泛大蒙之海,北至无通之乡。昔与若士为友,共弄彭祖扶床。往年暂到昆仑,复值瑶池举觞。周帝迎以上席,王母赠以玉浆。故乃寿如南山,志若金刚。”至于老胡文康怪异的外貌,以及他率领众门徒和灵兽前来进献的祝寿表演,诗人的描述也颇为详尽。明人胡震亨注解周舍之作曰:“梁武帝作《上云乐》,设西方老胡文康,生自上古者,青眼,高鼻,白发,导弄孔雀、凤凰、白鹿,慕梁朝来游,伏拜祝千岁寿,周舍为之辞。”[6]周舍这首《老胡文康辞》和后人的注解,使我们可大致了解梁武帝一手创制的《上云乐》歌舞的基本内容。他是借助一个生于上古时代的神仙(似老胡人),因倾慕梁朝国威昌盛而前来朝拜,并组织其门徒和珍禽奇兽为梁朝天子祝寿的神异虚幻故事,来宣扬和标榜皇权神授的天命观,为自己的统治地位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同时也借以抬高梁王朝,起到炫耀和夸示于异邦的作用。
无独有偶,时光流过二百年后,唐代大诗人李白对这个西域胡仙前来中原王朝为君王献寿的神奇传说竟也产生了兴趣,于是他拟周舍前作写下了一首同题的《老胡文康辞》,并充分展开了一代“诗仙”的天才想象力,形象而传神地再现了当年《上云乐》的故事表演情景。借助两位诗人的描述,我们似乎可以想象:当那位高鼻、青眼、满腮胡髭、形貌装扮怪异的仙人老胡率领他的门徒小子和凤凰、狮子一类禽兽,在和谐悦耳的箫管和铿锵震天的锣鼓声音伴奏下,不断地变化队形组合,进行一个个独舞或群舞的表演,展示着各种美妙的技能时,这个为皇帝祝寿的歌舞方队,俨然是一个神仙出会的行列。特殊的演员、特殊的舞蹈动作,共同构成了一种不同寻常别具特色的艺术感染力量,从而给人一种此番歌舞及表演者皆来自仙境,是天降神人来为世间帝王祝寿祈福的强烈印象。清人王琦《李太白文集辑注》卷三,评注李白《老胡文康辞》曰:“知《上云乐》者,乃舞之名也。令乐人扮老胡之状,率珍禽奇兽而为胡舞以祝天子万寿。”[4]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中更直接明白地称:“梁时上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5]这都是在前人作品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另外,鉴于六朝时社会上已出现很多志怪和神仙题材小说,人们在创作中已普遍重视作品的故事性,这对于《上云乐》的表演应该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作为产生在这个时期的一部神仙题材歌舞,《上云乐》或许也会有着更多一些的故事情节,只是缺乏相关资料的佐证,这里我们不好妄加猜测。但仅根据目前已有的材料来看,该歌舞表演主题明确,人物众多,场面显豁,已经非一般性的乐舞可比,而完全可称之为是一部神仙题材的歌舞剧了。此剧目自南朝梁至隋代很长一个时期上演不辍,隋炀帝大业年间还将其确定为官方第九部乐伎,用于国家各种正式礼仪的“礼毕”之时,作为众节目的“压轴”之戏进行表演,大概也在于它既有吉祥的内容,热热闹闹的排场,又颇能迎合历代帝王期冀长寿成仙心理之缘故。
三
隋唐时代,尤其是唐代,舞蹈已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独立的表演艺术。唐王朝开国后推行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统治政策,给国家带来了政治局面稳定、经济繁荣、军事力量强大、国际交流频繁的兴旺景象,这同时也给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就唐代乐舞艺术来说,当时国家设有专门的乐舞机构如教坊、梨园、太常寺等,集中培养了大批专业艺人。另据《通典》、《唐会要》等史籍记载,唐朝开国之初曾将隋朝整理过的汉魏六朝乐舞全部接收过来,宫廷乐制舞制照旧,《九部乐》照样演出。但太宗贞观十一年,即开始进行较大的调整,如宫廷用于宴享典礼的大型成套乐舞,便是对隋朝流传下来的《九部乐》进行增删改变而成为《十部乐》的,其中除宴乐、清乐为内容丰富的中原汉族传统乐舞外,其余八部都是兄弟民族乐舞以及传入的外国乐舞。这显然是国家统一、国力强盛、各民族之间以及与异邦文化艺术相互交流的结果。可以说,有唐一代,特别是在国家蓬勃向上发展的初盛唐时期,乐舞艺术已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表演艺术形式。大批专业艺人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创造,把唐代的乐舞推上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唐代的乐舞种类多,著名的乐舞节目也多,其间自然不乏与神仙题材有关的表演。论及于此,或许我们会马上想到那个极负盛名的《霓裳羽衣舞》,因为这部乐舞不仅在唐代众多的乐舞中极具代表性,而且与其相关的种种神秘而浪漫的神话传说在当时和后来也一直有着很大的影响。
《霓裳羽衣舞》是在唐玄宗李隆基亲手创制的《霓裳羽衣曲》基础上精心编排而成的,常用于宫廷和贵族士大夫宴会的场合。该乐舞从音乐、舞蹈到表演者的服饰,都力图创造一种神仙的境界,这是由作者最初的创作意图决定的。因为具有音乐创作和鉴赏才华的唐明皇,很喜欢把那种虚无缥缈的美妙神仙幻境用精妙的乐舞表现出来,所以社会上便流行有他因梦见十仙子而作《紫云曲》[6],因梦见龙女而作《凌波曲》[6]979的种种神话故事。《霓裳羽衣曲》的创制当然也不例外。如《异人录》记载:“开元六年,上皇与申天师中秋夜同游月中,见一大宫府,榜曰‘广寒清官之府’,兵卫守门不得进。天师引上皇跃超烟雾中,下视玉城,仙人道士乘云驾鹤往来其间,素娥十余人,舞笑于广庭大树下,乐音嘈杂清丽。上皇归,编律成音,制《霓裳羽衣曲》。”[7]《逸史》则如是记述:“罗公远中秋侍明皇宫中玩月,以拄杖向空中掷之,化为银桥。与帝升桥,寒气侵人,遂至月宫。女仙数百,素练霓衣,舞于广庭。上问曲名,曰‘霓裳羽衣’。上记其音,归作《霓裳羽衣曲》。”[7]125-126《鹿革事类》的记载又有不同:“八月望夜,叶法善与明皇游月宫,聆月中天乐。问曲名,曰《紫云回》。默记其声,归传人,名曰《霓裳羽衣曲》。”[7]125-126而在《幽怪录》的描述中,与天师同游月宫聆听仙音的已不止明皇一人:“开元正月望夜,帝欲与叶天师观广陵。俄虹桥起殿前,师奏:‘请行,但无回顾。’帝步上,高力士乐官数十从之。顷之到广陵,士女仰望日:‘仙人现。’师请令乐官奏《霓裳羽衣》一曲,乃回。后广陵奏:‘上元夜仙人乘云西来,临孝感寺,奏《霓裳羽衣曲》而去。’上大悦。”[7]125-126其他尚有《明皇杂录》、《杨妃外传》、《仙传拾遗》、《龙城录》及《开天传信纪》等种种有关的记述,大同小异,不一而足。唐人喜言开元、天宝事,而所传怪异荒诞亦在所不免。以上援引数例,其一是说明皇与申天师夜游月宫闻仙音,并不曾得知曲名;其二是由罗公远引导明皇至月宫,得悉《霓裳》曲名;其三是明皇与叶法善同游,得《紫云回》曲名而归易之;其四则是同游者又增加了高力士及乐官数十人,或许这是考虑到高力士总不离明皇帝左右,而众乐官也时常侍奉在其身边的缘故。种种的附会和传说,其用意无非是给人一种“此曲只应天上有”的神秘印象,从而在世人心目中为这部精妙的乐舞罩上一层月宫仙舞的美丽光环。
其实,《霓裳羽衣舞》虽是表现梦幻般的神仙境界,其创作并非凭空而来,更不可能是抄自月宫仙曲。倒是唐代诗人刘梦得一首咏叹诗,有助于我们认识唐明皇创造这部乐舞的缘由及其心态:“开元天子万事足,惟惜当年光景促。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仙心从此在瑶池,三清八景相追随。天上忽乘白云去,世间空有秋风词。”[8]正是由于唐明皇的持志求仙,才直接孕育了这部优美的所谓月宫仙舞,以及众多与此有关的演绎这位风流帝王漫游月宫的仙话传说。从唐人的有关记载来看,玄宗皇帝创作“霓裳羽衣曲”时并非一无所本,而是有着作者的一些生活体验和借鉴的。先是在求仙过程中某种特定环境里优美的山景和风声水声,把唐明皇的意念带入一种虚幻的境界,根据内心的特殊体验,他写下了“霓裳羽衣曲”的散序部分,继而西凉节度使杨敬述送来了印度传人的《婆罗门》曲,明皇认为此曲颇为符合自己的创作意图,于是以此作为素材整理吸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霓裳羽衣曲”的后半部。缘此,唐代诗人王建所作《霓裳辞十首》中便有“听风听水作霓裳”[3]816之句,亚在该诗题解中引《乐苑》的记载说:“《婆罗门》,商调曲。开元中,西凉府节度杨敬述进。”[3]816《唐会要》更明确记载:“天宝十三载,……《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同时王建在其《霓裳辞十首》题解中,还进一步把现实与神话传说杂糅在一起:“罗公远多秘术,尝与明皇进月宫,仙女数百,皆素练霓衣,舞于广庭。问其曲,曰《霓裳羽衣》。帝晓音律,因默记其音调。……及归,但记其半。会西凉府节度使杨敬述进《婆罗门》曲,声调相符,遂以月中所闻为散序,敬述所进为曲,而名《霓裳羽衣》。”[3]817类似说法还见于郑嵎《津阳门诗》注中,只是把引导和陪伴唐明皇游历月宫的神仙法师由罗公远改换成了叶法善。这些材料都有助于我们认识《霓裳羽衣曲》的创作缘起及乐曲中对于外来音乐的借鉴。
尽管如此,《霓裳羽衣舞》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还在于乐舞自身。此乐舞在唐代几个不同时期的表演并不完全相同,有独舞,有双人舞,有时还有群舞形式。舞蹈者的服饰也不尽统一,虽然演员上身的“羽衣”——孔雀翠衣一直保留,其裙装却有时是淡雅的月白色长裙,有时又是如同虹霓一样的淡彩色裙子。但不管发生何种变化,最根本的一点却是大家共同遵循的,就是此乐舞的表演者一定要装扮得像仙女一样高雅而美丽,展示于观众面前的是一群不同于凡俗的仙界美女形象。她们身着霓裳羽衣,饰以珠翠,在悠扬动听的乐曲伴奏下翩翩起舞,宛如飘飘然飞翔在云间的仙鹤,完全是一种梦幻般的诗意仙境,令观者能够陶醉其中。诗人白居易所作《霓裳羽衣歌》,在描写其舞容舞姿时便有这样的诗句:
桉前舞者颜如玉,不著人家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珮珊珊。……飘然旋转迴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9]。……
由于《霓裳羽衣舞》在音乐上既融入了传统的清商乐,又吸收了外来的西方佛曲,既创造出了感人的艺术效果,又着意渲染了神秘的仙境气氛,舞蹈编排上既采用了优美的民族舞姿,又糅进了西域舞蹈中精彩的旋转动作,加上又是唐明皇这位杰出音乐家亲自作曲编舞,由当时水平最高的皇家梨园乐队演奏,由技艺最佳的宫廷专业歌舞艺人表演,因而其艺术水平足可称之为唐代歌舞艺术的高峰。而乐舞自身所表现的游仙内容及时人附会的种种神秘色彩,都使得它在当时神仙题材歌舞表演中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
除了《霓裳羽衣舞》这部最具代表性的“仙女舞”外,唐代同类题材中比较著名的歌舞还有《凌波曲》、《紫云曲》、《菩萨蛮》等作品。
《凌波曲》相传是唐明皇在东都洛阳所作。因他梦中遇见凌波池中龙女,请他这位通晓“天音”的皇上赐给一首乐曲,于是明皇即兴为她演奏一曲,醒来后默记梦中所奏曲谱,并组织梨园乐师进行排练,然后在凌波池畔演奏,忽见池中波涛涌起,梦中龙女以仙女形象跃出水中,于是人们便在池边建起庙宇,岁岁祭祀这位美丽的龙女。传说当然不足为凭,但根据这个浪漫的故事,可以推知《凌波曲》的歌舞形象是表现美丽的龙女,其音乐、舞姿应该是非常优美且富有仙意的,带有一种虚幻神秘的色彩。乐舞《紫云曲》或作《紫云回》,其创作缘起是相传唐明皇梦见十位仙女乘云而下,手中均执有乐器演奏仙曲,乐声清越优美至极。明皇趋前与之论曲,众仙女告他:这就是上天仙界的音乐《紫云曲》,现在可以传授于你。梦醒之后,乐声似仍在耳畔回荡,于是明皇立即操玉笛演奏梦境中听来的仙音,遂创制了这支优美的《紫云曲》,并依曲编排出舞蹈,由皇家梨园加以演奏和表演,乐舞所表现的内容也就是唐明皇梦中所见仙女们的舞姿。《菩萨蛮舞》又称《四方菩萨蛮队》,是唐代又一著名的“仙女舞”。此乐舞产生于中唐懿宗时代,在西南少数民族乐舞的基础上改编而成,是一部带有佛教色彩的大型女子群舞。当数百名妙龄女子组成的豪华舞蹈阵容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其场面有如一群佛仙降落人间,其仙姿妙音,悦人耳目。从敦煌写卷保存的不少《菩萨蛮词》来看,这个乐舞在当时是颇为流行的,并且传播到了比较边远的地区。另在唐人崔令钦所著《教坊记》中,还载有一部名为《迎仙客》的流行乐舞。据有关专家考证,此乐舞可能是表现迎接神仙降临的内容,自然会有仙人形象出场表演,其音乐舞蹈风格也应是典雅优美的[10]。
综观唐代出现的一批神仙题材乐舞表演,它们无论是表现月宫中的仙子,凌波池中的龙女,还是西天的菩萨,总是要塑造出美丽的仙女形象,将观者带入一个神话般的意境,从而得到艺术美的享受。较之同时期已经出现的诸如《兰陵王》、《踏摇娘》之类歌舞小戏,这类乐舞的内容相对来说可能显得虚无缥缈,故事性不是太强,但是在艺术表现形式方面自然是华美的,否则就不会在当时得到高度的赞赏,并得到广泛的流传。如果说早在汉代的“百戏”中已有扮演众仙献艺的大型歌舞《总会仙倡》出现,那么唐代的这批“仙女舞”则是以独立的乐舞形式,充分地展现不同身份仙女的美丽形象。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乐舞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同时也表明与神仙有关的题材是唐代乐舞中长于表现的内容。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唐代的乐舞与真正的戏剧表演尚有较大的距离。所以论及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从秦汉到隋唐的千余年间,虽说构成戏剧的诸多因素已经大量出现,但直到唐王朝,真正的戏剧时代并没有真正到来。唐代从本质上来说是诗的时代,也是音乐、舞蹈和书法等多种艺术蔚为壮观的时代。这些高水平的艺术形式无不洋溢着诗的神韵,诗的风采,而戏剧在这个时期却还只是停留在它的初级阶段。虽说自南北朝以来,社会上已陆续出现了以滑稽戏谑表演为主的“参军戏”和以舞蹈动作为主的如《踏摇娘》之类歌舞小戏,但由于其内容的单薄和表演形式的简朴,人们尚难把它们视为成熟的戏剧形式。诚如王国维所云:“唐五代之戏剧,或以歌舞为主,而失其自由,或演一事,而不能被以歌舞。其视南宋金元之戏剧,尚未可同日而语也。”[11]也是出于这种原因,他认为北齐以来出现的《大面》、《踏摇娘》之类歌舞戏“顾其事至简,与其谓之戏,不若谓之舞为当也。”尽管如此,由先秦歌舞、两汉之角抵百戏到唐代之参军戏、歌舞戏及音乐歌舞表演,各种泛戏剧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渗透逐渐加强,事实上仍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古代戏剧艺术不断走向自身的完善和成熟。曾有研究者这样评述说:“历史上的歌舞戏,优戏和一些伎艺表演(包括角抵戏),以服从故事情节为中心而趋向融合,向唱、做、念、打综合艺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是我国古代戏曲的重大发展。”[12]循此思路,我们有理由把唐代乐舞作为早期戏剧孕育和完善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构成因素、一种泛戏剧形态来看待,就此角度对其做一些较为深入的研究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戏剧的早期发展阶段,当构成戏剧的各种要素尚处在相互影响、渗透和融合的演变过程之中,独立而成熟的戏剧艺术尚未明朗之际,我们选择魏晋至隋唐的神仙题材乐舞作为考察对象,而它又正好能够体现出当时社会上人们的神仙信仰和观念,从而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神仙题材戏剧的早期表现形态,应该说是有一定意义的。
标签:霓裳羽衣舞论文; 唐朝服饰论文; 歌舞论文; 唐朝论文; 戏剧论文; 婆罗门论文; 乐府诗集论文; 踏摇娘论文; 仙女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