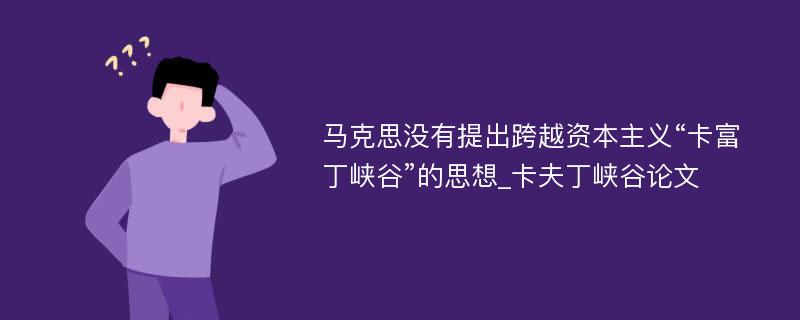
马克思没有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峡谷论文,思想论文,卡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 (1999)03—0010—04
长期以来,理论界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提出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并据此注解苏联和东欧等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马克思关于“跨越”思想在现实中的具体实现。笔者认为,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一、“卡夫丁峡谷”的确切内涵
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所酝酿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含义,必须从维·伊·查苏利奇给马克思的信说起。
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正值俄国废除奴隶制, 开始向资本主义发展之际,俄国学者和政论家对《资本论》中所提出的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和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以及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1881年2月16日, 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说:“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她希望马克思能说明“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版,第857页。)。
1881年2月至3月,马克思为给查苏利奇复信,先后写了一稿、二稿、三稿和四稿。最后将第四稿作为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复信。在复信的草稿中,马克思指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分析,明确地限于欧洲各国。俄国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历史必然性”不适用于俄国。在西欧,“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在俄国,以土地公有制为特征的农村公社依然存在。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应用到公社中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436页。)。
显而易见,如果将“卡夫丁峡谷”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来理解,是明显的同语反复的语法错误。同时也和马克思前面所谈论的俄国农村公社的生产不是一致的。所以,将“卡夫丁峡谷”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来理解是不确切的。那么“卡夫丁峡谷”是否指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整个过程呢?马克思在一稿中指出,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 第431页。)。在此我们可以看出, “卡夫丁峡谷”是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相联的,但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全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波折”以及产生这些“波折”的生产阶段。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无疑是指马克思曾多次鞭挞的、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及其灾难性后果。所以,马克思所说的“卡夫丁峡谷”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及其灾难。二是指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阶段。这样马克思就明确回答了查苏利奇所提出的关于“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是否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问题。
二、马克思有过俄国农村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酝酿,而没有提出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马克思致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共计写了四稿,最后一稿是作为正式复信发出的。在四个复信稿中,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谷”问题的表述是这样的。
在初稿中,马克思指出,在俄国,“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接着马克思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能否改造成先进的社会起点的两个必备条件——经济上改造的需要和物质上实现改造的条件后,指出,俄国农村公社“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页。)。
上述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谷”的表述说明,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既是十分谨慎的,也是不确定的。他在初稿中由“可以不通过”到“有可能不通过”的转变,表明马克思对该问题的非完全肯定态度。因为,马克思在此之前主要从事的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弊端以及灭亡的研究,得出了未来的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诞生的论断。要回答当时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方向,对马克思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所以,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一开始就表现出十分的慎重。
在复信的二稿中,马克思指出,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4 页。)。
在该复信稿中,马克思根本没提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只是说明了在保存俄国农村公社的前提下,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明成果来改造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这种由初稿的可以不通过、可能不通过到可以吸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以发展和改造俄国农村公社的进一步思想变化,表明了马克思在是否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上是时而肯定,时而不确定,和时而否定的。说明马克思在一直思考着这个他一时难以确定的问题。
在第三稿中,马克思在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天生的二重性和可能导致的两种结果后指出,“现在,我们暂且不谈俄国公社所遭遇的灾难,只来考察一下它的可能的发展”。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
在此复信稿中,马克思对能否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又基本上作了“肯定”的回答。但这种肯定是有前提的。即:“暂且不谈俄国公社所遭遇的灾难,只来考察一下它的可能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 由于这种“可以不通过”只是一种可能的发展,所以,这种肯定也是不确定的。它展示了马克思在该问题上还没有作出最后的结论。
在正式复信的第四稿中,马克思指出:“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版,第775页。)
在这封正式复信中,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及“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问题。而只是根据俄国农村公社当时的公有制基础作出了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的论断。这难道是马克思的疏忽吗?回答是否定的。由于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方向一开始就认为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451页。)。所以在正式复信中,马克思必然表现出更大的慎重。他所作出的俄国农村公社是社会新生支点的论断,主要是针对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而言的。而公有制作为社会新生的支点,又是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其它经典著作中所阐述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一致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确实对俄国农村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作过一定的酝酿,但最后没有提出可以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因为,马克思所提的“卡夫丁峡谷”问题,只是在复信的初稿和第三稿中出现过。其间经历了一个由“可以不通过”→“可能不通过”→不提“卡夫丁峡谷”问题→“可以不通过”的过程。马克思在前三个复信草稿中的这种思想反复,表明了他对该问题孜孜不倦的探究和在新的理论根据没有出现以前,他不会作出非科学结论的严谨学风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同时也反映了他对该问题的不确定性。尽管他在初稿和第三稿中提出了可以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但前三稿均是草稿。马克思之所以没有将其任何一稿作为正式的复信,这说明马克思自己也认为对该问题考虑的并不成熟,尚在酝酿之中。第四稿作为正式复信表明马克思经过深刻的思考之后,作出了他对该问题的最后论断。所以,第四稿才是马克思最终的真实思想表达。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的思想、观点和主张的提出只能以其公开的讲话或正式的文字表达为依据,在公开讲话或正式文字表达前的思考、分析和探索,只能是对问题的酝酿。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在前三个复信草稿中所提出的“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只能说明马克思对该问题有过思想上的酝酿,但最后并未提出可以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三、马克思提出了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问题,没有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目前,理论界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晚年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与当前的现实有一种直接的关联。相当多的人从中找到东方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当代改革的‘理论源头’”(注:布成良、陈海涛:《我国没有走出“卡夫丁峡谷”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6期。)。但在马克思致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 只有“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表述,从未出现过“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文字。这决不是在咬文嚼字。因为作为“跨越”和“可以不通过”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马克思“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指:由古代原始公社演变而来的俄国农村公社,由于保存了土地公有制,在俄国社会给予社会必要垫款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同时存在为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的情况下,有可能绕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阶段以及所导致的经济危机,而选择另一条继续向前发展的道路。这样就可以避免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受的波折和灾难。而“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则是指:俄国的农村公社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生产阶段。这既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他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愿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276页。)。在1867年的《资本论》序言中,他又指出,当时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正以“铁的必然性”向前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前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版,第100页。)。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发展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版,第101页。)。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针对“跨越论”者、 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赫尔岑所提出的“俄国公社可以使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的观点,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指出,“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征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出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页。)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是继承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人们只能了解、掌握和利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去推进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决不能人为主观地改变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版,第33页。)。从农业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然要经历若干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在过渡时期,只有完成了从落后、简陋的小生产向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变,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根本转变,完成了从愚昧向现代文明的转变,完成了从封闭体系向开放体系的转变,才具备了进一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跃进的最起码的基本条件。否则,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通过变更生产关系的形式,强行向高级经济形态的过渡,要么根本不成功,要么只是形式上的,要么自受其害。
收稿日期:1998—11—16
标签:卡夫丁峡谷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跨越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资本论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