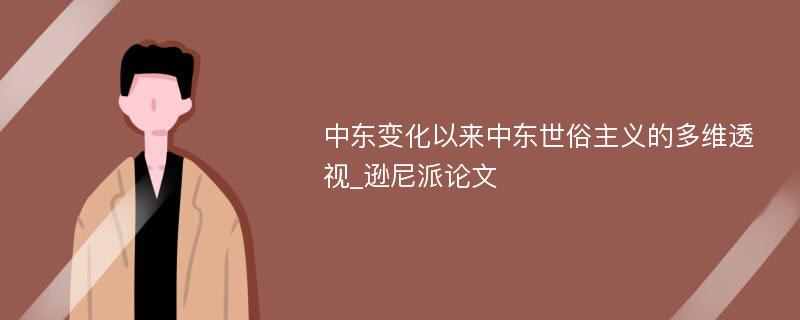
对中东变局以来中东教派主义的多维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多维论文,教派论文,变局论文,透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斯兰教两大教派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不仅影响中东伊斯兰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且通过跨国教派渗透影响国家间关系乃至地区格局。中东变局发生以来,教派因素不仅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如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动荡中的教派矛盾),而且充当了各派力量尤其是地区大国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对中东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产生了深刻影响。“阿拉伯起义的浪潮加深了近年来一直存在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族群和宗教关系的紧张,使其再度走上中东政治的前台。”①在国际关系层面,复杂的教派矛盾不仅突出表现为沙特和伊朗围绕巴林问题、叙利亚问题和也门问题的矛盾,还表现为逊尼派内部的矛盾,尤其是传统伊斯兰力量与现代伊斯兰力量的矛盾,如以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和部分伊斯兰政党为代表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与瓦哈比-萨拉菲派力量为代表的传统伊斯兰力量之间的矛盾,并在国际关系层面表现为土耳其和沙特对逊尼派世界领导地位的争夺。对此,一些学者评价指出:“目前中东的地缘政治对抗正在什叶派势力伊朗、逊尼派激进势力沙特阿拉伯和逊尼派温和势力土耳其三大力量之间展开。”②此外,教派矛盾也成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塑造和传播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家”的政治工具。 近几年来,教派因素在中东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反映到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便形成了一种言必称教派矛盾的倾向,这种有着深刻政治意蕴的舆论倾向在中东和西方媒体中最为严重。当前,舆论界对教派矛盾的认识多存在简单化之嫌,似乎中东国家只要有不同的教派,教派矛盾和冲突就必然存在。但是,“中东各国的教派矛盾并非是一种先天存在的必然,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在长期的历史中、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和谐共处,当前教派矛盾的凸显是长期以来各种矛盾累积的产物。”③因此,客观评估中东变局以来教派矛盾的新发展,准确认识教派矛盾的实质,无疑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东变局以来,教派矛盾新发展的典型特征在于教派矛盾的高度政治化,即教派主义的加剧。教派主义泛指宗教和教派认同被政治化的过程。当前,中东政治中的教派主义同过去教派冲突的区别在于,一些国家统治者基于教派关系对政治进行评估,即从教派角度进行战略决策,根据教派关系制定自己的内政与外交政策。④尽管教派矛盾并非中东变局的直接原因,但随着教派主义逐渐成为海湾逊尼派国家应对中东变局和稳固国内政权的关键性手段,中东地区的教派矛盾被充分激化。教派主义不仅体现于国内层面的政治斗争,还表现为地区层面的权力博弈。在巴林、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国家,教派矛盾的激化及其外溢导致地区范围内的教派矛盾,这种矛盾一方面通过外溢形成以教派为标识的阵营分化,另一方面又使巴林、叙利亚、也门的教派矛盾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演变为代理人之争,同时成为“伊斯兰国”等宗教极端组织极力运用的政治工具。本文将从国内政治、地区政治以及宗教极端主义3个层面对中东教派矛盾进行分析与评估。 教派主义与阿拉伯国家的国内政治 中东变局以来,教派主义对阿拉伯国家国内政治的影响突出表现为海湾阿拉伯国家为应对中东变局,对民众抗议活动进行基于教派话语的塑造和建构,进而将国内社会矛盾转化为教派矛盾,这在巴林和沙特最为突出。 在海湾君主制国家中,巴林是受中东变局冲击最为严重的国家。面对以发展民主、要求自由和政治改革为主要目标的抗议运动,巴林逊尼派王室政权、政治组织和官方控制的媒体积极利用教派因素进行政治动员,将反对派的政治抗议归结为伊朗的“阴谋”,以获取对什叶派进行镇压的政治合法性。 在巴林,王室成员来自逊尼派少数群体,为维护逊尼派的绝对统治,王室对占本国人口60%~70%的什叶派多数群体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一方面拉拢支持政府的什叶派群体,另一方面打压要求改革或持不同政见的什叶派反对派群体。2011年初,由“2月14日革命青年联盟”(February 14 Revolution Youth Coalition)通过互联网发起的民众抗议浪潮爆发。起初,参加抗议群众既包括什叶派信众,也包括逊尼派信众,这在当时抗议者高呼的“没有逊尼派,没有什叶派,只有巴林人”⑤的政治口号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什叶派反对派“和谐协会”(al-Wefaq)⑥等组织并非抗议的发起者,它们直至抗议浪潮达到一定规模后才决定加入抗议行列。“2月14日革命青年联盟”是一个缺乏统一领导的松散组织,其成员大部分是大、中学生,是一个不属于特定教派或政党的跨教派青年组织。它号召巴林青年以和平非暴力手段进行示威抗议活动,实现民主、公正和选举自由。而“和谐协会”也强调自己的巴林和阿拉伯属性,多次否认该组织与外国势力存在联系。⑦ 但是,以逊尼派和什叶派为载体的反对派内部分歧,很快就导致了反对派的教派分化,这无疑为巴林王室利用教派矛盾获取对反对派进行镇压的合法性提供了机会,政府声称“暴动的根源在于教派冲突”,是“伊朗支持下的什叶派暴动”。⑧在政府渲染教派冲突的同时,“民族联合阵线”(National Unity Gathering)和巴林穆兄会、萨拉菲派等逊尼派政治组织和团体也不断强调“现政府的垮台将导致在巴林建立类似伊朗的神权政体”;官方控制的媒体也极力炒作教派矛盾,例如巴林《国家报》(Al Watan)、“巴林论坛”(Bahrain Forums)网站都不断熏染教派冲突以及伊朗对巴林什叶派的支持。⑨ 巴林王室以镇压什叶派骚乱为名对反对派抗议活动进行镇压,但始终无法控制局势。2011年3月14日,海合会决定向巴林派驻沙特和阿联酋联合部队,协助巴林政府镇压示威人群。沙特的军事介入引来了伊朗政府和阿拉伯什叶派的谴责,使巴林抗议运动迅速转变为海湾大国间的代理人冲突。在外部因素作用下,巴林政治史无前例地两极化,教派身份成为影响国内政治阵营分化的关键因素。⑩ 在巴林政治动荡中,逊尼派王室政府及其控制的媒体和政治组织不断强调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形成的教派主义逻辑: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朗支持包括巴林在内的海湾什叶派革命——镇压什叶派革命亦即反对来自伊朗的颠覆。但是,巴林政府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伊朗直接支持了巴林的示威游行。巴林反对派强调民众的诉求是更合理的分配权力和利益,而非挑动教派矛盾。”(11)事实上,参加民众抗议浪潮的什叶派民众并无明确的建立伊朗式神权的政治目标。2009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反对和支持在巴林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什叶派信徒的比例分别为63%和25%,(12)反对者远胜于支持者。但政府对民众抗议的镇压以及事后对抗议者的清算,如取消参加抗议的什叶派学生的奖学金,搁置授予学位和就业歧视等措施,都“加剧了什叶派的受害者心理,导致教派冲突进一步加剧。”(13) 在沙特,利用教派主义强化和巩固逊尼派多数群体对政权的忠诚,煽动逊尼派对什叶派的教派仇恨,防止逊尼派内部改革派、自由派与什叶派联合进行反政府抗议活动,构成了沙特王室应对中东变局的重要手段之一。沙特王室积极利用瓦哈比主义的宗教教义,尤其是运用其中将什叶派定义为“异端”的教派话语,反对政治上表现活跃的什叶派少数群体,同时要求逊尼派多数群体放弃政治变革的诉求,进而阻止具有跨教派、跨地区、跨意识形态和跨部落特征的政治反对派的产生。对此,一些人士指出,由于沙特政权不断利用教派矛盾构建教派主义的政治话语,沙特始终难以形成强有力的超越教派意识的政治反对派,抗议群体虽不断呼吁政治改革,但却很难对沙特政权构成实质性的威胁。(14) 中东变局对沙特国内政治的冲击主要表现为东部什叶派出现抗议活动,其重要原因在于什叶派在沙特长期受到压制。沙特外交、安全、军队、警察以及石油等重点行业和部门的要职通常都将什叶派排除在外;什叶派经常面临宗教警察的干扰和迫害,什叶派清真寺等宗教场所也面临随时可能被关闭的处境。(15)针对什叶派的抗议活动,沙特王室采取了政治-宗教的双重应对策略。在政治上,沙特政府出动安全部队镇压东部什叶派聚居区的抗议活动,并将抗议活动定性为“什叶派阴谋”和“以伊朗为首的外国势力资助的起义”,同时通过逊尼派人士强调“任何抗议活动都将导致沙特的碎片化和地方主义、教派主义和部落主义的回潮”。(16)在宗教上,沙特王室通过官方宗教机构动员宗教人士支持当局。首先,沙特王室通过沙特官方最高宗教机构宗教学者委员会(Council of Senior Scholars)颁布的法特瓦(宗教教令),反对示威抗议活动。(17)沙特媒体和安全机构控制的网站均对法特瓦进行了广泛报道和宣传,政府还印制了1.5万份法特瓦传单,并在清真寺和社区派发,利用宗教声明广泛论证和宣传抗议活动的非法性。(18)其次,沙特官方借助知名宗教学者引导国内舆论,通过清真寺、宗教讲座、研讨会和网络视频声讨什叶派,将抗议运动描绘成得到伊朗支持、由国内外什叶派势力共同组织发起的“什叶派阴谋”,倘若任其发展,将会导致国家陷入“碎片化、部落战争、内战和血洗”。(19) 值得注意的是,沙特王室在构建反对“什叶派异端”的宗教话语体系外,还构建了一套所谓的自由派政治话语。它主要表现为沙特王室允许逊尼派所谓的自由主义精英分子利用媒体对教派主义进行谴责,这并不意味着沙特王室支持自由派的主张,其实质是沙特王室通过刻意制造和激化逊尼派和什叶派、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宗教人士之间的分歧,防止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跨教派的政治反对派,并使沙特政府在自由派与伊斯兰势力、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扮演调停者角色,以服务于王室政权的利益。(20)由于沙特国内不存在工会、专业团体和政党等有组织的公民社团,反对派在组织抗议运动时难以进行真正有效的跨教派动员,这为沙特王室利用教派主义分化抗议群体提供了条件。 教派主义与中东地区主导权的争夺 在地区层面,教派主义构成了沙特、伊朗和土耳其等地区大国攻击政治对手、实现政治利益、争夺地区领导权的有效途径,导致教派矛盾成为地区大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重要载体,这不仅表现在逊尼派和什叶派阵营之间的跨国竞争,还体现在逊尼派内部的阵营分化和微妙竞争。 1.教派主义与沙特、伊朗的地区主导权之争 伴随教派因素在中东变局中作用的上升,逊尼派和什叶派都开始从教派利益的角度观察中东变局对于自身的影响。“在许多逊尼派看来,阿拉伯起义为削弱伊朗-真主党-叙利亚的什叶派轴心提供了机会。因为对于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所有的什叶派都是忠诚于伊朗的铁杆分子(iron-clad Iranian loyalists),而伊朗则是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坚定支持者,并坚信伊朗对叙利亚事务进行了深度干预。”(21)其结果是,“过去在伊斯兰世界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什叶派,目前正在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国家积极地争取其权力,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22)而什叶派则认为,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力量在阿拉伯转型国家取得执政地位、逊尼派反对派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严峻挑战、巴林逊尼派政府对什叶派抗议的镇压、伊拉克逊尼派反对派挑战什叶派主导的政府、沙特等国家大力支持巴林逊尼派政府和叙利亚逊尼派反对派,“都促使什叶派认为逊尼派的威胁在不断扩大”。(23) 当前,在中东地区,“主要教派冲突已演变为地区权力斗争,这反过来又逐步转变成大国竞争”。(24)地区国家利用热点问题构建教派主义话语,在他国扶植和动员支持力量,建立具有跨国认同的意识形态体系,其实质是利用教派资源争夺势力范围和地区主导权的斗争,这在沙特与伊朗的对抗中体现得最为突出。 在国内层面,沙特对中东变局的反应主要出于对逊尼派和什叶派反对派可能会出现联合的担忧。(25)为阻止国内出现类似巴林示威抗议运动,通过催生“教派恐慌”情绪,将国内政治矛盾转嫁至地区层面反对伊朗和叙利亚巴沙尔什叶派政权的教派矛盾,(26)便成为沙特的战略选择。因此,沙特王室和国内政治精英积极利用宗教操控政治,在国内和地区层面构建起一套“教派话语”,通过主流媒体、论坛网站、社交媒体和宗教人士、媒体精英等散布“什叶派威胁论”(27),目的在于对内减少中东变局对沙特的负面影响,维护政权稳定;对外通过领导逊尼派国家抗衡伊朗,争取地区主导权。 在对外政策层面,沙特在中东变局中对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突尼斯、埃及的政策相对低调,甚至对美国抛弃盟友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同时对两个国家的过渡政权给予了一定的经济援助;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沙特的政策明显较为激进,积极支持政治反对派推翻卡扎菲和巴沙尔政权;在巴林问题上,沙特却截然相反,不仅对巴林政府提供经济援助,还以海合会名义出兵镇压巴林的民众抗议浪潮;在也门问题上,沙特主导的海合会先是通过斡旋实现了也门政权的和平过渡,但在什叶派胡塞武装不断坐大后,沙特开始于2015年3月组织阿拉伯盟军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 教派因素构成了沙特对不同阿拉伯国家采取不同政策的重要原因。总体来说,沙特对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共和制国家的政治变革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但对叙利亚和巴林的不同政策,则充分体现了沙特对教派矛盾斗争的考虑,镇压巴林什叶派抗议,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巴沙尔什叶派政权,其共同目标都是维护逊尼派的共同利益,同时也是为了肢解伊朗主导的“什叶派联盟”。(28) 总之,自中东变局以来,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试图通过“什叶派阴谋论”激活地区教派冲突,力图以教派逻辑定义地区关系和建立地区秩序,通过强化海湾地区逊尼派同盟,对伊朗和什叶派势力进行打压和孤立。 在中东变局中,伊朗与沙特主动挑起地区教派矛盾做法有所不同,它一直试图避免掉入沙特设置的教派话语陷阱。“伊朗希望避免一场教派主义的大火,更不会火上浇油”,(29)其重要原因在于担心因教派矛盾使伊朗在中东地区陷入孤立。但这并不妨碍伊朗将什叶派教义作为动员中东什叶派反对西方及其盟友的一种软实力工具。(30)伊朗介入巴林危机、叙利亚危机和也门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其教派动员虽然有实有虚,但“以教派为基础的联盟是伊朗确保其影响力为数不多的手段之一”(31)。 在巴林问题上,伊朗认为2011年的民众抗议运动具有非教派和民粹主义的特征,(32)而不是教派冲突。在政策取向上,伊朗主要在道义和外交层面对巴林反对派予以舆论支持,并不强调教派问题。一些学者评价指出:“伊朗在巴林(问题上)无论如何都是赢家,如果王室以武力镇压什叶派,德黑兰可以振振有词地声称镇压得到了美国授意;如果反对派推翻政权,伊朗可以借机努力建立新的地区秩序。”(33)但是,随着沙特的军事介入和煽动教派主义,伊朗不可避免地被塑造成巴林什叶派的支持者。 在叙利亚危机上,叙利亚反对派的示威抗议活动最初主要是以政权腐败、社会不公、治理不善为由要求巴沙尔政权下台,反对派曾打出“无论我们是逊尼派还是阿拉维派,无论我们是库尔德人还是阿拉伯人,我们都要自由”的标语,(34)表明它并非教派性质的抗议活动。但是,伴随海湾逊尼派国家、土耳其等国家对逊尼派反对派组织的资助,叙利亚国内冲突开始呈现教派化趋势,教派暴力频发和宗教极端势力崛起导致叙利亚内战的教派色彩不断加深。(35)伊朗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支持并非单纯出于教派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考量,而是出于维护双方同盟关系和共同安全利益的战略需求,同时也为了巩固叙利亚在“什叶派新月地带”中的战略枢纽地位,反对沙特、土耳其和西方通过颠覆巴沙尔政权削弱伊朗的图谋。 在也门危机上,沙特动用大量军事力量和政治资源,集结十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空袭,其重要现实考虑之一在于担心什叶派在也门掌权将进一步扩大伊朗的地区影响。针对也门危机,伊朗的态度十分谨慎。伊朗在主观上不愿在伊核谈判的关键节点卷入也门冲突,更不愿掉入沙特设置的教派冲突陷阱。此外,胡塞武装对于伊朗的重要性也远不及巴沙尔政权和真主党两个战略盟友。 沙特和伊朗还在舆论层面展开话语权的争夺,但沙特显然处于攻势地位。近年来,沙特政府和社会不断宣传和渲染什叶派的威胁。例如,沙特王室通过“萨哈(al-Saha)和沙特自由网(Saudi Liberal Network)等论坛网站,发布各类诋毁什叶派的信息”,极端萨拉菲派更是把什叶派和犹太人视为“伊斯兰教的敌人”。一些萨拉菲派神职人员甚至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戈兰高地炸死黎巴嫩什叶派真主党领导人持肯定态度。例如,萨拉菲派神职人员穆罕默德·巴拉克(Mohammed al-Barrak)于2015年1月18日在“推特”(Twitter)网站上写道:“什叶派死在犹太人手里,感谢真主回应了我们的祈祷”。“什叶派对穆斯林的危害比犹太人对穆斯林的危害更大,因为过去4年中什叶派犯下的罪状已经超过了犹太人过去60年犯下的罪状。……什叶派是穆斯林最坏的敌人,因为他们的宗教是犹太人创造的,这令什叶派变成了比西方异教徒或忠于以色列国的犹太人更加糟糕的敌人。”(36) 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al-Arabiya)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Al-Jazeera)与伊朗阿拉伯语电视台世界新闻频道(al-Alam)围绕教派问题展开了激烈竞争。阿拉比亚电视台和半岛电视台在新闻报道中煽动教派偏见,通过强调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对立贬损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什叶派政权合法性,沙特媒体甚至还使用有什叶派背景的主持人进行反对什叶派的宣传。伊朗主导的什叶派也不甘示弱,伊朗媒体和黎巴嫩真主党下属的“路标”电视台(al-Manar)也常常从什叶派与逊尼派冲突的角度,放大巴林、叙利亚和也门国内政治社会冲突中的教派色彩。伊朗历史剧《穆赫塔尔》(Mokhtar Nameh)与沙特和卡塔尔联合摄制的历史剧《欧麦尔》(Omar)就是典型代表之一,双方都通过历史剧刻意渲染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矛盾。 2.逊尼派国家间矛盾和地区主导权竞争 中东变局以来,教派主义的政治动员模式不仅表现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紧张关系,也表现为逊尼派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以沙特瓦哈比-萨拉菲派为代表的保守伊斯兰力量,同以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埃及穆兄会为代表的现代伊斯兰力量之间围绕伊斯兰政治模式的分歧不断加深,导致逊尼派国家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 在中东变局中,土耳其与沙特围绕埃及政治转型的争夺体现了逊尼派内部现代伊斯兰势力与传统保守伊斯兰势力的潜在竞争。在埃及政治转型过程中,土耳其大力支持穆兄会,其重要原因在于埃及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同属现代伊斯兰势力的代表,土耳其力图通过支持穆兄会对外输出现代伊斯兰主义,并与沙特的伊斯兰保守势力进行意识形态争夺,这是土耳其与沙特关系趋于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多年来,尤其是中东变局以来,沙特一直不遗余力地打压穆兄会,试图遏制穆兄会不断壮大。在埃及的政治转型中,在土耳其、卡塔尔等国家的资助下,穆尔西领导的穆兄会下属自由与正义党赢得大选并上台执政。在穆尔西执政时期,埃及不仅允许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在首都开罗扩大业务,还同伊朗迅速改善关系,实现两国元首互访,这都令沙特极为不满。2013年7月,在埃及军方废黜穆尔西政权后,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致信埃及军方,称赞埃及军方在关键时刻拯救了国家。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很快表示将分别向埃及提供50亿美元和3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此后,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对埃及军方的清场行动也表示支持。在沙特的带动下,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阿曼都表示支持埃及临时政府。(37)2014年3月,沙特内政部正式把穆兄会定性为恐怖组织。 为抑制穆兄会的发展,沙特、阿联酋和科威特投入巨资支持组建埃及光明党等萨拉菲派政治力量,其政治考虑主要有三:第一,支持埃及萨拉菲派与穆兄会进行伊斯兰政治模式的抗争;第二,同支持穆兄会的卡塔尔、土耳其进行地区主导权的博弈;第三,利用萨拉菲派推广反伊朗、反什叶派的教派主义话语,构建更加广泛的反伊朗、反什叶派联盟。2013年4月,50多名伊朗游客赴埃及旅游时,曾遭到萨拉菲派团体的反对,(38)这显然与沙特等海湾国家对萨拉菲派的影响有关。沙特等海湾国家反对穆兄会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现实的政治考虑。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发展模式的角度看,沙特力图避免现代伊斯兰力量成为中东地区的主导力量,并在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方面对海湾君主制国家构成挑战。 在埃及转型过程中,土耳其一直是穆兄会的坚定支持者,对埃及军方镇压穆兄会表示强烈反对。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土耳其对穆兄会予以大力支持,并在穆尔西当选总统后向埃及提供了约合20亿美元的经济支持。(39)2012年9月30日,穆尔西还应邀出席了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代表大会。2013年7月,穆尔西政权被埃及军方推翻后,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称军事政变是民主的敌人,是“不可被接受的政变”。2013年8月,埃及军方强力驱散支持穆尔西的抗议营地之后,土埃关系严重恶化,双方互相召回大使,导致双边外交关系被降至临时代办级别。(40) 在穆兄会沉浮的过程中,不仅埃及国内的宗教和世俗两大力量展开激烈对抗,地区力量也基于对伊斯兰主义的不同立场展开了复杂的博弈。在此过程中,沙特领导的海湾君主制国家构成了中东地区内反对穆兄会主要的力量,而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成为穆兄会最坚定的支持者,而背后则是逊尼派内部传统与现代伊斯兰力量围绕意识形态、发展模式与地区主导权的争夺。 宗教极端主义对教派主义的利用 利用教派主义构建宗教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中东伊斯兰极端组织惯用的手段,“基地”组织和“圣战萨拉菲”组织都曾将什叶派描绘成“异教徒”或“叛教者”,并作为暴力活动的主要社会动员模式。随着“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教派主义已成为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进行社会动员、强化极端暴力行径宗教合法性的主要手段。宗教极端主义的偏执和仇恨心理,已成为加剧地区动荡与政治冲突的重要因素,“导致地区安全问题趋于复杂化。”(41)在当前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教派主义扮演着重要角色,呈现出教派主义工具化、狂热化等特征。 在地区层面,由于叙利亚危机、也门乱局经常被塑造成沙特和伊朗通过代理人战争进行的教派战争,这套服务于权力争夺的教派话语体系,经过地区极端组织的改造,已经异化为引发宗教狂热、宗教仇恨和宗教暴力的极端主义话语体系。 “伊斯兰国”组织充分利用教派话语体系激化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业已存在的对立,通过泛化“异教徒定判”(takfir)和“圣战”观念,调动极端分子的教派仇恨和宗教狂热,为其暴力恐怖行径提供宗教合法性,并为重建所谓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哈里发国家”提供宗教法理依据。其中,“异教徒定判”观念经过极端组织异化后,成为可以随意判定非逊尼派穆斯林、其他宗教信徒、无神论者为异教徒,并对其进行处决的观念。“异教徒定判”观念已成为“伊斯兰国”组织极端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该组织挑选所谓的教法学家,从法特瓦中寻找所谓证据来解释“异教徒定判”观念,尽管这类解释经常缺乏逻辑并自相矛盾,但却公然成为极端组织处死所谓异教徒的宗教依据。“伊斯兰国”组织利用年轻人的宗教情感,灌输并且强迫年轻人“信仰”这种被严重曲解和异化的“异教徒定判”观念并付诸实施。当前,该组织内部已出现年轻人将自己的父亲判定为“叛教者”和“异教徒”并要求将其处死的极端现象。(42) “异教徒定判”观念的蔓延构成了中东教派暴力加剧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2015年以来,逊尼派和什叶派相互袭击的事件不断上升。例如,“伊斯兰国”组织也门分支于2015年3月20日对萨那胡塞武装组织控制下的两座清真寺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43)胡塞武装组织也对也门当地极具影响的萨拉菲派长老和政治人物的住所发动了袭击;(44)又如,2015年5~6月,“伊斯兰国”组织先后对沙特东部卡提夫地区和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的什叶派清真寺发起自杀式炸弹袭击。 在“伊斯兰国”组织的话语体系中,受到严重异化和泛化的“异教徒定判”观念是其极端意识形态的主要思想来源,这种排斥异质宗教信仰的极端观念,往往成为评判该组织成员忠诚度的重要标准。逊尼派圣战分子对什叶派和其他宗教信徒的狭隘偏见与仇恨,既是“伊斯兰国”组织实现教派主义叙事狂热化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该组织动员极端分子发动“异教徒定判圣战”(takfri jihad)的主要动机。 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伊斯兰国”组织教派主义的叙事手法催生出了一批狂热且非理性的极端分子,这些人不仅将世俗政权、基督徒、西方人、什叶派作为袭击对象,也将逊尼派作为袭击对象。该组织成员破坏逊尼派历史学家、萨拉丁军队的书记官伊本·艾西尔的陵墓,到处滥杀其他逊尼派成员,这表明逊尼派的身份认同并非“伊斯兰国”组织的真正基础,只是该组织对自身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加工时使用的叙事工具。 此外,极端组织还利用社交媒体煽动教派仇恨和宗教狂热,进而实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渗透。据一项统计报告,推特上公开支持“伊斯兰国”组织的账号保守估计约有4.6万个,最多可能有9万个。(45)“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通过电子期刊、社交网站、视频音频、宣传手册等媒介,蓄意煽动教派仇恨,动员逊尼派极端分子针对什叶派穆斯林实施报复性攻击,激化了中东国家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 中东变局以来教派矛盾的发展突出体现在中东国家国内政治、中东地区格局两个主要层面,而“伊斯兰国”等宗教极端组织对教派矛盾的利用,则成为教派矛盾影响中东政治的特殊表现形式。这些表现背后的根源则在于教派主义对教派矛盾的政治化和工具化,即中东国家内部利用教派矛盾的政治权力斗争、地区大国利用教派矛盾构建政治联盟,争夺地区主导权、极端组织利用教派矛盾构建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因此,认识中东的教派矛盾,需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同时更要重视挖掘教派矛盾的历史与现实根源。受篇幅所限,这里就中东教派矛盾的根源及其实质提出以下两点认识:(46) 首先,中东各国的教派矛盾并非是一种先天存在的必然,当前中东地区教派矛盾的加剧是长期以来各种矛盾累积的产物。就近代以来的情况而言,从外部因素来看,教派矛盾多与西方殖民主义“分而治之”政策的历史遗产有关。1916年,英、法签订《赛克斯-皮科协定》,无视中东的民族与宗教等人文地理,把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划分到不同国家,导致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家的族群和教派结构异常复杂。而英、法在委任统治时期“分而治之”政策的推行进一步固化了教派权力格局。例如,在叙利亚,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为对抗逊尼派民族主义力量,不仅扶植阿拉维派建立自治共和国,而且大量吸收阿拉维派进入逊尼派不愿参加的军队,这是阿拉维派后来掌握军队主导权并能够长期把持叙利亚政权的重要因素。 从内部因素看,教派矛盾的累积与中东国家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分配、社会文化政策等领域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即便如此,在二战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同教派大多能和平共处,倡导教派和谐的人士在两大教派中均大有人在。因此,教派矛盾只是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的表象,而不是本质,不可本末倒置。有评论言:“伊朗革命、伊拉克内战、黎巴嫩的真主党-以色列战争以及近期的叙利亚内战,都在海湾地区引起反应,激发起教派情绪,煽动着派系斗争的表达。然而,逊尼派-什叶派紧张关系最终的根源在于国内层面,而非地区性事件。”(47) 其次,教派矛盾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和部分中东国家极力建构的政治话语体系,是服务于其政策需要的意识形态体系。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推行“输出革命”的战略,促使沙特等海湾逊尼派国家开始注重从教派关系的角度对地区格局进行塑造,以服务于抗衡伊朗的战略需要。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沙特、约旦等国家基于对什叶派影响扩大的担心,提出了“什叶派新月地带”的概念。而美国也不断把亲美阵营和反美阵营的矛盾归结为教派矛盾,以此来塑造地区格局。在沙特的官方政治话语中,什叶派经常被置于“异端”地位,宗教学者经常将什叶派描绘成“危险的骗子”和“伊斯兰教的敌人”。(48)美国、以色列等国家也纷纷使用“逊尼派-什叶派分歧”、“什叶派崛起”等教派话语概念构建反伊朗、反什叶派阵营。对此,一些清醒的美国学者曾指出:“近来来整个伊斯兰世界教派矛盾被强化,这反映出西方利用教派分歧来组建反伊朗的地区联盟这一战略。”(49) 中东变局发生几年来,沙特等地区国家更是极力建构教派冲突的话语体系,不断放大了伊朗什叶派的地区影响。例如,沙特不断强调伊朗支持巴林、叙利亚和也门的什叶派,但迄今为止并无证据表明伊朗介入了巴林和也门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有一定的“阴谋论”色彩,其重要图谋是以抵制伊朗什叶派扩张为由防范国内什叶派骚乱,同时为介入巴林和也门事务提供合法性。而伊朗和叙利亚结盟的根本因素也并非宗教和教派因素,因为二者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极大差异,伊朗为坚持伊斯兰主义的什叶派神权,而叙利亚政权尽管为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执政,但其意识形态是复兴党的世俗民族主义,可见二者结盟的根本基础是利益需要,而非教派因素。因此,从本质上看,无论是叙利亚危机、也门危机还是伊拉克乱局中的教派冲突,其地缘政治特征都远远超过宗教特征。 当前,中国学界和媒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夸大教派矛盾的倾向,这不利于对中东问题本质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过分强调教派矛盾和冲突不利于中国中东政策的宣示和宣传。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曾3次行使否决权,当时被部分阿拉伯舆论解读为中国支持什叶派,在国内甚至也有舆论将中国、俄罗斯划入支持什叶派的阵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误解。因为中国的政策并未从教派出发,而是以反对武力干涉、主张政治解决作为政策立足点。但是,如果中国舆论过分强调教派矛盾,无疑会让外界对中国的中东研究和中东政策产生误解。因此,围绕中东的教派问题,无论是中国学界还是舆论界,都要在研究层面做到历史、客观,在舆论宣传层面做到保持清醒,避免人云亦云。 ①Geneive Abdo,"The New Sectarianism:The Arab Uprisings and the Rebirth of the Shi'a-Sunni Divide",The 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at Brookings,Analysis Paper,No.29,April 2013,p.2. ②Evangelos Venetis,"The Struggle between Turkey and Saudi Arabia for the Leadership of Sunni Islam",Athens:Hellenic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and Foreign Policy,Working Paper,No 39,February 2014,p.3. ③刘中民:《勿用教派冲突简单概括中东问题》,载《环球时报》2015年4月21日。 ④Toby Matthiesen,Sectarian Gulf:Bahrain,Saudi Arabia,and the Arab Spring That Wasn't,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 xii-xiii ⑤Geneive Abdo,op.cit.,p.14. ⑥“伊斯兰和谐民族协会”(Al-Wefaq National Islamic Society),简称“和谐协会”(Al-Wefaq),是巴林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在巴林议会中拥有近一半席位,阿里·萨尔曼(Ali Salman)为该协会秘书长。2011年2月27日,“和谐协会”18名议员向议会提交集体辞呈,抗议王室对支持改革的巴林抗议者采取武力镇压的行为。 ⑦Toby Matthiesen,op.cit.,pp.43-49. ⑧Geneive Abdo,op.cit.,p 14. ⑨Ibid,pp.18,23-24. ⑩李福泉:《中东伊斯兰教派矛盾的演进与影响》,载《国际论坛》2014年第6期,第63页。 (11)吴冰冰:《中东伊斯兰教派矛盾的新变化》,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5期,第43页。 (12)Geneive Abdo,op.cit,p.24. (13)Ibid.,p.18. (14)Madawi al-Rasheed,"Sectarianism as Counter-Revolution:Saudi Responses to the Arab Spring",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Vol.11,Issue 3,December 2011,pp 514-515. (15)Toby Matthiesen,op.cit,p.73. (16)Madawi al-Rasheed,op.cit.,p.520. (17)2011年3月6日,沙特大穆夫提谢赫阿卜杜·阿齐兹签署法特瓦令,其中提到:“委员会在此重申,唯具有合法形式的改革和忠告才能带来福祉和避免邪恶,而非通过发表声明进行恐吓、挑起冲突和征集签名。……在沙特,不应以示威游行和其他引发动乱和分裂社会的形式和途径实现改革和忠告。从古至今,沙特的宗教学者都禁止和警告发生此类行为。委员会强调,本国禁止示威游行,避免造成破坏实现福祉的合法途径在于互进忠言(al-Munasahah)。”See "A Fatwa from the Council of Senior Scholars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Warning against Mass Demonstrations",Islamopediaonline,March 10,2011,http://islamopediaonline.org/fatwa/fatwa-council-senior-scholars-kingdom-saudi-arabia-warning-against-mass-demonstrations,2012-03-01. (18)"Hay' ah Kibar al-‘ulama' fi al-Su' udiyyah Tuharrim al-Muzaharat fi al-Bilad wa-Tuhaththir min al-' irtibatat al-Fikriyyah wal-Hizbiyyah al-Munharifah",Al-Sharq al-Awsat,March 7,2011; "Saudi Arabia Prints 1.5m Copies of Religious Edict Banning Protests",Guardian,March 29,2011. (19)Madawi al-Rasheed,op.cit,pp.521-522. (20)Ibid,pp.521-523. (21)Geneive Abdo,op.cit,p.4. (22)Ibid.,p.6. (23)Ibid.,p.4. (24)Greg R.Lawson,"A Thirty Years' War in the Middle East",The National Interest,April 16,2014,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irty-years-war-the-middle-east-10266,2014-12-30. (25)Toby Matthiesen,op.cit.,p.19. (26)Madawi al-Rasheed,op.cit,pp.513-526. (27)Ibid,p.521. (28)刘中民:《伊斯兰教与当代沙特外交》,载徐以骅:《宗教与美国社会》第9辑,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 (29)Daniel Byman,"Sectarianiam Afflicts the New Middle East",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Vol.56,No 1,2014,p.80. (30)Mehdi Khalaji,"Yemen's Zaidis:A Window for Iranian Influence",The Washington Institute,February 2,2015,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yemens-zaidis-a-window-for-iranian-influence,2015-03-11. (31)Daniel Byman,op.cit.,p.80. (32)"Uprisings in Bahrai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hiism or Sunnism:Leader",Mehr News,March 22,2011,quoted from Frederic M.Wehrey,Sectarian Politics in the Gulf:From the Iraq War to the Arab Uprising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p.39. (33)Michael Scott Doran,"The Heirs of Nasser:Who Will Benefit from the Second Arab Revolution",Foreign Affairs,Vol.90,No 3,May/June 2011,p.24. (34)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Popular Protest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VI):The Syrian People's Slow-motion Revolution",Middle East/North Africa Report,No 108,July 6,2011,p.8. (35)Emile Hokayem,Syria's Uprising and the Fracturing of the Levant,Abingdon:Routledge for the IISS,2013,p.9. (36)See http://twitter.com/mohamdalbarrak,2015-01-20. (37)陈天社:《埃及的政治与社会转型》,载刘中民、朱威烈:《中东地区发展报告》(2013年卷),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138页。 (38)Geneive Abdo,"Sectarianism Spreads to Egypt",Brookings Institution,April 12,2013,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3/04/12-egypt-sectarianism-abdo,2013-04-15. (39)昝涛:《“土耳其模式”之困》,载《东方早报》2013年7月23日。 (40)"Egypt Expels Turkish Ambassador",BBC,November 23,2013,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25066115,2013-11-24. (41)Sajjad Malik,"Politics of Sec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China org.cn,March 12,2015,http://www.china.org.cn/opinion/2015-03/12/content_35023992.htm,2015-03-14. (42)"Mani ‘al-Mani':Al-Takfir Hadaf Ra' is li-Tanzim Da‘esh...’ajbaruni‘ala Ittiba,Manhajihim",Ajel,Feburary 9,2015,http://www.ajel.sa/local/1520356,2015-03-10. (43)袭击事件发生后,“伊斯兰国”组织迅速通过推特宣称对事件负责,但“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却声称其从不攻击清真寺,以此与“伊斯兰国”组织划清界限。 (44)Alexis Knutsen,"ISIS in Yemen:Fueling the Sectarian Fire,Critical Threats",March 20,2015,http://www.criticalthreatsorg/yemen/knutsen-isis-yemen-fueling-sectarian-fire-march-20-2015,2015-03-22. (45)J.M.Berger and Jonathon Morga,"The ISIS Twitter Census:Defining and Describing the Population of ISIS Supporters on Twitter",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March 2015,p.9. (46)以下观点详见刘中民:《勿用教派冲突简单概括中东问题》,载《环球时报》2015年4月21日。 (47)Frederic M.Wehrey,op.cit.,p.207. (48)Bayan Perazzo,"Propaganda & Sectarianism:How the Saudi Government Stifles the Truth about Qatif",Muftah,January 4,2013,http://muftahorg/propaganda-sectarianism-how-the-saudi-government-stifles-the-truth-about-qatif,2015-01-05. (49)Shireen Hunter,"Sunni-Shia Tensions Are More about Politics,Power and Privilege than Theology",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at Georgetown Washington,http://acmcu.georgetown edu/sunni-shia-tensions,2015-06-01.标签:逊尼派论文; 什叶派论文; 沙特论文; 中东历史论文; 叙利亚危机论文; 土耳其总统论文; 叙利亚的局势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中东论文; 伊朗革命论文; 叙利亚反对派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伊朗政治论文; 伊朗经济论文; 伊朗石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