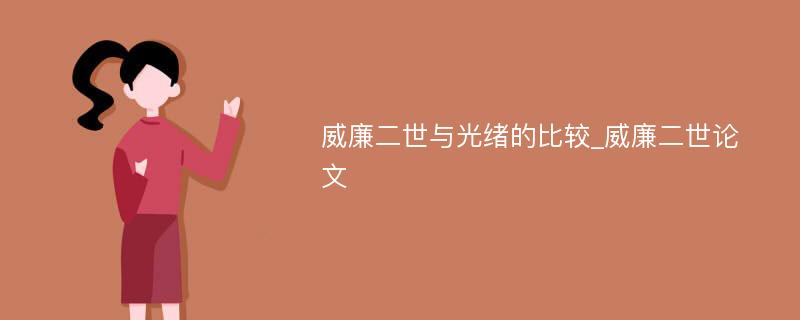
威廉二世与光绪皇帝之试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光绪论文,威廉论文,二世论文,皇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1859—1941)是有五百年历史的霍亨索伦家族的最后一位君主,(注:威廉二世(Wilhelm Ⅱ,1859—1941),普鲁士国王,德意志第二帝国末代皇帝。参见朱庭光主编《世界历史名人谱》近代卷Ⅴ第29—32页。)同时也是德国帝制的最后一名皇帝,自他以后,德国迈入了共和时代。
爱新觉罗·溥仪,是在襁褓之中便被实际掌握朝政大权的慈禧皇太后抱入宫中,以便于她继续操纵权柄,很快又因为共和革命被赶出了皇宫,所以笔者认为在严格意义上讲他并不能算是中国最后一位亲政的皇帝,(注: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清朝的末代皇帝,史称宣统帝。参见《清代皇帝传略》第407—431页。)真正意义上亲政的末代皇帝应该是爱新觉罗·载湉——光绪皇帝(1871—1908)。(注:参见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第3页。)比较这两个末世皇帝, 能给我们理解这两个老大帝国带来很多新的启示。
1、成长的环境——个人背景与心理因素的分析
我们在分析帝王的时候不得不花相当的篇幅来探讨皇帝本身的成长轨迹,因为他的成长过程和所受到的影响将对他未来统治帝国产生莫大的潜意识中的作用,即由君主统治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君主本身的素质所决定的,而这个素质的培养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极其没有规律可以把握的。
威廉二世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物,更是一个极富自我特色的君主,他声称:“我只知道有两个政治派别,即支持我的派别和反对我的派别”。作为一个皇帝而如此不知“刚柔相济”之道,实在令人感到遗憾。威廉二世作为皇帝,他需要的是绝对的服从和他的个人意志的彻底贯彻,这就必然决定了留在他身边的只能是一些“阿谀奉迎者和造谣中伤者”,这使他很难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的思考和洞察力以及知人之明,甚至做事常常失去作为君主必要的分寸和灵活。对于威廉二世这样一个本身就有许多身体上的缺陷的青年君王来说更是如此。
威廉二世身体上有先天的缺陷,主要是他的左臂患有先天性的不治之症,很小的时候就有左腿、左耳和左侧头痛,(注:[德]阿米尔著,李世隆等译《德意志皇帝列传》第510页。 )后来虽然他凭借自己的毅力和勇气通过锻炼克服了这些疾患,但这些毛病仍然使他一生受困。37岁时,他甚至明显出现过“非常忧郁的情绪”,致使精神失常。(注:[德]阿米尔著,李世隆等译《德意志皇帝列传》,第509页。 )也许正因为这些客观上的残疾,造成了威廉二世心理上迥异于常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弗里德里希·瑙曼对他自相矛盾的性格做了比较精彩的概括:舞台式的铺张华丽与自然本色的朴实无华,政治上的想入非非与健康的正常理智,讨人喜欢的正直与无视真理,无微不至的关怀与不得体的举止,绝对的慷慨与过度的敏感,温暖与冷酷,怯懦与傲慢,尤其是没完没了不着边际的咒骂!(注:[德]阿米尔著,李世隆等译《德意志皇帝列传》,第511页。 )这就是威廉二世的个人风格和性格特色。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绝不是一个可以按照常理度之的人。
光绪皇帝也是一样,他的处境可能比威廉二世更加不如。光绪帝载湉4岁即位,在位34年,终年仅38岁,在位时间比威廉二世还长。光绪帝之所以继承清王朝的皇位,一方面在于他的血缘关系,他的父亲奕譞是道光帝晏宁的第七子,其母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另一方面当权的慈禧皇太后不愿意交出大权,因而扶起这么个冲龄儿童,以便于她理直气壮地继续垂帘听政。慈禧热衷的只在于权力,出于对同治之死的总结,她虽然也努力去沟通与小光绪的感情,但由于她为人苛厉,动辄对小光绪以白眼、训斥,乃至罚跪,没有正常的母爱。
在这种环境下,光绪的性格会是怎样的呢?赵良先生在其大作《恋尸者阴影下的萎缩生灵——光绪》中对此有一段颇为精辟的论述:在威权笼罩的封闭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天天承受一个神秘莫测暴君的斥责和处罚,性格发展一般有两个走向:懦弱与残忍。……而大多数孩子则在威权下形成懦弱的性格。光绪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那个总是和罚跪、鞭笞、训斥联系在一起的冷面女人的高压下,变得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惴惴不安,大有不堪消受之势。(注:赵良著《天子的隐秘——七位中国帝王的心理传记》,第275—276页。)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作为皇帝,他连选择自己皇后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个儿皇帝,慈禧强迫光绪选择了自己的侄女——未来的隆裕皇后。赵良先生揭示了这一事件对未来光绪政治道路的关系:一个早年有伟大抱负,渴望成为“中兴圣主”的孩子,在确立自我的青少年时代各方面受挫,尤其是个人生活方面的挫折——没有获得心爱的女人,缺乏爱情的滋润,犹如一股推动力,抵制了纷扬的欲望,把他置入实现早年理想的单一努力之中,作为对自我损失的挽救。(注:赵良著《天子的隐秘——七位中国帝王的心理传记》,第294页。)
相比之下,不难发现威廉二世与光绪皇帝都是有些心理疾病的人物,威廉二世更多的是由身体残疾造成的一种愤世嫉俗或者偏执的心理疾病;而光绪皇帝则是自幼年起心理就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和打击,心理疾病的种子早就埋下了。这对于他们走上权力顶峰是极其不利的,对未来国家的政治事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2、机遇的把握与理想的实现——时代背景的全景式分析
从个人身世的小背景中走出来,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大时代背景。因为他们都是皇帝,在他们身上寄托的不仅是个人的家庭的前途,更有国家的未来和命运。对于他们来说,因为血缘的关系和其它一些不可明言的政治因素,走上皇位并没有太多的周折,似乎顺理成章的成分更多些,但等待他们的并不是一帆风顺。
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运筹帷幄之下,普鲁士在1871年成功地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将奥地利排除在德意志国家之外,实现了全德意志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普鲁士国王威廉成为德意志皇帝。接着,俾斯麦以其务实政策,继续大力发展经济。19世纪后半期在德国完成的经济转变,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德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现代高效率的工业国家。俾斯麦在19世纪70—80年代期间,大力推进在新技术革命基础上的工业革命,为德国成为经济政治强国并进而挑战美国霸主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切,就是先辈留给威廉二世的宝贵财富,政治上的统一、技术和科学的进步以及在生产力上的运用、德法战争胜利所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等等。也正是这些有利的因素和条件,为威廉二世即将要提出的野心勃勃的“世界政策”提供足够的底气。
从国际上来说,至少在欧洲,德国的强大地位一时之间不容挑战。威廉二世的时代,德国已经成为欧洲的工业强国。经济发展必然要求寻求新的原料来源、外销工业产品的出路乃至资本投放的新途径,换言之,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已经使得彼此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抢占市场和瓜分殖民地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在19世纪末期,由于俾斯麦审慎稳重的大陆政策,德国以保求其大陆安全为第一要务,所以德国殖民地在当时不到英国的10%,这与雄心勃勃的威廉二世的胃口是极不相符的,从“大陆政策”转到“世界政策”,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已成为威廉二世的政策重心。
从个人角度审查,威廉二世很可能正是那种由于个人状况的不完美,便希望通过其它途径来转移视线并摆脱困扰的君主。企图从政治上获得巨大成功和建树丰功伟绩以补偿个人其它不足的考虑,是符合心理学的原理和威廉二世本人的性格特点的。
中国则不同,虽然当时离林则徐等人“放眼向洋看世界”已经有了几十个年头,洋务运动以“自强”为目的也进行了不少时候,但效果似乎并不显著。李鸿章辛辛苦苦练以为国之栋梁的北洋海军竟然不堪一击,在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之后的战争中奉行不主动出击原则,最终导致全军覆没,朝野对此一片哗然,举子们通过“公车上书”请求“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注:史仲文主编《中国近代名人思想库——变革者言》第193页。)
内忧外患,国家将濒之于亡,光绪帝自幼所接受的那套成为“有道明君”的传统儒家教育开始产生作用。他对个人生活已经绝望,只有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才能弥补他的心理的创伤。而当时的大背景又确实给他提供了这个奋发图强的机会。因为即使保守如慈禧也并不反对变法图强,她曾对光绪表示:实行变法乃是我一贯的主张,早在同治初年,就曾采纳曾国藩的建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这一切无不是为了谋求国家的富强。(注:赵良著《天子的隐秘——七位中国帝王的心理传记》第295页。)得到了慈禧的承诺, 光绪终于有了一次实现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机会了。
3、权力结构的平衡稳定架——实际权力的重要性
光绪帝很不幸,作为皇帝,虽然他在位34年,但没有一天可以说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虽然按照道理他贵为君王,但因为他的上面还有更高的太上皇——慈禧皇太后,他虽然以选择慈禧钦点的皇后为代价获得了“亲政”的权力,但事实上慈禧的阴影从未退出朝廷的殿堂,当时的政治权力结构基本是这样的。所谓的“帝党”、“后党”之分,其实并不尽然。至少在光绪自己,没有想到过结党的概念。但当时确实有一批围绕在光绪周围的政治势力,他们的代表人物除了光绪的师傅翁同龢之外,还有汪鸣銮、志锐、文廷式、李盛铎等台馆诸臣,这些言官敢于对抗慈禧的宠臣,做事也比较大胆,渐渐引起了慈禧的猜忌。而后党骨干则包括主持清廷日常政务的庆亲王奕(匡力)、手握军权的直隶总督荣禄等人。慈禧通过自己的亲信牢牢掌握了军政大权,根本就不把光绪放在眼里,对光绪的变法行为也只认做孩子的玩耍而已,只要她想收回这只暂时放飞的风筝,她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收回来,事实证明,慈禧确实是牢牢地掌控着这场斗争的主动权。在权力场中,光绪根本就没有任何和慈禧斗争的资本。
威廉二世则不然,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皇帝,有名也有实。在他最初登上帝位的时候,他也曾面临权力的挑战。当时的德国宰相是完成德意志第二帝国统一大业、威望极高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威廉二世为了解决“谁有大权在德意志内外政策上作主”的问题,毫不客气地开展了驱逐俾斯麦的一系列活动。他首先建立了一个私人小圈子,依仗皇帝特权,不把俾斯麦放在眼里,事实上形成一个“私人内阁”,核心人物有大工业家斯土姆、枢密顾问和外交大臣霍尔斯泰因、宫廷大臣奥伊伦布尔、总参谋长瓦德西等;之后不惜在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上同时与俾斯麦正面发生冲突,激化双方矛盾。1890年3月18日, 俾斯麦被迫下台,结束了德国历史上颇为辉煌的长达28年之久的俾斯麦时代。这也标志着新的威廉时代的开端。
对二者在权力场中的实力和权力获取的手段与初衷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其差异是较大的。威廉二世完全是主动的,一切以我为中心的,以获取全部权力为目的而不惜一切代价。光绪则不然,他所要求的不是绝对的权力,而仅仅是从慈禧(绝对权力拥有者)那里获得部分的权力——变革的权力,他始终没有设想过作为皇帝自己应获得绝对权力,而他获取权力的方式也是可笑的,只是乞怜式的获得慈禧的一些施舍。最后的结果当然也不一样,有了绝对的权力,威廉二世可以毫不逆转地执行自己的顽强意志,哪怕这个决策是错误的;光绪则随时都可能被人收回放飞风筝的线端,他的理想随时都可能因为慈禧的好恶化为泡影。
4、“戊戌变法”与“世界政策”
光绪作为一个皇帝最值得书一笔的就是“戊戌变法”,虽然“戊戌变法”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毕竟他是一次奋勇搏击,向旧的封建势力,同时也是光绪帝一次与自己的软弱个性的斗争,虽然失败了,虽然这种试验在他34年的皇帝生涯中只有百天的时间,但毕竟它是一个标志,是一个不甘败落、挽救衰亡的象征。这至少表明光绪还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年轻皇帝。
威廉二世则是雄心勃勃,他所提出的“世界政策”,美其名曰是争取德意志人的“生存空间”,其实明明白白就是一份强盗式的宣言书。这一点,当时的德国宰相兼普鲁士首相比洛(注:比洛(Bernhard von Buelow, 1849—1929),在威廉二世时代任德国宰相兼普鲁士首相,著有《德意志帝国》一书。 参见丁建弘著《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第445页。)在一次国会的演说中作了再好不过的解释,他认为:德国公民离开德国,是因为没有他们生存的空间。所以德国需要成为一个殖民帝国,并要有一支海军来保卫它。威廉二世对英国作家休斯顿·斯图瓦特·张伯伦的著作《十九世纪的基础》很感兴趣,这部书从横跨欧洲大陆的神圣罗马帝国兴起展开,以日耳曼民族在欧洲大陆的九个世纪的历史为主导线索,展示了日耳曼民族在军事、科技、经济和文化上的成就和影响,最终得出了一个颇为荒谬的结论:日耳曼民族是人类历史上的“优秀人种”。这种理论进一步刺激了威廉二世狂妄的“大日耳曼民族神圣”和“世界帝国”的梦想。
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不仅符合德国军国主义者的胃口,更博得了以斯土姆为代表的大批资产阶级工业巨头们的赞赏,因为当时德国经济飞速发展,呈跳跃式姿态,从1870年—1913年,德国工业总产值增加4.6倍,在世界上所占比重从13%增加为16%,电子、 化工等工业技术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钢铁和军火工业均位居欧洲前列,国家总体经济能力仅次于美国排世界第二位。国内经济的发展急需开辟海外市场。
应该说,“戊戌变法”与“世界政策”是两个皇帝的重大决策,不幸的是,这两个皇帝的代表作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宣告了他们的失败。
戊戌变法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指的是从1889年6月11日到9月21日慈禧及其后党分子发动政变止,在此期间,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法令。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宣布“亲政”, 下令搜捕维新派,废除变法法令。变法重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6人被杀, 史称“戊戌六君子”。戊戌变法从开始到失败,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总的来说,戊戌变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也是中国的皇权统治的开明人物与知识分子阶层救亡图存的大胆尝试。光绪皇帝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他不掌握封建权力的运作程序,他以为凭着皇帝的诏书就可以雷厉风行地尽变全国之法,各级官僚对他的木偶人地位早就心中有数,全都在看慈禧的颜色行事。他所依仗的康有为等人,虽有一腔变革之心、图强之情,但更多的属于书生式的纸上谈兵,一到关键时刻,根本就不能组织有效的力量来和慈禧集团抗衡,所以失败应在预料之中。
从客观上来讲,光绪等人所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利益虽代表了历史进步的趋势,但中国当时的国情显然是封建专制的势力仍占上风,资产阶级的整体力量还很弱,没有形成进行大规模变革的有力的社会基础。历史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不具备挽救中国的力量。光绪要实现自己贤君政治的方案也从此灰飞烟灭,孔祥吉先生在其大作《光绪帝载湉》中这样描写光绪的死亡:政敌的陷害,疾病的折磨,和一些目前人们也许还尚未明了的原因,使颇想有些作为的光绪帝在慈禧死去的前一天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人世。人们说,紫禁城上空的一颗希望之星陨落了。( 注:孔祥吉《光绪帝载湉》, 载左步清主编《清代皇帝传略》,第406页。)毕竟, 光绪帝代表了末世的清王朝想振作崛起的尝试,也是中华精神中“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一个注脚。其行虽败,其气犹存。
与光绪帝手中无权相比,威廉二世驱逐俾斯麦之后,获得了统治德国的绝对权力,同时也将德国驱赶上了世界大战的战车。这是威廉二世推行其“世界政策”的必然结果,正如丁建弘先生在《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爆发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扩张贪欲,已变成了争霸欧洲和世界的不可遏止的推动力,而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的体现者皇帝和总参谋部,恰恰给予这种争霸以武力保证。(注:丁建弘等著《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第468页。)
事实也是如此:1941年6月, 当其盟国奥匈帝国的皇储弗朗茨·菲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秘密的民族主义足赤的成员刺杀后,威廉二世就迫不及待地利用这次机会挑动了战争。在德国支持下,奥匈帝国于1914年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德、俄、法、 英等国相继参战。交战双方形成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和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全面爆发。1918年,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威廉二世匆忙逃亡国外,德意志第二帝国灭亡。
我们不妨来试看一下这两个君主的代表作,为什么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呢?
首先是战略决策的制定与正确性。应当指出,戊戌变法有其存在的理性基础,虽然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尚远不够强大,但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是历史的必然。从大的方面来说,变法之策是正确的。威廉二世则不然,他所制定的“世界政策”,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吻合国内大资产阶级寻求国外市场的需要和利益,但其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争霸世界,决策的非正义性决定了其失败的必然性。且忽略了德国的地缘政治背景,多方树敌,后来进一步陷入两线作战,焉有不败之理?
其次是对于决策的贯彻。由于光绪的幼稚以及中国政策运作的复杂性,戊戌变法的正确决策基本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诏书虽然写得气势磅礴、鼓舞人心,但那些老谋深算的封疆大吏们根本就没放在心上,更多的是将其束之高阁,静候“老佛爷”的懿旨。而威廉二世所拥有的绝对权力以及专制作风,使其错误的“世界政策”能够在全德国雷厉风行地得到贯彻,当一次大战爆发后,“除了极少数和平主义者外,全体德国人都一致支持帝国政府。”(注:丁建弘等著《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第470页。)
其三,透过决策本身看两国文化的传承影响。一方面,重要决策的做出当然与其大背景不能分开,但另一方面,决策本身的正确与否和决策者本身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关系。而决策者的思维方式更多地受到本国文化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内圣外王”的儒家那一套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光绪的根本出发点还在于当一个儒家式贤君明主;德国文化精神则是浮士德式的积极进取、永不满足型,从查理大帝(注: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法兰克国王和罗马人皇帝, 公元8—9世纪之交西欧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参见朱庭光主编《世界历史名人谱》古代卷Ⅴ第92—97页。)开始到腓特烈一世(注: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Ⅰ,1123—1190),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参见朱庭光主编《世界历史名人谱》古代卷Ⅲ第225—229页。)、弗里德里希大王(注:弗里德里希大王(FriedrichⅡ,1712—1786), 普鲁士国王,又称弗里德里希二世(或腓特烈大帝),18世纪欧洲一位颇有影响的君主。参见朱庭光主编《世界历史名人谱》近代卷Ⅴ第136—137页。)都是以战争为手段,所以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也有着极大的胃口,要称霸世界。
5、余响未绝——帝制解体对民族前途的深远影响
这里所要讨论是两个皇帝作为皇帝的共性,即所谓的“末代皇帝”头衔。既然是末代,就意味着封建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新时代,首先是“共和”的概念。
1918年11月4日,以基尔港水兵起义为导火索, 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威廉二世仓惶出逃荷兰,霍亨索伦王朝结束,之后建立了德国历史上的民主共和国“魏玛共和国”。
中国也是一样,1911年爆发的武昌起义赢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赢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推翻了象征着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清王朝。随即中国第一个共和政府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建立。
光绪与威廉二世虽然主观上都想通过自己的政治“杰作”来创新自己的政治事业,但在客观上却加速了帝制的解体过程。光绪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徒有救国鼎新之抱负,却受制于自己权力欲望极强的姨妈。维新失败,固然有种种客观因素,但他个人意志薄弱、不敢抗争、不善斗争,虽有图强之心,却无挽狂澜之力。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中国的民众更加认清了清政府的本来面目,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义无反顾地举起了起义大旗,从客观上来说,维新失败加速了清政府的败亡,加快了由封建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过渡进程;而威廉二世则是自掘坟墓,他刚愎自用,轻易地就改变了俾斯麦的内外政策,尤其是将俾斯麦精心制定的“大陆政策”一变而为“世界政策”,缺乏必要的过渡,也不符合稳定的长期的德国利益。丁建弘先生称:“这个时代整个德国的特点,是光辉灿烂的物质繁荣和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的恶性发展。”(注:丁建弘等著《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第444页。 )中德两国都有一句谚语,叫做“玩火者必自焚”(Wer Wind saet,wird Sturm ernten),威廉二世是自食其果。
威廉二世与光绪,一个意志坚强,一个意志薄弱;一个在地球西方一个在世界东部;一个要称霸世界,一个要变法图强;一个独断专行,一个手无寸权。但他们却殊途同归,在为本国帝制解体的进程中做出了相当的“贡献”,虽然他们主观上可能正是为了维护这种君主政体。而帝制的解体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意义重大。君主制度用黄宗羲的话来说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注:黄宗羲《原君》,载毕唐书、陶继新主编《中华名人修身治家宝典》第683 页。)民主共和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进步,它使民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在政治上、思想上获得解放。
从客观上加速中德两国人民步入民主共和制度的进程,是威廉二世和光绪皇帝的共通之处,不管他们主观思想如何,这一点对未来两国社会和民族国家的发展是影响深远的。
标签:威廉二世论文; 光绪论文; 俾斯麦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德国皇帝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历史论文; 慈禧论文; 戊戌变法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启蒙运动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一战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