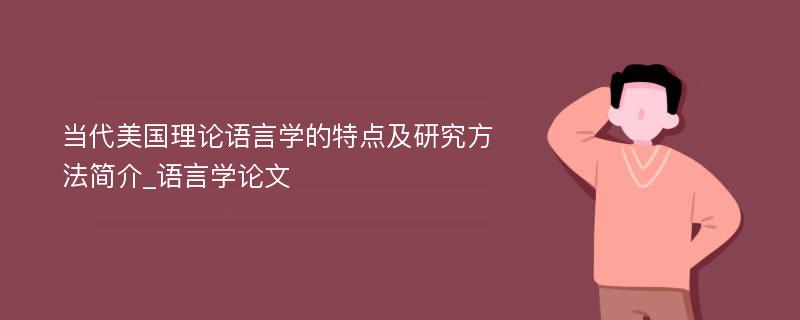
简述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的特征及研究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美国论文,当代论文,特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引言
近四十年间在美国及西欧相继出现了许多语言学理论,生成语法、概括性短语结构语法(现已演变为“中心词短语结构语法”(Head-Driven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格语法、功能语法、关系语法、词项功能语法等理论模型。按解释性语言学和描写性语言学的分类,这些语言学理论基本上都属于解释性语言理论,或称理论语言学。本文将从基础、对象、性质、目标、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等六个方面对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的特征进行简要的讨论。
1.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的基础
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是哲学上的认识论。无论是自己进行语言研究,还是评论别人的语言学理论,搞清楚语言研究的认识论背景是进行语言学评论的前提,也就是先要搞清语言知识和能力〔1 〕是什么和如何获得的问题。按照西方哲学认识论传统,Chomsky 之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认识论基础是典型的经验主义和行为主义。这种认识论思想在语言研究上的表现有三:(一)语言是用于交际的一套符号系统,语言知识就是关于这套符号系统的知识,会讲某种语言就是会使用这种语言的符号系统;(二)作为语言的符号系统没有限定,就是说什么样的符号系统可以成为人类语言是没有限定的,是在没有任何限定的情况下“约定俗成”的,人们约定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三)如果把一种语言看成是有许许多多句子组成的话,那么一个孩子学会使用这种语言所要做的只是听父母讲一句,记一句〔2〕,父母讲多少就记多少, 而后就会用多少。在这种行为主义认识论思想的左右下,结构主义语言学便自然会否认认识主体自身在获得语言知识和能力过程中的作用,把认识主体排斥在语言研究范围之外,把人脑在获得语言知识能力的能动〔3 〕作用降低到消极、被动甚至是毫无作用的地位。Chomsky 认为行为主义的认识论不对,语言学研究方向应该修正,理由主要有下面五条:(一)行为主义认识论不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不能回答为什么只有人才能说话,而动物(比如一条狗)无论怎样刺激训练也不能说话,也不能掌握人类语言这套符号系统。(二)语言中有很多东西是“学”不来的(unlearnable)。比如, 从没有人教过孩子说“爸爸很喜欢他”中的“他”和主语“爸爸”不可同指一个人,可孩子可无师自通,从不会听错,用错。(三)儿童后来能说出来的句子不都是听到过的,表现出一种语言能力上的“创造性”。(四)儿童学习语言不必依靠成人的“有意识的训练”,没有所谓“负面根据”,即父母从不告诉孩子“不应该怎样说”,从不给孩子纠正什么错误,即使好心的父母为孩子纠正什么“错误”,孩子似乎不太理睬,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某种既定路线坚持在父母看来是错误的说法,直至某个时期,孩子自然而然地讲出和成人相仿的话来。(五)孩子听到的,父母所讲的话都是杂乱无章的,不像外语教材那样经过分析编排过那样。儿童甲听到的话和儿童乙听到的话从内容安排上可能相差很远,学习时间长短也可能很不相同,但他们最后形成的语言能力,所持有的语法是一样的,不然他们之间会发生交际上的困难。出于上面这些考虑,Chomsky改造了笛卡尔的认识论思想〔4〕,提出了著名的“心智主义”(mentalism )认识论观和“语言获得机制”(LAD)〔5〕。“心智主义”认识论在美国语言研究中的影响是巨大的,的确在语言研究和认知研究领域中引起了一场科学革命,成为美国当代语言学理论的先导。之所以是一场科学革命,是因为心智主义的语言观大大地动摇了美国传统语言学理论的认识论基础,从而为语言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确立了一个新的目标,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表述形式。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是研究人脑的认知系统,新的目标是为人脑的认知系统(包括语言系统)提供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方法是演绎的模块式程序方法,理论表述是形式化的。所有这些变化不能不说都是从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引起的,集中地表现在“普遍语法”(UG)思想上。普遍语法基本内容是这样的:人脑按人类遗传规定生下来就呈现出一种狗脑不会呈现出的生物-生理状态, 称作“初始态”(initial state), 这种初始态的形式属性称作“普遍语法”或“语言获得机制”。大脑在处于初始态时,孩子并不会说话,随大脑继续发育成长,初始态进入“稳定态”,普遍语法变成个别语法,这时孩子才具有使用一种具体语言的能力。这个从初始态到稳定态,从普遍语法到个别语法的过程是一个生物—生理发育变化的过程。人脑的这个发育变化、普遍语法演变成具体语法的过程不是任意的,它首先受人脑初始态或普遍语法的制约,就是说孩子将来讲出什么样的话来,沿着什么样的“学习”路线学会说话都是有一定之规的。这个发育变化过程离不开外界的条件〔6〕,这就是语言环境。 不过孩子在某个语言环境中所听到的语言材料(输入)是未曾被整理加工过的、杂乱无章的东西,孩子必须对这些原始的语言材料加工处理,进行加工处理所依据的是大脑天生的固有结构,不同的孩子,不同的语言环境,加工处理的结果是一样的。因此,人脑的初始态不是被动的“听、记”句子,而是能动地分析、解释和处理听到的语言信息,最后进入到稳定态。美国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大多数都相信人脑遗传属性对语言知识能力获得的内因性作用,相信Chomsky意义上的普遍语法的存在。 因此美国语言学界的主要研究力量投注于对普遍语法的寻找上。但在人脑的与语言相关联的特定结构是什么,普遍语法有哪些内容和是什么的问题上,各有各的看法,也就出现了不同的理论模型。
2.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的对象
以行为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对象是语言本身,是语言事实本身,是句子的各个成分(语音的,结构的,词汇的等)。要回答的是作为符号系统的具体语言是什么样子的,语言事实有哪些、是什么样子。研究对象是事实本身。以“心智主义”为认识论基础的美国当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停留在语言事实上,不停留在回答语言事实(如句子)是什么样的问题上,而是要研究语言事实的成因(etiology),回答语言为什么只能是这个样子而不会是那个样子,句子为什么只能这样说,不能那样说,只能这样理解,而不能那样理解。回答这些问题时又同人脑的结构属性联系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研究的不是语言,而是人脑和人脑的语言系统。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如果问一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说某人会讲汉语是什么意思,他可能会告诉你说“这个人会使用汉语这套符号系统”。如果问一位当代语言学家,尤其是生成语法学家,他会说这个会汉语的人的大脑里形成了一个象计算机程序一样的系统,出现了一部“汉语语法”。汉语已经“内化”(internalized)成了人脑的一个部分,体现为一种人脑的生理结构状态。不会讲汉语的人的大脑工作状态和会讲汉语的人的大脑工作状态是不同的,不会讲汉语的人的脑里尚未出现那部“汉语语法”,而会讲汉语的人的大脑里出现了那部“汉语语法”。所以,当代语言学家会说他们在研究会讲话的人讲话时大脑是怎样工作的,从不会说话到会说话大脑发生什么变化,那部“汉语语法”是怎样在人脑中出现的,那部人脑里的“汉语语法”又是什么样子的。当然人脑里的这部“汉语语法”绝不会是我们在书店里买到的那本“汉语语法”。
(二)一个人的大脑里出现了那部“汉语语法”就等于说那个人有了说汉语的能力。即使这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即他没有使用汉语,没有表现为一种语言的运用时,这个人的语言能力还在,因为那部“汉语语法”还在他的大脑里。如果,这个人大脑受到损害或发生病变,而可巧伤害的部分又是那部“汉语语法”,那么这个人便丧失了语言能力,没有能力也就没有运用可言。能力是本源的,运用是表征。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区分是两个除了普遍语法思想之外在世界语言学界影响最大的理论概念,得到极其广泛的运用和发挥。有了这种简单的区分,可以说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除了有语言运用外,更重要的要研究语言能力,研究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关系。〔7〕
(三)人脑的语言系统又是人脑整个认知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语言系统和认知系统中的其他子系统(如发音系统,语用系统,感知系统等〔8〕)存在着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关系。所以, 美国当代语言学家大多数都把语言系统放在整个认知系统中研究,研究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关系。但是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研究认知系统中所有的子系统,而是各有各的侧重。
(四)人的语言知识和能力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这就是它的直觉性。几乎所有的语言行为都是在下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有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味道。比如说,人人都知道“这个人,我不认识”是一句汉语,而“一个人,我不认识”不是(“一”字轻读)。如果问为什么,恐怕谁都说不出道理来。当代语言学十分重视对语言直觉的研究,研究语言直觉的内容,为语言直觉提供一个清晰的系统的描述。
(五)传统语法研究具体语言的具体特征,研究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的差异,认为任何一种符号系统都可以成为人类语言,否认什么可以成为人类语言是有限制(constraint)的。当代语言学普遍承认人类语言有一定限制,因而寻找这些限制便成为当代语言学家们共同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而这些限制又和人脑的特定结构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总的说来,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要比传统语言理论研究的对象大得多、深得多。
3.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的性质、目标和表述形式
既然当代语言学理论圈定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那么它的具体的目标又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先从语言理论的性质讲起。在当代语言研究中有一个很常见的分野,这就是从理论性质方面把语言理论分成描写性语言学(descriptive linguistics)和解释性语言学(explanatory linguistics)〔9〕。两者的差别集中到两点。第一, 在对语言事实和语感的态度上:描写性语言理论只描写语言事实不解释事实的成因,只依靠语感而不揭示、不表述语感的内容。解释性语言理论不停留在语言事实面前,不满足于对语言事实的描写,而进一步要揭示事实背后的成因以及人们说(听)话时所凭借的语感的内容。第二,传统语言理论对具体语言的具体事实做了很充分的描写,归纳概括出许多具体的描写性规则。但是,这些规则之间缺乏使用上的条件和顺序,规则与规则之间也没有联系,由规则构成的语法系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系统性和操作性。解释性语言理论中的概念,定义,规则是统一系统中的,都得对整个系统的总体任务负责,各个规则都有使用上的条件,规则与规则之间又有使用上的顺序,整个语法系统具有鲜明的操作性。大多数美国当代语言学理论都属于解释性的语言理论。解释性语言理论并不排斥对语言的事实性描写,只是不拘泥于事实的描写上,在追求描写上的充分性(descriptive adequacy)的同时追求解释上的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
另外,从语言理论的表述上,语言理论也可以分成两类:形式化语言理论(formal linguistics)和非形式化语言理论(informal linguistics)。 前者具有自然科学中一切形式化系统的一般特征—— 缜密性(explicitness),后者的理论表述则以自然语言的形式为主。美国当代语言理论这两种表述都有,但形式化的理论似乎是绝大多数语言学家的最终追求。至于说,为什么都追求形式化语言理论,不能看成是为了计算机处理语言的应用,也不是为了搞机器翻译,更不是为了搞好外语教学,而首先是由其理论对象——人脑的语言器官的特殊属性所决定的。从语言理论性质上看,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属于解释性的形式化语言理论。不能用描写性理论和非形式化理论的标准来认识解释性的形式化理论。
理论性质上的解释性,理论表述上的形式化,而理论对象又是同人脑认知系统相联系的语言系统和普遍语法,为这个语言系统和普遍语法提供一个形式化的、解释性的理论系统就自然成为美国当代语言学理论的目标了。大多数理论语言学家都坚持这种形式化的信条,现在能做到多少就做多少,以能形式化的为起点逐步向外、向周边扩展。
4.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理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脑中的那个体现语言能力、主司语言行为的语言系统,而这个研究对象是人们“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个如何研究一种不能用直接甚至是间接的方法观察得到的东西的问题。这里我们不妨想一想语言研究之外的两个情景。第一个是物理学中的“原子”。原子的存在已是人们的常识,但是人们怎样感知它的存在却并不为人们的常识所知。实际上,任何人通过任何仪器、任何手段也不能象我们看见一个鸡蛋,观察到一个细胞那样“看见”一个原子。那么人们是怎样确认原子的存在的呢?首先,我们得有一个科学家们建立起来的关于原子属性的一个理论模型,这个模型是由许多有关原子物理属性的数据构成,而这些数据又是依据各种测定物理属性的仪表界定的,这就好象是一张关于什么是原子的图,当与原子反应堆相连的各种仪表显示出的数据同科学家们事先拟订好的理论模型中的相吻合时,我们在此时此刻便“看见”了原子。这就是说,人们是按照事先画好了的那张“原子图”找到原子的。其中颇有“按图索骥”的味道。〔10〕另一个例子是遗传基因模型。现在人们在电镜下可以真切地观察到DNA,但是仍然要靠孟德尔-莫根早年勾画出来那张“基因图”,那个他们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模型,离开这个模型,我们在电镜下看到的只不过是血肉模糊的一片。理论模型的作用和科学意义在所有学科领域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语言研究以研究人脑语言系统为目标,同样需要一个理论模型,一张关于人脑这个系统是什么样、怎样工作的图。不过这张图不是形象的图画,而是象几何、数学那样的由特定的概念、 符号、 规则、 公式、 算法等形式化的“构件”(formal objects)画出来的形式系统。
和任何科学研究一样,理论模型的建立不是任意的,无一例外都的是依据人们所感知到的事实。语言系统模型的建立靠语言事实〔11〕。但在一种具体语言中的语言事实(如句子)是无限多的,鲁迅作品中的句子,北京某四合院李奶奶讲的句子,古人讲过的句子,后来人将要讲的句子都是语言事实。不仅如此,任何一种语言中的句子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句子与句子之间有着一定联系,这也是事实,也是无限的。想要把一种语言中所有的句子及它们之间的联系都搜集起来,观察研究,而后再建立起一个系统模型,一没有可能,二也没有必要。在无限多的语言事实面前,在不可直接观察的人脑面前,经验的、实证的方法都无法应付,而只好采用一种可称为“系统模型演绎法”〔12〕的研究方法来解决。这种方法在语言研究中的运用首先表现在系统的模块性(modularity)上。其大体意思是这样的:
语言系统是由几个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都是由一些规则构成。各子系统之间表现为输入—输出的操作性关系,在每一个子系统内,规则都有使用上的条件,规则之间又有使用上的顺序等。这种结构称作语言系统的内模块模型。语言系统还是整个认知系统的子系统,因而有它的外模块结构关系,它与认知系统的其他系统之间也呈现为输入—输出的操作性关系。所以,要确立语言系统的模型首先得确定该系统的外模块关系,而这种外模块关系的确立依据的是数量极为有限的“相关事实”(theory-related facts )。 比如说, Chomsky的“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eriously”的这句著名的英文句子就被看成是可以确定语法系统与另一个称作“信念系统”或“语用系统”的认知子系统的外模块关系。根据这种外模块关系,我们便可以确定语法系统的总体任务,就是说作为一个同其他认知子系统相联的语法系统应该输出什么。比如说,生成语法学家及大多数句法学家们都认为应该输出关于所有可能句的语音描写式和语义描写式〔13〕。在语法系统的外模块关系上,美国当代语言学家之间似乎看法比较一致。但在语法系统的内模块结构关系的确认上则各家之间有很大的分歧,即使在生成语法内部,在统一理论模型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也有很大的差异。原因是,语言学家们都在不断地调整已有的语法内部结构,根据新的语言事实优化结构关系,在维持已有的解释上的充分性同时,扩大描写上的充分性。但不管如何调整,都不会改变整个系统的总任务。因此,如何确定语法系统的外模块关系和总任务对于语法系统的内模块结构有决定性的意义。总任务变了,完成总任务的各部门有多少及如何分工也就得跟着调整。这种系统模块演绎法表现在下面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巧上。
第一,对比研究方法(contrastive study)
对比研究方法是美国当代语言研究最著名的研究方法,在语言学的各个学科、各个方面都得到广泛的应用,有着很深刻的理论意义。概括的讲,对比法在使用上有两个要点:第一,对比是关于句子与非句子,可能与不可能,“符合语法的”或“造得好的”与“不符合语法”或“造得不好的”〔14〕等相对概念之间的对比,是关于“是”与“非”,“有”与“无”,“成立”与“不成立”等绝对概念的对比;第二,对比要在“最小差异对”(minimum pair)中进行,就是说对比的对象要满足“一切相同,只差一点”的条件,而不是任意差异都有可比性。在表述上,常用打星号*和不打星号来表示。
对比法是一种在无限的事实中寻找本质特征的可靠方法。由于语言事实的无限性,对比法便表现出其他方法不可代替的科学理论意义。比如说,我们想知道一种语言中的句子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到底有那些本质特征,句子的生成到底遵循哪些条件等,满足这种理论需要的一种传统的方法是把事实搜集起来,从所搜集到的事实中归纳、整理出一些概括性的规律来,这种方法虽不失其科学理论意义,但免不了要碰到这样一个经验性的问题,这就是,事实是无限多的,我们没有办法把事实全部都搜集起来供我们研究,我们能研究的只能是无限多的事实中的一部分。从无限中的一部分得出来的结论免不了会同从无限中的另一部分中得出来的结论相矛盾。旨在为建立一个可保证生成无限多事实的语言系统的当代理论语言学,似乎不能依赖穷举事实的“穷尽法”,也不能依赖“归纳法”。这里我们不免想起语言研究之外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想知道人的种属属性是什么,什么使人成为人,就和我们想知道句子的属性是什么,什么使句子成为句子一样。实现这个想法的方法有两种。第一个办法是把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一个一个都叫过来,就和我们把英语、汉语、斯瓦希里语、僮语等语言的句子1、句子2、句子3、句子4、……一个一个搜集起来一样。然后,对召集过来的人进行观察研究,归纳总结他们的共同属性。但是,我们无法从这些属性中找出使张三,也使李四、王五,赵六成为一个人的那些属性。但有一点我们是确定无疑的:使张三成为人的东西肯定也是使李四成为人的东西,也是使王五、赵六成为人的东西。因此,要想知道究竟什么东西使人成为人,就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对他们进行观察研究,把任何一个人叫来观察研究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具有人的属性。所以,我们就可以只把张三叫来就足够了。又怎样做才能知道什么东西使张三成为人,即什么东西使一个人成为一个人呢?方法就是我们这里说的对比法。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把张三和任何一个“非人”的实体(比如一条狗)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对照组。比较之后,我们便可发现他们之间的最本质差异不在五官、躯体等,而在张三会讲话,那条狗不会讲话。是否会讲话便成了张三与那条狗之间的区别性特征来。实际上也是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条狗的种属区别特征,本质特征。当然,语言中的对比不会来得如此简单,但作为一种方法论讨论也是很说明问题的。一个东西的本质属性往往显露在一个东西与另一个东西的最小差异之间。同样道理,我们想知道人类语言的本质,寻找普遍语法也就不必把英语、汉语、斯瓦希里语、僮语中的句子都搜集起来放在一起进行研究,而把句子与非句子组成一个个最小差异对,进行对比研究会得出更有价值、更深刻的本质的认识。
孤立的对比研究虽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句子的本质特征,但并不能反映语言系统的全貌,因为语言与句子不是种属与个体的关系,一个句子的存在条件不等于其所属语言的全部,要想把握一种语言的全部本质特征还必须对该语言中所有可能的对比对进行研究,从中找出全部句子与非句子的区别特征。但句子是无限多的,这便引出了方法论上的另一个问题:如何从无限多的事实中找出有限的规律来?
第二,语言事实的关联研究
说语言是句子的无限集合只不过是对语言的一种数学描述,不等于说在这个集合中句子是孤立存在的。相反,句子与句子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 这就是在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中常见到的“依存关系”(dependency)的一个重要含义。所谓句子的依存关系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广义的,一种狭义的。广义的句子依存关系指的是在篇章话语中句子与句子之间的某种非语言的(extralinguistic)事实关系。比如说, 句子(1)和句子(2)在下面的篇章中就可能呈现一种以(1 )所述事实为因,以(2)所述事实为果的因果关系:
(1)天很冷。
(2)我感冒了。
根据我们的常识信念,听话者和讲话者都会接受这两句话的前因后果的关系,但是这种因果关系不是语言系统本身的规定,而是由语言之外的非语言因素决定的。至于说这种非语言因素究竟有哪些,人们还只能含含混混的说是某些语用的、常识推理的东西,尚没有成功的形式化的描述。对于非语言的广义依存关系,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家中乐观主义者认为非语言依存关系最终可以得到形式化的描写,悲观主义者认为很难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奥秘”。但他们至少都采取了十分清醒冷静的态度:一方面归纳整理人的推理规则,积极探索这些语用、常识推理的形式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着眼于扩大形式化了的语言系统(主要是句法系统)的句法功能。不管怎么说,美国语言学家都承认语言因素与非语言因素的差别。
狭义句子依存关系主要表现在一个或一种句子的存在要以另外一个或一种句子的存在为条件。换句话说,一个句子之所以是某种语言中的句子和另外一个句子之所以是这种语言中的句子是相关联的。如果句子A不存在句子B也就不会存在了。比如,如果(3)不是一句汉语的话, 那么句子(4)(5)和(6)肯定也不会是汉语句子:
(3)有人打跑了那条狗
(4)有人把那条狗打跑了
(5)那条狗被打跑了
(6)那条狗打跑了
所以,研究语言除了研究句子之外,还必须研究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即语言事实间的依存关系,语法不但要对某种语言中的所有可能的句子作出结构描写,还要抓住句间的依存关系。这种句间依存关系在当代理论语言学大多数语法系统中都表现为一种“转换”关系。这种转换关系在语法系统中由系统的推导过程来实现。
第三,理论接近法
语言中有那么多句子,句子间有着那么繁杂的依存关系,世界上又有那么多的语言,究竟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完整的具有普遍语法属性的语言系统,以保证生成所有语言中的所有可能的合乎语法的句子,通过对比研究实现当代语言理论所确定的目标呢?
概括地讲,当代语言学家采用一种可称为“接近法”(approximation)的理论方法。 这个方法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首先对部分语言事实进行观察,从中概括出最简的规则或规则系统,称作第一接近(the first approximation), 然后再把第一接近放在另一些相关事实中去检验看规则是否可行,在事实与第一接近之间找出规则条件限制上的不充分性(往往是条件限制过松),再对已有规则进行修改,形成为第二接近(the second approximation),依此类推,得出第三接近,第四接近,……以至最后接近“真理”。下面举一个具体例子说明“接近法”的应用情况和意义。假如我们对下面这个最小差异对产生了兴趣:
(1)John likes him
(2)John likes himself
在这个最小差异对中两者之间在句法结构上没有任何差异,差异只表现在人称代词“him”与反身代词“himself”的指称意义上,“him ”不能同“John”共指一个人,“himself”只能与“John”共指一个人。 根据这类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下面这个第一接近:
(3)第一接近
a.反身代词必须被约束。〔15〕
b.人称代词必须不被约束。
这一接近完全可以解释(1)与(2)所代表的事实,同时又可以避免造成(4)和(5)描写的事实:
(4)*John[,i] likes him[,i]
(5)*John[,i] likes himseif[,j]
但是,在下面一些语言事实面前却遇到了麻烦:
(6)*John[,i] thinks himseif[,j] is intelligent
(7)John[,i] thinks he[,i] is intelligent
在(6)中,反身代词“himself”被约束,可是,事实上不存在(6 )这样的英文句子。显然,第一接近与(6)所代表的事实不符。(7)中,人称代词“he”也被约束,按(3)的规定人称代词不可以被约束,这等于说英文中没(7)这样的句子。可是事实正相反,(7)是一句英文。因此,第一接近不但与(6)所代表的事实矛盾,而且与(7)所代表的语言事实矛盾。按接近法的要求,当第一接近与某些语言事实发生矛盾的时候,不能“另起炉灶”再并列提出另外一套规则,而应积极地研究矛盾发生的情况,进一步修改已有的接近,把第一接近提升为第二接近,从而使第二接近不但能概括描述第一接近所覆盖的事实而且能同时覆盖与第一接近相矛盾的新语言事实。按照这种接近的方法论思想,我们发现(3)中规定过松,反身代词应被约束, 人称代词不应该被约束,这似乎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它们被约束或不被约束得有个起限定作用的结构域。因此,有必要对约束的结构范围加以限制,从而得出下面这个第二接近:
(8)第二接近
a.反身代词在其支配范畴内应被约束;〔16〕
b.人称代词在其支配范畴内应不被约束。从第一接近到第二接近,所覆盖的事实范围扩大了,理论解释上的充分性保持不变,而理论描写上的充分性增强了。但是,第二理论接近仍不是终极的真理,在下面的事实面前又遇到了麻烦:
(9)Mary[,j] was upset by John's[,i] criticism of himseif[,j]
(10)Mary[,i] was upset by John's[,i] criticism of her[,i].
(9)中的“himself”被“John”约束,但约束的范围不是(8 )中所定义的“支配范畴”;而(10)中的“him”被“Mary”约束, 约束的范围却是(8)中所定义的“支配范畴”。因此有必要在(8)的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的接近,对什么是支配范畴再做限定,结果得出了为人们所熟知的“管约论”(The Binding Theory)。而后,人们还在不断的根据新的语言事实做进一步的接近。
从上面关于接近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理论语言学在对待“例外”(exception)和“反例”(counterexample )的问题上采取了与传统语言理论不一样的态度。当代语言学理论十分欢迎“例外”和“反例”,认为与已有规则相矛盾的“例外”和“反例”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动力,从不为维护已有理论规则把“例外”和“反例”拒之门外,而是主动积极寻找“例外”,把已有理论放在“例外”和“反例”面前,接纳它们,研究它们,从中找出理论的不足,长期不懈地追求理论上的最大完美。
第四,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所刻意追求的不只是为一种具体语言提供一个形式的语法操作系统,还要为普遍语法提供一个理论模型。这个普遍语法的理论模型包括获得任何一种可能人类语言所要遵循的普遍语法原理和参数,一方面对什么是可能的人类语言限制具有充分的解释力,一方面又保证足以覆盖所有具体语言的特异性(idiosyncracies)。虽然,大多数美国语言学家们都认为普遍语法可以在一种具体语言中全部找到。但是,从实践上讲,很难在一个孤立的个体中发现共性的东西,很难从一种具体语言中辨别出所有人类语言所共有的东西。这样,普遍语法就不可避免得在多种具体语言的现实中寻找。 “跨语研究”(cross-linguistic study)或“比较研究”就成为美国当代理论语学另一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从总的方法上讲,比较研究大体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在现象事实的归纳概括上比较, 具有明显的描写性,
简称事实比较(factualcomparison)或事实比附;另一类是关于系统理论普遍语法原理在具体语言中的可行性的比较,简称理论性比较。先看第一类的比较。在这类比较研究中可见以下几个内容和方法。
事实性比较的内容在两种语言间都是显性的、有标记的,结构上的异同和语序就是典型的例子。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在一种语言中的有标记(marked)事实与另一种语言中无标记的(unmarked)事实之间进行比较。这样一种语言中有,而另一种语言中无的现象在传统语法中有详细的描写。但在解释这种“你有我无”的跨语现象时,当代语言理论与传统语言理论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说来,传统语法认为“有便是有,无便是无”,这是两种语言的特异处,没有共通的地方可言。而当代理论语言学,有者为有,无者也为有,差别不过是前者有在“明处”有标记,后者在“暗处”,“明处”无标记。有的学者反对这种说法,认为一种语言中有标记的成分不一定会在另一种语言中以无标记的形式存在,而正好相反,有者只能是有形态的,无形态者则为无。这两者一有一无正是两种语言的差异。
理论性比较是把基于一种语言事实得出的普遍语法原理联系另一种语言中的相关事实,比较普遍语法原理的可行程度,作为修改和提高普遍语法原理应用性的依据。象著名的“毗邻原理”、“空范畴原理”等普遍语法规则的可行性就在多种语言中得到了比较,比较结果又成为改造这些原理的事实根据。
比较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一)可以增强普遍语法原理的普遍性,进而增强语言理论的解释力;(二)可以发现在一种语言不易发现的具有普遍语法意义的东西,进而丰富普遍语法的理论内容;(三)可以更多地找出语言的特异处,使普遍原理的参数化更加概括和优化,增强理论描写力,扩大理论覆盖范围;(四)促进语言类型学(Typology)研究。
第五,二元特征描写法
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还有一个被广泛应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可概括地称为“二元特征系统”(Binary Feature System), 或简称“二元法”。这种研究方法的基本要领是把系统中的表示特征的概念都看成是一个概念的两个对立的、互相排斥的值,一个为正,一个为负,在正负之间没有任何其他属性。比如说,可以使用〔名词〕和〔动词〕这两个概念对词类进行二元划分:
(1)a.〔+/-名词〕
b.〔+/-动词〕
按照二元制方法,一般所说的名词便具有〔+名词〕特征,其他包括动词、形容词、介词等词类在内的所有词项都具有〔-名词〕的特征;动词具有〔+动词〕的特征,其他包括名词、形容词、介词在内的所有词项都具有〔-动词〕的特征。不管是用“名词”还是用“动词”的概念都可以穷尽所有的词类。但只靠“动词”“名词”这两个概念不足以描写出词项的句法特征。多个单一的有值概念可以组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有值的概念群(cluster)。
从(1)中的单一有值概念中可以得出下面四个有值概念群来:
(2)a.〔+名词,-动词〕
b.〔-名词,+动词〕
c.〔+名词,+动词〕
d.〔-名词,-名词〕
〔+名词,-动词〕和〔+名词〕同效,可用来代表所有的名词;〔-名词,+动词〕和〔+动词〕同效,可以代表所有的动词;〔+名词,+动词〕可以代表所有的形容词,〔-名词,-动词〕可以代表所有的介词。这种刻画词类句法属性的二元制方法实际上在当代理论语言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表面上看,这种二元的特征描写法与多元并列的特征描写法没有什么差别,说名词是〔+名词,-动词〕与说名词是“名词”没有什么差别,说介词是〔-名词,-动词〕与说介词是“介词”没有什么差别。实际上,这两种描述法是有差别的。假如,我们的理论需要把所有的实词从句法属性的角度无一遗漏地分成几类,就是说最后分成的类别能无一例外的把实词都囊括进去,有两种供我们选择的方法。一是用一套并列的概念(动词,名词,形容词,介词等),把实词分成相应的四类。那么,在句法操作规则中,就得要分别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动词,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名词,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形容词等等。如果,遇见需要讲明在什么情况下只能使用名词,就得在规则陈述中加上“只能”二字加以限制,如果遇见既可以使用动词又可以使用介词的情况,就得在规则中讲明既可以使用动词又可以使用介词。这样,规则显得繁杂,而且这种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的特性在句法的结构描写式中无法得以表现。
在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中使用二元特征描写法的实例有很多。而且,大多情况下是用在对数据性的词语进行特征刻画上,也有用在规定其他语言属性或属性群上的。比如,在语言类型学范围内,就有人用〔+/-中心词在先〕(〔+/-head-initial〕)或〔+/ -中心词在后〕(〔+/-head-final 〕)这一关于语言词序的属性概念把语言分成两类:任何一种语言要么属〔+中心词在先〕,要么属〔-中心词在先〕,别无其他的归属。〔+/-组列性〕(〔+/-configurational 〕)、〔+/-pro脱落〕、〔+/ -疑问词移动〕等也是常见的二元特征,也被用来对人类语言做类型学上的分类。
总之,当代理论语言学同传统语言学理论相比,在基础、对象、目标、性质、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等方面表现出许多根本不同的特征。把握这些特征对于了解美国当代语言学理论、从事语言研究是不可缺少的。
当提及当代语言学理论时,人们总免不了要问“究竟有什么用”的问题。一个旨在解释人为什么会说话,儿童是怎样学会说话的语言学理论有什么用?的确很难回答。你搞这种理论也好,不搞这种理论也好,人照旧用脑,照旧说话,孩子到时候自然而然讲出人话来。不过,这个难于回答的问题却使我们联想起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科学理论来。牛顿的引力学说解释的是苹果为什么往地上落。有什么用呢?哥白尼的日心说解释的是地球为什么围着太阳转。有什么用呢?孟德尔- 莫根的遗传学解释的是为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什么用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解释的是宇宙的时和空。有什么用呢?不知这些科学家如何回答这种问题。不知他们在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世界时,想到会有什么实际的用途没有。
值得最后一提的是:美国所有的当代语言学理论(包括生成语法在内),没有一个自称是已造好了的、可供直接使用的理论(not a thoery made ready for you to buy),而都认为是一种“坯子”, 让有志于此道的人来共同把它改造好。
注释:
〔1〕在英语文献中,人们最常使用的是knowledge或to know.我觉得汉语中“知识”一语似乎不能完全传达出knowledge或to know原本的含义,不如说成“知识和能力”好。比如说,the knowledge of language如果译成“语言知识”,the knwoledge of English 译成“英语知识”总不如“语言能力”,“英语能力”贴切,因为,当我们说I know English的确等于说“我会讲英语”,说We have the knowledge of language 的确等于说“我们会说话”,并不是把我们会说话看成是语言研究者或学习者有关于语言的知识。英文中还有一个专门表示“能力”的词competence,这个词在现代语言学理论中又极为常用,为了避免混淆,这里只好用“知识和能力”表示knowledge的意思。
〔2〕在我们的语言研究文献中, 常见有用“举一反三”的说法解释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这种说法好象等于英语文献中的analogy (类推)。如果对这种描述再深究一下,探索为什么人有这种“举一反三”的语言类推能力,这种能力是不是为人所独有的,“举一反三”中的“一”是什么,“三”又是什么的问题,凭借什么进行类推,类推出了什么,是不是所有的句子,所有的语言知识能力都可以通过类推的方法获得等问题,语言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就可能发生新的变化。
〔3〕我们虽然讲不清“能动”一词的准确含义, 只着眼于它的常识意义,这个词很生动地描绘出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以及对认识结果的作用。
〔4〕Chosmky肯定了笛卡尔关于“先(于)(经)验思想”在认识中的作用,但却明确地扬弃了笛卡尔的“二元论”思想。 详见Chomsky(1980,1995a,1995b)。
〔5〕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中的acquisition, 我们通常译成“习得”。但是,acquisition 一语的使用意义严格有别于learning,比如说“to learn a language”被认为是行为主义的看法,而说“to acquire a language”才能表述出“心智主义”认识论的语言观, 所以把“language acquisition”译成“语言习得”不如译成“语言获得”准确。
〔6〕有人认为Chomsky否认后天经验在获得某种语言知识进而会使用这种语言中的作用,而认为Chomsky的语言观是唯心主义的。 这种评价是不成立的。Chomsky既没有忽视也没有否认经验在认识中、 在语言知识的获得中的作用。如果说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中包含着认识主体(主要是人脑)这个“物”和认识对象这个“物”或认识过程这个经验之“物”,那么Chomsky 让人们不要忘记人脑这个“物”在认识中的作用,进而让科学研究回答人脑之“物”究竟有着一些什么属性,让人对世界的认识和鸡狗对于世界的认识区别开来,回答人脑之“物”究竟有着一些什么属性使人成为会说话的动物,而狗脑之“物”在什么样的经验环境中也不会讲出人话来。在Chomsky等语言学家看来, 经验是语言知识能力的获得中不可缺少的条件,具有“固形作用”(shaping effect),在语法系统模型中体现为“参数化”作用(parameterization)及“可学性”(learnability)与“不可学性”(unlearnability)之间的差别。
〔7〕有人认为Chomsky不管、不研究语言运用,这也是不恰当的评价。Chomsky 多处把“语言知识能力是如何运用的”列为语言研究中的三个“柏拉图问题”或“罗素题”中的最后一个。造成Chomsky 不研究语用问题这一印象的原因之一是,Chomsky 在他的语法模式中对“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作了区分,而他所追求的又是形式化的语法理论,在没有对“语言能力”作出形式化的描写之前,对“语言运用”作出形式化的描写是没有可能的。
〔8 〕在认知系统包含几个子系统的问题上美国语言学家和其他认知科学家们的看法不尽相同,这里的分法是句法学家们常常使用的。有的实验心理学家通过实证的方法认定了这个分法。
〔9 〕如果“理论语言学”一语不只在同“应用语言学”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的话,解释性语言学在很多方面很象我国语言学界所说的“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es )一语的使用在美国只局限于语言教学的研究。
〔10〕那位按图索骥的古人愚蠢可笑的地方是他忘记了自己脑袋里本来就有一张靠经验画好的骥图,凭着它满可以把那马找到,但他却要靠人家给他画出的图,不过找马总得靠一张关于马是什么样子的图,无论脑子里已经存有的直觉的图,还是用形象的办法在纸上画出来的,还是形式化的图表、数据表述出来的,总得有一张才行。
〔11〕什么是语言事实的问题也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为讨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一个既有声音又有意义的句子称作一个语言事实或语言事件。这个语言事件便具有两重属性:物理的和意识的,物理的发生在人的听觉和发音系统,意识的发生在一个我们尚不十分了解的系统。
〔12〕还没有发现有可以概括美国当代语言研究方法的词语。西方文献中多用“rationalism”之类词概述, 笔者认为汉语中“模块系统演绎法”这类的字眼可以捕捉到美国当代语言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基本特征。至于其中究竟包含什么内容,还得进一步发挥。
〔13〕在大部分美国语言学文献中,人们会发现有关语法系统生成句子的说法,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样说是不准确的,而应该说成语法生成“结构描写”(structural descriptions,SD's)。 而且是两种不同的结构描写,一是关于一句话声音的形式描写,另一就是关于同一句话意义的形式化描写。因为,句子总是有声音一面的属性和意义一面的属性。如果,我们让一个语法系统生成的是象“我和她都结婚了”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串声音的文字记录,而对这串声音所表述的意义并没有作任何描写,因而这不是句子,因为,生成这样的东西,对这句话要表达的“我和她分别和别人结婚,而不是我同她结婚”的意思并没有作出描写,而把这个任务推委给了理论接受者(读者)的语言直觉。
〔14〕well-formedness和ill-formedness 是美国语言学中极为常见的术语。我们一个习惯的译法是“造得好”和“造得不好”。从语言事实角度上看,an ill-formed sentence实际上指的是语言中不存在的“非句子”,a well-formed sentence指的是语言中的句子。语言中的句子并没有好坏、对错之分,也就没有“造得好”与“造得不好”之分。所以,“造得好”和“造得不好”不是理想的译法,至少不能从字面意义上理解。
〔15〕“约束”(bind)是依据“成分统领”(c-command )这个结构关系概念和“同标共指”这个语义关系概念建立起来的。
〔16〕“支配范畴”(governing category)是依据“支配者”(governor),“支配”(govern),“语阻”(barrier)和“accessible SUBJECT”等概念界定的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