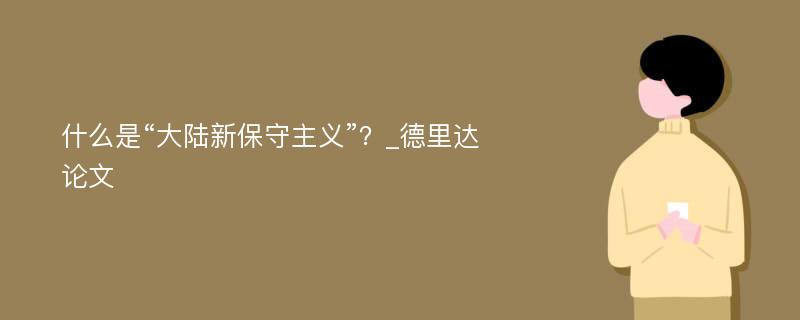
何谓“大陆新保守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陆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一文在《二十一世纪》刊出后,大陆不少学者收到文章作者的邀请评论的信,因此引起较广泛的注意。笔者也因此仔细拜读了数遍,现仅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写于下面。
《后学》将各种带“后”字的论点炒在一起,从中分析出大陆涌出新保守主义的结论,角度颇独特。大陆学术界目前有无保守主义者,笔者无从论证,只想探讨一下赵毅衡先生所涉及各种带有“后”字的说法是否可以算作“新保守主义”。首先各种“后”字的论点,从内容、背景、内涵所指各方面都各有自己的特点,仅从一个“后”字(甚至没有“后”字,不过引用了一批结构与解构理论的语言观点)就被归成一类,并冠之以“后学”又进而标之以“中国新保守主义”,作法似乎太形式化了。若因此得出一门所谓“后学”的学科就更草率了,大约只是严肃的学术论文中一句玩笑吧。
虽说近年各种活跃的学术观点各不相同,但其活跃的动力倒有相似之处,就是大家的共识是必须冲出当前的文化低谷,以迎接21世纪的文化新纪元。自9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并没有赵先生所认为的那种“自赎‘背叛民族文化’的罪孽”心态。反之,在80年代与90年代大量引进西方文化话语后,也即赵先生所谓的文化热后,不但不觉负罪,反而感到对西方文化应当了解得更透彻、更系统、更深入,以便与中华文化传统对比与互补,找出21世纪中华文化发展的自己的道路。中华文化自本世纪初就处于被批判、被怀疑、被否定的状态,经常被认为是保守的传统。“后学”一文大约也是出于这种批判精神,认为今天强调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性的说法为新保守主义的一种现象。今天大陆的学界既不会有世纪初的恐西症,也不会有汉文化中心主义,何来“背叛民族文化的罪孽”心态?人类文明,五大洲各有其自己的品种,中华品种无法以欧美品种代替,想来任何人也是同意的,因此今天为了改良自己的品种吸收其他品种的优良素质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引进其它文化时却讳言中华自己的文化传统,岂非本末倒置,忘记引进的初始目的?大陆的中华文化遗忘症确已有近一个世纪的病史,然而今天仍讳疾忌医,就令人难以理解了。
《后学》一文显然尚未意识到一个民族失去自己文化传统的失重状态的痛苦,因此将今天大陆学界关于文化现状的焦虑心情绘成这样一副可笑的脸谱:
“对80年代文化热更感羞惭”
“对80年代文化热的忏悔赎罪心情”
“对80年代文化精神高扬的清算是新保守主义的一个共同倾向”
“想自赎‘背叛民族文化’的罪孽”
其实只要不带偏见,不站在中华民族之外,谛听一下此间知识分子沸腾的讨论就会了解他们不论各派观点是如何不同,其关心的焦点却是一个,就是如何在社会转型时期为中华文化找到一条明日之路,因此他们所用心探讨的实为一种“新”学。这种新学也许都是为了让沉沉入睡的古老中华文化醒来,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的挑战,在相互激荡、相互启发中重新找回自己的活力。为此大陆知识界必须一面摇醒沉睡的文化巨人,一面更深入地探讨他文化的体系和表现,不能停止于一些术语的引进,这也许就是80年代后大陆学术界对自己的要求,有何“负罪”可言?
《后学》一文开头所提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为甚么这些讨论者都能用‘后学’支持保守观点?”何谓“保守”?如果上述的希望唤醒沉睡的5000年古老文化传统,使它能介入今天的人类文明是“保守观点”,而继续活埋自己的大众文化传统是“革命的观点”,我认为这是将白日称为黑夜,将黑夜称为白日,不值得辩论下去。我想今天大陆知识分子很少还相信应当继续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民族传统,无论东方西方的都不是纯而又纯的美好和高尚的,但又有谁愿意因为它有瑕疵而弃之如敝履?不幸人们这些此起彼伏的种种为了明天的讨论都被认为是“保守”的。文章作者对“保守”的概念十分模糊而陈旧,脱离了历史的时空。名词不过是一个失去所指的真实意义的抽象符号,正如作者在其大作第12节所说:“普遍性永远是有限度的,理论家应当对这限度有自觉,有反思。”赵先生所谓之“后”与“保守”“激进”等概念,当用于今天中国大陆,这尚未冷却的地球新生的活跃的地貌,这史无前例的大转型中的奇特的社会,其普遍性就更值得怀疑了。隔着大洋,隔着浓雾,遥读大陆一系列的学术讲座文章,真需要最大的无成见与耐心,否则就难以摸到大陆思想界的脉博。
(一)怎样理解“解构”与文明危机
《后学》一文中多次用“解构”一词,仿佛它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可以用之自外部任意互解、拆解任何事物。然而这实是作者自己想当然的说法,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观点无关。德里达文风晦涩,真正耐心去读他的著作者不多,但自60年代以来“解构”一词不胫而走,已成为舆论界的时髦术语,用者也有真理解的,也有给以想当然的字面解释的。后者往往从这一词表面的形象出发,认为是一种激进的暴力破坏行为,以为解构理论旨在摧毁一切秩序使人们生活在荡然无存的荒原上。赵先生对“解构”的理解也近似这类,但他认为西方文化固如金汤,不畏惧解构:
“西方文化……其根本性的意识形态没有面临危机……经得起任何一窝蜂的拆解,何况后结构主义拆解只是纸上谈兵。”
但他很不放心中国的文化中薄弱的人文传统;
“学西方后学家拆碎自己国家中薄弱的人文传统……用后结构主义瓦解人文精神……”
关于“解构”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并非强加于任何结构的外来摧毁力,它不过是揭露任何权威结构内在的危机,解放被它压抑的其它结构,所以原则上“解构”总是结构由于中心的不恒定而自我解构,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暂不详论。这里先讨论一下上述引文中所包含的几个可疑的论点:首先是关于对今日西方文化有无危机的估计。赵先生认为“西方文化不去说3000年,至少晚近500年的积累,已经极为富厚,而且体制化其根本性的意识形态没有面临危机”,也就是说西方人文主义与罗格斯中心形而上学今天的处境一如以往,并没受什么冲击,不存在危机问题。这说法在今天是很少有的乐观自信,能在距人文主义诞生近700多年的今天仍对其理想主义保持文艺复兴时期的兴奋与信心,在今天恐怕是很少的了,即使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也难找到这样的乐观,何况在过去的700年内米琪朗杰罗(Mlcnelangelo)时代的塑像中肌体丰满强壮的巨人早已萎缩成艾略特“荒原”中失魂落魄的小人物;启蒙时代对人类理性的威力万能的信念也随着尼采的“上帝已经死亡”的宣言而失去其神圣的源泉;牛顿时代的理性逻辑推理思维的绝对权威也被相对论与测不准论的诞生所修正;19世纪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失调、贫穷,人性的屈服于机械,流水生产线对人的自由创造性的扼杀,以及两次大战所暴露的人类的邪恶的一面,与科学的失控,原子时代的不安与恐惧,自然的被破坏,东欧的大转型,前苏联的陷入瓦解,民族间的仇恨战争……凡此种种,难道不都是对西方文化的基本意识形态的威胁?西方强大的物质富有也许对第三世界是不可抗拒的诱惑,但如不是一叶障目,总能感到精神危机、信仰危机正在暗中隐伏着。尤其是二战之后,西方思想界并不敢高枕无忧。高科技与商品社会繁荣的背后,失业与通货膨胀问题无一日不出现在新闻界。作为西方文化的脊梁骨的人文精神的危机,每时每刻都在干扰着西方学者的宁静。当代的所谓“后学”和前解构者的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及解构思维的奠基人德里达无不为后现代社会的危机而焦虑地思考着。如果西方文化的基本意识形态没有面临危机,这些“后学”又如何会一发不可收拾?澎湃的思潮之诞生必有其现实的依据。如果西方文化的人文主义果然没有危机,又如何能开展一场对形而上逻格斯中心的批判,对“绝对真理”的质疑,对“永恒”“先验超越”的解除幻觉,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对人文主义的及其它乌托邦理想国之梦的摇醒?这些正是解构及前解构以及部分结构主义者如莱维斯托劳斯、福柯甚至R·巴特的批判内容。“解构”如果是一种外来的摧毁力量,它的战术总是通过剖析对象的薄弱环节,揭发其内在的危机,以诱发对象的自我瓦解。德里达的文风所以如此晦涩,正是因为他用了很多的篇幅去钻入被批判对象的心脏,以揭发其危机。同时,他不创立解构的话语,不发表宣言,而是以形而上学本身的话语解剖形而上学的危机。所以从基本上讲,解构只引爆危房,特别是那些外观宏伟则内部危机四伏、虚伪的权威结构。正是人类思想文化史中这类虚伪的权威结构今日仍对人们有迷惑力,它们使得畏惧变迁的人们仍祈求它们的庇护。这种幻想中的安全感促使人们保护危房,而且怪罪那些促成危房倒塌,揭露其危险性的引爆者。解构理论之激进正在于揭穿权威之危机与虚伪。解构理论之盛行于70年代正是因为西方思想界,在历史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之后,对西方文化的基本意识形态比二战前的现代主义时期有更强烈的危机感,但却不再有现代主义那种对幻想破灭的哀叹。这给解构理论及其所诱发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一种冷色调的坚强与勇敢。在已成碎片的古典美学的宇宙观前表现出一种冷静。合谐完整虽然仍可以成为审美的爱好,但已经不会成为实践的目标,如何生存在这个科学也无法找到其完整合谐的最后规律的宇宙中,是解构时代人们的新思考。
由于解构论者并不认为任何外部暴力能摧毁(“拆解”,用赵先生的话说)一个结构,如果不是它内部已存有危机;为此它曾被英国学者伊格顿指责为逃避阶级斗争,而向语言宣战。②《后学》也斥解构理论为“纸上谈兵”。事实证明夺取政权的斗争远比冲破僵化的逻格斯中心、权威主义、二元对抗等的思维罗网要容易。由于思维的革新所要面对的并非一个可见的敌人,所以它的任务的艰巨,也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但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不是有不少革命政权因为并没有走出形而上中心论的罗网,在夺取政权后,也重蹈覆辙?伊格顿对解构理论不全面的认识正说明他对僵化的思想的危险性没有穿透性的理解。二元对抗思维方式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基础,伊格顿、F·詹姆逊等西方左派文学理论者在柏林墙倒塌,东欧、前苏联的转型与旧权威瓦解前无不以阶级斗争的敌我阶级对抗为纲,来观察文化、文学现象。伊格顿之所以蔑视解构理论,正因其不卷入政治上的阶级斗争,而从意识形态上擦抹传统形而上、逻格斯中心、二元对抗的权威。所谓“纸上谈兵”正是这种论调的余音。
二战以后,尤其是东欧与前苏联的政治实践失败之后,三十年代以来西方的左派乌托邦理想主义高潮得到一次最大的震撼。以F·杰姆逊(F·Jameson)在93年一次访华演说来看,他已经由二元对抗思维转向二元互辅、互转、互通的新立场。当东西方从人类最现代的乌托邦理想醒来后,人类思想史步入一个新阶段,就是:人文主义(包括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段的)之后人类的精神追求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萨特的新人文主义产生在东欧、前苏联集团巨变之前,今天可以重新审视,解构理论在此方面并无正面建树。它的看法主要有二:一,形而上学虽已被识破,但它深深地渗透整个西方文化与语言,已成为西方无法完全摆脱与消灭的“踪迹痕”(fraafruck),但它仍可能成为“有用的工具”,④只是必须接受踪迹运动的不断擦抹的改造与转型。二,在无绝对真理、无中心、无永恒中,人们从一个结构的解构走向一个新的结构,再解构,再结构……这就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无限锁链,⑤中心的不断替换,造成结构的自我解构,而“结构性”(sfrwefurality)、“中心”是一种功能,它延续着人类在生生灭灭中的生存史。⑥为此人类需要真正的浮沉于事物结——解的海洋中的超人的勇敢,悲剧性的勇敢。走出“荒原的哀叹”而又不进入对先验的“雨”的另一个幻想之“乐园”,⑦以免重复以往的幻灭。这就是许多“后学”在寻找的新路。21世纪作为转型中的大陆,面临商业文化(不同于民间文化、俗文化)的威胁,“科学主义”的日益垄断文化教育,理性至尚的倾向压倒知识的模糊与测不准的一面,逻辑思维在农村是不足的,在科学统治的城市又是绝对权威,起着一定的束缚作用。今天大陆知识界对明天的开放态度给予极大的兴趣与关注是必要而可喜的。涌现的形形色色的观点必然是正误混杂,甚至有些是浮躁幼稚的,但其多元性与生命力却是非常可贵的。最大的突破,就是人们学会了包容、思考、激烈而不敌对、鲜明而不排他。仅将这些千差万别的观点分成先锋与保守、激进与落后是一种粗糙的作法。若将这些匆忙上阵、瞬息万变的讨论看成某种西方观点的反照,输入后的反弹,也是太简单化了。《后学》一文证明大陆今日思想界的复杂是外界难于理解的,有哪个社会像大陆的今天这样章程、法则、价值标准上下浮动、左右移动如股市的行情牌一样?在这样复杂的心理、思维情况下,即使有外来的观点也必然不会只得到重复的再现。何况在多数情况下观点全属“土产”,只不过用了些进口涂料。今天大陆敏感而活跃的中青年理论家多半无兴趣对西方的某种学术体系加以细心钻研,他们复苏后十分活跃的思维,创造性压倒模仿性,全无学院气,这自然有利有弊。其生命力在于对“拿来主义”的狂放态度,不问原型;其弱点则是由于久经封闭,一旦解放,未免有疏狂之处,立论混乱,空泛无边,时而有之。大陆的诗论、文论只有在21世纪文化教育、特别是文史哲的中外古今历史能进入高中大学课程后,才有可能成熟起来。久居海外的大陆学者或汉学家短暂的访问往往不能深入了解今天大陆思想界的实景。赵先生出国多年,难免要以西方的观点套解今日中国大陆之实情。这就自难看真、认准,唯望不轻易下判断,耐心多接触。大陆的学者自然对西方的一切也难看得真。在不同的制度下生活,心态的沟通是十分困难的,但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所必须克服的。
(二)后结构理论是所谓“部族化”吗?
《后学》一文认为“当代文化理论之明显集团利益倾向……我宁愿称之为‘部族化’(fribalist)”,这其间包括解构理论和“……背靠后结构主义发展出来的形形式式的新后学,如女性主义、少数民族话语论、后殖民主义论等,则明白标榜种族、性别、阶级、地区。”一言以蔽之,文章作者认为这些理论都是“为特定集团的特定利益服务”并称之为“部族化”。
文章作者提出的第二个论据以说明解构理论只是为西方文化而设立的是:“福哥或德里达都以西方文化史思想为对象,他们自己并没有用之於非西方文化的想法。”(重点笔者所加)
这显然是赵先生的误解。德里达在批判西方文化的逻格斯中心时曾参照非西方文化的非拼音语言,特别是汉语,解构理论认为非拼音的汉语系统有破西方文化的逻格斯中心的功能。德里达说:“它们(汉语、日语)在结构上主要是图像的,或代数的。因此我们可视为证明,说明有一种很有力的文化运动发展在逻格斯中心体系之外。它们的书写并不曾减弱语音使化为自己,而是将它吸收在一个系统之中。”⑧他并且指出汉语中的图象、书写、语音之间的关系在打破西方逻格斯中心(即古时神言中心及索绪尔的语音中心)后,启发了范尼洛隆(Fenellosa)及庞德(E·Pound)他们的图象诗学(即世纪初的意象诗论),是“对于根深蒂固的西方传统的第一次突破。”⑨他认为庞德诗论受汉语图象的深层影响使得它获得极大的“历史意义”⑩。从这些引段看来,德里达的非逻格斯中心理论是得自他对西方拼音语言及东方非拼音语言进行哲学比较后的思考,并吸收了弗洛伊德关于语言与无意识的理论和海德格尔关于诗语的论述而形成的。海德格尔深受日本语言哲学及老子哲学中关于“道”的论述的影响,(11)德里达显然是受到这些语言哲学大家的启发,虽说与他们的一些具体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却是在血缘上相联的。德里达之强调“不在”(absence)与无形无影的踪迹(frace)之不停的运动,都无可回避地说明他的思路并不限于西方文化思想史,恰恰相反,他是以东方之“无学”攻西方之“有学”。德里达的学说是在比较东西方人类文明的不同途径、不同现象后而产生的。德里达在《位置》(Positions)中明确拼音书写不应成为西方的典范,它不过是“种族中心主义”使然。(12)。可见德里达明确的表示他的理论并非只为了西方文明的。德里达认为形而上学破产之日,西方文明中心主义也就失去它的地位。他多次批判西方种族主义。东西方文明,对于这位否定二元对抗的理论家来说,显然是互辅与互相转换,是歧异、踪迹普遍性运动中的文化现象。不知《后学》一文作者为什么要认为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只是“集团性”的理论,并认为:“他们自己并没有用之於非西方文化的想法”。这种主观臆测的错误解释,大大局限了解构理论对东西方20世纪及21世纪文化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在彻底走出对权威中心的依赖与盲目崇拜,和使思维从对抗的偏狭意识解放出来两方面的重大影响。这些都是20世纪下半叶人类文化觉悟的突破点。对于东方古国,思想意识的现代化,走向多元化,这方面的觉悟是首要的。20世纪的历史证明逻格斯中心往往化装成理想主义与战斗精神,引导古老的民族走向灾难。解构史观绝非为某个集团利益的理论。它是总结了人类政治、文化、思想的历程后提出的理论,旨在突破形而上学以虚幻的理想主义封闭人们思维的困境,使人类从几千年的先验幻想的自欺中走出来。无论西方和发展中的东方都能从中获得新的思维,新的史观。西方从中可以找到东方的智慧,东方可以在追求现代化、至富、科学化中警惕不重蹈西方的覆辙。今天大陆学界研究解构理论绝不是什么“学西方后学家拆碎自己国家中薄弱的人文传统”,《后学》作者这种论断,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色彩,将大陆的文化活动只看成西方文化的模仿与重现,能理解今天的大陆民心吗?
(三)女性主义、少数民族话语等是“部族化”理论吗?
《后学》一文将解构理论所诱发的多种20世纪新思潮也都看成“部族化”,他说:“而背靠后结构主义发展出来的形形式式的新后学,如女性主义、少数民族话语论、后殖民主义论等,则明白标榜种族、性别、阶级、地区。”言下之意,它们也都是只为“特定集团的特定利益服务”。然而果真这些问题与全人类无关吗?我认为这些理论,不论你是否同意其各家的具体论点,其涉及的问题却是20世纪人类文明共同关心的与人类文明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利害关系的问题。总之解构理论与其在文史哲各人文科学领域内触发的一系列新的理论研究,正是人类文化在20世纪学术探讨向纵深发展后,所提出的关系到人类命运的许多大问题,绝非什么“为特定集团利益”的小问题。福柯与德里达的研究虽多以西方社会及文化中的问题及现象为辨识与论证的对象,但他们所思考的利害却是人类普遍面对的;在20世纪末的今天不论哪一洲哪一种族的人都在精神上与自然环境上分担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利害;联合国存在的依据正在于此。不知为什么《后学》一文作者却将女性主义、少数民族、后殖民主义等都看成他所谓之“部族化”问题,不是全人类所共同关心的课题。事实果真如此吗?只要不逃避今天世界上沸沸腾腾的诸种矛盾的撞击与转换的人,都不可能认为上述的各种学科的探讨只涉及某些“部族”的利害。对这些20世纪新学科的各种具体理论,人们可以有不同看法不同评论,却无法认为它们的出现是“理论思维本身已精疲力尽”的表现,恰恰相反,二战后人文科学打开了很多新的领域,新的层面,而人类的思维也空前的活跃,绝谈不上“精疲力尽”,只是其发展之迅速令学术界迎接不暇,因此会有些学术秩序与宁静受威胁感,在这方面后结构主义的理论确实触发了一系列震波,动摇了自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逻各斯中心的理论大厦,使得它的权威性受到挑战。理论上非中心的多元局面的形成已是无可挽回的,多元是符合“自然”的复杂性,良莠不齐也是必然的,总比独家至尊,拔苗助长要更有生命力。赵先生认为,多元文化为“当代文化之剧降提供辩解”,又说:“新保守主义潮流的最重要表徵是自我唾弃精英地位或责任,转而与民间文化——俗文化认同”。俗文化与赵先生力主的精英文化不应成为对抗,而是各有各的园地,在良好的情况下,且有相互启发的效果。只是要通过教育,削减商业化倾斜对文化的独裁作用。危害当前文化素质的是商业化的金钱裁夺,并不是俗文化本身。精英文化在文化历史上也有过其新古典时期的衰微,宫廷音乐宫廷文学都曾受民间的俗音乐与俗文学冲击,并因此结合成新型的、更有生命力的音乐与文学。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席卷西方的浪漫主义运动中的音乐与诗歌正是批判、吸收、改造新古典的贵族精英、宫廷文艺而形成的。贝多芬、歌德、华兹华斯、斯托劳斯等等不就是这样产生的吗?所谓雅/俗、精英/市民实不应成为对抗的两极。赵先生关于自己力主精英文学的宣言,自然无可厚非,只是不应当忘记在《红楼梦》问世之前已有“话本”这种俗文学存在,在宋词的高雅中吸收了多少民间曲调,在毕加索的画中有多少非洲原始的雕塑,在《一个美国人在巴黎》(13)这样交响音乐中有多少“美式”俗音乐。总之对精英与俗一概肯定与一概否定都是偏狭的对抗思维。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偏爱,却不应以之束缚文学、艺术、学术自由发展的强大的生命力。多元的意识是很难树立的。代沟、种族沟、文化沟、经济沟等等都是无法抹平的,人类只有学会开放、共容、包涵,才能生活下去。多元是民主的要素,不以个人喜恶定论。在信仰、文化等精神生活方面权威(无论其为俗为雅)的压抑并不能调动创造的积极性。学院派、精英派、俗文化、民间文化都有自由发展的权力,而无一应成为压抑他类的权威。
(四)何谓激进主义
《后学》一文对“激进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等一系列名词的使用很含混。将后结构主义列为激进主义当然是可以的,但其原因并非因后结构主义所至之处一切都被“拆解”。如前面所说,后结构主义并不打倒、摧毁、消灭,因此与消灭敌人的想法不符。它只是擦抹权威,维护多元。如果《后学》作者认为激进与传统势不两立,那么后结构主义也许就不是激进主义,因为它承认传统的存在与它的踪迹的运转是无法摆脱的,而且并没有不承受传统的全新的创新。从这方面来讲德里达对传统力量的肯定按照《后学》一文的激进与保守的概念,也许就是“保守”的了?可见所谓激进与保守实非简单的标签所能解决的。
德里达在《书写与歧异》一书中转借莱维斯托劳斯(Le-stsauss)关于语言的“修补匠”(bricoleur)与“工程师”的区别的比喻,说明语言、文化都不可能是全新的创造,因为它不能脱离传统,所以永远只是经过修补的传统工具。德里达认为:
“修修补补(bricolage)这名字是我们用来称呼我们从继承到的文本中转借来观念,做为自己的之必须性。这文本多少有些联贯,也有些破损。必须认为每一种话语都是经过修补的活儿(blieoleur)。莱维斯托劳斯将工程师与修补匠区别开来。工程师应当是那建立他自己的语言、句法及词汇的整体的人。从这点看来,工程师是一个神话。他是那假设的自己话语的绝对来源,并且假设能从‘无’中建立起他的话语……工程师的涵义,作为一个与各种形式的,与转借无关者,因此是一个神学的理念。”(14)(重点是笔者所加)。
由此可知这位被认为激进主义的解构理论家在继承与创新,在对传统的评价上都并非全盘否定传统,也不承认神话式的全盘创新。他将传统看成,一不能全消灭,二仍是“有用的工具”。将主张文化话语全然摆脱传统、纯粹独创看成只是神话而已,只是一个“神学的理念”。用这样的“激进主义”观点来对照我们20世纪对待自己民族传统的激烈否定,对古典文学哲学一千多年的成就全盘抛弃,不知其究属“激进”还是“保守”?昔日之“激进”今朝实为落后的观点,大约我们都遇到过不少,大自政治、经济观点,小自起居饮食服装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就不在此多举。关于文化与传统的关系,在今天的大陆不会有人再主张“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而是一个回顾20世纪在文化方面所做所为的历史时期,对昔日的革、保观点也可以摆脱结论,重新审视一番。《后学》一文所谓用新理论阐释旧观点就是这种反思活动的一种。既然没有什么既定方针可束缚人们的思维,旧案重审也是无足可怪的。当然各种各样背景的人在一定历史时期可能有某些共同的见解,我认为动机问题不如留给历史实践去揭露,时代共识的产生必有其客观现实的根由,知识分子只须按照自己的良心去写文章,对他人的动机却无法瞻前顾后的去推测,历史的记载说明,永远的纯正的同志也许也只是人们的向往吧。
《红楼梦》中有两句开玩笑的打油诗:“这鸭头不比那丫头,头上哪有桂花油?”看来这里还有些哲理。这保守不比那保守;这激进不比那激进;这后结构不比那后结构;这后现代不比那后现代……以此类推就可避免忘记歧异,对大陆今天的形形色色“主义”,或炒在一起,或脱离其时间地点来理解。当然这种弹性的认识,不应成为某些不光明的目的的藉口。
(五)理想与理想主义
“理想”,无论是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都不否认,这是人生存在地球上的精神支柱与动力。尼采向艺术寻求理想,海德格尔在诗歌中寻找生命的存在,德里达用踪迹的无穷运转观照事物的生灭,而得到超然的欢快。今天在商业文化的冲击下,大陆的诗人、知识分子倍感“理想”失去它应有的空间。但是能否重新提出“理想主义”(包括人文主义)为医治精神空虚的良药呢?
古典意义上的“理想主义”是不可能再拥有它昔日的超验的权威了。因为柏拉图式的“理念”的至高至尚已在长长的历史岁月中证明难以在尘世实现。人间并无理想国,一旦以一切权力手段强行建立纯而又纯的理想国时,初时尚能吸引群众,最终总是以血腥的失败告终,因此,只有在多元文化中相辅相成相竞争相淘汰,人类才能在宽容中最大程度的走向理想。所以理想是任何流派也不会绝对舍弃的,但理想又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强行被捉住,被强加于群众。一旦以权力强行洗涤社会、人群,其后果只是血腥的灾难。
随着“理想国”(乌托邦)失去其真实性、本体性的权威,人的“理性”也不再是逻格斯的圣火(holyspark),人文主义大厦已失去昔日的辉煌,人性并不纯净高尚如神子,只有法律才能在有限的程度上抵制人的贪欲与以权力压制他人的野心,这些都是自13世纪以来人类共同的历史教训与认识。今天在20世纪末人类共同面对一个斯芬克斯为我们提出的谜语,就是在乌托邦幻影消失后,在人类已经站在现代主义的“荒原”上后,我们在后工业时代如何走出“荒原”?我们还能寄托希望于再一次呼来理想主义、人文主义的“圣雨”吗?走出理念与神子的乐园之后,我们还要再建一座幻想之园?这些是解构与前解构学者所思考的问题。
海德格尔在诗歌中找到生命的存在,尼采主张由哲学控制科学以免它只为实际利益服务,(15)并且如艾利·海勒(Erich Heller)在《尼采的要义》一书中所说:“(他)学会不需要信仰和真理而以超人的精神喜爱生活”,(16)接受破碎的现实,以顽强的悲剧的精神活下去,在艺术里找到智慧和力量。德里达继承了海德格尔与尼采的顽强与乐观的一面,进一步描述了他所理解的宇宙及人间的结构——解构——结构……的无穷变化,安于变化,放弃寻求并不存在的“安全”,所以解构思维对他们都是一种消极的积极和积极的消极,困难的是要走出依赖的心态,而得到“无待的自由”。
今天我们研究解构思维并非要摧毁“理想”,自甘堕落,而是要走出虚幻的“理想主义”,不哀叹地走出现代主义的“荒原”,面对那既非乐园也非沙漠的真实世界与宇宙,在不断地创造中生存下去。每一次解构是一个新的结构的开始,每一个新的结构的诞生也是一次解构的开始,尼采的欢乐和德里达的冷静是人类进入后现代时期的最佳心态。
注释:
①C.L'evi-strauss,M.Foucault,Roland Barthes
②LITERARY THEORY by Terry Eagleton,Oxford 1989
③见本人的《从对抗到多元——读弗·杰姆逊学术思想的新变化》,北京《外国文学评论》1993,NO4
④WRITING and DIFFERENCE,by J.Derrida,Univ of chicago Press 1989P284
⑤WRITING and DIFFERENCE,by J.Derrida,Univ of chicago Press 1989P279-280及POSITIONS by J.Derrida,Univ of Chicago Press P24
⑥WRITING and DIFFERENCE,by J.Derrida,Univ of chicago Press 1989P279-280
⑦“雨”指“荒原”结尾的雷雨
⑧OF GRAMMATOLOGY by J.Derrida,John Hopkins Univ Press 1976,P9
⑨OF GRAMMATOLOGY by J.Derrida,John Hopkins Univ Press 1976,P92
⑩OF GRAMMATOLOGY by J.Derrida,John Hopkins Univ Press 1976,P92
(11)CN THE WAY TO LANGUAGE by M.Heidegger,Harper & Row,U.S.A,"a dialoguc on language"
(12)POSITIONS by J.Derrida univ of Chicugo Press p25
(13)美作曲家George Gershwin(1898-1937)作品
(14) WRITING and DIFFERENCE,by J.Derrida,Univ of chicago Press 1989PP279-280
(15)PHILOSOPHY and TROTH by F.Nietgsche,london 1990,P8,9
(16)THE IMPORTANCE of NIETZSCHE,by Erich Heller,UDIV.of Chicago Piess 1988,P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