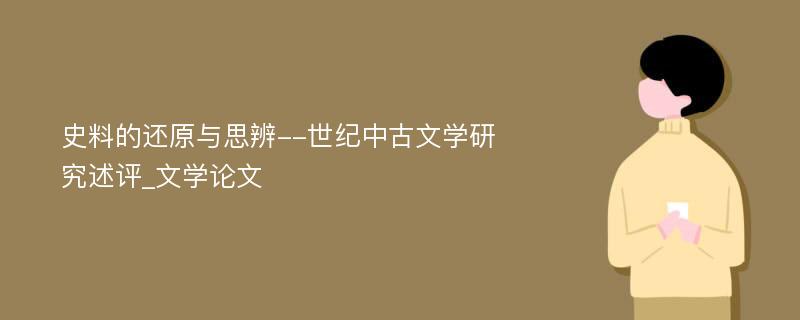
史料还原与思辨索原——中古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辨论文,中古论文,史料论文,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种研究中古文学的著作摆在案头,分别是:刘师培先生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集》及罗宗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自本世纪初刘师培明确地把中古文学作为独立研究对象至今,已约一个世纪。近百年中,中古文学研究领域人才辈出,佳作迭现,锐思精见,粲然可观,远非这四种著作所能概括。但择取其中有代表性者,以简驭繁,以点窥面,也不失为一种观察角度。选取这四种著作进行分析,除知名学者、代表著作的原因外,还因为它们每两种之间相隔约为二、三十年;这种排列构成一种时间阶梯,把百年光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从而简明地凸现出不同时期治学风气、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的各自特点。可以说从世纪初到世纪末,中古文学研究走过了一条从史料还原到思辨索原的道路。
一
近代学者中,把中古文学剥离出来,视为一独立单元来研究,自刘师培始。其治学路数,为注重历史的、资料的还原。文学或文学史研究在刘师培治学对象中,并非显族,阐发义理,也非其强项。然而其《中国中古文学史》一书,草创纲目,独标中古,在近代学者中独具慧眼,第一次将中古文学作为独立研究对象。本书体例为:先辑录胪列有关成说、史料,使人明其轮廓概貌;其次间杂己见,略加点染,使人明其脉络流变;然后照录有关文章,呼应前文,使说有所本,论有所归,无一字无来处。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是:以资料为主,我为客,让资料、史实说话,尊重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其字里行间明显有清代朴学、乾嘉考据的遗风余影在流荡,其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世纪初特征。
例如本书第三课“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先以导论略析脉络,次列《文心雕龙·时序》、《魏志·王粲传》、曹丕《典论·论文》、《宋书·谢灵运传》等资料38条,并案曰:“以上各条,于建安文章各体之得失,以及与两汉异同之故,均能深切著明,故摘录之。”后又继之以附录,并云:“汉魏之际,文学变迁,既如上课所述矣。然其变迁之迹,非证以当时文章各体,不足以考其变迁之由。今略录祢衡以下文章十二篇,以明概略。”在胪列祢衡《鲁夫子碑》、《吊张衡文》等文章后,作者才得出结论说:“魏文与汉不同者,盖有四焉:书檄之文,聘词以张势,一也;论说之文,渐事校练名理,二也;奏疏之文,质直而屏华,三也;诗赋之文,益事华靡,多慷慨之音,四也。凡此四者,概与建安以前有异,此则研究者所当知也。”另如论晋文之别于魏文,在辑录《文心雕龙·情采》等篇之后,作者案曰:“晋文异于汉魏者,用字平易,一也;偶语益增,二也;论序益繁,三也。彦和所论三则,殆尽之矣。”又案:“《雕龙》此节推论两晋文学之变迁,最为详尽。”又案:“《雕龙·通变》所论,于魏晋文学亦得大凡。”以上略举数端,可见刘师培治文学史的基本方法。他师承旧学,恪守家传,以古为本,颇有述而不作之风。在辑录资料的同时,他已把这些资料间的联系、逻辑及所揭示的现象思考、咀嚼了数遍,而他的思想观点就隐含在资料中,所谓“殆尽之矣”、“最为详尽”、“亦得大凡”云云,均是隐观点于资料,尽量不掺杂己见。读者翻卷,一上来只见资料,不见观点,欲知作者所云,自己必须得下一番重新思考、咀嚼的功夫。
以资料为主,并非意味着只有资料价值。首先这些资料是按作者意图排列的,作者以“汉魏文学之变迁”、“魏晋文学之变迁”、“宋齐梁陈文学概论”为纲,简明勾勒出中古文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又以尚骈偶、重文采、文笔辨体、讲究声律等为纬,重点剖析具体文学现象,扼要描画出此期文学发展之关键所在。纲举目张,脉络清楚,读后基本可领略中古文学全貌。另外,在作者用笔十分吝啬有限的案语及评点当中,不乏思维火花,时有真知灼见闪现,给人以深刻启迪,有些观念至今还为人所重视。如作者定义建安文学的几个特征为:清竣、通脱、骋词、华靡,并分析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竣,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脱;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由汉至魏文体变革的时代、社会、人文原因,一一剖析明了。又如论由魏至晋文体的演进,分此期文学之士为两派——“一为王弼、何晏之文,清竣简约,文质兼备,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为近者。此派之文,盖成于傅嘏,而王、何集其大成;夏侯玄、钟会之流,亦属此派。溯其远源,则孔融、王粲实开其基。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纵采骋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盛于竹林诸贤,溯其远源,则阮瑀、陈琳已开其始。”虽同为正始玄学的热衷者,但王弼、何晏辈注重辨析名理,而阮籍、嵇康一派则偏重哲学的实践与体性自然,故其心态、性情形之于文也各异。正始文风上承建安风气的余绪,但刘师培之前提及此者不多,对此作者分析原因说:“惟阮、陈不善持论,孔、王善持论,而不能藻以玄思,故世之论魏晋者,味其远源之所出。”随后的案语中,作者又例举《世说新语·文学篇》、干宝《晋纪总论》等资料证明当时士林中玄风之盛,遍及文苑,已在暗示魏晋玄学与当时文风关系密切,研究文学应与研究社会思潮、士人心态、生活习俗相结合。惜未展开深入论述,然而却为后来研究者留下了一个思考焦点。刘师培于南朝文学,亦有灼见,传统流行的观点是,魏晋为文学自觉独立时期,但作者依据资料指出:“中国文学,至两汉、魏晋而大盛,然斯时文学,未尝别为一科,故儒生学士,莫不工文。其以文学特立一科者,自刘宋始。考之史籍,则宋文帝时,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文学馆,使司徒参军谢元掌之。”对齐梁文学得失,作者总结四点,即沉迷用典、风靡宫体、崇尚讲论、流行隐谐。针对世于齐梁文学颇多贬语,作者公允评价说:“齐梁以降,虽然侈艳之作,然文词雅懿,文体清竣者,正自弗之。斯时诗什,盖又由数典而趋琢句,然清丽秀逸,亦自可观。”并指出齐粱文学的历史功绩:“至当时文格所以上变晋、宋而下启隋、唐者,厥有二因:一曰声律说之发明,二曰文笔之区别。”凡上所举,均能证明作者于资料之外,不乏自己独到见解。这些见解涉及中古代文学领域的基本点,连缀起来,就可勾勒出此期文学发展的粗略轮廓,给后人研究指明当下手处。当然,刘书的主要成分是资料的胪列,但是,这不是一些静止的资料,是经过作者的思维“咀嚼”过的资料,是按照一定的逻辑联系排列组合的资料还原。任何领域草创之初,勾沉、整理、解读原始资料,归还历史原貌,均为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原者,原始面貌也,真实状态也,脱离这真“原”,一切思想阐发和文化关照都无从谈起。刘师培老老实实地迈出了这一步,为中古文学研究开了一个好头儿。
二
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下简称《魏晋风度》),作于1927年7月,原为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的学术讲演稿。 就学术承接联系而论,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讲义》直接影响了鲁迅。
文章开头便说:“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又说:“研究那时(指魏晋)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他在另一处也说:“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指中国文学史一类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太多。”(《鲁迅全集》第九卷)可见刘师培《讲义》在当时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开拓意义。鲁迅概括自己的讲演取舍时明确地说:“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详一点。”可知鲁迅对刘师培的基本观点有全面的了解,因其已为人所知,故无须重复;而对刘所忽略未及的,则有所补充,有所创新,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鲁迅对汉、魏文风的概括,明显从刘师培《讲义》脱胎而来,他说:“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以说是:清竣、通脱、华丽、壮大。”可见刘师培观点中的可取之处,确为鲁迅所采纳,又加以改造。这种有明显承接关系的论述,在鲁迅的讲演中,属于“略”的范围。讲演“详”的主体是在刘的《讲义》所提供的材料、内容之上,引申发挥,纵横开合,钩沉发微,把中古文学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对此,鲁迅关于《魏晋风度》讲演的最大贡献是,开启了从研究社会思潮、生活习俗、文人心理入手探讨文学现象的先河,这条治学思路,直到今天对学术界尤其对治文学史者还不无影响。
《魏晋风度》明确把“药”和“酒”与文章并列,看似随意点画,信手拈来,实则触及一个一直为前人所忽略的研究课题。关于这一课题的材料早已为人熟知,是历史的存在,但从无人把它们提到与文章、文学同样的高度,鲁迅把“药”、“酒”与文章并列而谈,把治文学史者的注意力从单纯分析文学现象本身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日常行为习俗,从而展开一种立体的文化式的研究。这种研究牵涉到当时的政局、思潮、生活习俗、士人心理、社会氛围等,是一种综合的系统工程。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看似漫无筌次,实则博大精深。由于是讲演稿,《魏晋风度》对一些问题只是点到为止,并未展开深入,如论魏晋之际文学的变化,作者只是说:“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此期文学风气的变迁,即所谓“文章上起了个重大变化”,与何晏辈的关系究竟如何,作者未涉及,留下一片思维的空白,但却点明:“(关于)何晏有两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魏晋士人清谈、服药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与复杂的历史背景,这些社会的历史的环境、氛围,同样也是文学赖以生存的土壤,魏晋士人往往一身而兼三职:清谈玄理高手,服药饮酒楷模,文学辞章领袖。所以研究这时期的文学变迁,清谈、服药、饮酒等生活习俗,是研究者绕不过去的课题。刘师培的《讲义》虽也注意到这方面的资料,并将谈玄、服药饮酒的王弼、何晏、阮籍、嵇康作为由建安向正始文学过渡的代表,但并未将士人行为习俗提到与文章同等的地位。《魏晋风度》抓住“药”与“酒”重点分析,较之刘的《讲义》更触及问题本质,使人能抓住魏晋文学变迁的关键。明标“药”与“酒”,而作者真正用心却在服药饮酒士人日常行为背后的深刻社会原因。魏晋政局屡迁,人情世态多变,现实的残酷、危险把士人逼向逃避、麻醉一途,服药潇洒,饮酒陶然,望之若神仙中人的背后是深深的苦闷。正如鲁迅尖锐指出的:“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又说:“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就学起来,而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阮籍《咏怀》诗:“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可证。作者分析阮籍得以终其天年而嵇康难逃一死的原因说:“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戏言中亦有深意。
《魏晋风度》中的思维亮点很多,由于讲演稿中不能征引材料进行辨析,妨碍了观点的进一步深入展开,却给后人留下充分探讨的天地。鲁迅的《魏晋风度》略刘之《讲义》所详,而详其所略,清楚标明“风度”、“药”、“酒”乃其侧重。文中一反传统舆论以魏晋名士为名教罪人的成说,对嵇阮为代表的玄学家以高度评价。无独有偶,刘师培亦持这种观点,其《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云:“近人顾亭林又以王、何、嵇、阮为罪人,致一时之舆论均以两晋六朝学风为非,不知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故一时学士大夫其自视既高,超然有出尘之想。不为尘网所撄,由放旷而为高尚,由厌世而为乐天……”(《左庵外集》卷九)这种评价是否影响了鲁迅?《魏晋风度》中未提及,只是说现在研究魏晋较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除刘师培的《讲义》外,这“有人做过工作”,是否也包括刘对魏晋士风政俗的分析,不好断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刘师培关于汉魏六朝文学思潮的分析对鲁迅有直接影响,“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说明鲁迅对其著作并不陌生,极可能在阅读时由文学而涉及学风与政俗。刘在鲁之前写出《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重视对社会生活习俗的研究,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引人注意的信号。鲁迅申明《魏晋风度》要略其所详,这“所详”也极有可能包含刘的上述观点。要之,在近代,《魏晋风度》首开强调从社会思潮、生活习俗、士人心理入手探讨魏晋文学变迁的风气,其活跃的思维给人以丰富的启迪,其拓荒式的开垦给后来学者留下了精耕细作的园地,惜其为讲演稿,不能铺排材料,也未能深入挖掘,形成体系,但启迪来学,嘉惠后人,其功不可浅测。
三
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集》(以下简称《论集》)写于1942年至1948年期间。关于《论集》的学术承袭渊源,作者在1981年《重版后记》中明言:“由本书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研究中古文学史的思路和方法,是深深受到鲁迅《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影响的。鲁迅对魏晋文学有精湛的研究,长期以来,作者确实是以他的文章和言论作为自己的工作指针的。”又说:“鲁迅把他拟写的六朝文学的一章定名为‘酒·药·女·佛’,这四个字指的都是文学现象;关于‘酒’和‘药’同文学的关系,我们已在《魏晋风度》一文中得知梗概,关于‘女’和‘佛’,当然是指弥漫于齐梁的宫体诗以及佛教翻译的流行,这些现象既同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有联系,又同文人的生活和作品有联系,是可以反映和概括文学史的历史特征的。”这种申明,同鲁迅说过要略刘之《讲义》所详而详其所略一样,都是老实道出自己治学思路同前人的继承联系。
渊源有自,并非重复前人,而是有所拓展和超越。如对“药”的问题,王瑶先生说:“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一文中,指出了这个现象,但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发生这个现象,以及它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怎样的关系,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为此,他深入剖析了当时的社会心理。人生本来短促,生死本为文艺咏叹的永恒主题。但汉末魏晋世态百变,社会无序,生命没有保障,许多人为因素加速了人的非自然死亡。于是生死问题尤为集中和突出。作者举出当时道、佛、玄学得以流行的实例,说明对生死的思考、怀疑为士人注重热点,他们学术上崇尚玄远虚无,生活实践上讲究服药求长生以增加生命的长度,创作中则低徊咏叹“人生几何”。王瑶指出:“明白了这种情形,才能了解当时人的心境,才容易理解当时的作品。这是文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作者还从美姿容,清谈,人物品藻,房中术诸方面分析了服药得以风行的社会原因。于是,《魏晋风度》中关于药的命题在《论集》中繁衍成“文人与药”,就显得丰满、质实许多,作者使“药”与诗文风貌经过文人心理的中介过滤产生多种内在联系,显然有所超越。《论集》中的“文人与酒”也是如此,既承袭前说又有所拓展。作者分析,服药为追求增加生命的长度,着眼来世;饮酒为追求增加生命的密度,注重现世,二者形式不同,但都是由对生活的同一思考与认识所导出的相关行为。饮酒何以解忧?作者分析说:“照老庄哲学的说法,形神相亲则神全,因而可求得一物我两冥的自然境界,酒正是追求的一种手段。……其实所谓酒中趣即是自然,一种在冥想中超脱现实世界的幻觉。”这样就把饮酒上升到哲学境界,不单纯是一种生活行为。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发奇想,把饮酒与音乐联系起来,他举阮、嵇有关音乐的论述之后说:“这是一种幻觉中的境界,阮嵇都是诗人、音乐家,又都笃信老庄,因之也都向往这一种由老庄哲学出发的自然的艺术的和谐境界;同时他们也都努力创造和追求它。我们试看,饮酒所达到的形神相亲而接近自然的胜地,不正就是这里所描写的音乐的合乎自然的和谐境界吗?”酒,音乐,生命,自然和谐境界,混然一体,论点新颖,发前人所未发。
除“药”与“酒”的题目外,《论集》又补《魏晋风度》之未及,开辟了“小说与方术”,“玄言·山水·田园”,“隶事·声律·宫体”,“徐庚与骈体”,“论希企隐逸之风”等篇,描绘出一幅幅魏晋文人与社会习俗的生动图画。王瑶十分推崇朱自清先生写文学史的态度,朱先生在林庚的《中国文学史》序中曾说:“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许多学科做依据,主要是史学,广义的史学。”王瑶对这种做法完全肯定,并将自己的思考融入学术实践中。《论集》中既有刘师培重视从大量有关古代典籍中钩沉抉奥,挖掘资料的朴学精神,又有对鲁迅先生善于从丰富复杂的史料中总结规律、阐释源流的现实态度,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可以说,直到王瑶先生才有意识地把刘师培、鲁迅二位学者所代表两代学人的治学特点和长处结合起来,加上自己的创造,使中古文学研究面貌一新。
首先,它表现为一种“广义的史学”精神,或曰“以史证文”的实证态度。《论集》继承刘师培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中的朴学精神”,每论述一个问题,总是最大限度占有资料,力求一网打尽。全书为探讨魏晋时期的文人思想、生活和文学风貌,对有关的文学和历史典籍的材料,《论集》几乎是搜罗殆尽。作者每作一判断,都不是凭空臆想,而是有大量的材料作为依据,故能从大量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带有规律性的科学论断。为支持一个论断,作者经常要连续引用十几条资料,有时,从一条材料出发,作者又能独到地阐发一个新颖之论。如对清谈、玄风、傅粉、服药的论述都是如此,兹不赘言。
其次,《论集》重视阐释与批评,避免堆积材料和繁琐考证,表现出史识重于史料的态度。王瑶的《论集》是在一代著名学者朱自清、闻一多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写成的,作者曾说,“(这本书)在属稿期间,每一篇写成后,作者都先请朱佩弦师过目,得到的启示和校正非常多。已故的闻一多师,也曾给过作者不少的校正。”(注:王瑶:《中古文学风貌——中古文学史论之三》序,棠棣出版社,1951。)事隔四十年后,作者又说:“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受到朱自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的指导,……这是一种‘亲承音旨’式的当面讨论的方式。”(注: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重版题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在朱先生刚刚过世,王瑶撰文纪念说:“他的观点是历史的,他的立场是现实的。……基于这种观点,他反对繁琐的死板的考据,……他以为绝对的超然客观,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考证的尺度必须放宽,必须和批评联系起来,才有价值。”(注:王瑶:《朱自清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国文月刊》,1948.9。)上述观点,构成《论集》的基本学术框架,作者努力体会朱、闻二师治文学史的态度和方法,并在写作中实践躬行,形成自己的史识和史观。具体来说,就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对于古典文学现象进行批判的接受,“放宽了的考据”为确立观点、展开论述服务,以科学的实证的精神进行更高层面的理论研究。在被朱自清先生许为“觉得十分精彩”的《小说与方术》一章中,典型地体现了作者所追求的科学实证精神和特点。本章共分六部分,每一部分都是既有严谨绵密的考证,又有关于小说产生与道家方术兴盛之间千丝万缕联系的精彩理论阐述。如第四节,在引用几十条资料说明方术之士善以搜奇辑怪蛊惑帝王之后,作者对自己的判断加以理论升华:“这是宗教,态度可能是严肃的。因此小说虽然是丛残小语,在作者也许是相信它完全是实事和真理。这些事纵然是出于想象的创造,但基于宗教热情的幻想,也可能使自己相信它是真实的。因此小说的发展和道教的盛行,存在着极密切的关系。”要之,这一章较典型地体现了王瑶先生所追求的科学的实证精神和特点,他能考证辨伪,使自己的论述有深厚的历史依据,又能不陷于繁琐的考据之中,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规律性,并作出富于创建的理论性论断。
在接受前辈学人重考据、重史料、重事实的严谨学风的基础上,王瑶的《论集》将鲁迅先生善于从复杂史料中找出普遍性规律,闻一多先生所提倡的“阐释与批评”,及朱自清先生所说“放宽的考据”、“批判的接受”,融会贯通,消化在自己的写作中,从而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实现了对前人朴学式史料性还原的一种超越。《论集》中既有刘师培、鲁迅、朱自清的影子,也有自己独树一帜的创造。它对原始资料的还原程度,不亚于刘师培的朴学作风;它注意从社会风俗入手剖析文学现象,在鲁迅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它在闻一多、朱自清的亲自指导下,注重阐释与批评,又有一种对文学研究的现代自觉意识。因此,说它在中古文学乃至文化史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不过分的。朱自清谈到闻一多的学术计划时说:“就在被难的前几个月,他还在和我说要写一部唯物史观的文学史。”(注:《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第1卷。)从某种意义上说,《论集》作为研究中古的断代文学史, 弥补了这一缺憾。
四
罗宗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写于1986年,脱稿于1994年。这期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思想活跃,思辨性、系统性的专著层出迭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罗书名为“文学思想史”,是其主编的八卷本《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中的一卷。之所以选择它,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它注重对文学创作现象本身的研究,基本上按照文学史的时间段落和轮廓来阐述,其研究的第一步是吃透文学创作现象。作者曾不只一次强调“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离开文学创作实际是无法进行的”(《宋代文学思想史序》),“它(指文学思想)的主体,是由创作反映出来的,理论形态不过是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文学倾向的升华而已”(《魏晋文学思想史引言》)。
二是因为它特别强调“历史还原”,重视史料的整理,与自刘师培以来的“以史证文”的态度一脉相通。作者认为“‘历史还原’,就是要弄清上述种种因素在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广泛、认真、严谨的清理史料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对历史的活生生的体认。……往往需要通读一个时期的差不多所有存世之作,和作者的生平材料,才能形成其时文坛风貌的大致轮廓。……往往翻遍存世的能够找到的所有典籍,结果用得上的材料则百不得一,千不得一。”(《宋序》)这与刘师培注重史料的还原并无二致。
三是它承接了鲁迅、王瑶先生注重社会习俗、文艺思潮、生活方式的研究思路,进行广义的文学研究,有所继承,更有所创造,尤其是把士人心态从诸多因素中剥离、凸现出来——“文学思想的产生和变化,当然和社会环境有种种关系,如政局、社会思潮、学术思想、生活情趣、生活方式等等。但是,我以为,这些都不是直接的关系,直接的关系是士人心态。政局、社会思潮等等,是通过士人心态对文学思想发生作用的,士人心态是中间环节。”(《魏晋引言》)“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里文人普遍地走入仕参政的道路,文人的命运往往和政局的变化至为密切。他们的思想状况、精神风貌和创作面貌,也就随着政局的变化而变化。”(《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结语》)
以上三点,与刘师培、鲁迅、王瑶的学术精神是息息相通的。评价一种研究是否有价值,要看它是否超越前人,为时代提供了新的东西。在刘师培、鲁迅、王瑶已经达到的学术水平上展开研究,时代对研究者素质和起点的要求之高不言自明。可喜的是,我们在罗先生的著作中看到了新意。
高起点的研究源于高起点的认识。如上所述,罗著同样注重“历史的还原”,这里包含两重意思:一是史料的还原,即对原文的正确解读;二是思想或思辨的索原,即发现史料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新的结论。后者是一种广义的、更高一层的“历史还原”。早在90年代初,罗先生就正式提出了“理论索原”的概念,“从这个角度说,原文的正确解读不仅仅是文字本身,也包括着更为广阔的历史事实的清理,复原历史的原貌”。(《宋序》)索者,求也,思也,探也;较之历史还原,思辨式的索原是一种索解史料间逻辑联系、构建新的学术体系的主动突破精神。
为说明问题,最好解剖一只麻雀,以见何为理论思辨式的还原。试以山水文学为例。晋宋之际,山水文学崛起,所谓“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在刘师培和鲁迅笔下,几乎没有讨论山水文学。至王瑶,始立《玄言·山水·田园》一章,浅显描述了山水文学兴起的原因及基本面貌。文中认为,由玄言至山水,“‘老庄’其实并没有‘告退’,而是用山水乔装的姿态又出现了”。并指出,山水文学是爱好自然的主观思想和南方山水的客观美景相结合的产物。而在罗著中,思辨性的索原精神发挥了威力,对山水文学的起因进行了精彩描述。为寻求江南风景和山水审美趣味的原貌,作者特地考察了当时的环境,指出:“当时著名的士人,大多活动于从首都建康南到会稽、永嘉,西南至洵阳一带,相当于现在南京南至绍兴、温州,西南至九江。……他们聚会最多的地方,是会稽。晋时的会稽辖县十:山阴、上虞、余姚、句章、鄞、鄮、始宁、剡、永兴、诸暨。境内会稽山东连宛委、秦望、天柱诸山,为山水绝美之地。”然后胪列了《水经注·浙水注》、《嘉泰会稽志》、《剡录》、《绍兴府志》中十几条有关山水资料的记载,借以说明南方自然环境是山水审美情趣生成的客观原因。就山水审美而言,这种追寻当时士人们的真实生活环境的“历史还原”工作,似乎尚无人做过。在这种资料性的“历史还原”之后,作者进一步做了理论性的“思辨索原”。作者认为,晋宋之际的山水审美与弥漫士族中的偏安心态有关。永嘉南渡,政局发生剧烈变化,衣冠士族苍黄南奔。东晋立国之本,一是“天限南北”的长江天险,二是中原和江南大族的扶持,并无余力统一天下,加之本身内乱不绝,这就决定了这一政权的偏安性质,笼罩南朝四代朝野的也是一种感伤情绪和偏安心态。作者举例说,桓温北伐,孙绰上表反对,最为生动地反映了东晋人士的偏安心态:“植根于江外数十年矣,一朝拔之,顿驱踧于空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餐之饭,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将顿仆道途,飘溺江川,仅有达者。”作者分析说:“为什么愿意偏安江左?因为南渡一代的悽恻怅惘已成过去,一切都习惯了,田宅舟车、生业坟墓都安顿在了江南。……虽政局动荡不安,但南北割据已成定局。这样的局面有利于追求安宁、追求平静。于是走向内心,去寻求另一个广阔天地,去寻找精神的慰藉。终江左百年,未离这种境界。”而山水游处,则为东晋士人追求安宁平静境界的一种方式。
这样一来,政局变化——士人心态——山水审美之间的层层逻辑推进关系十分清晰。这就比泛泛而谈山水审美要深入一步。在没有进行这种“思辨性索原”的精神劳动之前,政局变化、士人心态、山水审美情趣,只是资料性地各自单独存在,如不挖掘,孙绰的上疏所表现的虽是一种士人心态,和山水审美情趣也毫无牵涉。它们确是历史原貌,也许被人从不同角度注意到,但彼此毫无关联。在“思辨索原”之后,资料由思想贯穿起来,有了逻辑联系,展现了一种更深入、更真实的历史原貌,使人对山水文学的兴趣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探究“士人心态”,让静止的史料活起来,观照士人内心世界的“原装”或“原貌”,做的实际上是一种“思辨式索原”的工作。罗著中,像这种从士人心态着手深入剖析的例子很多。从本书各个章节的次序排列上,就可见出这一点。如第一章为“建安文学思想”,第一节即为“士人心态的巨大变化”;第二章为“正始玄风与正始之音”,第一节即为“正始玄风与士人心态的变化”;第三章为“西晋士风与西晋文学思想”,第一节即为“西晋士风的变化”;第四章为“东晋文学思想”,第一节即为“偏安心态与江南山水所带来的审美趣味的变化”……士人心态在文学研究中的位置可见一斑。如上所述,论及社会文化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时,作者曾说“直接的关系是士人心态”,“士人心态是中间环节”,书中明显从始至终贯彻了这一思想,从而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以上对本世纪的中古文学研究做了一简单巡礼,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从刘师培、鲁迅、王瑶到罗宗强诸位先生,其间先后承接、递进的精神痕迹十分明显。这其间除了体现踵事增华、光景常新的普遍发展规律外,从史料的还原到思辨的索原是其另一鲜明特征。自刘师培始,中古文学筚路蓝缕之初,就注重“历史的还原”,即尊重资料的客观性,以资料为主,我为客,故其研究形式为胪列加案语;至鲁迅,注意从社会背景和生活习俗研究文学现象,给后人留下极大思维空间和开垦余地;王瑶上承鲁迅,开疆拓土,进行广义的文学研究,虽未明言,已初露“思辨性索原”迹象;至罗宗强先生,除继承了诸位先贤“历史还原”的治学态度外,又明确提出了“理论索原”的概念,并付诸实施,将士人心态视为分析文学现象的关键环节,斩获颇多。从史料的还原到思辨的索原,可以看到这一领域研究方法、学术思想的进步,任何古典文化研究领域,都要注重“历史的还原”,否则即成空疏文学;但所谓“历史的还原”有两层含意:一是史料的还原,二是思辨的索原。一“还”一“索”,层次分明。没有前者,研究缺乏根基;没有后者,学术难以创新、突破。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我们看到了这两种“历史的还原”。笔者窃以为,这其中所反映的规律不仅适用于中古文学,对其他古典文化研究亦有借鉴意义。
标签:文学论文; 刘师培论文; 鲁迅论文; 王瑶论文; 魏晋风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艺术论文; 魏晋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