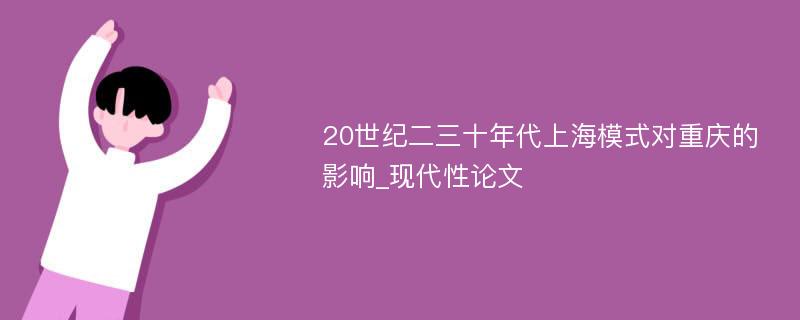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庆论文,上海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二三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K263;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0)03—0110—06
美国学者说,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在上海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注:(美)罗兹·墨非:《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对于这个问题,张仲礼指出, 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广州对外开放以后,城市的现代化都不同程度地获得启动,但程度并不一样,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五口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形成了五口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上海一支独秀的局面(注:张仲礼编著:《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的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忻平也认为抗战前十年的上海城市现代化“表现得最为典型,尽管并不成熟,但毕竟开创了第一个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本模式,提供了一个可供解构的典型”(注: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2页。)。于是,20世纪30 年代中国现代派作家笔下的上海被制作成中国现代都市的惟一文本与感觉(注:参见张英进著,冯洁音译:《都市的线条: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笔下的上海》,《现代文学评论》1997年4期。)在近代中国城市中, 上海有着“现代化运动”火车头之称,各城市要搞“现代化”,或以上海为模式,或派人至上海学习观摩,或到上海采办机器、聘用人员(注:参见梁元生:《近代城市中的文化张力与“视野交融”——清末上海“双视野人”的分析》,《史林》1997年第1期,第75页。)。所谓“上海模式”, 主要指衡量上海城市现代化发展程度的若干城市物化环境的现代性指标。在这里“上海模式”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内涵揉合了这一时期的广州、上海、汉口等城市的市政建设经验与举措;因习惯上以上海为中国现代化的“火车头”,因此笔者用“上海模式”作为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最高成就的代表者。本文试图以“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为解剖点,从另一视角探究民国重庆城市现代化外部动力机制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探讨内陆开埠口岸特殊的城市发展轨迹。
一
柯文在研究王韬时说,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未曾研究的巨大课题是沿海与内地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深刻地影响了沿海与内陆城市的发展模式与速度(注:(美)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近代以来,西方人首先在中国的沿海建立据点,以后扩展到长江沿岸。在这些据点及周围地区,逐渐发展出一种文化:它在经济基础上是商业超过农业,在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是现代性多于传统性;其思想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它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更是外向而非内向。这即是近代中国“条约口岸体系”。通商口岸是受西方强权和文化直接影响的焦点,也是中国最具现代性特征的城市群,上海在条约体系中城市现代化程度最高。民国时期,“上海模式”集中具备了同时代中国现代城市的所有物化环境指标,如高楼大厦、电影院、咖啡屋、西餐馆、崭新的轿车和新式的路灯,以及城市的新兴公用事业如照明、自来水、电话等,成为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象征;同时,“由于拥有巨大的经济和文化辐射力,上海已经成为一个远远超出其城市地域的影响源泉”(注:Joseph
W. Esherick,"Introduction", inConstructing the Modern in Chinese
Cities
1900- 1950,forthcoming,p.19.),在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历程中,“上海模式”的辐射和影响力具有绝对的文化霸权。
就条约体系城市群看,尽管比上海开埠晚了近半个世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庆市还是具备了若干“现代性”的特征。到抗战爆发时,重庆已是“柏油马路,四五层的立体式大厦,影院、剧场、咖啡室,西餐社,油璧辉煌的汽车,和闪烁光芒的霓虹灯,凡都市所有者,无不应有尽有”(注:吴济生:《新都见闻录》,上海光明书局1940年版,第15页。)。纵观这一时期的重庆城市景观,随处可见“上海模式”的踪影,“颇有沪汉之风”(注: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64页。)、 “洋场十里俨然小上海也”(注:邢长铭:《巴县及重庆实习调查日记》,肖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39辑,台湾影印出版。), 是描述重庆的典型话语。概括来讲,“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重庆城市市政体制和建设模式的冲击,导致重庆对外部现代性冲击的回应机制的初步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20年代末期重庆的城市即是“上海模式”冲击的结果。1927年9月, 重庆商埠督办呈请川康边务督办公署将商埠督办改为重庆市,其理由便是“上海、南京、广州、杭州等商埠地方,均经先后改市,成绩昭然”(注:《重庆商埠月刊》,1927年8月,第9期。),以求与沿海城市的市政模式“划一”而设市;重庆市政组织结构也主要参考南京、上海和杭州的城市组织规则,制定出《重庆特别市暂行条例》。如果说,重庆的建市是重庆城市现代化的开端的话,那么,重庆建制本身已体现了若干“上海模式”的影响。
“上海模式”的强烈示范效应,使其渗透内陆,介入、打破重庆城市传统社会的自然演化的逻辑发展进程。30年代重庆城市建设的模式取向主要以“上海模式”为主要参照系,逐步形成市政建设的“小上海”风格,开埠以来重庆在城市体制上对外来现代性冲击的“回应机制”也初步形成。从1926年开始,重庆处于刘湘21军“近乎完全自治的”(注:Robert A.Kapp:Szechwan and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14.)“军人干政”管理模式之下。 但截至20年代中期,这个“华洋杂处”、“商务繁盛”的开埠口岸仍然是“市政窳败,街道之狭隘,沟渠之污秽,煤烟之蒸蔽,其不堪居住”不仅是“全世界通商各埠所无”,且市区“地狭人稠,肩摩踵接”。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潮流,刘湘政府采取了模仿“上海模式”的市政建设取向。市政当局开始认识到“非推行市政,为谋改造,实不足以策交通实业之发展”(注:唐式遵:《重庆市政计划大纲》,《重庆商埠汇刊》1926年。)。商埠督办曾多次派人到长江中下游各大都市和其他省市考察市政,以“求攻错于他山”(注:《重庆商埠月刊》,1927 年3月,第3期。)。 重庆市市长潘文华更以符合“世界潮流”的建设指导方针晓谕市民道:“文华当督饬提挈并进兼营分途发展俾重庆市精神形式焕然一新,得与欧美各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上臻国际之光荣,下为各县之模范。”(注:潘文华:《告全市人民书》,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财政局全宗,卷920,第69页。)此外,在督促市政建设方面, 注重选拔有“曾游学欧美”(注:《请委郑璧臣技术员一案》,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财政局全宗,卷920。)背景的专业工程人员。1932 年刘湘采纳留美归来的胡光麃提出的充实重庆发电容量的建议,改换全市的输电设备,大大推进了重庆城市现代公用事业的起步(注:胡光麃:《波逐六十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2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第295—296页。)。刘湘时期重庆市政建设的诸多举措既是军人政府对“上海模式”的认同,也是军人政府直接介入重庆城市现代化过程的表现。同时,重庆城市当局顺应时代潮流,加强城市建设,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整个社会对“上海模式”的广泛认同。重庆在城市行政建制和市政建设上逐步建立起对外部现代性冲击的回应机制。1929年以后的重庆市政改革被西方世界称为现代意义发展的开端,
是“按照现代结构”的城市建设计划(注:CentralIntelligence Agency,edit,Briefs on Selected PRC Cities,Chungking,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GovernmentPrinting Office.November,1975,p.3.另参见J.E.Spencer: ChangingChungking,The Rebuild Of An Old Chinese City, in
TheGeographical Review,29 (1939),pp.47-50.),有的传教士甚至称重庆“正在沿着时代的步伐前进”(注:Chungking News,in The WestChina Missionary News,January 1929,p.27.),“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新城市了”(注:Chungking Jottings,in The West ChinaMissionary News,June 1931,p.40.)。
(二)对重庆城市社会层面的广泛冲击,并逐步形成追随“上海模式”——上海摩登的城市商业文化。上海自开埠以后,大量西方文化和中国南北文化随着中国和外国的移民的涌入,上海成为中外文化的碰撞点、融汇点,同样也是中国南北文化、内地文化和沿海文化的汇合点。多种文化类型之间的互相渗透、借鉴、移植、认同十分活跃,形成了上海城市兼容并蓄、吐故纳新的文化特色。这种文化的交汇使上海文化具备了典型的“边缘文化”的特征,且在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使得上海始终以快速的更新领先于其他地区,进而担当了近代中国文化中心的角色。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摩登”是重庆自开埠以来所受到的最为强烈的现代意识的冲击。从文化层面上看,“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不仅是官方,而且在民间也有深入的影响,导致30年代重庆城市商业文化的初步形成。对“上海模式”的向往、认同与仿效,显示了重庆人现代意识的觉醒,这无疑是对民国以来的“川人治川”的军阀政治理念的冲击。“上海模式”是二三十年代重庆城市现代化的最直接参照系统,市民对上海摩登的模仿心态的形成,在相当宽泛的社会层面上表明重庆城市对它的认同。“上海模式”强大的示范效应最明显地表现在物质消费上,“模仿”上海摩登是30年代重庆追求城市现代化的时尚和实际之举,并逐渐形成民国时期重庆人超经济的追逐“现代”的取向:“新式女子,裸膝露肘”(注:《训令重庆市市长潘文化警备司令李根固为禁止奇装异服以敦风俗一案》,陆军第二十一军司令部政务处编《施政续编》,1935年2月印行,第35页。),“一般摩登妇女, 咸皆奇装异服,时髦趋新”(注:《商务日报》1935年5月27日。)。 30年代上海媒体“摩登”一词开始风靡,很快重庆媒体就紧随其后,重庆主要传媒的商业广告,“风行申杭”(注:《商务日报》1934年4月1日。)等话语几乎是“现代”、“摩登”的代名词。这一时期上海男性时髦装束是“头戴铜盆帽(礼帽),手拿司的克(手杖),眼戴金丝眼镜,蓄西式小胡子,口叼雪茄,挟一皮包,西装革履”(注:前引忻平书,第365页。); 而同时期的重庆《商务日报》漫画中的时髦男女形象也已十分接近。重庆的中产阶层,如编辑、律师等城市白领群体更是对上海摩登亦步亦趋,休闲消费的去向往往是咖啡馆、西餐馆等处,“着花毛呢单衫,鼻驾克罗米眼镜”(注:刘残音编《重庆通信箱汇刊》第1 集,重庆《商务日报》编辑出版,1937年11月,第79页。),成为这一阶层的服饰象征;他们追逐上海摩登的行为既影响着整个市民社会,也展示了重庆人对现代模式认识的心路轨迹。
(三)对重庆的冲击力远远大于条约体系中的“西方冲击”。当沿海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已经表现出相当的现代性,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的“中心”时,深处内陆的重庆,现代化启动极缓,成为保留太多传统性的远离“中心”的“边缘”。在这个沿海——内陆城市现代性的“二元结构”中,“中心”与“边缘”的差异不仅异常显著,而且“中心”对“边缘”辐射力远远大于“西方的冲击”。沿海条约体系与内陆开埠口岸现代化的巨大差异在于现代性要素冲击源的差异。尽管同属条约口岸体系,“上海模式”对重庆的拉力远远大于西方冲击,显示出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二元结构”模式自身的超强稳定性结构取向,和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浪潮由“沿海”而“内陆”层次递进的特殊性。换句话说,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在区域上的不平衡,而且也表现在同一体系内部的不平衡,由此造成了“上海模式”成为低度发展城市的重要参照系。就外力对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作用看,一方面内陆城市所受外来现代性要素的冲击力有逐步弱化的迹象;另一方面沿海开埠口岸的示范作用有取代西方冲击的态势,加之拥有中华同源文化的凝聚“拉力”,其对内陆城市的冲击效应远远大于“西方文明”的直接渗透。
二
20世纪30年代上海模式为重庆所广泛认同、吸纳的条件是成熟的。长江使这个远离大海的条约城市与沿海口岸始终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尤其是川江航运业的繁荣始终使重庆与“下江”保持了开放的态势。早在民初,川江轮船航运的开辟使“重庆已不再像从前间只有依赖民船作为唯一的交通工具才能达到的遥远城市”(注:《重庆海关1912—1921年十年报告》,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页。)。20年代后期, 长江中下游的各中外轮船公司时常有轮船行驶重庆,既加强了重庆与长江中下游的各大都市的交往,也带来了“下江”地区若干“现代性”因素。川江轮船航运业的繁荣与发达也为“上海模式”穿透相对封闭的环境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尤其是卢作孚致力于川江航运事业,致力于沟通川内外,为“上海模式”西上巴渝架起了桥梁。1932年6月, 民生公司开辟了重庆—上海航线,这是长江上最长的直达航线,重庆与“下江”的联系更为密切和直接。加之30年代中期川局较为安定的局势,川江上“来往旅客日见增多,以前仅川人来往,外省者不及十分之一,今则各半”(注:庄泽宣:《陇蜀之游》,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9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138—139页。)。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初期,在“水陆交通俱繁”(注:胡焕庸编著:《四川地理》,正中书局,1938年版,第130页。)的情况下, 航空运输业又在重庆出现,成为城市交通运输史上的里程碑。“交通革命打破许多观念,飞机之促进文化与政治,殊有不可思议之威灵”(注:季鸾:《入蜀记》,《国闻周报》第12卷第19期,1935年5月20日。 )。一旦现代化和缺少现代化的地区之间人们彼此交往,“不论是否施加外力,现代化的模式都会被非现代化社会吸收”(注:(美)M·J·列维著,吴荫译:《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下江人”(注:“下江人”是抗战时期获得广泛认同的具有明显文化特征的社会群体,不过这一特殊的群体却形成于20年代中期(笔者另文专述)。在近代重庆城市发展历史上,“下江人”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下江人”以“上海模式”审视2、30年代的重庆城市景观的话语, 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重庆城市发展变迁实况。)也发出“蜀道何难”(注:庄泽宣:《陇蜀之游》,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9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166页。)的感叹。伴随“下江人”、 外省人的入川,来自沿海的城市文明对重庆人的思想观念、意识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初以来的“川人治川”——军阀封闭自为的政治理念受到严峻的挑战。在文化层面上启迪了川人的觉悟和地方精英的现代化意识,为重庆城市的现代化积淀了一定的素养。交通建设的进步,放大了重庆在川江水系中的区位优势,同时30年代中期以后,重庆与四川省内各地的公路和航空线建设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重庆逐渐成为四川的水、陆、空转运中心,当然具备了将“上海模式”呈东转西的“亚辐射”功能。
“上海模式”对重庆的最大冲击在于对重庆人意识、市民心态变迁的整合作用。从社会底层激起对外部现代性因素的向往与认同,是“上海模式”得以在重庆发展出内陆特色的城市发展模式的最为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一方面重庆社会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转型时期,“传统性”仍然占据相当优势。另一方面以卢作孚为代表的重庆“现代化的最早呼唤者”(注:孙力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第215页。)逐步成长,且显示出难得的现代意识觉醒。作为在重庆颇具影响力的地方精英和民族资本的代表,他的“中国当前的途径非常明了,不管是社会组织亦或是物质建设,只有迈步前进,追逐现代或更超现代,不然便会受现代的淘汰”(注:《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324页。),和“到底如何才可以促起人们的觉悟?唯一的方法,便是拨开现局,使人们伸伸头来,看看现局以外,还有一重天地,不误以为现局便是天地。如果人们长埋在现局中间,纵然觉悟了现局之坏,然而不知道如何才好,永远不会从现局中间自拔出来,跳到另外一重天地里去。因为他们从没有见过另外一重天地”(注:《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68页。)等话语为“上海模式”的输入奠定了相当思想基础;而卢作孚致力于沟通封闭的四川与外界商业行为——川江航运事业,又为重庆接纳“上海模式”提供了现实的途径。
应当看到,对“上海模式”的向往与追求,表明重庆正处于不得不靠引进外部现代要素的时期。外部现代性的示范效应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将提前实现的条件。但这种人为地将一种异质性因素——“上海模式”引入既有的社会结构之中,打破了本社会固有的发展逻辑;同时由于被引进的“上海模式”运作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其结果也就发生了明显的差异。还应该看到重庆巨大经济价值,使刘湘对治理重庆城市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卷入了地方经济建设。通过吸收和接纳城市地方精英参政,刘湘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归国人才的建议,利用“上海模式”作为重庆城市建设的直接参照模式,这在相当意义上既谈化了“军人干政”色彩,又增添其政权合法性资源,但这又不能不给重庆在消化“上海模式”上带来负面的影响。实际上,这一时期“上海模式”主要表现为物质范畴——即器物层面的内涵,以潘文华任市长期间颇具“现代”色彩的市政建设看,重庆城市现代化举措基本上停留在仿效“上海模式”物质层面上。潘文华在重庆商埠成立之初便指出,“欲唤起人民之注意,先有一种事实之表现,其他精神建设不易见功,不如从物质方面亟急开动,较易新人耳目”(注:《九年来之重庆市政》第1编总纲,重庆1936年版。)。 不能从根本上做到对“上海模式”的理解与吸收,从而化为自身的有效发展资源,其结果便是一方面急于超越上海与重庆之间的差距,因为“如果他们不拼命去缩小差距,不在一个超常规模上进行建设,他们就要继续受到歧视,继续被视为等外品”(注:(美)M·J·列维著,吴荫译:《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另一方面则是将“上海模式”置于一个很陌生的规模上进行建设,致使以“上海模式”为主要参照模式的重庆城市现代化带有明显的人为刻划的痕迹。难怪“下江人”参观重庆市区中央公园内的“涨秋”西餐室时,见室内布置几乎与上海的大餐馆一样富丽堂皇时,尖锐地批评道:“四川人各事善模仿外间,都市繁荣,虚有其表。”(注:陈友琴:《川游漫记》,南京正中书局1934年版,第34页。)这就是有学者指出的现代化“畸变”现象(注:孙立平:《后生外发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第217页。)。
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外部效应与内部要素的相互渗透叠加,共同制约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走向,也使得中国现代化呈现出复杂多元、交错共生的格局。一方面,我们看到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首批条约口岸,其发展模式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城市的发展轨迹,是启开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历史的钥匙;另一方面,丰富多彩的中国城市社会变迁又实实在在地走出了不同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界“超越上海”(注:参见Lee McIs AAc,Beyond Shanghai:Chinese Cities Viewed From San Diego,in the Wall and Market—Chinese Urban History News,volumel,Number2,Fall 1996.)的城市研究模式呼声,为人们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多元模式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就重庆而言,一方面,对“上海模式”的追逐与模仿为重庆城市现代化提供了可供利用的沿海城市现代化发展模式资源;另一方面,“上海模式”也使得内陆城市自身的发展模式得以启动:这是一种主要参照“上海模式”,而不是主要参照“西方模式”的变异现代化模式——“重庆模式”。因此,二三十年代“上海模式”对重庆城市现代化的启动至关重要,是近代重庆城市社会走出前现代的边缘,引进现代化要素的积累的开始,基本定下了民国时期重庆城市发展的“容纳与渴望新知要素”的内在趋向。这也是继1891年重庆开埠以后重庆受到的又一次外来的现代性因素的冲击。在“上海模式”的刺激下,在本社会还缺少现代性因素的积累的情况下,20世纪20年代末期重庆借助外部的现代性因素——上海模式,初步实现了城市现代化的强行启动。
【收稿日期】1999—5—25
标签:现代性论文; 重庆发展论文; 重庆文化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上海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刘湘论文; 现代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