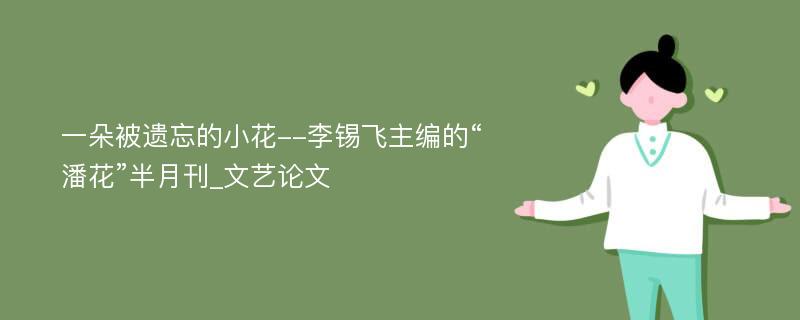
一朵被遗忘的小花——黎昔非主编的《昙华》文艺半月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半月刊论文,一朵论文,小花论文,被遗忘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边城”北平萧瑟的文苑中曾经绽放一朵美丽的小花——《昙华》文艺 半月刊。然而对于这份文艺刊物,不仅一般读者不了解,就连许多专业的中国现代文艺 刊物目录也没有提及。今年是她创刊70周年,故特向世人介绍这朵被遗忘了的小花。
《昙华》文艺半月刊创办于1933年,1月1日出版了创刊号第一卷第一期,此后则每逢1 日、16日出版一期,至同年4月1日出版第七期之后停刊,一共出版了七期。那么,这份 刊物是怎样创办起来的,为什么如此来去匆匆,有如昙花一现呢?其主要内容如何?欲知 其中的缘由,还得从《昙华》文艺社及其主编黎昔非谈起。
《昙华》文艺半月刊的主编黎昔非,1902年5月31日诞生于广东省兴宁市罗岗镇甘村, 1930年7月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中国文学系。时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 院长,故黎昔非与胡适有了师生关系。1930年8月黎昔非从上海赴北平,1931年春考取 了北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指导教授为黄节,研究课题为《诗经学史》。恰巧1930年11 月胡适也从上海迁平,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于是黎昔非与胡适再度有了师生关系 。1932年3月胡适邀请黎昔非帮助他办理《独立评论》,担任经理人。黎昔非从上海来 到北平的目的,据他在《自传》中说是“想在学术上搞出点成绩”来的,因而对于是否 出任《独立评论》经理人的工作曾经是相当犹豫的。由于胡适的一再邀请,于是他不得 不中止了在北京大学研究院的学业,从1932年4月开始了他在《独立评论》社长达五年 有余的经理人生涯。
然而文学创作也曾经是黎昔非的人生奋斗目标之一。他对于文学创作的追求,是在192 9年春从上海持志大学文史系转学中国公学之后的事情,他在《自传》中对此追述道: “直到转入中公,才开始注意到新文艺,喜看翻译小说,尤其是鲁迅的翻译。对做学问 的看法,也有了转变:觉得从事创作也是条路,不一定要专搞古代的东西。不过认识不 足,以为创作是轻而易举的,要保证将来有饭吃,就要有实学,即是对古代的东西要有 点研究才可。”在中国公学时对于他立志从事文艺创作影响最大的是担任他们创作课程 的沈从文,黎昔非就这一问题曾经这样回忆:“我所以想从事创作,一固然是由于自己 喜欢它,一也是受沈从文的鼓励:因我来自农村,深知农民大众的痛苦,每所暴露的都 是当时社会的黑暗面。他认为这比那些坐在上海亭子间里的‘普罗作家’所写的还较真 切,故极力怂恿我走创作这路。”怀着这种“想新旧兼为”的抱负,黎昔非在中国公学 毕业后即转赴北平。当时,“从事创作好呢?还是搞古代的东西的两种思想,便在我的 思想深处时在斗争着,结果竟想二者得兼,即以研究古代东西为主,暇则从事于创作。 主意既定,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毅然只身到北京去,满以为专搞一二年,总能搞出一点 东西来,便不难跻身于教授、学者之列了。”“我离沪前晚,沈从文曾写了几封介绍信 ,抵平后曾按址去访一位清华教授林宰平,一个作家黎锦明,因那作家给我有一句没一 句的态度,便把其余的函压在箱角里,不愿让它们再见世面了!我于是整天沉醉在北平 图书馆的经史籍中,把‘创作’这事搁在一边了。”正当他一心一意从事学术研究时, 胡适邀请他主持《独立评论》一事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本来,我打算只干他半年至 一年,藉以维持生活,以期完成自己的论文便罢了。没想到那种工作这么烦忙,有时忙 到连报纸都要到夜深才得闲来看,也没想到一再推辞,直到北京沦陷前夕都还没和它完 全绝了关系……再三推却,都以不易找到相当接替的人而被留住了!”直到1937年“七 七”事变之后,在坚持出版了《独立评论》242号(7月11日)、243号(7月18日)、244号( 7月25日)之后,于7月27日离开北平南回故里。
黎昔非在办理《独立评论》期间,1932年秋,他的中国公学同学、同乡、朋友丁白清 携女友陈菲村(也是中国公学中国文学系学生)到北平来找他。不久,另一位中国公学中 国文学系同学潘齐平(广东惠阳人)也来到北平。加上当时在北平大学法学院读书的、黎 昔非的同乡刘在海,一共五人,他们一起成立了《昙华》文艺社,并决定创办《昙华》 文艺半月刊。黎昔非在追忆此事时写道:“同时‘作家’这二字也时在脑海里晃荡着” ,“追求‘名’的思想仍是很剧烈的,于1933年春曾和丁白清、陈亚菲、潘齐平、刘在 海四人,共同出钱出力,办一‘昙华’文艺半月刊,竟想由此而成为一个作家。”1931 年5月至1937年7月先后就读于北平东城大同中学、辅仁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的 黎昔非的同乡、朋友林钧南曾目睹他们五人创办《昙华》半月刊的情况,在《清白一世奉献毕生——忆故友黎昔非同志》一文中对此回忆道:“1932年9月,同乡、同学丁
白清突然与同学陈菲村小姐一起从上海来看昔非,并说中公同学潘齐平过几天也要来北 平。当时就读于北平大学的同乡刘在海也前来参加。他们商议决定组织一个文艺社,出 版一个文艺刊物,以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为主。目前人数虽少,可以逐步吸 收热衷文艺的青年参加。大家委托昔非去请求胡适题签,并推举昔非担任主编,出版费 用大家来分担。由于筹备出版琐碎费时,至翌年1月1日才出版了创刊号。其后就按时每 月出版两期。”《昙华》同人丁白清1958年给组织写的一份材料中对此追述道:黎昔非 “是我大学里的一个要好同学,过从是很密的,他对中国文学,是造诣很深的;尤其是 对《诗经》这一门,特别有研究……我们在1933年春,在北平举办昙华社,出版《昙华 》文艺半月刊,是事出很偶然的,原因也简单:我们昙华文艺社社员,根本不多也不少 ,就只有五个:昔非、潘齐平、刘在海、陈菲村和我。五人中,除刘在海外,我们都是 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的同学:我和昔非同班,齐平比我们低一班,菲村比我们低两 班。而且,五人中,除刘在海读法律系外(北平大学法学系毕业),我们都是读文学的, 甚至都是中国文学系。谁都知道,在旧中国时代,办刊物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就是销路 问题,无名小卒,是不吃香的,何况又要自己掏腰包来办呢!可是,又为什么要搞它呢? 因为我们都是读文学的,又是青年,求知欲,创作欲,都很强;同时,又在万里的他乡 遇故知,心情特别舒畅,于是,我们的‘昙华’就出现了。”
《昙华》的创办,还与胡适和《独立评论》多少有一些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通过黎 昔非而得以实现的。首先,《昙华》文艺社的社址就是利用后门慈慧殿北月牙胡同2号 《独立评论》社址和它的办公室,这对于经费并不宽裕的《昙华》同人来说是一个帮助 。其次,胡适为刊物题签,对于提高这份刊物的身份也有一定意义。第三,《独立评论 》与《昙华》互登对方的广告,对于宣传推广《昙华》也有一定的作用。《独立评论》 第34号、36号、41号、46号,曾分别刊登了《昙华》第1、2、3、4、7期出版的广告。 与此同时,《昙华》第1、2、3期,也曾分别刊登了《独立评论》第32号、第35号、第3 6号出版的广告。
与胡适、《独立评论》的这种关系对于《昙华》所起的作用,在林钧南1998年10月14 日给笔者来信中透露了个中一些内情,他说:“据我所知,这是丁白清、陈菲村到北平 旅行结婚时,住在‘独评’社附近,其后又来了潘齐平,然后他们提议创办的。你爸爸 工作忙,并不热心,迫于同学关系,只好答应。所以他请胡先生题书名,发行人也是他 ,社址也是‘独评’的地址,还在‘独评’登广告,因而外界不了解内情者都以为是胡 先生参与创办的。故第一期很快就销售一空。还有汇款来订购的。”“因是胡适题字, 加上地址又与独立评论社址相同,故外人也说《昙华》是胡适主办的,办了三期(应是 七期)都畅销,订户也多。”
黎昔非是这份刊物的核心人物。不仅上述《昙华》与胡适及《独立评论》的这种特殊 关系都是因黎昔非才有可能发生的,更重要的是这份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也是黎昔 非在具体负责和操持的,正如黎昔非在《自传》中所说:“编辑、写稿、校对、发行全 由我一人负责。”据黎昔非的友人回忆,《昙华》的每一期都有他的作品。但是他的作 品都是以笔名发表的,有的甚至没有署名。现在能够确认是他的作品的,只有四篇:它 们是《昙华》创刊号上的《发刊词》,第一期署名艮心的小说《南旋》,第三期署名胡 谭的小说《友谊》,第四期署名甘村的小说《活财产》。此外,第三期署名罗岗的小说 《爱与仇》也有一半的可能是他的作品,因为《昙华》同人中只有他和刘在海是兴宁县 罗岗镇人。
《昙华》五位同人中1991年尚在世的陈菲村先生于同年4月4日给笔者寄来一帧《昙华 》同人1932年在北平的合影,她在信中说:“最近我翻阅旧照相簿,发现了1932年在北 平出版昙花文艺杂志时,与您爸及刘在海,潘齐平和白清照的相。我们五个同人,他们 四位,先先后后离开了人间,最先是刘在海,以后是您爸,再后是白清,最后是齐平。 只我一人还在人间。看了照片总不免满怀惆怅!这张照片,是齐平在生前向我索去复印 了几张,又寄回给我两张。不知您爸留给您没有?现我给您寄一张。您看,您爸坐在椅 上多英俊呵!……虎侄!我们编的昙华文艺杂志,您爸留下没有?我在土改时,放在石马 家中,给没收了!十分可惜,齐平生前也没有呢!”
关于《昙华》的停刊,《昙华》同人及林钧南先生都有一些相关的回忆。黎昔非在《 自传》中写道:“在这数年中,我总是想写点较专门的东西,对于时事,则不能说所要 说的话,又不愿‘歌颂功德’,故没写过一句,——出了数期,因人员星散,经济困难 而告停刊,不然,我们可能被压出些东西来,虽然能值一读与否是不敢必的。”又说: “不久人员星散,款项无着,且编辑、写稿、校对、发行全由我一人负责,也有点应付 维艰而宣告夭折。”这里列举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人员星散,二是经济困难,三是主编 黎昔非的负担太重,应付维艰。
《昙华》同人星散的原因,大的背景是当时的形势使然,林钧南先生回忆道:《昙华 》于1933年4月突然停刊“这是由于日寇侵占我热河省之后,又进攻长城各口,与我守 军商震部、宋哲元部激战,原驻北平的中央军黄杰师和关麟征师也参加抵御敌军,因而 北平形势非常紧张,人心惶惶,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南下。”但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 《昙华》同人的星散也还有不同的具体原因和情况。对此,丁白清的回忆最为详细,他 说:“昙华文艺半月刊,我记得只出刊了7期。在1933年,4月1日出刊了7期后,就停刊 了。原因是:最先,齐平转学厦门大学,取录了,他到厦门去:跟着母校复办了,迁上 海汶林路,她(指陈菲村)又回去就读;最后,时局紧张,热河沦陷,喜峰口、古北口告 急,北平时出现日机,时闻高射炮声,人心惶惶,同时我家催我速即南下,我即于5月 中旬离开北平。这样,在北平,同人只剩下昔非和在海,人力、财力都成问题,‘昙华 ’便真成‘一现’了。”五个同人中有两人(潘齐平、陈菲村)是因上学而离开北平,一 人(丁白清)因北平形势紧张而南下,留在北平的二人中,有一人为在读学生(法商学院 学生刘在海)。在这种情况下,只靠黎昔非一人势难以为继,因而不得不宣告停刊。
《昙华》从1933年1月1日创刊,至同年4月1日第7期停刊为止,一共出刊7期,但是现 在我们能够找到的只有6期,其中第6期未能找到。刊物为16开本,每期16页。未设单独 的封面,第1页右侧的长条黑框内,上部为竖写的刊头“曇崋”二字,字的左
下方,钤有一枚篆字阴文方形图章:“胡适之印。”下面分别为出版时间、刊期、定价 (每期三分)、通讯地址(北平 北平大学法学院第二院号房转)及“本期目次”等。左侧 即为第一篇文章的内容。
《昙华》半月刊各期的作品篇目如下:
第一期 发刊辞 菲村《某日》
小平《祖母的怨望》 鹤子《战区之一角》
零零《快乐的结局》 艮心《南旋》
刘枕涛《灯下谈丛》
第二期 菲村《迟了》 零零《宴会》
潘小平《先生的儿子》 申伯《一个女理想家的懊悔》
第三期 罗岗《爱与仇》 胡谭《友谊》
夏蒂《孩子们》 朱无挂《猎名作家与成名作家》
刘枕涛《灯下谈丛》
第四期 夏蒂《电报》 潘小平《偷走》
辰仲《还愿》 甘村《活财产》
刘枕涛《灯下谈丛(续)》
第五期 朱无挂译《歌德与音乐》 徐平《云姑》
潘小平《先生,写信吧》 刘枕涛《国难声中之科学贡献》
申伯《现代青年》 亦明《温情与热爱》(诗)
丁未《时光老人》(诗) 未生《光明的太阳》(诗)
方桥《归车》(诗) 小姑娘《会客》
第七期 飞灵《廿四夜》 零零《克复以后》
亦明《脚病》 夏蒂《期待》
未生《无聊?惆怅!》(诗) 徐平《考试日记》
现存的六期《昙华》,共发表作品36篇,其中小说25篇,评论5篇,诗歌5首,译文1篇 。显然,小说是《昙华》的主要内容。
《昙华》对于“美”和“真”的追求,集中体现在她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中国最主要 的社会现实就是农村、农民以及与他们相关的问题。由于《昙华》同人多来自农村,比 较熟悉和了解农村,因而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题材在《昙华》的作品中最为引人注目。属 于这方面的小说有《某日》、《祖母的怨望》、《南旋》、《迟了》、《先生的儿子》 、《偷走》、《还愿》、《活财产》、《云姑》、《廿四夜》等。
《昙华》中乡土文学的突出,一方面由于《昙华》文艺社的成员都是来自农村,有着 这方面的生活体验。另一方面也与主编黎昔非的文学思想有密切关系,他在谈到从事文 学创作的原因时曾说:“一固然是由于自己喜欢它,一也是受沈从文的鼓励:因我来自 农村,深知农民大众的痛苦,每所暴露的都是当时社会的黑暗面。他认为这比那些坐在 上海亭子间里的‘普罗作家’所写的还较真切,故极力怂恿我走创作之路。”
20世纪30年代初期正处于日本侵略中国日益剧烈的时期,反日救国已经成为每一个爱 国者的心声。“昙华”文艺社产生和消失的本身就是与中国当时面临的民族危机紧密相 连的。因而《昙华》对于现实的关注也突出表现在她所发表的以反抗日本侵略为题材的 作品中。《战区之一角》、《宴会》、《友谊》、《孩子们》、《电报》、《克复以后 》等都是属于这类题材的小说。
《昙华》文艺社的成员,都是当时热爱文学的青年。比起其它生活领域,他们更熟悉 青年的生活与心理。因此,关于青年问题题材的作品,也是《昙华》的重心之一。《昙 华》所发表的小说中,涉及青年生活及其问题的有《快乐的结局》、《先生的儿子》、 《一个女理想家的懊悔》、《爱与仇》、《现代青年》、《会客》、《脚病》、《期待 》、《考试日记》等。透过这些作品所反映的各个生活层面,触摸了当时青年生活的脉 搏。
此外,从第五期开始,《昙华》出现诗歌栏目,有《温情与热爱》、《时光老人》、 《光明的太阳》、《无聊?惆怅》、《归车》等诗篇。这些都是抒情诗,青年人常有的 对爱情、时间、人生感慨是这些诗歌的主题。
《昙华》虽然只是一现,没有能够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显著的痕迹。但是,她为我们 留下了那个时代较为真实的声音。文学史固然离不开一些大家和名刊,但也同样不能忽 略如“昙华”一样美丽而“一现”的刊物和作者。尤其是主编黎昔非,在20世纪30年代 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中,为实现他的“作家梦”,繁荣文艺创作,尽他最大的努力与同 伴一起出版《昙华》半月刊,那种热爱文学为文学献身的精神对今天来说,也是一份弥 足珍贵的财富。《昙华》是一份不应被遗忘的文学史资料,恢复它在现代文学史视野中 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也是完全有必要的。(上述资料及引文,参见黎虎主编《黎昔非与< 独立评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